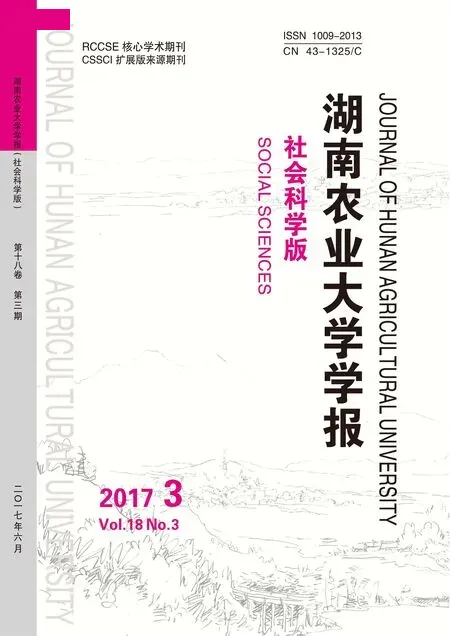农民拆迁意愿及其诱致性变迁路径——基于华北王村的个案考察
2017-02-24陈锋侯同佳
陈锋,侯同佳
农民拆迁意愿及其诱致性变迁路径——基于华北王村的个案考察
陈锋,侯同佳
(北京工业大学 a.人文社会科学学院;b.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124)
基于华北王村的调查表明:受经济和代际的影响,农民拆迁意愿存在一定差异;尽管总体而言农民拆迁意愿相对消极,但大多数农民最终都响应政府要求同意拆迁。农民拆迁意愿之所以会发生变迁,主要是受到村庄内外权力-关系网络的影响,政府、矿场等村庄外部力量通过政策鼓动、利益诱惑形成对农民与村庄精英的动员,村庄熟人社会和家庭等内部力量通过彼此间的连带关系、代际联动形成村庄内部的自我动员,最终促使多数农民同意拆迁。但在权力-关系网络中,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拆迁意愿并未获得满足,可能会带来诸多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农民拆迁;拆迁意愿;诱致性变迁;权力-关系网络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国家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各项惠农政策逐步实施,乡村逐步转型为“协商治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由原来的服从和执行关系逐渐变成了一种博弈关系。乡村这一转型有效阻止了权力的滥用和对农民权利的损害[1]。在各地“拆村并村”,建立新型社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征地、拆迁补偿,还是住房安置等政策的制订与落实,展现的是农民与国家的博弈过程[2-3]。
学界对乡村“协商治理”背景下农民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与行为进行了一定研究。有学者认为政府具有利益竞争者和竞争规则制定者的双重身份,为片面追求政绩而无视农民意愿,往往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4-6],导致农民利益受损而对政策不认可,进而产生失范行为[7]。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急功近利地追求农民“进城”、“上楼”的不良外部效应,如生活成本上升、基础设施跟不上[2]、农民精神生活消解[8]、代际关系变化导致的中老年经济社会地位边缘化[9]、福利两极分化[10]问题。有学者认为其中许多问题的产生与制度和法律不健全有关[11-13],并提出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种城镇化模式等策略来化解矛盾,推进新型城镇化[2,4]。
近年不少人将城镇化和推动“农民拆迁”、“农民上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过多地归结于政府失职和制度不完善,给人以“政府的权力过于强大且无止境”和“农民是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的印象[14]。实际上除政府外,还有许多社会因素对农民“拆迁”、“上楼”的意愿与行为有影响[15]。农民的拆迁其实是在权力-关系网络中进行的多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16]。乡村权力-关系网络是村民在长期互动过程中由村庄内部权力和关系互构形成的被村民普遍认可的“场域”。村庄内部与外部各种力量通过乡村权力-关系网络共同促成了农民的“拆迁”、“上楼”。
华北王村因煤矿开采导致地表下陷,当地政府以村下有煤矿需要继续开采为由启动村民拆迁。在拆迁实施过程中,全村540户的多数农民开始对拆迁普遍持消极态度,不愿意拆迁和“上楼”,但最后有516户签订了拆迁协议。农户拆迁意愿和行为之间何以如此相悖?它的诱致性变迁路径又有哪些?鉴于目前基于“权力-关系网络”视角对于拆迁中农民与政府博弈的案例研究阙如,笔者拟以华北王村为典型个案,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以“权力-关系网络”为视角,对农民有悖于自己初衷最后签订拆迁协议的行为及其诱致性变迁路径进行剖析。
二、农民拆迁意愿及其差异分析
王村有村民540户,2 160人,其中从事煤矿生产的工人350人,农民1 810人(家庭中有成员是教师的也统计在农民内)。基于38位不同年龄和职业的村民(包括村干部)的调查表明:农民拆迁意愿具有一定差异,即使是一户内部,不同年龄的成员意愿也有不同。现主要对基于经济和代际影响的农民拆迁意愿差异予以简要分析。
1.基于经济的拆迁意愿差异
农民拆迁的成功实施需要两个过程,即搬离与迁入,两者在政策上对应为赔偿标准和购房条件。当两者中任意一项未达到农民底线要求时,农民就会反对而难以实施拆迁。
王村村民职业差异带来的经济分化,与村民拆迁意愿有紧密联系。一般而言,职业层次与收入层次呈正相关,收入层次与农民意愿有密切联系[17]。王村村民多数是农民、矿场工人和在外打工者,少数村民是教师或退休教师,极个别村民是“大老板”。按照职业划分,王村村民收入从多到少依次为教师和工人、在外打工者、农民。教师和工人的月收入或退休金平均在3 500元左右,在外打工者平均每月1 500元,每户村民年平均收入50 000元。
据了解,王村这次拆迁基本赔偿按照以下标准实施:砖木结构房屋赔偿490元/m2,砖混结构房屋赔偿630元/m2,“楼”(农村的两三层“别墅”)按照700元/m2赔偿,临时棚屋按照160元/m2赔偿,装修费用按照房屋赔偿金的15%赔偿,宅基地按150元/m2赔偿。购房则是按照每人40 m2配给楼房居住面积,每户可以多申请10 m2(不包括车库和储藏室面积)。每户规定范围内的居住面积以1 050元/m2购买,超出居住面积按照1 450元/m2购买,车库800元/m2,储藏室500元/m2。因拆迁赔偿标准低,购房花费太高,多数村民表示无法接受,因为拆迁后需要补贴两年家庭收入才能实现换房;离开宽敞的大房大院,以高价换得几套小房子让他们感觉十分“憋屈”。此外,很多家庭考虑到儿子结婚需要更多房屋和更大的面积,其换购压力更加难以承受。村民普遍认为拆迁就应该越搬越富,可是这次搬迁并没有使他们得到好处,反而越搬越穷,这使村民十分不满。
由于经济状况不同,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不同,导致各户拆迁意愿强弱有别。一个家庭中教师、工人或打工者的数量,直接影响该家庭的收入状况,教师和工人越多,打工者越多,该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就更有可能同意拆迁。
案例1王大娘一家四口人,有0.13公顷地,丈夫和儿媳妇是工人,孙子是打工者,每年家庭收入约75 000元,处于中上阶层。王大娘家有200 m2的砖木结构房屋,三分四宅基地,可以得到146 700元的赔偿;在此次拆迁中,王大娘家最多能用平价购买170m2的房屋,他们选了一套120m2和一套80m2的房子,超额申请30m2的房屋,另外还申请了30m2的车库和20m2的储存室,应付款256 000元。除去赔偿金,还需补交109 300元,相当于一年半的家庭收入。
案例2唐大嫂一家三口人,有0.07公顷地,丈夫是工人,儿子是打工者,每年一家人有53 800元的收入,处于中等阶层。唐大嫂家有150m2的砖木结构房屋,三分宅基地,可以得到114 535元的赔偿;在此次拆迁中,唐大嫂家最多能购买130m2的房屋,他们选了两套80m2的房子,超额申请30m2的房屋,另外还申请了30m2的车库和20m2的储存室,应付款214 000元。除去赔偿金,还需补交99 465元,相当于两年左右的家庭收入。
案例3张二姐一家四口,不种地,丈夫是打工者,一个孩子在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年一家有10 000元的收入,处于下层阶层。张二姐家有150m2的砖木结构房屋,三分宅基地,可以得到114 535元赔偿;在此次拆迁中,张二姐家最多能申请130m2的房屋,他们选择了一套120m2的房子,20m2的储藏室,应付款136 000元。除去赔偿金,还需补交21 465元,相当于两年多的家庭收入。
在老王村居住条件相当的村民,由于所在家庭经济状况不同,拆迁需要承受的经济压力也存在差异。对于成员中有更多工人、教师,更多打工者的家庭来讲,如案例1中的王大娘家,在村庄中处于中上层,经济压力相对较轻,申请超过额定的居住面积,仍能较好地消化负担,反对拆迁的意愿较轻;反之,对于工人、教师和打工者较少的家庭来讲,比如案例3中的张二姐家,在村庄中处于下层,申请在额定居住面积内的房屋,仍会使他们感受到较重的经济压力,反对拆迁的意愿较强。总体而言,在现有拆迁政策下,多数村民反对拆迁,但各户又因其经济状况不同在反对拆迁的强度上有些差异。这种收入差距导致的经济状况差异,直接影响每户对赔偿标准和购房花费的关注程度、购买安置房的经济能力和为拆迁承受的经济压力状况,从而直接影响该户的拆迁意愿。
2.基于代际的拆迁意愿差异
夏永久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城镇化意愿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年龄因素带来的代际差异使村民对拆迁有不同意愿[18]。王村拆迁虽然不是为了实现当地城镇化,但居住方式由平房变为楼房也是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表现,代际之间对此也存在差异化的需求。大多数习惯了平房生活的村民表示不愿意拆迁,但可以尝试适应楼房生活,但老年人的反对意愿相对其他年龄段显然更加强烈。
对于青年人来讲,尽管王村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但他们的适应能力较强,对拆迁并不是非常反感。相当多的青年人根本不住在王村,正如案例4中胡小哥所说,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青年人在外打工,且有一半在县城有房子,对于一年不回村几次的他们来说,拆迁与否无所谓,一般都是听从于中年父母的选择。
案例4胡小哥,25岁,在县城打工有房子,他坦言:“你来这调查看见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没见着几个吧?他们和我一样都去县城打工了,像我们这些九零后除了在家带孩子的,没几个还住在村里,一半在县城都有房子,所以对我来说搬不搬无所谓。真正在乎搬不搬的都是中老年人,他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没意见。”
对于中年人来说,拆迁意味着带来换购新房、增加各种支出的经济困难,意味着打破几十年的平房生活方式,没有院子不能养花种草种菜,楼房生活不自由。这使他们对楼房生活不太满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现代化产品的进入和楼房的干净、舒适和便利,让他们慢慢感受到楼房生活的好处,也就使他们渐渐适应了楼房生活。
案例5唐大娘,50岁农民,以干农活、做家务为主,她说:“如果土地不塌陷,俺不愿意离开老房子‘上楼’,每天爬楼梯多累……拆迁不合理,赔偿太少、买房太贵,以后啥都得用钱买,水电也得买,煤气也得买……你说在这没有院子,不能种种菜养养花,连菜都得买……但住在这里很干净,难闻的气味少了很多,和之前相比也很方便,去做饭干点什么都在一个屋子里,不用跑来跑去,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也挺好的……”
老年人习惯于在平房生活,对于适应能力较差的他们来说,换一种生活方式无疑是一次巨大考验,特别是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与邻居朋友交流不便,不识字不能看书看报消磨时间,每天无事可做,使他们难以接受。怨气最大的是住在20 m2储藏室的老人,案例6中的倪奶奶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多因上下楼困难、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而蜷缩在车库或储藏室里,生活十分不便,而且与家人距离较远,缺乏家人的关心和照顾,使他们更加难以适应楼房生活。
案例6倪奶奶,78岁,儿子家住在五层,儿子以倪奶奶腿脚不便不能‘上楼’为由,让她住在储藏室,儿子家每天给老人送饭。有一次,儿子家忘记给她送饭,她就自己爬到五层去要,这件事成为村民们私下相传的谈资。倪奶奶说:“在这里住着很干净,但电费比老家贵,没法烧柴火烧锅,还得交煤气费……没有厕所,小便还可以用尿盆接着,大便可怎么办啊,只能走几百米到乡镇政府旁边的厕所,……,这就是不让人过日子啊!你看在这住着倒是干净,但就那么大点地方,还没个院子……住在这真是遭罪啊!”
总之,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对拆迁有着差异化的意愿表达,老年人反对拆迁的意愿往往更加强烈,而青年人对拆迁的反对程度较弱。不过,多数村民有一个基本共识:“如果地不塌就不搬。”
三、农民拆迁意愿的诱致性变迁路径
虽然王村多数村民开始时反对拆迁,但最终却签订了拆迁协议。农民对拆迁的态度之所以产生如此变化,主要是村庄内外力量共同形塑的诱致性变迁路径所致。现将其具体策略和路径分述如下。
1.政策鼓动增进村民的相对获得感
拆迁政策是实施拆迁项目的基础和依据,因此优化相关政策有助于减少村民对拆迁的埋怨,增进相对获得感,最终使村民同意拆迁。
村民对拆迁不满意主要来自对拆迁补偿的不满意[7]。为此,政府等拆迁主体必须合理制定拆迁补偿标准,尽力使村民在拆迁中没有经济负担[19]。当既定政策不能达到村民对拆迁补偿的基本预期时,便应该在严格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实施相应的奖励政策,以减少村民经济压力,促进村民拆迁。为推动王村拆迁有效进行,2015年乡政府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对规定时间内拆迁的村民给予每户20 000元的奖励;并在村民入住安置房前,给予每户村民一年半的租房补贴9 000元,补贴500元/户的搬家费,激发了村民的拆迁积极性。虽然村民仍认为补偿标准较低,购房花费较高,但补贴的29 500元有效缓解了压力,有些申请居住面积较少的家庭甚至可以不必补交购房费,因此不少村民同意拆迁。对多数村民而言,他们支持拆迁或者确切地说不反对入住社区的底线就是‘拆旧搬新’在经济上大体均衡[20]。这就需要政府根据村民平均经济状况,制定合理的拆迁补偿和奖励政策。
农村拆迁通常主要涉及乡政府、村委会和村民三个利益主体,三者在利益博弈过程中难免互相猜疑,特别是村民经常对村委会工作的廉洁程度存在疑虑,认为一些村干部和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村民可能从中谋取比自己更多的利益,这些疑虑使村民难以遵循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要求,从而拒绝拆迁。如果政策执行能体现出公平性和透明度,就会让村民产生自身利益不会受损的信念,从而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催生相对获得感,最终同意拆迁。2015年乡政府在拆迁政策中加入了详细的选房政策,即村民按照排队和抽签顺序相加除以2的数字顺序从小到大选房,各户的选房顺序和安置房申请情况一目了然,村民可以到村委会查询记录,实现对村委会工作的严格监督。这样的选房政策提高了拆迁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使村民能够信任村委会的工作,产生心理平衡感,从而同意拆迁。
政策鼓动之所以使村民同意拆迁源于两点:一是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补偿;二是农民对比前后政策后生发的相对获得感。因此,政府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和权力,通过优化后的拆迁政策,尽量满足农民经济利益,提高政策实施透明度,增加了农民对拆迁的未来预期以及相对获得感,从而使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2.利益诱惑促使村庄精英作出示范
村庄精英的经济来源与乡政府和矿场有密切关联。乡政府和矿场通过控制和影响村庄精英的利益而对其施加影响,促进其同意拆迁。村庄精英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示范性,对带动其他村民拆迁有不可忽视的效果。
为实现基层治理目标,乡村组织广泛以“利益制衡”的方式进行连带式治理[21]。王村每三年一次村干部选举,虽然主要是通过海选完成,但是乡政府的意志仍可以通过村级党组织来实现。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工资、村委的活动经费多依靠财政拨款,这就使得村干部对于乡政府更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拆迁过程中,对于一开始拒绝拆迁的村干部,乡政府会以“谈话”的形式劝其拆迁,这些谈话往往具有诫勉的性质,对多数村干部具有很强的威慑力。除了一户村干部家庭因认为条件不合理拒绝拆迁以外,其他村干部家庭都签字同意;乡政府在多次约谈未果后,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将这个村干部撤除了职位。这一事件展现了政府拆迁的决心,也对村干部与村民产生了很大的震慑效应。另外,乡政府还要求教师带头拆迁。王村少数村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当地小学、初中当教师,这些教师的工资和退休金虽然由县级财政统筹但却由乡政府分发,这就使教师一般不敢与乡政府作对,最终同意拆迁。此外,矿场为了开采老王村的煤矿,也积极参与到村民拆迁中,告诫工人“如果不拆迁就不让上班”,这样工人就无法达到规定工作时长而难以获得工资。这些措施对工人拆迁行为产生了影响,在一些人被矿场约谈后,最后多数工人“被迫”同意拆迁。
政府和矿场利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领导关系和管理关系、经济上的雇佣关系,促使乡村精英拆迁,达到了通过村庄精英带动其他村民拆迁的目的。对于多数村干部、教师和工人来讲,乡政府和矿场提供的经济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与损失一定资金购买安置房相比,失去可靠且稳定的经济来源可能对他们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以村干部、教师和工人的工资作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农户往往较早同意拆迁。
此外,村民认为政府权力和意志不可挑战的集体记忆,也导致不少村民倾向于遵循政府要求同意拆迁。王村一些村庄精英30多年前因抵制拆迁利益受损的深刻教训,在村民中形成了政府意志不可轻易违背的集体记忆①。因此,即使乡政府并未对村民进行实质性威胁,但是当村民看到拒绝拆迁的村庄精英被约谈后,仍然心生畏惧。因此,利益诱惑不仅动员了村庄精英,也对普通村民形成了一定示范效应。
3.熟人社会多重关系的带动效应
村民生活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村民间的关系会对其拆迁行为产生影响。村民往往通过考虑与村庄整体的关系,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判断自己是否同意拆迁。
村民与村庄整体的关系会影响其行为选择,换言之,村民会受到其他村民选择的影响。在相互熟知的群体中,人们往往选择身边的人作为参照群体,来获得“相对满足”或“相对剥夺”,在群体成员彼此相互作用的条件下,会发生一种彼此接近、趋同的类化过程。当村民认为其他村民倾向于一种行为选择时,害怕自己被孤立,往往会采取与主流相同的行为取向,以保持和多数人一致[22]。因此,当村民了解到多数人同意拆迁时,便可能产生从众效应,作出类似的选择。
当然,更重要的是,农民拆迁的行为选择会受到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村干部与村民都有或多或少的连带关系,关系紧密程度由强到弱往往是血缘关系、姻缘关系、“拜把子兄弟”关系、邻里关系等。在王村,与村民利益最为密切的群体便是村干部。与村干部关系紧密,便意味着村民能在长期互动中形成利益互惠的交换关系。村干部因其职位便利掌握着村内外很多资源与信息,通常会将最新的动态和信息优先分享给与其关系紧密的村民。一方面是为了促使关联紧密的村民支持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与这些村民分享有利资源,让他们更容易选到心仪的房子,从而稳固与这些村民的关系,为下一次再度当选村干部奠定群众基础。囿于与村干部的紧密关系,也为了能在今后享受更多的资源,这些村民往往会同意拆迁。而且,一旦在拆迁过程中出现不利的情况,他们也可以通过与村干部的紧密关系突破规则,最大限度保护自身利益。换言之,虽然各地都有严格的拆迁标准,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还会有较大弹性空间[14],这些具有特殊关系的村民可以获取超出普通村民补偿标准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房屋和宅基地的丈量和评估上。一位村民坦言,因其与村干部的密切关系,在房屋赔偿过程中多要了几百元。
熟人社会的连带关系在农民拆迁中发挥作用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是熟人社会的关系结构,二是村干部在村庄中的影响力。熟人社会中交错复杂的关系会对农民行为选择产生指向性和约束力,农民通常难以摆脱熟人社会中各种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在村庄权力关系中处于相对核心地位的村干部以面子、人情及其掌握的村内外重要资源作为交换,动员村民一起拆迁;而与村干部关系紧密的村民也期待以此逾越规则获得非常规的利益,最终引发熟人社会内部的从众效应,有效促进村民拆迁。不过,乡村社会也因此不断进行特殊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最终促发了“特殊主义”行为逻辑在乡村社会的复制。
4.代际联动促使家庭内部成员妥协
代际联动是指在家庭中掌握支配性地位的成员,通过代际之间的关系,利用其家庭地位影响其他家庭成员行为选择。在王村的拆迁过程中,主要体现在掌握家庭主要资源处于支配地位的青年人、中年人对老年人的影响。
老年人比较习惯原有居住环境,对于拆迁普遍有抵触情绪,但除了乡政府每个月给的100元左右的“老人钱”,缺乏其他经济来源,因而大多数老年人需要得到儿子、女儿的赡养。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家庭成员所处的地位并未完全平等,这直接影响其拆迁意愿的表达。老年人虽然对拆迁持较为强烈的反对态度,但因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拆迁行为选择往往由青年人、中年人决定,老年人只能违背意愿而选择迁就;相对而言,有经济收入来源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如若做出拆迁的决定,并不会因老年人的意愿而动摇,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经济支配性地位,进行引导或威胁,通过代际关系直接要求老年人拆迁。
“代际联动”是家庭内部的影响机制,在家庭中掌握主要经济来源的成员在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基础上,利用其在家庭中的权力中心地位联动其他成员同意拆迁。“代际联动”对拆迁行为的影响直接来自于代际地位的不平衡。年轻人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孝道伦理、传统价值的支配,完全步入理性算计的时代[23]。老年人年龄越大,越难以给子女带来经济利益,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越低下,越受控于子女的意愿。
总之,乡政府和矿场的“政策鼓动”、“利益诱惑”,村庄内部的“连带关系”、“代际联动”都有效促进了村民拆迁意愿的转变。由此可以看出,村民拆迁的意愿无处不受政府、矿场、村庄和家庭所型塑的权力-关系网络的影响。在农民拆迁的博弈过程中,相比于村干部和村民,政府、矿场等位于权力的塔尖位置,而“政策鼓动”和“利益诱惑”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则依赖于政府、矿场与各种村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在村庄熟人社会的“连带关系”和家庭的“代际联动”中,农民拆迁的行为选择看似是在熟人社会或家庭内部之间的一种关系连带结果,却也无处不裹挟于占据村庄或家庭内部资源的强势地位者的权力之中。因此,农民拆迁之所以出现意愿的变迁,其根本在于多数农民难以跳脱“权力-关系”网络的阻隔。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对于多数农民来讲,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告别习惯的生活方式进入新社区生活,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尤其对于位居经济状况下层的家庭和较难以适应的老年人而言,适应新环境是他们面临的重大难题。村民对于拆迁的意愿也因此总体呈现出消极态度。不过,绝大多数农民最终同意拆迁根源在于难以跳脱“权力-关系”网络的阻隔。政府、矿场等村庄外部力量通过“政策鼓动”和“利益诱惑”发挥了对村庄精英的作用,而村庄熟人社会及家庭则通过“连带关系”和“代际联动”进行内部的自我动员,使得拆迁成为最终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关系”网络中,农民拆迁得以成功实现,但其真实需求并未获得真正的满足,因此可能掩盖潜藏的社会矛盾。对于一些经济处于下层且以务农为生的农民而言,拆迁进入新社区必将带来生产生活成本的提高,进而大大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对于较难适应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因为生活空间的挤压可能引发愈来愈多的代际矛盾和代际紧张,或者因为各种原因,生活质量出现断崖式下降。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一旦激化,就会形成对政府的二次甚至多次的“找补”式上访,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同样,受到“利益诱惑”的部分村庄精英,只是暂时因政府的威慑而抑制内心的不满情绪,但基层政府的权威也必然受损。因此,农民拆迁问题,不应该是政府单向度推动的过程,需要双方达成更多的共识,尤其要注意“被上楼”所掩盖的社会矛盾,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如此一来,方能在推动政策有效实行的同时,维护社会的长久稳定。
注释:
① 30年前,王村也因矿场生产导致地表下陷要求村民搬迁。为平复村民情绪,矿场和乡政府许诺,为所有健康的18~40岁男性村民提供工人岗位,但乡政府为解决县城失业问题没有兑现承诺,激怒了王村村民导致几百名村民自发集资到省政府和北京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村民处于弱势,多数村民被关押三天,并与上访处工作人员、有政府力量做支撑的灰黑势力发生了多次肢体冲突,受到了皮肉之苦。还有一些村民在回村后遭遇了牢狱之灾,坚决不妥协的村民至今都在老王村居住,并被乡政府剥夺了参与乡村事务的权利。
[1] 陈锋.从整体支配到协商治理:乡村治理转型及其困境——基于北镇“钉子户”治理的历史考察[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21-27.
[2] 李昌平,马士娟,曹雅思.对“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的系统思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3):33-36.
[3] 赵茜宇,孟庆香,张占录.农村土地整治的博弈分析及路径选择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4(11):216-221.
[4] 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8.
[5] 鲍海君,方妍,雷佩.征地利益冲突: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行为选择机制及其实证证据[J].中国土地科学,2016(8):21-27;37.
[6] 徐晨,王振亚.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乡镇政府的角色悖论及其行为选择[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5-72.
[7] 刘征.拆迁政策与行为失范关系的统计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8):113-117.
[8] 袁明宝,朱启臻.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院落的价值和功能探析[J].民俗研究,2013(6):121-126.
[9] 范成杰,龚继红.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基于华北李村农民“上楼”的分析[J].青年研究,2015(2):85-93;96.
[10] 钟晓华.可行能力视域下农民“上楼”前后多维福利的追踪测度[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2):93-100.
[11] 丁开杰.依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15(54):45-46.
[12] 魏天辉.“农民上楼”与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路径[J].新视野,2012(1):94-97.
[13] 郑风田.撤村并居中的土地问题:现状、原因与对策[J].现代城市研究,2013(6):20-24.
[14] 杨华.农村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博弈:空间、主体与策略——基于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39-49;181.
[15] 陈柏峰.征地拆迁上访的类型与机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5-33.
[16] 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5):21-45;243.
[17] 陈成文,赵锦山.农村社会阶层的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选择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8(10):37-40;83.
[18] 夏永久,储金龙.基于代际比较视角的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来自皖北的实证[J].城市发展研究,2014(9):12-17.
[19] 黄仁露.关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政策的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1):5-7.
[20] 张颖举,吴一平.已建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入住意愿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5(6):59-66;111.
[21] 陈锋.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J].社会,2012(1):104-125.
[22] 熊凤水.压力与从众视角下的农民生男偏好——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07(2):8-14.
[23] 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3(5):47-63,75.
责任编辑:曾凡盛
Farmers’ removal will and induced changes path: Based on an individual case in Wang village located in north China
CHEN Feng, HOU Tongjia
(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Beijing Society-Building & Social Governa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of the individual case in Wang village showed that with the impacts of economy and intergeneration, farmers’ will has diversities. Although farmers show their passive attitudes, most of them respo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and determine to remove eventually. It’s the inside and outside power-relationship net that causes farmers’ relocated will change: government and mine company,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external influence, encourages villagers and village elites to remove by policies and benefits, while villag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family, which can be grouped into the internal influence, urges the villagers to interact to move up stairs by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generation. These four mechanisms ultimately impel most farmers to remove. However, for farmers in the power-relationship system, especially for the vulnerable group, it’s not a satisfied result for them to contend their will, which may cause society instability in the future.
farmers’ removal; will of relocating; induced changes; power-relationship net
10.13331/j.cnki.jhau(ss).2017.03.007
C912.82
A
1009–2013(2017)03–0037–07
2017-05-1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KS022)
陈锋(1985—),男,福建永泰人,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