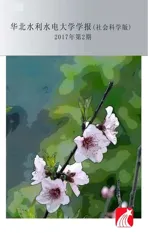波德莱尔现代性美学思想分析
2017-02-24程勇真
程勇真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波德莱尔现代性美学思想分析
程勇真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开创者,他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历史进程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他认为,美的事物必然具有两重性,即绝对美和特殊美。在这两种美中,他显然更倾向于后者。重视特殊美其实就是近代美学精神的体现。他还认为,自然实际上充满了道德的邪恶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由此他非常重视艺术美的内涵和价值。他不仅把美建立在了对丑与恶事物的肯定上,而且对死亡的事物与主题充满迷恋。正是对于颓败、丑陋甚至死亡事物的迷醉,波德莱尔的美学才被我们称为审丑美学和死亡美学。其死亡美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有普遍的人类经验意义与形上色彩。
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绝对美;特殊美;自然美;艺术美;审丑美学;死亡美学
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开创者,波德莱尔对颓败都市生活的书写,对于恶之美的发现,以及对于时间意识的敏锐感觉,都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历史进程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今天,我们尝试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美学思想予以整体分析,以期引起人们最大程度的审美关切和审美注意。
一、美的两重性:绝对美和特殊美
柏拉图的理念论对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甚远。柏拉图把美分为三个层次:美的理念、美的事物、美的艺术。美的艺术及美的事物是对美的理念的模仿,本质上是虚假而靠不住的,只有美的理念才真实永恒。柏拉图实际上把存在分为真实与非真实两种。至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根据二元论思想把世界划分为天堂和地狱、灵魂和肉体、上帝和魔鬼等,上帝是至善和最高的美,其他事物则是对上帝的分有和模仿。
西方这种二元论美学思想对波德莱尔影响至深,以至于波德莱尔认为,美的事物必然具有两重性,即绝对美和特殊美。他说:“如同任何可能的现象一样,任何美都包含某种永恒的东西和某种过渡的东西,即绝对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绝对的、永恒的美不存在,或者说它是各种美的普遍的、外表上经过抽象的精华。每一种美的特殊成分来自激情,而由于我们有我们特殊的激情,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美。”[1]272他还说:“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我不相信人们能发现什么美的标本是不包含这两种成分的。”[1]431根据波德莱尔的看法,绝对美即某种永恒的、不变的美,特殊美由于受到时代、风尚、道德、情欲等影响,具有相对性和短暂性等特点。波德莱尔强调说,任何美的标本都包含这两种成分。
不过,在这两种美中,波德莱尔显然更倾向于后一种美。波德莱尔认为,多样化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个性则是铭刻在生活中的显著徽记,单调的、没有个性的事物,就像厌倦的虚无一样巨大。由此他把个性与古怪作为了美的事物的核心要素。波德莱尔曾说:“美总是古怪的。……这种古怪的成分组成并决定了个性,而没有个性,就没有美。”[1]327因此,波德莱尔非常重视不同时代、民族、职业、阶级、风尚、道德、情欲等造就的不同的特殊美。他曾说:“……每个世纪可以说都有自己的风致。这样的看法也可用于职业,每种职业都从它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中抽出它的外部的美。在有些职业中,这种美以刚毅为特征,而在另一些职业中,则可能带有闲适的明显标记。”[1]451在阶级审美上,波德莱尔非常鄙视村妇和乌合之众,认为他们作为自然力的受害者,由于一切皆得之于“淳朴的自然”,缺乏微妙的纯粹精神,所以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品德上,都是可厌的。相反,浪荡子由于富有闲暇和金钱,能够单纯地在自己身上培植美的观念并勇于拒绝庸俗与平庸,因此,浪荡子的厌倦、冷漠、无所事事,以及挑衅性的高傲,都赢得了波德莱尔毫不犹豫的青睐。波德莱尔甚至断言说,浪荡子是人类“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1]455。
当然,波德莱尔重视特殊美,在一定意义上是受到浪漫派美学的影响。浪漫派重视情感、想象力、个性、特征对于美的事物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波德莱尔,使其坚决反对古典派及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原则及模仿原则,而把梦幻、热情、想象力、暗示作为艺术创作的中心。波德莱尔甚至认为,如果诗人“描写现存之物”,就降格了;如果“叙述可能之物”,就是“忠于职守”。波德莱尔由此认为诗人就是一个“集体的灵魂,询问,哭泣,希望,有时则猜测”[1]95。值得注意的是,波德莱尔视浪漫主义为“美的最新近、最现时的表现”[1]198,并把它看作现代艺术。他说:“谁说浪漫主义,谁就是说现代艺术,即各种艺术所包含的一切手段表现出来的亲切、灵性、色彩和对无限的向往。”[1]199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波德莱尔重视特殊美其实就是近代美学精神的体现。近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普遍重视特征、情致、意蕴、表现、有限和历史等的美学意义。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曾说:“随着个人和种族的教育从注重形式表现力走到注重显出特征的表现力,……力量和意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347因此,波德莱尔重视特殊美,无疑体现了西方近代美学精神的新转向。
二、两种美学态度
西方文化对于自然美的态度,自十八世纪以来主要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自然肯定论者,认为自然本美,文明则是人类的堕落;另一种则否定自然美,肯定艺术美,如黑格尔就认为,相对于艺术,自然乃理念最浅近的客观存在,相对缺少生气灌注的主体观念的统一性与主体自由,所以自然美是有缺陷的存在。
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美肯定论思想影响十八世纪美学甚深,人们普遍认为自然乃美和善的源泉。但波德莱尔却反驳道,十八世纪以来人们关于善和美来源于自然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大部分关于美的错误产生于十八世纪关于道德的错误观念。那时,自然被当做一切可能的善和美的源泉和典型。对于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盲目来说,否认原罪起了不小的作用。”[1]457波德莱尔认为,自然实际上充满了道德的邪恶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因为“一旦我们走出必要和需要的范围而进入奢侈和享乐的范围,我们就会看到自然只能劝人犯罪。正是这个万无一失的自然造出了杀害父母的人和吃人肉的人,以及千百种其他十恶不赦的事情”[1]457-458。即使动物和植物,在波德莱尔看来,本质上也是“丑和恶的代表”,竞相做出“一个个毫不含糊的鬼脸”[1]73。波德莱尔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一切恶和不道德都是自然和前定的,那么一切美和善,则都是“理性和算计”的结果,是“艺术的产物”[1]458。
在艺术美学观念上,波德莱尔追求敏感的想象力、模糊的回忆与朦胧的梦幻,坚决反对模仿性艺术。波德莱尔认为,诗歌仅仅存在于丰富的想象里,而不是拘囿于真实和准确。他甚至说,梦幻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幸福”,而“表现梦幻的东西是一种光荣”[1]366。波德莱尔还特别重视艺术的暗示性特征与应和功能。他说,“纯粹的艺术”,就是“创造一种暗示的魔力,同时包含着客体和主体,艺术家之外的世界和艺术家本身”[1]347。波德莱尔更认为,在人类精神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神秘的应和关系,它像一条神秘的精神锁链,把人与物紧密相连,这一点在其诗歌《应和》中得到了形象说明。
就艺术的审美风格而言,波德莱尔特别推崇崇高和宏伟的风格与气度。波德莱尔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相信想象力,蔑视宏伟的东西,喜爱(不,这个词太美了)并专门从事一种技艺,这是他的堕落的主要原因。”[1]359他还说:“在自然中和在艺术中,假定价值相等,我偏爱宏伟的东西,巨大的动物,雄伟的风景,巨大的船,高大的男人,高大的女人,宏伟的教堂,等等,把我的趣味变成原则,我认为在缪斯的眼中,规模也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1]392正是由于推崇崇高的风格,波德莱尔才特别喜爱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认为他由于善于表现人类伟大的激情与痛苦,所以其画作中充满了丰富的感觉和思想,蕴藏着无限的美与力量。
然而似乎有点矛盾的是,波德莱尔比较偏爱艺术作品忧郁的色调。他认为,忧郁、痛苦与绝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气质,自然具有一种动人的色彩和高贵的力量。他说,如果一首诗和一阕音乐,能让灵魂“窥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并能“使人热泪盈眶”;如果一首诗通过眼泪能表明“一种发怒的忧郁,一种精神的请求,一种在不完美之中流徙的天性”,那么这首诗就能“立即在地上获得被揭示出来的天堂”[1]187。
关于艺术,我们还想说的是,波德莱尔极力反对艺术与现代工业的结合。他认为诗与工业,完全是“两个本能地相互仇恨的野心家”,如果让它们狭路相逢,其中一个必然为另一个服务[1]365。在波德莱尔看来,以摄影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技术,完全缺乏想象力和情感,缺少内在的灵魂维度,所以摄影一旦侵犯了不可触知的、艺术的传统领域,便会无情地排斥和腐蚀艺术,最终沦为“平庸艺术家的庇护所”。这是波德莱尔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他极力反对摄影进入艺术领域。
不得不提的是,从贝多芬忧郁和绝望的音乐中,从麦图林的小说、拜伦的诗歌,以及爱伦·坡的诗歌和小说对人类激情的谴责性表达中,波德莱尔还看到了潜藏于人心深处的魔鬼。他因此总结说,人类的现代艺术有着强烈的“魔鬼倾向”。他是这样表达的:“现代艺术在本质上说有魔鬼的倾向。似乎人的这一地狱部分(人很喜欢自己对自己进行解释)日益增大,仿佛魔鬼把通过人工的方法使之增大作为消遣似的……”[1]123波德莱尔通过比较,看到了古代艺术热衷于对“美的、快乐的、高尚的、伟大的、有节奏的”事物的表现,而现代艺术则沉浸于对丑陋的、忧郁的、绝望的、痛苦的事物的描绘。可贵的是,波德莱尔虽然看到了现代艺术的不和谐之处,但他依然醉心于对人类病态激情的不朽呈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勇气说波德莱尔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开启者。
三、审美现代性的典型体现:审丑美学与死亡美学
在西方传统美学中,美作为一种神圣性的存在,往往与至善、幸福、快乐、自由、无限等相关联。丑则是与美截然相反的事物。然而波德莱尔把美建立在了对丑与恶事物的肯定上。他认为,即使在卑贱与丑恶的事物中,也往往隐藏着伟大与神圣的消息与秘密。美实际上就是恶之花。因此,波德莱尔把自己的美学严格建立在了对丑陋、孱弱、残废、颓败、腐烂,甚至死亡事物的肯定基础上。波德莱尔本人也经常游走于都市阴郁的僻处,在那里静静地窥视被生活的风暴所摧残的人们,流浪汉、妓女、酒鬼、寡妇、卖艺者,甚至死尸,都成了波德莱尔无限迷恋和深情注视的对象。波德莱尔曾说:“阴郁的僻处是命运的残亡者相聚的地方。”这里,“风暴还发出残延的怒吼”。并且正是这些场所,“往往是诗人与哲学家喜欢猜测和遐想的地方。这里有着一种确实存在的精神食粮”[3]40。在此基础上,波德莱尔把美界定为“某种热烈而忧伤之物”,“某种有点朦胧、容许猜度之物”[3]40。正是对于颓败、丑陋甚至死亡事物的迷醉,波德莱尔的美学才被我们称为审丑美学和死亡美学,而这也才是审美现代性的真正体现。
关于波德莱尔美学的审美现代性问题,卡林内斯库在《波德莱尔与审美现代性的悖论》一文中,除了强调波德莱尔对现代性之新颖性、当下性等时间意识敏锐的感觉和捕捉外,还谈到了其对社会政治现代性的批评,对都市现代性的迷恋,对艺术有机性的拒绝,以及极其明显的反自然主义、反进步主义及反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同时更重要的是,卡林内斯库还指出了波德莱尔另一重要的审美现代性美学症候,即其对于美之“撒旦”特性的理解。卡林内斯库说:“有趣的是,这个段落又一次包含了相当明确的在美学上忠实于现代性的承诺:美,波德莱尔说,传达出一种陌生感、神秘感,‘最终(为了勇敢地承认我在美学上感觉是如何现代)还有一种幸福感’。有意思的是,这个出色段落的结尾引入了撒旦的形象:‘……阳刚美的最完美原型是撒旦——就如弥尔顿眼中的他。”[4]55把“撒旦”定义为美、特别是阳刚美的基本内涵和特性,这是波德莱尔对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重大突破、对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有力开启。而实质上,“撒旦”除了“丑”和“恶”两种基本审美意涵外,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渎神和反抗的色彩。所以,波德莱尔的美学并非仅仅一种简单的审丑美学和死亡美学,其思想的根柢处更充满着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大胆质疑与反抗,以及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的深沉同情与怜悯。
特别是波德莱尔的死亡美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有普遍的人类经验意义与形上色彩。波德莱尔认为,人生本身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只宛如一块“被隐约的恐怖包围的”顽石,充满了苦涩的欲望与残忍破败的回忆。而包围生命的整个大地也犹如“一间潮湿的牢房”,连希望也“如蝙蝠般飞去”(《忧郁之四》)。既然人生充满了如此无尽的颓败、厌倦、痛苦与绝望,那么,死亡也许就是穷人和艺术家最好的归宿了,至少能够给他们以最后的尊严与慰藉。不过不像叔本华和尼采那样,对死亡的超越建立在对艺术的渴求与谛视上,波德莱尔在诗作中焦灼地呼喊着死亡如黑夜一般的降临。如在《快乐的死者》一诗中,他希望自己能够“在一片爬满了蜗牛的沃土上”,“挖一个深深的墓坑”,可以随意“把老骨头摊放,睡在遗忘里如鲨鱼浪里藏生”。在《被杀的女人》《腐尸》《穷人之死》《艺术家之死》《虚无的滋味》《死后的悔恨》《痛苦的炼金术》《忧郁之一》《忧郁之二》《忧郁之三》等诗作中,波德莱尔更是直接面对死亡本身,对之展开不厌其烦的细腻描绘和灰色想象。死亡于波德莱尔,也许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不可逃离的主题,紧紧地缠绕着他,包围着他,弥漫了他整个生命,使其甚至不能呼吸。他的确希望从生命的苦役中解脱。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死亡根本上是内在于每一个生命的,它甚至就是生命本身,内在地规定着一个人的基本生命态度与世界梦想。在此意义上,波德莱尔的文本简直就是一个个黑色的死亡文本,充满了对死亡的骚动与渴求。当然,波德莱尔的死亡美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和他的爱主题、隐晦的性主题密切相关的,是和他对整体宇宙人生的深沉理解相关的。
关于波德莱尔对死亡主题的无限热爱,戈蒂耶进行了冷静的深层的社会学解释。他说,“这些强烈的全色调”,只不过“应和着秋天、落日、熟透的果子和文明的末日”罢了[5]33。这即是说,波德莱尔热衷于对颓败、死亡等事物的描写,只不过是应和了这个腐败、衰落的时代而已,其他别无深意。但我们却认为,波德莱尔对丑陋、死亡、荒诞与无意义等主题的热爱,实际上不仅仅预示了一个时代的衰落和死亡,更标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崛起,即现代性社会的姗姗来临。丑陋、虚无、荒诞与死亡,不仅是现代主义热衷表现的主题,其本身更是现代美学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色彩。
阐释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不仅具体影响了法国和英国颓废派文学的诞生及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文学的产生,而且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开创者,波德莱尔对整个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历史进程影响巨大。
[1]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 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M].亚丁,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5.
[4]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5] 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M].陈圣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李翔)
An Analysis of Baudelaire’s Modern Aesthetic Thought
CHENG Yong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Baudelaire’s aesthetic thought is very important. As a pioneer of aesthetic modernity, h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odern aesthetics. Baudelaire believed that the beauty of things must have a dual nature, that is, the absolute beauty and special beauty. In the two kinds of beauty, Baudelaire is obviously more inclined to the latter kind of beauty. Baudelaire’s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beauty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aesthetics. Baudelaire also believed that the nature was actually full of evil of morality, and the nature was the root of all evil, so Baudelair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artistic beauty. Baudelaire not only established his aesthetics on the affirmation of ugly and evil things, but also showed a fascination with the theme of death. Because of the decadent and ugly things and even death intoxication, Baudelaire’s aesthetics is called ugliness aesthetics and death aesthetics. Baudelaire’s death aesthetics thought, in a certain sense, has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 and metaphysical color.
Baudelaire; aesthetic modernity; absolute beauty; special beauty; natural beauty; artistic beauty; the aesthetics of appreciating ugliness; death aesthetics
2016-11-18
2015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废墟美学研究”(SKL-2015-1085)阶段成果;2014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消逝的乡村美学及重新建构”(2014BZX005)阶段成果
程勇真(1971—),女,河南原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学。
B83
A
1008—4444(2017)02—005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