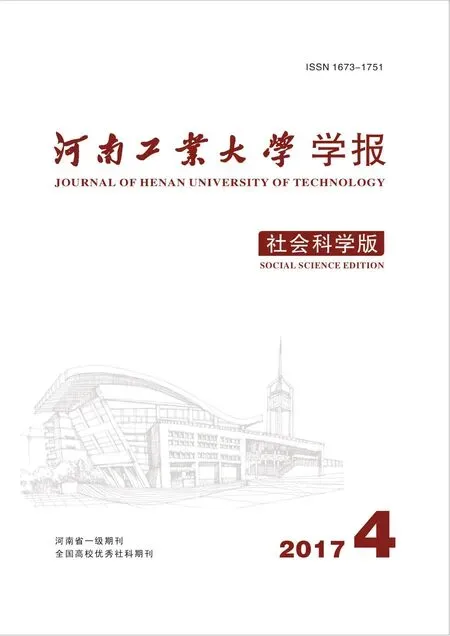略论民国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
2017-02-23刘晖
刘 晖
(河南行政学院 省情教研室,河南 郑州 451000)
略论民国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
刘 晖
(河南行政学院 省情教研室,河南 郑州 451000)
民国时期,伴随城市的资金、商品、服务等诸多市场因素的发展,城市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城市经济功能逐步彰显。现代工业的导入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现代经济部门在城市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城市从过去的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逐步转变为现代经济主导下的复合型的经济、政治或文化中心。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还体现在洋行、银行、股票、百货公司、城市贸易等其他经济部门的功能演化方面,推动了城市其他经济部门的普遍设立及职能更新,亦促进了城市商业发展和消费功能转型。
民国;城市;经济功能;生产;消费
从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近代城市的形成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运动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近代化则主要是通过经济要素特别是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来完成的[1]。就近代中国而言,通商口岸的设立,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的整备,使得商品流通的速度大为提升,商业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民国时期中国的城市体系初步得以建构。资本的本能是追逐利润,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民族资本,投到城市市场所获取的利益往往比投到农村要大得多。加之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吸引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部门。生产要素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使得民国经济社会呈现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城市在新的资源配置体系中获益并快速成长,与此同时,城市的经济功能发生巨变,呈现与传统城市迥异的现代性特征。生产要素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与集聚,推动了城市工业生产的增长,也使得社会生产的主要来源地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民国时期的城市不仅仅是民众消费的集中地,同时也是近代工业生产的集聚地。在城市的整体经济功能中,生产功能的地位渐次上升。就当时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二者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言,虽无法妄称孰重孰轻,但城市经济由自然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的补充部门上升为工业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的主导部门,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民国城市的资金、商品、服务等市场因素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其他经济部门的普遍设立及职能更新,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功能的内涵式提升。
1 城市经济结构重构并带动生产能力提高
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经济功能的提升,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现代经济部门在城市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经济时代以手工工具、人力、畜力及自然力为特征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逐渐被以机器生产和蒸汽机动力为特征的现代城市工业和商业贸易所取代[2],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步增强。在这种情势下,城市开始逐渐从过去功能单一型的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转变为现代经济主导下的复合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导入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产业结构不断得以调整,生产的效率化、规模化持续提升,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和城市人口激增,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型城市的建立与扩容,并推动城市经济功能的进一步提升。近代中国城市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其原因涉及方方面面,但最为重要的因素源自产业发展,现代产业的不断生长是城市成长的根本动力,上海、汉口、天津等均是凭借工商关系发展成为大都市的。“此等都市在数十年前,还是无人过问之地,工商业的快速发展,遂促成今日之发达,而其他工商业不居重要位置的通都大邑则日渐衰落”[3]。开埠以后,除天津、汉口和上海之外,大连、哈尔滨、青岛、烟台、重庆、厦门等新兴城市,伴随城市现代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也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扩张,逐渐发展成为融合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大城市或特大城市。
外国资本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率先落脚,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亦在沿海、沿江城市开始起步并发展起来。从1895—1913年的统计资料看,其间全国共设立549家厂矿企业,沿海城市占61.35%,内地占38.65%[2],内陆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沿海、沿江城市,沿海、沿江城市遂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领头雁。
从空间演化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脉络,设立通商口岸是沿江、沿海地区发生巨变的逻辑起点,然后现代经济沿着水运通道和铁路交通线逐步扩展到内地,在港口与腹地的互动过程中引发区域变迁。中国近代区域经济的发展,大致体现出从重要开放口岸沿河流、铁路、公路与主要的传统陆上道路向内陆腹地逐渐推进的特点[4],这种空间变化在作为过渡地带的内陆省份——河南省表现得非常明显。铁路的筑通,使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愈发不平衡,形成了“发达”“落后”“衰退”三类地区。其中,发达地区多位于铁路沿线;落后地区不但远离铁路而且多位于群山之中;衰退区域则多位于河谷地带。由于铁路的运输能力与作用远远超过河流,所以过去仅仅依靠河流得以发展的那些地区就衰退了[5],铁路成为区域时空和城市功能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进入20世纪之后, 中国的传统产业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在城市渐次产生,中国城市的产业化的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在通商口岸,一些新兴工业城市以及交通枢纽型城市渐次诞生,城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步增强。据统计,中国的工厂总数,1922年约为600余家,1927年增加到约2 000家,1937年则为3 849家,1947年骤增到11 877家,比1922年增长18.3 倍[6]。从个案城市来看,上海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工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1911年仅有工厂48家,1933年有工厂3 485家,1947年为7 738 家。上海的产业工人人数,1894年仅有3万余名,民国时期快速增长,1928年达到22万余人,1946年则达到50万人。1949年,上海产业工人占城市总就业人口的21.8%。1950年,上海市的产业工人总数已经超过商业部门的就业总数(约43.6万人),工业资本额超过了商业资本额(两者比值为54.02:45.98)[7]。如果说开埠之初的上海还仅仅是一座单纯意义上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城市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商业贸易和港口中转贸易层面,但到了民国时期,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成为全国综合性的、工商业并举的经济中心城市。
郑州作为中部内陆地区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其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初期的城市工业多与铁路相关联,带有明显的铁路特色。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附属的一批工厂,是近代郑州工业化的先声。这批工厂主要包括郑州修理厂、郑州机器厂、机务修理厂、电务修理厂以及材料厂等,为铁路营运提供配套服务,同时兼营一些地方业务。郑州一厂(郑州修理厂)建于1907年,初建时规模并不大,厂房面积1140 m2,有汽机2台,75马力电机一台,其他机械29具[8],后有所发展。郑州机器厂,是郑州较早建立的工厂之一,直属北京政府交通部,工厂共有男工100余名,女工20余名,并聘有外国技师[9]。郑州机器厂位于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叉点附近,靠近郑州铁路站场的东部,以便利山西煤炭和铁等原材料的运入,这为兼具冶铁和铁器制造性质的工厂,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发展条件。郑州机务修理厂当时有职员12人,工人216名,主要制造机车应用配件并承担机车、货车的修理任务。郑州电务修理厂建于1914年,共有职员15人,工人119名,全厂占地4000m2,各种修理室、库房等计20间[8],拥有各类电修工具,承担电话、电路、发电机、发动机、轧票机等的修配业务。正是铁路的带动,使得郑州的城市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当然这与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重庆作为中国西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在清末民初时期,其工业基础还较为薄弱。1911年仅有20余家工厂, 2000余名工人,此后缓慢发展,1937年其工厂总数也只有77家。随着沿海工业企业大批内迁和西南地区现代交通的整备,到了1945年,重庆的工厂总数骤增为1690家,工人总数已达10万余人[10]。从全国范围来看,1933年前后,工厂数超过100家的城市至少有12个,超过1000家的城市有4个,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城市产业工人总数超过1万人的城市有7个[11],城市现代工业得以快速发展。
苏州的丝织业向来比较发达,到了清末民初时期,丝制品的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推动了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快速成长和丝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据统计,1918年苏州生产纱缎107 040 匹,多数对外销售,外销量占总产量的72.8%,为77 930匹;纱缎的年产值为2 414 250元,其中外销额为1 184 550元,占总产值的49.02%;丝织工人共有16 779名,其中从事外销产品生产的为9 949人,占工人总数的59.29%[12],显示苏州城市丝织业外向型发展的显著特征。
从整体上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产业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到了1949年,中国工业(包括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依然非常低,仅为23%,全国工人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仅为1%,只有少数沿海沿江城市在城市产业化发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工业呈现极端非均衡化发展的态势,全国工业多数集中在上海一地,包括资本、工厂数、工人数以及产值均是如此,上海、天津、汉口、青岛、广州、重庆、无锡等少数几个沿海沿江城市集中了全国80%的工业力量[1],这充分表明了民国时期城市产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
2 民国城市诸多经济部门功能的演化
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还体现在洋行、银行、股票、百货公司等其他经济部门功能的演化方面。近代以降,在中国商业贸易特别是在对外贸易领域,洋行势力普遍扩张,洋行所控制的外向型商业贸易网络,为中国城市现代经济体系的形成及其功能演化打上了特殊的印记。洋行是外国商人在华从事贸易以及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业等的代理行号或机构,除贸易代理和从事商贸经营之外,它还渗透到轮船运输、船舶修建、码头仓储、银行保险等行业,甲午战争之后洋行业务又延及采矿、冶炼、棉纺等工业制造领域。随着西方对华贸易、资本输出及新兴产业投资的增长,洋行势力快速膨胀,活跃在城市经济的诸多领域。在鸦片战争前夕的1837年,外国资本共在华设立洋行150家。到了1894年,全国范围内有552家洋行。此后,欧美国家加强对华资本输出,洋行作为其在华贸易经营、产业投资的代理机构,迅速在中国各大中城市涌现。到了1913年,中国共有3 805家洋行,1930年则达到8 297家[13]。洋行作为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商贸交往及产业经营的载体,按照近代西方商业贸易体制进行运转,它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均是西式的,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与方法被植入中国,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现代性成长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在中国与世界实现初步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中国商业贸易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洋行无疑成为中国商业贸易近代化和对外贸易依附性增长的一个酶体。基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近代商务、金融、航运等专门机构得以建立,公所、行会、钱庄等传统的城市经济组织随外贸关系的发展发生诸多变化,一些新职业纷纷诞生,买办、掮客、经纪人、报关员等新式职业活跃在通商口岸城市的经济舞台上,这些新式机构、职业和商人在商业贸易乃至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洋行贸易相伴,西方国家基于投放过剩资本、追求资本回报的需要,开始在中国开始设立西式银行。我国最先开办外资银行的城市是香港和广州,于1845年兴办了英资银行,上海的外资银行则初现于1847年。1912年,在中国设立的外资银行共有20余家,分支机构85个。此后,外资银行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1936年全国也仅有30家外资银行, 114个总分支机构[6]。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是国内第一家全资中资银行。1910年,全国共有中资银行14家,到了1925年,中资银行发展到158家,1936年为164家,1945年国统区银行达3 489家[14],城市金融业得以快速发展。
伴随大批洋务派军用及民用企业的创办,特别是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一道难题。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资金,成为近代中国企业常用的融资方式。中国最早的股票交易出现于1850—1860年代,上海在1869年就有一些外国商号开始股票买卖及相关业务[1]。1905年,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机构——上海众业公所设立,这是一家由外商创办的证券交易所。而第一家华商创立的证券交易所出现于1916年的汉口,北京、上海华商创业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18年和1920年开业。到了1921年,上海的各类证券交易机构已多达112家,汉、穗、津、宁、苏、甬等地设立的交易所共计也有52家,出现了一股“交易所风潮”[15]。除了虚拟市场的融资渠道之外,实体性质的私人金融机构也为近代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撑。1936年,全国约有钱庄、银号1 500家,典当行5000家,华资银行98家,三者分别占该年私人金融资本总额的32%、19%和36.4%[16],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票据承兑及贴现市场。各类钱庄、票号与银行建立起密切的协作关系,相互拆借、交换、承兑票据,这些实体性金融机构与证券交易机构之间“虚实结合”,共同为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转型提供了多元化的资本融通渠道。
民国初年,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制造业亦得以快速发展,各种洋货、土货充斥城乡市场,广州、上海等城市先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销售业务的大型百货公司。1911年,广州先施公司经营的百货商场开业。此后,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创立,其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达1万余种,营业额在1918年达360万元。同年,上海永安公司成立,投入资本额高达40万元,其1912年的营业额更是高达455万元[17]。天津亦先后创办了劝业场、中原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愈加丰富。进入20世纪后,随着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新式商业机构,各大城市商业从业人员大为增加,现代意义上的商会、协会等经济协作组织纷纷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民国城市经济的规范运行和现代转型。与此同时,旧式的会馆、公所在城市工商业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它把传统的地缘关系与新兴行业融为一体,把旧式的人际关系与职业行规、近代社会契约和民主意识结合起来,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总之,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洋行等商贸平台的建构,证券公司等新式融资系统的初步形成及与银行、旧式金融机构的互动,百货公司在城市的普遍设立,使得民国城市经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融通发展,新旧事物在矛盾冲突中相互融合、互补共进,推动了诸多城市经济部门的设立及这些经济部门功能的演化,进一步推动了民国城市经济的近代化进程。
3 民国城市经济功能变迁促进城市商业发展和消费功能转型
近代工业的导入及其快速发展,使得产业部门对原材料的需求大为增加,工业制成品充斥全国各地,商品流通的路径大为拓展,新式商业应运而生。这些商业机构一改传统商业的产销模式,其商业活动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工业产品,抢占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收购廉价原材料服务,从而使外国产业资本实现了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循环。在上海等大中城市,涌现出诸多新兴商业,这些商业普遍采用经销、包销、代销、拍卖等新的交易方式,开始设立专营性质的批发行号,注重广告宣传,扩大行业影响,进而垄断市场。上海市南京路上的先施、新新、永定等新设商场,通常都有较为健全的簿记制度和纯粹的雇佣制度,并采用新式橱窗装饰,注意商品陈列等[2],这与传统的小农式的自产自销模式存在根本不同。
上海城市人口的扩容,刺激了城市的生产与消费。随着对外开放与五方人口的羼入,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人的消费习俗日趋尚新求奇。诸如印染花布、人造丝绸、针织衫袜、毛料等新式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家,销售量急剧上升。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为上海棉织业、针织业、毛织业与丝绸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伴随城市人口总量的变化,城市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均呈现多元化倾向,消费市场的规模以及消费水平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大量多元异质的移民进入上海,不仅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也刺激消费市场结构向多元异质方向发展[18],这也是民国城市社会日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电车、公共汽车在较大城市逐渐普及,成为近代城市各生产要素沟通、交换的通道和助力器,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渐成规模,对推动商业繁荣和消费升级大有助益。就北京而言,第一家电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21年6月成立,1924年12月正式运行,到了1929年共拥有6条电车线路:“第一路为红牌车,从天桥至西直门;第二路为黄牌车,从天桥至北新桥;第三路为蓝牌车,从东四至西四;第四路白牌车,从北新桥至太平仓;第五路为绿牌车,从崇文门至宣武门;第六路粉牌车,从崇文门外至和平门外”[19]。天津的电车首先出现在老城区,主要原因是老城区人口密集,交通需求迫切。此外,旧城墙的拆除和围城马路的修筑,为天津铺设电车轨道、规划设计行车路线提供了良好条件。1906年2月16日,天津第一辆有轨电车沿四条围城马路开始营运。到了1918年,天津又有5条电车路线先后通车,覆盖整个老城区和俄法、意、日、奥5国租界。天津公共汽车营运较晚,直至1920年代初期才出现提供租赁汽车服务的汽车行,而最早投入运营的公共汽车也是由租赁汽车行创办的。同兴汽车公司于1925年进口数辆旧汽车,在万国桥(解放桥)至河东大直沽之间运行,这是天津第一条公共汽车路线[20]。此后,又有多家公共汽车公司从事客运服务,天津的公共汽车作为北京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部门共投入规模运营的时间较晚,到了1935年6月,共开设7条公共汽车路线:“第一路为红牌车,由东四至西四;第二路为黄牌车,由珠市口至鼓楼;第三路为黄红牌车,由鼓楼至珠市口。第四路为蓝牌车,由天坛至交道口。第五路为蓝红牌车,由交道口至天坛。第六路为白牌车,由东华门过西直门直抵香山。第七路为白红牌车,由香山至东华门经阜成门”[21]。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进一步程度上激发并释放了城市消费需求,提升了城市经济功能。
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的区域中心城市,民国时期已经成为联结京汉、粤汉铁路与长江水运通道交通枢纽城市,工商业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大为增强。随着城市人口的集聚与扩张,造就了由官绅、中产者、产业工人、商品经营者等所构成的中国较早的市民阶层,各阶层居民以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途径与手段不断融入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并成为城市消费和生活的主体。
进入20世纪,中国西南重镇昆明快速成长,其城市的工商业功能及消费功能显著提升。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昆明遂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国际贸易、商货流通的重要节点城市。昆明市商埠总局的设立,加速了商埠区规划设计方案的落实、基础设施的敷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当时的昆明商埠区位于老城南门外,在火车站一带向外延展,银行、洋行、海关、邮局等近代机构均设于商埠区。以商埠区为基础形成的新城区,工厂、商店、旅馆、茶社林立,市面渐趋繁荣,商业功能日渐完善。与之相对,老城区往往保持着传统城市生活节奏,城区发展相对衰落。在这种情势下,实现新老城区的融合发展,就成为民国时期昆明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于是,推倒城墙、填平护城河、修筑环城马路、扩建街道、安装路灯、增设供水排水设施、敷设城市管网成为市政建设的主要内容[22]。从民国时期昆明城市发展的过程来看,其城市新功能——工商贸易功能逐渐得以强化,而传统的城市军事防御功能逐渐丧失,体现出这座西南边陲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城市化发展规律,这是近代昆明城市成长的一个鲜明特点。与此同时,昆明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亦带动城市消费内容的丰富和消费水平的提升。自铁路通车后,昆明一直领风气之先,引领了云南全省的消费潮流。在饮食方面,“近年滇省新人物辈出,或游学自海外归来,或服官由他处返里,舍其旧有朴实之风,而沐新学文明之化。款客时必用洋酒,非此不恭。故一席达数十元,视为恒事”[23];在居住方面,开始追求西式建筑的科学与华丽,比如强调建筑的采光和使用抽水马桶,建筑风格亦追求外在的奢华与时尚;在娱乐方面,电影、舞蹈等休闲娱乐方式开始融入城市生活。昆明早期的电影院主要有“新世界”“大世界”“大乐天”“百代”等,电影作为新的文化传播载体,带给昆明市民以崭新的视觉感受,颇受民众欢迎,“粉白黛绿,弥望市中,电影戏院四座几满”[24]。到了20世纪30年代,昆明又新设立了逸乐电影院、南屏大戏院、大众电影院等多家影院,昆明市民的消费品位及消费水平均得以明显提升。自20世纪20年代起,电影成为中国城市文化消费的一种主要形式,电影院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开设。1927年,中国一共有106家电影院,约68 000个座位,分布于18个城市,其中上海有26家,约占25%。1937年,上海已经有了36家影院[25],民国城市文化消费的现代性取向无疑大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和样态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对民众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引领城市消费转型升级,推动了城市生活的现代转型。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循环系统长期存在,加之落后的交通方式使得长距离大规模的商货流通受到限制,缺乏形成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土壤和充分条件。除水运通道、驿路沿线的一些商业性和手工业市镇之类功能型城市得到有限度的发展之外,中国的传统城市多是基于王权统治需要和军事防御需求而形成的,往往是以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为主导的单一功能型城市。进入近代直至“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功能逐步取代政治功能和军事防御功能而成为城市功能的主体,城市功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可以说,民国城市功能呈现明显的复合化特征,其经济功能日益彰显。
[1] 乐正.城市功能结构的近代变迁[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1):61—69.
[2] 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 冯飞.都市发达之历史的考察[J].东方杂志,1922,19(1):41—53.
[4] 吴松弟.通商口岸与近代的城市和区域发展——从港口—腹地的角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5-8 .
[5] 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M].岳谦厚,张玮,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7]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8] 铁道部铁道年鉴编纂委员会编.铁道年鉴(第1卷)[M].南京:铁道部铁道年鉴编纂委员会,1933.
[9] 东亚同文会.中国省別全志(第8巻,河南省)[M].东京: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別全志刊行会,1918.
[10]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1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12]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108—115.
[13]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4]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的金融市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16]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17]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8]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M](修订版).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19]李福海.北京电车史话[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13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20]京报编辑部.汽车计分七路[N].京报,1935-06-26(07).
[21]刘海岩.电车、公共交通与近代天津城市发展[J].史林,2006(3):20—25,125.
[22]车辚.清末民初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17-120.
[23]钱文选.游滇纪事[M].铅印本,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930:36-37.
[24]云南省档案馆.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25] 代春霞.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中国城市奢侈品消费的变动研究[J].中国物价,2011(10):66-69.
ON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CITIES IN THEREPUBLIC OF CHINA
LIU Hui
(Teaching & Research Section of Provincial Conditions, Hen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Zhengzhou 451000,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market factors such as capital, commodity and servic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city changed and the urban economic function gradually became prominent. Due to the i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y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transformed greatly and the industry structure changed gradually. The modern economic sector had gradually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cities had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political or military center in the past into a complex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modern economy.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economy function in China then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firm and bank, stock, department stores,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other economic sectors and the updating of urban function, and accelerated urban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functi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2017-03-29
2015年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招标课题:郑州城市起源及其发展路径研究——以交通演变为视角(Q2015-3)
刘晖(1972-),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1673-1751(2017)04-0118-07
F12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