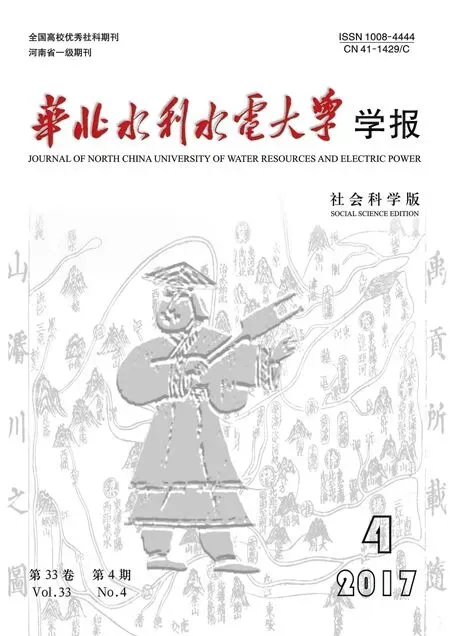治水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2017-02-23贾兵强
贾兵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治水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贾兵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治水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不同时期的治水活动都对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前时期,人类治水活动催生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曙光;夏商时期,我国沟洫农业和灌溉农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渠、都江堰的修建,形成了关中、巴蜀等灌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秦汉时期,秦始皇治水和王景治水,促使了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形成;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中下游成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域;自隋唐开始,随着南方农田水利的迅速发展,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隋唐至宋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基本形成。
治水;中华农业文明;形成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我国的治水活动自始至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治水活动催生了中华农业文明的产生、发展与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中华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与洪涝、干旱灾害作斗争的水事活动历史。
一、史前时期:治水与中华农业文明的肇始
水是生态之要,生产之基。“缘水而居,不耕不稼”[1]212,充分说明了水与农耕定居社会的渊源。史前的人类治水活动不仅包括筑堤建坝,修筑城池,疏浚河道,堆筑高台等防御水患的实践,而且还包括凿井、挖池、修渠以利取水、蓄水、排灌等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活动[2],这些构成了中华农业文明之源。
我国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址,是距今七八千年的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遗址。究其原因是黄河流域土壤肥沃,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是原始农业种植和生产的适宜土壤。因而,处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的重要起源地[3]3。研究表明:裴李岗文化遗址位于靠近河床的阶地上,或在两河的交汇处,或在靠近河流附近的丘陵地带,这类遗址既临河,又有大片可供农耕的土地,是人类生息活动的好场所[4]。如新郑裴李岗遗址位于裴李岗村西北的一块高出河床25米的岗地上,双洎河的水自遗址西边流过,在紧靠遗址的南部折向东流,遗址就在这一河湾上。裴李岗文化是中华古代农业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
对于水井与文明的关系,苏秉琦先生认为,水井与文明起源具有高度相关性[5]323。水井的出现,使人们由以采集渔猎为生到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出现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曙光。到了距今6 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距今5 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农田灌溉用井[6]。水井对于中华农业文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先秦时期:治水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形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的治水历史人物首推大禹。为了制止洪水泛滥,大禹总结父亲鲧的治水经验,采取由“围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利用水自高向低流动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大禹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7]。治水成功后,大禹“身执耒锸,以为民先……尽力乎沟洫”[8]455,带领民众兴建水利,开垦土地,植谷种粮,栽桑养蚕,发展农业生产。“予众庶稻”就是说的大禹率领群众引水灌田,种植水稻。考古工作者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当时的磨制石器铲、斧、凿、刀、镰、镞等,还有炭化农作物粟、黍、稻、大豆,都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改良和进步,耜耕得到了大力推广[9]。另外,通过对“九州”土壤的普查,大禹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地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促使旱作和稻作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沟洫农业的兴起是大禹治水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先民在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向前更进了一步[10]。商代的甲骨文中,描述田间沟渠、农田灌溉的文字说明沟洫农业在中原地区起源很早。西周时期的沟洫被描述为:“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11]就是将一块土地分为呈“井”字状的9块,中央是蓄水的井,其余8块是被渠道环绕的耕地。这种由蓄水、输水、分水、灌水、排水等不同功用的各级渠道所组成的系统,称作“井田沟洫”制度。随着农田沟洫系统的出现,沟洫农业逐渐形成。沟洫农业不仅可以防止水涝为害,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润泽土壤,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有收。沟洫农业的发展对后世耕作方法的演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兴建的灌溉工程诸如都江堰、郑国渠、漳水十二渠和芍陂等,为我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标示着我国灌溉农业文明逐步形成。研究发现:秦国的强盛主要依赖于郑国渠、都江堰、灵渠三大工程;楚国的强大主要得益于孙叔敖修芍陂。如都江堰在《史记·河渠书》被记载:“蜀守冰凿离堆(今宝瓶口),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都江堰具有灌溉、防洪、放牧等多种效益,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都江堰建成后,渠系密布,灌田万顷,“皆可行舟”[12]1407,从而使成都平原“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3]。迄今为止,都江堰仍然在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再如楚国令尹孙叔敖所建的芍陂,距今已有二千五六百年,是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由于芍陂的兴建,使安徽安丰一带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楚国东境出现的大粮仓,为庄王霸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人樊珣说:“昔叔敖芍陂能张楚国”[14],这是对芍陂初期重大作用的恰当评价。章樵《楚相孙叔敖碑》注引《元和郡县志》云:“寿州安丰县有芍陂,灌田万顷,与阳泉陂、大业陂并孙叔敖所作。叔敖庙在陂塘之上。”胡三省注《通鉴·魏纪六》引《华夷对境图》云:“芍陂与阳泉(陂)、大业(陂)并孙叔敖所作,开六门,灌田万顷。”
三、历史时期:治水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发展
“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15]3-4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水利事业、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之间的联系,也表明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是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基础。
秦汉时期,伴随着关中水利的兴修和黄河治理,初步形成了以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为主的农业文明区。秦王嬴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郑国渠动工兴建,渠长约300千米。郑国渠使关中数万亩农田产量大增,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关中成为沃野,被誉为“天下陆海之地。”《史记·河渠书》记载:“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汉武帝在西汉休养生息的基础上,为了巩固关中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扩大水浇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西汉政府在关中地区修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工程,使河湖泉水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形成了完备发达的灌溉网络。如关中最著名的六辅渠,又名“六渠”“辅渠”,是古代关中地区六条人工灌溉渠道的总称。东汉时期,国家经济重心向东转移,水利建设的重点也随之转移至南阳、汝南等郡及淮、汉流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郡太守,任命水利专家许杨为汝南郡的都水椽,负责修复鸿隙陂,从而使汝南郡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中原人口陆续南迁,为南方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技术。伴随着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长足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文化勃兴。东晋时,殷康在吴兴郡乌程县(今浙江省吴兴县)开荻塘,“溉田千顷”[16]1913,为太湖南部和东南部的浦圩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河湖滩地的围垦。当时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除了兴建传统的塘、陂、渠、堰以外,还把治水和治田结合起来,开辟了围田、圩田等。
隋唐时期,黄河中游的农业经济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唐德宗以后,南方水利建设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陂、塘、沟、渠、堰、浦、堤、湖等,大大推动了太湖流域、鄱阳湖附近和浙东三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尤其是当时的太湖农业,逐渐在全国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从政治上看,当时国家的重心仍然在北方,但基本经济区已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转移,其主要原因是唐代水利工程的兴修、江东犁的定型及水田耕作工具的不断进步,这些促使长江流域水稻种植技术趋于精细化,水稻土肥力提高,土地开垦面积也进一步扩大。五代十国时期,以都江堰为中心,成都平原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农业区。
宋朝政权的南移,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宋史·食货志》载“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手中原,故水利大兴”。据统计,宋代全国兴建的水利工程共有1 046项,其中江苏、浙江和福建3省占853项,约占总数的82%,这与《宋史》记载基本吻合[17]。宋朝时,荆江堤防的修筑和垸田兴起,标志着两湖平原农业的开发。“苏湖熟,天下足”,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使之成为全国的粮仓,进而使长江流域的经济繁荣起来,我国的文化中心、政治中心随之南移。
元朝时,国家在河渠和各路设置河渠司,各河渠司负责制定管理灌溉用水的规则。《元史·河渠志序》记载:“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元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修成的广济渠,能浇灌济源等五县的民田三千余顷,国家设置了河渠官提调水利,他们平时负责维护渠堰、验工分水,使广济渠沿线农民咸受其利。
明代以后,长江下游低洼地区普遍采用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即植桑养蚕与池塘养鱼综合经营),大大提高了土地与水资源的利用率。清代,南方沿江湖各州县出现了大量的捍田和圩田,其生产为南方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湖广地区有很多圩田,湖南龙阳县,至少有滨湖围田76 885亩;湖北监利县,清咸丰九年清丈时,有圩田共491处,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顷三十七亩”[18]。明朝中期以后,两湖平原人口渐增,农业开发与水利建设尤为兴盛。宋元至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在湖广地区的出现,与该地区的土壤、水热基础条件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密切相关。
四、结语
我国古代农田灌溉的发展和农田水利的兴修构成了中华农业文明的物质基础。研究表明:秦汉以前,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随着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田水利技术也随之被带到南方,为南方水稻种植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了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唐末,黄河流域作为国家经济重心的格局逐渐丧失。五代宋辽时期,长江流域的基本经济区处于主体地位。元明清时期,海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区兴起,太湖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经济区迅猛发展,加之此前的黄河流域经济,逐步形成了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多种农业经济区共同发展的中华农业文明格局。
[1]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张应桥.我国史前人类治水的考古学证明[J].中原文物,2005(3): 22-26.
[3] 贾兵强,朱晓鸿.图说治水与中华文明[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4] 王吉怀.论黄河流域前期新石器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J].东南文化,1999(4): 6-13.
[5] 苏秉琦.中国通史: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 贾兵强.夏商时期我国水井文化初探[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3):97-100.
[7] 贾兵强.大禹治水精神及其现实意义[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4):28-31.
[8]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 安金槐,李京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J].文物,1983(3):8-20.
[10] 王克林.略论我国沟洫的起源和用途[J].农业考古,1983(2):65-69.
[11] 李根蟠.先秦时代的沟洫农业[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1-11.
[12]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3] 罗开玉.论都江堰与“天府之国”的关系:古代“天府之国”专题研究之二[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53-64.
[14] 许芝祥.芍陂工程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J].中国农史,1984(4):43-63.
[15] 慕天颜.苏州府志:第11卷[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
[16] 乐史.太平寰宇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17] 顾浩,陈茂山.古代中国的灌溉文明[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8(8): 1-8.
[18]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保问题[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3-8.
(责任编辑:王兰锋)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JIA Bingqia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Water contro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prehistoric times, people′s water-control activities create the daw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China′s irrigation ditch agriculture and irrigation agriculture emerge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engguo Canal and Dujiang Weir formed the irrigation areas of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and Ba Shu,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 Qin Shihuang and Wang Jing respectively controlled the water, 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ic center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uaihe River became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gion. Sinc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south, the economic center of the country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south. During Sui and Song dynastie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earl River basin became the economic center of the whole country, which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ater conservancy;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study
2017-03-08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项目“南水北调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2016cx022)
贾兵强(1976—),男,河南汝州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水历史与农耕文明。
K928.4
A
1008—4444(2017)04—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