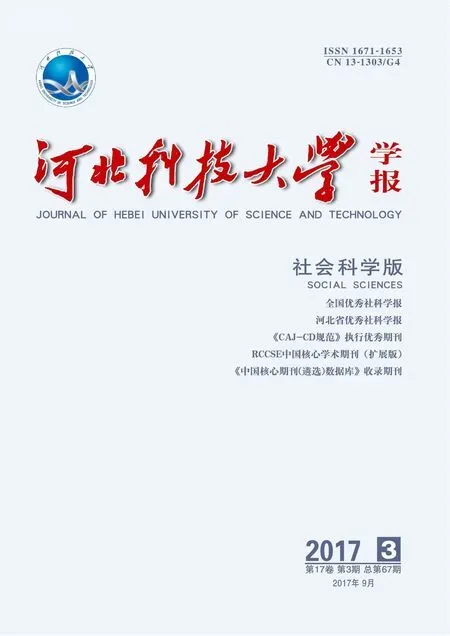论1930年代“左翼”“进城”书写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
2017-02-23盛翠菊
盛 翠 菊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论1930年代“左翼”“进城”书写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
盛 翠 菊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1930年代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多采用政治、经济视角展开社会批判,尤其是“左翼”倾向作家的“进城“书写更为明显。王统照的《山雨》、茅盾的《子夜》《微波》、丁玲的《奔》、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五篇小说构成了一幅1930年代的城乡“流民图”,小说旨在揭露和批判支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外来资本”的“罪恶”,呈现出“半殖民地”国家想象色彩。
1930年代;“乡下人进城”小说;半殖民地;“左翼”
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腐败无能,军阀混战,经济发展近于停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乡村中的封建地主阶层对农民的剥削日趋严重,“外来资本”对中国城乡的渗透日益加剧,城乡经济濒临破产,这种状况在这一时期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地呈现。王统照的小说《山雨》(1933)将叙事的空间大部分放在乡村,重在揭示乡村经济的破产而导致的乡下人“向城而生”,发出的是“乡村破败的哀叹”,这种“哀叹”我们在这一时期的“丰收成灾”类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叶紫的小说《杨七公公过年》(1934)和丁玲的小说《奔》(1933)从背井离乡“奔”向“黄金之城”的路上开始,重在呈现乡下人“城市梦”的破灭。茅盾的《子夜》(1933)《微波》(1935)直接把叙事的空间从乡村转向城市,旨在探讨乡村资本进入城市之后的命运,发出的是城市民族资本破产的哀叹。从乡村到城市,“外来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左右着乡下人的命运,无论进城与否,生存都难以为继,五部小说的并置,勾连起的是一个1930年代乡下人进城的“流民图”, 由此揭示了1930年代城乡社会政治、经济在外来殖民统治下的全面溃败。
一、城乡的溃败:“外来资本”的渗透与占据
对于安土重迁的乡下人而言,“进城”意味着对于土地的逃离,改变内在于血脉之中的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因此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缘何进城”?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们,促使他们背井离乡,向城而生。仔细阅读这些小说我们很容易发现,《山雨》中的乡下人多会和茅盾《春蚕》中老通宝相信陈老爷的话一样,坚信“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小说多把“外来资本”对乡村的渗透和占据作为导致乡村自然经济破产的最根本原因,呈现出“半殖民地”想象色彩。当然,这种“资本”想象还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对乡村的渗透确实很剧烈,并且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对第三世界有所波及……另一方面,‘资本’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影响也有可能使作家们表现出对‘资本’的特别关注。”[1](P68)
《山雨》中“外来资本”的渗透首先体现在陈家庄手工业的破产,小说第一段以一个地窖——“不满一丈八尺宽地下室”为公共空间,叙述了十几个乡下人冬闲时节在地下室编席时的闲谈,村中的首户陈庄主提到放贷利息虽高但自己已无钱放贷,小说借下层贫民宋大傻之口,提出了一个“今非昔比”(农村越来越贫困)的问题,“上去五年,不,得说十年吧,左近村庄谁不知道本村的陈家好体面的庄稼日子,自己又当着差事。现在说句不大中听的话,陈大爷,你就是剩得下一个官差了……”,也就是说连首户陈庄主的日子都不好过,由此引发了这十几个农人的讨论,为什么这二十年来物价飞涨,“乡间无论收成不收成不及以前宽裕”,“上头要钱又急又凶”,陈庄主的结论是“这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奚二叔深有同感,他认为“外国鬼子”是“几十年来作弄坏他们的美好生活的魔鬼”,纸烟、精巧的洋油炉、玻璃的器具等随着德国人修的“铁道”而来,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产品进入乡村,原来“快乐的地方”便因此“渐渐堕坏下去”,失去“古旧的安稳与丰富”。在奚二叔看来,乡村的破败主要是一些“不可抵抗的魔鬼的东西”,“这洋油,洋油灯,便是其中的一件,……洋油一筒筒的从远处来到县城,到各大镇市,即时如血流般灌满了许许多多乡村的脉管。”这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外国资本对于乡村的渗透和占据,他们破坏乡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秩序,导致乡村自然经济的破产。随着这种渗透的加剧,在此后的叙事中,地窖闲置了,人们不再需要手工编织的东西,杜烈也因为“一切都变了”,乡村用不到纺棉花,养蚕养不起,绣花没人定做而带妹妹进城。
这种“外来资本”的渗透而导致的“乡村”破产在1930年代一些“丰收成灾”的小说中也有呈现,可以和这一时期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形成相互印证。在此类小说中,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最具代表性。我们由茅盾的夫子自道来看《春蚕》的创作初衷:“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的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养蚕业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厂’丝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有扶助津贴,且受苛捐杂税之困),丝厂主和蚕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2]《春蚕》虽未直接点明老通宝们“丰收成灾”的原因,但小说中出现的洋纱、洋布、洋油、洋种的茧子、柴油引擎的小轮船等物化的外来“资本”也同样充斥在乡下人的生活之中,成为外来资本对乡村经济进行渗透和掠夺的凭借。老通宝始终不明白“洋鬼子怎样骗了钱去”,但却坚信陈老爷的话,“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他能感受到的是田里的东西一天天不值钱,镇上的东西却一天天的贵,父亲留下的家产逐渐变小到负债,小说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于传统乡村的“资本”渗透。同样,在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旧毡帽们”听说米价从十几跌至五块,非常生气不愿意粜米,店伙计却说“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洋米洋面对于乡村米价的影响,正是因为洋米洋面的“源源不断”,才导致米价的下跌。“外来资本”对于乡村的渗透和占据是方方面面的,洋米洋面对于乡村米价的掠夺只是外来资本掠夺的一种,琳琅满目的“洋货”充斥于乡下人生活之中,“旧毡帽们”本打算用卖米的钱买一些洋肥皂、洋火、洋油、洋布、洋镜子、洋囝囝、洋瓷盆、洋铁喇叭、洋铁铜鼓等“洋货”,这些“洋货”同样是外来资本掠夺的媒介,小说把这些“外来资本”作为乡下人“丰收成灾”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它们直接导致了乡村自然经济的破产。
乡村在“外来”资本中溃败,城市如何?在茅盾的《子夜》和《微波》中,吴荪甫、杜竹斋、冯云卿、李先生都是乡村的富户,他们与奚大有、杨七公公、张大憨子、乔老三、李祥林、王阿二等破产进城的乡下人不同,不是为了“求生”进城,他们是携带乡村“资本”进城,李先生把资本存在“中国兴业银行”,想依赖利息为生,吴荪甫、冯云卿的资本投入了商业运作,这些携带“资本”进城的乡下人的命运是否如其他进城者一样?逃离乡村的“资本”是否可以摆脱外来资本的渗透?我们在吴荪甫、冯云卿、李先生的城市遭遇中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斗争实质是源自于乡村的进城资本与买办资本的斗争,其中的“买办资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依附帝国主义并直接为它服务的资本,是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它靠外国垄断资本的扶持,对本国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3](P56)吴荪甫的失败是帝国主义资本的掠夺,是被“外来资本”收编。同样,小说《微波》中李先生是一个靠收租为生的地主,因米价贱,“收了租来完粮反而贴钱”,为躲避“教育公债”和土匪而被迫进城,进城之后的生活“一天一天弄穷了”。乡村经济破产迫使李先生进城,把全部的资产都存入“中国兴业银行”,靠利息维持城市生活,乡村收租告急和银行倒闭使李先生最终也没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影响。其中的“中国兴业银行”是一个由直系军阀控制的私营银行,1934年因投机失败停业[4](P355),它与吴荪甫的“益中信托投资公司”一样,是“外来资本”挤压下破产的民族资本。因此,李先生的破产与吴荪甫有异曲同工之处。
《山雨》《子夜》和茅盾1930年代的乡村叙事都不约而同地把“外来资本”的渗透和占据作为1920年代以来乡村和城市(乡村进城资本)破产的主导因素,带有鲜明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色彩,某种程度上忽略了1930年代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有点类似于柯文在 “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中论述“帝国主义”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如果从超历史的角度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它确实是一种神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它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我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能力。”[5](P130)换句话说就是外来“资本”的渗透和占据是乡村自然经济破产的一种力量,但不是全部,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乡村自然经济破产的一把“总钥匙”,政府的腐败无能、苛捐杂税的盘剥和1930年代军阀混战、自然灾害导致的兵祸匪患也是乡村溃败的因素。
二、“向城求生”:城市“黄金梦”的破灭
乡村经济在“外来资本”入侵下全面破产,迫使乡下人背井离乡“向城求生”。《山雨》《奔》《杨七公公过年》中的乡下人在进城之前都把城市作为“遍地是黄金的地方”,对他们而言,城市是一个“容易谋生”的地方,“进城”意味着“发财”,对于金钱的追逐成为他们进城的动因。当然,此处的“金钱追逐”大多停留于生存层面,实质上是一种“向城而生”。但这种“向城而生”最终均以“破灭”而告终,小说叙事背后指向的仍然是“外来资本”的罪恶,这种“城市发财梦”破灭的想象与城乡破产的想象一样,仍然是一种“半殖民地”国家想象,作家旨在通过“城市”政治经济的破产来控诉西方殖民入侵所带来的灾难。小说中的乡下人进城叙事在揭露西方外来资本政治经济入侵的同时,也凸显了左翼作家的政治倾向,“反抗”也成为这些作家此类叙事的题中应有之意。
《奔》中的张大傻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对同伴说“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们家里,阔人多得很,找口饭还不容易吗?”同样《杨七公公过年》中上海给杨七公公的印象的确是太好,“同乡六根爷爷就听说在上海发了大财了。上海有着各式各样的谋生方法,比方说:就是讨铜板吧,凭他这几根雪白的头发,一天三两千是可以稳拿的!……”对于像杨七公公一样逃离乡村的乡下人而言,上海是“遍地的黄金,穷人们的归宿”。《山雨》中的奚大有对城市“T岛”的期望是:“或者海那边有洋楼的地方里,有片银子地等待自己与老婆,孩子齐去挖掘……就这样,做买卖,置土地,盖起大人家的好房子。”“发财—做买卖—置土地—盖房子”是奚大有“进城”规划的“发财”四部曲,是作为乡下人的小农意识的体现,“土地”、“房子”仍然是他进城的奋斗目标。较之张大傻们和杨七公公一家,奚大有的“黄金梦”做得更大,但始终离不开乡村,甚至进城之后奚大有还是幻想挣钱返回乡村。这些城市“黄金梦”只是乡下人进城路上对于城市的期许,那么城市是否是一个“容易谋生”的黄金之地呢?
《山雨》是一个多层次的“进城”叙事,进城者的身份、目的以及命运各异,富裕中农奚大有“进城”是乡村破产之后的“向城而生”式进城,富裕中农杜烈、杜英进城成长为城市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赤贫农民宋大傻的进城也是乡村破产之后的“向城而生”,但与奚大有不同的是,宋大傻是“当兵进城”,“乡绅”陈庄主的儿子陈葵园是“乡村学子”进城,他们进城之后是否如预期一样成就“发财梦”呢?对于陈葵园而言,城市是他的发财之地,他并非我们此处讨论的“向城而生”,他的进城实质上有点类似于“子夜”模式。陈葵园是乡绅二代,父亲陈庄主是一村之主,因读了几年私塾而进城,凭投机钻营在县城谋得县教育委员一职,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借办学之名从本村捞到大笔学捐,逐渐成为县城“办事处的要角”,混到“税捐局长”成为“县里的第一个阔人”,这是一个进城“恶化”的乡绅形象,是一个在资本主义金钱逻辑下异化的进城乡下人。陈葵园的进城叙事不是《山雨》的着力点,小说最着力讲述的是奚大有的进城故事,其中穿插着杜烈、杜英和宋大傻的进城叙事。这些农民进城之后都有一个现代性的个体觉醒过程,杜烈、杜英成长为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先进人物,宋大傻在祝先生的影响下也有进步倾向,小说对于奚大有的觉醒有清晰的叙述。奚大有本是一个传统农民,“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向来没有重大的忧虑,也没有强烈的欢喜。从小时起最亲密的伴侣是牛犊,小猪……习惯了用力气去磨日子的生活……”对于进城,奚大有起初认为是“不安本分”的表现,“去外边”“手艺人”都是“不大规矩”的人,因此对于杜烈的进城奚大有并不羡慕,甚至和父亲奚二叔一样认为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表现。卖菜被欺欠债、一步步卖地、父亲去世、兵匪横行等使得奚大有一步步破产,不得不选择“向城而生”。在《山雨》中,进城乡下人的生活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物质生活比乡村而言有所改善,精神层面更有一个现代性的个体觉醒。但城市也并非“黄金”之地,充满着剥削和压迫,外来侵略同样导致他们的城市生活危机四伏,小说结尾处的“大火”预示着反抗之火的熊熊之势。
城市对于杨七公公一家和张大憨子等进城乡下人而言,只是一个“噩梦”,乡村无法生存,城市生活同样难以为继。杨七公公一家靠租地为生,儿子福生不明白“田下的收成,一冬的粮食,凭空地要送给别人家里”,“为什么要这样呢?越是好的年成,越加要我们饿肚子!”福生不甘心,试图组织穷苦兄弟一起反抗,“要吃饭,就顾不了什么老板和佃家的”,杨七公公坚决反对,最终因人心不齐而告失败,无奈之下举家进城。杨七公公进城是来投奔先期进城的同乡小五子和六根爷爷,在杨七公公的记忆中他们在上海“发财”了,没想到他们正打算返乡,城里也无法生活。杨七公公一家衣食无着,码头警察的盘剥、安南巡警的欺凌、恶劣的天气、资本家的压迫致使杨七公公一家在年关陷入绝境,孙子四喜子和杨七公公病死,儿子福生在工厂参加罢工被捕,城市不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与乡村一样同样是一个穷人的“地狱”,小说的第六部分通过对比的手法叙述了一条港两岸的“过年”情景:
只隔一条港。那边,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放着爆竹,高高地举着红绿灯笼儿;口里咬嚼着花生、糖果,满脸笑嘻嘻地呼叫着,唱着各样的歌儿!……大人们,汽车,高大的洋房子,留声机传布出来的爵士音乐,丰盛的延席,尽情的欢笑声!……
只隔一条港。这边,什么声音都没有了!……[6](P128)
小说中的这段对比蕴含着政治话语色彩,阶级的剥削、半殖民统治(港的那边是租界)造成的贫富两重天,过年对于富人是欢歌笑语、宴席、爵士乐,对于杨七公公一家是饥肠辘辘、杨七公公的“升天”、福生的入狱,上海和乡下一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福生在乡下和城市都始终富于反抗意识,他和《山雨》中的杜烈、杜英、祝先生一样,是作品中的希望所在。
丁玲《奔》的进城模式类似于《杨七公公过年》,张大憨子、乔老三、王阿二、李祥林、老龙、小刘6个乡下人因为“乡下也没有饭吃”而进城,“收了一点,都还给东家了,肥料也扣还给他们,家里一粒也不剩。”他们和杨七公公一家一样,把上海看成是“容易谋生活人”的地方,也是来上海投奔先期进城的张大憨子的姐姐、姐夫、李祥林的叔叔而来,没有料想这些先期进城的乡下人在城市无法生存,正打算返回家乡。同样,小说选取一个公共空间“茶馆”作为“反抗”(政治话语色彩)思想的传播场所,通过一位进步工人之口传达出反抗的声音,“没有饭吃,应该问你们东家要,像我们一样,没有工做,也要问资本家要。你们的血汗,一点一滴落在田里,我们身上的肉和血,也不是在车间里一片一片榨给他们了吗……”这种反抗的声音在《山雨》《杨七公公过年》《奔》三篇小说中都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政治话语色彩,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作家的政治、经济批判的意旨,其指向的还是“外来资本”的罪恶,城市和乡村一样都难免“半殖民地国家”破产的命运。
三、“子夜”式进城:“都市逻辑”下的“国家”想象
在1930年代的“进城”想象中,《子夜》中的进城故事不同于《山雨》《奔》和《杨七公公过年》,一来是因为进城者的身份不同,二来是进城之后的命运遭际迥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对“城市”的想象不同,呈现出独特的“子夜”式进城模式。《子夜》中的进城者在进城之后都有一个被城市现代性“收编”的过程,他们在短时间内背离了乡村文化,成为城市的“新贵”。四小姐惠芬、七少爷阿萱、恶少曾家驹、屠维岳的都市化过程,地主后裔、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实业救国,乡绅冯云卿的城市投机等都体现出城市现代性对进城乡下人的改造。茅盾笔下这些人物身上所表现出城市化过程可以说是一种“骤变”,很少有渐进的过程,唯一坚守封建传统文化的吴老太爷以“死亡”方式呈现其封建性的“短命”,由此彰显出的是茅盾自身鲜明的价值取向:都市逻辑。传统封建乡村只是现代城市的附属,当二者遭遇时,乡村被裹挟进入城市发展逻辑之下。其中的“上海”想象承担的是双重“国家”想象色彩,其中既有此类小说叙事通常的“半殖民地”色彩(小说的进城乡下人和乡村资本在城市的命运遭际仍无法摆脱政治经济殖民入侵所带来的“失败”命运),也有茅盾“都市逻辑”下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想象。
这种“都市逻辑”首先通过进城地主后裔、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上海创办实业来呈现,走的是发展城市民族工业的路径。吴荪甫与通常的进城者不同,他是一个海归,是从更大的“城”(西方)归来的实业救国者。小说对于他的乡村背景只是交代父亲吴老太爷、七弟、四妹一直住在乡下,因为乡下暴动无奈进城。乡下老家“双桥镇”是吴荪甫多年苦心经营的“双桥王国”,除了土地还有米厂、当铺、钱庄等,乡村是其城市资本运作的“根”,双桥镇农民的暴动迫使吴老太爷携带他的“金童玉女”七少爷阿萱和四小姐蕙芳进城,吴老太爷的死亡和双桥镇产业的破产彻底割断了吴荪甫乡村封建的“血缘”关系。在这个人物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留学欧美的资产阶级现代民族资本家形象,其封建根性仅在家庭专制上有所体现,在工厂管理和资金运营方面吴荪甫更多呈现的是现代人的特色,总体而言这是一个近乎西化的现代资本家,这在现当代文学的“进城者”中是非常少见的。比起吴荪甫来,小说中的冯云卿则具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假道学”的伪善一面。小说对于他由一个封建地主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投资人的过程是借助“教唆女儿使美人计”这一经典情节来展现的。冯云卿是一个乡下土财主,是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素以“诗书传家”而自诩,靠“水磨工夫”收租放债、剥削农民而发家,过惯了的是“稳稳靠靠收租放债”的生活,因为乡村的土地改革风暴而进城。进城之后的冯云卿进入公债投机市场,成长为一个资本主义投资人。在金钱和封建伦理道德之间,冯云卿选择抛弃传统人伦,放弃人性,为了追逐金钱,这个传统的地主卸下了“诗书礼仪”的假伪善面孔,纵容姨太太在外荒淫无度,无耻地将自己的“风月”经验传授给女儿,教唆女儿冯眉卿使“美人计”色诱买办资产阶级、公债大王赵伯韬以换取金钱,封建地主的传统伦理道德在资本主义金钱逻辑之下彻底崩塌。
《子夜》中的都市逻辑在吴老太爷身上体现的也最明显,小说中唯一顽固不化的吴老太爷被茅盾安排在进城之时迅速“风化”,封建文化在面对现代城市时不堪一击,和“进城资本”一起呈现出全面溃败之势。《子夜》以吴老太爷进城为开场,小说中的吴老太爷是最早“风化”的一个进城者,他是封建传统文化的象征。吴老太爷因为乡村的“匪患”而被迫进城,对他而言,目睹儿子的“离经叛道”倒不如死了好。小说一开场就让这个封建文化的执着守护者以“死亡”形式完成对于封建文化的皈依,城市以充满现代质素的因素而大获全胜。
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膦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我们可以从上述对于城市的描述中看到鲜明的城市现代性因素:钢架桥、电车、电灯、广告……,吴老太爷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城市现代性冲击之下一命呜呼,以《太上感应篇》来表现对城市文明的极端仇视,但这种坚守在作者笔下是不堪一击的,他的死亡宣告了封建传统在遭遇城市现代性时的彻底落败。《太上感应篇》已经无法阻止城市现代性的步伐,看着子辈们的现代生活,封建传统的守护者宁愿死也不愿意目睹儿子的“离经叛道”。吴老太爷是作为《子夜》中“父辈”的代表身份出现的,他的死亡也昭示着封建传统文化的不堪一击。
此外,《子夜》中还有乡下恶绅冯家驹、七少爷阿萱、四小姐蕙芳以及屠维岳等“子辈”进城者,他们进城之后无一例外地迅速被城市现代文明“收编”。吴老太爷的金童玉女——七少爷阿萱和四小姐蕙芳是吴老太爷精心培育的封建文化的传承者,是“吴老太爷《太上感应篇》教育的成绩”,这对封建文化的“金童玉女”刚一到上海“魔窟”就变了。吴老太爷目睹七少爷阿萱贪婪地看着那位半裸体似的妖艳少妇的那种邪魔的眼光,听着四小姐蕙芳说的那一句“乡下女人装束也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这“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毁灭了吴老太爷的希望。屠维岳是吴荪甫的同乡,双桥镇人,是已故吴老太爷赏识的“人才”,其父与吴老太爷是朋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乡村的屠维岳也是一个封建世家的子弟。进城以后的屠维岳一直在吴荪甫工厂的账房间办庶务,因“泄露工厂削减工钱”的事情与吴荪甫有正面的冲突,吴荪甫看到的是一个“白净而精神饱满的脸上一点表情也不流露”,“眼睛却隐隐地闪着很自然而机警的光芒”,此时的屠维岳展现出的是一个现代个体形象,不卑不亢,搬出《工厂管理规定》来回答吴荪甫。得到赏识的屠维岳最终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走狗也是得益于他的胆识和能力,这与通常文学作品中那种有“软骨”病式惟命是从的走狗相比,是一个另类的现代走狗形象,是一个觉醒的现代个体形象。《子夜》中的进城乡下人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小说的地方在于传统性问题,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他们会很快向现代性“投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城市现代性倾向。这与茅盾自己的都市逻辑有关,正如茅盾曾坦言:“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城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了。”[8](P55)正是因为这种都市气质导致茅盾对于城市文明超乎寻常的喜爱,“他将中国城乡的空间结构归之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的结构,即过去现在的历时性构成,两者呈现出彼此代替的关系。既然上海已是现代化了的现代社会,那么相应的,在《子夜》中,古老中国的封建文化已不再构成上海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9](P74)《子夜》中进城乡下人正是在这种“都市逻辑”下呈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的追逐,无论是吴荪甫发展城市工业的梦想、冯云卿的公债投机,还是曾家驹、阿萱等城市化的过程均带有这种“茅盾式”都市想象色彩,从这一点而言,茅盾的“进城”想象又有别于1930年代其他作家的政治、经济视角,表现出对于现代城市的喜爱,带有鲜明的“都市逻辑”。但小说叙事中的这种“都市逻辑”仍然无法遮蔽“外来资本”的力量,吴荪甫的失败和城乡的溃败一样,同样呈现“半殖民地”国家想象色彩,只不过间或透露出茅盾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想象。
四、“进城”叙事背后:政治话语机制的彰显
在1930年代小说的“进城”叙事中,作家对于乡下人进城的动因大都归因于乡村经济的破产,其中“外来资本”的渗透和占据成为罪魁祸首。这些乡下人进城之后的生活同样是举步维艰的(《子夜》中的进城自有其特色),张大憨子等六人和杨七公公一家的城市“黄金梦”仍难免破产的命运,小说在此基础上意在写出农民在走投无路下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意识是1930年代小说受主流文坛“左翼”思潮影响的呈现,这是“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潮,是左翼作家团结广大进步作家,甚而包括部分中间作家共同创造的。”[10](P8)在这一文学主潮的影响之下,1930年代小说创作呈现出朱晓进所言的“政治化特征”,“三十年代许多重要文学作品都明显表露出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同时隐含着一种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它广泛涉及不同的党派、社群乃至个人的政治意愿,并以此为中介,影响和制约着三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11](P3)这一时期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毫无例外也同样具有一种“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书写并发现下层“劳苦大众”的反抗。
对于1930年代文学中的这种书写倾向,杨义有同样的论述,“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则以阶级论的历史透镜,在社会的血泊中发现了‘大众’,而且是被挤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劳苦‘大众’。”[10](P1)乡村经济的破产中进城求生的乡下人就是杨义所说的“大众”,这些“大众”在“阶级论的历史透镜”中呈现出被压迫者的阶级反抗色彩。乡村自然经济的破产迫使他们进城,而城市同样并非“乐土”,奚大有、杨七公公、张大憨子等人进城之后仍难免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半殖民地”国家想象在此类创作中最终指向的是杜烈、杜英、祝先生、杨福生等人的“反抗”,这种“反抗”在左翼倾向的作家笔下被赋予了革命话语色彩,进城的乡下人作为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当然的无产阶级,他们进城前后同样会遭受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的掠夺,在乡村是地主阶级、封建当权者的盘剥,在城市则变成是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剥削。阶级对立造成的剥削与压迫成为小说中乡下人“革命”式反抗的动因。吴组缃的小说《栀子花》更是借人物“大堂叔”直接表述作者创作的“革命”意旨:“中国的社会,不彻底革一次命,也真没有出路了。经济完全踹在帝国主义的脚下,政治是如此的紊乱,内地的农村社会加速地崩溃,失业的人都市里也没法收容,大家走头无路,不是去当土匪,就是在家里吃老米饭。”[12](P41)
在1930年代的左翼倾向作家看来,正是因为作为无产阶级的被压迫而产生的反抗意识,才最终促使他们起来“反抗”,这是无产阶级个体觉醒的标志。在上述小说中的进城乡下人中,最具革命话语色彩的应该是杜烈、杜英兄妹俩,他们是最早觉醒的先进工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也最具反抗意识。其次是《杨七公公过年》中的福生,小说通过父子两代人的对立和冲突来凸显福生的反抗意识。在老实、本分的杨七公公看来,乡村生活难以为继是“穷人的命”,农民就是“种地”的命,他最担心的是儿子福生的“不大肯守本分”,福生认为自己辛辛苦苦一年的收成凭什么都要送到别人家,试图组织穷苦兄弟一起反抗,虽因人心不齐而告失败,但其反抗意识却一直存在,进城后进入工厂的福生积极参加工人罢工,这是一个觉醒了的下层“工农劳苦大众”的典型形象。同样《奔》的结尾处,张大憨子等进城乡下人在“茶馆”中听到城市工人的“反抗”言论,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他们朦胧中意识到自己应该和城市工人一样起来反抗,小说最后王阿二歪着嘴角狠狠地道出的一句话“孙二疤子你等着!”(孙二疤子是地主),话语背后的潜台词是一种返乡反抗的意味。
小说中的“反抗”意识是1930年代政治话语色彩的呈现,但对于进城的乡下个体而言,却有了现代性个体觉醒的意味,小说通过乡下人的城市“遭遇”所呈现的是一种审美现代性批判立场,旨在揭露和批判“外来资本”的罪恶,正是因为“外来资本”的入侵才导致1930年代整个乡村和城市经济的全面破产。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小说于政治话语机制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之外仍不失“乡下人进城”小说自身独特的创作特征,小说通过进城乡下人的城市失败命运(吴荪甫、冯云卿等)表现出对于“国家现代化”的疑惧,话语背后彰显出的是一种审美现代性批判立场。茅盾的“都市逻辑”是个例外,表现出对城市物质现代性的追逐之势,在这种“都市逻辑”之下,乡村是传统的、封建的,而城市是现代的,充满了“Light,Heat,Power”,这种现代城市取代传统乡村的价值趋向是符合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逻辑的,小说中的上海承担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现代”意义的载体,城市逻辑在此等同于国家想象逻辑与现代化逻辑。但茅盾小说中这些进城乡下人个体命运的失败也同样让我们窥见了作家对于现代城市的复杂态度,其中也不无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味,凸显了“半殖民地”国家想象的复杂之处。
(注:本论文得到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1]丁 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茅 盾.我怎样写春蚕[J].青年知识, 1945,(3).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经济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4]张宪文,方庆秋,等.中华民国史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5](美)柯 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叶雪芬.叶紫代表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7]茅 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8]茅 盾.风景谈[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9]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D].杭州:浙江大学, 2006.
[10]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计 蕾.吴组缃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Discussiononthe"Semi-colony"NationalImaginationintheNovelsof"CountryPeopleEnteringtheCity"fromthe"Left-wing"Perspectivein1930s
SHENG Cui-ju
(School of Humanities,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18, China)
The novels of "Country People Entering City" in 1930s written und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were influenced by the "left-wing"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 in 1930s. Wang Tongzhao'sShanYu, Mao Dun'sMidnightandMicroWave, Ding Ling'sBen, and Ye Zi'sYangQiGonggongGuoNianall belong to this category. These novels try to reveal the invasion "evil" of "foreign capital" by means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nkruptc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which is a "semi-colony" national imagination.
1930s;the novels of "Country People Entering City"; semi-colony; "left-wing"
I206.6
ADOI10.3969/j.issn.1671-1653.2017.03.010
1671-1653(2017)03-0065-08
2017-07-16
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SJB1025);徐州工程学院2016年度科研基金培育项目(XKY2016104)
盛翠菊(1970-),女,江苏赣榆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