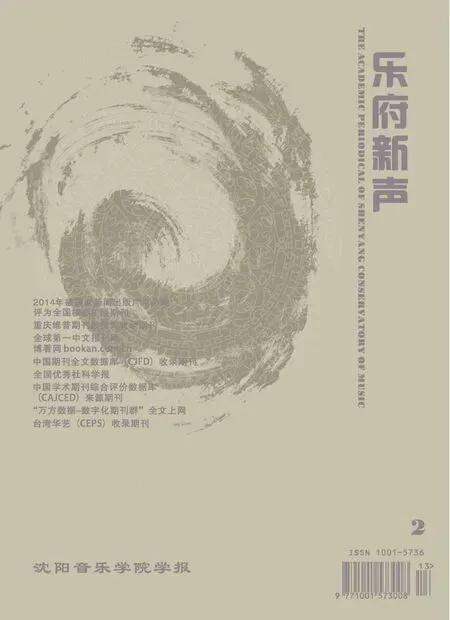中国传统多声部器乐的产生与发展
2017-02-14王硕
王 硕
中国传统多声部器乐的产生与发展
王 硕[1]
本文以中国传统器乐为研究对象,以器乐作品中的多声部发展为研究内容,通过对发展脉络的梳理,明确中国传统多声部器乐的产生与发展背景,更深层次地了解其风格形成的根源,从而为具体乐种、乐曲和乐器的多声部形态研究奠定基础。
多声部音乐/多声形态/发展脉络
一、早期社会中的乐舞
人类究竟是神模仿自己的样子并从动物中提取了善恶两种情感造出来的生物,还是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说是由猿进化而来?神究竟是真实存在过,还是现代人的精神臆想?唯心主义的有神论与唯物主义无神论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不可置否的是,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似乎只围绕四件事情而进行——祭祀、狩猎、农耕和战争,农耕和狩猎是满足基本生活的必要保障,有了粮食和肉才能够保障充足的体力,而有了体力才能够继续捕获猎物和抵御外来侵略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那么,左右粮食收成的气候便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的人们认为,气候是神的心情好坏和对人类庇护与否的体现,所有的猎物和粮食一部分作为自食,一部分必须作为向神的献礼以祈求风调雨顺,因此,对神的臣服、崇拜和依赖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导致了该时期音乐的体裁多为祭祀乐,题材多是狩猎和战争,其功能意义远大于娱乐意义。
祭祀乐的表演场合多于室外或较为宽敞的室内,那么,如此空旷的空间、如此宏大的题材,必然需要壮观的场面来表现,因此,表演人数众多的集歌、舞、诗、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艺术便应运而生了,以歌拟声、以舞拟形、以诗表意、以乐增加气氛,各方面统筹协调——这种形式被称之为“乐舞”。譬如,尧舜时期长达九个乐章的代表乐舞《韶》便是描写狩猎归来向祖先献上猎物的场面,在歌诗的吟唱和乐器(通常是排箫和鼓类打击乐器)的伴奏下,舞者或身披皮毛,或头插鸟羽来模仿鸟兽动作,由于音乐有九次变化,因此又被称为《九辩》或《九歌》;《咸池》通常在仲春二月农耕播种的季节来表演,用来祭祀主管五谷的西官星以求来年丰收;《濩》则是商代出现的庆贺战功、祭祀祖先的大型乐舞。到了周朝的时候,等级制度更加明确且规则严苛,从黄帝开始流传下来的六个代表性乐舞《云门》、《咸池》、《韶》、《大夏》、《大濩》以及歌颂武王伐纣的《大武》成为了比较固定的曲目,其风格和形式与之前一脉相承。尽管周朝时也出现了郑卫之音、南音、九歌等各地民间歌曲,题材既有描写生活场面和丰收景象,也有刻画爱情和思念等细腻的内心情感,但民间音乐在这时却并未占居主导,也没有发展到如何繁荣的地步,它们还处于主流音乐的边缘地带,属于非正式、非专业的音乐体裁。而这些民间音乐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与祭祀乐相关的印迹,从而具有娱乐和祭祀的双重功能——狂欢的歌舞是庆祝农耕的丰收,而农耕的丰收又取决于天神的庇佑。
无论是祭祀乐还是民间乐,尽管这个时期的乐器和音乐资料只能从考古记载而来,不可能聆听与分析,但人类群居的本性和祭祀乐所需要的宏大场面决定了该时期音乐必然是群体性音乐,既有群体、则必然存在多声;既有人声、有器乐,也必然会存在多声。因此,下文将从乐器构造和乐队编制两方面来论述该时期中国传统音乐中多声形态存在的可能性。
(一)乐器构造
从乐器的产生来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骨制乐器时期
早在夏商之前,在距今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出现了可吹出七声音阶的竖吹骨笛(出土于河南贾湖)和横吹骨哨(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标志着能发出乐音并有固定音高乐器的出现。
2.陶制乐器时期
到了夏朝,陶制乐器制作更为定型,品类也更为多样,主要有吹管乐器埙和打击乐器石磬、鼓、陶钟和陶铃等。埙能够吹出小三度音程,这不仅成为了后来中国多地传统音乐中最重要的音程,也为多声部结合奠定了音程基础。这两个时期的乐器均属单声乐器,音量不大、共鸣不强,其多声手法主要体现于器乐合奏时的音色差异上。
3.铜制乐器时期
周朝时,青铜铸造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铜制或部分铜质的乐器大量涌现出来,已有记载的约70余种,由此而出现了著名的“八音分类法”。[1]将所有乐器按照材质分为金(如钟)、石(如磬)、土(如埙)、革(如鼓)、丝(如琴)、木(如梆子)、匏(如笙)、竹(如箫),谓之“八音”。其中,打击乐器主要有编钟、甬钟、编磬、特磬、扭钟、铜铃等,它们通常体型庞大、发音具有金属的共鸣且余音悠远,更适合用于大型合奏乐中。该时期的弦乐器主要有金属制弦的琴和瑟,吹管乐器主要有笙、排箫和管,所谓“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乐器的多管和多弦造就了在同一件乐器中可同时发出两个或两个以上音的可能——管和弦的数量越多、可同时发出的音便越多,其演奏多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中,最重要的有多管乐器笙、多弦乐器古琴和打击乐器编钟。
编钟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了顶峰,1978年全套65件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也向世人展示了早在公元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制作精良、定音准确的多声打击乐器。一个钟能够在正鼓音和侧鼓音发出两个相距小三度的音角-徵和羽-宫,因此mi-sol-lado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最早出现的四声腔,中间的三个八度更是可以奏出完整的半音阶。四声腔中暗含了小三度/大六度、大三度/小六度、纯四度/纯五度音程,这成为了其它各声部结合的音程基础。由于编制庞大,因此须用数人同时演奏,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编钟可以奏出其音域范围内的所有的和声音程、多音和音并且转调灵活。
(二)乐队编制
至此,除拉弦乐器产生较晚之外,拥有吹管、弹拨和打击乐器且各组别中乐器均已定型定量的“管弦乐队”被基本确立:吹管乐器主要有笙、笛、箫、唢呐和管等;弹拨乐器主要有琴、筝等;打击乐器则主要有钟、磬和各种鼓类乐器等。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乐曲应用不同的乐队编制,如:汉代钟鼓乐队的主要乐器有笙、笳和排箫,演奏时弹瑟击筑,敲击编钟编磬;汉代相和大曲(丝竹乐,细腻抒情)的伴奏乐队由笙、笛、节、琴、瑟、琵琶、筝七种乐器组成,属丝竹乐队,擅长细腻抒情的乐曲;鼓吹乐则与之相反,它属于威武雄壮的西北音乐,因此乐队中以排箫、铙、笳等乐器为主。只不过由于乐器制作的限制、记谱法的缺失和以诗、舞为主导的特质造就了该时期音乐中的多声并没有成为构成音乐形态的主要因素,也缺少必要的设计和明确的规律,以单声旋律为主的多个声部齐奏成为了其多声形态构成的主要手段。
(三)多声形态
1.音色特征
人声与器乐的音色对比、各不同乐器之间的音色差异本身就是多声形态产生的基础,这种结合不仅可以使音色分层,也由于人声生理机能与乐器性能和演奏技术的不同而决定了各声部不可能是同一旋律的完全齐奏,这样,节奏对位便自然产生了。
2.节奏对位
舞蹈有其自身的节奏韵律,而歌唱、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的节奏又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从乐器性能来看,弹拨乐器可以连续演奏更为密集、更为复杂、更多装饰的节奏;吹管乐器则由于受气息控制的原因,不可能过长时间连续演奏过于复杂的节奏,而打击乐器(尤指鼓)通常以间隔敲击的方式来加强乐曲的韵律感,这样便形成了各声部疏密相间的节奏对位。
3.音调特征
既然节奏不同,那么在演奏或演唱同一基础旋律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的装饰变奏,这样,“支声”便产生了。尽管后来西方的多声音乐更多应用模仿和对比的手法,但其实“支声”才是多声音乐的源头,是在群体音乐中自然存在的多声现象。比如,声乐和器乐由于音域、音区的不同,在同时演奏同一旋律时是否会不时出现高八度或低八度的音呢?或者不是八度而是其它音程度数呢?在吹奏笙类乐器时会不会同时吹奏多音或弹奏琴类乐器时同时拨动两根或多根琴弦呢?又会不会将这种无意识应用在单个乐器中的两个或多个音变成有意识,从而将其音程关系提取出来分配于不同的声部呢?在祭祀乐或描写战争场面的音乐中所吹奏的巨大的牛角(只能发出一个音)是否是持续低音产生的基础呢?这些问题我们虽无法完全直接从乐谱或音响加以论证,但答案却是肯定的——乐器构造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各声部间节奏的不同,音域音区的不同必然会导致音高的不同,牛角号必然会出现低音的持续,而多弦或多管乐器也必然会演奏和声音程或多音和音。只不过将这种对多声部的无意识变为有意识并最终形成一整套具体的理论,再将理论反过来应用于创作,还需要在漫长的岁月逐渐发展与转变。
二、封建社会时期的宫廷乐与世俗乐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从秦、西汉、东汉、三国直到明的频繁朝代更替。政权的频繁更替必然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而战争则必然导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停滞,因此,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音乐的风格并没有出现大的转变和发展而是更多与之前一脉相承下来。
(一)宫廷乐
如果说宫廷乐是之前祭祀乐的延续未免稍显牵强,但二者同属于“表演人数众多的集歌、舞、诗、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同是“以歌拟声、以舞拟形、以诗表意、以乐增加气氛”,同起到服务统治阶级的作用却是一致的,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宫廷乐更华丽、更自由、更倾向于专业音乐创作。
1.魏晋时期的宫廷歌舞乐
魏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喜爱,大型故事歌舞“清商乐”成为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体裁形式之一。曹操尤爱清商乐,他不仅修建了铜雀台专供乐舞表演,还设立了专门的清商署来编撰整理乐曲。该时期的代表作有《踏谣娘》、《代面》等,伴奏乐器主要有篪、箜篌、琵琶、笙、筝、笛、筑、瑟、琴和筝。
2.隋唐时期的宫廷歌舞乐
隋唐时期,宫廷乐继续繁荣并发展至复杂和庞大的顶峰,代表体裁是燕乐和歌舞大曲。这两种体裁是综合了器乐、歌唱和舞蹈,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乐舞,乐队编制更加专业,乐曲结构更为严格,篇幅庞大,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的《霓裳羽衣曲》。该曲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速度由慢至快,分别是:散序(共六段,器乐依次演奏,不歌不舞,散板);中序、拍序、歌头(共十八段,抒情慢速舞蹈,节奏鲜明,或有歌);破或舞遍(共十二段,节奏急促舞蹈,或有歌)。伴奏乐器有坐、立部伎均十二人,坐部伎分三排,每排四人,依次为竖箜篌、直颈五弦琵琶、曲颈四弦琵琶、筝、笙、横笛、排箫、筚篥、铜钹、毛员鼓、细腰鼓和贝;立部伎同样三排,每排四人,依次为笙、排箫、竖笛、铜钹、横笛、筚篥、古琴、筝、曲颈四弦琵琶和直颈五弦琵琶。
3.北宋时期的宫廷歌舞乐
北宋时期的宫廷音乐基本延续了唐代大曲的风格和形式,并常常将其中最精美的段落摘出单独表演,称为“摘遍”。这预示了宏伟华丽的大型歌舞乐已经不受欢迎而小型乐曲则更为流行,宫廷乐逐渐走向衰落。
(二)世俗乐
到了宋代,伴随着大型城市的出现,市民音乐快速兴起,尤其是说唱艺术在这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成为了戏曲艺术的开端。元代出现了更为接近今天戏曲形式的元杂剧,它以折为单位,一本剧通常分为四折或五折,在中间加入过场戏性质的楔子。它有明确的角色分工,有主角和配角,乐曲结构也有严格的规定,伴奏乐器主要有筝、三弦、琵琶、笛子、鼓、板和锣等。从这一时期多声乐器的发展来看,琵琶与古琴的发展最为辉煌,名手辈出,演奏水平和创作水平都突飞猛进——琵琶的定弦由低至高分别为A-d-e-a,用手指急扫四根空弦时被称为“琵琶和弦”,被大量应用于各时期乐曲中。此外,琵琶也可演奏各种和声音程、多音和音、持续音衬托式等多声部织体,甚至是对比式复调型织体,代表作品有明代的《塞上曲》等。古琴的发展在该阶段仍旧繁荣,魏晋时期的《碣石调·幽兰》、《梅花三弄》、《酒狂》和《广陵散》等,隋唐时期的《离骚》都是古琴音乐的经典之作,明代出现了大量古琴谱,其中收录了大量乐曲,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对琴派进行理论总结的重要美学文献。古筝相比古琴来说张弦更多,既可演奏单声旋律,也可演奏和声音程、八音或八音以内的各种多音和音,甚至可以演奏对比式和模仿式复调型织体,它比古琴更适合演奏多声。元代是拉弦类乐器开始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火不思和各种胡类乐器,而到了明代,三弦则开始普及开来并成为了后来的戏曲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此外,笙、箜篌等乐器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顶峰,至此,吹拉弹打四大类乐器全部出现,乐队编制完整而固定——吹管类主要有笛、笙和唢呐;拉弦类主要有各种胡类乐器;弹拨类主要有扬琴、琵琶、阮和三弦;打击类则主要有各种鼓、锣、铙钹和小型的石、磬、铃、钟类乐器。乐器越多、乐队建制越完善,则多声技术越趋向于专业化,这些多声乐器的出现将音乐创作中多声的技术和难度推向了高峰,成为了音乐形态多声化进程的重要基础。
但无论如何,在历经了题材和结构的变化之后,“乐舞”这一体裁的表演形式和在中国音乐中所占的地位却未曾改变,因此,音乐中的多声形态也便由此而一脉相承了——首先,在封建君主制度中,君王大臣全部都是男性,而作为娱乐之用的歌舞之人则多为女性,这与西方该时期重用男声正好相反。生理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女性音色相比男性音色而言缺少低音的共鸣,因此,西方音乐所追求的“协和”是以五度音程为框架、以三度音程为填充的基于泛音结构的多声部协和音响;而中国音乐则更多追求单音的“协和”及歌舞所带来的华美,更加强调音乐的娱乐意义。其次,当西方音乐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作曲技术时,更讲求“礼数”的中国音乐则是更强调乐曲的风格和歌舞表演形式的不同。伴奏的乐器数量、座次,乐曲的结构,器乐、声乐与舞蹈的进入顺序与结合方式等远比各声部之间旋律的异同或配合更为重要。再次,中国的歌舞乐讲究乐随歌走,即:声乐、舞蹈为主,器乐为伴奏的演奏形式,声乐出于追求音调变化和韵味婉转而非共鸣与宏大音响的需要,单声旋律娓娓道来多于多个声部同时演唱;器乐多作为声乐的伴奏更加依附于声乐,因此,以声乐旋律为基础、在各器乐声部同时演奏这一旋律不同变体的支声型织体便仍然是中国该阶段音乐中最主要的多声织体类型。
清朝时期(1636-1912),器乐体裁更是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前的歌舞乐仍然存在,但却从宫廷歌舞逐渐转为民间世俗歌舞,如:汉族歌舞秧歌、花鼓、二人台,少数民族歌舞有藏族的堆谐、囊玛,新疆的木卡姆、云南的阿细跳月等。戏曲艺术继续发展,其中以吸收了元杂剧的曲牌和明清的民间歌曲、舞蹈并结合各地不同方言、不同民俗,在成套曲牌连接方面有一定规律的戏曲“传奇剧”最具代表性,代表作有梁辰鱼的《浣纱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以梆子腔为代表的乱弹剧和以皮黄腔为主、在北京发展起来的京剧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并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纯器乐的民间器乐合奏是最能够体现多声形态的体裁形式,主要有鼓吹乐(吹打乐)、丝竹乐和锣鼓乐三大类,其中包括十番锣鼓、潮州音乐、福建南音、西安鼓乐、辽南鼓吹、山西八大套等。清代荣斋所编的《弦索十三套》(1814年)由于收录乐曲十三部而得名,是清代以弦乐器为主的合奏曲选集。至此,封建君主统治下的中国传统器乐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而乐曲中的多声形态也逐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并最终走向了更为专业化、更为规则化的道路。乐器种类越多样则多声可能性越大,演奏水平越发达则多声手法越丰富,但不变的是对于单旋律的韵味和礼数的追求,因此,“支声”仍然是该时期多声部音乐中最主要应用的织体类型,而温和圆润、没有否定与反抗意识的性格特质也决定了与主要旋律形成对比的其它声部和音乐发展的矛盾冲突始终没有被广泛应用于音乐创作中。
三、20世纪的多声部器乐
客观来看,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应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带来了硝烟和战火,带来了国家的耻辱和人民生活的苦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固步自封和孤芳自赏,打破了我不犯人必得安乐的心理,激发了人们的斗志,从而直接促成了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战争将西方文明和意识形态带入中国,精华也好、糟粕也罢,它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文明大门,而当西方文明从各个方面逐渐渗入生活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心理也必然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最能够表现内心情感需要的音乐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1912年初,孙中山先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至此,中国脱离了封建制度的统治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音乐艺术也开始兼收并蓄而成为了真正的“现代”音乐。
当然,此“现代”非彼“现代”。
从音乐中的多声形态来看,1912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可看作是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多声理论的初级尝试阶段——西方复调音乐的精确对位和主调音乐的调式和声给中国作曲家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富的素材,尽管这时一些作品尚在探索阶段,但却为我们始终追求的如何在借鉴西方作曲技术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中国风味这一创作思路在实践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但由于这时国内政治仍然动荡,大小战事依然频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这就决定了音乐作品的题材必然以政治现实为主,体裁必然是声乐多于器乐(乐器并不普及,而人声则是最便于携带的“乐器”),形式必然是独唱(奏)多于重唱(奏)与合唱(奏),这使得对西方多声理论的借鉴受到了一定局限。
(一)借鉴功能和声的艺术歌曲
“艺术歌曲”的艺术性不仅体现在诗意的旋律中,也体现在钢琴伴奏的写作中——这里的钢琴并不完全处于伴奏的从属地位,而是与声乐水乳交融来共同渲染诗歌的意境,增加歌曲的表现力,二者完美结合才能够被称为真正完整的艺术歌曲。钢琴本身是一件多声乐器,这样,对西方多声理论的借鉴便是必然的了。如,在贺绿汀创作的艺术歌曲《嘉陵江上》中,钢琴伴奏部分便借鉴了西方大小调体系与功能和声的写法,通过长时值并强有力的柱式和弦织体与结构自由、具有朗诵风格的演唱表达了作者内心对家园失去的悲愤与收回土地的决心。此外,在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中也应用了同样的多声部织体。
(二)借鉴对位技术的钢琴小曲
钢琴曲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十分繁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它是民族调式旋律与西方对位技术的结合典范——声部的严格对位和节奏的差时结合无不应用了西方的复调技术,而高低两个声部的旋律却使用了中国五声调式,从而使其成为了探索中西结合道路的里程碑式作品。
无论如何,当西方的音乐理论知识和乐器法被介绍进来之后,在该时期中国音乐的创作中可明显听出对西方作曲技术的学习和借鉴——在多声领域中追求非同度或八度音程所带来的丰满与协和,更强调和声的重要性,也会用复调技术来创作作品,但乐曲的结构、曲调、调式调性等其它方面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中国传统音乐的风貌。作曲家们从一开始便清楚地认识到,单纯的模仿和生硬的搬套只会永远跟人之后而无法超越,只有结合自己的素材创作具有本民族风格的音乐才是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之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音乐也开始步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专业音乐院校的成立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规范的课程以及更多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因此,对于西方多声技术的学习也至此进入了体系化的成熟时期。除艺术歌曲和合唱的创作继续发展之外,各种体裁的器乐曲创作也相当繁荣,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交响曲、协奏曲和各类重奏曲,还有民族器乐曲、歌剧和舞剧等。多声技术的发展在该时期尤为迅速和明显,这其中既有延续中国传统音乐的支声型织体,也有学习西方的复调型织体;既应用西方大小调体系与功能和声的主调型织体,又开始探寻五声性和声的理论依据。
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中西方多声部音乐发展之差异
单声部音乐精致而纤细,它通过个人技术淋漓尽致地发挥来引起听众内心的共鸣;多声部音乐和谐而厚重,它通过群体的配合使音量增大、音域加宽,表现力更为丰富。单声部有单声部的美,多声部有多声部的和,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表现需求需要应用不同的织体类型。但总体来看,音乐的多声化更为受众——它不仅可以使人人参与其中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群体性”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而且它宏大的音量与天然的回声也可以与专业音乐舞台的空间相适应。如果说单声部音乐容易受到空间局限的话,多声部音乐则可以在更大的空间中引起更多人的心理认同与共鸣。
按照欧洲音乐的理论,单声部的圣咏为多声音乐提供了旋律基础,而在圣咏下方附加平行声部所产生的奥尔加农则真正开启了多声部音乐的大门。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在那些无法用乐谱记载下来的漫长岁月中,古希腊、古罗马、中国的夏商周朝,他们的音乐难道都是单声部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在没有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以狩猎和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中,群居是生存的必要手段,有群体必然有合作,有合作必然有音调的交叠,而不同性别的不同音色则必然会成为多声部存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音乐无谓先有单声还是多声,这二者是共同存在的,甚至可以大胆得出结论——多声部应早于单声部,只不过这种多声部是在群体劳作和生活中所产生的无意识、无规则、无精确记录的多声形态而已。这正是樊祖荫先生提到的“大混唱”理论——“原始人在独唱时,当然是单声部的,那么在集体‘和唱’时也是单声部的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原始人类尚无形成固定的音高和调式观念,再加上集体和唱的参加者各人生理条件(如音区、音域、气息及音色等)的不同,所以不可能做到在同一高度(音高)和同一节奏制约下的单声部齐唱。更多的可能是(甚至必然是)出现‘你喊你的,他唱他的’不同音高的‘多声部’大混唱(这里的‘多声’当与‘单声’相对而言。严格地说,这种大混唱尚无通常意义上的‘声部含义’)”。[1]樊祖荫《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因此,音乐的发展是遵循着从无意识多声形态(自由的民间音乐)——有意识单声形态(初级的专业音乐)——有意识多声形态(高级的专业音乐)的进程逻辑,它必将源于多声、归于多声。也就是说,音乐并非是从单声部走向多声部,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多声部的形态,只不过在政治、文化、语言等大环境的影响下,中西方的多声形态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已,这种发展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么,除去地域和语言所带来的差异之外,影响这种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中西方多声部音乐的发展进程
尽管中、西方多声部音乐都遵循着从民间到非民间再回到民间的发展方向,尽管此“民间”非彼“民间”,但其进程却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多声部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始于商周,第一个多声部音乐体裁是歌舞乐,周朝将中国传统之“礼”数发扬光大,奠定了专业音乐教育的基础;春秋战国是中国多声部音乐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时重人事轻天命的“礼崩乐坏”的哲学思想开始萌芽,雅乐的衰落之像开始显现而被称为“淫乐”、“乱世之音”的“郑卫之音”开始出现,它代表着音乐开始注重人文、开始走向世俗。这时的乐器制作精美,编钟、编磬、笙、琴、筝、箜篌、排箫等乐器性能趋于完备,由三分损益法所计算得出的乐律精确而完善,乐器的多样和思维的转变使这一时期的多声部音乐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状态;在唐代的宫廷大曲发展到极致之后,宋代开始全面转向世俗音乐,这也达到了中国音乐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时期。只不过从多声部的发展来看,欧洲很早便将音乐作为一个专业的学科来看待,而中国始终将其作为政权的附属品和娱乐品而存在,无人去研究、去有意识地对其中带规律性的现象予以总结和发展。从唐宋至西乐传入前,在“多声”上无任何进展,历代统治者不需要、也没有基督教这样性质的宗教提供试验场和孕育基地,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在多声部音乐发展中最大的差异之所在。
(二)中西方多声部音乐的发展方向
从古罗马帝国建立之后,中西方多声部音乐开始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影响这种不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信仰的不同决定了审美取向的不同
尽管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中西方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西方自基督教传入起,在经过了短暂的反抗之后便以迅雷之势大肆普及并完全控制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统治阶级也用它来作为同化人们思想并达到巩固其政权统治的工具,因此,西方音乐属于宗教音乐。而中国虽然也有佛教的传入,但其影响力也远远没有基督教那样强大,人们并不以它来解释一切生活现象,也没有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工具,因此,中国音乐属于非宗教音乐。这便决定了人们审美取向的不同——西方人求“异”多于求“同”,讲究事物的矛盾冲突,追求音乐的对比因素;中国人求“同”多于求“异”,讲究事物的贯连发展,追求音乐的意境美。
2.审美取向的不同决定了多声形态的不同
受审美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多声部音乐是以一脉相承的顺序发展为主而并不追求强烈的对比和矛盾冲突,“支声”是最能够体现这一观念的多声织体类型——它是指由同一旋律的不同变体产生一些分支形态的声部,这些声部时而分开、时而合并,时而加花、时而又在节奏上保持一致所形成的织体类型。虽偶尔也有对比旋律所形成的纵向音响,但却主要是作为旋律的协伴声部而存在,是在横向进行的基础上纵向偶合而成的非自觉和声,各声部的横向线条关系远远超过纵向和声关系。西方音乐则更强调纵向和声关系以及主题之间的强烈对比,音乐在矛盾冲突中达到高潮。对比声部的产生是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形成的基础,只不过复调音乐中的对比声部是并列的,而主调音乐则形成了鲜明的声部主次关系。
多声形态的不同最终决定了音乐风格的不同。
(责任编辑 张宝华)
On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part Music in Chinese Traditional Instrument Music
Wang Shuo
This paper focus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 With historical research, especially discuss multi-part music, further clarify generation, development background style root of Multi-part Music in Chinese traditional instrument music, and also provide a firm foundation for study music genre, pieces and multi-part instrument music.
multi part-music/development history
J632.09
A
1001-5736(2017)02-0060-8
[1]作者简介:王 硕(1979~)女,博士,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2012年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重点课题《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课题编号:12AD0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