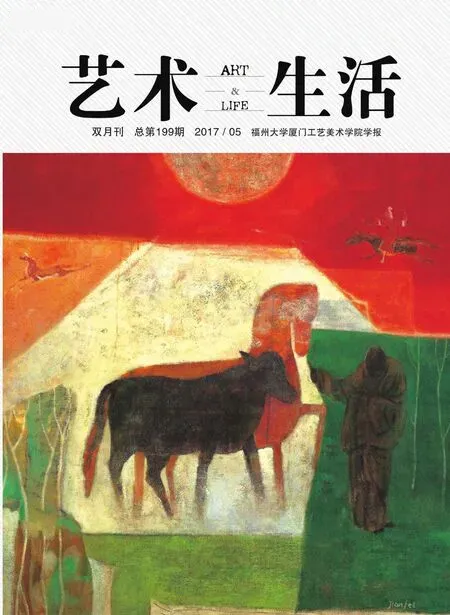大理周城白族扎染艺术刍议
2017-02-13朱青周敏
朱青 周敏
(云南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扎染又称之为“绞缬”“撮缬”或“撮晕缬”,在周城白族民间统称为“扎花布”或“疙瘩染”,是一种古老的染色技术,也是一种民间艺术。[1](P73)即在选好的布料上印设计好的图样花纹,用针线将图案进行缝紧直至成疙瘩后在染色缸中进行反复浸染,随后进行漂晾拆线,呈现出原先设计好图案纹样。由于针线缝制的松紧程度不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浸染效果,给人以不同的视觉享受。其产品花型活泼自如,色彩和谐,富有层次,自然柔美,有晕色、混色效果,是一种极为优雅而高尚的染色品,也是雅致而富有趣味的装饰品。其工艺过程主要有扎花、浸染、漂晾三道工序,是历史悠久的染布工艺,大理周城白族扎染是最为突出和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民间工艺,其富有文化内涵的纹饰特点以及精湛的工艺技巧,使之巍然屹立于我国传统民间艺术之林。
一、村落的文化概况
周城位于大理古城北,白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99%,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聚居自然村。周城是大理地区白族生活习俗、语言、服饰、民俗活动保存最完整的村落,有着“白族民俗活化石”的美誉,2012年1月24日,云南省政府授予该村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在此定居,是白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重要的扎染艺术集聚区。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白族扎染技艺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通过对白族扎染艺术的透视,它不仅反映了白族独特的审美情趣,更承载了白族丰厚的文化意蕴。
二、扎染的历史追溯
周城白族扎染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之一,关于其起源年代至今尚未发现有详细记载的史料和文献。大理白族地区位于我国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交汇处,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比较密切。公元713年至741年间,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大理国,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这为扎染技艺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平台。然而,仅从南诏大理国时期入手来追溯白族扎染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更需向前去搜寻历史遗迹。
据考古发现,洱海地区各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许多形制各异的陶制纺轮等手工纺织器具,其中大理苍山马龙遗址中仅陶制纺轮、纺锤就有车轮形、圆锥形、梯形、珍珠形等40件。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器具,有纺轮,分石制和陶制两种,陶制的纺轮就有5种样式。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制纺轮则多达8种样式。[2](P40)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就已经在进行扎染活动。
在《西洱河风土记》中有记载:“有丝、麻、蚕织之事,出絁、绢、丝、布、麻,幅广七寸以下,染色有绯帛。”[3](P03)在唐初就已经有了丝织业,但那时的工艺技术还不够成熟,后来由于养蚕织锦的发展,促进了丝织技术的发展。今之喜洲,即南诏时期的大厘城是远近闻名的织锦城,《南诏德化碑》中还有“大利流波濯锦”之语。南诏还从中原地区掳掠了一批扎染工匠,由此促进了南诏扎染工艺的发展。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派乐舞队到长安参加《南诏奉圣乐》表演,演员所穿服饰“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革”。①
《后汉书·哀牢传》中记载:“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兰幹细布,织成文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汗。”从唐至南朝宋时期的文献中皆可看出白族的纺织业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以及在当时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在大理地区明清时期的寺庙中发现有的菩萨塑像身衣有扎染残片,还有扎染经书包帕等物。直至民国时期,扎染技术在大理喜洲附近十分普遍,甚至形成了每家每户都在传承扎染技术的格局。[4]现在扎染已成了周城白族农民的重要副业,妇女和女孩一有空就在家门口、摊位上为大理周城民族轧染厂和各个作房手工加工结扎各种产品以便工厂和作房加以浸染,这已成为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三、扎染的工艺选择
周城白族扎染工艺过程涉及到布料、图案纹饰和染料的选择,三者间的和谐运用和恰当选择会让扎染艺术品呈现出非凡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美的享受,并获得身心的愉悦。
(一)在布料选择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原有的本村或周围村自家织造和生产的土布已被机械大生产的纯棉白布所取代,纯棉白布摸上去的手感较好,做成服装后更易于人们所穿,利于吸汗。目前周城扎染的品种主要有服装布料、桌布、床单、窗帘、小手帕、工艺布等。因用途不同,各种面料的尺寸大小、形状、图案也不尽相同。
(二)在图案选择方面。图案是艺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形式。图案艺术造型是以审美为核心,遵循图案造型的形式美法则,由此构成的造型对象才能显示出装饰美感与全新的视觉感受。周城白族民间扎染纹样图案丰富多彩,工艺精湛,题材广泛,内涵丰富,蕴藏着白族人民艺术的精粹,体现了白族人民的智慧和审美观念。
周城作为大理地区白族生活习俗、语言、服饰、民俗活动保存最完整的村落,白族人在获取图案方面是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与喜好所选择。白族扎染图案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它体现了白族人民的智慧和审美观念,蕴藏着白族艺术的精粹,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夺目的光辉。其中,最主要的纹样大致可分为鸟兽动物、花草植物等,但也有自然景观、几何图形和宗教图案等纹样题材类型。动物类纹样有蝴蝶、蜜蜂、鱼、毛虫、蚯蚓、喜鹊、白鹤、凤凰等。其中,蝴蝶纹饰有单体蝶纹、双体蝶纹、四体蝶纹,还有无数蝶纹组成一个圆圈等等,都是蝶纹的抽象演变,是现实蝴蝶的抽象化,由此也成为了周城白族扎染艺术品的主要艺术符号。自然景观类有蝴蝶泉、三塔、苍山及日月星辰、山水河流等。其他图形类有三角花、六角花、八角花、菱形、圆形、齿形、凸字形、凹字形,还有八卦图和福、禄、寿、喜等字体。白族宗教特征对白族的审美思想和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白族的图案艺术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白族受佛教、道教和本主教的影响,各种宗教常用的纹样直接被借用过来表现在白族的图案艺术中。比如佛教特有的宝相花、莲花、如意纹在扎染纹饰中也是常见的。因此,在扎染艺术品的图案方面也含有八卦太极图、佛塔、寺宇、亭阁等表现形式。[5](P52)
诚然,根据不同客户的纹样要求还会有一些新兴纹样。淳朴的白族扎染由于制艺的精美以及图案纹样的丰富深得国内外旅游者的喜爱,并且有90%的产品远销日本,甚至有日本的扎染艺术爱好者专程来周城进行观赏扎染的艺术魅力,并从中学习。由于多受日本旅游和扎染艺术爱好者的喜爱,周城白族人民为满足日本爱好者的需求,并适应国际发展趋势,便在扎染图案纹饰的设计中增添了日本的元素,如日本京都观景图、日本歌舞伎、日本京都塔、日本神社大门、日本式房屋建筑等,均为日本客户要求的图案[6],因此便会在扎染过程中进行设计绘制。
(三)在染料的选择方面。周城扎染的染料选择在过去则主要以植物染料为主,传统的染色技艺就是植物染料的运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世间丝、麻、裘、褐皆具素质,而使殊颜异色得以尚焉。谓造物不劳心者,吾不信也。……蓝靛:凡蓝五种皆可为淀。茶蓝即菘蓝,插根活。蓼蓝、马蓝、吴蓝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凡种茶蓝法,冬月割获,将叶片片削下,入窖造淀。其身斩去上下,近根留数寸,薰干,埋藏土内。春月烧净山土,使极肥松,然后用锥锄(其锄勾末向身,长八寸许)刺土打斜眼,插入于内,自然活根生叶。其余蓝皆收子撒种畦圃中。暮春生苗,六月采实,七月刈身造淀。凡造淀,叶与茎多者入窖,少者入桶与缸。水浸七日,其汁自来。每水浆一石下石灰五升,搅冲数十下。淀信即结。水性定时,淀沉于底。近来出产,闽人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航。其掠出浮抹晒干者,曰靛花。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计数。其最佳者曰标缸。”②一般的植物染料即为板蓝根染料,在染色的过程通过对植物染料的使用,布料的色泽会更加自然和谐,不至于出现过度的鲜泽;同时,对人体也没有危害,并具有消炎等保健作用。但由于大批量的生产,以及色彩明亮、着色快等优势,植物染料已不能满足生产规模的需求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化学染料已逐渐步入周城扎染厂或者私人作坊。
四、扎染的文化意蕴
周城白族在了解和掌握扎染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地将本民族喜好的植物与动物等图案纹样抽象化,形成独特的艺术符号并巧妙地运用在扎染工艺中,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扎染艺术品,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着世代相传的文化积淀;其中还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所在,譬如朴素的劳动感情,乐观的生活态度,美好的理想追求,以及除恶扬善、避邪扶正、和合圆满、吉祥如意等。白族扎染的审美特色不仅表现在材质的秀美和表现技巧的丰富上,还表现在它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
(一)蓝白色调的和谐运用
周城白族扎染的色调以蓝、白为主色调,两种颜色之间过渡自然和谐,给人以宁静、平和的视觉效果。白族是一个喜欢白色的民族,洱海的碧波,苍山的白云和白雪陶冶着白族人民的情操和雅兴,他们认为白色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喜白,以白为净,以白为美,因此把“白”作为自己的族称,成为了白族人民的传统审美意象;蓝色则有希望、淳朴等含义。蓝白色调的结合寓意白族“清清白白,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同时,苍山洱海地区是一块宁静和平的净土,其自然生态是能满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需要的。蓝色的天,蓝色的洱海,蓝色的点苍山,宁静而和平,造就了世世代代在苍山洱海之间生活的白族,培养了白族人民宁静而和平的心安世心态。故此,蓝色亦成为了白族传统审美意象的基调。这也是大理地区苍山雪白,洱海水蓝的艺术再现,充分表现了白族扎染来于民间,来于大自然的深刻寓意。
(二)蝴蝶图腾的农耕祭祀
闻名遐迩的蝴蝶泉在距周城村落一里之遥的西北边点苍山以东。蝴蝶树、蝴蝶花、蝴蝶、化蝶自然就成为了白族人民心中的美好希冀。早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就已开始在此生活繁衍,因此富有古老的农耕文明。周城人多地少,人们为了期盼丰衣足食,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由于自然的不可认知,便将阳光雨露视为神灵的恩惠才使得庄稼富足。因此会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并得到上天保佑,蝴蝶在白族的生活信仰中作为风调雨顺和吉祥的象征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周城白族的扎染艺术品中不乏出现蝴蝶图腾及纹饰。
(三)蝴蝶图案的生殖崇拜
金少萍在其《从传统到现代——大理周城白族扎染》一书中对白族扎染中喜用蝴蝶或蝴蝶纹饰符号做了集中解释:一为蝴蝶象征多子和生命繁衍;二为蝴蝶是美丽的化身;三为蝴蝶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四为花与蝴蝶的共生。文章说到蝴蝶雌雄交配后一次排子无数,因而往往成为多子和母亲的象征,寓意生命繁衍、人丁兴旺。白族地区的孩童至今仍恪守着“不能打蝴蝶,否则母亲的乳房会疼”的古规。
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蝴蝶图腾的崇拜,象征着他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对蝴蝶的崇拜是一种古老的图腾崇拜,它的共性是对生殖的崇拜。白族的蝴蝶崇拜很自然地跟古老的“蝴蝶泉”民间传说以及与此相关的“蝴蝶会”(每年农历四月十五,白族青年男女幽会于蝴蝶泉谈情说爱)有关,也与白族“绕三灵”(“三灵”即指“佛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圭寺,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白族民众就会进行为期三天的绕三灵会)有关。[7](P90-91)这些都是生命意识的体现,蝴蝶的多产正适合了人们延续生命的意识和心态。因此,蝴蝶成为周城白族扎染图案中一个吉祥的纹饰,寄托了人们对生育的希冀和追求。
结语
大理周城白族扎染技艺经历了悠久的历史长河,其承载了白族特有的文化记忆与历史特征,传达了白族人民真挚的内心情感与生活希冀。周城白族扎染在制作的过程中倾注了周城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每一件扎染就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传统手工白族扎染工艺扎根于民间,生长于民间,其散发着劳动者的纯朴之美,融合了周城白族扎染艺人的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体现出了一定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民族气质,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品质魅力;扎染艺术品的图案及纹饰也体现了白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及文化意蕴。正因为周城白族人的聪慧才智才使得扎染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扎染艺术品得以丰富和精美,其更是周城白族智慧的结晶、内心的映照,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手工艺园中的一枝奇葩。
注释:
①《新唐书.南蛮列传》卷222
②(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