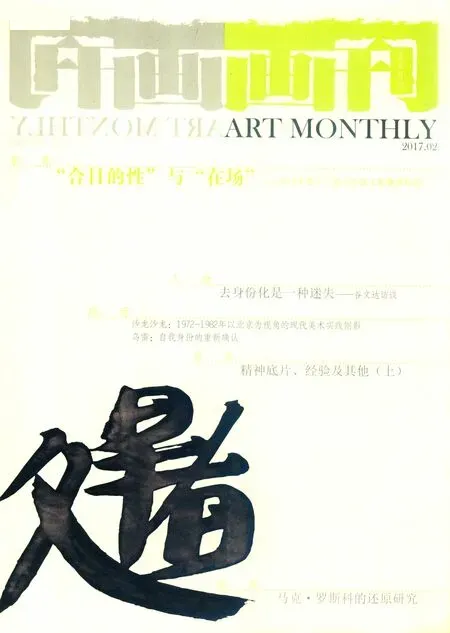精神底片、经验及其他(上)
2017-02-12严善錞张晓刚
严善錞 张晓刚
精神底片、经验及其他(上)
严善錞 张晓刚
编者按:2010年左右,学者、艺术家严善錞在自己的当代艺术家研究和写作领域中纳入了王广义和张晓刚。在他看来,王广义较多关注艺术的观念问题,而张晓刚更关注形式的问题。为了获得更多的素材,2011年,他和张晓刚展开了连续两日的对谈,最终整理成2万余字的一篇长文。这是一次严肃而又不失趣味的对话,它呈现了两位对艺术的认识和态度,其中既有一致,也存在各种分歧。本刊将此文分3期连载,以飨读者。
时间:2011年4月5、6日
地点:北京张家书房
严善錞:去年北京芝加哥大学中心召开水墨画会议的时候,黄专和我谈起当代艺术家的研究和写作问题。他谈起了一些画家,我说我就写你和广义吧,我谈了我的想法。我说这得花上10来年时间,慢慢写,不要抢时间。黄专说,你不在意时间,说得难听点只要离开这个世界前能看到就行了。这让我很感动。我和黄专后来聊的更多的是关于写作的切入点。写广义的部分,我心里有底,对他比较熟悉。写你的部分,对我来说就有种探险的感觉。我想我们还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回想过去写的一些文章,自己真正满意的就是写王川的那篇《蚌病成珠》。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常常和我争论,甚至把我的文章拿过去,一顿乱改。我不太喜欢那种机械的、单向的写作。我希望写完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这些词、这些内容只能放在这个人身上,而且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这个人的身上。选择你和广义两个人作为我的写作对象,是因为我一直在用两个观念考虑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用我们最熟悉的话来说,一个是形式的问题,一个是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广义较多关注的是观念问题,你较多关注的是形式问题。我们现在谈艺术的时候,更多还是谈一些艺术史的问题,我们基本上还是在沿用既往的一些美术史的观念和风格的词汇,也可以说,还是从艺术史的内部来讨论问题,也许这在今天是比较背时的。
大概在1995年前后,张颂仁就几次跟我说你的画有意思,他对你的画做了不少的功课,买了一些擦笔画的书,还问了我一些当时大陆的擦笔画的情况,包括月份牌。我们过去谈传统的转换,只是简单地把传统的元素嫁接过来,就像你之前说的“水墨油画”那样。张颂仁说,他一直考虑如何从近代的传统中找点当代艺术的资源,因为近代中已经有不少的现代因素,而且它们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成了传统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当然,这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与他的香港生活经历有关。在1995年爱丁堡艺术节的时候,他要我写一篇文章,因为我对其中的部分画家还没有找到感觉,我说能否就写一两个人,他说不太好。我本来想沿着他的
“我希望写完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这些词、这些内容只能放在这个人身上,而且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这个人的身上。”思路就你的画往下写,但是后来觉得实在有点为难,只能求范景中老师帮忙。他也是勉为其难,那篇文章的原稿好像还在我那里,下次找到送给你,做个留念。你对历史文献很珍惜。我没有保留书信的习惯,“八五”时期的一些重要书信我现在一封都没有了。
张晓刚:范老师也写中国的当代艺术?我一直以为他主要是研究西方。
严善錞:他写过几篇。当代艺术的写作,大家角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从各种现场活动的经验来写,范老师可能从传统、从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史学经验来写。我可能比较接近范老师的一些观念。关于你的写作,我主要是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转换问题,另一个是血缘背景的问题。听了你前几天的一些闲聊,我有了一个假设的“家庭背景”,我假设一个传统的伦理家庭如何走向现代、走向当代。从艺术家创作的立场来说,广义更多的是站在外面,他的艺术是表达了对艺术史以及当代艺术活动的一些观念乃至游戏规则的看法。你更多的是站在里面,你的艺术更主要的是表达了自己的心理经验。你们两个的成长背景是一样的,文化背景是一样的,但你是在往里走,他是往外走。
我先谈一下关于你的写作框架。就视觉角度来说,可以分几个层面。第一层,是最原始的视觉经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视觉经验。第二层,是梦里面的一种图像经验。我觉得,梦里面呈现出来的图像和我们现实中的图像是有区别的。梦里面不管是照片式的图像,还是电影式的图像,它的感觉往往比现实的更真实。人在做梦的时候,注意力似乎更集中。梦里的恐怖比现实的恐怖更恐怖,梦里的欢乐比现实的欢乐更欢乐。它产生的视觉经验、心理经验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与各种心理学的理论无关。我谈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讨论你的梦境和你作品的关系,因为我看你的作品觉得你肯定是个经常做梦的人。画超现实主义的画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简单的拼合,只是一些空间上的错乱、形式和色彩上的怪诞;另一种是表达自己深沉的心理经验。我觉得你是后一种,这些东西是超越日常经验的,它有一些比较陌生的生理的感受。第三层,我们童年时期的宣传画和连环画的经验,直到后来的苏俄和欧美艺术的经验。第四层,照片和电影的经验。我们过去谈写实主义问题的同时,常常会谈到一个变形的问题,严格地说,写实与变形在西方可能并不是一对普遍使用的形式概念,但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用了,并且还影响了我们的艺术创作和风格,所以,它成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所以我还是觉得用它来讨论比较方便。你的变形不像马蒂斯、毕加索那样从形式和彩色来切入的,你的变形是从广角相机的经验转换过来的。所以,我想把照片这块单独出来。你的作品另一个视觉经验就是电影。有电影经验的人,看你画的时候会联想到这个画面是有前后关系的,有一种暗示在里面,这个和简单地截取一个电影画面去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样,我们可能有了三个方面内容需要讨论,一个是图像的,一个是形式技法的,一个是心理经验的。它们都有自身的逻辑,但在交互过程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我想这样来写作会比较有意思。
张晓刚:那天聊了之后,我觉得,现在的一些批评家和策展人对我,或者说对我这类的艺术家了解不够。因为他们的主攻方向还是观念,做的展览和思考的问题都是和观念、实验相关的,学科性比较强在想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样的艺术家,想给自己定位。因为像广义、培力他们的观念性很强,而且非常清晰。他们一谈黑格尔,几句话就说完了,但是我看完一本书都难弄明白,所以我肯定不属于他们那种艺术家。另外,搞纯形式、搞材料的绘画,对我来说也很枯燥,不可能。我想,在批评家们的眼里那就没有我的位置了,当时国内美术界就是这样。我又没有观念、又没有材料,剩下只有“体验”了,但是这个词弄不好就成了学院派,何况我们当时也生活在学院里面,这样就很为难。我翻看美术史,发现好像还有一类人,他们比较内向,语言太暧昧。但他们很难生效,难成为明星式艺术家。我们权且就称他们为生命派,或者叫体验派的艺术家,从格列柯(El Greco)开始,一条线下来,到超现实主义这样的。我觉得国内这条线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语境下面,你要么就玩观念,要么就玩材料。要是你说话很含蓄、很暧昧,自言自语,说梦话,那基本上没人理。
严善錞: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批评氛围,没办法关注你感兴趣的问题。
张晓刚:几十年来,中国人骨子里一直认为艺术是工具,或者是武器,很难说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甚至很难从生活角度去理解艺术。其实像西南的艺术家,很多都是把艺术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读凡·高的书信他们会激动;读博伊斯,会去理解他,觉得他很了不起。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我是喜欢诗歌、文学、音乐、哲学,“诗书画”这样的东西。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开始比较着急,要生效。当时吕澎提出了“生效”这个概念,大家都在这样追求。所以,对于当时西南的艺术家,面临这样一种选择,你要不然就回到传统里面,要不然就像当时“生效”的人学习。但是,凡是学习的人,我觉得都比较别扭,有点做作,因为不是自发的。不像广义他们,他们有那种语言习惯。当时我想,己这样定位之后,就有了心理暗示,就无所谓了。也清楚别人在干什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我是在这样一个的心态下,画出了《大家庭》。在那之前,画“手记”的时候想得很多很乱。我后来发现这样一个道理,人在想法单纯的时候,才能做出复杂的东西;想复杂了,反而容易表达得肤浅。《大家庭》进了当代艺术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都打算放弃当代艺术、放弃前卫艺术了。
严善錞: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把你归到当代,至少在媒体、宣传、评价方面把你归到前卫圈子。
张晓刚:说实话,我觉得别扭,其实不是我要进某个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圈子,我的定位不是这么定位的,我的定位很自我。我也无可奈何。
严善錞:1994年的圣保罗双年展把你放在哪里?
张晓刚:圣保罗没有类别,就是新中国绘画。
严善錞:新绘画有哪些人?
张晓刚:新绘画有刘炜、方力钧,以及政治波普的几位画家。张颂仁把我和方力钧、刘炜他们划在一个类型。他们是“泼皮”那个展览出来的,都是新一代中国背景下采取的态度,是调侃的态度。我是“貌似怀旧”的,但最终还是一种调侃,策划者们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参加圣保罗展的,还有我画的红卫兵,我犹豫了半天,画了又改,改了又画。我想这个会不会让人觉得故意要这样,但是因为我要注明这是“文革”时期,“文革”那会儿的人都有这个。我刻意回避也不对,我要强调的是“文革”那个时期的一种生存状态和革命的方式。之后,威尼斯双年展邀请来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再弄这个时代,我应该弄另一个时代,是我熟悉的时代,就是知青的年代。现在想想,当时的观念还不太清晰,我后来才发现,我想画的不是那种社会学的东西,我只是想借这样一个背景,表达一种我个人体验到的东西。
严善錞:我跟广义也谈到了这么一个大的氛围,这也是我最初想把你们放在一起写的一个原因。我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不能重复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伦理观念,很多部分还是传统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旧式蒙学,但是很多的价值观还是从传统下来的,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还有《孔融让梨》。然后我们又有些共和时代的民主思想,然后又有毛时代的思想,现在又有改革开放的思想。假如我们把毛时代称为“乌托邦”时代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就像是“拜物教”时代。那天我跟广义谈的这两个概念,他很高兴,他说这也把他的《大批判》的意义给梳理出来了,它其实就是衔接了“乌托邦”到“拜物教”这两个时代。毛时代的“乌托邦”,出现了他的《大批判》中的工农兵形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崇尚物质和名牌。可口可乐和苹果是通过商业的模式,经过设计,经过逻辑推理出来的一种形式,这个是一种拜物教的产物,最后延伸成今天的商品模式;而这边,乌托邦的东西最后通过一种图像,比如通过宣传画这种方式,这两种东西最后遇合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也经历了这样四个时代,或者说受到了这样四种价值观的影响。虽然从我们的知识教育来说,有很大的欠缺。比如说,在旧的时期,我们应该受到“四书五经”那种教育,经史的教育;在共和时期,我们应该受到西方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科学知识的教育。我们受得比较完整的是毛时代的教育,它给我们构建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但是,这种教育中最特殊的是一种“集体经验”,这也正好从某种程度上反衬出你的个人主义的经验。其实当时有种很虚幻的经验,人和人之间虽然搞阶级斗争,但是反而有种集体的感觉,有一种安全感。这种伙伴或者同志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这种经验也慢慢地转化到了我们的内心世界。我刚才谈到了从外部看你的画的四层视觉经验,如果把这四层经验跟现在谈的四个时代的教育经验及其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结合在一起来谈论你的画,可能会写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是唯有我们这代人,或者是说唯有你能画这样的画的一个理由。我当时想在血缘、家庭的概念上做些文章,这与西方是很不同的,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关。我们的生活经历很容易从《家》《春》《秋》一直读到《红楼梦》,并且能体会到里面的情感变化。我和广义也谈过这个问题,谈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层层往外推的,第一层是最亲近的家庭,你的父母兄弟;第二层,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第三层,是一个社团。再外面的就是国家、全人类。今天这些东西都平面化了,家庭、血缘的概念慢慢都淡化了。所以我在想,如果把你的画放在这几个层面来讨论,可能会阐释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但这实在不是我擅长的。你在日记里谈的更多的还是朋友和社团方面,家庭方面很少。
张晓刚:家庭经验在我的画中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严善錞:你的画的原始理由是照片这样一个直观形象,还是一种家庭照片的纪念或者这种特殊的情感促使你持之以恒地这样画下去?
张晓刚:我觉得我的绘画受情绪和心理的影响很大,像《大家庭》这种画肯定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个结果,跟这种心理经验肯定有非常重要甚至是直接的关系。从小对家庭的感受、理解,到后来自己的“家庭”,再到后来和同事们在单位里一起时的家庭。我从小就住在单位,四川美院这样很小的单位,像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家长,权力大得不得了,他的一句话就能改变你,我就觉得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大家庭中,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去了西方,突然觉得西方人都很个体化的,与我们的反差特别强,也很不习惯。记得1996年,我不想上课了。回到成都以后,头天晚上吃了晚饭觉得很快乐,我自由了。第二天早上,我习惯性7点就起了。我想,从今天开始我不用上班,那我干什么呀?突然很不习惯。因为原来是业余画家的心态,上班完了就赶紧画画,突然一下子变成职业画家还真不习惯,觉得离开了那个“家”。对家的体验很有意思,中国人的个人价值从来都是被低估的,甚至是个人价值不允许存在。我之所以画“文革”,就是因为想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看看个人的价值。我最早画《大家庭》,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纠缠,我想用最平静的一种感觉来表达,没有任何情绪化,所以我把笔触去掉,色彩降低。到后来,慢慢发现家庭和个人的关系永远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并不只是集体压抑了个人。但是西方人只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也只愿意认可这一点,强调的是被压抑的受伤的个体。后来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我要表达的其实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而不仅仅是被压抑的感觉,同时他也许还常常在享受这种感觉。这就是大伙曾经迷恋的“好单位”情节。
严善錞:也许,对于这个个人和集体问题的思考,也正是我们的局限性。
张晓刚:对。你看现在80后的一代艺术家,他们就很个人的。他们很习惯从个人的角度看社会,而我们常常习惯从社会的角度去看个人。因为思维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样的个人是走不远的,你不可能做出很极端的事情,你总有一个社会在窥视你的感觉,所以不是真正的个人,是一个假想的个人。真正的个人,才能做到一些极端。现在艺术家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极端呢?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以个人的角度去看问题,甚至他觉得他没有和谁在一起,这可能就是一个改变。但是我觉得我的本质中没有这种东西。这种观念使你没有一个自由的思想,你的所作所为都处在一个整体观念之下。这些还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考虑思想的正确与否,只是先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我是这样来对比着看过去、看自己的。我一直是代表个人主义风格的画家,准确地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那会儿就觉得我要进去个人主义的状态,我要脱离乡土,我生病了,我就画生病,这是对个人主义最简单的一个表达。我从我的生活开始,进入我的个人主义。到《深渊集》的时候,我想超越,自己做一个选择;1989年之后,我又回到现实,寻找一种我和现实之间微妙的、暧昧的关系;再到《大家庭》,我把自己放到家庭中去看,我和
严善錞:你当时阅读卡夫卡这种极端欣赏内心的文学作品,包括像萨特的作品,是否还是想慢慢摆脱一下集体,看看一些个人的东西能挖掘到什么深度?只是短暂的体验,并不是真实的想追求,或者去那样生活?
张晓刚:是,要是真走到那个地步,还是有点可怕和困难,还是要有点距离的感觉。完全的自我和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还是不一样。
严善錞:你一直没有沉迷到这种状态?
张晓刚:我那几年就那样,老是想找一种孤独的感觉。老觉得我一个人出去,我就一定能找到个什么东西,因为我回到家里面,自己也不知道画什么。只能找朋友,画点肖像、画点风景,不过瘾。我老觉得我有什么东西没找到。那会儿,我一个人常常去彝族山区,很远,一待就两个星期。那会儿特别喜欢一个人,不像现在,我从来不一个人出门。
严善錞:你现在有没有因独处而产生恐惧的感觉?张晓刚:不,不会。我已经习惯了。跟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反而受不了,就想躲一躲。因为我在早些年,很孤僻的性格,特别不喜欢集体生活。所以在“八五”时期,是被毛旭辉硬拉来参加群体活动的?“新具象”那个展览,一开始我是反对的,我是觉得艺术是个人的事儿,干吗搞集体活动?我那会儿的性格,是有病的,有点儿自闭。我觉得我的有些思考,有些状态,有时候到达很危险的边缘。那时候就是画“魔鬼”的时期的状态,想寻找一种纯粹的个人,离我们班的同学越远越好。
严善錞:那个时候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寻找与自己的这种心境相对应的艺术样式的?
张晓刚:格列柯和超现实主义大概是那时期的挚爱。那会儿我觉得哲学、音乐、文学提供的氛围也很重要,更能激发人的一种状态。
严善錞:浙美那边那时候有点排斥这个东西。西南艺术群体中,这个现象好像很普遍。
张晓刚:对,都这样。其实到后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点可怕。西南艺术群体,就是很浪漫的一个文艺小群体。当时,我们一个星期要大醉一次、小醉两次,生活很乱,觉得那样才过瘾。一方面觉得很痛苦,一方面又很欣赏那种痛苦。有四年这种状态,所以到后来我觉得要垮了,身体也垮了,世界观也变了。所以我离开了。记得大毛到车站送我,他很绝望。刚开始是我和他一起送朋友,最后他送我。每送走一个人,在站台上喝醉一次,当时就这么一个状态。有时我觉得太情绪了,特别悲凉的一种世纪末的情绪。
严善錞:能将当时这样的一种氛围与后来艺术探索延续下来,并且相对成功的可能只有你,这很可惜。
张晓刚:这代表了中国另外一条非常人文、自我、热情的道路。我后来遇到舒群,我跟他说:“我要感谢你呀,那时候你写的那篇《形而下的冲动》,我们是你的批判对象,你觉得我们是低劣的人。因为你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反而促使我们坚定了要做这样的人。正因为我们坚定了以后,我们反而出来了。”舒群就在那儿笑,说:“那时候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其实我内心是很尊敬你们的。” (未完待续)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