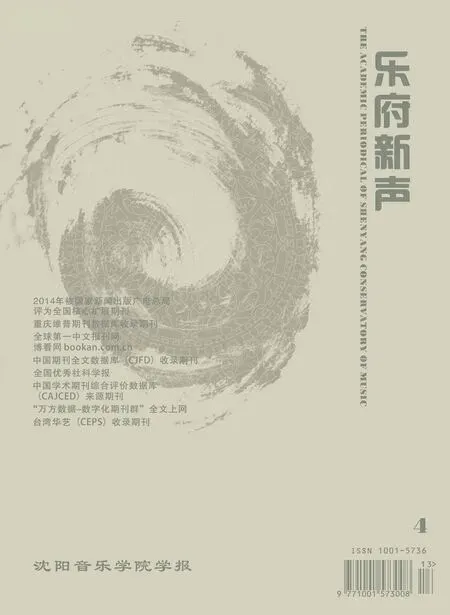红色经典歌剧中的美声角色演唱研究
—— 歌剧《星星之火》中“李母”的音乐形象塑造
2017-02-12白永欣
白永欣
红色经典歌剧中的美声角色演唱研究
—— 歌剧《星星之火》中“李母”的音乐形象塑造
白永欣[1]
有幸参加《星》剧的复排工作,在其中所饰演的李母得到各方面音乐人的好评,面对这样一次跨界的重要演绎,在经典的诠释与创新中,在各个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是受益良多的,本文意在与同行们分享美声唱法在有着传统色彩的红色中国民族歌剧中的演唱技巧调整及跨界演绎的实践心得。
歌剧《星星之火》/音乐元素/时代/民族风格/地域特色/创新/演唱/行腔/行字/中国歌剧/西洋歌剧/肢体语言/表演模式
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新中国的几代人中传唱至今,然而歌剧《星星之火》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历史从不疏漏对于时代经典的纪念!时隔60多年,歌剧《星星之火》的复排使得当代沈音人与老鲁艺的艺术家们真正的“握手”——共创经典歌剧《星星之火》新的辉煌!
一、植根于中国歌剧艺术理念下的红色经典
(一)《星星之火》——在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中走出的红色经典
歌剧是音乐与戏剧的最高综合形式,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经过四百多年的淘洗与雕琢,歌剧走过了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乐派等多个时期,歌剧早就以成熟的姿态呈现了它巨大的表现力与艺术魅力。几百年来一直占据着欧洲音乐生活的领军地位。其概念及各领域的艺术规格都已被完整的定义。随着喜歌剧的出现,欧洲各个国家的歌剧更是百花齐放的局面,遵循意大利歌剧原则,结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以及与本民族音乐元素的有机结合及应用,欧洲各国逐步确立自己歌剧的艺术风格及体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歌剧随着欧洲的文化、艺术一起舶至中国,中国音乐家们受其影响创作出大量的西洋作曲技法与本民族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声乐作品,也开启了中国歌剧的萌芽期。出现了《麻雀与小孩》、《观音》、《荆轲》、《扬子江暴风雨》等作品。1945年的《白毛女》是歌剧在中国“发展期”的标志。其创作集中了当时延安鲁艺的所有力量,创作者们都是五四以来新音乐运动至“新秧歌运动”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经过数十次的修改,在艺术创新上逐步解决了“吸收传统”与“借鉴西洋”的方式方法问题,《白毛女》的创作表现出很多前所未有的特点,永远的成为了红色经典歌剧的重要代表。
新中国的第一部歌剧《星星之火》也是在鲁艺的艺术家们手中诞生的,他们经过了多年战争生活中的艺术实践,对作品中饱含着其特殊的时代特征,以及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乐观的斗争精神有着深切、透彻的诠释。作为第一部以东北抗联及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歌剧,其戏剧创作紧密的围绕着中国文化特质及中国戏剧习惯,大量的采用地域文化与音乐元素,突出其时代性、地域性文化的特征。沿习中国戏曲的辙韵传统、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创作与剧情完美的结合及戏剧化的叙事模式与典型化的人物塑造等等,使《星星之火》成为继《白毛女》之后的中国红色歌剧的重要经典之作!
(二)《星星之火》的传承与创新
1950年,《星星之火》创作完成并首演于哈尔滨,新中国的第一部歌剧由此诞生。原本唱段54首,并且伴有大量的话剧式对白,整部歌剧历时3个多小时,
2015年,时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星星之火》在题材、思想内容、政治寓意,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等方面都是非常合适的作品,并且对于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也是非常好的作品。复排《星》剧也是对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献礼!如果要完整的再现《星星之火》首先存在的问题是——乐队总谱也已不复存在,歌剧整个结构过于冗长,表达的手法不完全符合现代中国歌剧结构等等,需要大量的台词用以交代剧情,而西洋歌剧注重音乐戏剧发展的连续推动性,不需要过分强调剧情细节。《星星之火》的原剧基本就是话剧与歌剧在中国传统戏剧习惯下的结合。在后来几十年的中国歌剧实践进程中,这种模式逐渐被改进,话剧模式逐渐被删减,西洋歌剧模式越来越被强调。
新的创编本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坚持原作的思想理念、音乐基调、时代特征、遵循现代中国歌剧的基本形式、结构及创作手法,将全剧改编、创编为目前的24首曲目。保持了原创的剧情、结构、音乐元素的主导地位。原作多为单曲、对唱与合唱,新作除保留了经典唱段外,提炼主要音乐元素改编、创编出二重唱、三重唱、五重唱、交响大合唱,重新编配了序曲和终曲。使得音乐戏剧冲突连接紧凑、脉络清晰、人物形象丰满。音乐创编团队在不失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对音乐表现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提炼,重新推敲音区、速度、调式、调性,保持音乐中原有的民族风格、地域特色、时代特色,也更适于当代声乐表演者的演唱。并与管弦乐队有机的对接,段落连接自然,主题贯穿始终,人物形象刻画鲜明,整体音乐实现了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化,完成了艺术性、交响性、时代性有机结合的创编初衷。
二、歌剧《星星之火》中李母的音乐形象塑造
(一)音乐元素的时代性与多重性
纵观全剧,我们逐渐对劫夫先生坚持的创作理念、创作方向、创作格调及多层面音乐语言运用,有了更多的,切实的了解及更深切地思考。李母的唱段虽然不是很多,但都是在戏剧冲突的重要转折处,也因此是重要的情感表达部分:
曲4《无边的森林》是李母的首次亮相,但只是在结尾处有一句宣叙调——“村里走来了孙晶石,大家说话要小心。”只是快速走来给大家报了个信,进出简短、迅速,但在情境中极为合理,音区不高,是按照语言的逻辑重音来安排的乐句起落。虽然仅此一句,颇有西洋歌剧宣叙调风格。
曲6《凤儿他妈》是李父被抓走之前与李母的一段对唱,李父的唱段删去了原作的27小节,其中部分唱词为“那窗户眼里有贼风,咬人的狗儿不露牙......,我这一去九死一生难回家。留下的种子你来种,没开的荒地你来挖,出土的嫩苗别叫人糟蹋。”创编后的唱段部分唱词为“凤儿他妈,你要记住我说的话,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凤她长大,别叫那贼风刮到她,别叫那疯狗咬了她,那大山里面有亲人,你叫她上山去种庄稼......”上下的大意都是在嘱托李母安排小凤去找游击队,虽然后者不甚详尽,但其简单、直接的风格合乎李父即将被掳离家的紧迫境况,音乐也延续了原作的东北地方音乐的风格,并通过速度的变化将二人的不同心境及李父被抓走后,李母毅然决定让女儿离家的决心,都交代得极为清晰。
曲7《母女分别》是全剧中最上口、最感人、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旋律。李母在丈夫被抓走之后,又要面对与女儿的分离,音乐的速度逐渐缓冲下来,从沉重的悲痛中回落慢慢转向温柔、伤感、不舍,随着“丫头、丫头,你快走吧,你给妈妈去打天下......”简洁、朴实的唱词开始,表达对女儿的依依不舍,继而在小凤的安慰及坚定的从军的信念中逐渐获得力量,这部分音乐基本保留了原作的主旋律,延续东北音乐的地方色彩,最后部分转为cano重唱,“母女如隔一重天涯,山高路远难相见呀,盼着革命早成功,咱们阖家得团圆。”期间洋溢着痛苦无奈下的控诉、从悲痛中转换出的勇敢与无畏及母女俩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第一幕也在这一曲中将人们引入了那个时代,以及对小凤母女俩未来的命运关注与担忧,成功地完成了戏剧发展的推动。
当李母再度出现,已经进入了第四幕,也就是曲19,这一曲是在原曲的基础上重新创编的歌词和旋律,是一段三重唱,歌词分别描写了不同的内容。小凤从村外高山进场,唱词描述了对母亲、家的思念;对儿时幸福生活追忆以及要为战友报仇的决心。“梆打三更,人更静,悄手悄脚摸进村,雾蒙蒙,看见我的小马架,野茫茫,盼见我的老妈妈。”李母的唱词表达的是对女儿的思念、对战争环境中亲人安危的挂念以及为实现革命理想的牺牲精神。孙晶石出现时的唱词是“盼抓赤匪我心焦急,盼一步登天做人上人,李母是块板上肉,我暗地里观察等苍蝇叮。”三个角色是陆续进入的,同一场景却又不在彼此的情境中,完美地呈现了复调音乐的“奇妙和谐”,声部间不严格的模仿,节奏、织体和速度的变化使重唱的最后部分的音响变得急促而紧张,之后又经过了三次模进,这样除了表达三个人的不同的心境与决心,也为下面的戏剧冲突做了很好的铺垫。这段三重唱的旋律是重新创作的,它保持了原曲的动机,从而与原曲在风格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在其中明显可见中国音乐创作元素与西洋歌剧创作手法的完美结合。这也是这一曲最突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曲22《日本鬼子好狠心》是李母唯一的一首咏叹调,完全采用了原曲,只是配器是全新的。此曲完全取材地方戏曲的风格,节奏、速度自由变化较多、音乐动机激烈,音乐幅度较大、力度变化较多。部分唱词为:“日本鬼子你好狠心,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一道血脉心连心,我怎能骨埋骨来亲埋亲。平地无水,打起了三尺浪,逼着我活埋自己的亲儿......天爷爷呀,地爷爷,这倒是阳世还是阴间。”在高亢、激昂、悲愤、控诉、质问、无奈的复杂情绪交织中,我们看到劫夫先生驾驭音乐冲突的能力,新的配器体现了原曲的动机与风格,使管弦乐队在其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曲23《妈妈不要哭》是作者结合劫夫先生三首曲目重新创编为小凤母女的二重唱,也是李母在剧中的最后一曲。情境是小凤扶起晕倒在地的母亲,唱道“妈妈你不要哭,妈妈你莫悲伤,哥哥和我在队上,报仇雪恨就上战场。”随后小凤先进一拍后李母唱道“丫头丫头我的肉,丫头丫头我的心肝,自那年你离开了家,娘日日夜夜就啃苦瓜。”接下来母女错落的分述离别之后的思念、痛苦与盼望。这段二重唱不再强调对比,而是引入了相似的曲调,以变体卡农的手法展现了母女二人词面意思不同但情感相通的意境,同时也展现了创意曲手法的多声部音乐对戏剧发展的推动力。
(二)跨界演唱的兼容性与二度创作技巧的把握
最初的中国歌剧的演唱受中国传统声乐理念以及中国戏曲演唱的影响,对于声种的分配更是模糊不清的,一直是通过音色来界第角色分配的。随着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美声唱法的植入,声种的概念已完全的进入了中国歌剧的角色分配中。中国民族歌剧也早就开始使用美声歌唱演员,各种声音色彩的介入使其音乐形象的层次感大大加强,戏剧推动的能力也更显灵活。
初识新作,只有旋律谱,单从旋律看到更多的是时代久远所带来的陌生感,以及强烈民间音乐、地方戏曲元素与美声演唱方式、习惯的直面冲突,大有不知该从何处着手的困惑。直至乐队的进入,所有的音乐元素、织体展现后,逐步开始了解了原作与新作有机结合的要旨以及音乐思想。
李母在剧中出场的次数并不是非常多的,主要在一、四幕,但却都处在主人公小凤命运转折时刻,或者可以说都出现在整部歌剧的重要戏剧冲突部分,担当了很重的音乐戏剧重担,因此在声部选择中必然要使用的是戏剧抒情女中音或女高音。李母因年迈虽然不能像女儿一样也投身到战斗中去,但身为救国会会员,跟随丈夫做了很多敌后的实际工作,从内心上讲,她是一个母亲、妻子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因此我们也能从她的音乐中听到她内心的温柔、软弱、悲苦与坚忍。不论是戏剧抒情女高音或女中音,完成上述两方面的音乐表达应该是不吃力的。但整部戏的音乐元素、风格对于美声唱法演员来讲是存在着相当的跨界成份的。那也就是说要用美声的歌唱技巧与声音色彩来融合这部戏的音乐元素、风格。
近些年来在人们的口中常常流行着一些新词,如:“美通”、“民通”、“民美”等等,这些词语虽未被理论界完整的定义,但上述概念下的演唱方式不论是在媒体视频或是剧院现场都大量被实践过了。中国声乐界的历代前辈一直主张“洋为中用”,中国作品的演唱也从未被忽视过,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以腔行字”的概念,歌唱审美的其中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字正腔圆”,然而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着“字”与“腔”的矛盾,汉语的语言结构、咬字方式及习惯与“美声腔”天生就有不对接之处。前人也曾这样说过:“先做传统的儿子,再做传统的叛逆”。“对立”中也必然可寻见“统一”。笔者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熟悉旋律连接中的行腔规律,结合这些特质,寻找“行腔”连接与“行字”的矛盾之处,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都要秉承审美原则,有针对性的对待。例如:《母女分离》的第一句唱词“丫头丫头,你快走吧。”这本是极为口语化的,但作曲者将这一段的音乐速度放慢、字与字之间拉得很开,尽情的使用地域音乐元素,更是让母亲难舍女儿的情绪充斥在其中,“丫(ya)”字归韵在“a”上。(本文中使用的都是汉语拼音)这本是个开放的元音,但后面的“头(tou)”字的辅音“t”是个受阻塞的齿舌音,阻塞音会使“行腔”音色受阻,笔者解决的方法是——缩短这个字从辅音到元音的距离、速度,然后快速放大这个字本应该使用的“腔”的大小来弥补被缩短的距离,这样只有歌者自身知道差别,而听众听起来是极其字正腔圆的,察觉不出变化的。“你”是完全的闭口字,闭口字对“行腔”来说毋庸置疑是存在阻塞的,笔者解决的方法是:当“字”碰到“腔”的同时,拉长这个已经形成了的声线,让它们有足够的空间相融合,以弥补“字”、“腔”不协调的弊端,听起来不言而喻也就字正腔圆了。“快(kuai)”字有两个元音“u”和“ai”这就存在了归韵的问题,汉语的归韵常伴随着元音到元音之间的连接动作,不论两个元音的连接动作是从里向外绕,还是从外向里绕,都要快速的脱离咬字的口腔位置而进入“腔”里去完成,听起来就也会是字正腔圆的了。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融合民族音乐、戏曲音乐韵味与美声声音审美习惯的问题。例如曲22《日本鬼子你好狠心》曲作者采用的完全是地方戏曲的音乐元素,乐句时而铿锵有力;时而顿挫抑扬;时而轻柔婉转;时而如泣如诉。美声的声音表现力虽然也涵盖这些特质,但风格迥异,当然在技术动作上的连接也就不同了,遵循以中国音乐元素为主导的原则,以美声歌唱技巧为支撑,当然这中间也不能存在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问题,而是相辅相承的协作关系,因此,无论是“以字行腔”还是“以腔行字”其过程中夹杂特殊的音乐韵味的任务无疑又是多了一重困难,所秉承的原则一定是“有缺失就一定要有补充”。此处缺了它处补,相辅相承,“字”、“腔”、“韵”协同配合,寻求各部分审美的高度统一,没有缺失,只会尽善尽美。当然,声音的审美与歌唱技艺的程度决定着最后的实践高度。
(三)中国歌剧与西洋歌剧表演冲突中的扬弃
中国歌剧的表演方式除了要遵循民族文化、民族音乐文化的习惯及人文气质,也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中的唱、念、做、打是早已植根在中国戏剧舞台表演中的基础模式,具有表演风格大开大合,民族性情表现鲜明等特点。无论表演者还是观众早已形成了基于这种模式下的审美习惯,中国歌剧的表演当然也不可脱离这种审美。而西洋歌剧的表演具有生活气息浓郁的特质,基本就是现实生活基础下的舞台加工。表演中自然成分较高,人物身份、阶层特质鲜明,表演真实、清新、简约、自然。
作为已经习惯了西洋歌剧表演模式的演员,首先在形体习惯上就与中国年代民族歌剧人物形象大相径庭,西洋歌剧人物无论身份地位,都是腰身挺拔、颈挺肩落,下巴高抬,目宇开阔、眼神豁朗,脚下步履虽跟随节奏,但流畅有秩,绝不在节拍中展示肢体活动刻意的棱角。但《星》剧中李母的形象是已过中年的中国最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一生辛苦劳作、勉强温饱、饱经沧桑、失去丈夫、与儿女离散等状况,这些条件已经可以决定李母的基本肢体状态了,加之生活条件艰苦,服饰粗简,李母的外部形象要比实际的年纪显得苍老,所以李母的上下身肢体都要微现佝偻,但就是这样一个劳动妇女也是革命者的一员,并不挺拔的身躯,凄苦的生活境况仍掩饰不住革命的意志与必胜的信念,这在她的唱段音乐中表现无疑。这一切决定了对于西洋歌剧演员已习惯的肢体语言的颠覆程度。佝偻着上身,微曲双腿,与服饰、年龄贴切的步态,全部要重新改变、设计、组合,适应过程中最困难的应该说心理部分,对于适应古典音乐气质的演员而言,人物塑造大多已通过唱段音乐、声音色彩表达了大半,交由肢体表达的只是必要的部分。除此之外,全剧交给李母一定戏剧冲突重担,使得肢体语言、神情表演的转换等方面的变化幅度都是相当大、相当复杂的。就连多次的摔倒方式都是绝无重复的。其中重点要考虑的是——肢体语言表演与人物音乐语言的相得益彰,既要表现人物肢体形象的特殊规定,又不能超出人物音乐形象表达的力度,否则就会给人——“戏”在音乐之外的感觉。一切艺术都源于生活本身,放弃西洋歌剧与中国民族歌剧的演绎中冲突概念,遵循音乐人物的内心表达,单纯的静默于人物的时代、身份、音乐戏剧要求,以全新的态度认知、体会、实践。最终,既没有完全的类同于民族歌剧表演,也跳脱出西洋歌剧的表演习惯,塑造出“李母”这一坚忍、坚韧、慈爱,勤劳、勇敢并极具时代感的、极具革命意识的中国传统劳动妇女形象。
结 语
在《星星之火》复排的全过程中,笔者的获益远不仅如此,技艺与身、心、灵似被淘洗过而同沐新生,始终沉浸在经典的诠释与创新的兴奋与快意中,跨越时空与60年前的红色经典对话,我们致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歌剧星星之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研究文集[M].沈阳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
[2]编委会主编.中国音乐史.中国歌剧史1920-2000[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3]刘辉主编.红色经典音乐概论[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第二届高等艺术院校美声教学研讨会发言稿与论文[J].西安音乐学院,2016
[5]钱苑、林华著.歌剧概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J642.31
A
1001-5736(2017)04-0144-6
[1]
白永欣(1970~)女,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