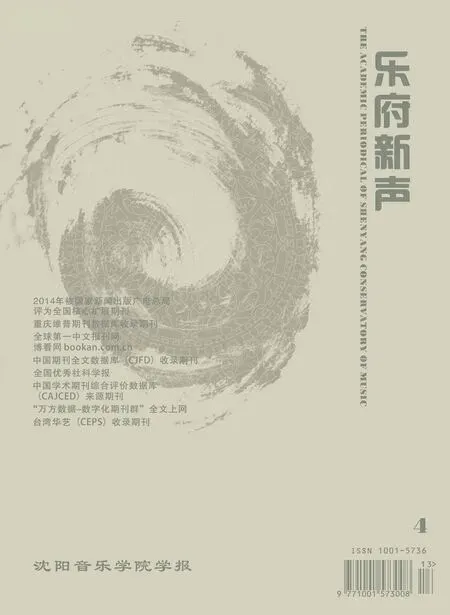混生音乐族性的美学分析(导论)
2017-02-12宋瑾
宋 瑾
混生音乐族性的美学分析(导论)
宋 瑾[1]
混生音乐即跨文化杂交音乐,可分双源混生、多源混生/一度混生和再度混生等类型,因此混生音乐的族性很复杂。其族性混杂,却往往归属某一来源族体。对此,极少有人关注。在混生音乐创作上,存在族性体现缺乏感性效果的现象。今天进行非遗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需要从美学上分析各种混生音乐族性及其相关问题。
混生音乐/族性/感性效果
一、“混生音乐”指谓
“混生音乐”(hybrid music或 mixed music),全球化语境中的用语,亦为音乐人类学和后殖民批评语境中的用语。相对于“原生音乐”(“根源音乐”original music)或“传统音乐”(traditional music),混生音乐是由不同文化中的既有音乐混合而成的音乐,发生在跨文化交流之中。亦可称为“杂交音乐”。有的为双元或双源混合(杂交),有的为多元或多源混合(杂糅)。历史上的原生音乐即传统音乐,与原初族体(ethnos)相关;当下的原生音乐指新出现的音乐品种,如单纯的电子音乐,与新生创作、研究和爱好者族群相关。混生音乐可分一度混生音乐和再度混生音乐。前者由不同的原生音乐混合而成,后者由一度混生音乐和其他音乐再度混合而成。这里涉及“原种”(stock)、“基因”(gene)等基本概念。原初族体在相对稳定而封闭的地理、社会环境生活,产生了相应的原生音乐。无论是人种还是乐种,“原种”意味着最初始的族体和根源音乐(由于追溯的困难,事实上“原种”的纯粹性难以确定,只能在相对意义上确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原种的遗传总是会出现变异,但是只要基因未发生质变,人种和乐种就还是原种。对作为文化事物的音乐而言,用“基因”来描述是一种隐喻,但却有助于说明问题。因为混生音乐意味着乐种的变异。打个比方,如果中国传统音乐是驴,西方古典音乐是马,那么20世纪出现的中西结合的“新音乐”就是骡,它是杂交的物种,基因发生了变异。而在隋唐时期,四夷音乐纳入宫廷的“十部乐”、“九部乐”,被汉化了,就像小溪流或山涧流入黄河,被染黄了;黄河水没有变色,传统音乐没有质变(但却具有可感知可分析的混生特点)。而新音乐则像黄河遭遇了蓝色海洋,变成了“绿色”,是新的混生乐种。详见后述。
二、混生音乐典型
其一,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新音乐”,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结合产生的音乐,如国歌。属于官方音乐及其影响范围的社会大众音乐范畴。其他东方国家的新音乐也如此。
其二,中国学术语境中的“新潮音乐”,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结合产生的音乐。属于艺术音乐范畴。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同或相似的新潮音乐。新潮音乐往往属于专业作曲家群体和相应的学术界。
其三,中国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新民乐”,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产生的音乐。如“女子十二乐坊”,各地旅游文化中变异的乡土音乐;文化产业中的相关音乐。属于流行音乐范畴,与相应的表演群体和粉丝群体相关。
其四,世界传播的民族音乐变型,如扎伊尔、古巴等国的杂交音乐,具有多源多样的混生性,主要归属此两国。再如方丹戈(fandangos),是西班牙、墨西哥、印第安等的音乐,加上流行音乐元素混和而成的音乐,都与文化产业有关,主要归属西班牙和墨西哥。还有弗拉门戈(f l amenco),是由吉普赛人将印度、阿拉伯、西班牙犹太人的音乐混生而成的,主要归属西班牙。在传播上,“归属”仅仅是一种标签。
其五,全球化中新异质化的音乐,如爵士乐、摇滚乐、“第三潮流”等。近年来人们熟知的“摇摆巴赫”也是典型之一,属于再度混生音乐。它们以美国为中心向全球辐射(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各有各的复杂性),各有喜爱的群体, 等等。总之,所有跨文化杂交的音乐,都是混生音乐;它们各自归属某个文化群体。
三、混生音乐的族性和归属
如上所述,特定混生音乐与特定族体相关,反映了族体的特点,体现了族体的精神面貌;它们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时期,为了满足特定族体的需要而产生的。混生音乐的族性很复杂,因为原初族体不断衍变;新族群不断出现。本课题的“民族”采用以下民族学研究成果:种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民族(nation)。种族如初民的部落,今日的家族,是同血缘关系的族体。族群如汉族、蒙族等官方确认的56个民族,是若干种族联合的族体。民族如中华民族,是若干(56个)族群联合的族体。此外,本课题的族性也涉及“文化群体”,如宗教文化群体(基督徒、佛教徒等),它已超越了初始国别、族群和种族,也有相应的音乐样式,其中包括某些混生音乐样式。新近还有“赛伯族”(cybernation),指因特网的网民,具有更大范围的超地理国界和超原始族体的特点,但也具有“亚族体”的特点,即非典型的族体特点。虽然赛伯族是精神族类,身体只有进入虚拟世界(音频视频或间接触觉关联)时才是在场的,但是他们毕竟带有现实中与生俱来的初始族体印记。“赛伯格”(cyborg)指局部电子人,将现代电子装置与人体结合,实现更迅捷的人-机互动;如果加入赛伯族,可视为升级的网络人。网络歌曲、口技打击乐(Beatboxing)、混搭(Mashups)等音乐类型属于这个新族体文化,其中的混搭具有显著的混生性,其他则具有相对于原始族性而言的中性化特征。与族体相关的日常用语如“人民”、“公民”等,多用在政治语境中;相对上述族体而言,它们具有模糊性。
混生音乐的族性及其归属问题,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看,都很复杂。
从时间维度看,一方面跟历史相关(族体历史文化的根脉),另一方面跟时代相关(族体精神因社会变化而变化的特征)。例如中国的新音乐,是20世纪“新文化”“新音乐”运动的产物。国人力图祛除自己族性中的劣根,改变受压迫的状态,被动-主动双向学习西方列强音乐文化,与未完全被抛弃的自身传统音乐结合而成新音乐。新文化主体具有民族传统的根脉,但力图超越而成新族体,接受新思想,设定新目标,甚至从发型、服饰、语言等方面都力图革新。事实上所有的“新”都来自中西结合。中国新音乐作为中西结合的产物,被归在中国一边,就像骡子被归在驴的国度一样。但是它毕竟有马的基因成分,在中性或中立标准(如抽象学理标准)的参照下,也可以归属马的国度。有的新音乐作品由于采用了接近欧洲族群的少数民族(例如新疆各民族)的音乐,结合西方古典音乐创作技法,音乐语言和作品风格显得洋腔洋调,如小提琴曲《红太阳的光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无须费劲就可看出它隶属于“马”的程度更大。还有一种族性归属的说法,即新音乐归属新生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20世纪以来形成一个新族体;新音乐的族性体现这个族体的特点。即便如此,无论是非遗保护还是民族复兴,都指向传统族体音乐文化;比起新音乐来,传统音乐文化这一“元”离西方音乐文化那一“元”更远,更有独特性,它的传承或重建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生态更有利,对国家软实力提升更有利。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从空间维度看,一方面跟多源原生音乐相关(与两种或多种原初族群音乐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具有独特的整体特征,并且在分布上不同于原生音乐的疆界。这跟跨文化传播和融合有关。例如西方小提琴传到印度,出现了“印度学派”,以至于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生前还专程去印度“学习”。再如原本就是混生的爵士乐或摇滚乐,从西方传播到全球,在各地出现了异质化分支。中国的摇滚乐就混合了汉语、五声音乐和国人气质等成分(却削弱甚至祛除了原有的批判精神)。“摇摆巴赫”则是再度混生音乐,即美-非一度混生的爵士乐和欧洲巴洛克时期巴赫的音乐再度混合。由于超越了传统意义的“二度创作”范围,音乐语言和风格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摇滚巴赫”隶属于爵士乐的程度更大(本来如此)。宗教音乐初始作为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部分,传承过程具有稳定性甚至惰性(长期不变或逐渐量变)。随着全球传播,信众成分逐渐混杂,音乐也出现异质化分支;许多分支在地方化的同时出现混生性。如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和东南亚,如今传播到全球各地,已经不再限于东方;其佛事音声在世界各地也有差异。基督教和天主教从西方传播到全世界,信徒和音乐也都出现多样性和混生性。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亦然。群体和音乐都变化的情况下,混生音乐的族性也就超越了原初的族体。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下列论文大多为某个区域、某个混生现象的研究成果。[1]搜索IIMPFT(国际音乐期刊全文库),输入hybrid,得到1592条结果;2016-10-25得到10008条结果;输入hybrid music 得到8845条。限制在学术期刊全文文献,得到1397条。
2009年11月21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民族音乐学第54届年会的亚洲音乐学会分会上,斯蒂芬·布卢姆(Blum, Stephen)作了题为《一个学会和它的杂志:混生性的故事》(A Society and Its Journal:Stories of Hybridity)。布卢姆是受学会委托为亚洲音乐学会成立50周年而写的综述性文章,刊登在该学会学术期刊《亚洲音乐》2011年冬季至春季号[2]Asian Music42.1 (Winter-Spring 2011): 3-23.。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重点探讨亚洲音乐文化的混生性和后殖民性。
L-基多施(López-Gydosh, Dilia)和汉考克(Hancock, Joseph)的论文《美国人及其身份:当代美国黑人和拉丁风格》(American Men and Identity: Contemporary African-American and Latino Style)发表于2009年《美国文化杂志》。[1]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32.1 (Mar 2009): 16-28.论文考察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文化风格,探讨二者之间的音乐关系、社会和视觉识别等,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的流行趋势。
汤因比(Toynbee, Jason)和威尔克斯(Wilks,Linda)发表的论文《英国黑人爵士乐的受众、世界主义和不平等》(Audiences, Cosmopolitanism, and Inequality in Black British Jazz),[2]Black Music Research Journal33.1 (Spring 2013): 27-48.作者通过考察以英国黑人音乐家为特点的爵士乐音乐会观众,认为英国黑人爵士乐包含了实际上被称为世界主义的风格,尽管其中因成分不均等可以划分为若干重要的不同方式。
汤普森(Thompson, Tok)的文章《口技节奏、混搭和赛伯格身份:21世纪的民俗音乐》(Beatboxing, Mashups, and Cyborg Identity: Folk Music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3]Western Folklore70.2 (Spring 2011): 171-193.该文探讨两种新艺术的音乐传统,即口技节奏和混搭,认为从其公共的、变化的形式所显示的迹象看,它们往往跟民俗音乐相关。作者考察审美选择和身份之间的关系,关注点聚焦在“人-机”主题上。赛伯格(局部电子人)、人与机器交互连接的认知功能,所有这一切在21世纪初日益变为现实。
拉波特(Rapport, Evan)发表了题为《彼尔·法恩根的格斯文改编曲与美国的混生性观念》(Bill Finegan's Gershwin Arrangements and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Hybridity)的文章,[4]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Music2.4 (Nov 2008): 507-530.探察了法恩根对格斯文《蓝色狂想曲》、《F大调协奏曲》的管弦乐改编曲,认为它们提供了阐释格斯文作品的基础,即法恩根的改编曲提示格斯文这些作品的风格是以流行音乐技法为基础的。作者认为他们二人的作品突出了美国的混生性观念,尤其是关注“爵士交响乐”、“爵士音乐会”以及种族的理念,等等。
在关于族性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要提到的是英国的斯蒂夫·芬顿的《族性》[5][英]斯蒂夫·芬顿.劳焕强等译《族性》,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是民族学基本概念深度研究的成果,涉及该领域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族体、族裔、种族、族群、民族、群体、人民、族性和文化等等,以及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后者如 “族性”与“文化”的关系。在范围上,有时文化大于族性,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文化具有世界性,超越了原初种族、族体和族性;有时小于族性,如同一族群内部分化的阶级、阶层、语言、习俗和信仰等文化的多样性或差异性。汉族这个族群内部就有这样的多样性或差异性。该书还列举了学者对马来西亚婆罗洲岛北部的沙捞越地区人口族体分析的例子,说明实际的族体划分和族性研究的复杂性。还用前苏联的族体、阶层等事例来说明国家意识形态介入族性分析的复杂性。美国移民的多源性则呈现了除了不同群体人口差异之外的等级差异。作者以纽约黑人为例,指出对这个族群的来历,用“南方移民”比用非洲黑人和奴隶,或非洲裔美国人好得多。而“白人”之间也有差异,如波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等。作者还介绍和分析了“构建论”和“原生论”的争论,涉及“原生群体”(primordial group)和“族裔倾向行为者”(ethnically oriented actor)、移民、“族裔纽带”(ethnic ties)及其具体化的“情感纽带”与“理性筹划”、族裔认同或文化身份认同、归属感与族性话语等重要问题。作者的分析对本课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社会性别的研究领域,西方学界对新出现的人群做了划分和探究,如女性主义、新女性主义、酷儿(queer)等等。这种人群的划分,基于性别观念、取向,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这些新族群拥有自己的音乐观念和选择行为。例如一个被称为“歌剧女王”的男同性恋群体,喜欢借助歌剧女主角的个人性征、相关角色剧情和歌唱特点等来抒发自己的情感。[1][美]露丝·索莉. 谢锺浩译《音乐学与差异》,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75-184页。
在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批评研究领域,部分西方学者集中讨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全球化研究将人群划分为“全球人”(globals)和“本土人”(locals)。前者指能经常跨地域活动的名人或精英,后者指没有能力离开本土的普通人。[2][美]齐格蒙特·鲍曼.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绪论2。福柯则别出心裁使用“全景监狱”(panopticon)、“对观监狱”(Synopticon)的词汇来划分社会权力关系中监视群体与被监视群体,以及媒体中的名人和电视机旁的普通人。[3]同上 .30-31、33、47、50、52。显然,这些划分都不是民族学意义的划分,而是全球化语境中的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层划分。
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族体划分,它的观念渗透到音乐人类学,出现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进而出现“局部局内人/局外人”等划分。本地人并非就是局内人。在后殖民批评领域,学者在殖民时期的宗主国和殖民地划分基础上,探讨殖民者撤退之后,原殖民地人依然延续西方中心主义状况。关于文化身份认同,情况更为复杂。殖民地人从第二代开始就受到西方音乐文化教育,移民西方国家的黑人和黄种人从第二代开始也逐渐蜕变,为此出现了奇特族体——黑皮肤、黄皮肤都掩盖不了“白心”的事实;人种已不能作为族体划分的依据。当今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的黄种人也如此。那么在原殖民地的本土人民又怎样呢?他们也接受西方式教育,文化身份认同是一回事,实际心性又是一回事。这些问题具体涉及到“地方性”(locality)。有学者指出如今的“地方”已经跟过去不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蜕变了。今天仍然将地方当作像过去那样具有整合性的共同体,那仅仅是一种预设或想象。
(二)国内相关研究
关于音乐民族性的研究。在中国,这个问题过去是在政治语境下探讨的。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对革命时期的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艺术的特点概括为“三化”,即革命化、大众化和民族化。首先要革命化,文艺才能作为“有力武器”;革命需要团结大众,所以文艺要大众化;借鉴西方文艺,需要民族化,才能在中国产生作用。就音乐而言,“借鉴西方作曲技术,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作品”已成为音乐家共同遵守的原则。后来的民族性问题探讨,则逐渐转移到学术语境中来。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新音乐的族性归属问题。即便有个别学者提出新音乐可以看成“中国风格的西方音乐”(刘靖之),却无人持续关注,更无人对此进行专门探讨。
关于新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生的“中西关系”问题讨论上。这方面的言论很多,有专著、学术期刊论文,也有学位论文;截至本文写作初始时期(2017年1月),中国知网“新音乐”主题文章将近3800多篇,不一一列举。但是都没有直接探讨族性归属问题,也很少探讨族性的直观有效性问题。
关于新潮音乐的研究,中国知网“新潮音乐”主题文章有180多篇,多集中在“中西关系”的问题上,尤其是西方现代技法的借鉴问题。由于涉及现代作曲技法,研究者多为专业音乐家或学子。另有一些争论集中在现代音乐的可听性问题上。还有一些重大课题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重大规划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器乐创作研究》,其中第二卷梳理了有关新潮音乐的争议。但是对新潮音乐的族性和感性问题的研究也很少或没有。
关于新民乐的研究,中国知网“新民乐”主题文章有230篇左右。由于新民乐与流行音乐有关,所以受到的关注面较大,也得到媒体的较多传播。这个领域曾经集中在一些时尚音乐群体的表演,如“女子十二乐坊”之类。从已发表的言论看,褒贬不一。赞扬者认为新民乐吸取了流行音乐元素,有利于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接触并喜爱传统音乐。批评者则认为它已经不是传统音乐,对青少年有误导作用。
关于“原生态音乐”的探讨,源自中央电视台青歌赛增加的“原生态”组。中国知网“原生态民歌”主题文章有3600多篇,集中讨论其特点和传承等情况。“原生态唱法”主题文章有1450篇左右,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唱法上,即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之外,是否可以再列出一个原生态唱法。特别是将它和民族唱法比较,认为都是民族的唱法,区分在于前者是民间的民族唱法,后者是学院的民族唱法。这些讨论没有吸取现代民族学关于“民族”的划分,概念上比较模糊,有待深入探讨。与本课题关系更为密切的问题是,原生态音乐(上文所说的“原生音乐”)一旦进入了现代传媒,就不再是原生态了。笔者曾经形容它们为“动物园里的动物”或“鱼缸里的鱼”,因为它们脱离了原生环境,进入了人工环境,中性化的环境;从自然文化变成人工文化,功能和价值也随之改变。虽然它们本身不是或不一定是混生音乐,但却由于环境和文化方式的改变而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对它们的研究,有利于探讨族性问题以及本课题其他相关问题,例如“族性”在音乐中的体现等。
近年来,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研究出现热潮。关于族性研究,出现了“中性化”文论。“中性”(neutrality)指没有原始民族性的性质,包括环境的中性化和人的中性化;出现了“中性人”的新指谓,指没有民族属性的族类。相应地,也出现了中性化音乐,即没有民族特征的音乐。中性人还有具体类别,按照信仰、职业、阶层、性趣等划分。[1]宋瑾《中性化:后西方化时代的趋势(引论)——多元音乐文化新样态预测》,交响2006年,第45-58页。这些族群的音乐有不少是混生性的,如上所述的宗教音乐分支、流行音乐等。
五、本项目拟解决的问题、目的与方法
(一)问题:混生音乐的感性特征、族性归属、功能与价值、生存与发展。
其一,混生音乐的感性特征。在两个或多个音乐原形(原生音乐)混生之后出现了新形,它携带着各原形的“基因”。这些音乐原形的特点可以通过理性分析抽取出来,但是在感性上,则具有整体格式塔特征,可以在直观中被感受和辨别。好比骡子,可以分析出马和驴的基因,更重要的是可以被直观为新品种,并从两个原形的参照中被区分开来。但是现代混生音乐(如新潮音乐)在理性分析上尚可找到原形,而在感性特征上却未必听得出来。以至于有不少现代音乐作品呈现出“中性化”特征,无法区分族性。不少国内外作曲家认为个性比族性更重要。也有作曲家认为族性无法抹除,彰显个性的同时,将自然流露出族性。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以利于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其二,混生音乐的族性归属。有趣的是,几乎全世界的混生音乐都被统归到某一个国家或民族。至少起源上如此。我国新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混合而成的音乐,如今已成为主流音乐。在族性归属上,毫无争议地纳入我国现代社会。其他东方国家的新音乐亦然。问题是,为什么骡子一定归属驴,而不是马?爵士乐是非洲传统音乐和美国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及南美民族音乐)混合而成,虽然后来在全世界传播,但依然归属美国。而摇滚乐是在爵士乐电声化的产物,路经是从美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然后传到全世界。归属上笼统为“西方流行音乐”,人们依然以美国为中心。New age里的Ethnic fusion类型,以及后现代主义无机拼贴的“复风格”类型,是一种“拼盘”,难以确定其族性归属。新音乐采用西方管弦乐写作,经常以民族传统音乐为主题。如何区分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民族风格的器乐,与西方作曲家采用中国民歌创作的器乐,二者之间的族性差异?普契尼歌剧《图兰多》中采用了“茉莉花”,无人认为它是中国作品。而中国作曲家改编的“茉莉花”也无人认为它是西方作品。那么音乐的族性是由作曲家的国别族别确定的吗?文化气质在感性上如何界定如何呈现?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音乐文化”观念成为共识,因此需要确认每一“元”。那些事实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的音乐类别,将合并同类项,归入某一元。
其三,混生音乐的功能和价值。混生音乐的起源本身就说明它是应运而生的,它被某个社会某个时代某个族体或人群所需要,因此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例如第三世界的新音乐,都和欧洲殖民主义有关。中国的新音乐也如此。在20世纪上叶,救国救民成为主流思潮。为了强大起来不受欺负,需要向强国学习。于是出现了各种新事物,包括新音乐。所谓“新”,就是和传统不一样;中西结合的结果,骡子不同于驴。它在当时具有启蒙、团结、激励国民为自由和幸福而抗争的功能和价值。建国以后,它又成为运动的声音。如今,它依然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保持主流身份和状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甚至有学者称之为“新传统”。同时,它和新潮音乐一道被当作学术探讨的问题,即“中西关系”、“古今关系”、“雅俗关系”和“(音乐)内外关系”等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外的音乐产业都乐于走混生道路,目的是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混生的新产品,往往拥有更大的受众。例如非洲和南美洲的许多新音乐,往往是多源混生的结果,被销售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
其四,混生音乐的生存和发展。目前中国处于新的转型期,政治上要求建构中国话语体系、软实力、国际传播和话语权,经济上要求实现工业向后工业的转变,文化上要求建立或复兴中华文化、美学精神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或语境中,混生音乐是否符合时代需要,能否担当转型的促进者责任,需要深入探讨。尤其是和“非遗”相比,和古老的文化传统相比,现代混生音乐的生存合理性在哪里?它应该走向何方?这是特别需要探讨的问题,关系到未来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二)目的:学术目的和实用目的
其一,学术目的。澄清各种相关思想观念、概念、争论,为建构“新音乐美学”奠定基础,为建构“多元音乐美学”提供“一元”。如上所述,混生音乐的族性问题未受到足够充分的关注。欧洲殖民主义的结果是所有东方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东西结合或混生的“新音乐”。由于西方音乐和各地新音乐的存活状态都良好,唯独传统音乐被边缘化并逐渐消失。“非遗”保护的意义就在于抢救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抢救这些资源是为了共享,为了多元文化生态的繁荣。笔者认为如今的“多元”处于人工态,它包括了被挖掘和保护的“原生态”的多元和新异质化的多元。换句话说,即各种原始的原形、现代新原形,各原形的变形,以及各种杂交形(混生音乐)——老原形之间的混生音乐、新原形之间的混生音乐、新老原形之间的混生音乐、各变形之间的混生音乐,各变形与各原形之间的混生音乐,等等。各种类型都归属相应的族群,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族群传播。区分这些音乐类型,有利于明确多元音乐文化之“多元”的具体情况。原形及其变形的族性相对容易辨别,但是混生音乐的族性则需要细致分析。从现实情况看,新音乐、新潮音乐这类中西混生音乐并没有独立的区别于原有民族的族性归属,而是依附于双源之一方,即中华民族。也就是骡子归属驴。即便如此,从多元生态看,不同原形混生的音乐,其族性特征不如原形那么鲜明。原形的鲜明度有利于一个民族构建自己的音乐文化体系或话语。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上,“原样保护”与“变化发展”之间,存在着持久的争议。其中存在观念、概念等问题需要澄清。如“非遗保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意义何在。相对于混生音乐,“非遗”保护的就是原形,是驴。混生音乐或杂交音乐,首先是以原生态音乐为参照的,是不同原形或其变形混合而成。反之,研究混生音乐,对原生态音乐或“非遗”的传承、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实用目的。促进混生音乐实践健康发展;为解决音乐教育中的相关疑难提供参照;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在非遗保护的同时,应放开思路,更多地创造,包括新形音乐和更多样的混生音乐。当然,对于已经出现的混生音乐,应给予理解和支持。这是促进当今多元音乐文化生态更加繁荣的需要。在全世界普遍存在混生音乐,而且随着新族群的出现,或者新商机的利用,还在增加混生音乐的种类。显然,特定混生音乐跟特定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影响。
具体目标:初步概括判断音乐族性的尺度;为解决混生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做出努力;分析迄今存有的几种混生音乐类型;探讨当今混生音乐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探究混生音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为新音乐美学、多元音乐美学建设提供参考。
(三)方法:比较方法与美学方法
其一,比较的方法。“混生音乐”与“原生音乐”的比较。通过比较,看清二者或三者的差异,抑或混生音乐与作为根源的诸种原生音乐的差异。同时,看清混生音乐中各种原生音乐的“基因”,及其所占的比例;借鉴模糊数学的“隶属度”计量法,看清混生音乐对各个根源音乐的隶属程度。例如通过比较分析,察觉新音乐具体作品在中-西之间的隶属度量。再者,比较混生音乐和原生音乐的族群归属——由乐看人,了解不同时代族群的特点和需要,由乐反观族群的衍变情况;由人看乐,了解不同时代混生音乐的合目的性以及功能的产生和实现情况。
其二,美学的方法。即注重感性分析的方法。虽然大家都知道乐谱和音响之间不等同,乐谱仅仅是用记号大致记录音乐;传统音乐的乐谱更为简略,仅仅记录音乐“骨架”,活态音乐指实际活动中的音乐声音。但是学界依然更多地通过乐谱分析来探讨音乐意义。于是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乐谱分析可以发觉的民族音乐成分,实际上却听不出来,无调性的现代主义作品尤其如此。改编类混生音乐,“移植”和“主题化”类型较容易分辩原生音乐,“意译”则不易分辨。“移步不换形”之“形”需要听觉能分辩;“形变魂不变”的“文化气质”更需要直观把握。因此,美学的感性分析非常必要。
Introduction of aesthetic analysis on ethnicity of hybrid music
Song Jin
Hybrid music is cross-culture music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many types including two or multiple origin, mixture once or more times. Many hybrids music which have complex ethnicity is from same origin. In composing of hybrid music is lack of sensibility.We need research with aesthetic perspective in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ybrid music, ethnicity, sensibility effect
J601
A
1001-5736(2017)04-0061-8
本文为2015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混生音乐族性的美学分析”之绪论,批准号15DD33。
[1]
宋 瑾(1956~),博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