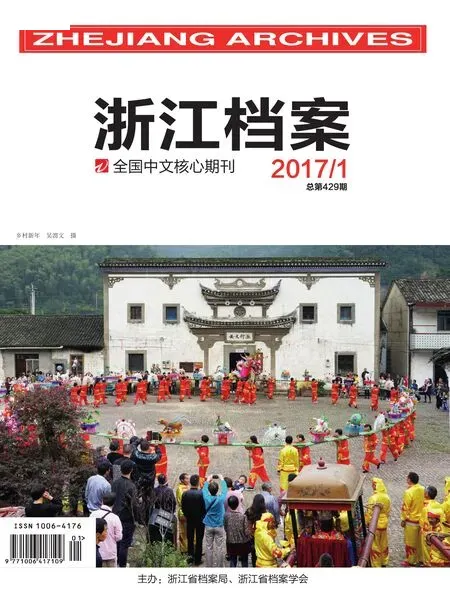弘一修改稿《弘师童年行述》的存世意义
2017-01-30王巨安浙江图书馆
王巨安/浙江图书馆
一、修改稿来历与背景
搜览有关研究、反映弘一法师(1880—1942)之家世、生平、童年等专著文章,发现多引用胡宅梵(1902—1980)《弘师童年行述》一文(下称“刊件”)。该文初载于竺摩法师(1913—2002)1941年元旦在澳门编辑出版的《觉音》杂志第20—2l期合刊上。弘一法师圆寂一周年时,又被改题为《记弘一大师之童年》,由弘一大师纪念会编入《弘一大师永怀录》一书出版。此后至今,该两题被反复刊载,颇多引用,传播极广。
胡宅梵,本名维铨,又名谪凡、梵凡、胜月,浙江余姚双桥(今慈溪桥头镇)人,布衣诗人,1931年刊著有《胜月吟剩》,201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有今人方向明点校本。该点校本附载的胡宅梵《弘一大师胜缘记略》称:1929年秋弘一法师住慈溪金仙寺时,亦幻法师介绍他与弘一法师认识,此后交往甚密,并皈依为弘一弟子,复被弘一取名为宅梵、胜月。
关于“刊件”之来历与价值,胡宅梵在《觉音》发表时加前言交代:
民国十九年,亦幻和尚住持慈溪白湖之金仙寺。秋末,弘师飘然莅至。予居固比邻白湖,故时得亲教。一日予谓师曰:“师之传略,尝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对师诞生一节,所载近乎神异,未知确乎?”师曰:“余之生平,自二十以后,友人多知之,惟自幼及壮,此二十年间之生活,殊鲜人知,即有传闻,亦多失实,然年幼无知,传亦何益?惟犹忆我父筱楼公乐善好施之行,颇堪风世励俗,差足传述,而与余幼年之生活,亦有密切之关系也。”于是师乃条述其幼年状况,予即秉笔为记,记毕呈阅,复经师亲以朱笔改正。则此篇可称其幼年之真实史也,可供欲为师写评传者之资料,故力求记载之详实,不计文辞之浅陋,抑亦自惜无生花之笔,为师撰史传耳!兹竺师为师出诞辰专刊,索稿急,无暇修辞,遂以此稿寄呈竺师,谅师必能为予润饰,以增文采也。
胡宅梵称“刊件”稿经弘一法师过目并经其亲笔修正,与事实有出入。因弘一法师修改稿存世,可见详情。
浙江图书馆藏有陈伯衡题签《亡友弘一上人遗墨》册页[1],收有弘一法师墨宝二十余件,首为章劲宇[2]题《弘一上人手简真迹》,署“丁酉夏日禹杭章劲宇抚”等语,其后是该修改稿,两开,无题(章劲宇边署“右为胡君宅梵手记上人传略,上人朱笔校定之,霜盖居士装池记”)。接下去是弘一法师致伯衡居士一通,致申甫居士[3]一通,致宅梵居士十三通连同5信封与所附数纸片语,以及弘一法师白描观世音菩萨一小帧,最后附丰子恺(1898—1975)致弘一法师与胡宅梵各一通。根据该册页提供的以上信息并经字迹比对,该文稿两开确为胡宅梵与弘一法师手笔。
考此丁酉即1957年,又从白描观世音菩萨题有“弘一大师手绘”“妙妙观世音,劲宇居士玄鉴,胜月胡宅梵敬赠”等信息看,上述弘一法师手迹不迟于1957年从胡宅梵等原藏家直接转归章劲宇收藏,并由章劲宇装裱成册,此后随章劲宇的其他一些藏品一并入藏浙江图书馆。
1996年9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第八卷,刊登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丁红女士整理的《弘一法师未刊书札》一文,收该册页中致胡宅梵十三通与致陈伯衡一通,并附丰子恺二通,但更为重要的弘一法师修改稿,却未引起重视而漏公布迄今。
二、修改稿与“刊件”差异明显
对比修改稿可以发现,“刊件”并非按照弘一法师认定与修改发表的,而是胡宅梵顾自行修改所成。
修改稿初由墨笔写成,依次复经蓝钢笔、朱笔、黑钢笔涂改。朱笔为弘一法师手迹,其他为胡宅梵手笔。如修改稿有用蓝钢笔加“棺木”二字,但被朱笔点去;又如修改稿有朱笔加“幼时”二字,黑钢笔绕过此处,另加“作大和尚”四字。也就是说,胡宅梵分别以墨笔、蓝钢笔书写、修改后,经弘一法师审定并以朱笔修改,但之后胡宅梵又加黑钢笔修改,却未经弘一法师再认定。兹将经弘一法师修改认定的修改稿内容整理于下,与“刊件”不同处字体颜色不同并依次说明:
大师生于天津,父筱楼公,生大师时年已六十有八。1师有长兄,长师近五十岁,师坠地2时,久已见背。筱楼公精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工夫,饮食起居,悉以《论语·乡党》篇为则,不少背3。晚年乐善好施,设义塾三4,创备济社一,范围甚广,用人5专事抚恤孤寡,施舍衣食6——先以签散洽,待孤寡贫寒等需衣食时,凭签付发。7又设存育所,每届冬季,收养乞丐,不使冻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年费钜万,亦不少吝。8津人咸颂之曰“李善人”。又9喜放生,所放鱼鸟不知凡几。
公自长子死后,仅存师之庶母所生之次子,长师十二岁。又恐夭亡,复娶师之生母,母10仅生师一人。当师生后,来卖鱼之求放生者11,聚绕若会,状极拥挤,鱼盆之水,溢于外者12,汇流成渠矣,公13则尽买放之。又放鸟14甚多。自后每逢师生辰等期,更加多放生。15
公年至七十二,16患痢疾,自知不起,将临终前,痢转17愈。公属人延请高僧学法老和尚,坐卧室诵《金刚经》,不许一人入内。18时师方五龄,亦解掀帏窥探。当公殁之日19,毫无痛苦,安详而逝,如入禅定。灵柩藏家凡七日,每日或延僧一班乃至三班20,日日诵经不绝。时师见僧众之行为甚可爱,以后常偕其侄等作“放焰口”之戏,己坐其中。21
师幼时,食必置姜一碟,盖效乃父不撤姜食之义。一日师食时,桌少偏,其生母训之曰:“席不正不坐”。22公之守《乡党》之则,已感化于妇孺,可谓行之严矣23。
自公逝后,家人死亡相继24。师虽25幼,亦深有26人事无常之感。
师至六七岁,其兄教督甚严,不得少越礼貌,并时以《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等属师浏览。时有王孝廉者,至普陀出家后27,居天津28无量庵。师之大侄妇早寡,常从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并学袁了凡记过功格。师时年七八岁,见之甚喜,常常在旁听之,即亦能诵,似即夙慧。29更从之学记功过格。师有乳母刘氏,能背诵《名贤集》(集为格言诗,四、五、七言递加),时时30教师习诵其词,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又如“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时31师虽在八九岁之间,闻之已起厌世之心32。至十余岁,尝见其33兄待人接物,礼貌则随贵贱而异34,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贫贱者敬之,富贵者轻之。性更喜蓄猫,而不平之心,时亦更偏35,往往敬猫如敬人,见人或反不36敬.人有目师作痴颠者,师亦不少动,变本加厉,甚致敬礼溺器,而轻视人类,于是思想无不偏癖。37康有为光绪戊戌之变政,颇合师之怀抱38,而厌弃世俗之心,亦日甚一日。
暇时辄习练小楷39,常摹刘世安所临文征明《心经》,甚久。兼事吟咏,如“人生有40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等句,可见厌世心之一斑,然亦可谓当时之代表其思想之作品也。41自是与其兄意见愈相背。42至二十岁,奉母来海上43。存育所、善堂仍由其兄继嗣,44及拳匪乱,方收45歇。备济社今尚46在,承办者虽亦为李氏,然已久易其主,而“李善人”之名,亦转属于彼李氏矣。
庚午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弘一师述后二日,弟子梵凡呵冻记于西轩,时方大雪。凡。47
按:1“刊件”此三句作“大师诞生于天津,本为富宦家,父筱楼公,当师坠地时,六十有八”;2“刊件”作“生”。3“刊件”作“违”。4“刊件”无“三”。5“刊件”此处加“极多”。6“刊件”此处加“棺木”。7“刊件”此四句作“每届秋末冬初,遣人至各乡村,向贫苦之家,探察情形,并计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给票据,至岁暮,凭票支付”。8“刊件”此二句作“年斥资千万计,而不少吝惜”。9“刊件”作“性”。10“刊件”无“母”。11“刊件”此二句作“当师诞生日,捕者以鱼虾蹱门求卖放生”。12“刊件”此处加“亦”。13刊件作“师”误,《弘一大师永怀录》作“公”。14“刊件”此处加“亦”。15“刊件”此二句作“自后每逢师生辰,必大举放生如故”。16“刊件”此处加“因”。17“刊件”作“忽”。18“刊件”此三句作“师乃属人延请高僧学法上人,于卧室朗诵《金刚经》静聆其音,而不许一人入内,以扰其心”,并将下句“时师”改作“师时”。19“刊件”作“当公临殁”。20“刊件”此句作“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21“刊件”此四句作“时师见僧之举动,均可爱敬,天真启发,以后即屡偕其侄辈,效焰口施食之戏,而自中据上座,为大和尚焉”。22“刊件”此处加“盖”。23“刊件”此句删。24“刊件”作“相随”。25“刊件”此处加“年”。26“刊件”作“时兴”。27“刊件”作“返”。28“刊件”此处加“之”。29“刊件”此五句作“时师年约七八岁,见之而甚喜,常从旁听之,即亦能诵,非即夙慧,乌能至是”,并将后句“更”改作“且亦能”。30“刊件”删一“时”。31“刊件”删“时”。32“刊件”此句作“亦颇起解其意”。33“刊件”作“乃”。34“刊件”此句作“其礼貌辄随人之贵贱而异”。35“刊件”此句作“时亦更趋偏激”。36刊件此处加“致”。37“刊件”此五句作“师亦不为动,且变本加厉,甚至敬礼溺器而藐视人类,童年有此反抗革命之思想,亦可谓奇矣”,下句前加“迨闻”。38“刊件”此句作“似有合乎怀抱”,并将后句“而”改作“于焉”。39“刊件”此句作“师闲居,必习练小楷”。40“刊件”作“犹”。41“刊件”此二句改作“皆为其幼年之作,谓其代表当时之思想可,即视为萌其出世之心,亦无不可”。42“刊件”此句作“由是与其兄意见差池愈远”。43“刊件”此句作“遂奉母来沪”。44“刊件”此句作“其居沪后,存育所、善堂等产业,皆由其兄继续办理”。45“刊件”作“罢”。46“刊件”此处加“存”。47“刊件”无此跋。又此“庚午”即1930年;“凡”为钤印。
修改稿末尾,又有胡宅梵蓝钢笔书写复经黑钢笔涂乙两段。这部分内容不见有弘一法师修改痕迹,是其后胡宅梵所加。前一段系对文中一处修改的草拟,后一段为:“总合师之生平思想,十龄内学圣贤;十岁至二十,断类放诞不羁之狂士;二十至三十,着意力学风流儒雅之为文人;三十以后,渐渐复其初性。”这段内容刊于“刊件”末,文字加小改。
三、修改稿存世意义
弘一法师手稿存世不多,一向为世所珍,而这份修改稿可以看成是弘一法师童年家世的一份档案,极具史料价值:
第一,证实“刊件”主体确来源于弘一法师口述且有具体时间,成稿过程中也有经弘一法师亲笔修改事实。弘一法师就其家世童年的回忆,所见仅此一次,幸赖该修改稿而存。
第二,展示该“刊件”内容原貌并厘清其错误与不足,有助于正确认识弘一法师家世与童年,并可纠正、补充后世因“刊件”而引起的相关研究、宣传的不足与缺陷,完善弘一法师形象。
通过校录可以看出,“刊件”主体虽源于弘一法师口述,但系追记于弘一法师口述后二日;虽经弘一法师亲笔改正,但之后胡宅梵又作较大修改,结果适得其反——“刊件”出现臆断夸张强加且文字拗口不畅,使人难以相信其前言所称经弘一法师亲笔改正这一事实,乃至有损弘一法师形象。如:
修改稿“设义塾三”,“刊件”去掉了“三”,三所变成了一所。
修改稿“用人专事抚恤孤寡,施舍衣食——先以签散洽,待孤寡贫寒等需衣食时,凭签付发”,“刊件”改为“用人极多,专事抚恤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每届秋末冬初,遣人至各乡村,向贫苦之家,探察情形,并计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给票据,至岁暮,凭票支付”。这里,筱楼公做善事用专人,被夸张成“用人极多”;而善举方式更被改变,甚至被夸大为“遣人至各乡村”主动查访,这是难以置信的。
修改稿“年费钜万”,“刊件”改为“年斥资千万计”,显然离谱。“钜万”只是形容为数多,以筱楼公的身份家产,行善举无法达千万,其时民间也罕见富达千万(银两或银元)的。
修改稿“于是思想无不偏癖”,“刊件”改作“童年有此反抗革命之思想,亦可谓奇矣”——这是胡宅梵的强加。
修改稿“然亦可谓时之代表其思想之作品也”,“刊件”改作“谓其代表当时之思想可,即视为萌其出世之心,亦无不可”——这是胡宅梵的随意推测。
“刊件”最后一段胡宅梵对弘一法师生平思想评论的添加,更是主观草率。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署“章氏霜盖庵藏,伯衡署签,时年七十七”。陈伯衡,即陈锡钧(1880—1961),字伯衡,江苏淮阴人,辛亥革命后宦居杭州,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碑帖收藏大家,解放初任职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旋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2]章劲宇(1916—1974),号霜盖,杭州人,章太炎堂弟,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解放后任职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精鉴赏,喜收藏。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3]堵申甫,即堵福诜(1883—1961),字申甫,浙江绍兴人,曾与弘一法师同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并两度长浙江余姚县。浙江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