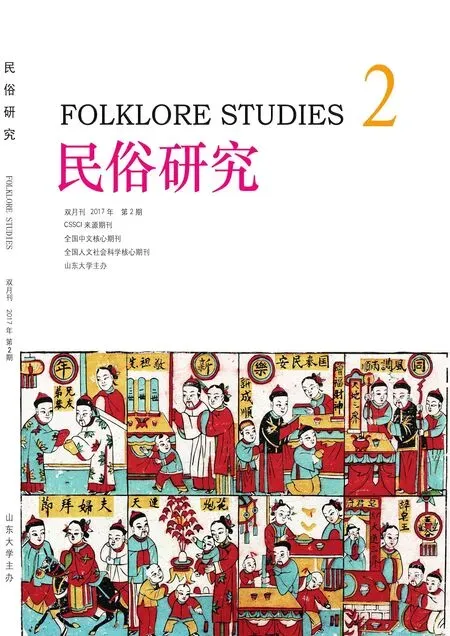汉族跳傩行为中的礼物馈赠与计算
2017-01-30曾澜
曾 澜
汉族跳傩行为中的礼物馈赠与计算
曾 澜
汉族傩祭仪式中的礼物馈赠实质上是赠神之物的分享行为,以跳傩弟子作为沟通者来实现它在人神之间的分享。赠神之物的分享不仅是跳傩弟子确证其人神沟通者身份的方式,更凸显了村民信仰者、傩神、跳傩弟子之间的文化同一性及由此凝聚的村落文化共同体意识。而傩仪的遗产化及其带来的市场价值使得赠神之物的分享转变为礼物的支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瓦解了基于傩神信仰之上的村落文化共同体意识。
礼物分享;礼物计算;文化同一性;文化共同体意识
自莫斯提出“礼物的精神”这一概念以来,礼物交换模式便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关注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有关国内礼物研究较早的学者是阎云翔,他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国内乡村社会中一般仪式性礼物交换的几种模式及其中所蕴含的社会交往关系,强调了礼物交换这一行为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培育和再生产。*Yan Yunxiang,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 in a Chinese Village,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与阎云翔着重于礼物交换之社会意义不同的是,本文主要分析乡村傩神信仰中赠神之物的文化意义。笔者以汉族傩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思维素材,以江西A村*因为文中涉及到收入等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所以为了保护该村的跳傩弟子和有关当事人,本文用A村来代替该村的实际名称。的跳傩行为为主要案例,通过具体分析跳傩行为中赠神之物由馈赠-分享模式转换为计算-支配模式的过程,阐释了文化转型时期赠神之物文化内涵及文化功能的变化。本文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各民族国家凸显其文化民族性特色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礼物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传统文化同一性的消解,使得诸多乡村传统文化、艺术趋于失传,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礼物的精神性馈赠:人Vs神
江西很多乡村遗存有傩戏。笔者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首选村——A村,是一个以吴氏为主的宗族村落。吴氏肇基祖吴希颜公自南宋绍兴五年(1135)来到A村定居后,A村便形成了吴氏宗族聚居为主的格局,吴氏子弟至今仍占村里人口的90%多。传统A村的发展主要掌握在吴姓宗族手中。然而,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吴氏宗族权力不断受到削弱,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直接由国家村级行政人员掌管。尽管如此,一些遗存至今的传统习俗,如傩祭仪式*傩祭仪式是指包括傩戏或傩舞表演在内的仪式行为,其中傩舞、傩戏表演的主要功能首先是呈现傩神驱鬼逐疫的行为,其次是娱神,娱人功能则附属于娱神功能。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傩祭仪式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还是由吴氏头人来组织管理。A村的傩祭仪式在正月举行,是一个全体村民都参与的,意在驱鬼逐疫、去灾降福的重大祭祀仪式。吴氏头人一般都要提前一两个月安排仪式的准备工作,大年三十仪式正式开始,历经“起傩”“演傩”“搜傩”“圆傩”四个进程,一直到正月二十日左右结束。在A村的傩祭仪式中,跳傩弟子不仅主导仪式的整个进程,而且戴上面具跳傩,驱鬼逐疫、去灾降福。与此同时,傩神信仰者则手捧线香,在仪式过程中配合跳傩弟子请神、迎神、娱神、送神,用特定的供品,包括橘子、茶饼、米饭、猪肉、鸡鸭肉或鱼肉等,馈赠给傩神,而跳傩弟子则代表傩神接受馈赠,并从馈赠中拨出一部分返还给傩神信仰者,其余部分则大多用于傩庙聚餐时与傩仪组织者(头人)或其他帮忙的村民一起分享。从表面上看,傩神信仰者与跳傩弟子构成了跳傩行为中礼物馈赠-受赠的双方。
然而,与乡村其他仪式性礼物不一样的是,传统傩祭仪式中的礼物馈赠-受赠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一,全体村民均参与仪式,成为礼物的馈赠者;第二,礼物是傩神信仰者赠予给傩神的,因此它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赠神之物,赠神之物不容僭越,亦无需回礼;第三,赠神之物虽然名义上馈赠给傩神,但是实际接收方是跳傩弟子,跳傩弟子围绕着礼物赠受实践其人神沟通者身份;第四,跳傩弟子接受了赠神礼物,并通过即时回馈一小部分赠神之物以及在傩庙与仪式组织者或其他村民一起共餐来分享礼物。因此,跳傩弟子表面上的回礼行为本质上是赠神之物的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傩祭仪式行为中的礼物经历了一个从人馈赠到神再由神返回并分享到人的圆满流通过程。由于礼物的馈赠方是全体村民信仰者,礼物的流通就超越了一般仪式性礼物基于村民个体人情伦理而架构的人际交往关系限囿,因此这个过程显然并不强调一般意义上诸如婚礼或丧葬礼仪中仪式性礼物对人际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傩祭仪式中赠神之物的功能就像古老图腾餐仪式中的血祭品一般,“血,特别是人的血,是玉液琼浆,它把人同神以及人同人联系起来”*[法]拉法格:《宗教和资本》,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3年,第31页。。傩祭仪式中的赠神之物亦是当地村民信仰者与傩神及傩神代表者跳傩弟子之间一种特殊的交往模式,呈现了赠神之物所隐喻的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精神交流和文化关联。由于赠神之物是以跳傩弟子作为沟通者来实现它在人-神-人之间的流通,赠神之物最终经由跳傩弟子从神回馈到人并实现了人神分享,这一过程所表征的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赠神之物在信仰层面上的意义,而指向了经由分享达成的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凝聚和文化认同。质而言之,这种特殊的交往模式不仅是跳傩弟子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实践、确证方式,更凸显了经由赠神之物的分享呈现于傩神信仰者与傩神之间的文化同一性,以及跳傩弟子与村民信仰者之间的成员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经由年复一年的礼物馈赠-分享仪式强化了由此同一性而凝聚的村落文化共同体意识。
一方面,对于赠神之物的收受方跳傩弟子来说,跳傩弟子代表傩神接受礼物的馈赠,是他们人神沟通者身份的一个重要确证方式和实践方式。
这首先体现在跳傩弟子接受赠神之物且无需回礼。在以傩神信仰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技术的观念框架之下,傩神往往是村民信仰者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想象,是能够左右他们生活平安、应对莫名灾难的神秘力量所在,因而傩神总是处于信仰层面的最高位置,它们只接受信仰者的朝拜和供奉,却并不允诺每一次供奉之后的必然回报。尽管如此,对于傩神信仰者来说,他们要获得傩神的护佑,就必须供奉礼物祭品以表达对傩神的敬仰,而不馈赠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因此,在赠予傩神的礼物交换中,礼物的馈赠是必需的,然而回报并不必然,受赠从而不具有一般仪式性礼物中负债*莫斯在其著作中阐释了礼物负债的内涵,详见[法]马塞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卢汇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的内涵。而在村民眼中“戴上面具即为神”的跳傩弟子,他们作为傩神的代言人,在收受赠神之物时不用回赠礼物。这种不回赠并不像其他仪式性礼物的不回赠行为那样,会降低收受者的伦理人格,因为在傩神信仰者眼中,跳傩弟子戴上面具便成为傩神的化身,代表了神灵,而神灵是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因此,跳傩弟子接受礼物馈赠这一行为,就显著体现了他们人神沟通者身份的不可僭越性。
更为重要的是,跳傩弟子接受、分享赠神之物的仪式性行为过程,成为他们人神沟通者身份实践及获得认同的一个重要方式。在跳傩仪式过程中,村民眼中戴上面具既成神的跳傩弟子,他们在接受礼物馈赠时,要及时地给馈赠者一些祝福:A村的跳傩弟子在接受主人家馈赠的米果、线香、纸钱、红包时,必须得把其中的一些馈赠重新交还给主人,并双手托着还礼说道:“人财两旺,财源茂盛。”由于赠神之物饱含了村民对于傩神神力萌护的愿望,因此在他们眼中,礼物一经供奉出去并为跳傩弟子接受,便具备了去灾降福的神秘力量,而跳傩弟子的礼物收受及投注于礼物之上的祝福则使得这一神秘力量有可能最终实现。在这里,分享的礼物显然并非只是作为实物的礼物,而是礼物中已经蕴含的傩神祝福和灵力:“归还的东西好让主人家吃后没病没灾”(A村头人语)。如此,在这一受礼与分享的仪式过程中,赠神之物就经历了从人(村民)到傩神(跳傩弟子)再到人(村民)的流通,礼物在接受之后被赋予的神灵力量亦通过礼物的分享最终传达到了馈赠者手中。当家户主人在跳傩弟子接受馈赠之后,他们的应答“约老爷”(即为“托傩神老爷的福”)就意味着村民信仰者的主观意念中已经认定了傩神爷接受了他们的虔诚和心愿,礼物的接受就意味着傩神的萌护。在这个过程中,跳傩弟子作为神的身份显然是得到了村民认同的。
除了主要的驱鬼逐疫和布施祝福外,接受馈赠的跳傩弟子还要承担起祭司和占卜者的双重功能。在A村跳傩仪式的“报饭单”*“报饭单”,即为跳傩弟子在傩仪最后一个环节向傩神通报他们在跳傩期间家户供饭和点心的各家支祖名单。搜傩仪式结束后,傩班回到傩神庙内,列队向傩神太子跪拜,傩班仪式主持者位于中间,念“跳傩回饭单”:“某年某月,某某公供饭(或点心),保佑公下子孙合家吉庆,财源茂盛。求愿中祷告。”念完之后,由大伯掷筊,若掷成阴阳筊(即两个筊片一阴一阳),说明供饭者或供点心者,诚心诚意,主持者方可继续报告下一家支祖宗名字。如果掷成阳筊或阴筊,则说明该供饭或供点心者诚意不够,傩神怪罪,主持者这时候就必须代供饭或点心者向傩神道歉,说“若有心三口四,求愿中祷告”。再掷一次,直至掷成阴阳筊。环节,跳傩弟子须通过报饭单和掷筊这一行为来向傩神传达信仰者的诚意并再一次为家户祈福。即便掷出来的不是阴阳筊,跳傩弟子也要为村民信仰者在仪式过程中有可能无意中触犯到傩神,犯下诸如供奉饭食的诚意不够或供奉中可能触犯禁忌等过失,承担起人神沟通者的身份功能,请求傩神的原谅,并为家户重新占卜,通过化身为“神”所具有的神秘力量以掷筊的方式与傩神沟通,为村民重新赢得傩神的护佑。如果按照“在祭司那里,人对神说话;而在占卜者那里,神对人说话”*William A. Lessa and Evon Z.Vogt(eds.), Reader in Comparative Religion-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 &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79, p302.的沟通方式来看,那么,在“报饭单”这个涉及供饭-食饭-报饭单-祈福的礼物馈赠仪式中,跳傩弟子则充当了沟通傩神的“祭司”与为人消灾祝福的“占卜者”双重角色。这样,在整个跳傩仪式涉及到家户个人福佑的礼物馈赠中,跳傩弟子的人神沟通者身份再一次得到了实践,而他们不断掷筊请求傩神为家户护佑的仪式行为,则进一步告知了馈赠者傩神附体及其对于他们馈赠之物的承诺。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承诺,却能够从村民自愿馈赠饭食和提供点心的行为中看到村民信仰者对这一身份的认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跳傩弟子人神沟通者身份的实践和确证,除了主要通过佩戴开过光、象征傩神的傩面具,在跳傩仪式中“执戈扬盾”、驱鬼逐疫,经由个人的跳傩体验而获得自我的体认与确证之外,礼物的受赠行为及受赠之后的仪式性承担,亦是他们身份得以实践和获得认同的一个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对于馈赠方村民信仰者来说,跳傩仪式的礼物馈赠首先承载了村民对傩神护佑和解除自身生活困厄期冀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的表达并不是以物质交换方式和互惠原则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种想象性的精神交流来实践并实现的。在跳傩仪式奉迎傩神的过程中,村民信仰者总是将自己对于生活、生命的期许寄寓于精心准备给傩神的礼物之中,并在奉迎傩神、馈赠礼物的仪式过程中毕恭毕敬,恪守禁忌。然而,神并不回赠礼物,神回赠的只是附身于跳傩弟子并通过跳傩弟子“神”与“人”之角色的扮演而给予信仰者精神上的抚慰和允诺。礼物的仪式性馈赠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村民对傩神的敬畏虔诚之情,也使他们相信能够获取傩神的威能和灵力。在这里,傩神信仰者馈赠礼物的心理是建立在信仰者“信”这一心理层面之上的。“信”是村民们馈赠礼物的主要动机,而“报”则是他们对于馈赠礼物的一种想象性的颠覆了因果关联的结果。这也是大多数村民对于神灵存在“宁可信其有”并不断馈赠神礼物的根本原因。
很显然,基于信仰之上的礼物馈赠一开始只是信仰者之于神灵的一种单方面精神契约,这种单方面性就体现为馈赠行为是一种单向度的、自下而上的礼物流动。然而,跳傩弟子围绕着受礼而进行的“神”“人”角色扮演以及他们与村民信仰者分享赠神之物的仪式性行为,不仅完成了礼物自下而上而后又自上而下的圆满流通,更是实现了赠神之物在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和乡村共同体认同。
其次,赠神之物的分享及其禁忌体现了傩神信仰者与傩神的文化同一性。傩祭仪式中赠神之物的分享具有类似于北库页岛上基里亚克人分享熊图腾餐的意义:“我们吃熊肉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使熊的力量转移到我们身上来。”*[苏]N·H·尼基弗罗夫:《宗教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本质何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9页。虽然不像图腾餐一样直接杀食图腾以获取图腾的灵力,但是馈赠给神的礼物经由代表神灵的跳傩弟子重新分享到人,礼物分享便等同于分享了傩神的愿力和灵力。这种分享使得信仰者能够不断地信仰傩神,认同傩神,与傩神保持“同一性”,成为傩神的虔诚信徒,因为“共享祭品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表示神和人们间的‘休戚与共’”*[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在傩祭仪式中,傩神信仰者与傩神之间休戚与共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特性的同构性上。在以傩神信仰为生活总体把握方式的江西传统傩乡,傩神与鬼怪由信仰者所创造,被赋予了信仰者的特性和喜好,傩神信仰者也总是习惯于把傩神信仰及由此信仰形塑的具有地方特殊性的文化,当作应对他们日常生活而时刻需要知道的那些基础性东西,与其建立一种深层次的心理认同,并与其他需要这一文化的人们形成一种默契,在生活中显化出来,成为日常生活中无意识溢出的惯习或惯例。而赠神之物作为傩神信仰这一惯例性符号体系的一个重要代码,因其被赋予的神圣意味和被寄予的现世期许而指导、规约着人们的行为,成为傩祭仪式中的礼物禁忌。傩神信仰者努力遵循禁忌来进行赠神之物的馈赠和分享,体验赠神之物在仪式性流通中的神圣意味和精神交流,并以此来维持自身与傩神的同一性。赠神之物的禁忌及其弥散于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心理和规则,不仅保证了赠神之物的圆满流通和分享,而且反映了村落共同体于村落文化的共享深度,显现了傩神信仰圈之内傩神禁忌所代表的村落公共意志和共同体意识,并在不断轮回式的仪式操演中得到复现乃至强化。
更为重要的是,跳傩弟子围绕着受礼而进行的“神”“人”角色扮演,体现了傩神信仰者与跳傩弟子之间的成员同一性及由此同一性凝聚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作为人神沟通者的跳傩弟子通过扮演傩神承担起驱鬼逐疫、赐福式共享礼物的仪式功能,并通过人之角色的仪式性回归,与村民互动,插科打诨,戏谑傩神,以使村民在笑声中舒缓面对傩神的精神性压力,从而进一步认同傩神,并在相信傩神的灵验中忘却生活的苦厄,重建人与神、人与人的正常秩序,并重建人对生活的自信和人对于自身力量的肯定。*参见拙文:《民间傩仪式的空间特性与傩艺人人神角色的偏移》,《兰州学刊》2010年第10期;《从乡村戏台到城镇舞台:江西傩艺人身份的艺术人类学考察》,《戏曲艺术》2016年第2期。表面上看,跳傩弟子因为仪式的各种情境性条件而成为人神沟通者,其神灵代言人的身份不容僭越,然而跳傩弟子扮演神之角色与村民的礼物共享以及跳傩弟子扮演人之角色与村民的“径还酬酢”式互动,使得整个村落成为一个流动的仪式剧场,“看戏与作戏人合而为一,不知孰作孰看?”*(清)徐珂:《清稗类钞》第37册《戏剧类》,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20页。。跳傩弟子的“人”“神”角色扮演由此淡化乃至弥合了作为“神”的跳傩弟子与作为“人”的村民信仰者之间的身份差异性,凸显了基于同一个傩神信仰之上跳傩弟子与其他村民信仰者之间的身份同一性。
就跳傩弟子人-神沟通者身份的认同而言,跳傩弟子在跳傩仪式中戴上面具成为神,并非仅仅限于其面具所指向的身份的神灵化,而更多的是向人(村民)与神(傩神)这两个对立维度弥散了:其身份在仪式中的实践呈现了仪式情境中跳傩弟子的“自我”及与其相对应的“傩神”与“村民”这两个他者,然而跳傩弟子围绕着礼物的馈赠与分享,在与人、与神进行沟通的仪式中将这两个“他者”分别转化为他们与之对话的两个对象“你”,并进而在人与神之角色转化中,将这两个“你”分别认同成为了“我(我们)”。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与其说是礼物的馈赠-接受呈现出跳傩弟子自我与其他村民信仰者的身份差异性,还不如说是礼物的分享凸显了“我”融入“我们”的地方文化同一性。当然这种同一性又是通过“我们”的世界,即“人”的世界与作为“他者”的神灵鬼怪/疫疾所代表的“神/鬼”的世界的差异性来凸显和强化的,尽管赠神之物表面上呈现出来的是跳傩弟子与傩神的同一,即跳傩弟子“戴上面具即为神”。质而言之,赠神之物的馈赠与分享使得跳傩弟子通过与傩神的同一强化了与其他村民信仰者的同一,亦强化了由此同一性而凝聚的村落共同体意识。
二、礼物的商品性计算:人Vs人
在江西传统的跳傩仪式中,无论是对于赠神之物的馈赠方傩神信仰者,还是收受方跳傩弟子来说,这种赠神之物的馈赠和分享都是信仰者个人或集体的信仰情感、生存意志和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仪式性表达。这种表达对于安心于乡村生活、恪守传统价值观的村民来说,其本质上是反市场理性、与经济利益无关的,“这不是市场和利润的规范与逻辑,而是要抵挡它们的”*[法]莫里斯·古德利尔:《礼物之谜》,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它承载着当地现世生活与历史记忆交流的规范和逻辑,创设了傩神信仰圈中村民信仰者和跳傩弟子确证自身身份认同的意义体系,强化了人神鬼观念框架之下的独特的村落文化共同体意识。
然而,当跳傩仪式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尤其是当其被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身份,成为傩戏*笔者这里用“傩戏”,意指从傩祭仪式中剥离出来、经常在舞台展演,具有文化、艺术研究价值的傩舞、傩戏表演部分。对此,笔者用“傩戏民俗表演行为”来称谓,以与较为原生态的传统“傩祭仪式行为”相区分。,且傩戏身份隐含的市场价值被跳傩弟子及村民意识到并不断重视的时候,经济利益作为一种“生活理性”,开始越过传统跳傩仪式之礼物馈赠的神性,而成为仪式礼物的一种功利性计算。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意识也开始逐渐消解了由傩神信仰所规约的村落共同体意识,赠神之物呈现的人-神精神交流,也逐步被人-人经济交换所取代。在地方信仰和神性不断弱化甚至被抹灭的民俗文化或民间民族艺术展演中,傩戏作为一种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价值,促使了乡村傩仪中赠神之物的变异。
也就是说,当江西乡村傩仪成为一种民俗、民间、民族文化或艺术的传播手段并走向舞台成为傩戏民俗表演行为时,礼物馈赠形式及功能就难免会发生变异。最显著的则是礼物的形式载体发生了变化,以实物馈赠为主转变为以金钱或红包为主。当红包的比重在礼物馈赠中成为一种经济利益的算计且越来越趋于重要的时候,赠神之物*在傩戏表演行为情境中,尤其是在乡村展开的傩戏表演行为,大多数红包仍是以赠予傩庙的名义来进行馈赠的,所以表面上看还是赠神之物。的神性就在很大程度上被俗性所取代。当神性消失的时候,被剥离了信仰的傩戏就转化为一个独立于生活、信仰之外的文化、艺术事项,可以被单独拿出来展演,具备了商品交换的价值。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则是礼物馈赠的馈赠主体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傩戏民俗表演行为情境中,仪式情境中以村民信仰者为主体的馈赠方,转变为舞台展演情境中对于展演抱有各类诸如文化艺术研究、异文化猎奇、传统文化保护等等观看期待的现代观众。这些现代观众大多数没有祈求于傩神的虔诚愿信,缺失与傩神交流的精神体验,再加上舞台表演情境中民俗信息的不完全、仪式环节的精简、表演中傩仪艺术因子的宣传和放大,这就使得他们在观看傩戏时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一种像在电影院观看电影或在剧院观看戏剧之类的观看情境之中:舞台上的傩戏展演实际上是与观众自身生活毫无关联的,他们无须参与祭拜神灵,无须精心准备供奉神灵的礼物,亦无须在馈赠礼物的时候恪守禁忌、“毕恭毕敬”。*关于傩戏展演情境与傩祭仪式情境的差异,请参见拙文:《重叠或交错:乡村傩祭仪式和傩戏民俗表演中空间关联模式的变异》,《戏曲艺术》2011年第4期。他们更多的是沉默地、隔离式地、自高而下地旁观、审视,并以金钱的方式支付报酬。此外,傩祭仪式中礼物馈赠的收受者——跳傩弟子的身份,也从人神沟通者身份转变为傩戏表演的民间艺术家或民族文化传承者。
以金钱为主要报酬的礼物计算越来越成为傩戏民俗表演行为不容忽略的算计,这一点仅从跳傩弟子参与各类民俗表演情境所获得的报酬收入便能窥见一斑。据笔者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凡是来到A村要求傩班弟子表演傩舞的,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旅游团,一般都要支付600元的香火钱,其中一半给傩神庙,另一半则由参与表演的傩班弟子平分,而他们一年里或多或少都要接待好几批这样的观看者。如果傩班弟子外出表演,则由邀请方支付报酬。1998年A村傩班弟子应邀去北京表演了三个月,一般每天上午表演,下午没有游客就不表演,老板支付他们每人每天50多元的劳务费,那么跳傩弟子每人每个月就至少可以有1500元的收入,三个月就至少有4500元。这样一笔钱对于当时年平均收入只有2047.98元的江西农民*这一数据摘编自《中国农业年鉴1999》,网址:http://tjsj.baidu.com/pages/jxyd/5/22/6a4245c4adef275c50939377345e87ba_0.html来说,是一笔不可忽略的财富。某跳傩弟子告诉笔者,他现在自己住的房子就是用1998年去北京表演时赚的这一笔钱盖起来的。此外,笔者还了解到,2008年A村傩班去法国表演,前后大约一周时间,得到的报酬大约是每人3000多元人民币。由此,“红包”的多少及其在个人收入上所占的比重,开始以颠覆其在传统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而受到跳傩弟子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红包所获取的个人收入计算也就愈益凸显出来。即便是在传统的傩祭仪式行为情境中,红包所占有的比重也愈益凸显出来。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赠神之物主要以实物形式出现,馈赠的金钱数额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家户给予赠神之物中的“红包”也就越来越多。1992年A村傩班正月跳傩之后,每位跳傩弟子分得113元,1993年分得130多元,而A村村民1992年的年平均收入才785元。*这一数据来源于余大喜的田野调查结果。参见余大喜、刘之凡:《江西省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的跳傩》,(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年,第101、9页。2010年正月,笔者在A村田野调查时,于正月十六直接参与观察了傩班弟子分发剩余红包的场景:除去交给傩神庙里*俗称“殿上”。这一笔钱主要用于傩神庙的维修、管理及跳傩期间的一切事宜,诸如面具开光、买蜡烛火炮、请官员吃饭等。的钱及请头人吃饭的开销,他们当天每人分得了342.5元。而从正月初一到十六,他们每天都会分到一些钱,半个月的收入保守估计也至少有三千多元。在乡村社会生活并不是很富裕的条件下,跳傩弟子半月辛苦跳傩所获取的收入显然是无法被忽略掉的。
礼物中红包占比例程度的算计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赠神之物的神性,礼物的馈赠与分享转变为礼物的商品性交换,成为一种个人利益算计,礼物的文化功能由此发生了变异。
首先,礼物接受者跳傩弟子对傩戏礼物的算计,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跳傩弟子与傩神之间的同一性,跳傩弟子原本经由礼物馈赠与分享获得的人神沟通者身份,在傩戏展演情境中往往得不到认同。傩戏的舞台展演是为了某种艺术审美或文化探究而非傩神护佑而建构起来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赠神之物的馈赠与分享,由此也往往截断了跳傩弟子通过面具及驱鬼逐疫、去灾降福的仪式性动作与傩神进行的精神交汇。因此,虽然跳傩弟子仍然按照展演情境的需求戴上面具,扮演了各路神灵,但是实际表演过程中赠神之物的缺失、傩神信仰的缺失及由此缺失造成的傩神的缺席,使得跳傩弟子的人神沟通者身份失去了其存在的依凭。再加上观看主体的不参与式旁观或研究审视,他们的人神沟通者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无法实现特定情境下的自我认同和观众认同。这种认同感的丧失造成大多数跳傩弟子生出“跳的人是疯子,看的人是傻子”的感叹,“‘疯子’和‘傻子’的身份表达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舞台之下的傩艺人对于舞台之上自身身份定位吊诡现象的一种隐秘的自觉”*曾澜:《从乡村戏台到城镇舞台:江西傩艺人身份的艺术人类学考察》,《戏曲艺术》2016年第2期。。与此同时,跳傩弟子被赋予的“民间艺术家”身份逐渐替代了人神沟通者身份,成为傩戏展演情境中跳傩弟子的主要身份。“民间艺术家”的身份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认可了傩戏的文化艺术价值,而且强化了傩戏的商品交换价值。这一价值显然并不是通过传统艺术中的赠神之物得以体现的,而是通过观众及邀请方以金钱报酬的方式来偿还的。由此,礼物的红包性质极大地淡化了跳傩弟子的人神沟通者身份,傩戏被赋予的现代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亦对人神沟通者的身份内涵形成了某种解构,缺乏身份理性反省能力的跳傩弟子无疑会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疑虑。
与此同时,跳傩行为中礼物的算计亦剥离了赠神之物的神圣性,逐渐消解了傩神信仰者与傩神的文化同一性。当傩戏展演情境直接在乡村中建构起来的时候,这些曾经在仪式中积极参与的村民也会被围观的现代观众感染而进入到一种类似于剧场式的观看行为:他们从仪式行为惯例中抽身出来,在观看中,他们并不需要恭迎、恭送傩神太子,也无需点燃鞭炮、手捧线香奉上贡品馈赠给傩神。和现代观众一起,他们“居高临下”,沉默而又“超然”地旁观。
而且,这部分经常参与和“外面人”一同观看傩戏表演的村民,也会在逐渐熟悉现代观众对傩戏展演的评价中,不自觉地改变自己以往对于跳傩弟子扮演行为的观看角度和评判标准,具有了类似于现代观众观看傩戏展演时所具有的评判权力。当然,在传统跳傩仪式中,跳傩弟子扮演神灵的主要评价标准仍然着落于仪式的灵验效果。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在传统的跳傩仪式之轮回式的展演中,围观的村民已经将跳傩弟子的扮演视为一种“熟视无睹”的常规而忽略了现代人眼中傩舞、傩戏动作所包含的艺术因子。他们关注的仅仅是跳傩弟子的神灵扮演,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他们诉诸于神力需要解决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愿望。不仅如此,傩神扮演的好坏评判因为基于神之信仰的确定性而成为乡村中的一种禁忌制约。然而,在傩戏展演情境中,村民却往往把神灵的扮演与现代观众对傩舞傩戏表演的评判结合起来,在旁观中附加了仪式之外的意味,比如一种现代人惯于关注在傩戏之上而形诸于村民们想象之中的关于“美的”或“艺术的”“传统文化的”意味。此外,即便是在年度跳傩仪式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村民同样也会用摄像镜头取代眼睛的观看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传统跳傩仪式。由此,在傩戏展演情境中,原本对傩神毕恭毕敬、以虔诚之心馈赠礼物的村民,成为现代观众的一部分;在他们沉默而又“超然”地旁观中,傩神的不可僭越性被超越,傩神的神性消失,成为一个他者,两者之间的文化同一性亦趋向于解构。
最后,礼物的算计及其重要性的凸显,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跳傩弟子与村民基于傩神信仰形塑的成员同一性及村落共同体意识。礼物的分享性行为成为某种权势或权力的支配性行为,基于信仰之上的村落共同体意识被瓦解,而趋向于一种以利益关联的地方性认同。在傩戏展演情境中,以金钱方式为礼物报酬的接收方不再是跳傩弟子,而是由村民与跳傩弟子一起分享了礼物蕴含的经济利益。在傩戏热的20世纪90年代,傩戏作为文化资源的经济利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那时候在A村采访傩戏是需要支付红包的:
吴轩云听说小晋要办采访证,骨牌也不打了,让我们稍候。过了一会儿,他脑袋冒汗,跑去跑回,手中举了个红本本,就是那个在当地非常管用的采访证。他接过小晋100块钱,然后把采访证郑重递上,小晋也郑重接着。吴轩云也许被小晋那股认真劲儿打动,说:“如果一个人要照相,100块,不照相的,我们有一个功德箱子,愿意捐多少,随你自己。各位记者和机关的人,如果要跳一台傩给你们看,收200块。跳傩的工资另外给。”一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姿态。*陈彤、刘春撰文,晋永权摄影:《最后的汉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表演情境中,赠神之物转化为类似于工资的酬金,馈赠关系由村民信仰者和承担人神沟通者身份的跳傩弟子,转变为现代观众与以民间艺术家为身份标识的跳傩弟子。当然,村民也因为利益的分享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礼物的间接接收方,即在傩戏民俗表演情境中,村民由原本在仪式情境的馈赠方转变成了接收方。在这些转变之中,神性被淡化甚至消失了,围绕着仪式中赠神之物的信仰和精神受惠关系,被表演中以酬金为支付报酬的商品交换关系所取代。以酬金表达出来的傩仪之傩戏转化的文化艺术使用价值和商品交换价值日益凸显。
此外,傩班不断外出表演,使得地方傩戏的名声越来越响,并不断地得到文化管理部门的重视。这不仅使得傩戏所在的A村获得了在传统社会中所不能企及的地方利益,也使得当地及附近的村民增强了对于A村傩神灵验的信心。虽然大多数村民将地方的发达归因于傩神的护佑,但是他们对傩神灵验信心的强化显然是在文化管理部门对傩戏文化价值认可的前提下,因为地方利益的获得而达成并强化的,且这种信心最终的目的亦是为了充分利用傩戏的文化资源来获取更多的个人或地方利益。这样,村民个人和整个地方村落对傩戏的组织、管理、扶持和宣传也就更为用心,以傩戏作为文化商品进行礼物交换的红包也就变得更为丰厚。这种丰厚的礼物馈赠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表达了对傩神的敬畏,尤其是对村民来说,红包依然寄寓了他们对傩神的虔诚,但是与传统馈赠之中畏惧、感恩、欣悦之情淡化礼物功利*传统傩祭仪式中赠神之物的功利性,主要是基于中国民间信仰本身就具有人间性和功利性而言的,这一点区别于自身具有教义教规的宗教馈赠,诸如基督教中耶稣赠与门徒血与肉之类的具有代赎性质的礼物馈赠。色彩相反的是,通过红包的丰厚所呈现出来的礼物交换,始终无法遮掩馈赠者因为追求更多利益而呈现出来的更为功利的一面。
红包作为礼物交换的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村民个体或地方村落用来获取某种象征资本或等级权力。对村民个体而言,以丰厚的红包礼物对傩神的馈赠不仅可以获得傩神更多更强有力的护佑,而且也可以藉此宣扬自身的财富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威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一些在外经商成功或已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村民个体身上。在传统傩祭仪式展开期间,他们通过馈赠丰厚的红包,就能够要求傩班弟子进行全套的傩舞或傩戏表演,来吸引傩神及更多观礼者的关注。馈赠礼物由此成为他们炫富或为未来赢得更多利益、声望的功利性手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传统的傩祭仪式行为中,红包作为礼物所蕴含的支配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撕裂了以往因礼物分享而隐喻的傩神信仰者之间的成员同一性关联,强化了傩神信仰者之间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分层,基于傩神信仰层面形成的成员同一性亦逐渐趋于瓦解。
对地方村落来说,地方文化部门亦通过诸如资金扶持、基础设施修建、傩庙修葺等各类措施,介入傩班的管理和傩戏展演情境的建构,以此谋取傩戏这一地方文化资本带来的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然而,对于当地村民而言,通过红包体现的利益算计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和地方经济状况,如为方便外来的、带有各式观看目的的外来者,A村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扶持:修建了公厕,改善了村内的垃圾堆积状况,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小学的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等等。这些利益显然已被村民和跳傩弟子意识到并加以利用,传统的傩祭仪式行为因此以一种文化资源的模式纳入到了村民自身的地方文化建设之中。村民们主动调适彼此之间因为社会分层带来的各种隔膜,并主动积极地进行各项围绕着傩戏遗产化而开展的地方记忆创造和地方文化重建,以更好地迎合傩戏的市场开发。这种为了地方性利益的获得而重新凝聚起来的村落共同体意识,成为包括跳傩弟子在内的江西傩乡乡民与地方上的主要认同关联模式。
三、结 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江西傩乡,当傩戏被遗产化并不断被搬上各式展演舞台,成为一种文化表演行为时,乡村传统的跳傩行为情境就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不同跳傩行为情境中礼物的内涵和文化功能也发生了变异。当然,在不同的跳傩行为情境中,礼物变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傩戏民俗表演行为情境中礼物馈赠的主体为现代观众或文化管理部门,他们及其馈赠的红包礼物往往是作为乡村获取各类象征资本的在场性符号而受到重视。因此,礼物所表征的傩戏市场价值得到凸显,商品性交换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馈赠的信仰神性,并被有意识地纳入到不仅仅是村民个体,而且是整个乡村的现实生活改善或未来发展的算计之中。而在傩祭仪式行为情境中,由于礼物馈赠的主体仍为傩神信仰者,因此馈赠的红包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遗存了其信仰内涵。尽管如此,文化市场化以及傩戏民俗表演商品性交换所彰显的经济理性,也逐渐渗透到传统的傩祭仪式行为,使赠神之物的神圣性被各种诸如炫富、赢得声望等利益算计淡化。跳傩行为中用来敬奉给傩神的,链接了跳傩弟子、傩神和村民信仰者三者文化同一性的礼物,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赋予或增添了一些超出于信仰本身的功能,礼物的馈赠与分享逐渐转变为礼物的交换与计算。通过礼物交换和计算传达出来的,除了信仰方面的精神表达残余之外,可能更多地蕴含了村民信仰者包括跳傩弟子在内的个人经济利益算计、地方上的利益算计或一些互惠性质(包括个人、地方、文化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算计。
这种利益算计虽然会给礼物交换的双方带来短时期可以见到的互惠,然而从利益算计的负面影响来看,傩戏表演红包的多寡及其携带的各类象征资本价值正逐渐削弱傩戏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神性意味和地方性认同功能,而演变成为某些村庄传统傩祭仪式能否继续传承的一个核心因素。尤其是对于那些傩神信仰历史较短,仪式传承并非依附于当地大家族或宗族的村庄来说,利益方面的得失计算尤显重要。傩戏民俗表演机会的欠缺或支持经费的不平衡所造成个人利益或地方利益的不可得,往往成为当地年轻一代不愿承续傩艺、傩戏由此面临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与A村相邻的下坊村即面临着这一难题:该村傩戏组织者黄师傅告诉笔者,政府把支持的重点放在因傩戏闻名的A村,对他们村的傩戏投入的经费很少:“少儿傩班的孩子平时到县城表演每天只有30元,太少了。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每个人都要养家了。一天30元的工钱他们都不会去。(傩戏)失传了也没有办法。继承也很难搞,好多思想要做,家长啊,孩子啊……我年纪也这么大了,年青一代也没人组织。现在如果像县里那样搞,要你的时候打个电话,也不给经费,他们也不会去跳了,都说,没有钱,搞不到钱就不去了。”因为各方利益算计的原因而导致傩戏的渐趋失传,类似于这样的村落在江西并不在少数。
当然,傩祭仪式中礼物性质的改变并非一夕之间,由其所表征之傩戏本真性的流失或傩戏文化的失传亦是一个渐趋的过程。在本文语境中,这一过程与傩戏所依附之乡村宗族力量的强弱有着密切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文化与以宗族力量维系的乡村传统文化之间的博弈:宗族凝聚的力量越强大,博弈的过程就越漫长,改变的过程也就更为缓慢。尽管如此,随着傩神信仰从傩祭仪式中的逐渐剥离和礼物被赋予商品性意识、权力或权威意识的日益增强,赠神之物的神圣性亦有可能趋于消亡,基于信仰之上的傩戏也就极有可能失却其本真性甚至失传。笔者在A村田野中发现的乡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乡民用摄像镜头代替眼睛来观看周期性仪式的现象,至少表征了这种信仰神性的逐步淡化。
显然,在中国现代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或艺术趋于失传或失去其本真性的现象并不仅限于傩戏,而是普遍存在于大多数乡村之中。更内在的原因可能在于,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和乡村文化生态的破坏,对基建于传统生活方式中包括傩神信仰在内的传统文化合法性冲击,或许是更为深层的精神性抽离。因傩戏赠神之物的计算甚至算计而导致乡村成员同一性和文化共同体意识的瓦解,即是地方传统文化、艺术存在合法性被逐渐消解的典型案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各民族国家凸显其文化的民族性特色的文化全球化时代,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 王加华]
曾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
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重大研究项目“图像的文化书写: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图像文本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RWXKZD0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