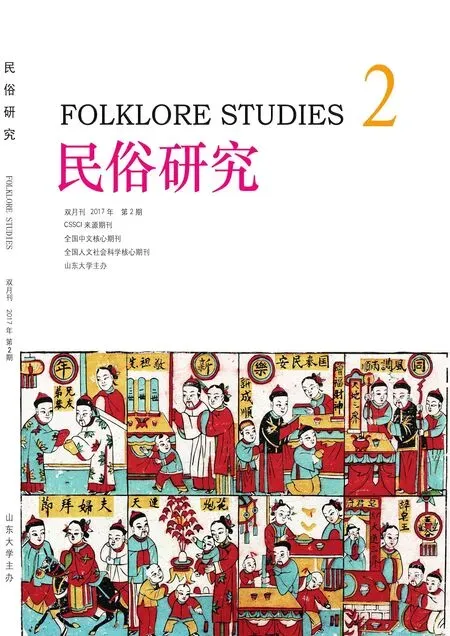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
——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新诗的建构
2017-01-30李瑞华
李瑞华
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
——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新诗的建构
李瑞华
五四时期,“歌谣体”成为新诗创作的重要来源,作为一种新诗实践,它在丰富诗歌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承载了启蒙主体的“平民化”诉求。三十年代在左翼文学“大众化”口号下,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歌谣化”又赋予了歌谣体以新兴阶级话语,在左翼主流话语逐步建构之下,四十年代“歌谣体”新诗渐趋圆熟。通过考察现代文学历程中“歌谣体”新诗的建构和发展,可以看到左翼文学“场域”对文学话语形式的决定作用和新诗建设中的得失,也会进一步引发对现代汉语诗歌发展方向的有益思索。
歌谣;民间;左翼;大众化;民族形式
歌谣是语言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植根于民间的一种传统文化,民间文学主要来自集体创作,通过普通民众的口头流传渗透于社会生活,主要包括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歌谣总集,而“歌”和“谣”的说法最早就出现于《诗经·园有桃》里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后来被统称为“歌谣”。关于歌谣的发生,《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解释,而《春秋公羊传》中则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说法,在中国诗歌千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歌谣作为一种民间创造,最初“起源于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繁衍的人类求生存的实践活动”*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并未被赋予太多的诗学意义,正如朱自清所论:“歌谣以声音的表现为主,意义的表现是不大重要的”。*朱自清:《〈粤海之风〉序》,《民俗周刊》1928年11月28日,第36期。但五四启蒙运动以来,歌谣以它在现代文学中启蒙使命的承担而和其他民间形式区分开来,成为左翼文学作家的革命武器。朱自清对“歌谣”的功能做出的论断,虽然背离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激进姿态,但却道出了歌谣真正原初意义上的价值承载。事实上,歌谣在五四启蒙初期步入文学革命的轨道,乃是五四精英的有意为之,意在丰富新诗资源,为建立一种“民族的诗”找寻方向,但在以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随着阶级和权力建构的发展变化,“歌谣体”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含义,承载了远远超过自身能量的多重使命,也引起了诸多争议肩负起社会和文学变革的任务,并伴随左翼文学的战略方向而不断发展变化,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一、五四启蒙知识者对歌谣的发现和征用
现代文学发展中对“歌谣”的发现源自于五四启蒙时期。虽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坛最早提出搜集和研究歌谣,但真正把这种倡导付诸行动的,则要归功于一批北大精英学者的推动。1918年2月,在文学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正式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发起歌谣征集运动目的相当明确,一方面是从启蒙者角度出发,希冀在文学革命大潮下为新诗变革寻求更多的表达形式,以呼应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则是从启蒙的对象考虑,推崇大众易于接受的民间形式,契合“平民化”的启蒙需要。机构的设立本身便预示着反抗,以民间视角对抗陈旧的贵族化文学,对保守派和卫道士造成冲击,五四初期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提倡,使得“歌谣体”新诗这种形式在五四时期出现之初,作为新文学建构的重要资源,带有明显的文化变革的诉求,成为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歌谣体”这种被埋没已久的民间形式在五四时期被引入现代新诗的建构时,倡导者对功用价值的期待就明显高于审美价值,体现出一种泛政治化倾向。
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发起“歌谣运动”之后,俞平伯、刘半农等大批诗人纷纷投入到拟歌谣体新诗创作中,这种体式的新诗采取了方言入诗的手法,带有强烈的乡土地域色彩,一时间,“几乎形成了新诗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张桃洲:《论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资源:谱系、形态与难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尽管新文化运动以推翻旧传统为主要旨归,五四学人却把来自民间传统的歌谣援引到反传统的新诗建设中,诗人把歌谣作为新诗建设的重要资源,其中最为看重的便是它的真实和朴拙。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希望“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以“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周作人:《歌谣》,《晨报副刊》1922年4月13日。。他在论述歌谣和新诗的关系时中还这样说到:“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周作人:《歌谣》,《晨报副刊》1922年4月13日。而对“歌谣化”的提倡和实践用力最多的刘半农,也和大多数启蒙者对于“歌谣体”的看法不同,更多着眼于从诗歌的审美质素出发把其纳入新诗建设之中。在《国外民歌译》序言中谈及创建歌谣征集处的缘起时,周作人重申自己对于歌谣的旨趣“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真实”是刘半农诗歌审美的核心价值,在他看来,民歌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借着歌词,把自己所感所受所愿所喜所冥想,痛快的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灵上之慰安”*刘半农:《海外民歌序》,《语丝》第127期,1927年4月。。而这些民歌的初创者,“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样的“抒发”,乃是“文字上最重要的一个原素”*刘半农:《海外民歌序》,《语丝》第127期,1927年4月。。
从诗歌的审美功能出发,刘半农更看重歌谣所承载的民间文化价值,他搜求和整理了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歌谣,甚至在地摊上收集唱本,并运用家乡江阴方言中“四句头山歌”的声调自拟民歌,1926年结集出版《瓦釜集》和《扬鞭集》。《楚辞》中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句,刘半农的《瓦釜集》就是要尝试尽一己之力用民歌的形式“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北新书局,1926年。。诗歌采用了江阴方言,并配以江阴民歌的声调,集后还附上了他之前采集来的大量江南船歌,是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写作的民歌体新诗集;《扬鞭集》则是诗人把自己诗歌创作十年中的作品加以删减,按时间顺序编成的集子。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来看,这两部诗集称得上是现代新诗史上“歌谣化”新诗的经典之作,沈从文就认为《扬鞭集》是刘半农诗歌中最美的作品,是“为官能的放肆而兴趣的欲望,用微见忧郁却仍然极其健康的调子,唱出他的爱憎,混和原始民族的单纯与近代人的狡狯,按歌谣平静从容的节拍,歌热情郁怫的心绪”*沈从文:《论刘半农的〈扬鞭集〉》,《文艺月刊》2卷2号,1931年2月15日。。
在这些拟歌谣体的诗作里,张扬着民间纯朴的情爱欲望,散发出活泼生动的民间意趣,如《瓦釜集》附录第一歌:“结识私情过条河,手攀杨柳望情哥,娘问女儿‘你勒浪望啥个?’,‘我望水面浪穿条能更多!’”*刘半农:《瓦釜集》,北新书局,1926年,第63页。诗歌运用了大量方言展现江阴底层民众的风俗民情,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语言素朴粗犷,情感自由恣肆,体现出真实有趣的“民间性”特质。周作人也乘兴用绍兴话为该书写下序诗:“半农哥呀半农哥,偌真唱得好山歌,一唱唱得十来首,偌格本事直头大。……今朝轮到我做一篇小序,岂不是坑死俺也么哥!——倘若偌一定要我话一句,我只好连连点头说‘好个,好个’!”。*周作人:《题半农〈瓦釜集〉》,刘半农《瓦釜集》,北新书局,1926年,第1-2页。与刘半农的歌谣相映成趣。但是,由于这种特质和后来左翼文化所建构的道德导向和审美倾向大异其趣,刘半农在歌谣征集上更多呈现出的学者研究兴趣要远大于革命姿态,加之受众在方言理解上的局限性,无法走向“大众”,因此,尽管这些民间歌谣把五四时期新诗歌谣化的理论提倡在实践上推向了新高度,但在以后的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却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和重视,在后来的文坛中,“以寂寞的样子产生,存在于无人注意的情形中”。*沈从文:《论刘半农的〈扬鞭集〉》,1931年2月15日《文艺月刊》2卷2号
在新诗坛上,和刘半农同时进行歌谣化诗歌实践的还有刘大白和沈玄庐,他们除了作为新诗诗人的活跃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代表大会最早的几个发起人之一,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对歌谣的切入和利用上采取了更为贴近现实变革的角度,作为左翼诗人的早期代表,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侧重于站在鲜明的政党立场上,在诗歌内容中书写劳动阶层的生活和困苦,希望通过这一源于民间的形式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如刘大白1920年创作的歌谣体叙事诗《卖布谣》,“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土布稀,洋布贵,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刘大白:《卖布谣》,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10月,第14-15页。单从诗歌艺术上来说,这首诗的审美价值远逊于其抒情诗,但却因其中包含的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情绪,又加上1922年被著名作曲家赵元任谱上曲子,把农村底层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演绎的如泣如诉,而受到启蒙者激赏。沈玄庐发表于《觉悟》上的《十五娘》,以民间说唱文学为基础加以创新,抒写了一个农村妇女悲惨孤寂的人生命运,被朱自清称作新诗史上“第一首叙事诗”。他们的创作使得“歌谣体”这种作为平民身份的文化象征意味得以彰显,于是,这一本来无意于功利价值的古老诗歌表现形式被援引到急剧变革的文学中,以极端矛盾的方式进入了新文学的视野。
这种体式的出现和创作为其后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成员蒲风、杨骚、任钧等人强劲的无产阶级诗歌开启了一代诗风。此外,新诗对歌谣化的重视改变了以往诗歌在内容和语言上的贵族性,呼应了五四启蒙时期“平民化”的价值诉求,也为后来的民族性和大众化的诗歌建设奠定了基础。由于五四时期文坛的欧化倾向,大部分歌谣体新诗并未引起关注,在众声喧哗的文坛中发出的声音相对微弱,再加上在自身创作上“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中华书局,1936年,第108页。,歌谣体一时也为诗坛诟病。最重要的是,民间歌谣里展露的情思意绪有悖于五四启蒙精神,因而它作为一种新诗资源是否体现了现代发展方向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朱自清在观察了“歌谣体”新诗的发展后认为,歌谣不能称作新诗:“歌谣的文艺价值在作为一种诗,供人作文学史的研究;供人欣赏,也供人模仿——当作玩意儿,却不能发展为新体,所以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朱自清:《歌谣与诗》,朱正编注:《朱自清集》,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对于五四时期文坛对“歌谣体”新诗存在的争议,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五四的民俗文学研究既不是由国家官方发起,也不是市民文化推动的结果。追其导因,则应回到民国初年的历史中去看,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社会和知识菁英的功能与角色之变迁中去看。”*刘禾:《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45页。追溯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起源可以发现,对民俗最初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是来自北大师生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的提倡,而从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一种文学体式的兴起和推动,还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变动以及意识形态的变更演进,具有直接的关联,这也是为何在以后的左翼主流话语中,对刘大白和沈玄庐的“歌谣体”新诗意义和价值的较为推崇的重要原因。
二、“大众化”语境中“歌谣体”新诗的承担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深化,五卅惨案点燃了革命激情,阶级观念日益突出。郭沫若写下了《革命与文学》,把文学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类,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号召文学青年们“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成仿吾在1928年初也谈到文学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为我们的对待。”*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第1卷第9期。由此提出“普罗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茅盾在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并规定了创作的题材、方法和形式,“在形式方面,作品的文字组织,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因此,作家必须竭力排除智识分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言语的表现法”*茅盾:《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8期。“大众化”逐渐成为左翼文学的主流话语,作为“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语”成为左翼文学言说的主要方式。在诗歌领域,“大众化”也成为左翼诗歌的艺术目标,它要求新诗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大众进行政治动员,争取最大限度地得到大众的接受和理解,从而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歌谣以其民间特点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被进一步赋予特殊功能和意义。
诗歌“大众化”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导下成为文学主潮,而中国诗歌会的“新诗歌谣化”运动则最为显明地贯彻了这一方向。1932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之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组织,倡导采用朗诵诗和民歌体等多种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形式推进诗歌大众化,其创作宗旨与左联的革命导向保持高度一致,因此,这一组织所致力的“新诗歌谣化”,和左联30年代提倡的“大众化”之间具有同构关系。1933年2月,《新诗歌》创刊号的《发刊词》发出了为“歌谣化”新诗定下基调:“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同人:《发刊词》,《新诗歌》创刊号,1933年2月。其中所说的“大众歌调”就是要从以新月派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洋化和风花雪月的风气中拯救诗歌,借用民间文学资源以承担新诗的社会使命。事实上,早在中国诗歌会成立之前,瞿秋白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言说,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直接手段,使文艺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艺”。在1932年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中,瞿秋白再次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作为左联领袖,瞿秋白的论述对中国诗歌会产生了直接影响,歌谣作为新诗的一种资源,以牺牲审美感性的代价被纳入了现实政治框架,绑缚其上的意识形态力量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当时阶级意识和政治诉求上升的产物。
左翼启蒙下的“大众化”要求采用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以实现对大众的“教化”,他们认为诗歌是听觉的艺术,因而极其重视歌谣的作用,为了让“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喜欢听,喜欢唱”*蒲风:《关于前线上的诗歌写作》,《蒲风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922页。,《新诗歌》在1934年6月的第2卷第1期还特意开设了《歌谣专号》,刊出歌22首,谣22首,时调与四川、湖南、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的民歌数十首。诗人穆木天在“歌谣专号”中写道:“新的诗歌应当是大众的娱乐,应当是大众的糕粮。诗歌应当同音乐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民众所歌唱的东西。是应当使民众,在歌着新的歌曲之际,不知不觉,得到新的情感的熏陶。这样,才得以完成它的教育意义。”*穆木天《关于歌谣之制作》,《新诗歌》1934年6月第2卷第1期“歌谣专号”。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歌谣化”运动通过诗歌创作实践把新兴的阶级话语和歌谣体这一传统形式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倾向。中国诗歌会诗人任钧在《我歌唱》中慷慨激昂地写道:“我歌唱——我是一口大钟!要用洪亮的声音,去唤醒沉迷的大众……”*任钧:《战歌》,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7年。整首诗歌以宣传号召为主,语言表达平实简洁,形式上自由奔放,而诗歌中的“唤醒沉迷的大众”则紧密契合左翼诗歌实践所提倡的“为着教养、训导大众”*瞿秋:《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的“大众化”目的。但事实上,这些歌谣体新诗尽管采用通俗形式为手段,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感染力,却仍然和大众的心理存在距离,诗句“唤醒沉迷的大众”背后潜隐的正是知识分子对大众自上而下的“训导”,这也是当时左翼文学语境中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时存在的问题,“大众化”的口号和贵族式的姿态出现了一种悖谬。虽然中国诗歌会尝试“旧瓶装新酒”,以民间传统形式承载新的时代内容,但却缺乏一种真正“向下”的眼光,因此尽管杨骚借用中国弹词的格式和调子创作了《受难者短曲》,却反应微弱,成为歌谣体新诗创作一个失败的例子。民间形式成为知识者写作中的乌托邦,而真实的民间并没有和知识分子融为一体,正如鲁迅早年所描述的启蒙者困境中所说,先驱者在追寻光明时“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他们的箜篌了。”*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1-252页。存在于民众和启蒙者之间那难以消弭的“厚障壁”,使得左翼启蒙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实践中遭遇了重重阻碍,在强烈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歌谣体新诗显然变成知识者的集体独白,而真正需要表达自我的民众则成了沉默的失语者。
三十年代左翼“大众化”的倡导把歌谣作为一种重要的阶级文化选择植入新诗创作,其间蕴含的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随之而来的“民族形式”讨论又赋予了歌谣体新诗以新的历史使命。三十年代,面对日益激化的民资矛盾,“民族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话语方式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是左翼力量还是国民党方面都非常重视“民族形式”的运用。站在左翼启蒙角度来看,“民族”主体即是工农大众,早在左联期间,“大众化”和“通俗化”就成为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抗战全面爆发后,宣传抗日和动员群众的要求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内在驱力,进一步把“大众化”推向了中心。因而,左翼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形式”时侧重于对工农大众的启蒙,而“旧瓶装新酒”则是这一时期左翼启蒙作家们创作的主要方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下,“歌谣”这一贴近民间的形式就成为承担新诗“大众化”实践的重要工具。虽然鲁迅在三十年代“大众化运动”讨论中就曾经对“旧形式”这一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早采取旧形式应“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但是,左翼知识分子在利用这一形式的时候,带着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启蒙预设,致使进入新文学视域中的歌谣创作,已不同于以往歌谣所呈现出的民间化和原生态的特点,而是承载着更多的意识形态任务,在诗歌艺术上也缺乏深入探讨。施蛰存就批评中国诗歌会的大众化“乃是民间小曲的革新,并不是新诗的进步”*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1卷第1期,1933年11月。。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抵御外侮的战争进一步激发了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如何更好地利用“民族形式”以配合时代变化成为文坛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郭沫若在分析了当时的现实状况后认为,“民族形式”并非是复活旧形式,而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所以“为鼓舞大多数人起见,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的使用价值,放在民间形式上面”。*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大公报》1940年6月9、10日。而歌谣源自民间,作为民族传统中“野趣”的一种重要载体,在民族认同中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基础功能,而且由于表达方式和语言上的通俗性和直接性,更由于它的构成和生产始终建立在集体性的想象和幻想的基础上,与大众和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思想感情相吻合,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因而在民众中易于传播。四十年代“民族形式”的倡导是对五四以来“全面反传统”宗旨的一次反拨,也是中国现代启蒙者从精英化真正走向大众化的重要转折点。考察“歌谣体”新诗进入左翼启蒙话语的路径,可以看到现实需求的驱动,以及在这驱动背后革命文学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引导,在整合后的“民族文化”观照下,这一诗歌形式被左翼作家挪用到现实经验中,和当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针对被启蒙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功用。
三、从民族形式到“人民”话语的建构
四十年代战争语境下,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如果说三十年代“大众化”文艺的倡导是左翼知识分子由上而下的启蒙,那么进入四十年代以后,左翼文化界出于动员民众的需要,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创作形式,把重点转向发动民众,希望利用大众自身的文化素养来实现文艺的大众化。1938年初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面向大众发出“征求歌谣”的启事,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首次使用“民族形式”一词,提倡树立“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报告无疑对左翼文坛起着决定性作用,延安文艺界反响强烈,其影响甚至还伸展到国统区,从而引发了之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民族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话语之一,歌谣体新诗的发展也在“民族形式”的弘扬下获得了广阔的生长空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所谓的“新文化”应该是把“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两者相结合,这无疑给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指向。这些文艺活动和方针政策说明了这一时期左翼文学对“民族形式”的利用主要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以,试图从美学层次上去分析和评价四十年代的“歌谣体”诗歌的价值也许是徒劳的,知识者对于现代民族形式的乌托邦想象以及左翼内部多种力量的合力建构,共同形成了“歌谣体”新诗生长的历史情境。
左翼文学历来有两大传统,一是让文学起到鼓舞人民和唤起民众的现实战斗作用;二是试图解决文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尽管左翼文学肇始之初就抱着启蒙大众的真诚理想,但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走入了“化大众”而不是“大众化”的误区,无法做到真正的沟通和平等。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讲话》中提出,希望作家们转变高高在上的俯瞰大众的姿态,把注意力投射在接受主体即“工农兵”身上,真正融入大众,采用他们易于接受的形式,创作出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文学。尤其在谈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无疑为“民族形式”的利用又加强了理论上的支撑和政策上的导向。这一姿态的改变也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分水岭,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文学通俗化成为众多左翼作家创作时抱持的观念,同时,高雅艺术由于和群众接受水平不相匹配而被排斥在文学主流之外,“歌谣体”新诗也借由意识形态话语被进一步重视。
承续着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对新诗歌谣化和大众化探索的传统,结合毛泽东讲话内容的精神和对“民族形式”的合理运用,四十年代左翼作家在歌谣化诗歌创作实践中收获颇丰,国统区有以袁水拍为代表的政治讽刺诗,解放区有以李季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以歌颂为主调的民歌体叙事诗,两种不同基调的诗歌相颉颃,成为这一时期“歌谣化”新诗的优秀代表,把“五四”早期白话诗倡导的“歌谣体”新诗试验和“诗的平民化”命题发挥到极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诗作者李季深入陕北民间,亲自采集了近三千首信天游民歌加以利用和改造,把歌谣的形式和方言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歌体叙事诗。这种新型民歌把陕北信天游中大量关于“性”的朴野表达过滤成男女间纯洁的爱情故事,来自贫农家庭的男女主人公则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使民间话语不仅获得了一个合理合目的性的“民族形式”,还植入了现实政治中最为核心的阶级革命斗争主题,从而使阶级性和民族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里的民间已失去了它原初的意义,成为被革命话语改造的“民间”,一种经过“人民性”伦理建构的“民间”。长诗的出现契合了左翼文学对“人民”话语的诉求,成为延安左翼文化表述中“划时代的大事件”,迅速走向经典化。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采用通俗易懂的“山歌”这一创作形式为普通老百姓代言,讽刺国民党当局,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与亲近,在国统区获得了高度评价,这种政治讽喻诗在四十年代社会场域中发挥出独特的政治批判功能,成为国统区“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方向”成功结合的典范代表。可以说,在歌谣体新诗的探索中,四十年代的创作达到了一个巅峰。
从二十年代初期北大学人对“歌谣体”的探讨,到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大众化”口号下诗歌和民间的结合,再到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大力提倡,歌谣这一民间形式在左翼启蒙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可否认,歌谣体新诗的发展历程,是启蒙话语、民间话语和现代诗学相伴相生和复杂纠葛的过程,也是左翼话语和历史语境的双重体现。虽然诗歌中承载的政治功利性使它在社会革命的现实层面获得了众多赞誉,但从诗歌审美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很多欠缺,出现了许多粗浅苍白之作。从现代美学意义上来看,过于直接的政治功利性会造成艺术上的“伪革命”状态,正如马尔库塞所论:“文学并不因为它为工人阶级或为‘革命’而写,便是革命的。……艺术品越带有直接的政治性,便越削弱了疏隔的力量,缩小了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2页。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中国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发展,4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社论文章《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在接下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做了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在一系列行政干预下,一场群众性的诗歌“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面对民歌在新诗创作中几乎一统江山的局面,关于新民歌运动的争议也越来越多。何其芳就认为,因为民歌体自身的限制,它“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会成为支配的形式”*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何其芳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页。。他从诗学角度分析指出,民歌体式的弊端主要在于其句法和现代口语的矛盾,以及相较于现代格律诗在体裁上的单一狭窄,所以在新诗的民族形式建构基础和来源上应该多元化,建议“批判地吸取我国过去的格律诗和外国可以借鉴的格律诗的合理因素,包括民歌的合理因素在内,按照我们的现代口语的特点来创造性地建立新的格律诗”*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何其芳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页。。何其芳把现代口语作为新诗建设的主要因素来考虑,提倡为新诗构造一种合适的格律,然而他关于格律诗的设想引来了大量批判,他有益的提醒也很快就被淹没在“新民歌运动”狂热的众声喧哗之中。
纵观歌谣体新诗在现代文坛的发展,从左翼文学对它的选择和建构再到围绕它的边缘化或中心化的种种争议,背后都有复杂的权力运作的程序,对形式的选择和建构本身就标示了某种价值判断乃至价值等级。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创立初衷是要让民俗成为一种有关“现在的”学问,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认识和改造社会生活”,*中国现代民俗研究开始于1918年2月1日,标志是蔡元培先是成立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在《北大日刊》上征集歌谣,1920年冬又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17日,编印《歌谣》周刊。1925年6月《歌谣》周刊停刊,歌谣运动走过了7年时间走向衰亡,直到1936年胡适主持复刊《歌谣》,又出了一年。歌谣征集是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从这种宗旨来看,歌谣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方式也是现代启蒙的题中应有之意,歌谣体新诗的发现和征用本身又是启蒙者借助民间文学向传统挑战和反抗的一种方式,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歌谣被重新发现并引入现代新诗资源,到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的“新歌谣运动”,再到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歌谣承载了革命话语、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多重功能和意义,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但同时也由于各个时期政治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相应地被赋予不同的特质,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随着场域的不断变化而生成不同的现实意义。
历史和社会语境等外部条件的干预固然对歌谣体新诗的发展走向造成一定影响,但从诗歌的内在发展来看,诗歌形式和诗歌本质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注定了它在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行之不远的命运,正如有学者对“新民歌运动”的分析:“‘新民歌运动’可被看做‘五四’以来新诗走向‘大众化’(民间化乃至民族化)的一次努力。只不过,众所周知,这次努力最终以‘古典’+‘民歌’的极端模式纳入了政治化的轨道,从而适得其反地将诗推向它的反面即‘非诗’,新诗的‘大众化’也未能真正实现,而是越来越远离这一目标。”*张桃洲:《“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现代新民歌由于充塞了越来越多意识形态的内容,销蚀了它天然具有的质朴本真的个性,也缺乏真正的民间立场和民间世界的自在呈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其审美性特质,也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诗歌资源应有的魅力和光彩。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歌谣体”新诗虽然表面上出现了短暂勃兴,但却渐显无力,在诗歌艺术上已难见昔日荣光。通过“歌谣体新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命运,诗歌的民族形式如何与复杂变动的时代相结合,“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9-640页。,这些都将是以后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和建设的历程中需要不断致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 刘宗迪]
李瑞华,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4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创作研究”(编号:12BZW08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