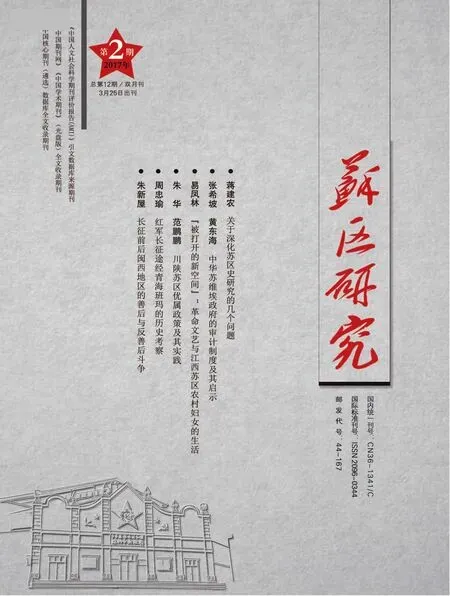关于深化苏区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2017-01-29蒋建农
蒋建农
关于深化苏区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蒋建农
深化苏区史研究,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推进;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考察;要从历史发展的空间来考察;要从苏区史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察;要开展各革命根据地的比较研究。当前苏区史研究面临新的契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重视党史研究,而且十分注重利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庆日,推进党史研究。因此,要避免固步自封,当务之急是整合资源,发挥湘鄂赣苏区论坛之类的机制和平台的作用,协同推进苏区史研究。
苏区史;协同推进;整合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5周年纪念日,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在铜鼓举行,这表达了老区人民对革命前辈当年所创造的革命业绩的无限敬仰。在这块最早响应八七会议的号召发动武装起义和开始创建中华苏维埃斗争的地方,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纪念当年的历史壮举,也表达了湘鄂赣老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好新的长征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定决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推进苏区史研究。时代的高度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可能是对我们党史事业特别偏爱,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就亲自分管党史工作。2010年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下发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党史工作的中央文件,即《关于改进和加强新时期党史工作的意见》。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还作了重要的讲话。在这之后,他围绕党史、国史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比如说在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培训班的讲话、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讲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诞生60周年的讲话、纪念建党95周年的讲话、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等。此外,他还就领袖人物评价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观点。比如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陈云诞辰110周年和朱德诞辰13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阐述了一系列的新思想和新论断,集中阐释了一种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和时代的历史观,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对我们党史研究来说,既是方法论,也是一些具体的结论,是我们深入开展党史研究和宣传重要的思想指引。苏区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精神,站在时代的高度,加强和推进对苏区史的研究。当年,湘鄂赣苏区和其他各个苏区一样,走的是一条中国式的,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今天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的道路。但是秉承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这三大思想原则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因此,我们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通过总结前人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走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借鉴、提供一往直前的动力。
第二,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考察。历史的发展走向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基本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结果,都需要有一定的积淀和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代表的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就是如此。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红军的组成、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区,必须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现在各地都比较注重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做了一些宣传,有不少的文艺作品,也有不少关于苏区研究的成果。但是,有的宣传文章和论著为追求可读性,一味地猎奇,讲传奇、故事比较多,脱离史实附会了许多吸人眼球的内容。我曾听过一位教授讲关于井冈山斗争的课,他过分地强调王佐、袁文才的作用。他说没有王佐、袁文才,毛泽东就无法落脚井冈山;那么失去了王佐、袁文才,红军就没有办法在井冈山立足。在座的很多都是苏区史研究的专家,不难判断他的那种观点是很片面的。在讲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问题时,那位老师也是强调偶然性,说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是因为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让宋任穷同志带来一封信所致。真的这么简单吗?我觉得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参加秋收起义的一个团长王新亚,大革命时期和袁文才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发动之初就从他那里知道宁冈有袁文才领导的农民武装;秋收起义军向永新开进时,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一个学员叫陈慕平,他是袁文才手下一个重要骨干,他奉袁文才之命专程迎接毛泽东;抵达永新三湾的时候,李立后来回忆他就曾奉毛泽东命令给袁文才送过信。可见联系的渠道是多个而不是只有一个。再者,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领导的而不是由江西省委领导的,因此,汪泽楷让宋任穷同志带的信不具有上级指示的性质。从毛泽东个人的情况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明确地把废除封建地主统治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内容,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中他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这实际有建立新型农村政权的意思;提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提出“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是一些非常宝贵的思想火花,是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最初探索。可惜,这一探索由于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没有实现。所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说他关于必须站在农民前头领导农民的观点,“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由此,他得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结论。正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思想基础,大革命失败之后,瞿秋白让他到上海去,到中央工作,他不去,他要下湖上山,所以他在打长沙遇挫后选择去井冈山去落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见,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不是一种偶然,他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红色政权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三位一体”。所谓“三位一体”就是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这和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革命后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思想探索,就没有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率队伍上井冈山的历史抉择。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一定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去看历史,而不是过分地强调偶然性和戏剧性。那样的话,高等学校的教授不就沦为井冈山的导游了吗?
再如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究竟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还是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抑或是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学术界观点不一。我觉得如果把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不难划分出若干阶段,并得出一些相应的概念。如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个人认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井冈山时期形成的,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是第三次反“围剿”时形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时间,还是应该以1936年10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课为标志,这可能更恰当些。总之,孤立地看某一历史现象,往往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总是将其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联系起来,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联系起来,与中国近代170多年的历史联系起来,甚至与社会主义学说500多年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他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联系的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我们在研究苏区史时必须学习和运用的。
第三,要从历史发展的空间来考察。每一个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都有其地缘因素。现在各地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时候,大家纷争不已。我们一些党史工作者也推波助澜。比如说鄂豫皖根据地那是一块有着共同的地缘因素的革命老区。现在湖北红安的同志说许世友的家乡当年属于红安,现在划到河南新县,因此计算各县将军数的时候,许世友上将应该算到红安;河南商城和安徽金寨也争,河南的同志说洪学智自己填表就说他是商城人,现在怎么可以因区划变更将其出生地划入金寨而说他是金寨人呢?与此相关,有些县的党史工作者脱离历史实际,不恰当地强调他所在县在创建鄂豫皖苏区中的作用。如果都这么各说各的,县与县、省与省出版的书籍互相矛盾。那么,我们的苏区史研究就会支离破碎。这种现象在前几年申报苏区县的时候,尤为突出。一些学者不惜歪曲历史,突出自己所在县市当年在中央苏区时的地位,贬低邻近地区的作用,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学术作品”。这对苏区史研究干扰很大。事实上,鄂豫皖地区是因大别山纵横其间而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了相同的经济、相同的文化和相同的习俗,以及盘根错节的血缘和宗亲关系,这种状况由来已久。不能因为今天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我们就非要把这种共同的历史空间割裂开来,各说各的。不管前因、不管后果,把空间也彻底撇开,只突出某个县、某个市。
再如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研究,也存在着刻意渲染两个根据地之间矛盾的做法和故意为肃反错误文过饰非的行为。事实上,这两块根据地都处于少数民族和汉族发达地区中间地带,有着共同地缘和宗亲关系。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陕北根据地的支持与帮助,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陕甘边根据地的帮助与支持。由于反动统治势力的分割,在一个时期里,这两个根据地相对独立地平行发展;虽然它们与上级的领导关系不一样,一个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一个由中共北方局领导;虽然双方在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方式、方法上不尽相同,甚至在其完全融为一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干扰、危害的情况下,在一部分同志中间甚至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在总的方面,它们都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都是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开展斗争的;这两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参与者,有着共同的奋斗理想和斗争目标,有共同的地域关系和生活环境,自打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根据地在干部、人员方面互有交叉和补充;在发展指向和区域上,既各有侧重,又经常不谋而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双方不仅在战略上互为依托和支撑,而且在战役、战术方面的配合更是一种常态。即使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肃反,虽然主要矛头指向了陕甘边根据地的领袖和骨干,但是陕北根据地红二十七军的领导人,也一同被撤职、调离,受到打击和歧视。总之,双方这种亲密无间、共同奋斗的关系,是其最终能够融为一体共同组成陕甘根据地的根本条件。因此,我们说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不只是陕甘边,还包括陕北;同样,我们说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也不只是陕北,不能撇开原来的陕甘边根据地。所以,我们研究苏区史不能人为地撕裂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地缘空间,而应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和深化苏区史研究。
第四,要从苏区史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中国社会性质有什么变化?与此相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些问题在当年曾引起国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的两派意见争论不已;在国统区进行了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国史大论战、中国农村问题的三大论战,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各党派和各界人士都踊跃地参加,论战前后持续三年之久;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围绕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党的六大明确了中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这些都符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任务的实际。但是也有不和谐的,那就是应该由谁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当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恰恰含混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叫中产阶级,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是不是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了?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是革命的团结和依靠对象呢?对此,党内的认识有错误。再者,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不是和中产阶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的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当年的错误恰恰就是在于混淆了他们究竟是团结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对象问题。于是就把中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作为革命的敌人,一同打击。当时在各个苏区普遍地开展反第三党、反改组派的斗争。第三党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会委员会,他们始终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邓演达将其发展为平民革命的理论),坚持进行反对蒋介石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组派首领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臭名昭著。但是改组派的旗号是要恢复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改组精神,它和第三党一样也是反蒋的,其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在改组派中有不少国民党的左派,比如何香凝和许德珩(新中国成立后都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就曾经参加过改组派,改组派中的不少人也受到蒋介石的追捕和暗杀。但是,当年我们却把他们都作为敌人对待。这就混淆了革命的对象,这是各苏区普遍出现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主要原因。
肃反问题是苏区史研究的热点,也是坊间一直广为关注的问题。对于肃反扩大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学术界认识不一。我认为既有革命斗争形势严酷,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白色恐怖下,我们内部有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反水;又有蒋介石和其他反动势力派人进行策反或打入我们内部的现象;还有我们队伍中的土客籍矛盾、山头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不良影响;也有盲目学习、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一些不恰当指挥的因素,特别是在几次由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党中央领导权的时期,还存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问题。上述五种情况都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留下血的教训。而这些血的教训的一再发生,反过来增强了人们对肃反必要性的认识和对肃反扩大化现象的宽容。当时在各个苏区都设置有多个层次的政治保卫局,红军各军团中的保卫局局长级别很高,与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平级。我认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对阶级力量的分析不正确,也就是在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这一阶级路线问题上出现偏差,把在民主革命阶段本来应作为团结和依靠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作为打击的对象,甚至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才导致各苏区普遍出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由于存在上述主客观的因素,因此也可以说,肃反扩大化的恶果尽管让人痛心疾首,但势在难免。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同志呢?肃反扩大化错误为害时间很长,几乎延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同志为数很多,包括一些党的领袖人物,还不乏一些著名的革命烈士。各自犯此错误的原因也比较复杂。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初期,主要是受认识水平的局限;也有一些是因为中央的路线错了,他们因贯彻中央路线而犯错误,像派到湘鄂赣根据地的林瑞笙、闽浙赣苏区的万永诚、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和派到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成员顾作霖等,都是奉命去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的王明路线,后来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犯错误同志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并转而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如邓中夏烈士曾经被派到湘鄂西苏区(洪湖)贯彻“立三路线”,后被派去推行王明路线的夏曦以执行中央路线不力而受到打击。回到上海后,邓中夏向党内同志坦承自己的错误,并转而坚决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直至被捕英勇牺牲。再如沈泽民,他在鄂豫皖积极执行王明的路线,但是他革命立场十分坚定,他本来可以在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当时他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但是他泣别妻子张琴秋,主动要求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继续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一直到病逝。在病逝之前,已经觉悟的沈泽民用最后的气力给中央写信,深刻检讨他所犯的“左”倾错误,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当然,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人当中也有少数执迷不悟的,一错再错;还有李韶九、戴季英那种个人品质恶劣者肆虐其中,更有张国焘那种利用肃反消除异己的罪恶行径。总之,尽管肃反扩大化错误危害极大,达到让人深恶痛绝、无法容忍的程度。但是从总体上看,肃反非常必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保证革命事业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而肃反扩大化是历史造成的,犯此错误同志中的绝大多数是一种思想认识的错误。我们既要永远汲取其中的沉痛教训,又要对此错误予以历史的分析,更要看到在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已经全面地纠正此种错误,并开始查找其历史和思想认识根源,力图从源头上予以防范。对于那些不同程度犯此错误的同志,也要有辩证的分析和评价。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有“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的诗句。套用其意,犯此错误的多数同志与受其冤屈迫害的同志,以及未受牵连的其他同志一样,在总的革命目标和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或是改正了错误,或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即使是其中错误严重、非议很多的夏曦,也是作为革命烈士载入史册。在如何看待中共自身的错误问题上,80多年前邓中夏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被捕后严厉驳斥敌人的挑拨时说:我要问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疮三期的人,有何资格笑话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错误,我们有很高的自信力,我们敢于揭发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也能克服一切错误。我们知道相对于我们的正确主张,错误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你们有何脸说别人的错误与缺点,你们真是不知羞耻。今天,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不能罔顾这段历史的主流而把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史写成我们党犯“左”倾错误的内斗史。十年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重新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炬,发展了30万的红军,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大众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既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主流。
与此同理,在苏区革命斗争史上,尽管当年的共产党人在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甚至有一些今天看来幼稚可笑的行为。但在总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屈不挠勇于奋斗的,他们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是坚持推进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其基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他们是站在历史潮头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弄潮儿。我们只有紧扣历史背景,以是否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为准绳,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现象,才能够正确地把握历史,防止以偏概全和一叶障目。
第五,要开展各革命根据地的比较研究。毛泽东1930年1月5日在给林彪的信也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做过一些修改),就讲到李文林式的、方志敏式的、朱毛式的和贺龙式的根据地。也就是说,当年在各苏区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各根据地具有不同的特点。党内总结和交流各苏区的经验,可以取长补短,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今天通过对各苏区的比较研究,则是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各个苏区的发展历史有共同的内容,比如都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都是贯彻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湘鄂赣苏区是最早响应八七会议的号召,在1927年的8月中旬就开始有武装起义、武装暴动;湘鄂赣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坚持了十年,一直到改编成新四军,是贯穿土地革命时期十年历史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又是处在三省省会城市的中心区,就是长沙,南昌,武汉,也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区,其战略地位和辐射作用是其他根据地不能比拟的;这个地区成长起来的红军部队,不仅为中央红军提供了红三军团这样的主力军团,也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提供了重要的有生力量;湘鄂赣苏区不仅辐射到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区,而且还影响和支持了在不同阶段存在的井冈山根据地、湘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以至鄂豫皖这样一些地方。再如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红四军,党的领导作用非常突出,可以说创造了“党指挥枪”的典范。这支队伍最早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上井冈山之前的三湾改编中就把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经常给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写报告,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甚至是明知道上级的指示与实际不符,一方面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见,同时仍要执行命令,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原则和自觉的组织观念;从1928年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开始的时候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就改成红四军),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就举行了9次;中共红四军前委不仅指挥红四军的行动,而且指挥红四军所在区域的党的工作,走到哪里都和当地的地方党召开联席会议,这就是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开端。总之,每一个根据地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都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现在当务之急是加强各苏区的比较研究。众所共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全面总结。假如我们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系列结论为指导,反过来逐一对照和梳理各个苏区的历史情况,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进行比较,看看哪项政策是哪个根据地最早提出的,又是哪个根据地在贯彻执行中最富成效或最有心得。我想通过反复地比较和研究,肯定可以大大地推进和深化对苏区史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经验的认识。
苏区史研究面临新的契机。有一种现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重视党史研究,而且十分注重利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庆日,推进党史研究。比如说抗战的研究,在2014年和2015年围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形成浓厚的宣传和研究的氛围,全国的抗战史研究因此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变化。今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又有一系列活动安排,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7月18日在宁夏将台堡讲长征、9月23日在参观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时再讲、在10月21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更是发表了全面深入的重要讲话,他的这些重要讲话和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大大地推动了对红军长征历史的研究。明年是建军90周年,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党中央肯定会有一些重要的举措来纪念和宣传。那样,苏区史研究很可能在明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契机和新的发展。现在像湘鄂赣论坛已经连续召开四届这样的平台,已经很少见了。我们当务之急是整合资源,发挥湘鄂赣苏区论坛之类的机制和平台的作用,协同推进苏区史研究。反之,如果继续各自为战,各守着一方水土,固步自封,甚至不惜贬低其他地区的光荣历史以突出各自领地的作用。那么,苏区史研究很可能就走上一条歧路。我个人建议江西省挑头,组织一个中国苏区研究会,吸引和协调全国乃至海外的中国苏区史研究力量,有计划有分工分步骤分课题,搞好整体规划,多组织些类似于湘鄂赣论坛这样的平台,利用好《苏区研究》的窗口效用,肯定可以推进和繁荣苏区史研究。
(此文是作者2016年11月6日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的主题发言)
责任编辑:何友良
Several Issues on Deepening the Studies of Soviet History
Jiang Jiannong
In order to deepen the study of Soviet history, we need to advance it by 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the times; investigate it from these aspects, comprising the logic and the spa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e also need to carry ou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The current study of Soviet history is facing a new opportunity, that i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not onl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Party History research, but also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promote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by utilizing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festivals. Therefore, we shouldn't feel conceited, and should avoid complacency. It is imperative now to integrate resources, by exerting the mechanism and platform of the Forums in Hunan, Hubei, and Jiangxi Soviet areas, in order to push on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Soviet history.
Soviet history;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integrate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2.001
蒋建农,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主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