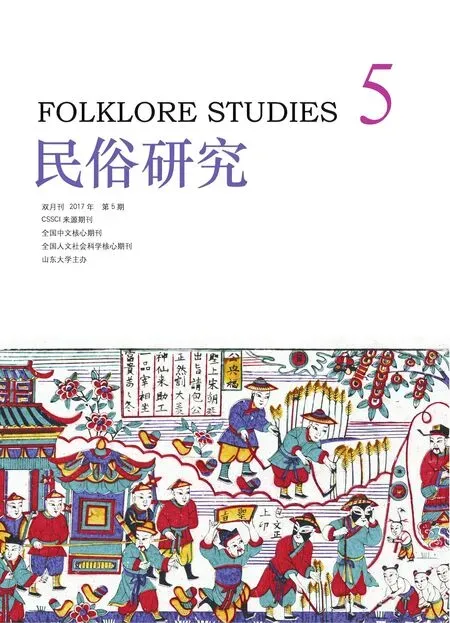论节日空间的生成机制
2017-01-28宋颖
宋 颖
论节日空间的生成机制
宋 颖
以往对于节日的研究大多关注在时间上把节日作为一个独特节点的风俗,在空间视角上使用“文化空间”的概念来描述文化活动的存在现状而缺乏相应的学术支撑,理论探讨后续乏力。因此,针对“文化空间”的局限性而提出了“节日空间”的概念并详细探讨了生成机制及文化意义,重新讨论了“文化空间”“民间”等说法及其与空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节日的六种空间机制和生成原理,旨在探讨节日发生的根源,这其实是在关注节日作为社会活动的空间化表达及“每一次呈现”的表述意义,强调“这一空间”的理论价值。节日空间的研究是重要的学术问题,对于节日空间的深入理解将推进节日研究。
节日空间;生成机制;文化空间;民间;文化表述
节日研究往往着眼于“传统”。中国的几个重大节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事象多样。作为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节日民俗的梳理与研究,也多关注历史发展脉络和沉积形成过程,看重田野个案积累。此类事象研究和过程研究,由于时代原因,基本上是对以“乡村”为主的生活内容的记录和分析。回顾民俗资料和整理的百年史,相较以往而言,尽管已经突破了一般化或地方化的风俗描述和收集,有关节日的研究还是大多停滞在时间维度上对于一个独特时间节点的关照,研究集中在探讨时间上的独特性而引发的民俗事象的变化与传承。即便是记录或关注地方风俗的差异化和多样性,也是以节日作为时间的节点,重点在于事象的细节描绘,而非关注空间上的特质。
空间作为考察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维度*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可以推动节日研究面对当下的时代语境,有必要尝试打破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划分。更重要的是,突破对于节日的“时间”特性的关注,而将节日发生置于“空间”中来重新审视。这一聚焦于空间的视角,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加贴近对于节日本质的探索,更新相关的认识。
一、“文化空间”的局限性
空间视角和相应的概念,并非第一次引入节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语境中,已经从文件层面上在申报过程中使用并应用了“文化空间”的概念。自2001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文化空间”来命名当时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后来延用至“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截至目前,有十余项被冠以“文化空间”而得到承认。尽管在1989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就出现了“文化空间”一词,主要用来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种重要形态。一个具有文化性质或意义的物理空间或地点,被称为“文化空间”,这一地点集中举行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也包含了人类文化活动出现的时间。因此,“文化空间”这一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它强调先要有一处物理意义上的场所,通常包含有建筑或遗址等;其次要有以人为主体的文化活动,通常是当地有突出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活动;第三是要在一段时期反复出现的活动,这意味着通常是当地的某种传统,周期性地发生并出现在这一场所内。
当“文化空间”这一概念出现后,常用来描述某一场所“集中表现”的人类文化活动。不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化空间项目的认定过程中使用,而且被搬移并直接应用于指称类似的文化活动。当澄清了文中上述三点的概念内涵之后,即“地点”“人”“时间”,一旦当人们认识到这一概念同时也包含了时间上反复出现的某种“传统”式的活动之后,独特的空间视角便消失于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活动的理解中。这样一来,“文化空间”往往就此被当成了“有文化传统的地点”,而失去了从空间视角来考察文化活动的意义。又或者是,“文化空间”中自身强调的“文化事件的时间”,最终还是导致了人们忽视了“空间”视角。
正是基于组织化的工作认定产生的概念,引起了学界试图征引概念居多,一般篇幅不长,或如向云驹、张博、李玉臻侧重于谈论非遗保护*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李玉臻:《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或如詹福瑞等脱离非遗语境挪用“文化空间”概念*詹福瑞等人的专题讨论,见《转型时代文化空间的建构》,《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另有注重于讨论节日风俗,兼用一点“文化空间”的概念*萧放:《城市节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宋明以来都市节日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关昕:《文化空间构建与传统节日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5期。,如萧放是在研究古代城市中的节日习俗时提及了庙会的市场空间和消费空间,又如关昕在行文中提到了节俗的“生活场景”“生活环境”,使用了复合式的“节日文化空间”。除了陈桂波讨论了“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的区别与联系外*陈桂波:《非遗视野下的文化空间理论研究刍议》,《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能兼顾术语流脉的探讨则非常之少。因此,在理论探索和延展上,这一术语显得后续乏力。
概念的应用便捷导致了理论上的过少探索,相应的,由于缺少学术流脉的连接和延伸,概念的局限性便逐渐暴露出来。乌丙安使用了“民俗文化空间”*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认为这是“每年固定周期性地在固定场所举办的具有规模性的综合文化活动”,而“在三批90个代表作中……也把节日文化空间计算在内统计的话,共有19个”,他在计算国家级非遗项目时,也把“节日”当作“文化空间”来统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保护工作中,“节日”像这样被等同于“文化空间”,当然也有人干脆用“文化空间”来重新定义节日。如崔莉萍认为,“节日是人类在时空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空间”*崔莉萍:《节日传播的文化空间建构》,《新闻大学》2012年第4期。,提出了四个维度的节日文化空间建构,包括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展开,讨论节日传播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和呈现原因。
上述研究认为节日是文化空间,这说明了,从术语层面上“节日”和“文化空间”之间缺乏辨析,或被混为一体,或被替代使用。也说明了对于节日的研究,很有必要与“文化空间”的概念和工作认定相互辨清,或者另寻他路来使用其他术语应用到节日研究当中,而不是简单搬移一个工作概念。可以说,由于“文化空间”概念本身仅是描述文化活动存在状态的有限概念,把节日局限于“文化空间”这一工作使用的“文件间概念”上,不仅脱离了“节日”作为一个学科术语的理论流脉,也不具备进一步展开理论延伸的可能性。
在节日研究中,突破时间维度后,并非要强调节日的“地点”特质,也不必把“习俗事象”换成“文化事件”,而是要讨论节日生成的“空间”层次及其价值。综合来看,无论是从十余年来的非遗保护工作认定还是国内学界使用情况上,“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仅是某些人类活动存在状态的现状描述,缺乏学术解释力,不具有“节日”生成机制意义上的探索能力。同时,更糟的情况是,简单地替换“节日”会抹杀节日在时间维度上长久以来的积累和认知。因此,与其说,节日是某一“文化空间”,不如说文化空间是节日在某些特定时空和特定视角中的一种呈现方式。与其把节日当作一个“文化空间”,不如在“节日”以往研究的学术基础上,使用“节日空间”这一术语,来重新审视在空间维度上具备多个层次和多重意义的节日,立足于“节日”本身,从而推动对于节日的认识和研究。“节日空间”作为一个术语,并不影响“文化空间”的概念在现实工作层面上的继续使用,却有益于推动节日研究的理论进展。
二、在空间维度上探索节日
在文化空间的基础上,提出“节日空间”这一术语,不仅超越传统上的时间维度研究的束缚,还可以超越文化空间的泛化描述,在此立足点上,可以初步探讨节日空间发生的几种可能的存在状态,进而对于节日空间的生成机制有所认识。
笔者认为,“节日空间”包括了如下一些层次:
(一)绝对空间。与时间维度相呼应,并可以在此相互分界的是,绝对空间强调了节日空间的本质意义。从源起上看,节日是时间中的节点,是漫长的、一元方向的、同质性的时间流中的一个特殊的点,节日发生并打破了时间的同质性,出现了不一样的时间点,由此才开始在时间流中分出了“二”,有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时间。而新产生的节日时间点,同时也是同质空间中不同的空间点,由此在空间当中划分出了“二”,形成了不同于一般空间的新空间,成为了“节日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日的节点不仅是一个时间点,也是一个空间点。节日出现会伴随着节日空间的产生,空间与时间之间由此产生了基于“节日”的关联,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时间和空间的独特意义。节日空间同时也与节日时间发生了关联。可以说,在人们庆祝某一节日时,才真正地使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相互之间区分开来,“节日空间”是这种独特意义上的新空间,在这种特定时间点上,某一个特定的空间才真正地存在并具有了特定的意义。也就是说,混沌一片的空间,由于节日的产生,才伴随着时间上的区隔而彼此之间相互区隔开来。节日时间的呈现和表达,是借助节日在空间当中的发生和变化而得以呈现和表达出来的。这种绝对空间,可以说是纯粹的节日空间,从理念上来说,是与节日时间发生密切相关的,是最为基本却最为抽象的一种存在状态。
(二)概念空间。节日形成以来,一个节日与另一个节日之间,时间点是肯定不同,空间上的表现也有所不同。这都离不开人类作为主体的参与和表达。一些节日在传承过程中,成为了不同于其他节日的重大节日或者传统节日,像中国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以笔者曾经研究过并较为熟悉的端午节习俗和事象为例,可以从中来进行一般意义和概念上的“端午节”观念的传承和认知探讨,与节日有关的“概念空间”使得处于历史长河的人们之间,无论是书写者、记述者,还是被书写讲述的人类活动,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交流、比较和对照,共同来探讨某种“我们的”(属于某一群体的)“端午节”,形成“共识的”端午节。如果没有这种“概念空间”,基本上也就失去了人类主体性的意义,难以形成节日的文化认同,相应的传承和凝聚力也无从谈起。因此,这种承载空间即是这里所提及的“概念空间”。在这一层次上,节日的本意和基本概念有了可供讨论和比照的标准。“概念空间”承载着的是对这一节日的观念上的界定、认识和想象。节日的本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也是抽象的,不具体的。无论节日怎么变迁和表现,在概念中的端午节基本是不变的,是具有最广泛的共同性的某种“共识”,在最大程度和范围上能够“共有”。这使得概念空间承载着节日的传承,是节日传承存在的基础。
(三)认知空间。对于传统节日描述和认识,首先是基于节日的传承,这种传承就形成了节日的历史。因此,不可忽略的是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和回忆性的风俗岁时笔录。节日的历史和相应的发展过程,在之后的“未来”当中都会有某种呈现和表达。在这一层次上,展现的是“记忆”与“回忆”的端午节,“描述”与“书写”的端午节,记录者以一种面向过去的姿态,在他记录的当下来呈现某种形态的端午节,可以看做是书写和记忆对于端午节习俗的“阐释”和“再现”。这种记忆,充满了不确定性,徘徊在记忆和遗忘之间,充斥着模糊与精确的纠葛。不过,在这一过程发生的同时,像端午这样重大节日的习俗事象成为文献,成为某种传统,成为某种认识,而重叠和沉淀在这“认知空间”当中。这些端午节的资料和呈现,不仅面向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所谓的“传统”节日习俗,由此而具备了未来再次再现和演绎的基础。这也是节日习俗在当今时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再现和面向公众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节日发生的“认知空间”,可以脱离时间,并且不必拘泥于某个时间而存在。
在认知空间,有人的主体参与和理解,不同于概念空间的是,它不再拘泥于某种“共识”或者“共有”,而是强调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不断发生着对这一节日的赋义和再阐释。认知空间为节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它是具体的,是可供描述的,并且这种描述是可以反复出现和存在的。认知空间,使得节日具备了不断出现的、各具特色的、多样化的呈现和表达的可能性。
(四)事实空间。这一空间承载着节日期间真实发生的活动和行为。作为现象呈现的端午节,充满了具体的细节,是可以被观察、被记录、被描述的,是在四维空间中发生的行为与活动、仪式与祭祀、游乐与生活等的内容和实践。这些真实发生在实践当中的阐释、呈现和表征,每一次都是独特的一次,都是不可重复的,都是没法复制的,都是瞬息即逝的。每一次发生都不一样。因此,节日在这一空间中,每一次发生就将空间重新表达了一次,将空间形塑为“这一空间”,而非其他任何空间。事实空间可以根据行为实际的空间领域而细分,包括:城市—乡村、家庭—社会、宫廷—民间。例如清代徐扬的端阳故事画册,是在端午当日由宫廷献给皇帝的。在敬献的彼时,是事实空间的行为,可以称作第四空间的行为,真实事件发生之后,就归属于第三认知空间的端午节事象。并不是所有第四空间的节日行为发生之后都能够归属并沉淀入第三空间。这种归属需要借助于其他载体来呈现而得以实现,行为的主体并不必然要一致。顺带来说,“民间”也产生于这种空间之上。基于这种空间,才有民间。*[德]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作者提到,民间不是指向历史世界的,而是基于“空间”产生的。这一说法值得关注。
基于这四种节日发生的空间存在形态上的划分,我们才有可能穿行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空间当中来认识并探讨诸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及其习俗的表现。这种讨论是“文化空间”概念所远远不能支撑和讨论的,是工作概念难以企及的某种学理思考。
三、“这一空间”的重要价值
可以说,基于“节日空间”这一术语和相关讨论,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节日的发生,使得某一空间成为“这一空间”而非其他空间,从而将“这一空间”区别开来,同时赋予了“这一空间”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这样,一次发生才有了被书写和记忆的可能性,也才有可能继续传承和得到再次呈现,尽管,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会完全相同,也无法完全相同。
每一次呈现的意义,同时也是文化表述的意义,是现象存在的意义,是最贴近节日本质的意义。因为,只有在每一次呈现中,人们才其实是“过了这个节”,才是真实地“过了一个节”。如果节日失去了空间上的呈现,而仅存有时间上的节期标识,不得不说,这时的节日已经是个死亡的节日了,“它消失了”,像寒食节。
而另一方面,如果节日的空间不断被搬移、被展示、只在具体现实中呈现自身,对于这种失去源头,或者失去群体,或者失去记忆而作为断裂的碎片的呈现,如何来理解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这究竟还是不是节日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完全可以从“节日空间”的多个层次上来加以理解:这种呈现,由于只是节日空间多个层次当中的一种,它也形成了节日空间中的“这一空间”,仅仅作为一种表述存在。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这样看,节日在某一当下的表述,成为某种民俗主义的展演现象。对于节日研究而言,这种被传统的节日研究所鄙弃的展示活动,恰好是民俗主义视角的一种新关照,也是值得讨论的节日现象,也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在学术与实践之间,“节日空间”这一术语,提供了与“民俗主义”等概念相互之间衔接和讨论的可能性。在民俗主义视角下,比如说节日展示的事象细节等内容,或面对的受众对象等特点,或其他实践当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权衡关系等,都成为可供讨论的学术问题。而相应的是,民俗主义的文化展演产生了很多割裂成碎片的“这一空间”,像这种以往无法纳入研究的展示,在“节日空间”的术语基点和理论认知的多种层次上,就可以成为研究对象,进入到节日研究的关注和解释中来。这对于理论和实践两种立场的人类文化行为都有益处,一方面,学术研究有了更大的包容力;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有了相应的解释性。
对于这种情形,有必要在这里用具体的传统节日来说明。从端午节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节日空间”和“民俗主义”两种概念的应用曙光。传统的端午节,很早之前就有一种被称为“竞渡”的民俗事象得以发展,非常活跃而成为了“龙舟赛”,不仅超出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在实践中也跨越了国界。节日当中的一种民俗事象,或者一种文化活动,固定地出现在某一地点,不仅是某一“文化空间”,而且超越了这一“文化空间”,而延展为体育赛事。可以说,对于这种事象的理解、认识和把握,不仅超出了以往民俗学的研究范围,而且超出了文化空间的工作概念,几乎很难用这些既有的概念来把握这种具有文化性质的活动事件。于是,以往我们常常认为这种新发展不是民俗,也无法加以研究,而把它们冷落在一边。而传统节日,也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象发展成类似的模样,而显得格外冷清,亟待保护。
但是,在具体实践当中,甚至在国际交往中,某一空间中的文化事件不容易得到交流和相互理解,通常只能被看作是被个别群体所拥有的“遗产”,结果只能将这一空间当中的人与其他空间当中的人隔离开来。但是在人类的真实生活中,诸如龙舟赛所代表的人类小规模的群体性体育运动,本质上却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和对话的可能。因此,从节日发展过程中看,从竞渡习俗发展而来的龙舟体育赛事,超越了地方性,超越了民族性,超越了国界,得到了更大范围更广人群的喜爱,这一活动频繁地、固定地、有延续性地举办和进行着,有益于将某种具有文化意义的节日符号转化为身体训练和单一诉求的功能化的工具,突破了多种限制而得以普遍流传,更容易进行文化交流,甚至更容易传播某种节日原有的文化意义,即使它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这种传统意义。在端午节的传统中,龙舟竞渡是较为普遍的节日事象,这种单纯诉求的体育交流,并没有完全淡化和消解端午节作为一个节日的符号性,而龙舟赛成为理解端午节的入口,节日也在龙舟赛这种空间表达中延续。可以说,龙舟赛这种体育赛事,甚至并没有完全摆脱和抛弃节日的文化意义。
因此上,看似无关的体育赛事,可以成为传统节日复兴的契机。在每一个龙舟赛事举行的空间里,都可以视为是对节日当中“这一空间”的搬演,是对“节日空间”中多个层次和多重意义上的某一层次的呈现和表述。
而节日风俗当中的多样事象,不一定具有相同分量的功能和意义。具体以端午节为例,“划龙舟”在很多情形下被视为是端午节的一个符号。相应的是,出现了“符号化”的节日。节日中的符号作为一个整体或单独作为一个事象,再次呈现为一个符号化的节日。节日中的符号可以单一“移借”,这种现象,笔者曾在“节日事象的共有、扩散和移借”中有所讨论,但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针对节日事象的研究,另文详述。而节日事象“移借”所带来的空间效应,简言之,当若干符号在一个空间中组合为或者重组为一个节日,就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重新形成一个符号化的节日。这使得恢复某种书面上的、或者历史上的、或者“他处”(其他地方有过)节日的传统“样貌”,也即是节日的“复兴”成为可能。“节日空间”的概念和多层表达,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些复杂的当代生活现象。并对其中一些复杂多维过程,有所认知和理解,乃至有可能应用于实践当中去,让传统节日的恢复和庆祝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传统节日,或者索性创造出一个新兴节日来。脱离开“节日”来说,空间维度提供的探索模式,可以应用于多种民俗事象的复兴或再造。
“文化空间”概念可以追溯到列斐伏尔讨论城市化时提出的“空间的生产”等观念。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区隔,往往意味着乡村与城市的空间区隔。从空间来看,城市特有的娱乐与消遣部分的节日习俗事象,如端午节中的画舫嬉游,极尽工巧的香囊绣品等,在乡村生活中也有某种可能会发生或者会被记录,尽管也是充满了明确的目的性和功能性的,背后却常常蕴含着宗教般的祈愿和信仰的意义;这种情形与在城市中的习俗表现是明显不同的,城市中的节日习俗脱离了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下赋予的意义,而成为了表述(表征)*[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同时具备了符号化存在的可能性。在城市中,节日习俗可以成为某种展演、展示,可以用来单纯消遣,而消解了背后的生死观念、灵魂观念和意义追求。这种现象并不是当前全球化和现代化之后才有的,而是在古代中国城市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以往被我们以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和历史眼光遮蔽了。“文化空间”概念也无从把握和分析这部分现象,而从“节日空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习俗,对于当下的文化复兴和习俗再造及其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保护和存续,可以提供值得借鉴和反复思考与讨论的经验。
四、“节日空间”的未来发展
阿诺德·J·汤因比在其《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的挑战》中指出,要从世界性政府、高级宗教和科学技术等三个方面来思考人类文明的各种习俗在当今所面临的挑战,并发生变革。*[英]阿诺德·J.汤因比:《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的挑战》,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受政权更迭和信仰的影响,传统节日的习俗已经在数千年来发生着缓慢的变革,那些新的成为了旧的,那些旧的也在不断地翻新。而对于节日发生和呈现空间的未来发展,还要纳入技术的因素,并作为更为重要的一个变量来加以考虑,这里继续探讨两种空间存在的状态:
(一)虚拟空间。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载体,在创意城市概念探索及其建设和实现的过程中,可能为节日的发生和存续提供广阔虚拟空间。这不仅包括了目前网络上的以节日习俗为主体的信息传播,还包括对于以往的认知空间和事实空间相结合的一种展现的新的可能性。这部分也有可能成为公共民俗演绎的广阔舞台。例如,春节有屏幕上的鞭炮声,清明有网上扫墓寄托哀思,端午节也可能出现新的游戏和娱乐方式,如网上虚拟的龙舟赛,虚拟香包,以类似于“愤怒的小鸟”式的游戏来重新消灭“枭”与“獍”,弘扬孝道等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更为崇高的爱国主义,借助多媒体手段的展示、再现和传播节日习俗并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的内容。
(二)多重空间。借助手机终端等设备和新型通讯渠道的发展使得人类可以同时存在于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同时穿行于认知空间和事实空间,实现多重空间内同时存在的状态。对于多重空间的节日习俗表现和多维度同时发生的交流,只要准备好开放的头脑和眼光,准备好接受新的冲击和挑战,完全可以对此拭目以待。
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指出,日常生活并非自行发生的、超越于人的存在,而是受控的、非主体的、已经成为社会组织运作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并不是说要把一种欲望或者一种功能,定位在一个已经存在的空间中,而是相反,要将社会活动空间化。”*[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在节日习俗的历史流变和书写中,在节日发生空间的“每一次”及“这一次”的呈现中,让我们共同参与并创造面向未来节日习俗的新变革,而这一切在当前新世纪的发展中,已经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刁统菊]
宋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文学的传承、创新与影像表达研究”(项目编号:17BZW17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