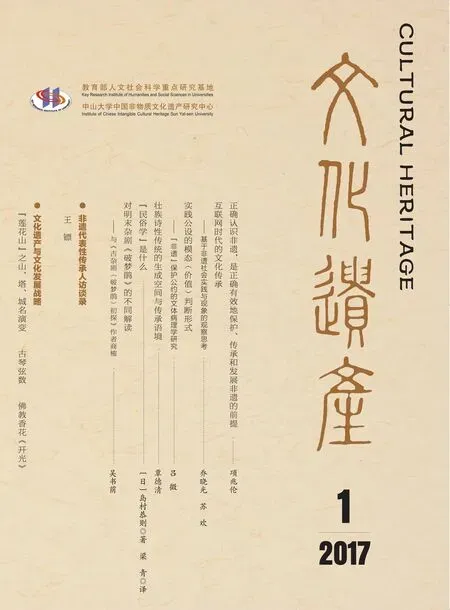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2017-01-28刘建华
刘建华
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刘建华
在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民间故事中,异类婚故事资源都极为丰富且影响深远。但我们关于异类婚型民间故事的“概念”大多是建立在汉民族汉文化异类婚故事的基础上,并由此形成一些有关异类婚故事的“刻板印象”,而维吾尔族异类婚故事在很多方面却恰恰颠覆了我们对异类婚的“常识性”认识,在婚恋行为本身,婚恋对象、婚恋结局等多方面都与汉民族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折射出民族文化特质方面的差异。通过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面上认识和发掘两种文化的内蕴及其特质。
民间故事 异类婚 比较研究 维吾尔族 汉族
“异类婚型”民间故事一直广受维、汉等各民族人们的喜爱,此类故事研究成果也远远多于其他类型的民间故事。人们将自己对“他世界”的神奇想象和对爱情的美好祈愿融合起来,注入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所构造的瑰丽幻想世界里。但在以往研究中我们所涉猎和研究的大都是汉民族的相关故事,对其他民族的了解较少,尤其是对维吾尔族异类婚故事。通过对极具异域特色的维吾尔故事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汉民族异类婚故事的深层文化意蕴,同样,在参照汉民族故事的基础上反观维吾尔族故事,我们亦可以在差异中洞悉维吾尔文化的精神内核。“异类”,究其含义,异即不同,一是旧时指称外族,二是指草木鸟兽等不同的种类。有学者指出异类婚故事中的异类即是与人相异的一类,指用幻想手法创造出来的可以与人婚恋的所有配偶,具体而言异类可以指与人相异的草木鸟兽等大自然中的实体以及妖怪鬼神等幻想出来的“非人类”。这样异类婚恋故事就具有了非常宽泛的内涵。维吾尔族的异类婚故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动物妻故事,一类为仙妻故事。我们主要就这两类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本文所涉及的异类婚主要是指人类男性与异类女性之间的婚恋关系,至于另一种异类婚形态,即人类女性与异类男性的婚恋本文暂不涉及。而且在进行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时,主要将着眼点放在二者之间差异的比较上,其相同、相似之处暂且略过。此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异类婚是民间故事范畴内的,与文人作品中的异类婚故事尽管存在很多共性,但终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和范畴,民间故事是集体创作、口头传播的,具有很强的类型化特征,情节等相对简单,而且存在大量的重复,可以抽绎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而文人作品更强调鲜明的个性和独创性,相对复杂和多样,尽管很多文人创作都或多或少从民间故事中汲取营养,但二者终究存在很大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从民间故事中抽绎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很难覆盖文人叙事中异类婚故事的特性。这一点是需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加以区分和界定的。
一、婚恋行为本身的差异
(一)求婚仪式的差异
在维吾尔民间故事中,异类婚本身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主人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求取婚配。维吾尔异类婚故事大都是以缔结婚姻为直接前提和基础的,故事的缘起本就是求婚。如《玛依穆尼亚克》、《青蛙新娘》等故事,开端即点明主人公在父亲的旨意下射箭求婚,这与求取一般意义上的人类配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而且在故事进展过程中,除了求婚之外,往往还特别提到隆重盛大的婚礼。《湖底女王的婚姻》中“婚礼空前盛大,热闹异常,隆重的婚礼继续了四十昼夜”。*赵世杰:《猎人娶狼女》,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猎人娶狼女》中猎人举办了非常正式的婚宴,村民们唱歌跳舞,热烈庆贺。而在同类型的汉族故事中,求婚和婚礼都极少涉及。人与异类的结缘多出于无意之举,或是意外邂逅。李丽丹在《18-20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中指出异类婚故事的开场母题主要为以下几种:A1路遇;A2求异类为偶(主要是文人叙事);A3自荐(异类自荐);A4异境艳遇;A5园亭之遇;A6善行(无意中救助受伤动物、爱惜小生物、帮助动物度过难关、养花草等)。*李丽丹:《18-20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古代小说中的这种模式用在汉民族异类婚型民间故事中也基本吻合。从汉民族异类婚的遇合类型来看,偶然、意外、梦境、报恩、夙缘、天赐等因素所占比重极大,自发主动、清晰明确的求婚和正式的婚礼仪式却大多缺失。即便此后双方生活在一起,大多也是草草了事。大部分作为人类的男性主人公在角色设置上是极为扁平化的符号性存在,在关系的最初大多不作为,处于非常被动的姿态。在这一点上一向讲究“明媒正娶”的汉民族在异类婚恋关系中却显得随意而“放肆”,也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论题。
还有些汉民族的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根本不涉及婚姻,只是一段短暂奇特的露水情缘。唐瑛在《古代小说中异类姻缘故事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谈到,除正式婚姻之外的异类与人间男女的邂逅爱慕,偶尔的春风一度,甚至莞尔相视都被看作人与异类相恋的姻缘故事,这一点的确颇为符合汉民族的异类婚恋观。*唐瑛:《古代小说中异类姻缘故事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因此相比于维吾尔族的异类婚故事,汉族民间故事中“异类婚”和“异类姻缘”之类的命名其实并不那么贴切,因为很多故事与婚姻无关,彼此只是互为生命中的插曲或过客,短暂的交汇后边各自回到各自的人生轨迹。而维吾尔异类婚故事则是以男主人公主动求婚为起点,以正式的婚礼为阶段性转折,以艰难的爱情考验为过程的。
(二)婚姻考验的差异
1.考验异类妻子
维吾尔异类婚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就是动物妻来到世俗世界的人类生活当中要接受“职能”的考验,以确证其是否可以成为合格的被接受的妻子。考验内容大多是有关纺织、缝纫、烹饪之类的家务劳动。其考验模式类似于民间普遍流传的“巧女故事”,“巧媳妇故事”。在维吾尔异类婚故事中的这种对异类女性的考验说明在婚恋关系中人类男性是处于相对的优势状态,在整体地位上而言处于社会的较高阶层。如《玛依穆尼亚克》中三兄弟射箭求婚,大哥娶到了汗王的女儿,二哥娶到大臣的女儿,可见其家族本身即属于社会的上层。而在《猎人娶狼女》中,狼女的父母对猎人毕恭毕敬,奉为上宾;《青蛙新娘》中男主人公是国王最小的儿子。深层次上讲,面对与异类女性的关系,男主人公是采取俯视视角的。因此动物妻要通过考验才能真正取得男性家庭成员的资格,这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对维吾尔民族现实生活中低阶层女性通过婚姻迈进高阶层男性家族的一种曲折反映。而在汉民族故事中,尽管考验女性的“巧女故事”十分盛行,但这种考验在其异类婚恋故事中却是极为少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汉民族异类婚中男主人公多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在具体情境方面或是深陷困境,或是经济上极度匮乏,而与之相对的动物妻大多是全能而神奇的,可以满足人类男性各种需求。就其带来的现实利益的层面而言,人类男性对异类女性大多是持仰视视角的。田螺女、龙女、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男主人公大多家境贫寒,无依无靠,世俗生活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限制使他们往往面临难以娶妻的境地。所以面对异类妻子,相当一部分男主人公的第一反应除了惊诧外更多的是惊喜,抛开其他因素,其实质上的婚姻关系对男主人公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命运的额外眷顾。
2.考验人类丈夫
维吾尔异类婚故事中除了一部分是对异类妻子的考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人类丈夫的考验。在感情的发展过程当中男主人公要赢得爱情与婚姻是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的。《玛依穆尼亚克》中娶了猴妻子的男主人公,因违背禁忌提前烧毁猴皮使得妻子不得已离去,但为找回妻子,他打了七双铁鞋、三根铁手杖。“走过没有水的沙漠,穿过茂密的森林,越过高山峻岭,绕过陷人的泥潭,爬上积雪的山崖,他这样走了好几年,七双铁鞋穿破了,三枝铁手杖也拉弯了。”*[俄]穆·诺·加毕洛夫,沃·夫·沙赫马托夫:《维吾尔民间故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正是其矢志不渝的爱情信念使得其婚姻在历经考验后重新获得圆满。
相对比而言面对异类配偶,汉民族异类婚恋故事中男主人公大多是接受者或受益者的姿态。当妻子的异类身份泄露而遭受歧视和非议时,一些男主人公选择不作为;在妻子因种种原因离去之后,男主人公也较少积极去寻找妻子或挽回婚姻。总体上结局圆满的较为少见。尽管在发展到后来的“牛郎织女”型异类婚故事中加入了寻妻的情节,但结果最终以失败告终。唯一的亮色当属发展到后来的龙女型异类婚故事,但纵观其整个婚恋过程,则更像是表现龙女坚贞爱情的独角戏,男主人公只是其中的点缀。
二、婚恋对象的差异
(一)动物妻的差异
在维吾尔族动物婚故事中,几乎没有人直接与化身动物的异类缔结婚姻的样态。或者说极少存在“动物化人型”的异类婚姻,基本上都属于“人化动物型”的异类婚姻。也就是说,男主人公缔结婚姻的对象原本就是人,只是因种种原因或被施加了魔法、咒语才化为动物,在结婚之后异类们最终又化为人类。《玛依穆尼亚克》中的猴妻是被继母施加了法术。《猎人娶狼女》则是一家人都被巫婆的魔法变成了狼。《青蛙新娘》亦是如此。而在汉民族异类婚故事中,异类配偶本就是异类,因修行、夙缘、报恩、偶遇或单纯的思恋凡尘,化身人形,在婚姻之后仍旧保留其异类本性。田螺女本身即为田螺所化,白娘子本身即为白蛇所化,老虎妻子本身即为老虎精,至于搅动人间的狐狸精本就是山野之狐。汉族民间故事中异类化身为人,最终因外界因素复又变回异类形象,大多最终以分离告终。尽管结局多不圆满,但人与动物化身的异类通婚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其文化所理解的,至于接受的程度及婚姻存续的可能性和长久性则是另外的问题。
维吾尔异类婚的对象之所以本质上是“人”的身份,而且只能是“人”的身份,其原因还要从深层的宗教文化角度加以探究。维吾尔先民信仰过多种宗教,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都曾繁盛一时,直至伊斯兰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其中产生最早的是萨满教,萨满教的核心思想是“泛灵论”,在此基础上人与异类的沟通、互化都成为可能。这也是图腾神话产生的基础。“最原始的图腾神话所讲到的动物,总是将动物讲成是最有力的,它反映出那时人类在动物野兽面前的软弱无力。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驯服了某些动物或者具有了战胜猛兽的能力,人们的视野得到拓展,神话从歌颂动物神到歌颂半人半兽的神,然后歌颂拟人神”。*戴佩丽:《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北京:中央民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维吾尔族早期的文化观念也是如此,尽管随着历史发展,人的自我中心意识逐步加强,异类在神坛的地位逐渐下降,但依旧被看做是具有灵性的存在,可以在某种层面上与人类进行沟通。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泛神论”和“泛灵论”日渐失去其存在的土壤。伊斯兰教倡导严格意义上的一神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对其他神灵包括自然物的信奉和崇拜都是“以物配主”,是伊斯兰教教义中首当其冲的“大罪”。真主是全知全能的,是唯一的。世间万物天地诸神没有什么可以比拟和匹配它。在这样的宗教信仰指导下,对其他异类灵的信仰就完全被排斥了。异类的神性色彩淡化,与人的“通婚”也不再被允许。狼女、猴女、青蛙新娘等无法再以动物的身份与人类缔结姻缘。因此这类型的民间故事经过当时的伊斯兰文化“洗礼”之后就转变成了另外一种样态,基本的故事形态不变,只是异类女性的身份被改写,她们根本的出身不再是“异类”,而是“人类”。在被迫以“异类”的身份存在一段时间之后,终究复归为人。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受到西方民间故事的影响。西域自古以来是连接亚欧的重要通道,更是多种文化荟萃之地,欧洲的许多民间故事的“异类婚”故事中异类配偶本身也大多是受到魔法所致。
(二)仙妻的差异
在后来的维吾尔民间故事中,仙女的形象也是经过伊斯兰文化改造了的。是在其早期萨满教“神女”的基础上,结合了伊斯兰教天使和仙女的特质。在降临凡间与人间男子结合这一点上维、汉异类婚中的仙女是相通的。但其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在维吾尔民间故事中,仙女们一旦与人间男性结合,就较少出现中途离去的现象,少有“思乡”“念归”的情结,而是满怀热情地开始人间生活。 “她们与人类相爱时不受任何习惯势力的限制,通过自己超凡而神秘的力量来创造美好的生活,并消除企图破坏她们生活的恶势力。”*哈斯也提·艾比布拉:《试论维吾尔民间故事中的仙女和神奇姑娘形象》,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在整个婚姻过程中,仙女都极为主动,努力争取人间的情爱和圆满的结局。《一副仙女画像》中的仙女与人间王子一见钟情,为与王子成为眷属,不惜相约逃离仙女国,历尽曲折后仙女与王子恩爱一生。《湖底女王的婚姻》湖底女王爱慕人间的国王,便想出巧妙的计策,通过引起国王的好奇心引领他来到湖底世界。同时还设计了巧妙的难题考验国王的智慧,最终国王通过考验,湖底女王随国王双双来到地上王国,更加公正的治理国家。
而汉民族的仙妻来到人间之后却常常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自身的思归;二是天界的清规戒律和世俗的压力;三是凡男的用情不终。第一种情况是婚恋关系本身即非出于自愿,其对仙界的眷恋远大于对人间情爱的眷恋,亲情和爱情都阻挡不了她离去的脚步;第二种则是迫于无奈,没有反抗外界阻力的足够力量和勇气,最终人仙两隔;在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异类与人类的差异,阶层的界限和差异是难以逾越的,身份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烙印,如果说人类与动物妻之间存在着鸿沟,那么仙妻与人类之间同样存在着的鸿沟。第三种则大多见于文人作品,更是常态下两性关系的反映,并不因对象是仙而有根本不同。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以失败告终的。汉文化的“仙”妻即便字面意义上具有高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但实质上仍被视为不可实现完全沟通的“异类”。因此民间故事中的人仙之恋亦往往以失败告终。
三、婚恋过程及结局的差异
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中男主人公面对异类妻子,从初识到故事结局,其感情历程是大不相同的。纵观维吾尔族的异类婚故事,在其整个感情发展过程中,在最初阶段对异类配偶的态度大多是厌弃。男主人公意识到妻子为异类时,最开始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和鄙夷排斥。《猎人娶狼女》中即便狼女脱下狼皮,变成一位身材苗条、秀丽可爱的姑娘并温情脉脉地向猎人鞠躬问好,猎人依旧吓的魂飞魄散,只想逃走。而且对猎人娶狼为妻的消息,村民和亲友开始都难以接受,但在最初的排斥之后,因为相信婚姻是真主安拉的安排和旨意,最终接受了异类配偶。在异类配偶化为人之后夫妻合力共同面对外界的压力和考验,最终以大团圆为结局。其感情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抗拒——考验——恩爱圆满。
而就感情发展过程而言汉民族故事中男主人公一开始对异类配偶大多是较为接受的。当他们偷窥到来历不明的异类变为美妙女子为自己操持家务时,大多对其异类身份少有质疑并自愿与之结为夫妻;还有些男主人公为了将异类留在人间偷偷藏起她们的衣服或毛皮使之难以返回天界不得不成为其妻子。总之最初面对异类婚姻,男主人公是欣然接受的。但是当异类妻子的身份成为障碍之时,男主人公却很少站在妻子一方,使其成为孤立无援的被歧视者。 故事中亲戚的闲言,邻里的传唱,丈夫的不敬,使妻子一次次被当作异类嘲笑,她终于无法忍受而离去了。*黎亮:《“离去型”中国民间故事的文化原型论》,《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田螺女故事中螺女在风雨之夕找到螺壳,毅然离去;老虎妻故事中虎妻子找到虎皮翻身化为猛虎,在离开时甚至咬死嘲笑她的邻人和自己的丈夫。她们可以忍受实质上的洒扫持家的女佣人的地位,却无法容忍精神上的贬低。其感情发展模式可概括为:欣喜恩爱——厌弃——分离。
同样是异类婚,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普遍的文化观念中,异类婚都是一种非常态的、被排斥和歧视的婚姻样态,这一点在汉民族和维吾尔族当中也不例外。但在相同的大背景下,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异类婚恋故事本身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维吾尔民间故事中,此类故事也往往历经“违禁 ——分离”的过程,但分离后终究通过共同努力再次复合团聚。在汉民族民间故事中则最终是人兽殊途、人仙殊途。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维吾尔族的婚姻天定观。即认为婚姻中的配偶是真主安拉的既定安排,无论对方是谁,都是上天的旨意,因此少有内心的挣扎选择,大多顺应天命。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以《古兰经》为指导,形成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人生礼仪、道德风俗、饮食文化、人际往来无不由伊斯兰教文化积淀而成。在其日常生活中,讲究“五功”必做,“六信”必具。其中“六信”包括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前定、信后世。*吕大吉:《牟钟鉴.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以“敬畏”为核心的对安拉的忠诚之心。强调敬畏是一种宗教美德,并以之确定人与人、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田真:《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在维吾尔族异类婚故事中,既然出于对真主的信奉和敬畏,在婚姻缔结之后已经完全接受配偶的异类身份,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巩固和持续婚姻,在此基础上遇到的考验和难题双方可以全力以赴竭诚面对。
而在汉民族的异类婚中,异类身份问题始终横亘于二者的关系之中,而且婚姻的出发点更多世俗或者说现实利益的考虑,即便是人仙恋的神仙世界中,也终究不脱尘世烟火气。处处以现实生存为立足点。《聊斋志异》卷八的《嫦娥》,故事结尾异史氏曰:室有仙人,幸能极我之乐,消我之灾,长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乡乐,老焉可矣。*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7页。这一点颇可代表汉文化对异类婚的期许。汉文化对仙的感情并不是单纯的崇拜或皈依,神存在的意义本质上就在于解决人的问题。“普通的中国人是以超然中立的观点看待宗教信仰的。当他需要神时,他就献上一定的供物祭品,自己做祷告。但在平常,对这些神仙却无人去问津……在中国人看来,神仙也是靠凡人而生活,正如凡人也要靠神仙的慈悲和恩惠生活一样。”*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8页。因此民众对人仙恋的潜在心理预设自然也就离不开现实的考量,至少其结果往往印证了这种心理上的内在需求。而在既得利益满足之后,婚姻的存续问题很多时候已经不复是男主人公考虑的首要问题了。而与之相对的,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们则认为上帝或真主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和真主单方面赐福于人类,却不需要人类反馈式的供给。
至于汉民族异类婚中的动物妻,其异类身份问题在世俗的生活当中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承认人与物(动物、植物等)互化的可能性,但终究认为精怪、妖异的变化违反了认识原则和宇宙秩序。物类间的互变、互化,触犯了生命繁殖的秩序。人们对其的认识也就从“非常”转向具有负面语意的“反常”。认为物精变化成的“人”冒犯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本质尊严。其对男女两性所造成的“性的侵犯”,颠覆了人类的家庭、社会秩序,从而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秩序。*李丰楙:《神话与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8 页。在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文化心态下,精怪化人作为一种带有浓重负面色彩的现象之所以以神话思维的方式长期存在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且又为人们喜闻乐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这些故事的叙述模式的终点大都指向分离,精怪来到人间世界,不论上演出怎样的悲喜剧或荒诞剧,最终曲终人散之后都将再次回到自己的世界,留下只是“故事”而已,并不可能对人的世界造成根本上的触动和改变。
如上所述,异类婚型民间故事在维吾尔族和汉民族的文化中都是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尽管依据以往的研究经验,不同民族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常常会相互影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同质化倾向,但通过对维吾尔族异类婚故事的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异类婚故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呈现,从求婚仪式,到情感发展过程,再到婚恋对象的本质身份,直至最终婚恋的结局,都与我们一般的认知有很大不同。当然面对数量众多且又纷繁芜杂的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我们的研究只是概括其主要特征和倾向性,并不能事无巨细地囊括所有相关故事和异文。尽管如此,这种比较研究仍旧从根本上深化了我们对异类婚故事的认识,引发我们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发掘和思考。
[责任编辑]蒋明智
刘建华(1981-),女,汉族,新疆奎屯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河南信阳,464000)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民族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CZW065)的阶段性成果。
K890
A
1674-0890(2017)01-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