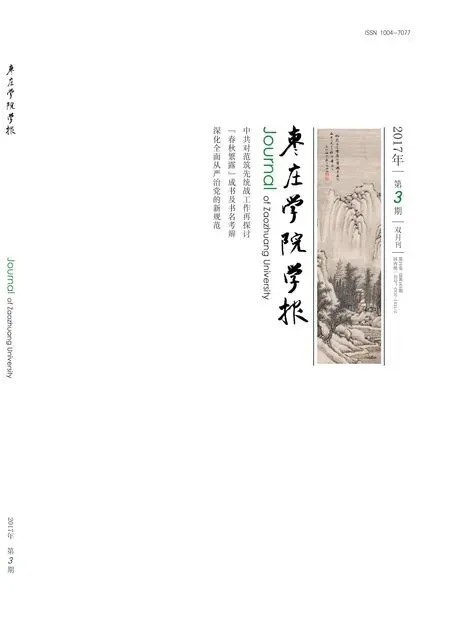创新·拓展·增值
——评张梅《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
2017-01-28朱自强
朱自强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创新·拓展·增值
——评张梅《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
朱自强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张梅学术专著《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性成果,并带来了视野的拓展和学术的增值。首先在构建大儿童文学概念的基础上,以图像为切入点考察中国儿童文学史成为该书的一大突破。其次,重视原始资料的挖掘和考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既是作者非常可贵的严谨治学态度,同时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又把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最后该书把儿童文学的发展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上考察也深化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
晚清五四;儿童读物;图像叙事;张梅①
近十几年来,儿童文学的学科面貌正在悄然改观,不论是儿童文学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儿童文学的队伍,都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其中的一个体现,就是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越来越多的学科的博士学位攻读者,选择儿童文学课题作博士论文。
我与张梅老师认识,是在她师从山东师范大学魏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魏建教授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视野开阔,对儿童文学研究非常关注和重视。大约在2010年,魏建教授主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的编写工作,嘱我撰写“现代儿童文学”一章,后来因为篇幅所限等原因,改为由我撰写研究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派的文学”一章,以“儿童文学”为其中的一节。虽然这次学术写作未能“尽兴”,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写作,能以一定规模和体式,纳入儿童文学,正如教材主编在“前言”中所说,是“尽可能弥补了此前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缺失”。
广西建立了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协同管理专项转移支付的机制,在分配、下达、执行、监督、绩效方面进一步厘清部门之间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的责任和权力。如在分配环节,主管部门要在每年10月20日前研究提出资金分配方案,需要报自治区政府审批的,要求在每年10月15日前研究提出资金分配方案。在下达环节,财政厅会同主管部门在自治区人大审查批准自治区本级预算后60日内印发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文件。在绩效管理方面,主管部门要编制绩效目标,实施绩效监控,开展绩效评价等。协同管理的机制,进一步明晰了责任,形成了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的合力。
由于对学术的包容理解,魏建教授很支持他的博士生从事跨领域研究。2009年的某一天,魏建教授给我电话,说是他的一位博士生打算撰写儿童文学方面的学位论文,嘱我多与她作些交流。不久,我就接到了张梅老师的电话,开始了我们之间学术上的交流和相互切磋。
因为了解到张梅的图像叙事研究这一课题,自然关注她的研究成果。2014年,我编撰《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一书,在解说郑振铎的《<儿童世界>宣言》时,就引用了张梅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中的观点:
在《儿童世界》的实际编辑过程中,“图画”的儿童文学功能越来越受到了重视。张梅指出:“《儿童世界》上有一个最受儿童欢迎的栏目‘图画故事’。最初,郑振铎仅仅沿用了《儿童教育画》上‘滑稽画’这种名称。到第1卷第9期,郑振铎便放弃了使用‘滑稽画’,创制了‘图画故事’的新名称。这说明郑振铎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文体的产生对儿童文学的意义,并开始从最初的沿袭到了自觉建设这种新文体的阶段。”
“a gesture of withdrawal”是“a small offended laugh”的同位语,即这种略显恼怒的微笑本身就是一种离开的姿态。原译却将二者处理成并列结构。
张梅选择了晚清五四时期的几种重要期刊、教科书、儿童文学读物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策略就体现出了她对儿童文学观念的拓展,正如她在书中所言,“本书在破除儿童文学的纯文学观念、建立大儿童文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把晚清五四以来的蒙学读物、儿童书籍、刊物、报纸、近代教科书都囊括进来,从中抽取典型文本诸如《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教科书、《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进行深度扫描,力图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图像叙事能有一个清晰的史的勾勒。”
2016年9月,我收到张梅希望我为她的大作《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作序的电话,自然欣然答应。不隔几日,书稿校样也到了,就利用十一长假通读书稿,并有了以下几个感受。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的《中文版序》中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各种阐释还在不断地推出,脱离了上述那种语境联系的这些阐释必然失之肤浅,它们拘泥于文本的内部分析并不能给中国文学赋予多少思想史的深度,而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
张梅的这部学术著作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性成果,它明显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视野的拓展和学术的增值。
中小企业管理者大多数专业素质较低,只局限于眼前利益,不理解内部控制及风险评估的基本含义及作用,在国家发布并试行内部控制的要求时,由于内部控制的定义并不明确,大多管理者将内部控制与企业管理制度规范混为一谈,控制风险的意识较薄弱,因此企业内部不存在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
最后,我想谈谈儿童文学史研究中思想观照的重要性。
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观念。作为一个对事物认识的观念,儿童文学观一方面会随着对事物认识渐趋丰富而改变,一方面会随着接受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而发生改变。从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可以感受到所谓“读图时代”的问题意识,而她所借鉴、汲取的图像理论、媒介理论、童年研究方法,则拓展了、深化了她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帮助她发展出与以往的许多儿童文学史研究所不同的言说方式。
从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的角度,研究晚清五四时期儿童书刊的图像叙事,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非常令人期待。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到张梅,我几次问过她博士论文是否出版。她总是谦虚地说,还想进一步斟酌、修改,于此我感受到她是一个踏实、严谨的学者。
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和考据是该著作的一大特点。
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专家傅斯年曾说过一句可以视为历史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原则的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应该说,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较为认真地实行了这一学术原则。
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大都以某一种书刊的研究为章节,以史料的介绍、展示以及图像文本解读见长,不过,全书依然贯穿着一条历史叙事的线索,在这一条线索上,显示出张梅的现代性视野。顾彬曾自信地评价他自己的文学史写作,“我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如果说,张梅的这部著作也有一条时隐时现的“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我觉得就是“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
1)浮标站主导风向主要为东北方向和西南方向,主要受江流分布影响,这两个方向的干扰因素最少;从各个方位风速情况看,东北、西南方向的风速也高于其它方向。
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所谓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勉力为之,不勉强出之。在学术风气浮躁,以数量傲人的当下,这种踏实的学术作风是非常可贵的。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许多管理者的经济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大多数管理者本身文化水平较低,没有接受正规的信息技术教育,导致他们对信息化手段的专业管理、应用及维护知识知之甚少。他们的日常经济管理工作仅限于利用信息化手段搜索、整理和发布一定的经济信息资源,结果是即使农村已经广泛铺设了信息网络,搭建了过硬的信息技术设备和设施,因缺乏信息化手段应用专业管理人才,农村经济管理也不能实现信息化手段的有效应用。
有史有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该著作的另一个特点和优点。
在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张梅放出历史观的眼光,将图像叙事视为“另一种现代性诉求”,认为“图像正是推动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我认为,这种定位图像叙事的儿童文学史观,抓准了儿童文学取得现代性的历史脉搏。我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虽然也指出主编《儿童世界》的郑振铎重视以图像诉诸儿童的视觉,“这一点在当时是颇具现代性的”,“具有鲜明的‘儿童本位’倾向”,但是并没有作详细的研究。现在,张梅对《儿童世界》(也包括对其他儿童杂志)的图像叙事所作的详细介绍、深入研究,是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这一儿童文学史的大动脉式的问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呈现了大量的图像,用哪些图像,不用哪些图像,这显然是研究之后的选择,因此,选用什么图像就是研究本身。作者重视对所选图像的“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发现和阐释。比如,作者在研究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教科书《新修身》里的孝故事时,以《事亲》为例,通过绘画,探究文字中不予表现的成人(父母)对儿童孝行的态度:“这种画面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父为尊、子为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夏天,父亲欣慰地坐在一旁等待黄香为其扇凉枕席;冬天,父亲手捧一本书坦然地等待黄香为其暖被。”然后,将其与《养蒙图说》中《扇枕温衾》里的父亲形象相比较:“《养蒙图说》中《扇枕温衾》的父亲,在黄香大汗淋漓地奋力扇枕之际,光着一只脚、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在旁边坐着。何止是坦然受之,简直对黄香的孝行不以为意、熟视无睹。和《事亲》中父亲的姿态何其相似?《新修身》自然没有把‘二十四孝’中极不人道的‘郭巨埋儿’编入教科书,在思想史上是一大进步。但从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上看出,清末的儿童仍然处于被漠视的卑下地位,这种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关于论从史出,这里也试举几例。
在史料的基础上立论,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张梅在详细地列举、分析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由“滑稽画”到“图画故事”的转变情形之后,联系到当下的“图画书热”这一形势,论说道:“我们通常把现代图画书作为儿童文学的新文体,而‘图画故事’就是图画书的雏形。郑振铎当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文体的产生对儿童文学的意义,他已经从最初的沿袭上升到了自觉建设这种新文体的阶段。的确,以文字和图画互相配合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它涉及的内容是广泛的,如果仅仅用‘滑稽画’来命名,无疑是自缚手脚,大大削弱了它表意的范围和深度。长此以往,很容易为滑稽而滑稽。郑振铎最先有了这种自觉,从‘滑稽画’到‘图画故事’,看似只是简单的名称变化,但由此催生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文体。由于‘滑稽画’更倾向于美术,而不是文学。‘图画故事’则落脚点在‘故事’,很明显是属于文学的。而且‘滑稽’仅仅是儿童文学的一个方面,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儿童文学内容的全部。”“‘图画故事’从文中插图、‘滑稽画’一步步成长而来,最终成为今天儿童文学的重要文类——图画书,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新文体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今天的图画书仍然是一个充满弹性和生机的文体,许多文体都可以采用图画书的方式去陈述。而这种文体实验在郑振铎创编《儿童世界》时就开始了。”这种联系当下的精当的阐释,就真正将郑振铎对“图画故事”的一书探索放在了恰当的历史位置之上。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纯然客观的历史叙事。当历史的叙事者选择或一史料加以呈现,其观点已经蕴含其中。张梅研究《儿童世界》时,特别介绍了附夹于杂志的“小画报”这一细节,并于细微处发现了大问题:“在徐应昶主编期间,从1923年第7卷第1期开始随杂志发行附载一种‘小画报’,这应该就是儿童连环画。后来《儿童世界》杂志社嫌每期琐碎,改为每月一厚册。单独印制,且印刷精美,可以说与现代图画书的形制愈发接近了。但是遗憾的是‘小画报’大约发行了一年左右,邮政局不许夹在《儿童世界》里一齐邮寄。1924年第11卷第8期《儿童世界》杂志社把‘小画报’改作‘图画故事增刊’,每隔四期一次,和《儿童世界》一起钉印,至于内容,仍和从前一样,不过版式不同罢了。就这样图画故事发展成为现代图画书的一种可能性被压制了。”
我在《从感性到理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方法——以夏志清和顾彬的文学史写作为参考》一文中曾说:“研究文学这个‘细腻的东西’的演化过程的文学史,也应该是‘细腻’的。……如果文学史写作只是在作宏大的、粗放的论述,不去关注“微小的事物”,就容易使文学史写作变得大而空,玄而虚。”作为儿童文学史论著作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不仅选取非常具体的研究对象,而且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具体细节,主要是图像叙事的细节之中,将图像叙事变成了“细腻的东西”,把儿童文学史研究落到了细处和实处。
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极少涉及到图像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是一个大的突破。图像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不同于图像之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属于一种跨文类的文学艺术,图像叙事就是其中的一个文类。对自己所研究的图像叙事的意义,张梅是具有学术自觉和学科建设自觉的。她在“绪论”中指出:“如果我们再在儿童文学纯文学的圈子里固步自封,就会丧失儿童文学学科嬗变的历史机遇。”“在儿童文学纯文学的圈子里固步自封”,这的确是以往儿童文学研究史存在的问题。
第三,职业技能。具体包括语言运用技能和技巧、人际交往技能和技巧、组织协调技能和技巧、游客安全保护能力、快速计算技能和应变能力等一般技能,还有,一定的外语交际技能和心理咨询技能。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整整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面、深入地反映和讴歌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了就小猕猴杂志社《小猕猴智力画刊》“两个童年——改革开放给了我和爸爸不一样的童年”这一选题的出版做一定的宣传,小猕猴杂志社举办了“两个童年”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的征集对象为小学生和自己的爸爸或妈妈,要求以亲子组合的形式参加。现从征文活动来稿中选择一对江西父女和一对山东母女的作品,在本期《美文品读课》做一次特别呈现,祝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而言,顾彬的上述观点更值得认同。我们的一些儿童文学史著述,或者观点肤浅,或者自相矛盾,往往是因为缺乏“思想史深度”,而有的儿童文学史著述,在重大的、核心的问题的阐述上出现的不当甚至谬见,原因也是出自思想的蒙蔽。
张梅在书中说,“……想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用史料说话。避免以讹传讹,妄谈虚论。”这不是一种标榜,而是留下了足印的践行。这里试举一例。关于叶圣陶童话的发表出处,作者订正了以往研究的一些讹误,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花园之外》这篇童话也发表在《儿童世界》上,但是作者经过资料查询,证明其实并无其事,而是由郑振铎亲手发表在他所接编的第三集《童话》丛书之中。再比如,有研究者说“1923年至1924年这两年内,叶圣陶还在《儿童世界》上发表过《牧羊儿》《聪明的野牛》等5篇童话,成为他前一个时期童话创作的尾声”,针对此种说法,张梅指出:“如果查一下原始资料就会知道,上述说法并不确切”,“在‘1923年至1924年这两年内’,《儿童世界》上只有《聪明的野牛》一篇。”为此我也查阅了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小说月报》,果然在第十五卷第一号上见到了《牧羊儿》这篇童话,可以作为张梅所质疑的一个补充证据。
张梅在研究《儿童教育画报》时,列有“从图像来看现代儿童的建构过程”这样的题目。在作者的描述、论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童年”的被现代化的过程。作者关注到某些图像中的深意:“第7期的封面是一男孩身着童子军服,帅气地骑着自行车。到了第75期的封面虽然还是穿着童子军服的男孩骑自行车,但这时不仅仅是骑,而是潇洒地玩弄着车技。这似乎暗示了现代的儿童可以驾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同期内页‘滑稽画’栏目中一个红衣男孩嬉笑着踩着高跷,一辆蒸汽火车呼啸着正从他胯下通过。文字表述为‘高脚人的胯下,可以通过火车’。这是在1917年6月,火车还是绝大多数中国儿童闻所未闻的新式交通工具。”对这幅画,作者的解读是,“如果火车喻指西方现代文明,高跷就喻指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种顽皮的想像、大胆的东西方并置可谓别有深意。这个画面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心思想的一种隐秘曲折的表达。但这些骑自行车的或踩高跷的儿童的确体现了一种现代儿童的自信:我们是现代社会的主人。”
张梅重视儿童读物中的“启蒙”内涵,比如她追问:“在晚清旧的教育机制的变革过程中,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核心学习内容的私塾教育与新兴学堂、新兴教科书兴起是怎么碰撞、交流、融合的?”并指出:“在晚清西学东渐历史语境下,《蒙学报》把孔子像放置在创刊号的首页成为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举动。”
综上所述,对于腰-硬联合麻醉下血糖控制良好的2型糖尿病患者,术中稳定输注少量(500 mL)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虽然有利于减少体内酮体的生成,但是血糖升高明显,故术中单独输注应慎重,若无胰岛素配合使用,不宜作为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常规晶体液输注。
她分析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儿童期刊《蒙学报》里图像对孝故事的“成人本位”的表现:“由于实践常常偏离儒家思想,统治阶级又一味强化各种愚忠愚孝,这就给图像的表达带来一定难度。尤其是当孝子是儿童时。很多儿童孝子常被画师处理成背影或侧背影,比如第10期‘孝行’中‘怀橘遗亲’的陆绩也是个背影。从画面看袁术是重点表现的人物,他正面冲着读者,身材高大,穿着华贵,占据着右上方的位置。而作为主角的孝子‘陆绩’背冲读者,由于是跪姿,画面中占的空间很小,处于左下方的位置。总体看袁术刻画得细致入微,陆绩的表情、服饰刻画得相对粗疏。袁术形象的高大和陆绩形象的渺小构成了一种上对下、成人对儿童的威压。这种构图方法完全颠倒了主角、配角的关系,突出的反而是应该作为陪衬的成人袁术。这种情况在《蒙学报》很普遍。如果成人和儿童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视觉的焦点一定是成人。在以孝悌为根基构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中,‘子’位置决定了即使儿童是故事的主角在画面中也被压制成从属角色。”
我国高校教师TPACK能力的应用实施主要体现在课堂以及微课等教育变量中。王新新学者基于TPACK框架,研究了微课在高校英语教师教学中的应用设计情况[8]。课堂方面张利桃[9]指出“课内+课外”以及“学生+教师”的TPACK双重整合模式在高校的应用实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当前,国内教师TPACK能力的研究已经从理论层面逐步转向应用实践层面,但国外已有多年理论研究基础并在实践中应用发展,我国高校教师TPACK能力研究有必要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开展,构建一种双赢模式,推动TPACK理论与实践的并重发展,从而优化教学效果,这是教育研究者需要持续关注的方向。
张梅警惕《小孩月报》的“启蒙”是否具有现代性,她引用并认同陈恩黎的重要观点(《小孩月报》“并不通向西方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信仰、理性、自由与怀疑’等核心价值,而是通向如何以现代媒介为载体的‘形塑儿童’之路……《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指出“《小孩月报》中的儿童形象并没有呈现出现代儿童观主张的儿童主体性。”
在国学热、中国文化本位思潮兴起的当下,张梅对“西方”有一种放松的心态:她指出许敦谷笔下的“小姑娘的脸部造型其实更酷似于西方儿童,而且手中的洋娃娃的造型和装束完全是西方的儿童形象。”并认为,“也许在一个万物皆有灵且平等的童话世界里,一个长袍马褂的‘缩小的成人’形象会显得怪异”。“鲁迅所批判的‘钩头耸肩,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脸相的所谓‘好孩子’的儿童形象,或者鲁迅所言的多数儿童呈现出的‘中国式的衰惫的气象’在《儿童世界》是看不到的。”张梅颇有意味地指出:“看民国成人书刊会明显感到民国气象,即使最新潮的月份牌和《良友》中的风气之先的时尚女郎,也多是旗袍装束。而看儿童读物,则没有距离感,也没有陌生感。因为民国儿童书刊中的儿童形象与当下儿童形象实在相似。……儿童书刊根本放弃使用生活中真实儿童为写生对象,勾画的全是西方式的儿童。图像中的儿童没有长袍马褂,没有褴褛,没有苦难,没有一点老中国的影子。这当然都是一厢情愿地对西方的现代想象。”“正是这股强大的想象西方的冲动和实践,对20世纪儿童文学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深刻影响着当下成人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如果当时还是对西方的一种想象式的描画,那么现在‘全球化’已经‘化’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审美习惯。至少当初五四文人们对儿童形象的某些设定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难能可贵的是,张梅在认同以“西方”的现代性资源进行“童年”的启蒙时,并不轻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张梅的现代性观念里,也包含着对传统资源的发掘和现代转化这一意识:“学界普遍认同近代教科书是在参照外国教科书形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具体表述却多把关注点放在近代教科书‘新’和‘启蒙’的方面,对近代教科书的传统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忽视。至少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蒙学读物自身的改良和近代教科书对蒙学读物形式、内容的传承论述不够。然而蒙学教育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蒙学读物更是汗牛充栋,近代教科书的形成绝不是无本之木。笔者更愿意把近代教科书的诞生看成是蒙学读物的现代转型。传统蒙学的现代转型主要是从以下两种路径来实现的:蒙学读物自身的改良和近代教科书在中、外资源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
总之,在近年的关于儿童文学史研究著述的阅读中,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是令我眼睛为之一亮,思绪为之一动的著作。在书籍尚未付梓之时,我能先睹为快,深感是自己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幸事、乐事。
[责任编辑:吕 艳]
2017-02-25
朱自强(1957-),男,河南信阳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教育、文化产业等研究。
I206
A
1004-7077(2017)03-0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