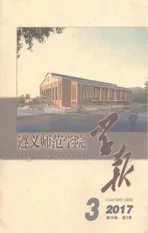论贵州锦屏县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
2017-01-28李良品谢鑫陈迎春
李良品,谢鑫,陈迎春
(长江师范学院1.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文学院;3.政治与历史学院,重庆涪陵408100)
土司研究
论贵州锦屏县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
李良品1,谢鑫2,陈迎春3
(长江师范学院1.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文学院;3.政治与历史学院,重庆涪陵408100)
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分为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之后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三个时期;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出政治地位下降、社会结构变迁、生产方式改变、风俗习惯嬗变、饮食文化巨变等特点;国家行政力量保障、多元文化主导、宗族组织引导,三种力量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
贵州锦屏县;亮司;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
【主持人语】土司研究正在走向深入,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研究者的眼界更宽,选题更有新意。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反映了这一点。贵州黎平府属亮寨长官司,在明清众多的土司中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员,即使在贵州,也不过是一百多个长官司之一,论地位,论影响,远不及播州、永顺、丽江、容美等一批土司,甚至远不如同为长官司的唐崖,因此以往并未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而李良品等人的《论贵州锦屏县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一文,或许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作者的这个选题的确值得称道,他们在收集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实地考察,从而论述了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社会变迁表现出的五个特点,以及造成这一变迁的三方面原因,这对于探讨土司制度的推行在西南民族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特别是了解改土归流以后土司后裔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状况,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希望这一研究能继续深入下去。土司朝贡是土司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往对明清时期的土司朝贡论述较多,而对土司创建初期元朝的土司朝贡研究不多,这主要是受史料的限制。彭福荣的《元代土官朝贡及其制度化》一文,即努力弥补了这一缺憾。作者梳理了元朝土司朝贡的史料,进而总结了元朝土司朝贡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土司主动朝贡,以表示对国家统治的认同,从而换取国家的承认与保护;另一方面,元政府又有各种引导性措施,使土司朝贡逐步形成制度化,并为明代土司朝贡的健全与完善奠定了基础。作者的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的。当然,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与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世愉)
位于贵州锦屏县东南部亮江左岸的亮寨,原名亮寨司或诸葛寨,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孟获时在此安营扎寨而得名。亮寨是一个拥有4200余人(其中龙姓人数达3700余人)且独具特色的千古苗寨,被誉为“黔东第一苗寨”。亮寨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变迁值得深入研究,迄今为止,凯里学院李斌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生王勤美,或就亮司龙氏兴学活动与社会变迁、亮司宗族的建构历程,或就龙氏家族的发展与演变等问题做过探讨,目前还没有对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的研究。因怀揣对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发展与演变深入研究的梦想,笔者于2016年8月13日至16日带领一批师生,深入该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对亮司龙氏家族的社会变迁有了一定的了解。本文拟就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的历程
自龙氏土司世居亮寨迄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变革,其社会变迁也不尽一致,以笔者之见,从龙氏家族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看,其社会变迁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土司时期
龙氏作为亮寨村第一大姓,自元末龙政忠率众入黔,与新化、欧阳诸司头人分域而治,自守亮寨以来,龙氏家族开始在亮寨逐渐发展。特别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龙政忠从官军前往征讨当时的白岩塘、铜关、铁寨等处反叛并以功授亮寨长官司之后,该家族作为朝廷命官掌管地方事务不断发展壮大,在明清时期黎平府内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P2-3有明一代,龙氏土司世代承袭亮寨长官司长官,正六品,封授承直郎,在辖地内可任意征粮、派款、派役,对辖区内民众拥有生杀予夺之权。清朝前中期,亮寨龙氏仍然世代承袭,享有较大特权,在其辖地内可自行征派赋税徭役及受讼词。雍正以后,清廷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有的土司权力渐被限制乃至完全被剥夺;至嘉庆后期,龙氏土司已由原来的地方独裁变成替官府征收钱粮、维护地方治安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明代和清代前中期的亮寨龙氏土司,虽然他们身处少数民族地区和湖广(即清代中后期的湖南)与贵州交界地带,无法进入帝国的“核心圈”,但由于他们是明清中央政府的命官,处于边远地区的中心,且他们一直在营造边远地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帝国权威的象征和帝国行使地方权力的“代理人”,成为地方的权威。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龙政忠始,至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龙家谟止,亮寨司龙氏家族20世、计23人相继世袭亮寨蛮夷长官司长官之职,时间长达470余年。龙氏家族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完成自身形象塑造的同时,不仅与地方精英结成利益团体,而且还通过宗族组织修建宗祠、书写族谱、塑造祖先、选举族长、制订族规、设置义庄等形式,把整个家族牢牢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家族势力。例如龙氏土司在《龙氏迪光录》中就有《训诫》、《杜篡篇》、《训言》、《家训》、《传家殷监》、《约》等族规族训性质,成为约束龙氏家族的教条。[2]通过这些规约,促使亮寨龙氏土司家族成为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浓缩版的地方政府和缩微型的乡村社会,且通过军事征调、朝贡纳赋等义务的履行长期维持与明清中央王朝的良好互动关系。
同时,龙氏家族通过培养本族和亲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实现了“政与儒”的迭相互动。亮寨龙氏土司执政期间,仅亮寨本寨就出现诸如龙潜、龙祖甲、龙享极、龙绍俭、龙文和、龙文广、龙月、龙绍纳等优秀的科举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的龙氏士人,在提升龙氏家族整体文化素养和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提高了龙氏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对于一个客居异地而又主宰地方的豪族大姓来说,要想真正融入贵州黎平地区,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龙氏家族的确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他们或利用婚姻关系,积极主动攀附黎平地区的著姓望族,以期迅速完成其“移民土著化”的历史过程;或通过建立关系网络,以提升龙氏家族的社会影响。从实际效果看,龙氏家族的做法是成功的,他们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逐渐成为黎平地区的望族。
(二)改土归流之后到民国时期
然而,龙氏家族的发展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周期性的社会变革,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之后实施的改土归流,无疑对龙氏家族的打击十分巨大。虽然龙氏家族组织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但失去特权和没有政治地位的宗族组织,在后来的发展中举步维艰,甚至在清咸丰年间除遭戴老十、黄金亮等匪患击毙数十人外,匪患还点火烧房数十间、毁坏庵庙、挖去神像藏金,在没有土司权力之下的龙氏家族惨遭诸如拆坏民房板壁、毁弃字纸、抛腻饭食、劫掳财物,并捉其人民,使之擂米、挑水、煮饭、服役,或灼烤火烙,逼要钱赎等万端蹂躏。[1]P39-40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龙氏家族不得不由传统的宗族组织向现代家庭转变。特别是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龙氏家族的近代化趋势更为明显,甚至有些不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过诸如近代进步人士龙步瀛、抗日救国军军政宣传部尉官龙家裕、亮司平民子弟学校校长龙云远等优秀人士以及龙田、龙世衔、龙绍月、龙云远、龙天衢等文武官员,但也出现过“与匪勾结,控制清水江流域关津商埠,扣押过往百货、鸦片、木材,巧取豪夺,鱼肉百姓,中饱私囊”[3]P475-504的下江县(今属贵州从江县)县长的龙青云。由于时局变化太快,龙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可以说,清道光年间亮寨龙氏土司家族被改土归流之后,失去原有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方面的特权,社会地位直线下降。以往的辉煌终究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中,难以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长足发展。
(三)新中国成立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亮寨龙氏土司家族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同样在不断变化。尤其是打工潮兴起后,他们不断改善衣食住行的条件,诸如木房改成砖房、自行车换成小轿车等,此不赘述,但有三个问题在此必作强调。
1.家族归属感增强。亮寨龙氏宗祠是龙氏家族数百年辉煌历史的见证,是龙氏家族的文化象征。随着时间流逝,龙氏宗祠被湮没在时代的更迭里,外表显得十分破落。自新中国成立至1981年,历经数次社会洗礼,龙氏宗族组织完全被政府的镇、乡、村社组织所取代,外形几乎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龙氏宗族注入新的活力,内核开始绵延,建祠堂、修族谱等又兴盛起来。亮司人非常注重宗祠,他们认为宗祠具有十分强烈的家族归属感,他们将破败的宗祠进行维修,希望“复修宗祠人文蔚起,整治殿堂人才辈出”,以实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目标。因此,龙氏家族2016年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锦屏、黎平、榕江、从江以及亮寨临近的龙氏人为“亮司龙颜弼宗祠”两次维修捐款竟达63400元。由此可见,亮司龙氏宗族在文化符号(宗祠)逐步重构下,其内在影响也将不断增强,蕴涵深厚思想内涵的宗族文化将会薪火传承。
2.重大事件常发生。新中国成立后,亮寨龙氏土司家族本应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借助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依靠党和政府给予的各种优厚条件,比邻近村寨发展得更快更好。然而,龙氏家族在长达数十年中,没有出现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引导和带领该村走向康庄大道,未能与时俱进,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整个大家族常常表现出与时代不合拍、与社会不相融的态度,基本上每10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重大事件,这就使拥有接近4000人的龙氏家族出现整体沉沦的现象。事例一:屠杀解放军事件。据《敦寨镇志》记载:1950年锦屏县“和平解放”,刘书善等南下干部受任敦寨区人民政府行政领导,康阜等解放军干部到敦寨、亮司等地开展征粮工作,锦屏县敦寨区土匪支队队长的龙景昌于1950年3月13日凌晨,一面派人围攻刚建立的敦寨区公所,捕杀贵州锦屏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兼公安局长孙瑞民、锦屏县敦寨区区长刘书善,一面亲自带人袭击亮司八家巷的共产党征粮干部临时住处,杀害了锦屏县政府民政科科长康阜、锦屏县敦寨区政府财经助理员尚存养、征粮解放军战士王月亮和刘云芝等四名解放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3.13”血案。[3]P246-247对于这次事件,我们在问卷调查中设有“亮司龙氏家族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这些重要事件对这个族群产生过哪些重要作用或影响?在族群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等问题,有位老教师的答卷是:“在我们亮司龙氏家族中,1950年曾经发生过地方国民党残余与湖、广、贵三省土匪叛乱,造成血腥地屠杀进步人士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对我们这个地方龙氏家族产生过不好的影响。”此事件导致龙氏家族伪乡长龙景昌等10余名土匪及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被枪毙、20余人被判刑。事例二:流氓团伙事件。上世纪七十年代,亮司流氓犯罪事件猖獗,1974年1月破获亮司轮奸妇女50余人的流氓团伙案,依法逮捕9名,判处首犯龙大毛死刑。[3]P227事例三:群体械斗案件。1991年8月25日亮寨村与临近村因争金矿发生群体械斗案件,亮司二村龙忠玖和营业所退休干部刘永程等5人当场被打死,另伤20多人。为了急于要求政府惩办凶手,8月25日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千余人抬着死尸到敦寨街上游行,以强求政府领导当场出面处理。8月29日,亮司部分群众将龙忠玖尸体装棺抬到区公所操场开追悼会,有人竟然持火枪木棒冲击区公所。导致敦寨至锦屏的交通受阻。后经多方做思想工作,于8月31日下午事件才得以平息。[据地方志不完全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村因屠杀解放军以及杀人、群殴、赌博、吸毒、贩毒、流氓等犯罪,被政府枪决和判刑已达80人以上。[3]P219-228
3.龙姓恢复为苗族。清代苗族学者、亮寨龙氏族人龙绍讷撰写的《龙氏迪光录》卷二之“户口”有“亮寨司户口人丁俱系黑苗”之说,“风俗”篇也称“司属村寨苗疆侗地”,并有苗侗民族语言、服饰、习俗之叙述。这些文献、文物、史实有力地佐证了亮寨龙氏土司家族为苗族的本源。又,《龙氏迪光录》载:明朝在亮寨设置“亮寨蛮夷长官司”,实行“以夷治夷”。于是,亮寨长官司辖区内苗民逐渐汉化,以致其语言、服饰、习俗都等同于汉族,甚至连民族成份都改成了汉族。据《龙氏迪光录》称,龙氏在“宋,应天人,宦游江西,有太祖龙禹官,初为南昌节制副使,寻为黔楚安抚招讨使,卒于官遂。为南楚人,复自楚徙今之亮寨职”[2]。可见,在奉行民族岐视和压迫的封建时代,亮寨龙氏土司家族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背根本,“自损以受用”于汉人,将长期以来本属于苗族的子孙,却逐渐演变成了汉人,当了几百年的假汉族。1986年元月3日锦屏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黔族字(1981)40号、63号两个文件精神,以及当地历史事实,正本清源,同意亮寨司龙氏489户,2281人恢复为苗族,亮寨临近龙姓也恢复为苗族,有的村寨树碑记载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3]P61-62如平江村民立碑撰文载叙:“其祖原藉系湖南绥宁县东山人氏,于元朝年间其祖定爵,迁居贵州省锦屏县亮寨石门坎,其子龙便福移居平江,后子孙发达,分居迁徙到九南、竹山坪、平捧、高寨、色界、架寨、管寨、云亮、乐安屯、州洞溪、塘保等地。龙运朝、龙运廷在明朝年间受统治者横加镇压,逼迫改苗服汉。恩蒙党的民族政策,1986年恢复苗族。”①该碑立于贵州锦屏县敦寨镇平江村村口,内容为笔者实录。
总之,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社会变迁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南、中南地区一些土司家族社会变迁的基本面貌,也真实反映了土司家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而演变的历史过程。
二、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的特点
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社会无不处于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只不过社会变迁的深度、广度、速度等在程度上有一定区别而已。随着明清以来至今的我国政治体制的不断变化,亮寨龙氏土司家族也必然随着这种变化而不断发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呈现出五个方面较为突出的特点。
(一)政治地位下降
据《明史》卷三百一十六《贵州土司》、《万历黔记》卷五十八《亮寨司》、《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贵州》、《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四裔考·西南夷》、《明史稿·列传》一百九十《黎平》、《贵州通志》卷之二十一《秩官·土司》之“亮寨长官司”条、《贵州通志·土司志四》之“黎平土司”、《黔南职方纪略》之“亮寨长官龙氏”、《龙氏迪光录》等历史文献记载,自明代洪武年间始,亮寨龙姓就逐渐发展成为黎平辖区之巨族。在龙氏担任亮寨长官司长官期间,其辖区与当今锦屏县敦寨镇的管辖面积相等。在明代中央政府授龙氏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世代承袭,官至六品,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不仅掌握着当地民众的生杀权力,而且还可以在辖区内任意征粮、派款、派役,对辖区内民众进行苛派剥削。但道光年间以降,随着改土归流政策推行的逐渐深入,龙氏家族各种特权丧失殆尽。特别是清政府通过清查户口、推行保甲、兴办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加速了亮司龙氏家族政治地位的急速下降。龙氏家族由以往的土司家族一夜成为一般平民家族,特殊的身份、地位已成过眼烟云。
(二)社会结构变迁
在亮寨龙氏土司统治时期,辖区内社会呈现出“二元结构”,既有以龙氏土司为首的官僚群体统治阶层,又有以当地夷民为主的被统治阶层。据《龙氏迪光录》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亮寨龙氏土司辖区内有1298户,5618人。而亮寨司内仅有120户,544人。[2]也就说,龙氏土司家族500余人管理(或者说统治)着辖区内的其余5000多人。此外,亮寨司还享受着司外民众无法获得的待遇:一是土司衙署左边的花园——览翠园,这里环境优雅,是司内民众游息之所,花木交荫,最为秀雅。[2]二是司内建有多种学校,给司内子弟读书带来极大的方便。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司内民众的一些优厚待遇也被剥夺。亮司龙氏家族已由原来统治阶层转变为以中央政府派驻的流官为代表的被统治阶层。时至今日,庞大的龙氏家族也与当地其他各族民众一样,只能自觉接受各级政府的领导,从事农副渔工等各类职业。
(三)生计方式改变
据《龙氏迪光录》卷二之“土产”条载:亮寨司的物产较为丰富,谷类有稻、禾、玉米、蕨粉、葛粉;果类有山核桃、茶蔗、丁香柿、丈菊、花红;菜类有姜、茭瓜、黄瓜、椿芽、薤、菜丝瓜、地黄瓜、红萝卜、木姜子等;食类有波丝糖、米花糖、油茶、米花、炒米、麻叶、密渍、圣韭、酸韭、乾盐菜、醅肉等;兽类有豕、豚等;鱼类有草鱼、鲢、鳙、鳢、鳑、鲇等;介类有团鱼、脚鱼、鳖等。[2]从这些物产看,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在土司时期的生计方式主要依靠传统的农业、渔业、副业等,龙氏土司辖区的九南、鞍马、敦寨、颓寨、赖寨、满寨等29寨民众则以传统的务农为生。龙氏家族500余人的生计方式除了传统的务农以外,还分享29寨其余5000余人上交给土司的赋税红利。虽然当时有“各户或抗延不速,或包揽入私,或自顾赴柜”[5]等现象,但田赋迟早还是要交的。改土归流以降的清朝末年、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亮寨龙氏土司家族民众的生计方式不得不由传统的务农逐渐演变为发展农业、副业、手工业以及外出打工,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据2014年的不完全统计,该村有农业人口4275人,耕地面积3246.75亩,除农业、副业、手工业及外出务工收入外,仅生态农林旅游生产总值就达487.00万元。
(四)风俗习惯嬗变
亮寨龙氏土司家族成员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传统风俗习惯来约束自己,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龙氏迪光录》载:“风俗者,自上施之为风,自下施之为俗。俗之美恶,视风之盛衰耳。(亮)司之风俗所变,在汉唐则榛榛狂狂然,在宋明则浑浑穆穆然,到清则彬彬雅雅然……军民杂处,汉土相安,四百年守世衔,十八寨民无叛志,以筋力之勤惰争贫富,以生童之多寡争盛衰,以人士之贤愚争贵贱。”[5]这段文字是对亮司风俗的总述,虽有过誉之处,但也不乏实情反映。同时,该篇对明清时期民俗还作了概述。亮寨的传统节日有除夕、春节、社日、清明节、立夏节、端午节、月半节、中秋节和重阳节,此外还有三月三日上花山、六月食新节、七月中元节、八月飞山节等节日,都具有民族特色。亮寨现在主要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节日,基本上与全国其他地方差别不大。亮司人的丧葬既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也吸收了汉族的风俗,苗汉两种风俗的混杂更显风韵。如丧葬流程从择期、收殓、报客、选穴、开堂吊奠到发丧出柩、登山安葬、打扫屋子、安家先、扶山,经过各种程序最终才将去世之人入土,相当复杂。[1]P23-25时至今日,虽然简化了一些程序,但总的规矩、程序仍较复杂。
(五)饮食文化巨变
如前所述,亮司物产较为丰富,饮食有大米、玉米、蕨粉、葛粉、姜、茭瓜、黄瓜、椿芽、薤、菜丝瓜、地黄瓜、红萝卜、油茶、米花、炒米、乾盐菜、醅肉等,但以大米、玉米为主食。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人们与贵州其他地方的民众一样,饮食总体上兼具辣、香、酸,古朴醇厚、风味独特,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情怀。亮司人过去立夏节是“吃蛋节”,端午节要喝“雄黄酒”,“中元节”要吃“夹酿酒”或“晃荡酒”。迄今为止,亮司人与贵州其他地方各族民众一样,饮食文化已基本汉化。
三 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的成因
对于亮寨蛮夷长官司改土归流的时间,无论是《清史稿》、《贵州通志》、《锦屏县志》,还是《龙氏迪光录》均无确切记载。笔者翻检资料发现,直至道光二十三年,亮寨龙氏末代土司龙家谟还在重修亮寨蛮夷长官司司署[1]P18,说明此时要么就没有革职,要么还在担任近似于长官司的职务。可见,自龙政忠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任“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一职至清道光年间龙家谟承袭最后一任亮寨蛮夷长官司止,龙氏家族在亮寨至少有470余年的辉煌,龙氏家族中的有识之士、文人武官,俱载入《龙氏迪光录》之中。繁华毕竟落尽,昔日辉煌难再。鼎盛一时的亮寨龙氏土司家族,为何社会变迁如此之快,竟然走向了落败?究其根由,原因有三。
(一)国家行政力量使然
一个地方的社会变迁是由多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明代及清代前中期,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政权及长治久安,运用国家行政权力设计了土司制度、卫所制度、里甲制度、保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套国家制度在西南民族地区自上而下地推进。亮寨龙氏土司在国家行政力量面前显得十分式微,只能遵照执行,整个龙氏土司家族社会稳定,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亮寨司改土归流后,国家通过改土归流将亮寨龙氏土司原辖区完全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体系之中,特别是通过保甲制度、团练制度等制度以及派驻流官、编查户口、兴修水利、劝民农桑等举措,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行政力量直接进入龙氏家族内部,从而在制度上打破了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原有的文化空间,为汉文化在亮寨地区的传播、渗透开辟了广阔道路;通过动用国家权力颁令禁止土司地区原有的一些文化制度、习俗,迫使龙氏家族文化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国家整合的需要;以保甲、团练、乡镇、村社与聚落、家族、家庭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组织取代土司时期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从根本上彻底消灭了土司地区地方势力与地方政权相对抗的实力与基础;通过设置各类学校,推行科举考试,实施新式教育或义务教育,推行“两减一免”,鼓励各族子弟读书考学,进入国家行政人员系列等措施,使汉文化全面作用于原土司地区社会,造成包括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在内的民族地区发生深刻的文化变迁。[4]由此可见,国家行政力量造成的制度变迁、文化变迁,对亮寨龙氏土司家族文化的承续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是国家运用行政力量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制度建设作保障、以文化消解作前提的强迫土司家族进行社会变迁的有力举措。
(二)多元文化主导
无论是土司时期,还是改土归流之后,文化交流与融合所产生的多元文化共生,在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些文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主流文化。明清时期亮司地区在“以汉化夷”、“以夷制夷”的文化攻略下,龙氏家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主流文化,积极互动交流,创办纯一堂、双樟书院、满寨公学、平江书馆等[2],自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以后的210多年间,仅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就出现仕宦类20人,科第类5人,文学类5人,贡生22人,监生59人,文武生员100余人,还有术艺、释道、巫师等三教九流之人。其中出类拔萃者有龙绍俭(著有《周易图说》二卷,《全黔人鉴》一卷,《广义》四卷,《诗·古文》八卷,《声律易简》二卷,《黎平府志》十五卷)、龙仁山(著龙氏家谱《迪光录》一部)、龙绍讷(著名苗族学者和作家,著《亮川集》等)、龙嘉会等,可谓人文蔚起,人才辈出。正是在这些人才以及主流文化引领之下,亮寨龙氏土司家族才形成了相互尊重、兼容并包、交流互动和协同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二是地方民族文化。据史料记载,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年4月,亮寨龙氏土司与欧阳等五个长官司杀牛分酒,议定款规13条:“一、不许以重压轻、以大压小,以富欺贫,以强欺弱、将恶压善;二、不许报官兵劫官担,三、不许杀人放火;四、不许挖坟劫墓;五、不许假制造仇恨;六、不许拿黑放白、拿假作真;七、不许通司作弊,内勾外引,里应外合;八、不许行盗贼,挖墙拱壁;九、不许窝藏盗贼;十、不许买办事务;十一、不许偷牛盗马;十二、不许拦路抢劫他人财物;十三、不许估骗人财,强占田地,山塘水库,各界有址,不许混争霸占。”凡参加款组织的村寨,一年或数年参加合款一次,制订修改款约。若一个村寨受到外敌相犯,全款村寨就顷然相助。款首由各寨头人联合产生,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辈首担任,少则1人,多则2―3人,大小款均各制订条约,内容主要是惩罚盗贼、内奸、恶棍,解决财产纠纷;轻者令其赔礼道歉,偿还损失,处以罚金,重者驱出乡里,甚至以火烧、水溺等形式处死。[3]P219这种款组织不仅是村寨之间严密的组织关系,而且更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文化。三是龙氏家族文化。《龙氏迪光录》中包括“戒纵闺门”、“戒索饮食”、“戒忘恩德”、“戒恃富豪”、“戒行刁唆”、“戒欺寡弱”、“戒好游戏”、“戒侵田园”、“戒重货财”共九戒[2],华国公的“明伦理”、“崇厚道”、、“正体统”、“尚直道”、“戒用势”、“戒生事”共六训[2],对父子、妯娌、夫妻、兄弟、婆媳、祖孙等关系的约定以及其他有关训诫、家训、规约、家规等体现了国家主流文化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之外,在习惯法中还有“禁同姓为婚”的规定,这无疑彰显了龙氏家族文化特色。由此可见,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排除地方民族文化、龙氏家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各种文化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总能达成一定的妥协,逐步实现多元文化对社会变迁的主导作用。
(三)宗族组织引导
亮寨龙氏土司家族从长官司的地位,从土司衙署所在地逐渐降为乡镇政府所在地,再降为亮司村所在地,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亮司演变成为锦屏县敦寨镇下面的两个行政村。亮司辉煌的时代至此翻篇,不再管辖相当于当今敦寨镇的广大区域。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而艰辛的变革,但几百年居于统治地位的龙氏家族,“老大”心态在龙氏族人心里根深蒂固,不可剔除。即便进入21世纪高科技发展时代,龙氏家族还停留在过去辉煌的时代,时有与当今社会未能对接的现象出现。笔者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当我们与龙氏族人交谈期间,随时可听到“我龙氏”、“我龙氏家族”等口头禅;在笔者翻检《龙氏迪光录》卷二之“山川”、“管辖”[2]等内容时,他们经常会出现“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龙家的”、“九男和敦寨等二十几个寨原来也是我们龙家管辖的地盘”。众所周知,国家行政力量作为一种政治强力,对原土司地区的社会变迁带有强制性质。由于亮寨龙氏土司家族族大人繁、利益多样、纠纷复杂,家族内部本身就很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如果国家行政力量未能被家族社会消解吸收,就容易形成民族冲突,造成民族隔阂,以致再次出现前面提到的种种事件。付广华先生说的“宽容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境界”[5]这句话很有哲理。其实,包括亮寨龙氏土司家族在内的原土司地区的大多数民众基本上具有这种宽容的心态,并且在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社会变迁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龙氏家族也充分认识到,只有服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地方政府的领导,只有本族群内部以及相邻族群之间相互宽容、和睦相处,才能给本家族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或许长官华国公碑镌的“明伦理”、“崇厚道”、“正体统”、“尚直道”、“戒用势”、“戒生事”的六条训言对亮寨龙氏土司家族起到到了引导作用。或许亮司龙颜弼宗祠作为龙氏家族的文化象征,族谱《龙氏迪光录》作为龙氏家族的文物遗产,《龙氏迪光录》中的训诫、训言、家训、规约、族规作为龙氏宗族的法律文书,龙氏家族的族长作为管理全宗族内外事务的首脑,宗祠、族谱、训规和族长,这四者古往今来一直在龙氏家族社会变迁中发挥引导作用。
总之,国家行政力量的作用、多元文化的主导、宗族组织的引导,三种力量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社会变迁。
[1]单洪根.黔东第一苗寨——亮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2][清]龙绍讷.龙氏迪光录(卷一)[Z].锦屏:锦屏档案局藏,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3]焦正芳.敦寨镇志[Z].锦屏:锦屏县敦寨镇人民政府,2011.
[4]刘伦文.国家行政力量与民间社会力量的互动——论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4):13-17.
[5]付广华.人类学视野下的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J].桂海论丛,2009,(2):89-93.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the Tusi Headed by the Long Family in the Liang Village of Jinping County in Guizhou
LI Liang-pin,XIE Xing,CHEN Ying-chun
(1.The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ety,Economy and Culture along Wujiang Basin,2.Literary School,3.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Fuling 408100,China)
Social change is a historical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The Tusi in Liang Village headed by the Long family falls into three periods:Tusi Period,the period from Gaituguiliu to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ter-1949 period.The Tusi in Liang Village headed by the Long family in the social change assumed the following features:its political status decreased;and its social structure, productive way,customs and food culture changed;etc.,which resulted from politics,multiple culture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Jinping county of Guizhou;Tusi in Liang village;Tusi headed by the Long family;social change
G127
A
1009-3583(2017)-0011-06
2017-03-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16BMZ017);长江师范学院民族学开放基金项目“贵州省锦屏县亮司龙氏土司家族社会变迁调查与研究”(2015XTJ01)
李良品,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