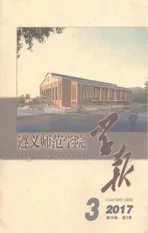集权边缘与边疆治理:汉唐羁縻制度考略
2017-01-28王友富
王友富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集权边缘与边疆治理:汉唐羁縻制度考略
王友富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对待边疆民族地区,因受主客观原因的制约,只能“因俗而治”。历代封建王朝对待民族地区,只能将之视为中央集权的边缘地带,采取特殊的办法治理边疆,秦汉在边地设初郡,设置护羌校尉、西域都护等官职,进行松散管理。唐朝广推羁縻府州制度,虽然随着唐朝自身实力的盛衰而消长,但是羁縻效果还是明显的。三国两晋等王朝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了一些变通方法,一样达到了羁縻效果。迨至元,羁縻制度式微,被土司制度取而代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民族地区;边疆治理;羁縻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就是一部集权斗争史,随着汉唐王朝的强势崛起,版图日益扩大,边疆民族地区开始纳入封建王朝的治理视野,但因受现实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封建王朝不得不采取了“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于是羁縻制度便应运而生。秦汉王朝(秦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道”,但秦历15年而亡,汉承秦制,故略秦)初创了这一制度,唐王朝继承光大之,至宋则式微,迨至元则被土司制度取代。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为研究对象,以期推进对羁縻制度的进一步研究。
一、两汉时期羁縻制度的形成原因
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强盛,欲宾服四海,为了强化对周边民族地区的治理,特设置了羁縻制度。汉武帝当政时,一改汉初“黄老”思想,集中国力对付北方强邻匈奴,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兵先后深入匈奴腹地,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为了断匈奴右臂,汉朝势力首先伸入河西地区(设置了河西四郡,即张掖、武威、敦煌、酒泉),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达到了隔绝羌胡的目的。
汉朝经略河湟。元鼎六年(前113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10万伐羌,羌人败走,部分羌人“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1]P1117汉军驻扎在河湟地区,设置了西平亭(后改西平郡,即今西宁),首次将青海东部纳入汉朝版图,这样一来,原居此地的羌族就成为被统治民族,对这些羌族部落如何管理,就成为汉朝廷面临的实际问题了。汉朝特别设置了一个新的官职来负责羌族事务,即护羌校尉。但羌族屡屡反抗,汉军平叛后,为了强化治理,汉将军赵充国上书建议实行屯田(目的是为了就近解决军食,以减轻后勤供应负担),他本人表示愿意举家迁徙至青海湟水流域,为大汉守边。汉廷决意施行,于是发内地囚徒、军户迁往青海东部,充实边防。纵观西汉一朝,羌汉之间虽时有杀伐,但总体上是以和平时间居长。东汉则不然,羌汉之间战争连年,烽火不息。羌族的五次大起义,让东汉王朝穷于应付,几近耗空国库,但羌人也受到沉重打击。两汉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呈现正反两种结果,这样的结果为后世王朝提供了一个借鉴案例。
汉朝经略西域。随着汉军的节节胜利,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为了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汉朝一方面制定优抚政策争取了西域各国的民心,另一方面为了管理西域事务的需要,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前60年),由西域都护负责西域具体事务。西域都护府是管辖西域各国的最高地方政权机构。都护是一种军事长官,掌管西域各属国的军事与外交,调解各国之间的矛盾,民政事务则归当地王侯管辖,各国之行政组织以原属国地盘为各自行政区划,虽然保留“国”之名义,但各国官吏需经中央政府的任命才具有合法性。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册封,二是赐印绶,如此一来,正好“说明他们是汉朝的地方官员”[2]P1999。西域三十六国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分居国与行国两类,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经略西域,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情势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一方面通过打击匈奴势力,拉近与西域各民族的距离,另一方面通过和亲之策,使汉朝皇室与西域势力较大的民族首领结成血盟,进一步使之向往中原,日久自然华化。例如,汉朝远嫁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王和亲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汉朝利用归附的匈奴部落充实北部边塞。西汉末,匈奴内讧,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击败,为了保存实力,决意率众南靠汉之边塞,为了取信于汉廷,呼韩邪单于遣子为质,对汉称臣。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朝见宣帝于甘泉宫,宣帝为示重视,封其为王,位在各诸侯王之上。元帝时,呼韩邪单于率众屯居于五原西部,后又迁往云中、美稷、朔方、定襄、雁门一带,这部分匈奴史称“南匈奴”。为了进一步密切汉匈关系,呼韩邪单于要求与汉和亲,汉元帝以王昭君许之,并厚加赏赐,以示笼络。迨至东汉明帝时,北匈奴势力有所恢复,不断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故明帝、章帝、和帝时,派兵大举讨伐,北匈奴遭到重创。汉朝为了安抚南匈奴,一边利用其充实边塞,监视北匈奴动向,一边正式设护匈奴中郎将卫护南单于。
汉朝在民族地区设置初郡,设属国都尉统领。初郡与中原地区的郡县有明显的不同,其管辖区域都是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地区,以原有的民族地区或者部落为单位,设置初郡,以部落首领为属国都尉(初郡最高长官),不改变其民族习俗,保证其原有的政治管理方式,不向汉廷缴纳赋税,只纳土贡,表示政治上对汉臣服即可。另,属国与郡县的区别,在于郡县是由郡守、县令、乡、亭、里首按地域形成金字塔式的体系统治,而属国则是由属国都尉、丞、左骑、千人官、候官等组成政权行政结构。汉设初郡始于元狩三年(前120年),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匈奴浑邪王4万余人归汉,为了安置他们,汉廷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史称“五属国”。汉王朝后将这一方式推广到其他民族地区。两汉在民族地区的这一系列措施都被历史证明是切实有效的边疆政策。
关于羁縻制度产生的原因,高士荣在《西北土司制度研究》中有很中肯的总结,高氏认为具体原因有四:一是与最高统治者统治少数民族的思想有关;二是羁縻政策的实施必须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羁縻措施的推广只能以少数民族的臣属为前提;三是与汉唐时代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繁荣、政治、军事力量强大分不开;四是西北地区民族复杂,适合于羁縻统治[2]P12。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这些民族地区之所以愿意归附是当时汉王朝与周边各种地方势力相互博弈的必然产物。在汉王朝强大时依附之,汉王朝势力衰弱时,反叛分裂,甚至入主中原,自立为王,如五胡乱华时期,前汉之刘渊,后赵之石勒等。
二、唐朝羁縻府州县的特点与运用效果
(一)唐朝羁縻府州县的特点
第一,随着唐王朝势力的盛衰,羁縻府州的设置或增或减。唐朝在鼎盛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推羁縻府州县制度。开元年间,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设置了八百六十四个羁縻府、州及四百三十七个县[3]P136。但当唐朝势力衰弱时,如高宗征伐高丽,始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后所存州仅十四。再如显庆五年(660年)平定百济,设置了五都督府,但仅存在了五年就废弃了[4]P165。唐朝欲将朝鲜半岛纳入统治范围,却由于地理偏远及政策不当等最终以失败收场。
第二,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府州,共抗强邻。在诸羌地区,在茂州地域设置羌州五十七,在黎州地区设置羌州五十二,“这是为了笼络此二地域的羌人部落,以对付旁边强大的吐蕃”[3]P136。
第三,羁縻府州县的规模很小,人口很少。唐制“正州”设置标准户满四万以上为上州,两万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两万户为下州。羁縻州户数甚至不及唐制的下州,龙朔三年(663年),昆明蛮七千户来归,唐以其地“置禄州、汤望州”[4]P6318,每州平均只有三千多户。羁縻县又小之,贞元九年(793年),东女国诸部落归附,“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4]P5279,每县平均也就二三百户。唐朝依其旧俗,以部落为单位大小酋领都有封赏,是为根本之故。
(二)唐朝羁縻政策的运用效果
唐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羁縻府州制度,将这些地区纳入统治体系。唐朝的羁縻府州由边州都督府或者都护府进行具体管理。唐制,管10州以上的为上都督府,不满10州的称都督府。都督府“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事,[5]P89都护府专设于较为边远的民族地区,主管当地少数民族事务。具体包括“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6]P99等。唐朝的都督府与都护府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地方政权组织机构。即官有定员,各司其职。都护府有大都护1人,秩为从二品,副大都护2人,秩为从三品,副都护2人,正四品,直属官员有长史1人,正五品上,司马1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即掌文书职),功曹参军事(掌组织),仓曹参军事(掌仓积),户曹参军事(掌财政),兵曹参军事(掌军事),法曹参军事(掌司法)各一人,均为正七品。大都督与大都护都是唐廷高官,与尚书同列。可见,唐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视程度胜过前朝。
唐代的羁縻府州是在总结了历代设置经验的基础上设置的,即参照内地行政机构而设的,目的是为将来改流而设的一个过渡时期。在民族地区安部设置府、州、县,配备相应的都督、刺史、县令等官职分级治理。内地府州,其都督、刺史由中央铨选官员充任,而羁縻府州都督、刺史则由各族首领担任,且世袭之。内地府州官员的配备有统一的定制,而羁縻府州的组织机构保留其原有的一套,唐廷认可其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和直接统治本民族的权力。牂牁蛮首领谢龙羽于“武德三年,遣使来朝,以其地为牂州,拜龙羽刺史,封夜郎郡公”。[4]P6319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正月,唐以龟兹为都督府,立原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都督[6]P6309。这种依靠原有统治机构维持民族地区统治的办法,达到了维稳的目的,避免了骤然设置内地府州制度可能引起的不适,划出一定的空间范围——羁縻府州让民族酋领去治理,同时保证了民族酋领的权力与地位,从而使他们乐意接受唐中央的羁縻,为将来参照内地府州设置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三、汉唐羁縻制度的影响
两汉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就效果而言,西汉是较为成功的。东汉由于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附,双方和亲相安多年,东汉王朝得以腾出手来专力对付羌人,由于多任护羌校尉欲建边功,屠杀羌人,引起了羌人的激烈反抗,虽屡屡被镇压,但东汉却为此而衰。两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教训为三国两晋南朝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借鉴。
三国时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三国中魏地辖境最广,东北有挹娄、夫余、高句丽、濊貊等民族,西北有氐羌及西域诸族。曹魏为了加强管理,在中央设置了管理民族地区的机构和官职,虽是沿袭汉制但却因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这是顺应时势的必然。曹魏在中央设置了“鸿胪少卿”与“客曹尚书”两官职,前者负责安排边疆少数民族酋领进京朝觐时的接待事务,后者主掌礼仪。曹魏在各民族地区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与官职分别管理。设有“护匈奴中郎将”、“护鲜卑校尉”、“护乌桓校尉”、“护东夷校尉”、“辽东属国都尉”、“护羌校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等官职。曹魏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分而治之,封赐民族酋领为“王”或“侯”;另一方面防止其做大,以免妨碍其最终的统一大业。蜀汉政权地处“西南夷”之地,面对这种局面,蜀汉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国策。蜀在中央设置的管理民族地区事物的机构与职官沿袭汉制,由“大鸿胪”主管民族地区事务,“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在地方上,将“南中”四郡改为七郡,郡守官员不是当地民族首领,而是中央委派的汉族官吏,大兴屯田,发展生产,开发了“南中”地区,改善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东吴据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起北境有五水蛮、西边有五溪蛮、东南有山越。吴政权在中央设置的机构与职官同于曹魏在民族地区上设置的机构与职官。在民族地区设郡十一,同时在民族地区设置军事监控机构——南部都尉与北部都尉。民族地区的郡守官员由中央政府委派汉族官员治理,这又与蜀汉类似,可见,东吴是参照曹魏与蜀汉对民族地区的治理结合自身实际兼而用之。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但对民族事务却较为重视。西晋对民族地区实行军事性的管制,以期强化管理,早日将这些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范围。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了平州和幽州,前者设护东夷校尉,后者设护乌桓校尉;在北方民族地区,设置了并州,设护匈奴中郎将;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长史府和戊己校尉;在西北民族地区,设置了雍州与护西戎校尉和凉州与护羌校尉,另设护羌戎中郎将;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了益州与西夷校尉和宁州与南夷校尉;在中南民族地区,设置荆州与南蛮校尉;在岭南地区,设置广州、交州与护越中郎将。西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这种管理可以视为前朝羁縻制度的一种变通方式。
东晋与南朝对民族地区的治理,设置了大量的“左郡左县”与“僚郡俚郡”。这是南朝在其控制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的一种特殊的行政机构,控制力强时多置,控制力弱时相对减少。这类郡县规模小人口少,有的郡甚至没有属县。史书记载简略,以致后人对其具体位置也不甚了了。特点是以当地酋领为郡县太守县令,允许其世长其民,世袭其职,只要他们表示臣服就行,南朝不强行改变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南朝现实政治的写照,对北方强邻全力对抗,对南方少数民族只能怀柔羁縻之。对东北与西北的民族政权只要奉南朝正朔,即封给“王”、“侯”、“都督”、“将军”等名号。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高丽王高琏遣使献贡,“诏进琏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7]P1970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吐谷浑王阿犲遣使贡方物以示臣服,少帝封阿犲“可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8]P2371,其目的就是遥为羁縻,引为外援,共抗北朝。
唐朝的羁縻制度对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关系较为紧张,辽、西夏、金、蒙古都对宋构成严重威胁,北宋败亡,都城被迫迁往杭州,南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了对民族地区的施政,逐渐形成了一套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制度。“这种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后来元、明、清时代土司制度的雏形。”[2]P125就这个意义来说,宋朝的羁縻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宋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在宋的北方边疆有契丹及之后取而代之的金,在西北地区有党项建立的西夏,在西南边疆有白蛮建立的大理国,势力较小的还有罗罗族的罗氏鬼国、壮族建立的南天国、吐蕃之后的四王政权等。南宋由于政治中心南移,特别注重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一方面沿袭旧例,继续实行羁縻府州;另一方面又有所变化。宋廷在中央设置了相应的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机构与职官。《宋史·职官志五》载鸿胪寺“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9]P3903。其负责的具体事务是“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辩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9]P3903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裁撤鸿胪寺,将有关事务并入礼部,设主客郎中一职主掌。对待周边民族政权,根据其实力大小分别封赐名号。对偏居西北一隅的青唐唃厮啰政权,为了共同对付西夏,双方都有意交好,早在北宋时期,宋廷就封角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希望其牵制西夏。对南方的大理国,宋朝始终保持对其册封的宗主权,大理则朝贡不断并要求互市,宋廷与大理的这种中央与地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蒙元南下相继而亡。对其能够控制的民族地区,“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具体做法就是设置羁縻州、县、峒,任命各民族大小首领以官职,使之成为宋廷的代理人,实现间接统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强势民族政权的崛起,羁縻制度在宋代已日趋式微,至元则被土司制度取代,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都是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在封建王朝时代就是君主集权,互为表里,相互配套。汉唐羁縻制度是在历代封建王朝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背景下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现实而有效的办法。相对于华夏中心而言,这些民族地区处于中央集权的边缘,但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放松对这些边疆地区的关注,历代王朝无论在中央还是在民族地区设置的管理边疆的相关机构与职官,本质上都是围绕“羁縻制度”而设的,其统治方式由间接控制向直接治理逐步过渡。随着中央政府政治、文化势力的日渐深入,边疆民族地区与华夏中心文明日渐契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向心力开始显现出来。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3]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简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脱脱.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魏登云)
Centralizing Verge and Border Management:A Brief Study of Ji Mi Policy
WANG You-fu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6,China)
Feudal governments in all ages carried out centralism,but enacted other policies according to minorities’customs in the border national areas becaus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strictions.The feudal governments treated the national areas as if they were the marginal areas of centralism and adopted some special policies to control them:Chu Jun system was carried out in the minority areas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and Hu Han military office and Xi Yu supervision office were conducted to implement loose management over those areas.In Tang Dynasty,the Ji Mi system was promoted though the system declined because of the Tang government itself;even though,this system still worked.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lessons,some flexible policies were adopted from Three kingdoms to Two Jin Dynasties,which worked as the Ji Mi system.Up to Song Dynasty,Ji Mi system began to decline,and finally was replaced by Tusi system,a necess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inority areas;border management;Ji Mi system
K234-242
A
1009-3583(2017)-0029-04
2017-02-15
王友富,男,四川南部县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