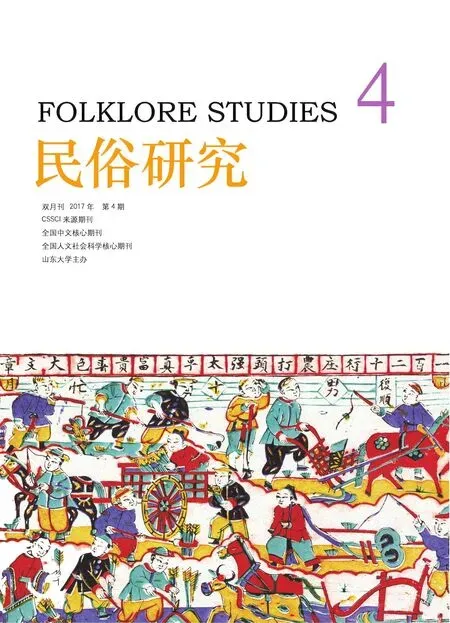“非遗”保护与手工艺类民俗的生活化特质
——以鲁西北黑陶制作技艺传承为例
2017-01-28荣红智
荣红智
“非遗”保护与手工艺类民俗的生活化特质
——以鲁西北黑陶制作技艺传承为例
荣红智
“非遗”语境下,传统手工艺复兴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话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本身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构建和想象,传统手工艺复兴是现代社会中各种力量共谋的结果。研究者需要看到传统手工艺本身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凝结着民间智慧的身体技术表达。本文立足于鲁西北黑陶技艺传承个案,讨论作为“传统”表现形式的手工艺如何被社会各种力量构建和塑造出来,又如何在生活中被赋予更多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
“非遗”;手工艺;生活化特质;身体的技术
前 言
现代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德]乌尔里希·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甚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社会精英开始反思现代性的后果*[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文化被纳入到世界市场中来,并最终被市场整合成趋同的格式化的单一文化样本,文化的多样性正在遭受极大挑战。正如阿加辛斯基所言,“世界化,像技术的全球化一样,拉近了世界各个地区的距离,并使所有社会都处于同一个时代”*[法]阿加辛斯基:《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吴云风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5页。。面对这种情况,不少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在本国传统文化表达中寻找民族性和文化多样性。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独立性,同时通过民族文化维系民众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具体到手工艺来说,它本身也被以“传统”为名而寄予民族文化内涵,对此潘鲁生认为,“相对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希望通过倡导发展手工艺,在现代化的生产中找到自我,在信息化社会,当技术、设备、资讯结成更为开放公共的平台,佳通、交流有了更便捷的路径,手工艺的意义和价值更在于构筑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自我”*潘鲁生:《手工艺的中国语境》,《装饰》2011年第1期。。
以此为时代背景,“非遗”保护运动应运而生。受多种因素影响,“非遗”保护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数十年后,国内才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引入大众视野,并且后来者居上,从2004年开始至今,短短十二三年时间里,我国的“非遗”保护运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是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项目还是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从数量和多样性上看,都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增长态势。
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开始对近乎“狂热”的“非遗”运动进行了反思。张青仁较早地提出民俗的基本特性在于“身体性”,并以此为立足点反思了当时“非遗”保护中轻视传承人主体的行为*张青仁:《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随后,刘铁梁提出“内价值”和“外价值”的概念*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指出“民俗文化的根本价值是它具有生活特征的内价值,而不是把它作为欣赏对象和商品包装的外价值”,并进一步指出当前“非遗”保护实践中出现重视民俗文化“外价值”而轻视或忽视“内价值”的问题。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实践中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纵是如此,在手工艺类“非遗”保护实践中仍有不少现实问题需要讨论。鉴于此,本文借助“内价值”和“外价值”的概念具体分析当前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产生诸多问题的内在机制,并认为手工艺类民俗文化的基本特性是其生活化特质,即手工艺品本身是制作者和使用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类型,其全部内价值都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被赋予的,而对于内价值的尊重正是“非遗”保护实践中所必须强调的伦理原则和底线。具体来说,本文主要立足于鲁西北黑陶技艺传承个案,讨论作为“传统”表现形式的手工艺如何被社会各种力量构建和塑造出来,又如何在生活中被赋予更多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同时引入“身体的技术”概念,具体讨论现代机械化生产对传统手工艺的影响,最后讨论将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保护的困境。
本文田野点为鲁西北德州地区,主要涉及德州市德城区和其下辖的齐河县。从地理区域上看,德州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南部齐河县隔黄河与济南地区相望,西北隔京杭大运河与河北故城县、景县相邻。整体上属于平原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土壤以沙质土壤和黏土为主。近现代以前,该地区民众以农业生产为主,辅之以传统手工业,如补锅、柳编、陶制品生产等。得力于该地区多粘性较强的红壤(俗称“胶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其陶制品生产在附近区域里颇为普遍和流行。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4000到6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该地即已有黑陶器物生产,并且早期的黑陶制品即已经具备了黑、薄、光、钮等艺术特点,素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硬如瓷”的说法。不过,受多种因素影响,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长达数千年时间里,黑陶工艺制作技术再没有较大突破,甚至再没有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黑陶艺术品现世。正如齐河黑陶创始人、中国黑陶研究所所长刘浩所言,“可以说,黑陶产品中断了几千年,这门手艺事实上已经失传了”*讲述人:刘浩,1939年生,齐河县人,中国黑陶研究所创始人,齐河刘浩黑陶陶艺馆馆长,讲述时间:2015年10月3日,讲述地点:齐河刘浩黑陶陶艺馆内。。不过,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再没有黑陶工艺品出现,但作为日常器物的陶制品(多为砖红色)生产却从未中断过。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德州及附近地区乡村里还有专门生产售卖陶盆、陶罐的流动商贩。直到今天,民间尚有歇后语,“卖琉琉盆的——一套一套的卖”,用以指称能说会道的人。由于陶制品本身有渗水性等缺陷,陶制盆罐在储放液体时极为不便,在对此,民间艺人仿照瓷器在陶制品制作过程中增加了“上釉”(民间将“釉”称为“琉璃”)环节,这样生产出来的陶盆陶罐就具有了防渗透特性。
一、“传统的发明”:鲁西北黑陶工艺的“重创”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家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一时间国门大开。当时国家为增加外汇储备,鼓励各地方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以“工艺美术品”换“外汇”。在政策支持下,许多地区以县域为单位纷纷成立各种工艺美术厂。在此时代背景下,1979年,德州市政府聘请寇维军、马淑荣两位民间艺人,在当时的德州市于官屯公社卢庄村建立市、社、村三级投资的德州美陶厂*杨阳:《黑陶艺术,何去何从——山东德州黑陶艺术发展现状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天津美术学院,2014年,第6页。。不过,受制作技术水平影响,当时美陶厂主要制作工艺花盆。1984年德州市政府在卢庄美陶厂基础上创建了德州工艺美陶研究所,在所长王宪利带领下,研究所开始探索从工艺花盆向更多品类转向。1986年在全所工艺美术师的努力下,终于研制成功黑陶技艺,取名“德州黑陶”,使得这一失传数千年的民间手工艺得以重新现世。其后“德州黑陶”相继在不少世界级博览会上获得各类奖项。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出口效益降低,且国企改制逐步深入,不少工艺美术厂开始走下坡路。到21世纪初,已经有不少地方的工艺美术厂宣告破产倒闭。这个阶段,德州地区制作黑陶工艺品的厂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2002年前后,1988年毕业于德州学院艺术系,后在德州工艺美陶研究所从事设计工作的梁丽霞创办了梁子黑陶研制中心。按照她的说法,当时德州工艺美陶研究所日益衰落,眼看刚刚起步十几年的黑陶工艺即将夭折。在这种情况下,凭着对黑陶艺术的热爱,梁丽霞用借来的7000元钱租了三间平房,并低价购进的两台二手机器,开始了她的“黑陶事业”。梁丽霞告诉笔者,“当时挺苦的,虽说当时是搞黑陶设计,但整个生产流程并不熟悉,先是两台旧机子,自己找人累了个窑,从制作到烧制成功,各个环节都得摸索,两个来月,第一批黑陶终于出来了,一看,颜色有黑有土红色,不均匀,有的烧裂了,非常难过。把所有的黑陶制品都砸了。整整一天,难过的不行”*讲述人:梁丽霞,德州梁子黑陶创始人,讲述时间:2013年11月12日,讲述地点:德州市德城区梁子黑陶文化园内。。难过之余,她到处找师傅学习,“可以说是遍访名师,最终从北京请来了烧窑专家,帮我解决了烧窑问题”*讲述人:梁丽霞,德州梁子黑陶创始人,讲述时间:2013年11月12日,讲述地点:德州市德城区梁子黑陶文化园内。。经过两年探索,她的黑陶事业逐渐走上正轨。2004年她雕刻设计的《玉凤马》获得了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2005年她扩建梁子黑陶研制中心为梁子黑陶文化园。2007年黑陶文化园被山东省文化厅定为山东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09年梁子黑陶被列入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梁子黑陶外,德州市下辖的齐河县黑陶制作技艺也较有特色,而且起步也比较早,这与“中国黑陶研究所”创始人刘浩的努力有莫大关系*需要提及的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曾听到不同看法,有同样在齐河开办黑陶制作厂的艺人说齐河黑陶技艺是从德州工艺美陶研究所习得的。由于笔者主要访谈的是刘浩本人,因此行文以其讲述为主,限于本文主题,对此问题不再进行深究。。早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的刘浩,在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河北馆陶县从事民间音乐创作活动,期间曾创作不少音乐作品。198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馆陶县,转而投身商海。“可以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了黑陶,我当时去博物馆,看到这个龙山文化,这个黑陶技艺很高啊,我自己是搞艺术的,搞音乐创作的,我一看就很喜欢。当时我已经回到了齐河。我们这里呢,有烧琉琉盆的老师傅已经开始琢磨黑陶了。我一看呀,挺喜欢,我也开始鼓捣黑陶,这是1988、1989年的事儿了”*讲述人:刘浩,讲述时间:2015年10月3日,讲述地点:齐河刘浩黑陶陶艺馆内。。刘浩在钻研过程中,四处寻找师傅,在多次试验失败后,终于获得成功,并在1980年代末开创性的举办现代黑陶艺术培训班,并帮助其学徒先后在济阳、东阿、章丘、日照等地区开设黑陶制作厂。随后十多年里,刘浩制作的黑陶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并屡获大奖。1990年代初受轻工业部中国陶协委托与清华大学共同建立中国黑陶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职务。2004年成立了刘浩陶艺馆,馆内主要展放其个人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制作的黑陶艺术品,另有不少当地新生代艺人的代表作。2007年刘浩策划主持了山东省首届黑陶陶艺国际学术理论研讨会,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齐河乃至山东地区黑陶文化的影响。笔者于2015年10月前去访谈时,早已退休的刘浩先生仍在思考着有关黑陶艺术的相关理论问题。2015年齐河黑陶制作技艺与薛家窑泥陶烧制技艺、黄泥古陶制作技艺一起被列入山东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除了梁子黑陶与刘浩黑陶外,目前德州地区从事黑陶制作、生产的厂家或作坊还有多家。限于篇幅,兹不赘述。通过对德城区梁子黑陶和齐河黑陶制作的发展历程的简要梳理,不难看到,德州地区黑陶制作技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技艺”,与其说其是古陶艺的复兴不如说是“重创”。当把研究目光从技艺本身转移到其制作者与所处的生活世界时,就会发现黑陶制作技艺的“重创”实际上是几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来自政府的推动力。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政府鼓励发展地域性工艺美术以带动外贸,因此有政府政策支持;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减弱,各地工艺美术厂开始走下坡路;2000年以后正在传统手工艺行将消逝之时,来自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运动再次给手工艺发展带来生机。
第二种力量来自于民间手工艺艺人,也可以说是手工艺的内生力。严格来说,黑陶制作的手工艺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艺人”,他们大都是经历过学校艺术教育,或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手工艺“合作化”时代习得的技艺,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在手工艺“重创”过程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第三种力量来自市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日益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传统手工艺在1980年代确实能够满足当时社会审美需求,刺激了手工艺的短期回暖,这也为21世纪后手工艺类“非遗”保护实践中保存了“传承人”。
第四种力量来自于消费者。黑陶制作工艺重创之初,受政策影响主要消费者是外国人,他们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广泛接受手工艺品,促进了手工艺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后来出口转内销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沉期。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机械化生产的商品审美渐趋疲劳,这为传统手工艺品回暖提供了国内消费市场。
二、“黑陶”制作:泥土中凝结的生活体验
在关注民间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时,张士闪等提出“民间工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创造、传承和演变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因而民间工艺研究的前景就在于呈现它与所属整体民俗生态的互动关系”*张士闪、邓霞:《当代民间工艺的语境认知与生态性保护——以山东惠民河南张泥玩具为个案》,《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本文认为,将黑陶工艺制作放置到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和社会生活中来考察,有利于理解其整体上的重要性及其社会意义。
(一)黑陶技艺传承中的身体记忆
在黑陶制作过程中,制作者既是将生活融于艺术中,同时也是将艺术融于生活中。正如笔者在田野中观察到的那样,很多人早年接触黑陶,也许并不是基于兴趣或对艺术的追求,而是基于生计需要。正是在这种谋生活或讨生活的行动中,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使其从普通日用物品逐渐变成具有审美意趣的艺术品。黑陶制品作为物质载体将这个过程深深地嵌在生活之中。此时,黑陶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更重要的是凝结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身体记忆,同时也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融相生的和谐关系。
简要回顾手工艺品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随着各种替代材料的出现,手工艺品的器用功能日趋减少,不过这也成就了其审美功能的日趋强盛。时至今日,合成材料与化工材料制成品充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以黑陶为代表的手工艺品已经逐渐成为纯粹的审美艺术品。它们经常地具体体现出汇聚在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与应需求而产生的古风,由少数人的范例所激发出的想象力,正是这些想象力进一步将手工艺品脱离出生活现场,就像构建脱离了地基的“空中楼阁”。当然,因为黑陶制作材料为泥土,这使得其具有了天然的“土气”,而在近代以来,“土气”正是现代城市人给乡村贴上的标签之一,于是,黑陶制品在此具有了乡村的气息和文化意义,这为厌倦了都市现代生活的城里人提供了一种可触可感的象征物,满足了他们探寻和想象乡村生活的“窥视欲”。正如法国学者罗什所言,“处于对这些旧式的乡村材料的嗜好,人们通过模仿和工业化手段大量复制,以满足其他需求”*[法]达尼埃尔·罗什:《平常事情的历史——消费自传统社会中的诞生(17世纪初-19世纪初)》,吴鼐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除手工艺品消费者之外,黑陶制作者也往往将属于其个人的生命历史融入黑陶制作中来。在制作者那里,黑陶已不再仅仅是物品,它们更是某段生命历程的见证。作为一门手艺,黑陶是制作者赖以谋生的方式;作为一种艺术品,黑陶是制作者回顾人生经历时重要的物质载体。笔者在齐河田野考察时,有位黑陶制作艺人回忆了她当年学习黑陶技艺的经历:
我给你说吧,那时候下了学,也没事干啊,后来就巧了,一个亲戚给我介绍让我来这里学黑陶,一看我就着迷了,感觉真是好玩。后来,那时候,正年轻,厂子里是半工制,就是你上一天班,学徒工,给你算半个工。什么时候出师才能挣整工的钱。那时厂子还实行几件和日工一块算的工资方式,有些老师傅为了多挣钱,人家就一直在那儿干活,哪有空管你啊,是不是,你一个学徒工,这时候我就偷学艺,就是在打杂时,偷学点。那时候也是真疯狂,你说着迷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们厂还有一个人,我俩,经常半夜偷偷跑到厂子里对着老师傅们做好的活儿,学习揣摩。我记得有一次,忘了什么时候了,也是晚上又爬窗户进去厂子,不知怎么的,就被窗户上铁丝挂了胳膊了,立马就是一道口子啊,疼的啊。就这样,第二天照常上班。现在孩子们可受不了这罪了。*讲述人:刘女士,1972年出生,现为某黑陶制作厂“大师傅”,主要负责压光、刻花等,讲述时间:2015年10月13日,讲述地点:齐河县城某黑陶制作厂。
(二)手工艺的“现代化”:从身体技术到机械生产
手工艺品凝结了制作者的生命体验和身体技艺,因此,可以说传统手工艺制作所体现出的是一种身体的技术。很多时候,这些取自于自然环境中的普通材料,经过制作者的加工,变成了能够产生某种生活意义的物品。自此,这些物品被赋予了生命,这些被称之为艺术品的手工艺品自然也就成了制作者身体的延伸。黑陶生产亦是如此。制作者将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嵌入身体的技艺与泥土表达出来,这时黑陶已经变成了行动叙事的载体。每个黑陶制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并不是泥土本身所散发出来的,而是饱含制作者的喜怒哀乐的日常叙事。
在田野调查时,我注意到一个拉坯师傅,一边同我交流,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转盘上的泥坯。他语速缓慢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像是给我讲述,也像是给黑陶讲述。等一个泥坯做完,他才从紧张中脱身出来,边擦拭额角的汗水,边对我说,“黑陶制作这门技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先不说从泥土到完整艺术品需要经过数十道繁杂的程序,但就成型这一项,稍有不慎,就变得面目全非”*讲述人:张姓师傅,男,齐河县人,40岁左右,16岁开始进厂学习黑陶制作,专门负责拉坯工艺,已经成为厂子里的“大师傅”,现在手下有3个徒弟,年纪均在16、17岁,讲述时间:2015年10月13日;讲述地点:齐河县某黑陶制作厂。。他告诉我,“我敢说,如果是纯手工的黑陶,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制品”*讲述人:张姓师傅,讲述时间:2015年10月13日;讲述地点:齐河县某黑陶制作厂。。他的手指缠绕在花瓶上,任由其形状变化。当经验告诉他已经差不多时,他会适时收手,一个泥坯的定型就算完成了。之后,他会小心翼翼地将其取下,放到旁边的空地上。他告诉我,好的黑陶制作者有两个境界,一个境界是能够做出几乎一样的物品,这是技术达到了非常高超境地的表现;另一个就是随心所欲做出的物品件件都能可圈可点,这是艺术达到了非常高超境地的表现。他特别强调了“技术”和“艺术”两个词,他说之所以谢谢我,是我认可了他的达到了第一层境界。他说对于黑陶艺人来说,一辈子能达到第一层境界已经很值得炫耀了。
虽说手工艺制作是身体的技术,但不可否认,几乎所有门类的手工艺品及手工艺制作者都需要借助工具。甚至在传统社会里,不少手工艺门类的制作工具本身就是“行业秘密”之所在。民间手工艺人常说,“三分艺七分器”,其中的器指的就是手工艺生产中作为身体延伸的工具。尽管在手工艺制作过程中,工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传统手工艺制作者仍将工具视为身体的辅助性工具。在手工艺品制作过程中,身体的技术仍占主导地位。身体技术很大程度上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术,这也为传统手工艺历经千年千而绵延不绝,还能保持其地域性或个体性特征提供了技术保障。
现代社会里,各种机械的广泛运用逐渐取代了传统工具,并且随着机械技术不断进步,在手工艺品生产过程中,身体技术逐渐退居第二位,也正因此现代社会里出现了大量的机械复制品。由于手工艺人身体参与程度较低,因此这些机械复制品呈现出标准化、批量化,辨识度不高等特点。随着艺人身体技术的退出,手工艺品逐渐成为工业品,它失去了在制作者日常生活中生成的现实土壤,因此变成了阿加辛斯基意义上的“幽灵”,而本雅明将其称为“灵光的消逝”*[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在文化工业时代哀悼“灵光”消逝》,李伟、郭东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换言之,现代手工艺品因其脱离了现实生活而变得没有灵魂可言,“现代世界中,技术以闻所未闻的方式在增强复制的可能性,而复制的原型又提供了模型。大量复制某些商品这种工业方式在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之外,可以生产和增加图画,其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最独特的复制。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图画,这使我们与幽灵们同处一室,并使我们不禁对我们时代的一致性提出质疑”*[法]阿加辛斯基:《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吴云风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以黑陶生产为例,在市场逐利的驱动下,不少现代黑陶制作厂家开始引进机器流水线作业,几乎所有的手工艺人都变成了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所从事的不再是具有个体创造性的艺术品,而是“依样画图”的生产工业产品,也正因如此,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特产”趋同化现象。而这并非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而是现代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全球范围内都出现的现象,日益世界化和机械化的文化,正在吞噬着富有地域特色文化多样性。某种意义上说,当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者变成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后,作为艺术品的黑陶就已经失去了其灵魂。当消费者将这些工业技术复制的工业品或复制品摆在房间里时,它们更像是胶泥烧制的幽灵。这种幽灵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与这些被赋予象征着传统意味的东西同处一室,就能经验和体验到过去。其实这不过是现代人一厢情愿的幻觉罢了。现代人妄图通过这些复制品连接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他们将这些毫无灵魂可言的幽灵看成是时间的摆渡者。但正如里茨尔在评论机械化时代流水线作业和快餐文化时所指出的那样,“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详见的,装配线携带许多不合理性。它明显地提供了一个非人道的工作场所,具有广泛技能和能力的人类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去重复履行数目有限而高度简化的任务。不是要求工人在工作中表现其个人的能力,而是强迫他们否定自己的人性并像机器人那样做着重复简单的劳动。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能表达他们自己”*[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三、“撕裂”的阵痛:手工艺类“非遗”保护的困境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机械生产的工业品日益渗入民众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承载着民族精神的手工艺明显衰败下去。正如英国学者威廉·莫里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呼吁的那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盼望,闪耀着睿智光芒的手工艺,将重新回到这个饱经战争、骚乱以及生活变幻无常之苦的世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将会开创出一个能够平和、周到地对待每个人的现世幸福的欢乐世界”*[英]威廉·莫里斯:《手工艺的复兴》,张琛译,《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1888]2002年第1期。。一百多年来,受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的感召,不少社会精英为“拯救”传统手工艺进行了多种探索。在日本学者柳宗悦看来,这些社会精英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艺术家,一类是社会知识精英。*[日]柳宗悦:《工艺文化》,徐艺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个体艺术家通过将民间手工艺从其生活现场中抽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美术作品,从而保留其形。正如柳宗悦所言,“他们抱着把工艺从实用工艺引向工艺美术的热情。使个性在工艺中得到必然的表现。以追求超越现实的纯正的美为目标”*[日]柳宗悦:《工艺文化》,徐艺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然而,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某种意义上说,当手工艺的基本特性从生活实用性转变成审美特性时,它的生命力就已经衰竭了,它作为手工艺的品格就丧失了,它已经变成了为纯粹审美而存在的“艺术品”。这样的艺术品只是保存了手工艺的外在形式,它从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个体创作中,它的审美也具有了独特性,它被署上了名字,它成为制作者的专属,因此,它脱离了民众。它成为特定社会阶级的玩物。此时,与其说是个体艺术家拯救了手工艺,不如说他们只是在手工艺的坟墓上攫取了一抔土。因此,面对传统手工艺的颓势,依靠个体艺术家的创作冲动来拯救并不是最佳路径。
社会知识精英在面对手工艺衰颓时,将其冠以“传统”之名进行保护。就中国具体实践而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知识精英广泛参与的“非遗”保护运动产生的社会效果最为明显。不过,手在现行的“非遗”保护条例中,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割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审美倾向明显、具有形式意义的“传统美术”;而另一部分是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具有实用意义的“传统技艺”。
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美术”最终旨趣与个体艺术家不谋而合了,因此这一部分在“非遗”保护中效果最为显著。而更能表现手工艺生活化特质的“传统技艺”却未得到更充分的认识。不可否认,直到目前,“非遗”保护者仍以“审美”为标准对其进行“格式化”处理。在进行保护对象选择时,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在遴选保护项目名录时,一般都是在既定的框架内选择与之相关的或相应的手工艺项目,如果不能保证既定框架具有相当的普适性,那么势必就会造成真正具有个性或地方性的手工艺最终并不能进入保护名录。
笔者在调查时,即发现平时联系不多的黑陶生产厂家所生产的黑陶作品几乎都是同样制式,比如“宝葫芦”题材、“笔筒”、“镂刻净瓶”等题材,这些工艺品制作者都声称作品来自于个体创作,但其实这都是早期“非遗”保护中未注重“技术权利”*廖明君、邱春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变迁——邱春林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0年第2期。而致使互相模仿抄袭的结果。虽然近几年来,无论学界还是政府都开始注意到“非遗”传承人“技术权利”问题,但在具体实施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邱春林所言“如今回归个体私营经济之后,技术的保密意识明显强过技术公开,这是否有利于年轻艺徒的成长?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廖明君、邱春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变迁——邱春林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0年第2期。。
另外,除“技术权利”之外,手工艺类“非遗”保护实践中仍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比如现在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比较盛行生产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宋俊华:《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陈华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吕品田:《在生产中保护和发展——谈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方式保护”》,《美术观察》2009年第7期等。、“资源化”*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学苑出版社,2010年。等保护理念。这些理念本意都是为解决“非遗”保护中只重形式不重内涵的“舍本逐末”倾向而出现的,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扔仍未触及“非遗”保护尤其是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是对其根本特质和价值需要重新综合评估,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建立合理有效的长期保护机制。否则,在具体实践中,手工艺类“非遗”保护无论是“生产性保护”还是“生态性保护”,还是“资源化”处理,最终仍然不免陷入表面化、标准化、趋同化等困境中去。
当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以上保护理念的不足,并提倡从“生产性保护”到“生活性保护”的转变,为本文继续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不过,该研究仍限于从局外人的视角去观察生活,忽视了手工艺类“非遗”生活化特质,而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本质上是要在推动传统文化生活样式的传承、延续乃至创新的同时,寻求民族国家现代文化发展的精神内核,要在文化意义的生产层面推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变迁”*胡惠林、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艺术百家》2013年第4期。。
同时,传统手工艺本身是身体性的,它对于反思现代性而言,最主要的特性在于身体性,即手工艺是对于制作者而言是身体技术的呈现,与现代机械时代的复制品相比,其更具传统“灵光”,这也是其独特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在讨论对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我们需要将其回归生活,使其在生活之流中得以延续。正如朱以青指出的那样,“对其保护的最好方式就是在生产中保持其核心技艺和核心价值,并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使之在生活中持久传承”*朱以青:《传统技艺的生产保护与生活传承》,《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当然,承认制作者传承和保护主体地位,并非完全放任自流,而需要有外部力量的适度干预。笔者调研中发现,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干预而放任自流,手工艺制作者在面对现代市场时,往往会选择迎合市场口味,丢弃不符合市场效率的纯粹手工制作和核心技艺,甚至通过制作各种现代机械来复制“徒具其形”的所谓传统工艺品来谋利,彻底破坏了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内涵;或者有些相对比较“保守”的制作者固守传统技艺本身,不参与现代市场和现代生活,结果在市场化浪潮冲击下,逐渐败下阵来,甚至难以寻觅合适的传承人;还有一种是“头脑比较灵活”的手工艺制作者在传统技艺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创新,既能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同时又能保持传统手工艺中的“核心技艺”。
结 语
在当前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生产性保护”已经基本成为社会共识。实际上,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倾向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因为在现代市场逐利效应影响下,“生产”与“生活”是相互脱离的,“生产”更多意味着标准化、规模化、趋同化等,而这与“非遗”保护运动维持文化多样性的初衷相违背。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传统手工艺的基本特性是身体性和生活化特质,而这一特质也是维系其生生不息,传承千年而不绝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在讨论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研究者有必要将其纳入到社会生活中来综合考量。脱离了生活本身,它们就是无根之水。将其剥离日常生活,而从所谓的文化意义上对其进行解读,最终并不能实现真正理解手工艺在当下社会存续或消亡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传统手工艺是深深地嵌入在社会生活之中的,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从未在生活中消失,因此,也无从谈其“复兴”问题。在不少文化学者眼里,所谓传统手工艺复兴实际上是其形式和要素的恢复,其精神内涵无论如何都不会恢复到“过去”。因为生活的现代性决定了以生活为土壤的手工艺必然会具有了现代性特征,或是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更不用据此就“呼天抢地”,认为“传统不再”之类。正是有赖于在与不同时代社会生活不断融合中有所创新,才使得传统手工艺本身能够传承至今,换言之,满足生活需求是传统手工艺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
荣红智,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山东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