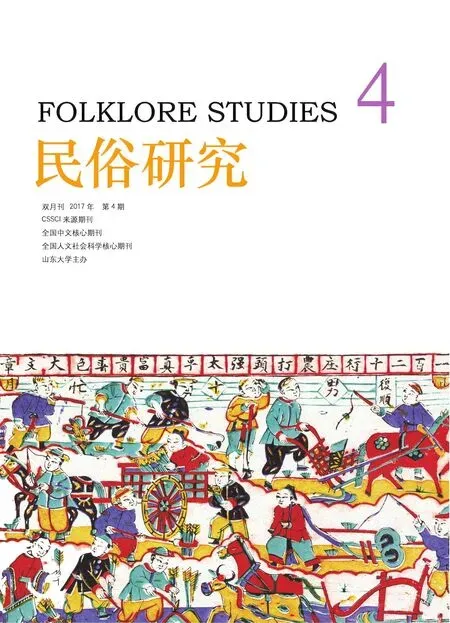文化迁变—卡舒巴城市文化思想评述
2017-01-28包汉毅
包汉毅
文化迁变—卡舒巴城市文化思想评述
包汉毅
卡舒巴认为把文化视作全部生活样式的宽泛定义可以作为研究城市文化动相与变相的概念基础。他指出,文化几乎只存在于迁变之中,是迁移的、变形的、混合的、杂交的、过程的……。依据“迁变生起”的标准,可以划分为自然发起的常规文化迁变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利益而人为有意推动的新式文化迁变,后者可以称为“文化的转基因”,并促成了新的共同体结成形式。借鉴西方经验,探析文化传承中的动相与变相,实现城市的移风易俗与社会和谐,是中国民俗学者的新使命。
文化迁变;常规文化迁变;新式文化迁变;共同体新结成形式
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1950年1月1日出生于德国格平根(Göppingen);1980年获得图宾根大学“经验文化学、政治学和哲学”的文科硕士学位,198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87年取得“经验文化学、民俗学”专业的大学特许任教资格;1992年起任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专业教授,1994年起任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德国国家融合与移民问题研究所所长、德国民俗学协会会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德国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等职务。
作为世界知名的民俗学者,卡舒巴著作等身,其研究重点为现代欧洲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民族和种族的身份认同、城镇和都市研究以及知识和科学历史。新世纪以来的中后期,其研究重心尤其聚焦于城市文化。本文即致力于厘清卡舒巴以“文化迁变”为核心观念的城市文化思想,在宽泛文化定义的基础上,首先阐发对于“文化迁变”的概念理解,然后依循“迁变生起”的标准,将卡舒巴所论述的文化迁变类型划分为“常规文化迁变”和“新式文化迁变”,其中后者又可细分为种种不同的类别,从而最终实现了文化迁变范畴的细致结构化。我国的文化遗产研究侧重于“不变”,而尤其偏向于乡村空间;卡舒巴以城市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而又特别着眼于文化的动相与变相。毋庸置疑,在我国城镇化过程愈来愈推进的今日,以卡舒巴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城市文化研究,是大有可以借鉴之处的。
一、文化定义基础
西方的文化概念起源于拉丁词“cultura”,本意指的是“对于土地的耕作”,后来慢慢延伸至“精神的耕耘”。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知识成为主导的准则,由此开始了对于文化概念的现代化认识。但是,学术界对于文化的定义非常繁多,如卡舒巴所说:“就连批评家们都讽刺说,文化的概念如此宽泛和开放,以至于文化在今日是指代一切事物和完全自由的。”*Wolfgang Kaschuba, “Einführung zum Kulturbegriff und dessen heterogene Bedeutung”, in Lieselotte Kugler and Gregor Isenbort (eds.), Glücksfälle-Störfälle. Facetten interkultureller Kommunikation. Berlin: Kataloge der Museumsstiftung Post und Telekommunikation, 2012, p.20.而如果要探讨文化的动相与变相,那么,那些僵化地将文化与某一种族、某一阶层或者某一形式等固定挂钩的文化概念就自然不能作为研究基础了。比如,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理解是“知识教育与人格培养”,就打有市民阶级的标签,与后来基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大众文化相对立,因为后者是与诸如电影、快餐、租房、地铁等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现象,遭到了市民阶级的歧视。纳粹分子许诺给予所有社会阶层和文化现象以同等地位,却又将之限定于雅利安人种之内,他们的由人种所论证的文化观念,就更不值一提了。
二战以后,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范围内的学术、政治讨论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日常生活和具体生活世界即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的缔造者。因而,正如卡舒巴所指出的,将文化定义为“全部的生活方式”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Wolfgang Kaschuba, “Einführung zum Kulturbegriff und dessen heterogene Bedeutung”, in Lieselotte Kugler and Gregor Isenbort (eds.), Glücksfälle-Störfälle. Facetten interkultureller Kommunikation. Berlin: Kataloge der Museumsstiftung Post und Telekommunikation, 2012, p.25.这一定义广为学者与大众接受的原因在于以下四点:首先,它修正了过去将文化区分为高等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错误;其次,它将精神的、物质的、符号的文化实践融合在一起;再者,它通过行为者的经验将历史与现实连接在一起;最后,它指出了文化实践的过程性与灵活性。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的概念,基于此,人们就可以认识到文化身份认同的可变性、可选性与多元性,由此文化也就失去了类似“抽屉体系”般的固定归属性,而具备了运动性与杂交性。
显而易见,这一宽泛的文化概念可以作为探讨文化“动相”与“变相”的基础。
二、文化迁变的概念理解
“文化迁变”译自德语“Kulturtransfer”(英语:culture transfer)。其实“transfer”的本义在于“迁移”,所强调的是“动相”,但卡舒巴教授特别指出:“文化迁变在内容和外观上也都意味着变形”*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34.,又特别点名了“变相”,因此笔者最终选择了“迁变”这一译词作为对应。
实际上,“文化迁变”是文化学和人种学中一个并不陌生的范畴,它特别突出了文化的空间性和运动性。历史上,民俗学“由于社会阶层划分而导致文化事物下沉”的观念、人种学所讨论的文化传播过程等等都是与文化迁变相关联。但是,如上所述,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术界的文化理解都是静态的,所探究的是长时间存续的传统模式、观念和价值,即是“文化遗产”。在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逐渐关注文化的运动、迁移、变形和合成的特性,乃至最终提出:“Kultur im/als Transfer”*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11.(文化在迁变中、文化作为迁变)。如果将这句话换作汉语的惯用表达方式,即是:无文化不迁变、无迁变不文化。卡舒巴教授明确指出:“强调来说,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事实上文化几乎只存在于迁变之中:作为过程和动态,在运动和混合中,作为引用和复制,在区别和联系中。”*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13.由是言之,如下的形容词可以作为描述文化迁变现象的关键词:迁移的、复制的、变形的、混合的、交流的、杂交的、过程的、推动的…
早在20多年前,德国的欧洲民族学界(民俗学界)就已经开始探讨种族社会和全球范围内文化迁变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文化迁变”已经成为文化分析的核心概念,其原因在于:它总能带来新的视角,而且尤其注重变动和混合的因素;它是研究跨文化现象的基础,因而又在全球化讨论中始终有着现实意义。
卡舒巴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种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迁变,依据笔者的分析,如果遵循“文化迁变的生起”这一标准,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类别:首先是在社会历史文化衍变过程中自然而然所发生的文化迁变,符合大众常规认知的,可以称之为“常规文化迁变”;其次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利益而人为有意推动所发生的文化迁变,主要是近几十年与“城市品牌化”(city branding)策略相伴而生的,可以称之为“新式文化迁变”,它是卡舒巴的研究重心所在。
三、常规文化迁变
常规文化迁变是跨空间的、由域外到域内的,其发生地是城市。城市是以迁徙、移民以及物品、思想和价值观的持续交流为其起源和主要特征的,是不同文化的会遇地、混合带。外来移民不同于游客的今天来、明天走,他们是要长期居留于此的,对于自己的“外来性”,他们一方面意图继续保有下去,另一方面却因为要融入当地土著们的生活环境而不得不作出“本地化”的努力,由此而发起文化迁变,它是“本地化的身份认同设计”。对此,卡舒巴教授举出了一个典例:很多莫斯科的快餐摊位所打的招牌竟然是“正宗柏林的土耳其烤肉馍(Döner)”,人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不是“正宗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烤肉馍”呢?实际上,这恰恰是因为莫斯科人真正深入地了解了饮食文化:传统的烤肉馍确实来自土耳其,但土耳其人总是将馍和肉分装在盘子里,在家中或是餐馆的餐桌边安静地用刀叉享用。1972年,在柏林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艾根(Mehmet Aygün)的土耳其移民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他认为土耳其的饮食文化必须要和柏林的城市环境结合在一起,因此把烤肉馍的馍、肉、酱汁、沙拉等等合成三明治的“集装箱”样式—自然,在这一迁移过程中,其制作材料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人们不再需要盘子,而是站着、走着都可以享用这种土耳其食品。这当然是“正宗的柏林土耳其烤肉馍”,无论在饮食文化、还是在身体补益的意义上,都显然更有价值。
对于常规文化迁变的特征,卡舒巴明确指出:“城市从来不是一个熔炉,因为现代文化从来就不是一种平滑无痕的合金物,其基本组成部分始终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明晰可辨的、混合的。”*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14.显然,在指出城市外来文化的“迁移”和“变形”两个特征之外,卡舒巴也强调其中不变的“传承性”,这也是“迁移”和“变形”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理由。“遗传”与“迁变”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之间是一种彼此依存、互动的辩证关系。
基于其动态性与交流性,大城市成为“文化迁变的天然区域”,它是“文化的高速公路”,是“开放的文化中转站”。倒过来,文化迁变又正是大都市特别优异的资本,因为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与充满张力的争衡状态,恰恰是城市社会活力与文化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四、新式文化迁变
在其系列文章中,卡舒巴所特别着意的是那些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利益而人为有意推动而发起的文化迁变,为了与上述自然而然所发生的常规文化迁变区别开来,笔者将其称为“新式文化迁变”,因为这类迁变主要是发生在近几十年,主要是与城市品牌化(city branding)策略联系在一起。其间所涉及到的是“场所营造”(place making)的问题,全球各大城市为了在吸引资本、繁荣旅游业等方面展开竞争,而主动积极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文化迁变,大体说来,主要有如下一些种类:
(一)由历史遗留到现代诠释的跨时间迁变
各大城市首先把目光都投向了自身所拥有的历史、传奇、建筑、记忆等种种具有独特地域色彩的文化事物,当然也并非是对这些经典事物原封不动地加以展示,而是予以有意义的重新包装、阐释,正如卡舒巴所阐明的:“在二战后的现代化时期,很多的城市和地区蠢蠢欲动,欲‘整理’历史遗留的景观与建筑,或者至少要剧烈地对其加以改造,以跟上新经济、新美学的步伐。”*Wolfgang Kaschuba, “Europäisches Kulturerbe”, in Volker Hassemer and Bernhard Schneider (eds.), Städte und Regionen. Ihr kultureller Auftrag für Europa und seine Umsetzung, Berlin: Schneider, p.134.这些文物古迹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蕴有独特的美学色彩,在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复兴以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触发、召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而且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从而助其在全球竞争之中取得些许领先身位。对于这一类型的迁变,笔者将其名为“由历史遗留到现代诠释的跨时间迁变”。
(二)由精神记忆到物质实体的跨形态迁变
此外,各个民族、城市都还拥有自己专属的集体记忆。长时间以来,这些记忆只是存积于人们的脑海之中,是纯精神的形态。然而,它们也开始逐步地通过一些特定的纪念建筑而被展示出来。对于这类迁变,笔者认为可以将之称为“由精神记忆到物质实体的跨形态迁变”。美国艺术家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在柏林所建造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即是一个典例,它将德意志民族的集体内在忏悔展现为可视的公开形态。它又具有独特的美学魅力,能够唤起人们种种不同的想象—公墓、田地或是道路。由于这些特质,这个纪念碑群也就成为记忆政策的一个典范。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人们也效仿建造了一座奥斯曼军团大屠杀的纪念碑,同样引发了轰动效应,以至于后来土耳其人在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备受压力。这类的跨形态迁变,其意义主要在于:第一,悄无声息的无形记忆变成为实体建筑承载的有形记忆;第二,都市的中心区域不再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场所,而是“编码”为彰显集体记忆的纪念场所;第三,承载记忆的建筑物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们“以特别方式体现着地域的历史、高等文化、艺术和建筑风格,所以被特别设计为都市的‘皇家宝石’。”*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19.简而言之,这种跨形态的文化迁变将记忆政策、品牌策略和城市建筑三者巧妙地融为一体。
(三)由世界主义的文化思想到物质实体的跨空间与跨形态迁变
然而,由无形到有形的迁变又不仅仅限于共有的集体记忆。比如,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同样以其噱头十足、令人目眩神迷的建筑风格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因为建筑师盖里(Gehry)将前卫的世界主义文化思想彰显于此,一经推出,即为世人所瞩目。默默无闻的小城毕尔巴鄂一夜之间也成为了全球家喻户晓的城市,演变为新的世界旅游热点,因而也就成为世界主义文化的代表之一。这一类“由世界主义的文化思想到物质实体的跨空间与跨形态迁变”特别具有吸引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不过,除了文化产业的意义之外,其负面效应也同样存在。比如在汉堡的易北河中央矗立起了一座“易北河音乐厅”,却引发了一番关于品牌化的争论,招致了不少汉堡人的反感,他们认为音乐厅所展示的优雅风格并不是汉堡人的特质。
(四)异域文化色彩的跨载体迁变
关乎到经济利益的迁变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比如,在柏林移民区有一家“土耳其菜市场”,本来这些“低廉土耳其产品”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阿拉伯人以及一些大学生和游客,效益低下。但是,后来经营者作出了“文化拔高”的努力,将市场的名字取名为“东方生态市场”。如此一来,原来由奥斯曼帝国历史、建筑、服饰、骆驼等所承载的浓厚异域风情就迁移到了市场商品的身上,市场所售蔬菜一如从前,然而就摇身一变成为了“生态”健康和“东方”情调的供给品。*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23.一时间,市场的生意火爆起来,土生土长的柏林人也蜂拥前来,环绕着这一市场的区域也因而完成了士绅化的过程,成为了一个繁荣的街区。这类“异域文化色彩的跨载体迁变”可称之为“民族品牌化”,不仅见于柏林的市场,也普遍显现于奥斯陆、伦敦、北京等各大都市的咖啡店、酒吧、时装屋、浴室等各种载体。
(五)宗教文化由边缘化到焦点化的跨视野迁变
由于全球性移民的不断增长和中产阶级精神追求、公民社会运动的不断加剧,城市中愈来愈出现“神的回归”这一现象。新的宗教实践活动也在新的建筑物与城市空间上寻求表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伊斯兰宗教场所的改头换面。长时间以来,被歧视的欧洲穆斯林居住于城市的边缘区域,而清真寺一般也都由废弃的老工厂改建而来。但是,年轻一代穆斯林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他们一方面要表达被认可的诉求,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强调自身宗教的“自我性”,因而要求新建庄严的伊斯兰清真寺,并且以此攻占市中心,试图与基督教教堂、犹太教会所一起分享城市市容。这种“宗教文化由边缘化到焦点化的跨视野迁变”其实也是一种积极融合政策的体现,但是却很容易导致纷争,因为“有些城市居民尤其把这些如今无可争议存在的新清真寺看作是一种危险‘平行社会’的标志。”*Wolfang Kaschuba, “Offene Städte!’”, in Nils Grosch and Sabine Zinn-Thomas, Sabine (eds.), Fremdheit-Migration-Musik.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Essays für Max Matter, Münster: Waxman, 2010, p.18.可以说,对于土著的欧洲基督徒们来说,所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城市属于谁?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起全体公民表决,最终否决了在市中心建造清真寺的提议,其间耐人寻味的是一副广告张贴画,清真寺的塔尖竟被描绘成炮弹般的危险形状。这是有意推动的新式文化迁变导致文化冲突的一个典例。
(六)生活环境和生活风尚的一揽子跨空间迁变
所谓“生活环境和生活风尚的一揽子跨空间迁变”是卡舒巴所浓墨重彩阐述的,对于欧洲、德国而言,目前主要指的是城市空间的“地中海化”,也就是“通过文化的迁变、拼贴,在市中心产生一个由阳光、沙滩和海洋所构建的城市绿洲的意象。”*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25.这个点子源于巴黎,始于欲把塞纳河畔妆点成地中海沿岸的意愿,后来则普及到全欧洲,却并不再始终依水而建,甚至就设于火车道的旁侧。所谓的一揽子迁变,主要涵盖三个方面:首先,所迁移的是意大利地中海区域的自然环境,如沙滩、棕榈树、意大利式硬陶盆中所种植的夹竹桃等;其次,是诸如“地中海式”的露天咖啡屋、啤酒公园、购物街等社会活动场所的模拟;最后,自然还有同躺椅、太阳镜、匹萨、意式浓缩咖啡等相挂钩的生活风尚的效仿。由此而形成的景象,正如卡舒巴所描述的:“每年春季,欧洲的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要经历一番美化,即是市区的棕榈化和沙滩化。成千上万的盆栽棕榈树、躺椅、太阳镜出现于露天环境,为的上演城市的‘海滨风情’。”*Wolfang Kaschuba, “Vom Wissen der Städte: Urbane Räume als Labore der Zivilgesellschaft”, in Wolfgang Kaschuba, Dominik Kleinen and Cornelia Kühn (eds.), Berliner Blätter-Ethnographische und ethnologische Beiträge, Berlin: Panama, 2015, p.21.由此而形成的地中海化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迁移之后有所变形:可以说,地中海沿岸的沙滩生活模式迁移到欧洲都市中心后变得细致化、多样了,比如正宗的意大利躺椅就可能为廉价的宜家轻椅、热带木椅或者波罗的海海滩蓬椅等各种变体所取代。
2.意象、效果的产生主要不是由于环境,而是基于参与者将都市“地中海化”的意愿以及一种游戏般的、自嘲式的、反思性的态度:事实上,露天咖啡吧和沙滩酒吧成为后福特主义享受群体的集聚地,他们坐在躺椅上,喝着卡布奇诺和开辟林娜鸡尾酒,就为了要程式化的表示:这很休闲、很酷!
3.此类的城市场所营造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和景观,也明显改变了市民的心性和身份认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德国人还是不会躺在户外吃喝玩乐的,否则就是对公众原则和伦理道德的严重挑战。然而,今天一切已经变得不同,“沙滩浪荡子”的形象已经是属于城市社会和文化的主流,
4.这是公共空间的私人化:所谓的“地中海沙滩”实际上成为居家阳台,是城市公共空间在美学和功能上的私人化。参与者们把城市当做自己的后花园,而且试图发掘它的美好的一面。
5.商业性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占有城市公共空间、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核心模块是消费,文化产业愈来愈成为最大的经济产业。像鸡尾酒、太阳镜、躺椅等等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价格不菲。地中海化于是逐渐衍变成为一种“对内旅游业”。
6.地中海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确开拓了城市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与实践活动,比如音乐、艺术、青年文化、业余生活文化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从经济、文化上缩窄了城市空间,因为它往往局限于异域的高端情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与流行青年文化,这自然就将很多普通人排除在外。另外一点负面效应在于,由于这种对内旅游业的兴旺,导致对外旅游业受到城市土著们的排挤与排斥。
(七)为了“文化化”而实施的全方位文化迁变
早在上世纪中叶,人们就已经开始抱怨城市生活的“荒芜”,城市的吸引力也越来越下降,都市中的有识之士不禁发出了“不要离开我们”的呼声,纽约市甚至专门发布了印有“I love New York!”口号的T恤。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作出了反应,正如卡舒巴所指出的:“所以,在1960年代城市就开始了系统的文化化。推动的力量是‘自上’的城市政策以及‘自下’的公民倡议。”*Wolfgang Kaschuba, “Kampfzone Stadtmitte: Wem gehört die City?”, in Johann Jessen (eds.), Altstadt für Alle? Urbanität als Zumutung. Esslingen: Zeitschrift Forum Stadt, 2014, p.364.于是,逐渐地,在都市中实施了一系列由上而下的城市文化振兴或者说“文化化”计划,包括资助各种文化项目、文化设施、文物古迹,举办种种文化活动,如音乐会、戏剧、文学丛刊、狂欢游行、大型派对、电影节、乃至富有特色的大型商业活动,等等。这样一来,对内而言,城市的魅力又逐步焕发,凝聚力得到加强;对外则是促进了旅游业的兴盛,推动了城市的国际性与品牌化。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组织活动囊括了种种形态的文化迁变,跨时间、跨空间、跨载体、跨形态等等,不一而足,是全方位的。
五、新式文化迁变的效应:促成新的共同体结成形式
在卡舒巴看来,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共同体定义可以适用于分析后现代城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与活动:“共同体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参与者(在情感或者传统上)主观感觉到归属在一起。”*Wolfgang Kaschuba, “Urbane Kulturtransfers: Globale Stile, mediale Bühnen, lokale Räume”, in Eszter B. Gantner and Péter Varga (eds.), Transfer-Interdisziplinär! Akteure, Topographien und Praxen des Wissenstransfers.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13, p.232.
基于种种的新式文化迁变,那么,相应地,在城市的沙滩上、休闲街边、露天咖啡厅里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组织活动中就不断地结成有新的群体或者说共同体,诸如音乐节的大型人群、类派对的游行人群、网约活动参与者等等。概括言之:新式文化迁变促成了共同体结成的新形式。这类“经历共同体”的主题、结构都丰富多样,具有非常自由的可塑性。其成员也往往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出生年代,反映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与宽容性。
根据韦伯的定义,共同体的结成其实牵涉到一个归属策略的问题。而由于新式文化迁变是源自“人为有意推动”,所以其中的集体关系、共同体的结成不再是自然成长,而是被人们有意的找寻和选择。可以说,种种新式迁变的现代文化活动是在归属策略上的一种宽泛供给,作为“我们的组织”,它们别具魅力而又能灵活适应后现代生活情境,这是因为:第一,其中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复合的,乃至允许彼此矛盾的身份认同结合在一起,比如一个人既可以是汽车发烧友、又可以是生态保护者。第二,这样的社会组织、活动具有一个很宽的弹性幅度,既可以是开放的公共活动,也可以是独特性、排他性极强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集体。第三,其美学与情感主要通过各种仪式与媒介而加以传达,比如礼仪、仪态、姿势、图片等等,所有人都可以轻易“看得见、摸得着”。第四,其空间维度特别显眼,大多展示于如大型广场的特定场所,因而彰显着城市所独有的特色。第五,其趋势是公共空间的私人化,或者说个人风尚的公共演绎。第六,这类活动的主题、模式、美学、风尚等等都是可以继续再进行迁变的,具有跨文化与行为主义的特点。
六、结 语
文化的外向性或者说开放性、文化的迁移和变形是城市文化实践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因为城市生活世界是“共享空间”(shared spaces)。常规文化迁变和种种新式文化迁变都是城市社会“文化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新式文化迁变以其可塑性和开放性能够让区域融汇入全球性的进程之中。城市空间因而成为“文化的实验室”,各种有关身份认同的构想、归属策略都可以在这里加以探索。可以说,行为者在城市里演绎着自己,同时也演绎着城市,而且越来越出现如“同龄人组”之类专门的行为者核心。另外,文化迁变固然可以帮助找到人群之间的共同点,但也会导致种种或大或小的种种对抗,如本地人对抗外来户、年轻人对抗其他年代人群、精英对抗大众、士绅化对抗街区活动、夜晚宁静对抗夜晚派对,等等。
笔者以为,同生物界中的基因遗传一样,人类社会中的文化遗传也存在着变异,而且是常态。生物界中的迁徙会导致基因突变、物种杂交,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人类社会的移民也会导向文化迁变与文化杂交,人们借之以实现个体、集体的重新定位与身份认同。转基因是现代生命科学的热门领域,而对于现代都市生活来说,人们有意推动、实施的种种新式文化迁变可谓“文化的转基因”。
全球化趋势与信息技术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文化迁变的蓬勃。相比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来说,我国的城市发展以及民俗学界对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相对有所滞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借鉴西方的经验、成果与教训,注重探析文化传承中的“变相”,顺应、引导城市生活中文化迁变的趋向,实现城市社会的移风易俗与安定和谐,满足政治利益、经济发展和“文化化”的种种诉求,无疑是中国民俗学者的新使命。
包汉毅,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山东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