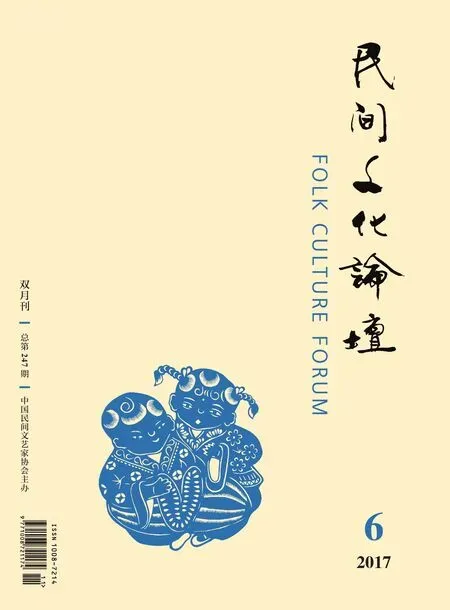朝向日常生活的妙峰山研究:二十年来妙峰山庙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7-01-28李华伟
李华伟
朝向日常生活的妙峰山研究:二十年来妙峰山庙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李华伟
新时期的妙峰山研究,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经历了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到关注民间信仰组织的变化,实现了从集体叙事到个体叙事的研究范式变迁,呈现了从山上到山下、从集中于神圣时空到关注日常生活时空的视角转换。某种意义上,妙峰山研究是当下各种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竞技场,通过对妙峰山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可以为北京宗教研究和民间信仰研究提供思想的源泉,甚至可为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反思性的理论框架与新的资源。
妙峰山;碧霞元君;国家与社会;集体叙事;个体叙事;宗教学理论
致力于妙峰山研究的吴效群曾概括说百年妙峰山研究“并没有显现出一条清晰可鉴的方法论线索”①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不过,在该断言发表前后,妙峰山研究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可以说,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妙峰山研究经历了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到关注民间信仰组织的变化,实现了从集体叙事到个体叙事的研究范式变迁,呈现了从山上到山下、从集中于神圣时空到关注日常生活时空的视角转换。本文希望通过对近二十年国内外妙峰山研究的梳理,为民间信仰研究和宗教学理论提供反思性的新见解。
一、引言:眼光向下与发现民间——被纳入研究视野的妙峰山及其早期成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对妙峰山的研究,我们必须回溯历史,了解民国时期由北京大学国学门顾颉刚为代表的团队对妙峰山考察的意义与影响。
在“到民间去”的呼召下②顾颉刚:《妙峰山》,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6页。,冒着被指责为“迷信”张目的危险,顾颉刚等人对妙峰山进行了调查,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不仅如此,顾颉刚认为妙峰山的香会是“民众信仰力和组织力的表现”,因此,号召大家对圣山和朝顶进香的事宜进行研究。在顾颉刚眼中,这些活动、精神与民族救亡紧密相关。他说:“要想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的,对于这种事实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都必须先了解了才可以走第二步呵!”③顾颉刚:《妙峰山•自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页。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仍以传统方法为主,重视归纳及考证。
北京大学国学门诸位同仁尤其是“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对妙峰山的开创性研究,被民俗学界赋予了非凡的意义,被认为“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④吕微:《民国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刘锡诚:《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第31页。,妙峰山也被称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⑤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此后的妙峰山研究,无论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方法,无论直接沿着顾颉刚的路径,还是试图超越甚至背离顾颉刚的路径,都或隐或显受到顾颉刚等人的影响。顾颉刚等民国同仁的研究不仅影响到学界对妙峰山的认知,也影响到民间香会/花会团体乃至妙峰山管理处、政界对妙峰山及香会/花会的认知,这些认知又反过来影响着调查者与研究者,由是循环往复夹杂在一起,使妙峰山成为历史与现实相交织、众说纷纭的一座圣山与取之不尽的研究对象。
民国时期对妙峰山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其意义在于将妙峰山庙会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自此以后,庙会及民众信仰逐步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顾颉刚等人的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盛烈的余影”,可供我们作重观研究。
由于顾颉刚等人在历史学界、民俗学界的盛名,其妙峰山研究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妙峰山成为1990年代至今中外学界一直关注的研究对象。
二、新时期对妙峰山庙会历史的对立解读:一致性(“communitas”)VS差异性
1.建构民间社会的“紫禁城”:吴效群寻求一致性(“communitas”) 的努力
作为首位以妙峰山庙会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博士研究生,吴效群自1996年开始对妙峰山的调查研究。1998年博士论文完成后,吴效群仍钟情于妙峰山,集中精力打磨研究,8年后出版了专著《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①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吴效群致力于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对妙峰山历史进行复原与解读,并对民间花会在当代北京的复兴及其与妙峰山庙会重建、发展演变的关系作了探析。
吴效群对妙峰山历史解读的突出的贡献在于其对妙峰山行香走会象征意义的解读,他指出妙峰山行香走会建构了民间社会“象征的紫禁城”。吴效群以《走进象征的紫禁城》作为其妙峰山民间文化田野考察一书的大标题,并打算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命名为《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紫禁城”》②在正式出版专著时,吴效群采纳了刘锡诚和高丙中的建议将书名做了改动,最后以《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为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参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此外,吴效群还发表数文探讨此问题,如1998年的《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庙会》③吴效群:《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庙会》,《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第46—52页。《妙峰山:民间社会紫禁城的建立》④吴效群:《妙峰山:民间社会紫禁城的建立》,吕微,《民间叙事的多样性:民间文化论坛》,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81—402页。《建构象征的紫禁城》⑤吴效群:《建构象征的“紫禁城”——近代北京民间香会妙峰山行香走会主题之一》,《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第27—42页。《妙峰山庙会:中国封建帝国首都的狂欢节》⑥吴效群:《妙峰山庙会:中国封建帝国首都的狂欢节》,《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55—61页。等。可以说,在吴效群的理解中,妙峰山在历史上就是北京民间社会的“象征的紫禁城”。
在对隋少甫的访谈中,吴效群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妙峰山行香走会的规则是在演绎汉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模仿王朝政府的政治制度模式”“庙会活动时民众向他们观念中的女皇进贡、祈祷,以获得她的赐福。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关系模式”①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28页。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通过对包括隋少甫在内的多位会头的访问,并结合历史资料,吴效群对“(妙峰山)行香走会所遵循的象征意义(隋少甫使用的是‘道理’一词)和为了达致象征意义所遵循的规则(会规)”②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进行了解读和复原。吴效群从张淑媛等《金銮殿朝夕》中取图一幅,形象地指出,十三档武会组成了庙宇图,具有象征意义,指出:“在妙峰山上,‘鼓幡齐动十三档’……具有神圣意义的宗教象征;各香会之间的关系也超越了世俗的意义,它们共同形成了碧霞元君的神圣性,成为表现碧霞元君信仰神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③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另外,吴效群认为,作为文会的茶棚则是碧霞元君的行宫,其内部摆设及二十八宿旗、四值功曹旗等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蕴含着深刻的哲学观念。
吴效群认为,妙峰山庙会是一场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说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在朝顶进香过程中,民众追求“平等”“被社会承认和接纳”,一方面表达着宗教情感,“一方面体验着在虚拟的‘紫禁城’里的荣耀和快乐”,他们建构了自己的紫禁城:“在这里没有等级森严,它充满了平等和友爱,大家各司其职,各明其份。在民众的‘紫禁城’里,只有奉献,没有索取。”④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127—128页。在庙会期间,妙峰山成为迥异于日常的“社会戏剧”剧场,香会组织的奉献、互道虔诚等,“使人们的情绪在生命激情洋溢的春季节日里互相感染,共同创造并进入communitas的虚幻境界,人们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琐碎和狭隘,建立起一座民间社会的‘紫禁城’。在充满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北京,民众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建立的‘紫禁城’是阶级对立和文化压迫在民间文化中的必然表现。民众在其中表达了平等、互助、友爱的社会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阶级间的冲突和对立”⑤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寻求差异性:韩书瑞对妙峰山何以成为圣地的研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韩书瑞教授⑥韩书瑞自1980年代即关注妙峰山,1986年首次就此议题发表论文,并于1987年和1988年5月在阎崇年和李世瑜的陪同下赴妙峰山进行调查([美]韩书瑞:《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韩书瑞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运用、理解及对历史的诠释远远超出同期的国内学人。的“The Peking Pilgrimage to Miao-feng Shan: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Sacred Site”⑦Susan Naquin.1992.“The Peking Pilgrimage to Miao-feng Shan: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Sacred Site”,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 Edit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Oxford, England,1992, P333-377.一文在学界影响颇为深远。该文的中文版由妙峰山研究专家吴效群翻译后发表在2003年的《民俗研究》⑧韩书瑞:《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周岩福、吴效群译,《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之后,迅速受到国内妙峰山研究者的关注。此外,该文的中文版也收录在2006年出版的韦思谛主编的《中国大众宗教》中,不过两个译文稍有差异。
韩书瑞一文关注的是参与朝圣的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朝圣者的身份、组织方式及其对到妙峰山朝圣的看法,该文比较重视香会之间的差异、香会组织内部的差异、个体的差异。韦斯谛指出,其实这是从事中国宗教研究的西方学者一致的看法,即“强调在从事同样仪式活动的人中其看法和动机不一致,即使像进香这样的活动也从来不能掩盖他们的争议”,并未能达到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说的一致性(“communitas”)那样的凝聚力。①[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序言》,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Unruly Gods :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edited by Meir Shahar and Robert P. Weller.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可以说,韩书瑞该文与吴效群建构民间社会的“紫禁城”的说法颇为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构成了对立的解读。中西学者颇为不同的解读,对于我们丰富对妙峰山的认知与理解颇有助益。如果深入挖掘,我们可以发现,两人解读妙峰山背后的理论框架与学术传统不同。继承了顾颉刚等人“到民间去”“眼光向下”的视角、试图从民众中寻求民族新鲜血液的动机,吴效群的解读将之推进一步,发现的是民间香会组织与民间社会的自治,以及民间在宗教节日这一神圣时空中的平等、互助与友爱。韩书瑞做出如此不同的解读,或许与其对碑文和西方文献的有效利用有关,也与西方汉学界尝试超越弗里德曼关于“存在一个中国宗教”②Maurice Freedman,“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Arthur P. Wol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4. [美]弗里德曼:《论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李华伟译,金泽、李华伟主编:《宗教社会学》(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的学术传统有关。
三、朝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对妙峰山重建后香会/花会组织研究的视角转换
自旅游开发成为妙峰山新时期的主题以来,妙峰山乡(镇)政府、景区管理处、京西旅游上市公司围绕妙峰山的旅游开发,不断组织各种活动扩大妙峰山的影响,而学界也重新关注了妙峰山,于是对妙峰山的研究也在各方力量的互动中得以展开。其明显的标志性事件是1995年于妙峰山庙会期间在妙峰山所在的门头沟区召开的首届“中国民俗论坛”,自此以后,关于妙峰山的研究论著大量问世,其研究范式也多有变化,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数位学者为典型代表,如吴效群、王晓莉、岳永逸、张青仁等。
此外,日本学者樱井龙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贺学君研究员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数位研究生于2004年—2005年庙会期间对妙峰山的香会组织进行了全程、集中调查,并汇编成书,该书对香会进香中所带实物作了图片资料汇编,对香会会期、门旗、手旗进行拍照存录,对个别香会会头进行了深入访谈,对香会碑文进行了拍照与辑录,对妙峰山管理处进行了深入访谈,对花会联谊会情况进行了记录与观察,对妙峰山为申请非遗所作的安排与举办的活动作了忠实的记录。该成果原始资料之翔实目前无人能及,但研究与分析的论文不多,这显示了日本汉学研究的特色。该书留下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与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观察与思考,可作为承前启后回访研究的重要参照。③樱井龙彦、贺学君主编:《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成果报告书(课题号码16652004).关于妙峰山庙会的民众信仰组织(香会)及其活动的基础研究》,2006年。
近年来,在妙峰山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及其本科教学实验团队。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自2005年以来带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对妙峰山庙会及香会组织进行调查,整合数届学生之力分别对几十个香会及其活动的村落进行调查,其调查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也为我们呈现了日常生活视野下的这些民间组织的常态与非常态生活,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妙峰山庙会与民间组织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有关妙峰山的地方文献的辑录与汇编在2004年出版①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中心编:《妙峰山地区历史文献专题资料汇编》,2004年;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录》,北京:中国书店,2004年。,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对妙峰山重建后香会/花会组织变迁的研究,发生了从总体或类型建构到个体香会/花会的研究。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无一个截然分割的界限。大致说来,早期的研究者文中所出现的单个香会是作为某类香会的代表而出现的,对单个香会的历史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样态并无详细的调查与分析,后期的研究者则把单个的香会作为其本身来对待,而非作为某种类型的代表。
1.对妙峰山重建后香会/花会组织总体的研究
吴效群对妙峰山重建过程及重建后香会组织的研究值得关注。作为首位对妙峰山现状进行重观研究的人员,又得益于与北京民间花会界的良好关系,加之对妙峰山的历史特别熟悉,吴效群对妙峰山重建后民间花会的变化之感受也颇为强烈。吴效群指出,香会/花会发生了三次转型,大体经历了追求行善和社会声望(原初)——邀取皇宠(晚清)——利益(当代)的三个阶段②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2—343页。。吴效群发现,悖谬的是,正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当代花会,却“最好地保持了‘传统’”“是碧霞元君信仰最忠实的捍卫者”,正是因着它们,妙峰山的“传统”才能保存下来。可以看出,吴效群正是从香会/花会总体来分析的。此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李海荣分析了香会组织在现代的复兴及其影响因素,并将现代香会组织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传统型(恪守信仰)、盈利型(审时度势)、社区型(文化自助)③李海荣:《北京妙峰山香会组织变迁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这也是从总体上进行的分析与分类。
2.个体的香会与日常生活中的妙峰山研究
对香会/花会组织个体的研究,在2004—2005年樱井龙彦和贺学君团队的研究中已有所呈现,并对数个香会/花会进行了深入的跟踪采访,但对其在日常生活中样态的关注仍不够深入,参与其日常活动亦较少④樱井龙彦、贺学君主编:《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成果报告书(课题号码16652004).关于妙峰山庙会的民众信仰组织(香会)及其活动的基础研究》,2006年。。作为公开的成果呈现出来的对香会个体的研究,则是由中国农业大学的苗大雷和王敏以及孙庆忠教授率领的本科生团队完成的。不过,明确提出“个体的香会”这一概念的则是时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张青仁⑤张青仁:《个体的香会——近百年来北京城“井”字里外的社会、关系与信仰》,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该论文后来以《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为题正式出版,但正式出版之后的书名较为平实,不如博士论文题目《个体的香会》那样具有学术冲击力。参见张青仁:《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
苗大雷以古城村秉心圣会为例,从民间组织的角度对妙峰山香会进行了个案研究⑥苗大雷:《民间组织荫蔽下的村庄意识——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研究》,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主编:《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1—247页。。该文从民间组织与村庄关系入手,“试图与吴效群主要关注香会行香走会理念之研究形成互补之势,弥补后者无法解释大量香会在当下复兴的不足”①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王敏是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西北旺高跷秧歌会这一皇会在当代社区生活中传承、重整及日常样态扎实的微观研究,王敏探讨了西北旺高跷秧歌与村落社区公共生活的关系,并指出,这一组织在建构民间与官方的“第三领域”之间发挥着特殊的功能②王敏:《花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西北旺高跷秧歌会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自2005年开始,孙庆忠每年都率团带队到妙峰山庙会进行调查。在积累多年之后,孙庆忠主编出版了三本研究妙峰山的著作。《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传承与处境》探讨了在村落与社区中香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和生存处境③孙庆忠主编:《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传承与处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诚为实现从山上到山下视角转换的重要代表作。《妙峰山:香会志与人生史》④孙庆忠主编:《妙峰山:香会志与人生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则通过口述史材料,为诸香会与会首留下了史志记录。
张青仁的博士论文则以《个体的香会——近百年来北京城“井”字里外的社会、关系与信仰》⑤张青仁:《个体的香会——近百年来北京城“井”字里外的社会、关系与信仰》,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为名,对香会组织的诚起、香会的维系、行香走会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将仪式空间中香会的交往与日常人情的运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用互惠的视角解读朝顶进香,某种意义上是对以往研究的解构。
某种意义上,对重建后这些进香组织的研究,发生了从山上到山下的视角转换,也逐步走向了朝向日常生活的香会/花会研究。这一视角是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深化与补充,转换的实现几乎是不约而同完成的,这与整个社会科学的进展与转型有关。在实现这一转换的努力中,樱井龙彦、贺学君团队⑥樱井龙彦、贺学君:《关于妙峰山庙会的民众信仰组织(香会)及其活动的基础研究》,2006年。,岳永逸团队⑦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孙庆忠团队⑧孙庆忠主编:《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传承与处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孙庆忠主编:《妙峰山:香会志与人生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以及张青仁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反思:范式的建构与解构
1.“民间社会的紫禁城”: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妙峰山研究
如前所述,把妙峰山作为“民间社会的紫禁城”,是吴效群对妙峰山历史研究的主要发现与贡献。自此以后,国内关于妙峰山的研究多关注其现状,而对其历史的研究则颇为零散、不成体系。
“民间社会的紫禁城”这一说法,是结合妙峰山的历史与口述史材料,采用维克多•特纳与巴赫金的理论,并结合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理解,对妙峰山香会的分类及其行香走会的象征意义的解读。通过对包括隋少甫在内的民间花会权威人士的访谈,吴效群对行香走会的规则进行了详细描述与展示,对打知、参驾、盘道、会规⑨当然,吴效群在研究中体悟到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话条子”,会规就是长期形成的一种默契。参吴效群,2006年,第121页。等的描述成为标准的版本。这一解读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描述,被认为是应然的事实,被当作妙峰山历史上曾经被完美地遵守过的整套规则。于是,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后来的研究者到妙峰山上调查时,总是带着今不如昔的感觉,来感叹妙峰山香会仪式的没落与礼仪的散乱。妙峰山管理处也将吴效群的这一研究成果当作香会应该继承的传统而有意在每年的花会联谊会上对新来的会提出进香的规范性礼仪①李华伟:《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妙峰山庙会之影响》,《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6期。。由此看来,这一研究已被各界接受成为不容质疑的传统。于是后来的研究者以此为标准,发现了当今香会/花会进香仪式的杂乱,并感叹民俗在现代化处境中之衰落。而也有部分香会除了请权威指导外,还直接找书来看,并将之化为自己的会规。
问题在于,由于1937年平津沦陷,朝顶进香基本停止,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允许行香走会,这些规矩如何能够完整地传递下来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一过程属于传统在当下的再造,并非传统的原样恢复。以花会权威隋少甫先生为例,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按照吴效群的记述和妙峰山上隋少甫碑文的记载,隋少甫出生于1920年,曾拜奎世峰为师,于18岁时(1939年)获得“万里云程踏车老会”的会腕,并曾于1942年带一帮青年朝顶进香,此后直到1990年再也未曾上过妙峰山。而且据记载,隋少甫1942年上山时,武会只有他们一家,“根本看不到往日的热闹”。而且据隋少甫自述,“小时候,父亲酷爱走会,知道的走会知识特别多,我知道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他告诉我的。很多事情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②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也就是说,隋少甫口述史的内容大部分并非其亲身经历而是其父亲的经历,而且,这些资料没有时间性③吴效群对此这一问题有着明确的意识,参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2页。。静止的没有时间感的历史叠加成了理想型的历史图像。由此没有明确时间界限的资料与历史记忆建构而成的传统成为一个凝固的存在,被当作真实的历史,不仅难以呈现这些传统与历史复杂的建构过程与历史的真实性,也遮蔽了对真实的动态历史的探讨。当然,我们并非要以此来质疑行香走会中这些规则存在的真实性,也并非质疑学者的研究,而是以此提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问题,期望引起讨论。这也是传统断裂之后,研究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者面临的普遍问题。
无论如何,关于行香走会历史的建构成为后来者认识妙峰山历史、观察当下的一种尺度。这一建构的认知框架影响深远,让包括笔者在内的后来的研究者一度以全知的上帝的视角来透视当下的香会组织,以建构的礼仪历史作为尺子来衡量当下的妙峰山,带着怀旧的情绪与民间文化守夜人的态度来观察当今的妙峰山。
2.历史的连续与断裂:“盛烈的余影”与历史的重构
由于花会权威口述史资料的时间性不明晰,而很多香会都将自己的成立时间设定在康乾时期④在调查香会的成立时期时,吴效群认为,“对康乾妙峰山香火的认识或许带有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因此容易诱导研究者将妙峰山四百年的历史视为一个一直繁荣的历史,将妙峰山鼎盛时期的样态视为其不变的常态。
加之,为了开发旅游,妙峰山网站及旅游宣传册将1985年以来重建的建筑宣称为明清时期的建筑,并将庙会期间的活动宣传为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原汁原味,更给研究者和游客带来事实性的误导。
对涉猎妙峰山研究的人员来说,要在短期内弄清楚妙峰山的历史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妙峰山明清时期的历史姑且不论,单就晚晴民国时期的妙峰山而言,也绝非一直鼎盛如1880年代。据多位学者的研究,1900年5月下旬,大批香客因突降的暴风雪而被冻毙。同年义和团攻入北京使馆区,北京被外国军队占领。直到1917年以后,妙峰山进香才开始恢复①金勋:《妙峰山志序》;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韩书瑞:《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235页。。1920年顾颉刚等人游西山走到妙峰山,看到妙峰山茶棚才引起他的关注②顾颉刚:《妙峰山琐记•序》,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到顾颉刚等人首次调查妙峰山的次年(即1926年),由于直奉战争,烧香的人数很少,因此在《妙峰山》出版时(1928年),顾颉刚将1925年看到的景象称为“盛烈的余影”③顾颉刚在《妙峰山》一书的序里说:“我们这一年去得真巧!次年的进香期,正是奉军初打下北京,人民极恐慌的时候,听说烧香的只剩数十人了。这两年中,北方人民宛转于军阀的铁蹄之下,哪有展眉的日子。今年虽把军阀驱除了,但因迁都之故,报纸上常说北平快成一座废城了,无限的失业者把这座大城点缀得更荒凉了。妙峰山娘娘之神,从前托了国都之福,受了无穷的香火;自今以往,怕要忍着馁吧?明年我北返,当再去看一下。如果山上殿宇竟衰落得成了一座枯庙,则这本《妙峰山》真是可以宝贵了:我们这件工作总算抢到了一些进香的事实,保存了这二百数十年来的盛烈的余影! ”。1929年第二次进香调查时,顾颉刚感叹道:“进香的人萧条得很,远比不上那一年。大约这种风俗,一因生计的艰难,再因民智的开通,快要消灭了。我们赶紧还是起来注意这垂尽的余焰罢!”④顾颉刚:《妙峰山琐记•序》,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
由此可见,妙峰山香会会首梦想中的妙峰山朝顶进香的盛况,只能是历史的“盛烈的余影”。完美的朝顶进香景象也许并非如描述的那样规整、协调。
3.对当下香会神圣性及其信仰组织身份的解构
从香会个体的视野、从日常生活视野中对当今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组织进行研究时,如果我们不以虚拟的、不曾真实出现于妙峰山上的理想型的礼仪作为标杆来衡量当今的香会的话,如果我们将当今的香会之存在样态与变迁当作其常态,对其频繁的重整、贺会甚至诚起当作历史的常态⑤[美]韩书瑞:《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再辅以历史的材料,那么,我们也许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进一步,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这些被称为香会的会,只是个“会”,并不是香会,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组织。这一假设和推论,可以得到历史文献和现实经验材料的证明。在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组织的自称与他称中均很少出现“香会”这一字眼,常见的是三种说法:圣会、老会、皇会。
这些文会与武会⑥韩书瑞指出,有可能这种文会和武会的分类是在1880年代受到皇室资助时形成的,因为其反映了帝王的象征意义。[美]韩书瑞:《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虽然到妙峰山朝顶进香,但文会多为行业组织(也有自己的行业神),而武会有各自的祖师爷,所供奉的并不是碧霞元君,问题是这些文会与武会的祖师爷与碧霞元君之间的关系,我们仍所知不详。另外,从武会的缘起来说,其作为八旗子弟的“子弟玩意儿”之娱乐性质远远超出其信仰团体的性质。调查中,我们也听西北旺幼童少林五虎棍会的负责人讲起,在历史上,他们会里的成员就是给人看家护院的。由此可见,学者的认知也许离事物的真实面目有较大的差距。随着对各香会的个案调查、对香会会首的访谈、对香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生活的调查,如对西北旺高跷秧歌的研究①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立阳:《山上山下:妙峰山庙会的传承与变异》,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王敏:《花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西北旺高跷秧歌会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对孙忠喜小车会的研究②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张青仁:《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红寺地秧歌的研究③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华伟:《多方建构的妙峰山》,樱井龙彦、贺学君:《关于妙峰山庙会的民众信仰组织(香会)及其活动的基础研究》,2006年;张青仁:《个体的香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对中幡圣会会首黄荣贵的访谈④张婷:《2008年妙峰山庙会调查报告》,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206—228页;张青仁:《个体的香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9—61页。以及对中幡圣会收徒的不同说法⑤张婷:《2008年妙峰山庙会调查报告》,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227页。张青仁:《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84页。,无形中可形成跟踪调查,这些材料可互为印证或补充,对于帮助我们厘清关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极有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民间团体成立时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进香,日常也不以进香作为主要事务,而只是带有信仰色彩的团体,在庙会期间朝顶进香。因此,也许香会这一称呼是受了顾颉刚的影响,而被后世的学者和民间团体、妙峰山管理处接受而流行起来。
张青仁的博士论文以《个体的香会——近百年来北京城“井”字里外的社会、关系与信仰》⑥张青仁:《个体的香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为名,从题目中几乎看不出其研究与妙峰山的关联,但这些香会/花会都是研究妙峰山的学者所熟悉的,也即从表面上看不出来该文与妙峰山研究的关系,但实际上该文是对以往妙峰山研究的颠覆。无论该文对香会组织的诚起、香会的维系的研究,还是对行香走会的研究,都关注香会的个体差异,不仅回到日常生活,而且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恩怨延伸至妙峰山庙会之中进行分析,将对仪式空间中香会交往的分析与日常人情的运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不啻是对以往研究的解构。
同样的事例放在不同的解释框架下,不仅会有颇为不同的解读方式,甚至能得出截然相反的诠释结果。比如,吴效群在调研中发现,有两个会在城里玩会的时候结下梁子,老会头想“别”对方可“别”不住,在妙峰山进香的时候遇到一起,老会头就把对方别在妙峰山上,之后由众香会会头调解并回城摆席道歉才算过去⑦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这一事例被作为民众将妙峰山建构为“民间社会的紫禁城”的例证之一。而类似的在仪式空间发生的“挑眼”行为,在张青仁那里则被解读为是人情关系在仪式空间的反映,是茶会借着仪式空间让不懂规矩的会首丢人给自己的朋友出气,因而是“会头之间关系的反映”,与世俗社会的规则、人情并无两样⑧张青仁:《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2—150页。。
对当下香会会首的访谈及对当下香会的研究表明,香会在当下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型。自吴效群开始,诸位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一转型的样态,但对这些香会(以下专指武会)到底转型到何种地步却缺少明确的论述。这些香会能否被称为妙峰山香会组织,或者是否如妙峰山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陈述的那样,是妙峰山三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代表?当下的香会组织与妙峰山到底是何种关系?根据前面的研究以及我们的调查与阅读,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当下的这些香会组织(甚至历史上也是如此),并不是只到妙峰山朝顶进香,也参加“三山五顶”甚至任何庙会的进香,也参加世俗意味颇浓的人生仪礼和各种庆典。从起源和功能上来说,这些会并不是专属妙峰山的。只是在当下,只有丫髻山和妙峰山开放,而且妙峰山开发更早、交通更便利,更容易受到关注,因此妙峰山庙会期间聚集了不少香会组织。认为这些香会属于妙峰山,只是学者的错觉和视野受限的表现,离事实真相相去甚远。更重要的事实则是,1950—1993年之间,这些组织在妙峰山中断期间仍有活动,参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庆典,服务于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的需要,其信仰成分几乎荡然无存。只是学者将顾颉刚等人的研究进行化约论处理,把这些组织视作纯粹的信仰团体,对其的认知僵固化了,忽视了这些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的样态。
对日常生活中妙峰山的研究能给我们更多启发。张婷通过对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妙峰山庙会的研究发现, “现在,妙峰山之于香会主要已经不再是获取神圣感觉、表达虔诚的所在,只不过是香会一个取得合法性的程式化地点而已,二者的主客关系已经异位,并变得貌合神离。”张婷指出,“‘信仰’在当下只不过是众多的香会传承下来的一个‘由头’,有限地表征着其存在的意义与合法性。”①张婷:《2008年妙峰山庙会调查报告》,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238页。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推出以下两个结论:一、当下的这些民间组织根本就不是信仰组织。即使其会头或成员拥有信仰,信仰成分也极弱,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信仰。二、这些组织在历史上,也并非纯粹的进香组织。进香只是其多重功能之一,从其起源和本质来看这些组织是世俗组织,只是带有信仰色彩而已。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结论,当下的这些民间组织不是信仰组织。至今,多位会首,把自己的会称为“子弟玩意”②李华伟:《同心同德少林圣会车道沟子弟文场会首访谈》,樱井龙彦、贺学君:《关于妙峰山庙会的民众信仰组织(香会)及其活动的基础研究》,2006年。张婷:《2008年妙峰山庙会调查报告》,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并未把会作为民间信仰的团体,可惜会首的这一表述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警觉,大多数人对此信息并不敏感。不过,包括王立阳、李华伟、张婷、张青仁等人在内的《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庙会》团队在内朝向日常生活视角下对这些组织的研究均已表明,这些组织不仅成员复杂,并不以信仰(更别说碧霞元君信仰,有不少会员根本没听说过碧霞元君)作为入会的条件,而且其信仰成分极弱。有研究者发现有组织拉武校学员和北漂艺人入会,拉戏校人员合作③张青仁:《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8、124页。张婷:《2008年妙峰山庙会调查报告》,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另外,“走局表演才是香会存在的普遍状态”④张青仁:《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页。,而研究者往往盯着这些组织在妙峰山庙会期间的活动,以为这是他们的常态。另外,即便这些组织有自己的祖师爷信仰,其信仰也较弱,而且其祖师爷信仰与当下的妙峰山并无联系。只是妙峰山研究者先入为主把这些组织定位为信仰组织,于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信仰的成分(尽管这一信仰还不一定是对碧霞元君的信仰),或者把灵验作为香会诚起的缘由,或者作为惩戒的表现,或者把显圣作为会头转变的标志①张青仁:《个体的香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其实民间信仰属于弥散型的信仰形态,弥散于世俗的组织中,我们只能认为这些组织带有信仰成分,但却不能认为这些世俗的组织是信仰组织。可惜研究者囿于“香会”这一名称,将其视为信仰组织,而未能看清其本质。
第二个推论不仅是根据对当下这些组织的状态而逆推出来的结论,也有历史文献资料可作证据。由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弥散型特征,“社”和“会”既有神圣的成分,更有世俗的成分,圣俗之间的区分并不是特别清晰。
根据以往的研究,到妙峰山朝顶的香会自称“圣会”“老会”或“某会”,但并未自称“香会”。历史上的香会可按照地缘与业缘关系分为三种:行会性质的会;村落的会;合街而起的会。 行会性质的多为座棚,信仰色彩较浓,但也不能称之为香会组织,只是行会自身带有的信仰因素与附属的功能之一。就后二者而言,按照韩书瑞的研究,1797—1882年的18个会的人数平均为204人②韩书瑞:《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根据以往的研究与资料,这一数字这并非香会固定成员的人数,而是参与香会活动或为其捐款助善的人数③根据顾颉刚的调查,这些香会组织多为“依亩捐钱”(顾颉刚:《妙峰山》,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22页),这说明,这些组织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愿组织,因此,从中寻求现代公民社会因素的尝试难以自圆其说。。这些武会组织,很少自称为“香会”,从其起源和本质来看其民间曲艺的成分更浓,只是其中带有信仰色彩。这些组织在历史上,也并非纯粹的进香组织,进香只是其定期的活动和多重功能之一。我们且看《旧京风俗志》(稿本)的记载:
所谓会者,京俗又名高乡会,即南方社火之意也。太平无事,生计充裕,一班社会青年,八旗子弟,职务上之相当工作已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于是互相集聚,而为排会之游戏,如中幡会、狮子会、五虎棍、开路、少林棍、双石头抗子、跨(挎)鼓、什不闲、扛箱,均于是日进香。各会常因细故,而演成凶殴,按此等娱乐,虽无关生计,然若辈视之,直同生命,譬如今日之会,共为数十档,某档在某档之前,某档居某档之后,秩序均需大费踌躇,倘或安排不当,即发生冲突,好勇斗狠,牺牲生命,往往有之。④旧吾:《旧京风俗志(稿本)》,孙景琛、刘恩伯:《北京传统节令风俗和歌舞》,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这一段记载表明这些后来被称为武会的团体在时人眼中并非信仰团体,只是“娱乐”,其“排会”规矩的形成可能也并非基于妙峰山朝顶进香。日常生活与交往中,这些会已形成走会的礼仪规矩,只是朝顶时移至妙峰山这一场域而已。
五、结语:成就、缺憾与未来展望
应当说,新时期对妙峰山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妙峰山研究经历了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公民社会)到关注民间信仰组织本身的变化,实现了从集体叙事到个体叙事的研究范式变迁,呈现了从山上到山下的视角转换。某种意义上,妙峰山研究是当下各种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竞技场。
当然,对妙峰山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大部分民俗学者研究妙峰山历史时,均注重“眼光向下”,只看到基层,缺乏上层视角,缺乏能囊括下层与上层互动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从这些妙峰山研究中看到的只是民间社会的自治与独立自存,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与文化思潮的影响、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对妙峰山的影响似乎并不存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包括,废庙兴学等宗教政策与社会改良运动对妙峰山庙会有无影响?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以及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对妙峰山庙会有何影响?政治双轨制的式微对妙峰山庙会有无影响?等等。此外,意欲在香会组织中发现民间社会自治甚至公民社会的因素这一动机,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割裂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①[加]卜正民、傅尧乐:《国家与社会》,张晓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遮蔽了对妙峰山庙宇非自治一面的探索。因此,此后的研究,或可以结合宗教学、历史学的方法,考证妙峰山庙宇的所有权及管理,并追溯其历代庙祝/方丈的生平,并详考历史上妙峰山庙祝/方丈的遴选机制,其与僧录司、道录司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探索妙峰山庙祝/方丈与香会、香客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将妙峰山的研究引向一个新的阶段,甚至为圣山研究提供典范框架与思路。
对妙峰山的研究,还可以为民间信仰以及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素材与资源。无论是对妙峰山成为圣地历程的考察,对民国时期王三奶奶神格变化的观察,还是从当今妙峰山庙宇格局的变化之中都可以看出民众信仰的一些特征,可以探究民众信仰的常与变及其动力学。对妙峰山兴起与繁荣的研究,还可以发现其与民间教派(无声老母信仰)、与民众流行信仰四大门的关系。碧霞元君作为后起的神灵能够迅速传播,从泰山传播到东岳庙并四处扩散,以民众所谓“老娘娘”的称号流行开来,并在北京逐步建立起三山五顶,并根据各处香火的灵验程度而有所转移,最后使妙峰山娘娘庙夺得各处的香火,成为“金顶”,并在1880年代达到鼎盛,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对妙峰山的研究必然要求研究者将其放在三山五顶的脉络之中,并考察这些朝顶的组织与各个庙会之间的关系,考察大众信仰的基础、特质及其与进香组织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妙峰山的研究关涉到民间信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涉及泰山、东岳庙等名山信仰及朝顶仪式,也涉及对进香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之社会学研究,更关涉到大众信仰及中国人神关系的特质。
对妙峰山的深入研究,可以打破西方的宗教类型学,并对西方关于狂欢与日常、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包括民间信仰组织在内的宗教组织作为公民社会雏形等的理论主张提出反思甚至批判。通过对妙峰山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可以为北京宗教研究和民间信仰研究提供刺激思想的源泉,甚至为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建设提供理论框架与经验材料。
K890
A
1008-7214(2017)06-0079-12
李华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新工程“宗教学理论创新”项目阶段性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岳永逸教授对本文个别字句的表述曾提出过积极的修改建议,特此申谢。
王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