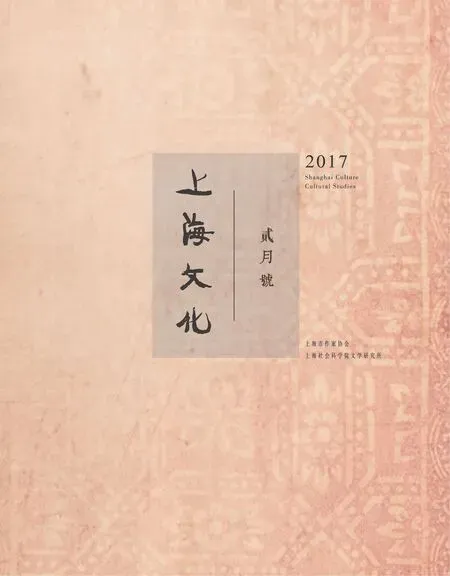信仰批判
2017-01-28颜翔林
颜翔林
学术专题(信仰问题讨论)
信仰批判
颜翔林*
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共同演进过程中,信仰从被个别的想象主体后验地意志设定和情感虚构,架构成为一种虚假而“可爱”的意识形态,进而转化成为先验形态的普遍群体的价值形态和实践行为的绝对标准,从而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运动轨迹,宰制了无数主体的精神活动与生活行为。信仰在赋予生活世界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导致无数的历史悲剧和人生灾难。信仰在逻辑上可以划分为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信仰等,它们尽管在外延上有所差异,但在存在论意义上都具有本质的同一性,都以概念的假定方式达到对主体意志的绝对支配。从功能意义和价值形态上考察,信仰的重构只有选择伦理信仰与审美信仰才符合理性与审美的目的性,也使人类命运转向美好的未来得以可能。
信仰 假定 非理性 逻各斯 批判
信仰(Belief)如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格劳孔篇》中所描述的“洞穴假象”。苏格拉底借与格劳孔的对话,叙述一则虚构的故事,它构成人类认识自我的哲学隐喻。信仰同样是人类认识自我的果实,它发端于文明的前期,成为人类精神的逻各斯中心之一。然而,信仰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主体精神的异化结果,表现为极少数“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是极少数个体依赖于逻辑假定的方式所建构的虚无化理想世界,它以唯美主义的许诺未来和描绘诗意化的世界图景,加之塑造圣明的人格神形象的方式,最终表现为无数群体对极少数个体的绝对服从。在时间性上,信仰一旦确立,它就超越历史和语境实行对芸芸众生的情感宰制,上升为一种非理性的强大势能;在存在论意义上,信仰虽然不属于先验的逻辑范畴,是经验世界或生活世界的后验产物。然而,一旦它获得生成和存在,对之后时间的所有信众就诞生了先验逻辑的意义,具有和先验概念等值的意义。因为后来主体对信仰是不能够进行质疑、提问、反思、否定、批判、重构、超越等任何的理性活动,他们只有在精神世界完全地、绝对地接纳与服从。信仰既成为人类历史文化中最早的图腾对象,也成为一种绝对的精神偶像。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行程中,信仰在赋予生活世界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导致无数的历史悲剧和人生灾难。信仰在逻辑上可以划分为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信仰等,它们尽管在外延上有所差异,但是存在论意义上都具有本质的同一性,都以概念的假定方式达到对主体意志的绝对支配。
一、形而上学之探究
无论是在生活世界还是知识信念中,是面临日常事物还是从事精神文化活动,人们对信仰总是持有不假思索的明证态度,因为信仰在本质上是以时间性上居先主体的想象活动,是极少数的主体以非理性、非逻辑的方式所确立的精神对象,信仰以超越实证和逻辑的绝对权威,先验地隐匿在我们约定俗成的知识谱系之中。
康德对信仰予以理性运思,他区分了意见、知识和信仰:“意见乃其主持一判断在意识上不仅客观的感其不充足即主观的亦感其不充足。若吾人所主持之判断,仅主观的充足,同时以为客观的不充足,此即吾人之所名为信仰者。最后,以一事物为真实云云,在主观客观两方面皆充足时,则为知识。”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64页。显然,在康德的哲学意义上,只有知识符合理性与逻辑的要求,呈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必然性。而信仰则表现为主体设定的意愿而不符合客观的事实,因而它被排斥在纯粹理性的逻辑范畴之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信仰与纯粹识见进行辩证地剖析:“纯粹识见知道信仰是与它自己、与理性和真理,正相反对的东西。在它看来,信仰一般地说是一团迷信、偏见和谬误的大杂烩,同样,对它说来,把握着这种内容的意识又更进一步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谬误王国,在这个王国里,谬误的识见,一方面,就是意识的直接的、天真朴素的、并没有自身反思的一般群众(allgemeine Masse),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包含有与天真朴素性分庭抗礼的自身反思或自我意识这样的环节,这后一种自身反思的环节,作为躲在背后的、为自己而坚持存在下来的识见和恶意,愚弄着那前一种直接的、天真的识见。一般群众于是成了这样一种教士阶层欺骗的牺牲品,这种教士阶层,其所作所为,无非是要满足其妄想永远独霸识见的嫉妒心以及其他私心,并且,它同时还与专制政体一起阴谋活动,狼狈为奸。”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2页。黑格尔辩证地阐释了对信仰与识见的差异与关联,显然,他对于信仰持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与批判。尽管如此,古典哲学家在对信仰批判和解构的同时,都对它采取某些宽容态度并维护其有限的尊严。
与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对信仰持有的辩证理性态度不同,众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尤其是统治者、极权主义者、阴谋家、政客等,当然也包括宗教人士,他们对信仰予以无以复加的溢美赞颂,既视其为救世的良方,也将其作为攫取权力或谋求利益的工具。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与动机,一方面将信仰和“绝对真理”进行逻辑等同,放弃任何的理性沉思,拒绝任何存在者对于信仰的存疑与否定、提问和批判等精神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对信仰的接受活动采取“绝对命令”的话语霸权,只灌输信仰的结果而不允许任何接受者追问信仰的起源及其缘由。他们将不同的信仰混为一谈,悬置所有对信仰有可能招致危机的逻辑命题,只守护唯一性和同一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命题:信仰即最高的精神本体。再一方面,他们设定信仰具有一种超越历史与超越现实的共时性(Synchrong)绝对本质,提升信仰为永恒的价值准则和不容任何更改的实践规范,如此顺理成章,信仰也演变为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审美标准之一。显然,在信仰这一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上,充满了传统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暴力和话语霸权,充满了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和理论领域的独断论。因此,毫无夸饰地说,信仰在酿造了人类的知识悲剧的同时,更多酿造了人类的社会悲剧与历史悲剧。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信仰的认识批判是被缺席的和悬搁的。只有在现象学视阈,信仰则属于被“悬置”或“加括号”的虚假意识。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洞见:“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性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①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页。他接着说:“一门新的科学要在此产生:这就是认识批判,它要整顿这种混乱并且向我们揭示认识的本质。显然,形而上学这门绝对的和最终意义上的存在科学(Seinswissenschaft)的可能性依赖于认识批判这门科学的成功。”②同上,第29页。
在此,本着现象学的哲学原则,我们对信仰进行辩证理性与历史理性相统一的认识批判。
从总体上看,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共同演进过程中,信仰是被个别的想象主体后验地意志设定和情感虚构,架构成为一种虚假而“可爱”的意识形态,进而转化成为先验形态的普遍群体的价值形态和实践行为的绝对标准,从而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运动轨迹,宰制了无数主体的精神活动与生活行为。信仰在赋予生活世界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导致无数的历史悲剧和人生灾难。倘若展开具体的逻辑分析,对信仰的认识批判则更为深入。
首先,信仰是能指和所指的语言游戏。信仰的能指是绝对的和明确的,而其所指则是飘浮的和不确定的。一方面,每一个主体都能够言说信仰,但在概念形态上,主体对信仰的所指往往模糊不清,将不同的信仰种类混淆一体;另一方面,每一个主体之间的信仰理念是不等同和不等值的,即使持有相同信仰的主体,每一个主体的信仰所指也不等同于群体的信仰所指;再一方面,不同信仰的个体和群体,他们之间的信仰所指也存在着巨大的精神鸿沟,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公约数。换言之,信仰之间没有共通性,没有相互对话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可能性。所以,不同信仰主体之间的所指是封闭的和排斥的,甚至是充满对抗性和敌意的。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的主体之间在历史上必然地存在着精神冲突和社会暴力。所以,信仰的能指与所指的语言游戏是信仰宿命性的内在矛盾,甚至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对立因素,这也是不同信仰之间无可妥协的精神对立和暴力冲突的逻辑缘由之一。
其次,在时间性上,信仰起源于后验。信仰是极少数主体依照宰制大众精神这一目的,以感性的想象活动和理性假定的策略所创造的心理结果,带着强烈的心理主义色彩。然而,这一后验的结果一旦作为包含话语霸权的命题得以确立,对后来的接受者而言,它就诞生了逻各斯意义,成为一种先验范畴和逻辑前提,具有普遍有效的必然性。所以,信仰同样包含着后验与先验的悖论和前者与后者的思维游戏。由此可见,信仰是先行设计者对后行接受者的精神魔咒。在空间性上,信仰以自我的绵延与扩张,一方面以心灵感化的策略,借助于语言蛊惑、情感诱导、利益笼络和理性说教等方法,逐渐实现传播地域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依赖精神威胁和集体暴力的方式开拓自我的疆土,超越国家、地区的版图限制,以达到对空间控制的最大化。在数学性上,信仰起源于少数个体,是极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的数学游戏,并且这种控制只有开端没有终结,它是一个无限延长的数字链条,是一个不断增加的数值。
再次,信仰表现出典型的心理主义倾向,而心理主义恰恰是现象学摒弃和批判的思潮。诚如所论,胡塞尔“首先是着力揭示心理主义结论的荒谬性,然后再抨击心理主义所据以建立的各种偏见”。①斯皮格伯格:《现象学的运动》,王炳文、张今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3页。信仰上的心理主义特性表现为,一方面,放弃对客观世界或现象界的遵守,不承诺现实世界的存在性与合理性,它只以自我想象和心理直觉为中心和价值尺度,以个人的主体性为生活世界立法和设定未来世界的所谓永恒准则;另一方面,以个人的心理知觉和体验活动为基准,设定认识标准、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信仰以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设定所谓的绝对、永恒、终极、无限、真理等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征服受众的精神结构和以许诺美好未来的迷醉感或蛊惑性,让无数缺乏反思意识的主体匍匐在它的脚下。再一方面,如果说宗教信仰历史性地包藏着对接受者的心理恐吓性,达到臣服民众的目的;那么,政治信仰则以现实性的感情诱拐和理性说服的双重策略招纳信徒。正是信仰的心理主义的哲学特性,让它周身弥散着典型的神话思维和话语霸权的气息。同时,它以独断论开辟思想道路,排除了对话和主体间性的存在,并且交织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思维暴力的要素,在客观上构成对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自由权力的压抑与剥夺。
最后,信仰不容辩证理性、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考问或检验。它以肯定自我垄断绝对真理的方式,拒绝辩证理性对自己的质疑与提问、否定与批判、反思与超越,不接受和不允许任何历史境域的主体对它的任何评价;它以期许共时性和超历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正当性与完美性的高度契合,排斥历史理性的在场。其实,自信仰诞生之日起,在它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充溢着对芸芸众生感性的诱惑、理性的欺骗和诗意的浮夸,另一方面是以持久的原始暴力和强权主义开拓传播与接受的地域空间。毫不夸张地说,自信仰诞生之日起,人类的历史就多了一个重要的纷争因素,而这一因素所导致的战争与杀戮则从来没有停息过。与其说信仰是文明的开始者和伴随者之一,不如说信仰是文明的毁坏者和终结者之一更合适。与其说这个纷乱的世界源于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源于信仰的冲突,因为文明的核心本质之一即由信仰等精神因素所构成。假如说这个纷争的世界悬搁了信仰,文明虽然缺少一个要素,但是,生活世界将获得更多的安宁与和谐。信仰由于其自身的非实证性和非实践性,它无法接受实践理性的检验,它既缺乏共时性(Synchrong)的伦理原则,也缺乏历时性(Diachrong)的道德规范,只有对同一信仰者生效的教义和教规,或者对同一政治团体的训导和戒律发挥功能。所以,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都和实践理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对于信仰的简要性质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批判,就使我们对迄今为止自以为明证和约定俗成的这一精神偶像产生怀疑和追问的理性冲动,它也许是人类精神的最后一件“皇帝的新衣”。简言之,信仰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性的情感假定,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虚假承诺。换言之,信仰是非理性的人类精神的异化,是理想化和虚无化的心灵幻影。它以极少数创造主体的心理偶然性开辟道路,却以广大接受者的必然性选择作为归宿,这本身就隐匿着逻辑与经验的双重荒谬。
二、概念分析和逻辑分类
在对信仰予以基本分类之前,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具体内涵,在疏理其概念的基本规定性之后,再分析它的主要逻辑外延。
信仰是接受主体对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主、政治领袖乃至某种物质形态的极端崇拜和迷信,并把他们遵奉为自我的认知标准和实践准则。因此,信仰蕴藏着直觉判断和情感体验的特征,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极致的心理体验必然导致理性的缺席。哲学则将信仰理解为“强烈的信念”,通常表现为对缺乏足够证据的、不能说服每一个理性人的事物的固执信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信仰诠释为:“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定势(或态度)。”①《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2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355页。并且认为,信仰显然是一种由内省产生的现象。合而言之,信仰是对宗教教义或政治主义极度地信服和尊重所生成的崇拜心理,主体并且以这种信仰作为统摄精神存在的最高的和唯一的价值观,将其看作指导实践行为的绝对准则和人生指南。《法苑珠林》曾云:“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宗教信仰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与信仰逻辑相关的信仰主义,它认为信仰既高于知识也高于认识,信仰是先验的真理形式。信仰主义认为,科学可以获得知识,但无法论证和解决信仰的问题,因为信仰是高于形而上学的先验命题,所谓的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唯有信仰能够解答。列宁称信仰主义为“一种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②《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16页。“信仰主义”,传统哲学上又称之为“僧侣主义”。在我国一度产生较大影响的由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纂的《简明哲学辞典》将其视为“重信仰而轻科学的反动理论”。③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308页。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在信仰与信仰主义之间画等号,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换言之,信仰是信仰主义的逻辑前提,信仰主义是信仰活动的必然结果。因为信仰主义者认为:“盲信是达到确信而获得拯救的最佳途径。他们根据神秘的经验、天启、人的内心需要、共同感觉等论证信仰。”①《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6卷,第304页。显然,在主体认识方面,信仰主义比信仰走得更远也更为虚妄。
从存在论意义上,信仰可以划分为原始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和哲学信仰诸类别。一方面,由于原始信仰可以归属于自然宗教信仰,因此排除在我们的探究范畴之外;另一方面,由于“哲学信仰”这一话语所指不等同一般意义的“信仰”所指,属于能指相同而所指差异的性质。因为哲学在本质上存在着与信仰的思维对立和逻辑差异,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意义上的“第一哲学”,它作为纯粹理性和纯粹认识论意义的思辨哲学,拒绝给予信仰留有存在的地盘。在现象学视野上,哲学应该保持对信仰的“悬置”和存而不论的态度。至于胡塞尔所心仪的“理性的信仰”,其所指和一般意义的信仰存在着天壤之别。诚如毕迈尔所论:“按照胡塞尔的意图,所以这些最后一定会导致使人对理性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希腊人那里第一次显示出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支配了人类——重新确立起来,由此,对作为理性自身实现场所的哲学的信仰,也会重新确立起来。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哲学在历史上就是人的理性向自身的复归,在哲学中,人类实现了对自身的辨明。由此也产生出一种哲学的伦理学功能:指导人类成为它必须成为的东西。”②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毕迈尔“编者导言”,第8页。因此,在现象学的意义上,理性的信仰或哲学的信仰与一般意义上“信仰”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话语和意义所指。从形而上学的严格意义上看,道德信仰理应不在信仰范畴。因为道德是历时性的存在,它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它缺乏信仰的恒久性和绝对性。所以,我们在此只讨论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这两种主要信仰类型。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认为,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和天启宗教是宗教信仰的基本类型,③参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7章。而绝对知识则是高于宗教形态的精神发展,“是在精神形态中认识着它自己的精神,换言之,是[精神对精神自身的]概念式的知识”。④同上,第266页。因此,宗教信仰不属于绝对知识,它是精神发展的相对低级形态,是一种无法达到精神对自身认识的“异化精神”。宗教信仰的对象包括经书、教主、教义、教规以及与此相关的器物等。诸如基督教对上帝、耶稣、《圣经》的信仰,对永生、复活、原罪、救赎、世界末日说等教义的信仰。佛教对释迦牟尼、佛教典籍的信仰,对“四圣谛”、轮回转世、色空观、无常观等教义的信仰。
宗教信仰主要由对教主和教义、教规及其经书的信仰所构成。换言之,这三个方面构成宗教信仰的基本对象。它们在客观上形成了逻各斯中心,形成所有信徒毋容置疑和不容超越的精神禁忌。首先,教主是信仰的中心或“第一信仰”。如果说上帝是人类情感的第一假定,也是人类理性的第一信仰,那么佛陀和真主同样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设定和第一设定。因为他们都被设定为真善美的最高形式,既是最高的知识形式和智慧创造,也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更是美的终极象征。所有宗教都在绝对权威的前提上规定对教主的信仰,在逻辑上这一信仰是先验的和不能追问的,在时间上这一信仰必须延续到教徒的整个人生历程,甚至教主的身体及其使用过的器物都可以成为被信仰或崇拜的对象。其次,有关典籍的信仰。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经书繁多,诸如《阿含经》、《涅槃经》、《金刚经》、《心经》、《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楞伽经》、《圆觉经》、《维摩诘经》、《坛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大般涅槃经》等。宗教典籍出自不同的历史年代和不同的人物之手笔,有些属于集体创作,它们汇聚了无数存在者的才能、灵感、智慧、想象力和审美精神,它们包含着宗教故事和传说,寄寓着丰富的教义教规,获得定型的“经书”即蜕变成为所有信众的最高和最权威的精神指南和百科全书,既是最高的理论宝库,同时也是指导人生实践的金科玉律。它们一旦被尊崇为“经书”,即成为与教主具有同等意义的最高信仰本体和作为最权威的理论根据,不允许对它们有任何的质疑和反思、批判与否定的精神活动。因此,所有的宗教典籍都无法接受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的提问与诘难,当然也无法面对科学与实证的检验。宗教教主与宗教典籍密切关联的逻辑之一,它们都隐匿着强烈的神话因素,宗教教主往往等同于神话中的最高神灵,而宗教经书中则包含大量的神话故事和虚构的传说,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接受者所信奉的神话或传说。最后是教义与教规的信仰。教义与教规是一种宗教类型总体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的观念、概念、意识、教条、戒律、禁忌等的总和,也是一种宗教类型区别于其他宗教类型的重要标志。它们是某种宗教信仰的具体呈现,也是所有教徒必须全部接纳的“绝对命令”,因此话语霸权和暴力思维构成它们两者的共同点。总而言之,宗教信仰的三种对象,都必然令存在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由自觉的意识和理性思维的能力。
如果说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信仰,那么,政治信仰是相对的信仰。尽管如此,与宗教信仰有着本质上的同一性,政治信仰同样构成对接受者心理的诱惑性势能,使主体丧失辩证理性和自由自觉的思考冲动。政治信仰主要包含有主义信仰、党派信仰、领袖信仰、国家信仰、民族信仰等内涵,转而演化为一种主义神话、党派神话、领袖神话、国家神话、民族神话等存在形式。
其一,在时间性上,如果说宗教信仰起源于文明的初始,那么,主义信仰则起始于近代社会。人类进入近代以来,“主义之争”日趋明显和白热化,意识形态上的某一主义,成为社会群体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后上升为一种盲目性的精神信仰。主义信仰是政治信仰的最高形式,它是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石和实践原则,也是政治信仰的基本教条和严格戒律。主义信仰寄寓着乌托邦色彩的未来许诺,同时它自身强烈的排他性必然酿造社会冲突及其暴力革命。因此主义之争最直接的逻辑结果是政治之争,最终导致政权之争和社会动荡,直接或间接地引发历史悲剧。其二,党派信仰是政治信仰的组织结构、社会基础和物质性存在的综合性呈现,它以政治纲领、组织契约和纪律条文等内容招纳成员,进而要求每一个成员保持对党派的主义、纲领、理论、实践、领袖等的忠诚,犹如教徒对自己的宗教忠诚一样。党派信仰是一个党派和其他党派争夺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是获得话语权和国家控制权的精神保证。其三,领袖信仰是政治信仰的核心和重要环节之一。领袖信仰和宗教信仰中的教主崇拜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所差异的是,宗教教主是唯一性的和绝对权威的精神偶像,在时间上拥有着自始至终的无限性。政治领袖是可以更替的暂时性偶像,他的被崇拜程度和他的集权程度、个人迷信程度及其专权时间成正比。在政治舞台上,党派领袖扮演着半人半神的角色,他的个人魅力就是巨大的政治感召力,而个人魅力的形成往往伴随着领袖的权力野心、独裁技巧、言辞蛊惑力、阴谋的策略等综合因素的提升。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领袖信仰总是共生着政治神话,因为政治领袖常常被塑造为等同或接近于神话人物,这既是因为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政治策略的必然选择。其四,政治信仰必然地蕴藏着国家信仰,因为政治活动常常以国家为单位。人类社会自国家诞生以来,围绕着国家权力的争夺,对外国入侵的抗击和对他国的征服就永不止息。爱国主义等国家意识的诞生和发展逐渐形成对国家的神圣信仰,继而转换成为国家神话。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中,深刻而精湛地运思了有关国家神话的问题,并认为在20世纪,国家神话成为政治神话的有机结构之一,他进而指出:“新的政治神话不是自由生长的,也不是丰富想象的野果,它们是能工巧匠编造的人工之物。它为20世纪这一我们自己伟大的技巧时代所保存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神话技巧。”①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国家信仰必然导致国家神话,国家神话显然成为人类历史的喜剧和悲剧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五,民族信仰同样是政治信仰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君主或政客、阴谋家们都非常擅长于借助于民族信仰的势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每一个民族都坚信自己民族的神圣性,想象自己民族是神意和天意的美妙果实,是世界历史的合理与合法的完善产物。一方面,民族信仰有着历史的进步功能;另一方面,民族信仰常常是罪恶的渊薮。20世纪,民族信仰在纳粹德国演化为种族信仰,最终酿成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三、解构与重建
对信仰的形而上学阐释及其分类性探究,令我们祛除虚假意识形态所包裹信仰的精神面具,得以窥视其真实的面目。然而,我们依然面临两方面的理论劳作:一方面,需要对信仰进一步地解构,希冀深入理解其生成和运作的逻辑动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运思如何重构何种信仰使人类相对完善的精神生活得以可能。
首先,信仰在生成论上起因于人类理性无法解释某些面对的问题,依赖于主体以假定的方式确立一个逻各斯中心或精神偶像,从而摆脱理性的困惑。所以,信仰在时间性上,起因于人类文明的肇始并延续至今。因此,我们可以界定信仰起源于主体能力的窘境和认识的有限性。与此相关,信仰导源于知识存在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活动的有限性。诚如庄子之叹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②《庄子·养生主》。换言之,信仰起因于主体的自我有限性意识。一方面,因为世界的无限性和知识存在的无限性;另一方面,因为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有限性,人类必然面临着以有限抗衡无限的理性困惑之中,于是,“有涯”对“无涯”的境况令主体自然而然地借助于信仰这一感性工具弥补理性之欠缺。
其次,信仰产生于人对自然和自身命运的恐惧意识。一方面,人类无法摆脱对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对象的永恒性恐惧。沃林格认为:“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内心不安的产物,而且,抽象冲动还具有宗教色彩地表现出对一切表象世界的明显的超验倾向,我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对空间的一种极大的心理恐惧。”①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吉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页。与对空间的恐惧相同,主体还存在着对时间的恐惧。古人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时间意识,即是对时间的恐惧感的明证。苏轼《赤壁赋》所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古人对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恐惧。时空的恐惧意识催生了精神内在的信仰需要,这是信仰诞生的缘由之一。主体对时间空间的恐惧还扩展到对生存境遇的恐惧,佛教的“苦集灭道”的“四圣谛”说,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说、原罪说、地狱说等,深刻地表明了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和恐惧,这种担忧与恐惧既涉及个体也包括群体,并且延展至所有的历史时间,甚至永无终止。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从哲学意义上再次表明人类精神对于时间以及自我命运的“畏、烦、死”的深切关怀。人类对于自我命运的担忧与恐惧已经扩展到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核扩散、艾滋病、癌症、气候变化、疫病传播、道德堕落、性开放、过度消费、犯罪、战争等。换言之,人类对自我存在状态的恐惧,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基本元素,向各个领域扩散。如果说对时间与空间的恐惧是人类需要信仰的自然性动因,后面的因素则是人类需要信仰的社会性动因,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无法摆脱信仰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缘由。
最后,信仰产生于人类对未来命运的期许与乌托邦的期待。在时间性上,信仰既是对过去的感性追溯和想象性超越,也是对未来的虚假而美好的期待。一方面,一部分主体具有成圣成王的深厚心理,他们期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所谓的“横渠四句”②张载:《西铭》,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即是少数理想主义者和心怀乌托邦梦想的“圣贤”们的“宏大叙事”,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诗意话语,而不是一个现实的事实与必然的未来。另一方面,人类是一个喜欢期许未来的生物,因为现实世界总是不完善或不完美,不符合理性或理想,所以借助于信仰的方式去建构未来世界的理想模式。期许未来是人类最传统、最普遍和最经济的思维方式,它渗透到生活世界的任何一隅。宗教和政治最善于和最喜欢以期许未来的方式诱惑受众,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也是以期许未来的方式获得自我存在的理由和策略。人类生活在不理想的当下,永远觊觎着美好的未来。这是主体需要信仰的必然逻辑。
对信仰之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并非意味着我们对信仰采取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的独断态度,在21世纪和未来的华夏,我们都需要重建信仰的精神大厦。这个信仰大厦不应该保留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这两个狭隘的结构,不至于像诸多人士呼唤信仰的复归,主要指向宗教与政治。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信仰重构,理应既不由宗教信仰也不由政治信仰来担当,而主要应该诉诸伦理信仰和审美信仰这两个方面。
如果说道德是历时性的伦理,那么,伦理则是共时性的道德。道德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思想观念、存在方式和运作策略,所以道德是流变的和相对的“伦理”;而伦理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确立的最基本的精神与行为的准则。它是人类得以存在的逻辑基础,也是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根本前提。简言之,伦理是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共时性基石,也是人类最核心的精神结构,是保证人类文化与文明得以延续的逻辑前提和思想支柱。所以,人类现实与未来的信仰重建,不应该回归于宗教和政治两个因素,而必须延请伦理信仰。换言之,由于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的诸种局限,我们不得不选择伦理作为人类现实与未来的信仰对象。①本人赞同陈伯海的建议:“我们亟需树立的是一种非宗教的信仰,而不是宗教信仰。”《上海文化》2016年第4期,第15页。显然,这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合乎逻辑原则与历史需要的必然性选择。
伦理信仰奠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并有所发展,最终形成稳定性的具有共时性普遍法则的价值与意义,诸如东方儒家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原则,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的人道主义原则,道家庄子提出的万物“齐一”的生命均等的哲学思想,理学家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的伦理观等。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等提出善、德性、正义、公平、诚信、爱、仁慈、宽容、自由等伦理概念,西方当代生命伦理学所提出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敬畏生命”、“关怀环境”等道德概念,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果实,是维护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价值原则和保证人类根本幸福的伦理法则。这些伦理法则均可以被提升为一种纯粹而绝对的超越历史时间、超越地域与国家、超越宗教、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普遍信仰,成为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的精神准则和实践依据。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道德法则对于绝对完满的存在者的意志是一条神圣性的法则,但对于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意志则是一条职责法则,一条道德强制性的法则,一条通过对法则的敬重以及出于对其职责的敬畏而决定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行为的法则。”③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9页。无论上述法则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是“神圣性的”还是“职责”或“敬重”性质的,它们理应成为处于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所有存在者必须敬畏和接受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信仰呈现出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它不应当被社会意识形态所左右,也不应当被政治集团、党派、国家所操纵,而保持着自我存在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它应该类同于普遍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成为整个人类在任何历史语境均可信奉的精神价值。因为只有伦理信仰才可以打破不同文明模式和不同文化结丛的界限,只有伦理信仰才可能超越民族、种族、宗教、政治等传统历史精神的藩篱,也只有伦理信仰使整个人类的主体间性和平等对话得以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唯有伦理信仰有可能达到孔子的“大同”、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Utopia)等社会理想,也唯有伦理信仰有可能使主体升华到符合人性和相对完善的精神境界。
如果说伦理信仰可以保证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可以保证人性的相当完善,那么,审美信仰则可以保证生活世界的审美性和诗意性的主观基础,可以保证主体的诗意生存和艺术创造,使人类的浪漫情怀得以可能。因此,主体仅有伦理信仰还是欠缺的和单向度的,还不能保证人性的完整性或完满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了主体存在的丰富感觉性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审美活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确证之一。“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起来。”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页。人类于生活世界一个重要的存在理由和追求目标就是“美”,它包括审美活动和审美创造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之外,对美的沉醉与向往即是人类存在于世界的重要诉求。换言之,倘若没有美的存在与追求,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境界必然丧失一部分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丧失诗意、激情、灵感,丧失一定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丧失诸多快乐和幸福。美必然地构成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对象,构成主体存在的重要理由和最核心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在中世纪,基督教以主流思潮设定如此的精神逻辑:上帝是最高的美;美就是上帝的。宗教思想家以上帝取代美,美被消解了独立存在的权力。普洛丁(Plotinus,205—270年)提出“真善美统一于神”的论点,他说:“如果要得到美本身,那就得抛弃尘世的王国以及对于整个大地、海和天的统治,如果能卑视这一切,也许就可转向美本身,就可以观照到它。”②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页。他将美看作是和宗教信仰等同的存在,而审美活动必然要摒弃现实世界的感性生活,走向内心对上帝的神秘体验,他的“美本身”就是上帝的象征品和替代物。圣·奥古斯丁(S.A.Augustinus,354—430年)直接提出“美在上帝”的命题。那么,中国现代的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的观念则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场革命,客观上展开了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价值颠覆。显然,以“美育代宗教”所隐匿的思想意义即逻辑地指向着建立审美信仰而取代宗教信仰这一理论目标。
审美信仰不应该是全新的命题。在人类历史的前期,美即成为主体的崇拜对象,成为精神意义的核心和逻辑起点,也成为存在者的心灵偶像和诗性追求。其实,中国老子的“道”不仅是哲学命题和哲学信念,也是美学命题和审美信仰的证明。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4页。道和自然是同一性的存在,它们都是主体的最高审美对象,也是审美信仰的最高目标和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天、地、人、道”四位一体的存在,它们一方面是审美对象,另一方面也构成主体的审美信仰,它们是人之存在的理由和全部意义之所在,同时也是哲学和诗的最高对象和最终的审美目的。如同康德哲学所言“人是目的”一样,老子的道、自然和人同样是目的。这一具有本体论和存在论相统一的目的,也就是最高的信仰形式,即审美信仰。
从生存论意义考察,人一方面是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另一方面也是诗性主体和审美主体,审美活动是人类最本质的活动之一,也是主体的生存理由和生存意义之所在。换言之,审美在最广泛、最自由的程度上呈现了主体的本体意义和生存意义。所以,审美信仰的建构就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结果。笔者在《怀疑论美学》中论述了“审美信仰”这一命题,②颜翔林:《怀疑论美学》第7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强调审美信仰中的自我意义和直觉功能,强调了审美活动中主体的优先地位,强调了直觉和想象力在审美信仰之中的主导性功能。
综上所述,后现代语境中的信仰重构理应包括伦理信仰和审美信仰这两个逻辑关联的精神维度,它们有可能为相对完善和相对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设提供一份精神价值的保证。在此,笔者援引广为人们所熟知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中的话:“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③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77页。人们在理解和诠释这段话语的时候,一般地将道德法则视为中心,而“星空”则作为一种美之陪衬。其实,在康德的美学意义上,星空具有和道德法则同等的价值意义,它们是逻辑上的并列关系。康德在强调道德法则(其实更是一种伦理法则)的同时,隐匿着审美法则。换言之,星空作为美学的隐喻和象征符号,它的所指就是“审美信仰”。置身于21世纪的后现代历史语境,存在者应该牢牢把握伦理信仰和审美信仰这两个精神向度的必然性,它保证着历史与未来的合理性和完善性,它不是虚假承诺的“理想国”、“乌托邦”或“桃花源”,而是守望在每一个心灵深处的根本意义和普遍价值,它是人类得以存在的逻辑,是主体得以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普遍价值,它是沟通此岸和彼岸的长满绿叶与鲜花的如诗如画的彩虹之桥。
责任编辑:沈洁
*颜翔林,男,1960年生,江苏淮安人。温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