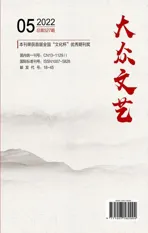从叙述学角度对史铁生《往事》的解析
2017-01-28刘浩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610000
刘浩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 610000)
从叙述学角度对史铁生《往事》的解析
刘浩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 610000)
《往事》是当代作家史铁生的一篇短篇小说,它的叙述方式十分巧妙。本文试图从叙述学的角度对《往事》的叙述艺术进行深入解析,在分析小说以梦境再述与插叙结合的叙述策略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小说独特的梦境再述,并用叙述学知识对相关叙述现象进行解释,希望能发掘出这篇小说在叙述上的闪光点。
往事;叙述;梦境再述
《往事》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200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述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采用了对三个梦境的再述和插叙的结合,以梦境叙述巧妙地交代了“我”和妻子闹离婚的故事背景,然后用插叙安排了其他人物的出场,二者前后叙述内容又有连接之处,把主要情节只有一晚上加一上午的“被叙述时间”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充实。本文将在下面结合具体文本说明这个叙述策略是如何实现的。小说对梦境的叙述是本文叙述结构的重要一环,也是《往事》的叙述的独到之处。笔者将把论述重点放在梦境叙述的特征以及这篇小说梦境叙述的合法性的分析之上。
一、巧妙的叙述结构
(一)梦境叙述的作用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梦与人类的关系密切,它也频频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神秘莫测的梦和文学作品一结合,使作品更富有趣味性,尤其是叙述性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当它们再融入对梦的叙述,会使作品的叙述层次更为丰富。《往事》这篇小说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主要情节叙述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三个梦的叙述,以梦境的叙述代替故事背景的叙述,避免整个小说的叙述落入俗套,激发起受述者的接收兴趣。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这篇小说的“被叙述时间”是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什么是“被叙述时间”呢?《广义叙述学》是这样定义的“指的是被叙述出来的文本内以各种符号表明的时间”1这篇小说在一开头给出的时间是“童年,某个除夕的下午……”2如果不知道后面的情节,我们肯定以为叙述者是在回忆童年的情景。就在这个“被叙述时间”里,叙述者给我们讲述了第一个梦的内容:“我”在街上玩耍,到天黑时准备回家但突然发现家不见了,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叙述者这时说道“醒了,是个梦。”3受述者方才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在第一个梦叙述完毕后,叙述者又给出了一个“被叙述时间”——“天还黑着,黑得透彻,估计也就是半夜两三点钟”。在第二个梦里,叙述者介绍了另一个重要人物——“我”的妻子。第二个梦的内容就是叙述“我”和妻子的对话,“我”跟妻子说起跟她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捡到了她的照片,但当妻子问“我”照片在哪儿,“我”才发现照片不见了。叙述者此时又说道“我又醒了。梦。还是梦”。紧接着,叙述者又给出了一个“被叙述时间”——“天蒙蒙亮了”。在第三个梦里,叙述者讲“我”和妻子准备去办离婚手续。“我”突然停下来,恳请她不要离开“我”,却发现怎么喊她也没反应。第三个梦叙述完后,叙述者照例说道“是呀,还是梦。”然后,叙述者再次给出“被叙述时间”——“天完全亮了……是夏天……刚8点半就跟下火似的了”。给出这次“被叙述时间”后,叙述者“谎称”自己都不确定这一次是不是还是在梦里,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后来终于确信了自己回到了现实,叙述者表达了无奈的感慨。通过对小说中“被叙述时间”的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把小说中的梦境和“现实”区别出来,但是受述者在接受这些叙述时很容易混淆梦境与“现实”。具体原因本文会在后面进行分析。
(二)梦境叙述与插叙的结合
小说通过第二个和第三个梦的叙述,让受述者了解了故事的大致背景。叙述者在第二个梦醒后写道“妻子通常睡着的地方没有人,那块床面也是冰凉凉的。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她已经走了。她有好些日子不来住了。她说还是离婚吧我真是受不了你了”4这让受述者明白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就是讲“我”和妻子闹离婚的事情。叙述者在讲“我”醒来后就要去找妻子办离婚手续了。如果二人“顺利”离婚,故事就结束了,整个叙述就会显得平淡无奇。小说作为虚构叙述的一个门类,追求情节的起伏和故事的转折是其一贯的特征。因此,《往事》的叙述者在故事的最后设置了“我”同学吴夜意外出事,离婚事件被搁置起来。小说前面的主要角色只有“我”和妻子,要增加其他人物,充实故事内容,只能增加其他事件的叙述。于是,叙述者又插叙了“我”在“大串联”时的故事。叙述者在插叙中交代了吴夜为什么会对“我”妻子念念不忘。因此,吴夜一听到“我们”准备离婚就回国追求妻子,于是才出现了后面的意外事故。那么,对梦境的叙述又与插叙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呢?
在第二个梦中,叙述者讲了“我”在梦中与妻子对话,回忆了二人初次见面的场景。“我”捡到了妻子(当时只是“我”同学)的照片,并把它保留了下来。但当妻子问“我”照片在哪儿,“我”才发现照片不见了。而在插叙的故事里,叙述者把照片的下落说出来了。原来在“大串联”的时候,吴夜有一晚说梦话一直喊着“冬雨”(妻子的名字),“我”为了让他安稳地睡觉,就把捡到的照片给了他。吴夜后来也以为自己那个梦是真实的,因为他手上有冬雨的照片,所以他才一直爱着冬雨。叙述者就这样巧妙地把梦境和插叙的内容结合起来,既让前后的故事情节相互照应,连成一个整体,又使第二个梦境更“真实”,让受述者感到疑惑,创造出了一种朦胧含混的艺术效果。
二、独特的梦境再述
《往事》这篇小说在叙述上最有特点和最具魅力之处就是它的梦境再述。为什么笔者称之为“再述”呢?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第三章详细地解释了梦为什么是一种叙述,因为“首先它们是媒介化(心像)的符号文本的再现,而不是直接经验;其次它们大都卷入有人物参与的情节,心像叙述者本人,就直接卷入情节”。5做梦本身就是一个叙述过程,当梦被讲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二次叙述”,是梦的“再次叙述”。6笔者在上一章分析了小说开头的三次梦境再述如何交代故事背景的,主要切入点是文本里面的“被叙述时间”。三次梦境再述的“被叙述时间”都清晰而明确,但这些时间标记却让受述者在接收叙述时容易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第二次梦境再述的“被叙述时间”是“半夜两三点钟”,第三次梦境再述的“被叙述时间”又是“天蒙蒙亮”。这两个时间具有序列性,而且与后面主叙述的时间一致,就产生了如下的接受效果:受述者在接受第二个梦境再述时以为那是“现实”,故事进入关于“现实”的叙述,然后叙述者说道“还是梦”;受述者在接受第三个梦境再述时又会以为故事进入了“现实”叙述,但那“还是梦”;因此当故事真正进入“现实”叙述时,受述者就会产生怀疑了,加上叙述者自己也重复说道“这是不是还是梦?”,于是受述者就感觉到梦境和“现实”有些混淆了。这时,受述者就不自觉地站到了叙述者的立场上,当叙述者感叹“想把现实当成梦时,自己却醒着的”时,受述者就会产生很深的认同感。当然,梦境再述的“被叙述时间”不是使受述者混淆梦境与“现实”的唯一原因。笔者认为“二我差”的不明显也是给受述者造成困扰的因素之一。什么是“二我差”呢?赵毅衡先生的定义是“(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者‘我’,写人物‘我’的故事,而且故事时间越来越迫近叙述时刻。而在这一刻之前(也就是在整个被叙述时段中)同一个‘我’,作为叙述者,作为人物,两者之间会争夺发言权,形成主体冲突”。7在小说第二个梦境再述和第三个梦境再述中,当叙述者没有说出那句“是梦,还是梦”之前,受述者很容易把叙述者和人物“我”的身份等同,因为二者在文本中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二我差”。
这篇小说的梦境再述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第一个梦境和第二个梦境形成了“梦中梦”的叙述形式。在第一个梦境叙述完后,叙述者说道“醒了。是个梦”。紧接着,叙述者开始第二个梦境的讲述,他首先讲了“我”与妻子关于上一个梦的对话。这样,第一个梦境就“嵌套”在了第二个梦境里。如果这样看的话,前面两个梦就只能算是一个梦。但是,这种叙述方式并不是叙述学中的“叙述分层”。赵毅衡先生曾给“叙述分层”做了如下定义“上一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下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或叙述框架。也就是说,上一叙述层次的某个人物成为下一叙述层次的叙述者……”8小说中第一个梦境和第二个梦境的叙述者都是“我”,这和后面情节的叙述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上。虽然叙述者采用了“梦中梦”的叙述方式,但第一个梦境并不是附属于第二个梦境的,它们其实是处于同一层次的事件。这样一看,“梦中梦”的叙述就不再那么神秘,它也只是叙述者的一种手段。叙述者采用这种方式一是让前后两个梦能有机联系起来,交代故事背景;二是增强小说开头那种朦胧的叙述氛围。
三、《往事》梦境再述的合法性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篇小说梦境再述的特征,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这些梦境再述的合法性问题,即梦境叙述为何能被受述者顺理成章地接受。在谈到三个梦境再述的“被叙述时间”时,我们能够看到每个梦境都有清晰的“被叙述时间”,而且在第一个梦境中,叙述者给出的“被叙述时间”是从早上到下午到晚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时间链条。有学者在分析梦叙述的时候提到“在梦中,由于意识处于暂时的休歇状态,所以意识之产物的时间也失去了明晰的、空间化的线性特征……梦中的事件显得很离奇,它们既标识不出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分辨不出同时性与序列性,它们只是一系列随机事件的随意组合”。9这个论断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根据我们自己做梦的经验,我们每次梦醒后很难记起梦中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也很难经历具有时序性的梦。为何在做梦时难以找寻到踪迹的时间在梦的再述中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呈现呢?
按照《广义叙述性》对叙述类型的划分,梦叙述属于心像叙述,而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梦境再述是一种记录类叙述。《广义叙述学》中把梦的再述判定为一种二次叙述,而且是“妥协式二次叙述”。笔者认为赵毅衡先生在分析“详梦”时的一段论述可以很好地解答上面的问题。他提到“因为梦境充满了自相矛盾,不合‘经验常理’之处,甚至逻辑也不可能会一再出现,因此‘详梦’的二次叙述,不仅要把叙述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时间环链、可理解的情节环链,最主要的是从似乎无理可循的混乱情节中说出一个因果与伦理价值”。10叙述者在对梦境进行再述时,要想让受述者比较容易地接受梦中的事件,那么就必须对梦叙述的文本进行创造加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能理解小说梦境再述为什么会有清晰的“被叙述时间”了。
当然,这不能完全解释小说中梦境叙述的合法性。在小说第一个梦境再述中,出现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在第二个梦境再述中,“我”与妻子有着很连贯的对话,而且“我”还对往事进行了回忆。这样的叙述与我们做梦的经验相当不符。在我们对梦进行二次叙述时,我们很难讲出其中的一些细节,传达出丰富的信息,更别提清楚地讲述梦中对往事的回忆。那为什么小说中的梦境再述能够做到呢?为什么它能被受述者所理解呢?笔者认为要从虚构型叙述的性质进行分析。在这里,我们要借用一下《广义叙述学》关于虚构叙述的“二度区隔”的论述。“为传达虚构文本,作者的人格中分裂出一个虚构叙述发出者人格,而且用某种形式提醒接收者,他期盼接收者分裂出一个人格接受虚构叙述。虚构文本的传达就形成虚构的叙述者——受述者两极传达关系。这个框架区隔里的再现,不再是一度媒介再现,而是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正因为这个原因,接收者不问虚构文本是否指称‘经验事实’,他们不再期待虚构文本具有指称性。”11小说中的梦境再述是虚构的,它与现实经验被叙述框架隔离开来,因此受述者在接收梦境再述时不会刻意把小说中的梦与经验世界中的梦进行对比,他们在意的不是叙述中的细节,而是情节的连贯。再加上三个梦境叙述给受述者造成了扑朔迷离的感觉,受述者就更加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文本的指称上了。从“二度区隔”来分析梦境叙述,我们就可以更为深入地解释梦境再述为何具有清晰的时间和时序,也可以更全面地解释《往事》的梦境再述的合法性。
注释:
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47.
2.史铁生.《往事》,见何言宏、张学昕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短篇小说卷1》,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3.同上,第3页。
4.史铁生.《往事》,见何言宏、张学昕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短篇小说卷1》,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5.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6.同上,第49页。
7.同上,第158页。
8.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264.
9.龙迪勇.《梦:时间与叙述》,《江西社会科学》,2002(8).
10.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16.
1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76.
[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2]史铁生.《往事》,见何言宏、张学昕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短篇小说卷1》,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龙迪勇.《梦:时间与叙述》,《江西社会科学》,2002(8).
刘浩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