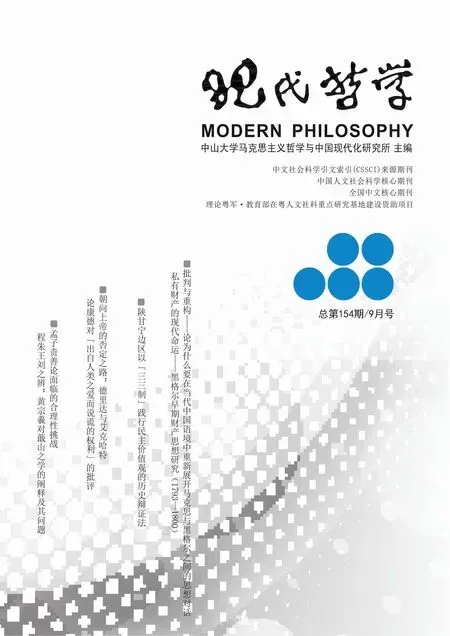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2017-01-27陈琼霞
陈琼霞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陈琼霞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在以往的讨论中,“仁爱原则”被视为儒家思想的黄金道德律(golden rule),也就是第一律之“道德理论”。学者往往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与基督宗教的“圣爱”进行对比,并将两者共同视为黄金道德律。但依照以往写作儒家当代生命伦理学理论之学者,则将“仁爱原则”视为第一律下的“中层原则”(middle level principles),也就是次于第一律的原则,其更贴近于案例与实践的运用。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
施益原则;仁爱原则;忠恕之道;爱人
一、前 言
生命伦理学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的研究领域涉及传统医学伦理(medical ethics)、健康照护伦理(health care ethics)、动物伦理(animal welfare)、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遗传伦理(gene ethics)等,是一门跨领域学科。生命伦理学这大范畴也开展出生命医学伦理(biomedical ethics)之研究。著名的生命医学伦理学家汤姆·比彻姆(Ton L. Beauchamp)与詹姆士·邱卓思(James F. Childress)合著的《生命医学伦理原则》*此书已复印至第七版,可谓是医学伦理中的圣经级书籍。(Principle of Biomedical Ethics)提出四个中层道德原则:不伤害原则(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施益原则(the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公平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尊重自主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这些原则可作为相关从业人员执业时的道德行动准则。
随着视野的扩大,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不同文化、地域的人群,皆存在一套属于自己文化圈的思维向度、属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因此形成专属自身社群文化的价值选择。在西方生命伦理学发端之后,中华文化圈亦有学者试图思考,能否在我们的文化圈中寻找适用于医疗、生命科技、医疗执业伦理等领域指导原则,一套属于中国儒家文化圈下的生命伦理原则。根据目前研究,关注此问题之研究者有三,他们各自提出“生命伦理原则”。其一,李瑞全先生在1999年《儒家生命伦理学》*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台北:鹅湖出版社,1999年。中提出儒家生命伦理两原则,分别是各尽其性分原则、参赞天道原则。其二,范瑞平先生在2011年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提到儒家生命伦理四原则,分别是仁爱原则、公义原则、诚信原则、和谐原则。其三,马家忠先生在2013年《仁术、中和和天道——中华文化身体学与生命伦理思想的多元历史建构》*马家忠:《仁术、中和和天道——中华文化身体学与生命伦理思想的多元历史建构》,南京:东南大学,2013年。中提出中华医学的生命伦理原则,分别是尊重生命原则、仁爱原则、精诚并重原则、社会责任原则。范瑞平先生与马家忠先生皆认为“仁爱原则”必须列为重要的生命伦理原则,李瑞全先生也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可涵摄西方生命伦理中“不伤害原则”与“施益原则”*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第60页。。儒家“仁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价值,且为华人医疗文化特别强调的部分。*清代名医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提到:“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提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倚。”故强调“仁爱原则”具意义与必要性。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首重对他人付出仁慈、进行增益他人之利他行为,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强调爱人、推恩他人之精神有其相似处。故将西方生命伦理的“施益原则”与华人医疗文化之核心“仁爱原则”进行对话,以增益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
二、对“施益原则”的再思考
“施益”(beneficence)主要指为利他、爱人和人道,更广泛的意义则指增进他人利益的行为。*Tom L. Beauchamp,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 of Biomedical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7.“施益”指为履行仁慈、善良的行为或做善事,也就是要施加利益在他人身上,增进他人的幸福或福祉。*萧宏恩:《医事伦理新论》,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施益作为一种原则,指为增进他人利益而行动的道德义务,其确立一个帮助他们增进其重要的合法利益的义务。*Tom L. Beauchamp,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 of Biomedical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7.“施益原则”指为做造福他人的行为。*萧宏恩:《医事伦理新论》,第105页。“施益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强调医疗人员应该努力把利益加在病人身上,尽可能地对病人施予仁慈且善良的德行。*黄苓岚:《医学伦理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台北:新文京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施益原则”与作为普世价值的“乐善好施”行为相同。因此,将“施益原则”作为中层伦理原则应没有任何疑义。然而,部分哲学家却探问:应该将“施益原则”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或仅作为“可选择地仁慈的行为”(非应然之行为)。换言之,“施益原则”究竟是一种道德理想,或应被提升至公共性道德义务成为“施益原则”讨论的焦点。此外,在一般情况下、特殊的情况下、不同的对象中,施益者对他人的施益程度与范围之界定,也成为延伸讨论的议题。。
有些哲学家,例如边沁(Jeremy Bentham)、罗斯(W.D. Ross)、辛格(Peter Singer)等,认为“施益”应被视为积极义务,但部分批评者质疑此论点。质疑者认为我们无法要求其他人必须协助需要帮助者,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加以施益他人。但罗斯认为我们需视施益是一种义务的理由在于“基于单纯的事实:这世界上有其他一些人,我们可使他们在德行、才智或快乐方面的状况获得改善。这是仁慈的义务”。*W.D. Ross, The right and the Go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30, p.21.辛格同意应该把施益视为义务,且划定可容许的施益范围与程度,他主张“如果我们有能力防止坏事发生,且不会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价值的东西,那么,在道德上我们应该这样做”*Peter Singer,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72, pp.229-243.。
部分批评者否定“任何时间、任何情况对大多数人施益”这一观点。汤姆·比彻姆(Tom L. Beauchamp)、詹姆士·邱卓思(James F. Childress)、麦可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就采取此类论点。斯洛特认为施益者无须牺牲“基本生活计划”加以施益他人,所以我们无须把施益他人视为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防止严重的恶行或伤害,且自身行动并不会严重扰乱自己的生活计划,那这个人才有义务进行施益。*Michael A. Slote, “The morality of Wealth”, in World Hungen and Moral Obligtlion, NJ: Prentice Hall, 1977, p.127.比彻姆和邱卓斯则看到人们面对不同施益对象之差异,都明确表明我们不可能相同地施益于不同的对象,面对亲属的施益远远大于对陌生人的施益。因此,比彻姆和邱卓斯虽主张须将“施益原则”列入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但否认施益原则凌驾其他原则之上。他们认为是否施益他人的标准在于:我们仍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是值得的。
学者们的争论隐含对普遍原则的渴望。这是当代伦理学寻求普遍客观原则的思路。学者们试图将“施益原则”抬高至公共道德的高度,这意味着将原则拉抬至职业相关从业人员皆须认同的普遍行为标准。但即使是采取批评立场的学者,也未全盘否认“施益原则”,而是试图完善“施益原则”的普遍标准。事实上,这只是降低了“施益原则”对他人作为应然义务的要求。
尽管学者们试图寻求“是否应施益的普遍标准”,但我们仍须进行提问:如何能准确地或者适当地估量我们自身所付出的风险与成本,以及衡量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回馈呢?即使现今已有量化的方式进行计算,例如成本-效益分析(CEA)、成本-利益分析(CBA)。但我们仍难以准确地估量人的内心感受所计算出来的风险和成本,这似乎是科学数据所无法提供的。我们能客观地计算付出的成本与整体获益是否值得,但我们难以估量、掌握施益者对自身所付出成本的感受,甚至考虑完成施益他人之后对施益者所造成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提问,台湾曾发生一个案例:一位罹患血癌的女童,透过某宗团体教骨髓数据库比对,找出两名完全吻合的捐赠者,*此两名捐赠者同意将自己骨髓资料给某宗教团体建档之初衷,应是同意未来有他人比对成功后愿意捐赠骨髓。但两名捐赠者被告知比对成功后却拒绝捐赠骨髓给女童。女童母亲透过媒体力量希望捐赠者能同意捐赠,但依旧未果,后来女童接受了另一名不完全吻合的捐赠者之捐赠,但却因排斥反应而死亡。*《两捐髓者都反悔,八岁癌童不治》,《苹果日报》2013年6月24日。捐献骨髓即可能救治女童性命,且根据台湾民众普遍具有“积阴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思维,两名捐赠者应捐赠骨髓。换言之,捐赠者付出之成本(捐赠骨髓)远低于其所产生的利益与回馈(救女童性命),但两名捐赠者却都拒绝了。我们无从猜测两名捐赠者内心的考虑,*移植骨髓需经过多次穿刺骨盆,以麻醉无痛进行骨盆穿刺抽取,但这其中有一些风险,麻醉可能造成死亡,穿刺抽取可能造成神经受损而瘫痪,这或许是捐赠者内心的考虑之一。但他们所选择的行动呈显出了施益的普遍标准未能估量施益者内心之感受。
关于第二个提问则有另一例子:媳妇同意捐赠已脑死先生的器官,捐赠之后却遭受亲友的责难与歧视之案例在台湾屡见不显。更有同意捐赠器官之家属,因无法忍受亲友责难而痛苦寻短。*《狠心?不爱他?同意器官捐赠家属却遭歧视痛苦寻短》,《Nownows今日新闻》2012年5月4日。器官捐赠让多人受益,执行行动之后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与回馈(一人捐赠多人受益),但倘若我们将行动之后所带来的影响放入行动所产生的利益进行考虑(媳妇所受的长期责难与心理煎熬),那么量化计算利益与回馈更显困难。
在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的讨论中,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普遍的“规范”以及衡量的“标准”,为医护人员、相关场域中的从业人员寻求一个依凭的准则,一种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标准。然深层地思考,即便拥有计算公式,但进行决策者的内心、心理状态似乎难以估量;即使已经客观化地使用“成本”、“风险”、“利益”这几个重要衡量指标,但将个体人的思维考虑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置入其中,普遍化的原则与衡量标准显得格外苍白。在此,我们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选择扬弃这种寻求普遍化准则的思维,二是为这种准则找到另一个增补的方式。而中华文化下的生命伦理学准则,提供出一种可能。
三、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内涵
生命伦理学相关议题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并在21世纪开始茁壮。关于儒家生命伦理原则之讨论在2000年前后逐渐被重视。儒学为中华文化之根本,“仁”亦是儒家文化之核心,与中国人的个人生命意义、家族关系、职场关系等“己与我”“群与己”之人伦关系休戚相关,故将之视为儒家生命伦理学原则之首当之无愧。本节主要说明马家忠先生与范瑞平先生所理解的“仁爱原则”之内涵,并反思此原则内涵完善程度。*李瑞全先生认为儒家生命伦理学以“仁”为核心架构,但未将“仁”视为一个原则。本文着重于“仁爱”作为中层原则之讨论,故本节将不引用李瑞全先生之论述。
马家忠先生提出中国传统宇宙论“天-地-人”之三元结构,强化“人”处于“天”和“地”之间,且人具有认识天地自然大道、顺应大道、修性养命达到整体社会和谐之能力,这些能力体现出人的中心位置和积极作用,因此“人”具有崇高的价值。“人贵论”的思考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马家忠:《仁术、中和和天道——中华文化身体学与生命伦理思想的多元历史建构》,第39—40页。马先生引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强调“仁”并非外加的,而是出自人之“本心”。他还以孔子之言提出推己及人的观念内涵,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庸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出于自然”的仁学,通过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重建社会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换言之,人之贵在于人有“仁心”且能通过己身的人心能力,将仁外推于社会中的其他人。*同上,第41—43页。因此,马先生认为医者须发扬“仁心”、“仁术”,由仁之爱人之情,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即使儒家强调爱有“差等”,但进入医学领域终将消散,将爱人之心扩展至所有病人群体中,医生对任何病人的职责都是救治性命,帮助恢复健康。*同上,第93—94页。
范瑞平先生也认为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应置入“仁爱原则”。他认为仁爱源于亲情,应当适当地推及他人以及天地万物;但人的家庭之爱应当具有优先地位;仁爱既是普遍之爱,也是差等之爱。*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范先生的论证理路为:“仁”是人天生本具,是上天根植于人心的自然能力。换言之,每个人天生具有爱他人的情感能力。人是家庭中的动物,即使爱是自然潜能,但爱的情感并不是平等地施给所有人,《孟子·滕文公上》:“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因此必须借助孟子所谓的“推恩”的功夫,《孟子·梁惠王章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仁”才能从一种自然情感上升为道德行为,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终成为一种人之品格。仁爱具差等性,但能向外推恩于万物,则有赖培养行动者的修养功夫,也就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使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通过严肃的礼仪行为,一个人培养、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感,从而合适地爱人爱物。*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246页。
马家忠先生所提的“仁爱原则”侧重培养医事从业人员的“仁心”、“仁术”,强化职业应有品格的要求。范瑞平先生虽亦侧重仁心推己及人之外推性,但特别强调家庭人伦之爱,认为必须先肯认家庭之爱,肯认仁爱具有差等性,继而强调仁爱的推扩意义,以达到宋明理学家强调“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境地。但不论哲学家们对生命伦理学“仁爱原则”的讨论为何,他们共同强调:1.“仁心”无须外求,人之本具;2.“仁”能向外推扩,借助推扩,达到对他人普遍之爱;3.“仁心”虽本具,仍需工夫加以培养优秀的品格。
我们必须提问,对“仁爱原则”的阐述已经足够了吗?若以“仁爱原则”分析癌童等待捐髓个案,能进行适当地伦理分析吗?强调“仁心”本具、差等之爱、推恩于外的观点下,骨髓配对成功者应该捐赠给女童。但在实际的情况中,捐赠者拒绝捐赠,难道这意味着捐赠者与亲友不具仁心吗?而拒绝捐赠器官亦即违反“仁爱原则”这一中国文化传统所共同肯认的品格,那么拒绝捐赠者必然受到社会中多数人施以鄙夷之眼光,这样合理吗?
四、对“仁爱原则”的反思:“忠恕之道”实践之力
中西方思维对伦理学发展的向度根本上不同。儒家生命伦理在“仁爱原则”的立基与朝向亦不同于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施益原则”本质上是一规范伦理学之思考,其尝试提出较具普遍性的规则与判准;而“仁爱原则”则强调由己身出发,尝试培养、教育生命医疗场域中利害关系人的本心自发之良善与推扩他人的爱人精神。
尽管西方哲学家对“施益原则”的探讨首重是否须将“施益原则”视为道德义务,进而延伸思考施益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如何订定,总结出多数伦理学家仍同意“施益者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衡量是否施益的标准。但如上文所述,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与衡量花费的成本是有其难度的,特别当施益者与受益者有特殊关系,甚至是施益者自身价值观与客观利益衡量产生冲突所造成的成本计算更显困难。“普遍原则”与“个体差异”本身即存在着鸿沟,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人格或具体生活情境中,只能是误入歧途。即使哲学家们试图寻求一种普遍性的施益规律可能是失败的,但这个失败却也指向出一种可能——“施益者的衡量”。“施益者的衡量”意味着回到施益者自身,让施益者的自主意志衡量施益的程度与范围。对于“施益者的衡量”彷佛可以回到儒家的“忠恕之道”中再度思考。
关于“仁爱原则”之讨论,其预设“仁”是人之本性,仁表现在爱人且必然利他行为上。但这明显忽略了不同情境下人际、人与物的利害相关性,在利益冲突下人之本性如何必然行“仁”?“仁爱”成为一种道德理想。这样的预设无法处理生命科学、医疗场域中的实际问题。尽管医护人员们知道需要具备医德,需要为患者和其家属着想;器官捐赠有利益于受赠者;生命科学研究者知道自身进行研究时需要对生命尊重,尽量不伤害具有成为生命潜能之生命,尽量不伤害研究主体,甚至是施益于研究主体,例如被研究的小动物们或者人体。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太多的利害冲突,我们实在无法确认医护人员或关系人在利害冲突下仍旧怀抱着推恩他人的精神。*一个实际的临床状况:刘小姐是一名教学医院的护理长,某日家里突然来电,告知其弟发生车祸需要进行紧急开刀,但邻近且适合执行此刀的医院皆无床位,家里希望刘小姐能动用自身的关系,为其弟挪移一张加护病房的床位出来,使其弟能尽快进行开刀。刘小姐确实动用自身关系,请求该科主治医生移走一名患者,使其弟接受开刀。基于仁爱原则的角度,亲亲造成的差等之爱使其动用关系挪出床位给其弟,但若考虑到“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那么刘小姐就不应该这么做。实则上差等之爱与推恩之爱存在着某种内部矛盾。(萧宏恩、姜月桃:《医护伦理:个案解析与探讨》,台北:高立出版社,2006年,第134—135页。)事实上,“仁爱原则”内容之建构落入中国哲学习以为常的传统建构模式,必须找到“仁”的人性本体论,再求修养功夫以养仁。一个原则的设立必然认为其能引导行动者进行更好的价值选择,并且提供可实际操作之方法与规则,使受引导者能有所本。反观现今“仁爱原则”内容更适当可运用于相关医疗、生命科学研究者等的伦理教育活动上,培养医护仁爱之心。但我们仍须反思,生命医学伦理问题不仅在于医事人员品格与行动之培养,更涉及各项生命价值选择的议题中,其作为一种原则,仍需作为道德抉择的一种行动指导方针,而不是一种高远的道德理想。因此,着重于思考“仁爱原则”的实践层面,使其面对医疗情境之可用也是“仁爱原则”所需补强的部分。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但他并未直接把“仁”视为人之本性。“仁”的实践方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论语》提出了“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论语·颜渊》)等三种行“仁”的方式。“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达到理想人格之修养方式,“爱人”是行仁的基本精神。“克己复礼”较强调对己身之修养,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展现出来的“忠恕之道”却更强调己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生命医疗相关场域,己身(医疗人员与利害关系人)需面对不同的对象,建构适当和谐的人间关系是更为重要的。
“忠恕之道”的提出者是曾子。曾子认为其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因此有了“忠恕之道”亦是孔子“仁”观念中重要的一环之说法。孔子自身并未对“忠恕之道”进行说明,充其量仅在《论语·卫灵公》中对“恕道”进行解释,即“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人逆推“忠”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庸也》)。现今对“忠恕之道”之诠解多元,但本文认为从“忠”与“恕”字源上之意义,以及《论语》本身的文本内在诠释可以提供一些视角活现“忠恕之道”作为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补充之必要。
“忠”、“恕”两字由孔颖达解释为:“如心为恕,谓之其己心也。”《周礼·大司徒》疏:“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忠”与“恕”字形为“中与心”、“如与心”。“中”于甲骨文字形为旗杆正中竖立,旗面飘扬。《说文解字》解为“内也”,《说文解字注》“内者,入也”。试想能竖立(站立)于正中者,必为主要之物。而“内”与“外”有别,内者是亲者,更为核心与重要者。换言之,“忠”对己身而言,强调“心之中”,内心重要的思考与想法、真诚地内心感受与思索,而非因受到各项外力影响所造成之想法。然而旗杆竖立于正中,是重要之物,亦可为当地之目标之物,具有特殊象征、精神指标之意涵。“忠”另一层面意味着是必须被追随的对象或象征。因此,“忠”一方面具有审视内心真实且重要地想法之意涵,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对象的追随与朝向。“如”从女从口,甲骨文字形象一人跪姿向言说之口。《说文解字》“随也”,徐锴曰“女子从父之教,从夫之命”,“如”意味着顺从。“恕”则可解释为随顺内心,审视内心之想法。一女子跪姿听人之言,意味着“恕”亦有随顺他人之言之意。因此,“恕”一方面强化随心,另一方面亦强调听从他人之言。由字源上之考察,“忠”与“恕”皆强化“心”的意义,而且是“己心”。更进一步推想“心之中”与“随心”皆隐晦地指出“人的主动性能力”,亦即“人之自主意识”,换言之,“忠”、“恕”字源意义强调人在进行行动前的内心运作、审视自身内在意识之能力。但“忠”、“恕”并非仅是对自身内心的审视与随顺,亦含有对外与他人、他物相连结之关系,并与他人形成一种追随与听从。实则上,“忠”、“恕”两者的运作皆强调对自身与对他人的双向运作关系,行动者具主动性能力,经过自身审视内心想法后,进行伦理判断形成行动之选择,然后将行动抛掷于外,成为与他人关系之建构。但“忠”、“恕”两者存在着对对象的一种服从。
在《论语》中对“忠”和“恕”的讨论相对于“仁”的讨论较为弱化。但孔子对“恕”进行了一种人文化的解释,让其成为所有人靠着自身修养而能所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由“己”作为生发,己身省视自身感受,并因同理他人而不将自己所恶之事推至他人。因此审视内在感受是重要的一环,但这里的审视并非仅对己身感受之审视,这个审视亦包含着周遭环境中的人、事、物投射于己身意识中感受,也因此“己”不仅仅是独活的自我,而包含外界环境所给出于我的“我的感受”,这是一个双向动态的结构交流,审视我的内心的同时,亦在审视你与我的关系,并且思索回应。正因为审视自身心中感受中有对象物所给出之物,那么行动者的决策行动就不仅仅是自我中心的仅只有自己,而有了对周遭事件的人、事、物的考虑,进而能进行更适切的行动方案。
“忠恕之道”并非提出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道德准则要求他人加以接受,或者受到规范之引导而生活,但其要求返回行动者主动性地内在审思,寻求行动者内在之自省能力,审视其内心真诚的想法。当然如前所述,这种考虑隐含着对他人感受之考虑,但其不仅希求行动者内省,更要求将内省的思真诚地为化为行动面对或协助他人。
“忠恕之道”的提出,一方面试图回应“施益原则”之缺失,另一方面将增补“仁爱原则”之实践方法。当然,儒家生命伦理学中“仁者爱人”之定义、“克己复礼”之行动皆不能抹杀,倘若不先培养“仁”之品格,培养“爱人”的情操,即失去医事人员、生命科学研究者济弱扶贫、善待万物之品格,因此以“仁爱原则”作为培养相关从业人员是伦理教育之大事。但我们仍须留意操作面向上之考虑,“施益原则”考察施益者施益的范围,但“仁爱原则”可透过“忠恕之道”提出对施益者内在之省察和推扩之力,让医事人员、生命科学研究者、医疗场域中之人经过慎思熟虑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道德判断继而行动,尽管这个判断可能存在着风险或者牺牲自己的成本,但那是属于行动者自身的行动选择。
五、结 论
本文提出以儒家“忠恕之道”回应“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忠恕之道”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忠”与“恕”字源意义下对内心之审视,更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所提出之我-他者之双向互动结构,其一方面强调我与外在环境之关系,另一方面强化了我-他者之关系与关怀,继而建基在爱人、关怀的前提下,拥有适当的行动、无悔的行动。行动者在行动中和他者相融合而失去了自我,但正因为失去了自我才更清晰地明白自己给出或牺牲之意义。因此“仁爱原则”更需补足此一实践与行动面向。
尽管有人质疑“忠恕之道”强调心的内在省察继而外推之功夫,并未实际解决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所遗留下来寻求标准、普遍规范的问题,严格来说,“忠恕之道”似乎也未能实际地给出相关从业人员或医疗场域中的人们一个道德抉择上的绝对方针,使其在临床方面获得具体的解决方法。但面对当前多变的社会环境,以及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个人,寻求一种绝对客观的普遍性实有难度。事实上,我们更该关心的是伦理行为的“共通性”(Communalizability),*Wei-ming Tu,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p.103.而“忠恕之道”回归人所共有之心作为共通性之基础,实际上正展现了一种人世间、建立在社群生活基础上的相对普遍性,在这种普遍性下没有死板的必然规范,有的是相对而不断调整且根植于己心而起于己行的人间之道。
B152
A
1000-7660(2017)05-0107-07
陈琼霞,(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西方生命伦理学四原则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对话与融合研究”(17kwpy66)
(责任编辑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