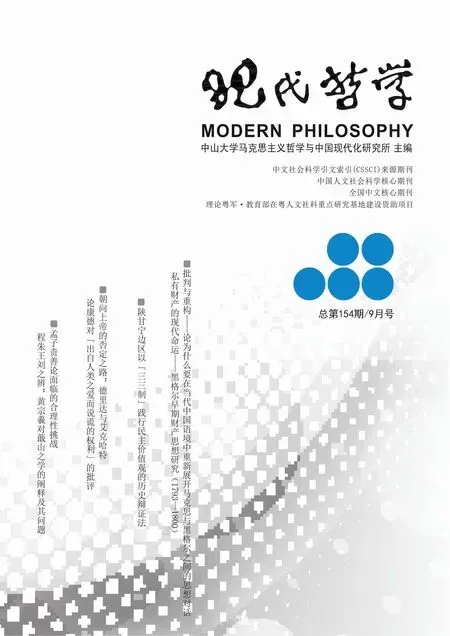作为超越的时间
——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如何为形而上伦理奠基?
2017-01-27林华敏
林华敏
作为超越的时间
——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如何为形而上伦理奠基?
林华敏
时间问题是列维纳斯他者伦理的地基,其核心是历时性(Diachronie)。历时性揭示了时间的异质性结构,同时也奠基了精神自我揭示和伦理的基本关系。历时性指出了时间的断裂与非连续:过去是不可追溯和不可弥补的过去,当下是不断破裂的瞬间,未来是纯粹的未来。时间作为一种绝对的异质性在他人的到来中进入意识,构成了精神全新的经验。关于他人的经验既是时间本身,也是基本的伦理事件。在无限的视域下,时间指向一种没有神的神学。不同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罗森茨威格,列维纳斯通过时间的历时性指出了一种精神与上帝关联的途径,而这个途径最后在伦理的他人那里获得了实现。
历时性;精神;他人;上帝
时间问题贯穿于列维纳斯的思想历程,其核心是时间的历时性(Diachronie)。如列维纳斯所说:“我最深的思考是关于时间的历时性,它支撑着我所有思考,我关于无限的思考——这种思考比关于有限的思考更早。”*E. Levinas, 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trans. Bettina Berg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xiv.在列维纳斯的思想进展中,对时间问题的处理是从内在性到超越(上帝)这个转换的核心枢纽。历时性概念渗透在列维纳斯整个思想脉络中,交叉在意识和伦理主题的讨论中,这些讨论最后都指向一种无神论的上帝(超越)。通过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时间的反思以及弥赛亚时间的整合,列维纳斯指出时间不是物理世界的客观结构,也不是意识的先验结构,它是无端的开端、超验性的开端。这个开端的最初产生,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本文拟就这个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围绕着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探讨其形而上伦理学如何从时间历时性这个基本概念中发生。
一、异质性的时间经验——时间的去结构化
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及“您现在作品主要的关注是什么”时,列维纳斯说:“我研究的根本主题是对时间这个概念的去结构化。”*E.Levinas,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trans. by Michael B. Smith and Barbara Harshav.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32.这个主题点明了列维纳斯对康德之后一直到海德格尔在时间问题上的批判和反思。康德将时间作为经验的基本形式;而到了黑格尔,这种时间形式辩证地与内容结合,获得了充实;胡塞尔时间构建也基于一种意识的基本结构(滞留、当下化和前摄的能力)。列维纳斯认为,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都将时间视为人类经验的结构形式,因此,对作为我思的统一体的时间的去结构化从伯格森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现代思想的问题。*Michael L. Morgan, Discovering Levni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20.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学生,他对时间的考察打破了胡塞尔的形式化。列维纳斯充分肯定了这点,认为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发展了柏格森早期的洞见,把时间理论发展为绵延的相互渗透的领域,揭开了“钟点时间”之下更深的结构——关于综合的“狂喜的”时间性,本质地与人的实践、知识、道德、在世、历史相连的时间,并且打开了存在者的揭示。*E.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xiii.海德格尔的时间考察也属于柏格森和罗森茨威格以来的“时间的去形式化”,*E.Levinas,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p.176.但是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并不彻底,它没有真正将时间引出存在总体。海德格尔虽然不问“时间是什么”,却通过“被抛”(过去)、“共在”(现在)、“先行”(将来)等概念试图以一种不同于度量时间的方式考察时间,以对此在的分析代替物理度量的方式来揭示时间,只是这种揭示始终没有摆脱“此在整体结构上的全体性”。即使海德格尔最终把时间延伸到了死亡经验,但列维纳斯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死亡之意义从一出发起就被解释成为存在于世之终结,消亡”*[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7页,第293页,第37页,第16页。“Levinas”被译为“列维纳斯”“勒维纳斯”,本文统一采用前者。。不同于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的“思想坚持‘从时间出发设想死亡,而不是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死亡出发设想时间。’死亡不再是成为可能性的虚无,而是虚无与陌生的暧昧——时间不再是存在的地平线,而是在与他人之关系中的主观性情节”*[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7页,第293页,第37页,第16页。“Levinas”被译为“列维纳斯”“勒维纳斯”,本文统一采用前者。。从海德格尔回溯至康德,列维纳斯认为“自始自终,本体论、存在与虚无的领会一直是任何意义的源泉。无限(它也许随着历时性、耐心和时间的长度接近思想)从来不以任何的方式被这一分析所暗示。自康德以来,哲学成了没有无限的终结性”*[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7页,第293页,第37页,第16页。“Levinas”被译为“列维纳斯”“勒维纳斯”,本文统一采用前者。。
列维纳斯时间考察的基本立场是超越康德以来的形式化的时间,将时间引向真正的本源和无限的时间。与海德格尔不同,列维纳斯指出“时间并非存在的界限,而是存在与无限的关系”,“死亡不是毁灭,而是必要的疑问,以便与无限的这一关系或曰时间得以产生”。*[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7页,第293页,第37页,第16页。“Levinas”被译为“列维纳斯”“勒维纳斯”,本文统一采用前者。在1947年的重要著作《从存在到存在者》开篇,列维纳斯就明确指出:“柏拉图置‘善’于存在彼岸的准则是引导这些研究的最概括也是最空泛的指南。这就意味着,引领一个存在者(existant)趋向善的过程并非是存在者上升为一种高级存在(existence)的超越行为,而是一个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的过程,是一种出越。”*[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这表明了列维纳斯思想的基本指向,也指出了他在时间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是时间考察的重要目的,而这个目的只能通过时间观的置换获得实现。我们知道,《从存在到存在者》阐明了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立场的基本差异:将每个具体的存在者从存在总体中实显出来,获得其独特的意义。这项工作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超越于存在(总体)的命运的时间经验。在第二年的著作《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进一步通过“他者”深化了这种超越:“时间不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的存在论境域,而是作为超越存在的一种样式,作为‘思’与他者的关系。”*E.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trans. by Richard A. Cohen,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7, p.30.对于列维纳斯,能够“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进而朝向善”的根本抓手是“他者”的时间。只有“他者”的时间才能打开“异于存在”的视域。在列维纳斯整个论述中,他将这种“他者”时间的论述转向了更为复杂晦涩的语境——“时间的历时性”。
“历时性”(Diachronie)是列维纳斯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有时为了与传统的用法区别,强调时间的异质性与断裂性,会采用Dia-chronie这一写法),多用于语言学符号学,与顺时性、共时性(Synchrony)相对,指事物(现象)的进程及其本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具固定性和稳定性;亦指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非共时性)。但是在列维纳斯的文本中,他寓于历时性这个概念丰富而晦涩的内涵:历时性描述了时间自身的异质性结构,“历时性如同是‘在同一个中的另一个’中的‘在……中’——而另一个还尚未能进入到同一个之中。古老得不可记忆者对不可预见者的敬重。时间既是这同一个中的另一个,又是这不能和同一个在一起、不能是共时的另一个”*[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第16—17页。。历时性也意味着精神和世界之间的“非构建”关系,它揭示了一种伦理的和启示(神学)的超越关系、所说(said)和言说(saying)之间的延异(踪迹)关系。历时性是“这样一种伦理的和启示的关系结构——他者的亲密性、无私、为他、所说之说”,“这种结构生成伦理和语言”。*E.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p.22.按照列维纳斯的看法,历时性这个概念始终与“不可包含者”(他者)相关联。*E. Levinas,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p.90.“历时性确切地描述了与绝对外在的东西的关系。”*E.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p.35.这种关系始终折射出意识原初的被动性以及对超越者的渴望(Desire)。
关于时间的历时性,首先要回到列维纳斯提到的两种时间:普遍历史的时间和历时性的时间。普遍历史的时间(顺时性的时间),也就是列维纳斯说的死亡的时间、总体化的时间,它是存在论的基础。“普遍历史的时间作为存在论基础持续着,在这种时间中个体性特殊的存在者失去了,它们的本质被计算和概括了。”*E.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 by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 p.55.这是一种同者的时间。在其中,个体命运是总体的一个环节,没有例外也没有惊奇。而历时性的时间是一种断裂的时间,一种非吻合的时间,它是“非一致性、驱逐自身的”*E. Levinas, 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p.xiv.,“要求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表明了受造者的极度分散与多样性”,它是“历史的总体化的连续——死亡时间所标志的——的破裂,是造物主安排在存在者中的一种破裂”。*E.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58.历时性“超越于所有永恒的在场之顺时性”*E. Levinas, Alterity and Transcendence, trans. by Michael B. Sm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pp.173-174.。“这一历时性——既相吻合,又不相吻合——或许正是超验性的特征。”*[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第263页。
以上引文表明列维纳斯对历时性概念的丰富而晦涩的使用。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语境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概念对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时间观的某种回应。首先,由于普遍历史的时间是存在论的基础,因此,历时性构成对海德格尔时间和存在论的一种回应。其次,分散与超越性也打破了胡塞尔的再现的时间经验。在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下,时间获得两个重要特征:时间不是水流,也不能被意识再现和主题化。“水流或潮汐这些用以解释时间的形象适用于时间中的存在者(etre),却并不适用于时间本身。时间并不像一条河流那样流淌。”*[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第89页。“历时性是这样一种结构,任何主题化和有目的的意识运动(记忆或希望)在它所建构的统一化中都无法吸收或填补这种历时性。自我的孤立的时间性被从未来和不可记忆的过去而来的不可预见的他人的来临打破。”*E. Levinas, 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p.xv.列维纳斯认为,时间是非连续和创生的,它无法被意识统摄进一个整体(片段)之中;过去和未来不是当下化(再现)能把握的,过去不是滞留的结果,未来也不容期待。“在最后的分析中,历史的时间的每个瞬间——在其中行动开始——是一种生产,它因此打破历史的连续性的时间——一种属于作品的时间而不是关于意志的时间。”*E.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58.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与历史之整体以及意识的主题化(意向性)决裂。时间经验不再是一个“整体”史的经验,也不是意向性的构造,它是关于不可预见的他人的超越经验。
我们知道,在胡塞尔那里,意识以一种基本(先验)结构将过去和未来当下化,同时赋予过去和未来以意义。列维纳斯通过时间的历时性指出:“(时间)的历-时性,历时性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单纯的破裂,而是意味着一种在先验统觉的一致性中找不到的无私和调和……意味着背叛它。”*E.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p.118.列维纳斯指出,通过计算和历史,时间的历时性被聚集在当下和再现中。*E. Levinas,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p.165.但是,“未来的历时性……与前摄并不是一样的”*E. Levinas, Alterity and Transcendence, p.36.,“过去之历时性位于时间的具体性的底部,它不能被集合到再-现(现在在场)”*E.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p.112.。由此可见,过去的流逝和未来的来临不附着在先验的主体结构(胡塞尔)中,时间经验的意义也不是先验的意识结构所赋予的。
在《历时性与再现》一文中,列维纳斯强调了时间的超越(外在)维度。过去是不可追溯的过去,总是在我(意识)介入的每个瞬间前已经在那儿。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过去,它无法被我们设想为“曾经的”在那儿。过去是一种无法推卸的“在”。未来,则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未来,是一种总是要应对(Response)却无法把握的临近,也因而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无限)责任(Responsibility)。因此,关于时间的经验是一种关于绝对不可把握的外在性的经验,这种关于外在性的经验内在于我们与陌生性相遇的经验中,这就是生存的时间性。通过陌生性与他人的关联,列维纳斯进而将时间(历时性)作为人与人关系的节点:“历时性——超越于所有永恒的在场之顺时性——是我和邻人(准确地说从我到他人)之间不可逆转的(或无私的)关系的节点,这种关系不可能是顺时性,并且同时是无私的,如同辞别,已经是一种爱。”*E. Levinas, Alterity and Transcendence,pp.173-174.在这里我们看到列维纳斯通过历时性概念揭示了时间的展开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向度:作为他人不可回忆的过去及其不可期待的未来。历时性的特征坐落在了他人身上:自我无法记忆他人经历过的事件;当他人从未来向我涌来,以一种不可根除和不可还原的差异的时间性与自我相遇时,自我既不能预见也不能期待面容的意义以及它作为责任的命令。任何主题化和意向性的意识运动都无法同化这种在他人身上所展现之时间历时性。
二、时间历时性为伦理奠基
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列维纳斯指出时间对存在论的超越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向一种比存在论更古老的伦理学”*[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第二版序言,第3页。。“超越存在之诘问,所得到的并非一个真理,而是善。”*同上,第11页。对此,理查德·科恩也曾指出:“(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这两位哲学家通过对时间和感受性的仔细分析开创他们完全不同的视角:在海德格尔那里是终有一死的和焦虑的存在者,在列维纳斯那里是道德的和服从的责任者。”*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 xiv.这表明了列维纳斯时间考察的伦理指向。而问题的根本在于时间如何与伦理关联并奠基伦理?
列维纳斯是如何理解伦理学这个概念的?在《上帝·死亡和时间》中,他这样界定伦理学:“伦理学是与他人、与下一个来者(其临近不应该跟空间意义上的一种相邻关系相混淆)的关系。‘下一个来者’,它首先强调了这一关系的偶然性特征,因为他人、下一个来者就是第一个来临者。这一关系是一种临近性,即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第158—159页。这个界定中,列维纳斯指出了伦理学内在的时间线索,“下一个来者”既是他人,也是未来。“时间-他人”这个关联一直位于列维纳斯思考的中心。1946年到1947年的以《时间和他者》为题的讲座中,列维纳斯直接点明了:“时间不是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存在的存在论视域,而是作为存在之外的形态,作为‘思’与他者的关系。”“时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主体的成果,而是与他人之关系的结果。”*E.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p.30, p.39.可以说,时间命题直指伦理,或者说时间在列维纳斯的讨论中,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中才能真正超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伦理的缺失”)。在列维纳斯那里,这二者的关联是通过主体性概念获得的,因为正是因为真正的时间(非物理的)的存在人才能从一般存在物中分离出来,作为伦理的存在者。主体性与时间密切关联。我们知道,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甚至于在奥古斯丁时间的灵魂转向)中,时间的内在化就已被明确提出,时间和主体性的关联也不是新的议题。对于列维纳斯,他所提问题之重点不在于时间和主体性的构成之间的关系,他要提出的是:时间的他者指向所包含的“时间-他人-主体”这个逻辑关联。在这个关联中,主体性看似问题的中心,实际上问题最后的落脚点是“他者性构成主体性”。也就是说在逻辑关系上,主体与时间的关联是通过他人(时间的历时性)而完成的,进而凸显出在主体性问题上他者(伦理)的关键地位。正是在这个路向上,列维纳斯那里的时间内在化进程才走出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讨论,时间的内在化才最终开显出外在性的视域。
相较于胡塞尔,主体性对于列维纳斯是个纯被动性问题,这个被动性最终发端于时间的历时性——不可追忆(古老)的过去和绝对的将来(陌生)对于意识的某种“迫近”。在胡塞尔那里,主体的在场是我作为我自身而在场,其他东西的存在都是从“我”这里被构建起来的,自我成了他者的主宰。列维纳斯通过历时性经验否定了自我对他者的在场性控制,在他者对意识的进入过程中,主体性是纯被动的。时间是自我和他者(未来)的特殊关系,未来不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东西,它不能被人所设定。*Ibid., p.79.因此,我们和未来的关系是和异质性的关系,和一种根本地外在于我的东西的关系。“和他者的非常的关系是和未来的关系。”*Ibid., p.77.这种关系是超越的,它是“没有关系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无限的张力和模棱两可性:未来绝对地外在于当下、外在于我,不能再现也不能期待,那么又如何与当下,与我发生关联?这是列维纳斯的“没有关系的关系”晦涩与困难之处,也是笛卡尔那里“自我包含无限”、“多寓于少”问题的核心。
但是列维纳斯没有沿着笛卡尔的思路往下走(去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是将这种紧张而模棱两可的超验关系落实(具体化)到了自我和他人身上。当下和未来的关系通过主体间的关系得以建立。“未来进入当下并不是主体自身得以完成的,而是通过主体间的关系。时间的条件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Ibid., p.79.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他人,时间是无法成其为时间的,时间经验就无法获得;反过来,如果没有历时性,与他人的关系就会被纳入到同一性的整体中。时间性(temporality)的本质是他者性(otherness),而他者性的核心在于他人的异质性。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与伦理关联。通过这种转换,把未来置换为他人,从而实现“绝对的未来——他人”的转换。可以说,如《时间与他者》的标题所揭示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他者,进一步地,就是他人;时间的历时性对应于他人的异质性。
《时间与他者》构成了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一种背离式的呼应:通过以他者的时间代替存在论的时间,列维纳斯打开了时间的伦理维度。时间作为“‘思’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存在论关系,也不是认知关系,而是超越关系。“与将来的关系,未来的在当下的在场,在与他人的面对面的关系中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面对面的境地才是时间的真正展开;当下对将来的进入并不是主体独自的成就,而是主体间的关系的成就。时间的条件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或者说,在历史之中”*Ibid., p.79.。将来的临近是一次基本的伦理事件,这个伦理事件是他人的亲临(proximity)以及随之而来的我对这种亲临的回应(response,或者说是“责任”)。正是在这个亲临和责任中,主体性才被构建起来。“时间——在其耐心、长度和等候中——并不是一种‘意向性’,不是一种终结,它属于无限性,并且在对他人的责任中显现出历时性(dia-chrony)。”*E. Levinas, 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p.81.对于列维纳斯,他人不是现象,而是“世界”现象的中断。时间发生在绝对不在场和在场之间。*王恒:《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177页。来自他者时间之中断打破了世界现象(显现)的连续性,带来了瞬间无休止的绽出以及意识对这种绽出的回应。
这种回应是无限的。回应总是对不可回应的回应。当下不断绽出,将来无法预期,过去永远无法追溯。在时间中,别人的一句“你好”、“再见”是永远无法同步的,永远无法真正“在场当下”回应。它与我是不同时的,甚至于不可追忆的。这使得我的回应,我的回答“你好”、“再见”永远只能是之后和没有回应的。德里达在列维纳斯的悼词中提到一件事:他与列维纳斯通电话时,列维纳斯在说完每句话或者每句话还没说完时,都会“喂、喂”(allo, allo)地问个不停。“他似乎在每个瞬间都担心被挂断,担心沉默或者消失,担心那个他所呼叫和通话的他人的‘没有回应’,伴随着在每个句子之间(有时甚至是在一个句子中间)不断的‘allo, allo’。”*Derrida, Jacques, Adieu to Emmanuel Levinas, trans.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9.与他人的关系预设了一次无限的分离,面容所显现出来的无限的打断,当另一次中断在死亡的片刻降临而更加无限地把第一次分离化作空虚,在中断的深处又有一次破碎性的中断。这种中断是向谁发出的,又是何时发出的?*Ibid., p.9.这是他者时间的核心问题,也是人与人之间伦理-时间的深渊。在这种中断之间,伴随的是一种伦理焦虑。在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时间)中,这种不同步(中断)是永远存在的,“对方”的回应永远在下一刻,“此刻”和“下一刻”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伦理的焦虑——不断的“allo, allo”来填补,而这种焦虑却永远无法把对方拉到同一个时间“当下(在场)”里。“通过以间断性、和总是重新开始性,也即将‘自身延异’意义上的‘历时性’当作时间性的基本界定后,真正的‘他’‘人’就(或才)一同呈现了。有了他人,才有责任或回应意义上的主体。”*王恒:《列维纳斯的他者:法国哲学的异质性理路》,《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8页。这是主体在时间中走向伦理的根本机制。
历时性打破存在与思的束缚,他人进入了时间的核心。时间的真正意义在于绝对的新奇(他人)的进入,这个意义远远超过对此在的领会(海德格尔)和意识的赋意(胡塞尔)。对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不论是存在还是意识,始终有一种自身同一性。但是,真正的时间——他人的亲临——打破了这种同一性。在历时性中彰显着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取消他者的异质性,但是确保了他者对“思”的非排斥性。“时间不是永恒的堕落、下降,而是与不允许自身被经验所吸收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不可被同一化,绝对的他者——的关系;或者是与不允许自身被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自身是无限——的关系。”*E.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p.32.这是一种与不可见之超越者的关系,一种介于“伦理-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他人或上帝(绝对他者)进入意识”与“未来进入意识”这两个事件是伦理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同一事件。列维纳斯称这种关系为“一种没有条件的关系,一种没有等待对象的等待,一种无法满足的愿望”,它是“一种距离,也是一种临近”。时间因而是一种彻底的伦理范畴。时间既是当下(瞬间)的凝聚(实显)和创造(出离),也是未来进入当下(自我)的不可抗拒和不可把握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面向他人的面容中得到实现。列维纳斯指出:“被理解为朝向绝对他者的无限的超越的时间的运动并不会在流俗的方式上时间化,并没有与意向性的光束的直接性相似。它的显示的方式,以死亡的神秘性为标志,通过进入与他人的关系的伦理冒险而实现了一种迂回。”*Ibid, p.33.
这个过程是没有任何预知和止境的,“他者”的进入是一个纯被动的过程,即使是最后的死亡也不是终点(预期)和完成。“并不是如海德格尔所想的存在的有限性构成了时间的本质,而是存在的无限(构成了时间的本质)。死亡的宣判并没有指向存在的结束,而是作为一种未知,这种未知悬搁了权力。间断的构造——它使存在从有限性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呼唤死亡。间断的虚无——一种死亡的时间——是无限性的产物。复活构成了时间最初的时间。”*E.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 284.对于主体而言,复活不是瞬间的完成,而是下一个瞬间的开端,是他人的介入打断了意识的自我沉醉,从而使得自我中心主义被打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不是因为瞬间的机制使得未来(他人)的来临成为可能,而是因为未来(他人)的到来使得瞬间被打破,下一个瞬间才到来,时间才得以构成。
这里,我们发现列维纳斯时间阐述的真正内核:时间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内在构建的;它是一个事件和行动——意识与绝对陌生性(他人)的相遇。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了,意识的暗夜(睡眠)才能被打破,继而存在和世界才能开显。这是一种本源的时间,之后才有“物理”和“再现”的时间。在列维纳斯时间考察的基本框架中,存在、意识、瞬间、过去、未来、复活(创造)、弥赛亚的末世等,这些概念都共同地指向那个活生生的他人(陌生人、邻人),指向任何一个我们可能遭遇到的面容。时间不是最后的审判,而是每个瞬间的完成与开始,每个瞬间对他者的责任。时间是“一个同者到他者的运动,这个运动永远不会回复到同者”,但它又不是完全朝着一个虚无的方向的运动。*Mark C. Taylor(ed.), “The Trace of the Other”, in Deconstruction in Context: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rans. by Alphonso Lingi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348.而如同《从存在到存在者》开篇提到的,这个指向必然地回到了柏拉图的“最高的善”,统一于那个绝对的外在者“上帝”。
三、结语与余论
“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的千古之问道出了时间问题的困境。从列维纳斯思想发展的轨迹看,时间本身不是其主旨,却是他思想运思的地基。在20世纪60年代,伦理、价值、主体性和普遍性被质疑(上帝之死与主体之死)的背景下,列维纳斯却坚持谈论伦理与主体性。这种坚持对其后法国哲学乃至欧洲哲学中伦理的恢复具有重大意义。在列维纳斯前后,许多思想家从物理时间(外时间)到心理时间(内时间),从存在到上帝等多维度探讨了时间,却较少有人将时间问题转为伦理(价值)问题讨论。在根本上,列维纳斯通过对时间重新描述了人类的基本经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验。他将时间与伦理关联从而拓展了时间与伦理议题的视域和内涵。列维纳斯要寻求一种他者的时间,一种不同寻常的时间——用列维纳斯的话说是“另类的时间”。*Sead Hand (ed.), The Levina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9, pp.80-81.这样一种另类的时间包含着在存在与意识(意向性)之外,列维纳斯对精神和生命(个体)独特的理解:时间经验不是关于时间本身的经验,而是人类生存的经验。人类的生存之所以是具有时间性(temporality)的,是因为它始终指向那个没有开端和结束的超越(无神论的“上帝”),那个我所无法预知和承担的他人。对于精神而言,精神的意义在于新的经验(而不在于主动地去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而与他人的遭遇是所有的经验中最独特与新奇的,也是最为平凡而常见的。恰恰是这种经验构成了主体性的意义、精神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如果说生命是时间的另一种表述,那么生命便是“新的经验”,是异质性、陌生性的不断进入,不断构成“我”的新的经验。没有新的(陌生差异的)东西进入意识,意识是死亡的,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列维纳斯,意识无法自我构建和自我赋意。过去、瞬间与未来正是在其不可回忆、不断的断裂以及绝对的陌生中给主体性提供了绝对不可把握(规约、划归为整体)的内容和意义。而这个过程在与他人(邻人、陌生人、弱者、寡妇等)的现实遭遇中获得具体的实现和效应。
时间是一种超越。在罗森茨威格那里,这种超越通过个体与上帝的关系获得了实现。列维纳斯同样也主张时间的绝对超越,只是这种超越同时具有深刻的伦理性。通过“时间-他者”的转换,我们意识到精神的内在性不能构造起时间性本身,只有当这种内在性不断被打破,时间性才获得意义。意识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意识的当下或者活着的生命(living life)的内核。胡塞尔及传统认识论的意识之光,由内而外的一种光照被打破,这个打破是惊醒,甚至于是惊厥,而真正能够引发这种打破与惊厥的是他人。他人作为另一个活着的生命,他(她)是不可追溯的过去(总是已经在那儿的),他(她)的经历(时间)是我所无法经历的,也是绝对的未来(不可期待的)。列维纳斯的时间考察充分揭示了,对于人的存在,时间和伦理并不属于两个事件,它们寓于同一个事件——与他人面容相遇。这个事件的不断发生才使得精神构成精神,才获得一种“活着”(living)。他人的进入是一个完全的新奇的事件,同时也是一次冒险事件,如同德里达所描述的“绝对的好客”所携带的危险性。但是,对于列维纳斯,精神的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未知性及其携带的冒险性,这是精神走向新的境地,发展与延伸的必要条件与内涵,也是时间的根本意味。
B565.59
A
1000-7660(2017)05-0078-07
林华敏,哲学博士,(南宁 530004)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列维纳斯现象学神学转向研究”(13CZX055)
(责任编辑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