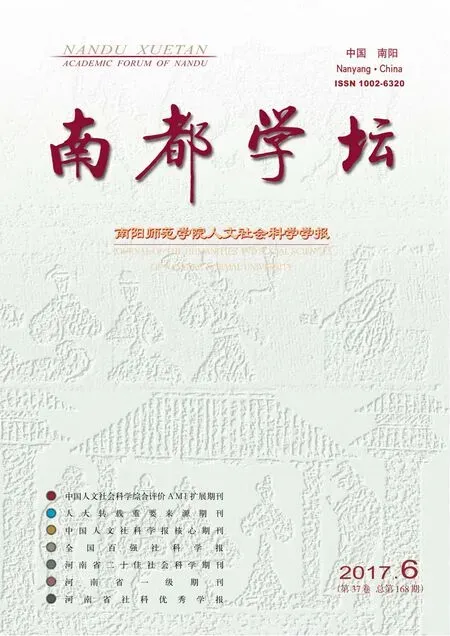从体制性依赖到行政化脱钩: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研究
2017-01-27尹广文
尹 广 文
(华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9;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0)
从体制性依赖到行政化脱钩: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研究
尹 广 文
(华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9;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0)
我国的行业协会在改革开放兴起之初,即为政府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的结果,深深地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其发展往往体现为身份的官民二重性、资源的体制内获取、管理的双重体制、发展的整体性依附等体制性依赖。而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较大依附于现行体制的行业协会,开始通过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和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等举措,实现着行业协会治理的行政化脱钩改革。当前乃至后续一段时期内,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发展将呈一种急剧推进的态势,呈现出诸多新的发展趋向。
体制性依赖; 行政化脱钩; 行业协会; 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大量的行业协会商会开始涌现出来,从1982年的几十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到2016年底形成7万多个全国的行业性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年增长率超过了11%[1]。作为市场经济形态下行业发展的一种结社形态,不论是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还是法德的指导性模式,抑或日本的政企合作模式,行业协会往往被看成是解决“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和“政府失败”*“政府失败”是指政府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的有效路径,成为企业连接市场和政府的桥梁和纽带,能够补充和升华企业的“私序”,进而影响甚至转化为社会的“公序”[2]。而中国行业协会的兴起,则更多源于市场的催化和政府管理职能转型这一双向互动博弈的结果,从当初对由市场发育而起的各类企业及其联合性组织所进行的“按行业组织、按行业管理、按行业规划”的行业协会建设,到之后行业协会在体制内增长和体制外发育,乃至当前全国各地行业协会组织的体制内存量转型和体制外的大量增生,“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关系始终是中国行业协会发展中面临的最核心、最普遍、也是最为困惑的问题”[3]。
围绕中国行业协会这种典型的发展特征,行业协会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尤其是行业协会的治理问题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议题。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组织在90年代初便已进入学界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视野,英国学者格登·怀特对浙江萧山地区行业协会的研究开启了中国社团研究的先河。之后余晖关于行业协会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关系判断,尤其是其所提出的行业协会对社会“公序”形塑的作用问题,对我们认知行业协会的既存具有较大的意义[2];朱英对行业协会的制度和变迁史的考察,也向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行业协会发展与国家的关联性[4];王名等人的《行业协会论纲》则较为全面检视了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问题[3],郁建兴等则从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入手,核心关注于行业协会的监管问题[5]。当前在社会治理的话语背景下,中国的行业协会也面临着一系列治理的实践转型,尤其是2015年8月国务院《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出台,亟需学界针对行业协会的治理问题进行体制创新的理论探讨,这也就成为本研究介入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研究的核心议题和价值追求所在。
一、中国行业协会发展概述
行业协会(Industry Association),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行业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发起的以保护和增进其会员企业合法性权益,具有行业服务性和自律性的社会团体组织。行业协会是一种介于国家权威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其发展成熟往往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与国家政府的权威监管间博弈的结果。作为一种独立的法人团体,行业协会兴起之初,便被深深地植入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夹缝里,呈现着行业协会的自主性、互益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特征。
最早的行业协会出现在中国的春秋时代,《论语》即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之记载,史景星就提出先秦时代行会被称为肆,汉代史籍中谓之“行列”“市列”[6];到唐宋则称之为“行”,加藤繁在《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中提到,“从唐代中叶以后到宋代中叶以后市制崩溃的时代,同时也是商业组织的行发展的时代”[7];而至清末民国初,则是各类商会组织的兴起,据一些史料统计,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的商会达到了2000余家,全国除西藏等个别地区外,几乎都存在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商会组织[8];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商联等社会组织改造浪潮的涌动,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销声匿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行业协会的兴起,则是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大量的行业协会才真正发展起来。按照民政部的相关统计数据估算,当前全国性和地方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多达7万多家。行业协会已成为反映行业诉求,保护和增进行业合法权益,有效沟通各类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考察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不论是封建社会的官僚化特色,还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买办性特征,抑或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官民二重性组织,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其在发展中行业自主性与国家政府监管性之间的一种关联。即一方面是各类同业企业之间寄希望借助行业协会的组织化形态,保护其合法权益,增进其合法化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政府寄希望于借助行业协会能够实现对各类企业“私序”的更好控制和管理,以使其“私序”提升或转化为社会的“公序”。当前我国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正处在一个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大量体制内生成的行业协会的发展转型和体制外行业协会的增量突破,传统的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组织治理需求。2015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及其之后民政部所确定的“2015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名单(共148家)”,即是对这种发展现实和治理需求的回应。可以说,行业协会的治理转型,将成为当前乃至后续一段时期,我国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重心,也是当前乃至未来学界有关行业协会研究的核心之所在。
二、行业协会治理转型——从体制性依赖到行政化脱钩
行业协会的治理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各类同业企业的自组织与自由市场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一种关系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组织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对下既要监管和约束同业企业,也要保护和服务于同业企业;对上则既需反映行业的诉求,以较好沟通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形成推动同业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也需要配合政府监管和督查,以保证同业企业活动的合法有序性。我国的行业协会在改革开放兴起之初,即为政府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的结果,深深地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其发展往往具有较强的体制依赖性特征。而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较大依附于现行体制的行业协会,已普遍出现政会不分、管办一体、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创新发展不足、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亟需对其现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现行业协会发展的行政化脱钩,进而推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的建立。
(一)体制性依赖:双重管理体制下的行业协会治理
体制性依赖,即我国的行业协会往往发育于国家主动的空间让渡,成立之初就牢牢依附于体制内资源并通过行政化方式以获取此资源,在日常的活动中又呈现出国家政府较强的行政性监控,具有较为明显的“官民二重性”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国家法团主义管理体制。在行业协会的现实发展中即表现为:身份的官民二重性、资源的体制内获取、管理的双重体制、发展的整体性依附等。
1.身份的官民二重性。官民二重性,即意味着行业协会的构成具有“半官半民”的二元结构,组织的行为受到行政机制和自治机制的双重支配,协会的运作往往依赖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渠道去获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种资源,以满足社会和政府的双重需求,因而协会的活动领域也只能是社会和政府共同认可的交叉地带。受传统的政府一元化主导行业、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多行业协会的设立往往源于政府的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型,是计划体制下行政全能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另一种延生,即把全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以一种“有限让步”的方式转嫁于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组织[9]。而在行业协会的具体运行中,其展开逻辑则呈现出了较强的变动性和过渡性特征,往往是政府的行政权力通过市场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实现了对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行动主体——企业的控制[10]。但在日常具体事务处理中,行业协会则又作为一个自治性的社会组织被“监护型管控”着,依然延续着登记准入上的“双重管理体制”,资源提供上的“政府财政拨款依赖”,具体运营上的“泛行政化趋势”,服务内容和人员配置上的“行政性指派”,服务成效评价上的“指标形式化”等民间社会组织在中国既存的现实境遇。行业协会这种身份属性的官民二重性特征就其实质而言,反映出来的则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型的不充分,也表征着当前行业协会发展的不成熟和不自主。
2.资源的体制内获取。中国的行业协会从一开始成立便是在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生成的,体现出了较强的“政企分开”取向,而不是企业自主需求特性[11]。相比较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实行的“统购统销”的管理策略,国家对体制内生成的行业协会则采取一种间接的管理方式,即通过业务主管单位进行企业发展的行业化管理。业务主管单位一般是正式的行政性政府部门,其对隶属的行业协会的指导依然是一种具有较强行政干预、命令性的管控。这种管控在现实中则往往通过登记要求、人员安排、经费垄断和职能配置等方式促使行业协会贯彻执行。与此相对应的是行业协会要寻求设立和发展,则必须依附于业务主管单位,以方便从现有既存体制内获取各类行业协会生发之所需资源。于是,我们看到在行业协会的发展现实中,诸多行业协会均争相挂靠或直接把其办公机构设置于其业务主管单位之下,要么联合办公,要么争取成为事业编制;行业协会也往往会主动承接其业务主管单位或某些具体的政府部门溢出的行政职能,进行授权式或委托式管理和执法;各类行业协会为了能够获得国家或地方的财政拨款,也往往采取与业务主管单位相混杂的资产财务制度;同时大量政府工作人员或离退休老干部也供职或兼职于行业协会组织,等等。这种行业协会发展的资源体制内获取的策略,短期内看似有助于行业协会的生成发展,长此以往则会使行业协会完全沦落为政府的附庸,进而丧失其作为社会组织的独立自主之本质特性,最终损害着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3.管理的双重体制。行业协会作为同业企业间的一种联合性、自组织性社会团体,其管理体制依然沿袭的是我国在1950年和1989年所制定的社团管理条例基础上,于1998年《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正式确立的国家对社团的“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体制。行业协会的这一双重管理体制依然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企业”传统的全能国家管理体制的延续,其实质是方便各业务主管单位通过行业协会来保留对所辖地区同业企业的干预和控制[3]。按照现行的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分级设立、双重管理、限制竞争构成了目前我国行业协会管理的典型特征。这种不同层级协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方式,以及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加之“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竞争性发展,共同塑造了当前行业协会发展的瓶颈。首先,在双重管理体制下,诸多体制外生成的行业协会因要么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其实大多行政部门也不愿意做其业务主管单位),要么因其自身的注册条件不足而无法达到注册标准,处于非法运营的“黑户”状态。其次,即使已获准注册登记的行业协会,在协会的组织运行中,登记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往往因部门的利益化,存在具体监管的权力真空,呈现出一种只注重事前监管,忽视事中和事后的约束和规制。最后,限制性的竞争策略,看似是为了更好地培育和发展壮大本就羸弱的行业协会,实则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行业性垄断,反而不利于新兴同业企业的发展。
4.发展的整体性依附。行业协会既生发于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型的空间让渡中,又不得不寻求体制内的资源以获取发展的条件,同时受双重管理体制的约束,使得我国行业协会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依附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协会组织获得依附单位资源、关系方面的庇护以寻求发展,但可能不得不以让渡部分自治权力作为交换。这一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组织三方博弈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社会行业协会发展的典型特征[12]。在这里,政府通过对协会严格的准入登记和直接的业务主管单位指导管理,实现了行政权能在同业企业的延续,规避了社会管理的政治风险,但也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行政程序和工作成本,造成行业协会现实发展中蕴藏的权力寻租和垄断性竞争的存在。而行业协会则往往会为了获取更大的体制内资源和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刻意迎合其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喜好,丧失其成立之时作为行业自治和自律的自组织的初衷,进而影响到其具体管理和服务中的组织权威和行业影响力。因此,依附式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大部分行业协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现实路径,也是协会组织发展的条件与动力所在。但是“依附”也可能成为行业协会发展的障碍,因为作为交换的自治权力的让渡,既可能造成压抑行业协会发展的过度外部控制,也可能钝化行业协会组织的自主发展能力,造成行业协会的依附性地位和体制性依赖,最终影响到行业协会的功能发挥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壮大。
总之,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行业协会的兴起源于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型所催生的结果,行业协会的生成之初即被打上了深深的体制内烙印,在身份属性上具有了官民二重性特征。而在协会组织的发展中,为了寻求更多的体制内庇护和发展性资源,行业协会往往依附于业务主管单位,在迎合和承接中实现其行业性协管功能。这种登记和管理的双重体制,保留了全能国家对企业的管控型指导,其实质则是通过分级设立、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方式,实现着政府对同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和控制。最终也造就了行业协会整体性依附式发展,当前我国行业协会治理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根源于这种“依附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性依赖的管理体制机制。
(二)行政化脱钩:现代行业协会组织治理体制的建立
行政化脱钩,即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中,通过继续加大政府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型的改革力度,理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组织的职能边界,明晰二者于同业企业发展的功能界限,促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这种行业协会与政府行政机关的脱钩,具体到行业协会的发展实践中即表现为:行业协会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和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等方面*参见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
1.机构分离,以破除官民二重性身份。即取消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以保障行业协会独立平等的法人地位。这种通过对政府、协会和市场的重新定位,促使“是政府的留给政府、是协会的还给协会、是市场的放还市场”三方互动格局的实现[12]。对政府而言,其不再是协会及其所代表的同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的干预者和管理者,而是经济活动主体的保驾护航者和服务提供人,这一转变既是对“小政府、大社会”型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转型助推,又通过授权式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扩大了政府对同业企业的整体性控制。对行业协会而言,通过消解其政府代言人和附庸者的依附状态,还原其作为同业企业利益代表者的主体性身份,既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化监管效能,也重塑了行业协会作为纽带桥梁性社会组织的本质性特性。对同业企业而言,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下,行业协会筑起了一道个体化企业与强大政府之间的纽带关联,成为其可信赖和依托的代言人和保护者。总之,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机构分离改革,破除了协会组织的官民二重性身份尴尬,真正实现了行业协会设立之初衷和形成之目的。
2.职能分离,以还原组织本质特性。即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的职能,剥离出协会的泛行政化之不当赋权,突出其监管服务之本质特征。行业协会在本质上是服务于企业和市场的互益性社会团体,其基本职能是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反映在行业协会实践中便是围绕“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各种功能性发挥[3]。但在改革开放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具体现实中,不管是官办主导还是民间自发的协会组织,都往往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职能,形成了一种对上(政府)依附对下(同业企业)行政化命令的错位性职能配置。这种职能性错位既是全能国家管控经济社会发展传统的延续,也反映出我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在一定意义上行业协会的行政化职能看似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组织及其所代表的同业企业的监管,实则既削弱了行业协会于企业的权威性认同,也降低了其存在意义的合法性认知。因此,行业协会与政府职能分离改革,能够重塑协会组织服务于并代表着同业企业之组织化既存的本质特性,既扩大了行业协会存在的合法性认同和权威性影响力,又在客观上实现了政府对协会组织及其同业企业的有效监管。
3.资产财务分离,以达至组织自主自立。即行业协会资产财务的单独核算和独立管理,以真正从源头上实现协会组织与业务主管单位的行政化脱钩,进而实现行业协会的自主和自立。行业协会内部的管理虽然有一套较为正式的理事设立和会员资格限定的明文性规定,但其资源来源除了较少的会员会费,主要的资产财务还是源于政府的专项财政支付。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业协会资源的体制内获取方式,使得大多行业协会不得不依附于业务主管单位之下,以便通过自主身份的部分丧失来换取更多的政府财政直接拨款。而对政府(主要是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而言,既然行业协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行业主管单位便需要对协会组织的资产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和管理。为了方便起见,诸多业务主管单位干脆把协会组织的资产和财务一并纳入本单位的统一预算和管理之中,造成了行业协会与业务主管单位之间资产财务混乱,进而产生诸多问题。因此,只有实现了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资产财务分离,才能真正达至组织的自主自立。毕竟,行业协会自治自律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协会组织的独立自主地位的确立与自治能力的加强,而这些总归取决于行业协会是否有自己一套充盈的资源保障以及独立健全的资产财务制度[13]。
4.人员管理分离,以消解权力寻租和隐性腐败。即保持行业协会从业人员的主体独立性,杜绝政府工作人员或离退休老干部供职或兼职于行业协会组织之现象,实现行业协会人事和管理制度的自主性和法治化。按照民政部2015年制定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不设置行政级别,不得由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公务员兼任。这一专门针对行业协会人事制度的规定以正式的法律法规形式呈现,确保了行业协会的人事自主权,也消除了国家公务人员继续染指行业协会的可能性。这种行业协会与业务主管单位之间人员管理的分离,将有助于消解因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政府机关领导干部插手或直接进入行业协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所掌握的权威性资源进行权力寻租的可能,也将从源头上杜绝行业协会为寻求政府庇护或获取更多资源,而与一些政府的领导干部或在职公务人员进行利益交换的可能。因此,赋予行业协会独立自主的人事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斩断行业协会与业务主管单位之间的垄断性联盟,以消解政府的权力寻租,破除行业协会的隐性腐败[14]。
5.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以实现组织有效监管。即行业协会的党建、外事、人力资源服务等事项与原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单位脱钩。在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协会组织既受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民政部门的监督,又受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专业管理部门的监管,但在行业协会的现实运行中,具有登记准入权限的民政部门更多承担着一种资格审查和事前监管的职能[15]。这种审查和监管对官办行业协会几乎只是一种形式,却把大量体制外生成的民间行业协会排除于合法性之外,难以形成行业协会发展的增量式增长。而就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而言,也存在对依附于其业务主管单位成立和运营的行业协会监管的形式化,对自主运营的民办协会组织压制性管理。双重管理体制看似严格,然其对行业协会发展的事中、事后监管的忽视,以及具体监管过程的形式化主义,都会造成权力的真空。因此,通过行业协会与业务主管单位之间党建、外事等事项的分离,将能够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组织中党组织的作用,也能够更好调动社会力量和协会会员的主动性,以实现协会组织更有效的监管。
总之,当前我国的行业协会正处在一个从体制内存量转移向体制外增量突破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各类行业协会组织依然延续着“依附式发展”模式,呈现出较浓的官办色彩和政社不分特性,造成协会组织自主性的不足和自治力的缺失。因此,如何通过政策倡导、法规制定和实践探索,推动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完成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机构分离,以破除官民二重性身份,职能分离,以还原组织本质特性;资产财务分离,以达至组织自主自立;人员管理分离,以消解权力寻租和隐性腐败;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以实现组织有效监管等,这些将成为当前乃至后续一段时期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行业协会发展的趋势与瞻望
随着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及其随后相关职能部门10个配套文件的陆续出台。按照《总体方案》的部署,“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工作由民政部牵头负责,2015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试点,2016年总结经验、扩大试点,2017年在更大范围试点,通过试点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后全面推开”,“各省(区、市)同步开展本地区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工作”。当前乃至后续一段时期内,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发展将呈一种急剧推进的态势,呈现出诸多新的发展趋向。
(一)政会脱钩、管办分离将成为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的发展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已明确提出要“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以发挥行业协会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协同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大主体中,政府实施宏观管理,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行业自律自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管理。作为一种市场主体为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以集结而成的组织化形态,行业协会本质上是一类非政府、非营利性同业企业自组织。但我国行业协会的兴起往往是脱胎或转化于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调整,具有较强的官办色彩,造成行业协会政会不分、管办一体,其结果是形成了行业协会的依附式发展,成为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延伸,严重偏离了其作为同业企业利益代表者和权益维护者的设计之初衷。政会脱钩、管办分离是我国当前社会组织治理改革的方向,更是行业协会急需进行治理转型调整的根本性出路。通过政会脱钩,在行业协会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和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中,还原行业协会自主自立自治之本真面目。通过管办分离,破解双重管理体制下行业协会发展滞后的诸多困境,实现其协同治理真正之功能。因此,基于当前行业协会的改革实践,政会脱钩、管办分离将成为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的发展方向。
(二)项目制政府购买服务将成为行业协会新的资源获取方式
2013年9月26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及其后广东、北京、江苏等地的试点实践,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当前诸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社会多元参与治理的一个主流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中,政府通过“授权”式的“外包”或“购买服务”等方式,以项目为载体,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既实现了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也改变了政府向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资源的决策方式,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由内向外的以社会公众需求为驱动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体制。社会组织则通过对服务或项目的承接,既获取了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又实现了组织非营利性、公益性的价值追求。可以说,项目制社会组织治理不仅表征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的新的体制设置和运作机制。行业协会作为我国社会组织治理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项目制政府购买服务将改变协会组织单一依附于政府资源,破解行业协会从资金财务源头上的附庸性,进而真正切断行业协会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项目制政府购买服务将成为行业协会新的资源获取方式。
(三)现代组织治理体系建构将是行业协会自身建设的主要内容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成为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现代组织治理体系构建既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之一,也是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理想的行业协会组织建设应该是既能够发挥会员大会、理事会、监理会和秘书处等主体的主动性和活力,又能够实现彼此之间的分权制衡和协调配合,以激发同业企业会员的参与热情和认同归属,从而提高协会运作的效率和决策的民主化,最终保障和维护同业企业的合法权益,实现行业协会的宗旨。为此,行业协会的组织建设应做到协会章程规范明晰、治理结构民主有效、活动过程合法有序、监督管理公开透明。首先是行业协会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章程制度规范,即根据协会成员授权以制定规则,并能将这些规则强制实施于成员授权之范围内的组织化制度设计;其次是行业协会民主有效的治理结构,既能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又能实现彼此的分权制衡;再次是行业协会活动过程的合法有序,即确保协会组织活动的程序正义合法,活动结果公平有效;最后是行业协会公开透明的监督管理机制,以保证会员企业的利益,扩大组织的权威认同和社会影响力。
(四)服务性自治组织建设将是行业协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行业协会的本质特性即在于其对同业企业会员的服务性和自律性监管,作为一种介于国家政府和市场企业之间的第三方治理的制度设计,行业协会往往被赋予诸多的职能,2000年国家轻工业局曾将行业协会职能概括为17项之多*参见2000年3月1日国家轻工业局《关于行业协会管理的暂行办法》之具体规定。,学者康晓光则从“非营利组织”角度归纳出了行业协会所具有的代表、沟通、协调、监督、公证、统计、研究和服务等八大基本职能[16]。虽然在我国行业协会实际的运行发展中,大部分行业协会因其官办色彩或依附性特征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之存在功能,进而造成行业协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的现实困局和发展难题。但当前随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各地行业协会治理改革探索实践的创新突破,行业协会的自治性和服务性将进一步突出。毕竟,行业协会的产生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下,同业企业寻求互益性发展的结果,也是政府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型的客观衍生之物。因此,如何在处理好行业协会与国家政府、同业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在行业协会从体制性依赖到行政化脱钩的治理转型中,通过现有行业协会组织自身建设,以促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1]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统计数据[EB/OL].[2017-04-30].http://www.gov.cn.
[2]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1):70-119.
[3]王名,贾西津.行业协会论纲[J].经济界,2004(1):71-76.
[4]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9-140.
[5]郁建兴,沈永东,周俊.从双重管理到合规性监管[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报),2014(4):107-115.
[6]史景星.行业协会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4.
[7]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37-369.
[8]社会部.人民团体统计[M].民国刊本(复印本).重庆:社会部统计处,1946:1.
[9]贾西津,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2-120.
[10]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与案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1-18.
[11]余晖.我国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08(8):31-39.
[12]郁建兴.行业协会:寻求与企业、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118-123.
[13]宫宝芝,赵倩.我国行业协会自律功能的缺失与拓展[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36-40.
[14]黎军.行业自治及其限制:行业协会研究论纲[J].深圳大学学报,2006(2):75-78.
[15]孙春苗.行业协会管理改革的比较研究[J].中国非营利评论,2008(2):114-129.
[16]康晓光.行业协会何去何从[J].中国改革,2001(4):34-36.
[责任编辑:张天景]
FromtheInstitutionalDependencetotheAdministrativeDisconnection:ResearchontheGovernanceTransformationofIndustryAssociation
YIN Guang-wen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063009, Chin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0,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industry association was the result of government’s restructuring of institu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s, so it has double identities of government and people, access to resources within the system, the dual system of management, and the integrity dependence of development. At pres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new normal of economy”, the larger industry associations attached to the current system are realizing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disconnection of industry association governance through the separation of institutions, functions, property and finance, people management, party construction and foreign affairs with government’s functional departments. Today, even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 will show the trend of a sharp advance.
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administrative disconne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2017-09-06
尹广文(1979— ),男,甘肃省崇信县人,华北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吉林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
C912
A
1002-6320(2017)06-008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