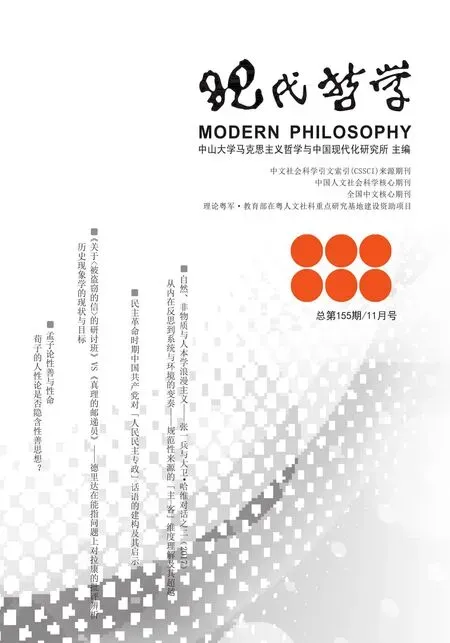走出视觉霸权,洗耳恭听世界
2017-01-27张聪
张 聪
走出视觉霸权,洗耳恭听世界
张 聪
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承诺,“视觉中心主义”肇始于古代希腊的科学与哲学主张。而作为一种人类的生活方式,“视觉霸权”是一个特殊的近代事件。“视觉霸权”助长了单一的理性控制权,将我们带入消费至上的碎片化、增殖化的商业世界,注定要扭曲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真实感知。因此,走出“视觉中心主义”,突破“视觉霸权”,端正视听关系,让我们能够通过“洗耳”而聆听世界,无疑是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听觉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在沟通神秘世界、形成文化共同体以及塑造政治力量等方面,人类听觉本身有着视觉器官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视觉中心主义;视觉霸权;听觉文化;洗耳恭听
一、我们真的需要终结视觉霸权吗?
自古以来,视觉与听觉的关系就是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从自然史的角度看,视觉与听觉都是我们感受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不同的方式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能力互有短长,只存在互补与相互强化的问题,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但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自古希腊先哲开始,视觉优先与视觉至上的主张就已经占了上风。此后,诸感知能力视觉就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和支配性的能力,美国西北大学哲学系教授迈克尔·莱文认为这就构成了人们所说的“视觉中心(ocularcentrism)范式”。*David Michael Levin,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在此基础上,自现代性展开以后,现代人进入一个“视觉霸权”(Hegemony of Vision)的时代。*Ibid., p.3.这是说自人类进入近代生活以来,以古腾堡印刷术的发展为标志,我们进入了阅读与视觉的时代。这一主张为当代理论家麦克卢汉、韦尔施等人的研究所强化。
显然,视听关系是一种流动发展、交互凸显的过程。一般认为,“视觉中心主义”是在希腊这个特殊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关于视听关系及其在希腊的发展,德国美学家韦尔施认为“最初,西方文化根本不是一种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但它首先得变成视觉文化。希腊社会起初是为听觉所主导的”,而“视觉的优先地位最初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初叶,进而言之,它主要集中在哲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声音理论家谢弗同样认为“在西方,耳朵让位于眼睛成为最为重要的信息收集者,那只是文艺复兴前后的事,是伴随着印刷术跟透视画法的发展而发生的”*R. M.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Rochester, VT: Destiny Books, 1994, p.10.。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视觉中心主义”是古代希腊以后的事情,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视觉霸权”或者视觉至上模式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视觉霸权”与现代性的展开密切关联,与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密切关联。
麦克卢汉追随经济史家、传播巨匠伊尼斯的研究,把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演进用“部落化-非部落化-新部落化”这一著名公式予以概括说明。在遥远的《荷马史诗》时代的前现代部落社会,人们的生活是游徙不定的,在文字滥觞以前,信息的传播主要来自部落间成员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以口语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模式所倚重的主要是人类的听觉器官。由于这种前现代的部落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的限制,因此,人们需要特定的声音标志——比如那些时时回响在大地上的部落号角和悠远鼓声——来区分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地域传统,同时唤起部落成员之间的心灵共鸣,最终成为联结部落历史的直接的、现实的经验纽带。从5000年前文字的发明到近代电能的发现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人类进入了依赖文字的书面文化时代。相对于部落时代以听觉为主导的、有机的、流动的、发散的、包容的感知方式,文字(特别是拼音文字)的抽象性与连续性,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感性因素悉数剥离,使得现代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开始严重地单纯依靠视觉的聚焦、透视和分割,这必然导致除视觉外其他感官功能(如听觉、触觉和味觉等)的削弱,并使得人们迅速从口语时代声音共鸣的魔力中、从部落共同体的情感痴迷中解脱出来。而电能时代的到来,则使麦克卢汉看到了走出单纯依靠视觉的新希望。
在麦克卢汉这样一种社会发展史的纵向讨论之外,关于视听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条思考线索。这条思考线索首先体现在宗教生活中,其次也体现在哲学共同体内部。这个思考线索的突出特征,就是将人类视觉对外部世界的观看,以及听觉对外部世界的倾听,与宗教生活与文化生活关联,并最终将其与其寻求人生的真理密切关联起来。在此意义上,上述争议点就转化为:如果我们要认识外部世界,尤其是要认识人生的终极真理,到底是应该依靠视觉,还是应该依靠听觉?
问题一经这样的转化,视听关系的竞争性一面就马上凸显出来。自古以来,在多数文明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定见:视觉是幻觉,而听觉才是真理的来源。但也有“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世界观。由于视觉在人类生理上具有先天优势,其对“光”有着积极反应,自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开始,西方人便将“真理”“理念”“认知”等与视觉紧密相连,认为视觉是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莱文讲到的希腊哲学传统,就特别突出地发展了视觉与真理关联的维度。及至启蒙运动,代表理性与真理的“光”成为带领人类走出“黑暗”“混沌”以及愚昧的天窗。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不仅仅在词源上与视觉之光(light)紧密契合,其所倡导的对神性的“祛魅”、对真理的“揭蔽”等,更多的是要倡导以“理性之眼”、以视觉的隐喻来获取对理性的最大认知。康德甚至把视觉看作是人类诸多感觉中最高贵的一种,因为“它在一切感觉中离直觉的最局限的状态即触觉是最远的,而且不仅在空间内包括了知觉的最大范围,而且也是最少感受到器官的激动的(否则它就不是单纯的视觉了),因此它接近于一种纯粹直观(没有明显的混杂感觉而对给予对象的直接表象)”*[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在康德看来,视觉是最客观、最纯粹、最能到接近真理的感官方式,但这种对视觉的高扬,也无可避免地将人类的其他感官(如听觉和触觉)排斥在理性之外。
但是,不论是在哲学共同体内部,还是在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中,一旦与真理问题关联,视觉与听觉谁才是中心的问题就变得不是那么清晰了。例如,基督教明确宣示的是“太初有道”,也就是说真理在语言所传达的信息中,需要通过倾听来获得。而当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区分“可闻的道”(audible Word)即宣讲的道与“可见的道”(visible Word)时,见与闻的关系就变的更加复杂。路德的区分关联着整个西方宗教传统中另外一个更为深远的传统,那就是认为上帝是隐匿的或隐秘的。“隐匿的上帝”的主张意味着人类无法至达上帝,至多可能通过听来的“道”与之接近。当然,更为激进的教派进一步主张,人类连听闻“道”的路径也是得不到保证的,世俗的事功并不必然为上帝所恩赏,世界是一场偶然的事件。在哲学共同体内部,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批评古代希腊以来的视觉中心的形而上学,尝试开拓听觉与真理之关系的新路径。
如此看来,“视觉中心论”的确是某些特殊的人类文化中的特殊的形而上学假设,而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视觉霸权”也的确只是近代以来的特殊现象。我们的分析只是要表明,在逻辑上,视听关系天然复杂,不同主张依赖于不同文化的特殊发展。在这样的表述中,作为文化现象的视觉霸权的确构成了近代技术化以来的特殊现象,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种近代现象,是与近代以来的印刷技术、电视技术的大发展密切关联的。大批思想家对这种霸权的社会批判有其针对性。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才可以清楚认识到,走出“视觉霸权”,重新诉诸我们的听觉能力,何以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走向。而在什么意义上需要彻底走出视觉与诉诸听觉,则仍有存疑。这也就不难理解,莱文何以忐忑地追问道:“要想改变这个世界,就真的需要终结视觉霸权吗?”*David Michael Levin,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3.
二、视觉霸权,霸道在哪里?
所谓“视觉霸权”或“视觉至上”,指的是人们大多通过视觉的方式、甚至仅仅依靠视觉的方式来获取对外界的认知或感受。从前述对西方哲学话语中的“视觉中心主义”的梳理可以看出,将视觉与人类对外界的认识,进而将视觉与理性思考模式紧密联系甚或等而视之,从而对视觉及视觉文化的研究客体进行单向度的阐扬,是西方社会文化的基本范式。随着近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展开,随着印刷技术、半导体技术、晶体管技术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当这种范式在当下社会愈演愈烈,以致形成理性主义和视觉霸权之后,现代人对视觉中心主义作出批判性反思就在所难免。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还是后现代思想家的消费社会概念,无不体现出现代思想家对视觉霸权现象的文化反思。“视觉霸权”有其缺陷,总结当代思想家对“视觉霸权”缺陷的批评,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分别加以阐明。
首先,以视觉为主导的文化模式趋向一种单向度的、以主体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使得主体与外在世界严重割裂,视觉经验不可避免地遮蔽人类其他的感官经验。由于过于偏执于理性的、目的的、工具的认知功能,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为一种支配的、核查的、控制的文化模式。
在古希腊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风采翩翩却傲慢执拗,当他在山野徘徊之时,小仙女厄科(Echo)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由于被天后施了魔咒,小仙女纵有千言万语却无法向美少年倾吐爱慕之情,只能简单地重复后者的话语,说出几句回声。那喀索斯循着回声见到了厄科,却以儿戏的态度弃绝她,掩上耳朵飞奔地逃走。厄科羞愧难耐,从此藏身林木之中,形容枯槁,最终化为一缕回声。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为了惩罚这个傲慢的少年,让他爱上了一个永远无法得到的形象——他自己的倒影。当有一天那喀索斯俯首一池清水并无意看见了一个美男子的形象,从此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镜像”。“他望着自己赞羡不已。他就这样目不转睛、分毫不动地注视这影子,就象用帕洛斯的大理石雕刻的人象一样。”“他不知道他所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是他看见的东西,他却如饥如渴地追求着。”*[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1页。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日日流连湖边,对其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痛苦异常,终于消逝了青春闭上了双眼,憔悴而死。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在自己的作品中特意提到该故事,认为这一古老的神话宣示了“视觉的致命性”:“因为那喀索斯唯有当他鄙视小仙女厄科,那纯粹语音的神秘化身,不愿意来‘听’,才成为那要命的视觉幻想的牺牲品。”*[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19页。在韦尔施看来,那喀索斯冷漠拒绝“Echo”的行为是一种隐喻,表明在“视觉至上”原则下听觉遭受“贬斥”的致命后果——只专注于看,而盲目对待听,最终将毁灭自己。
韦尔施将视觉文化看作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他认为,正是理性与视觉的合谋,才使得现代社会中包括建筑、音乐等各种文化门类无一幸免地转向视觉,本着对“可测度性”的尊崇,变得同质而单一。反之,由于视觉天生地关注那些持续的、固定的客观对象,远距离的观察与凝视必然使这种感官方式在与世界发生关联时,处处以“主人”的姿态对世界进行核查、把控和支配,人与世界的关系逐步变得紧张且对立。现代监视制度的应运而生便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子。韦尔施援引并扩展了杰里米·边沁“圆形监狱”的构想,认为圆形监狱是欧洲惩罚制度的典型范式。监狱中央所透射的光越明亮,就会有越多地监视和控制。“视觉至上和监视社会携手并进”,“彻底透明的社会变成彻底监视的社会。”*详情参见[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19页。现代社会大街小巷布满了监控镜头,是为“天网”,现代互联网技术又使得我们的几乎每一项消费都可以在大数据信息终端得到分析与汇总。我们生活在一个彻底透明的社会中,几乎变成没有阴影的透明人。新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与便利的同时,相应地也越来越突出地促使我们思考个人的隐私权以及公共权力应该如何得到有效监督等伦理与政治问题。
其次,以视觉为主导的文化,是一种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客观性以及抽象性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中,主体的感性经验逐渐被剥离,仅仅依靠序列性的、肢解化的、专门化的心理模式与外在世界发生关联。
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是麦克卢汉。在他看来,拼音文字的出现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应用给现代人带来的断裂,不仅表现在除视觉以外其他人类感觉被遮蔽以及共同体的衰落那么简单。由于其无意义的音素以及无意义的视觉符号所带来的双重抽象性,拼音书写为读者提供了抽象、分析、分类、编码和解码等一系列模式,继而在读者的潜意识里发生效力,“促进了分析(每个词分解为基本音素)、编码(口语词用视觉符号编码)和解码(朗读时这些视觉符号又还原为语音)”*[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1页。等思维特征的形成,而这种逻辑上的连续性逐渐影响到现代人的社会模式和心理模式,现代人往往抱着一种相当疏离超脱的态度,以一种“客观性的迷思”来面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部落时代的那种极富内聚性和凝聚力的社会形式慢慢被肢解分割,以专门化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思想最终全面占领社会。而由古登堡研制的印刷技术继而又将这种线性的、序列的、理性的、因果关系的视觉空间的感知模式进一步推向极致,“印刷术的发明对应用性知识新型的视觉倚重重新进行了确认,并使之延伸,提供第一个同样的、可重复流通的‘商品’、第一条装配线以及最早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第321—322页。。简言之,麦克卢汉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所出现的抽象性、专门性、碎片化、过度理性化等诸多弊端,均看作是西方世界自文字发明之后极度偏重文字和视觉的后果。
第三,在以视觉为主导的文化模式中,由于主体对视觉经验的过度依赖,致使视觉文化的客体——图像——出现过度碎片化、疯狂增殖化的倾向,现代人的审美也逐渐趋向浅表化、拟像化、符号化,主体的文化建构则以满足视欲幻觉为第一要务。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图像借助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将自己成功渗透进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代表“理性之光”的视觉中心主义发展到极致。按照当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对现代社会的哲学反思,西方社会进入到以影像为先导的“景观”时代。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德波认为在现代社会,丰腴的商品借助电子媒介疯狂积聚,致使社会各个层面都以表象的形式呈现,商品作为“物”的基本属性被“影像”取代,而视觉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优先性和至上性。“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汇成一条普遍的河流……世界影像的专门化,发展为一个自治的影像世界。景观在普遍意义上是生活的具体颠倒,因此,它是非生活的自治运动。”*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Press,2002, p.7.之所以称其为“景观社会”,在上述这一层意义之外,德波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景观的观看之中,人们对“影像”产生了发自内心的依赖而时时趋之若鹜,都妄图通过对影像的区别和选择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实现自我的主体价值。但按照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的观点,人们对影像看似自主的选择,不过是在后者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的一种幻觉,其实质依旧是依照资本逻辑对“景观”的霸权统治表示认同并心甘情愿接受其支配。
20世纪大众传媒技术的日益更新,促使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进行了最为有效的结合。借助解构主义、符号学等的最新理论成果,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入解剖,将德波的理论再度向前推进。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将物的符号化推向极致,出现了以“拟像”“仿真”与“超真实”为标志的社会文化危机。当形象、符号挣脱了意义、真实、深度的束缚获得新生,日常生活成为对“无原型”的象征性的模型加以模拟化的过程,真实和拟像之间的界限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变得模糊不清,“社会也因此消失了,各个阶级之间、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各种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告内爆”*[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内爆从根本上导致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世界的诞生,“我们进入了……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世界。即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鲍德里亚真切地感受到在消费社会中,在视觉显示张力的时代,主体陷入了由形象、景观和拟像所构成的超真实世界中,个体麻醉的意识开始处于形象和景观浸润的迷幻状态之中,并把对物品符号的欲求作为生存的至上原则,而真实的“现实”已经无处寻觅。
三、洗耳恭听,我们能够获得什么?
随着现代西方思想界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批判,走出视觉霸权的桎梏,弥合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分裂鸿沟,继而恢复人类整体感性经验,成为现代思想家们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对此,不同的研究者选择了不同的关注点,继而给出不同的出路。有学者仍旧寄希望于视觉,力图在视觉的理性认知维度之外补充进感性的直觉经验。例如,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代表人物阿恩海姆就通过科学的证明和阐释指出,在效能上,视觉思维的过程经由“抽象、分析、综合、补充、纠正、比较、结合、分离、在背景中突出”等步骤,最终达到主体对外在世界的积极探索、本质把握。简言之,主体运用视觉的感知方式对外界事物进行整合以及建构,这一过程既包含理性的分析,也包含感性的直觉。因此,视觉行为本身即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活动。也有学者干脆提出“触觉转向”,认为相较于视觉,触觉因其直接性、在场感、行动性、交互式等特点,能够使得我们更真实地把握世界。这种感觉取舍上的此消彼长,使现代人的感官经验选择不免陷入一场全新的“五官争宠”的犹疑不决之中。本文认为走出视觉中心主义,恢复现代人整体感性经验,不妨特别着重诉诸于我们的听觉,或者更准确地说,诉诸于以听觉为主导的、多种感觉形式互动互补的、开放的、流动的新型文化样态。
在这里,我们特别推荐以加拿大音乐家、声音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R.M.谢弗的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需要洗涤我们的听觉(Ear Cleaning),恭听和谐世界的完美华章。谢弗借用古代希腊人对音乐的理解,认为日神代表的是外在声音,代表着神示的宇宙和谐,“在日神的音乐观中,音乐是精准的、静翳的、数学的,关联于超验的乌托邦主张与诸界之和谐”*R. M.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Rochester, VT: Destiny Books, 1994, p.6.;而酒神的音乐观是一种非理性的与主观的。谢弗的整个工作就是围绕着日神的音乐观展开,提出“世界声音景观工程”,主张通过有意识有步骤的音乐训练,清洗我们的耳垢,重获对世界的清净倾听之禀赋。*See ibid., pp.4-12, pp.208-211.中文的“洗耳恭听”可以非常完美地表达谢弗的这一重要提议,其核心有二:第一,重视我们的听觉禀赋;第二,倾听世界的自然和谐。谢弗的这一主张是最近几十年来发端于西方的回归听觉的文化研究潮流之代表性主张,该研究潮流有时也被称作“声音文化研究”*关于“声音文化研究”及其研究重点之差异,可参见Michele Hilmes, “Is There a Field Called Sound Culture Studies? And Does It Matter?”, American Quaterly, 57.1(2005), pp.249-259.,已经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的文化研究领域。
在走出“视觉霸权”的过程中,“听觉”之所以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觉的基本特点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关心问题就是:洗耳恭听,我们能够获得什么?
首先,听觉是人类所有重要感官中最具前沿性的感官,可以与其他感官“协同作战”、互动互补,在感知互通的基础上形成丰富的、多层次的整体感性经验。从生理学意义上讲,人类的耳朵没有一种类似于眼睛的“耳睑”,人类的听觉是关闭或打开声音世界的首道大门,除非完全入睡,否则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决定自己听什么或是不听什么,也无法主观屏蔽外部世界的任何声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感觉史研究专家马克.M.史密斯形象地将听觉比喻成为“人类感觉的前哨”*Mark M.Smith, Introduction, in Hearing History: A Reader, Athen,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4, p.Ⅺ.,用以描述听觉在人类整体感知中的前沿性。史密斯的感觉史受到加拿大声音学家R·M·谢弗的深刻影响。在谢弗看来,“倾听是远距离接触的一种方式”*R. M.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Destiny Books, 1994, p.11.,听觉正是因为其前沿性和灵敏性,可以在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知觉的过程中营造出一种声音背景,在此背景基础上,听觉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与其他感觉相遇交汇,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最终聚合成为人类的社会性,对那些可以被听见的动态的事件生成进行知觉,从而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
其次,相较于以图像为主导的视觉,以声音为主要对象的听觉更具备观念性上的优势,因为“声音”具有强大的暗示和启迪作用,与社会现实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听觉文化在沟通神秘世界、形成文化共同体以及政治力量的塑造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对于不同的听觉文化、声音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在视觉文化的观察研究之外,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状况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探察脉络。
当代西方听觉文化研究者多分别选取不同的声音形式作为分析对象,尝试通过“声音”这一“表现和外在现象”来触摸社会内部存在的本质意义。例如,法国新文化史家阿兰·科尔班就选取19世纪法国乡土社会的“钟声”作为聚焦点,分析“钟声”在与非基督教文明的对峙中如何一步步失去丰盈的意义而走向贫瘠,从而对法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进行思考。*参见[法]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科尔班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感知模式,人们开始不再关心钟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先前由弥漫在乡土法国上空的神圣钟声所牵引出的心灵共同体也随之崩散,法国社会最终走向世俗化与革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米丽·汤普森在其《现代性的声音风景》一书梳理20世纪早期美国现代听觉文化史,将对声音的研究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相统一。汤普森充分借鉴了科尔班以及谢弗的研究方法,认为“声音景观,一如视觉风景,归根到底,与人类文明而不是与自然界更相关。正因为此,它不断地被建构,并总是处于变迁中”*Emily Thompson,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1900-1933,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4, p.2.。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不同文化共同体对声音的不同处理方式或组织方式给出不同的文化历史解释,以彰显其特殊性,继而进一步追问:不同文化的处理方式意味着什么?不同的听觉主体所身处的文化系统有何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
最后,耳朵不像眼睛那样聚焦、透视和分割信息,因此在听觉文化的关系中,主体在接受并处理外部世界的听觉信息时,需要进入一种沉浸式的、全神贯注的虚静境界。同时,听觉的客体则永远处于优先的地位,主体在客体面前,总是处于一种“虚怀若谷”的倾听或聆察的状态。这种主客体之间的浸入式的、融入式的传递与接收信息的模式,可以有效修正长期以来视觉中心主义所形成的那种咄咄逼人、核查监管、控制支配的文化模式。在韦尔施看来,听觉所关注的对象较之视觉总是短暂和缥缈的,那些一经发出的声音,只能经由主体专心致志的接收聆听,在其内心萦绕。而这种“萦绕”总是反向地循着声音的发生过程、与之相关的事件生活反溯,推动主体重新“聆察”客观的世界和周遭的生活。韦尔施曾援引海德格尔的观点:“听觉文化将加深我们对他人和自然的关怀;它将推动学习,而不是纯粹颁布法令;融会贯通、网络状的思想形式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它距听觉文化从一开始就较传统的逻辑切入要接近得多。它整个儿就是充满理解、含蓄、共生、接纳、开放、宽容——以及贝伦特所能推出的其他一切好听的属性。”*[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10页。
因此,本文认为在以听觉为主导的文化关系中,擅长倾听的主体可以凭着自身网络状的思维方式,进入并探察到某些曾经被忽略或是被遮蔽的东西,这种幽微地进入和悉心地探察也就使得主体与外在世界形成一种接受的、交流的、尊重的相处模式。因此,听觉文化也就成为韦尔施等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成为突破现代审美平庸泛滥、实现后现代多元化与异质性的有效路径。
四、借力电子媒介,端正视听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麦克卢汉还是韦尔施,他们一方面倾力呼唤要“进行一场听觉的革命”,另一方面也都客观承认视觉在人类生活中相对于听觉的优先性,原因在于我们关于外界世界的认识首先依赖于“看”,眼睛所接受到的信息往往具有先入为主的先天优势。麦克卢汉与韦尔施所批判的并非视觉本身,而是现代人对视觉的过度倚重、对听觉以及其他感觉的遗忘与默然,他们所担心的是“视觉的类型学刻写进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行为形式,我们的整个科学技术文明”,他们所谋求的是“我们人类如何应付我们的感觉影响到我们其余的自我存在以及我们作为整体的世俗行为”。*[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12页。也就是说,他们批评“视觉霸权”,但并不是在否定视觉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视听关系问题,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视与听,在其自然属性上,本是一种互补关系,也是一种谁离开了对方,就有残缺与遗憾的关系。只是在特定的文化叙述背景下,视听关系才被转变成一种竞争关系。因此,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强调的,在讨论听觉文化研究时,辨析混淆、以正视听非常重要。
对现代人而言,应该如何勘定视觉与听觉的边界呢?应该在何时观看,又应该在何时“聆察”呢?佛教经典中有“盲人摸象”的故事,众盲倚重自己的触觉来力图复原大象的样貌,追求整体,这才有“如萝菔根”“如箕”“如床”“如瓮”等大相径庭、令人啼笑皆非的探求结果。故事虽然荒诞,但当一种感官提供了其他感官不能提供的感受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倚重此一感官,它所提供的信息也理所当然成为我们感受外在世界的主要来源。正是基于此,我们才看重不同感官的独特贡献。
较之盲人摸象的古代社会,后现代社会高度差异化,现代人的思想主张以及审美趣味越来越多元纷呈,想要确切地勘定不同感官的明晰的边界也越来越困难。这种明确的差异化态势从理论上决定了并不存在一个我们主观构想中的整体的、理想的声音世界。“面对来势汹汹的视觉审美化,不应当强求一种大一统的听觉风格来作为补充,或示为平等的证据!”*[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31页。因此,我们所说的走出“视觉霸权”,洗耳恭听世界,主要目的是要在大众文化日益走向异化拜物的当代社会,从主体感觉的分裂和文化生产的趋同现象着手进行分析,探索一种以听觉为主导的、全息整体的、各感官相互交融的、感性的个体接受外部世界的方式。而这种充满个性的、多元的、异质的、流动的后现代文化特点,不仅与现代性前后相继,而且其本身即是现代性的诸多表现之一。那么,如何将作用不同特性各异的“五官”统一起来,从而构建(同时也是回归)一种全息整体的文化样态呢?麦克卢汉与韦尔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为听觉重振起雄风的电子媒介,认为相对于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下的视觉至上主义,正是电子时代唤醒了耳朵的回归。
电力时代之前,信息的传递总是由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辐射,总是从相对丰富的中心,传向信息相对贫瘠的地区。然而电力时代到来后,电子媒介通过编码和解码等程序,突破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等限制,“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宛若音乐的周遭环境或无穷的宇宙”*[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46页。,使人们在媒介的帮助下重新享受“部落时代”的“面对面”交流。这种由电子时代的听觉主导空间并不只依靠耳朵这一种感官,视觉乃至其他感觉仍然至关重要。由于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多重限制,使得那些惯常于时间中消逝的“飞掠的、转瞬即逝的、偶然事件式的存在”,与那些可以在空间中持续的、永久的存在一起,经由各种感官都被人们感觉到。韦尔施看到,电子媒介的新技术不仅仅只是为“促进民主、节省人类生活创造新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将真实与虚拟很好地结合,“通过多媒体的意识延伸……虚拟经验同样伸向味觉、嗅觉、触觉领域”*[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35页。。韦尔施借用波德莱尔的术语来描述电子媒介对人们日常经验的革命性影响,而这恰好是麦克卢汉“媒介延伸”理论的要旨所在。正如谢弗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尽管我有时把听觉与声音景当做纯粹的学科来加以处理,但是我并没有忘记,听觉只是诸多感觉器官中的一种。我们已经到了走出图书馆,走进生活环境之原野的时代了。”*R. M.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Rochester, VT: Destiny Books, 1994, p.12.
认识到“视觉霸权”的弊端之后,重新诉诸听觉并不意味着要从现有的视觉中心向听觉中心全面转换,也并非要用听觉文化完全替代视觉文化,而是要突破理性主义的桎梏,同时又警惕“本体反转”,防止在刚刚克服了“视觉中心主义”的弊端之后,又走进一种“听觉中心主义”,不过度纠结具体感官及其功用的边界勘定,而是以一种“虚静待物”的谦卑姿态,发展出一种以听觉为先导的、多种感觉形式共通共融的、感性审美的、开放流动的文化样态。谢弗反复强调,耳朵、眼睛、心灵与头脑都是我们感受人类生活的重要器官,无一可以偏废,也无一需要特别强调自身的优先性。唯因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听觉以及与听觉相关的文化,听觉才有了相对于我们的特殊性。*See ibid., pp.10-12.
然而,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享受置身不同电子世界中的感官快感,而主观思考以及情感接受却无法跟上电子处理器的瞬息万变,于是,一种对于缓慢的、自足的、无法重复的非媒介的自然经验的重新渴求就悄无声息地与日增长。“在电子潜能与日俱增的喧嚣世界中,不可再现的一个时刻和一次相会,其独特性正再次被我们重视起来。一只美丽的手,一双漂亮的眼睛,愈益叫我们欣喜不尽。我们在回忆那些简单行为的自在自足的完美,一次散步、一餐饭食、一片风景,以及孤居独处,摆脱了传媒,摆脱了一切传播机器的孤独。当然,对这类行为的重新发现和新的评价,不过是在抗议一个由传媒决定的世界的背景及其浮躁心态。”*[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59页。我们被廉价的各种电子噪音包围得无法喘息,我们心中更为怀恋“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的幽婉惆怅,当我们漂浮于无边的地球村里的电子符号海洋,我们耳畔响起的常常是与我们个体独特经验紧密相连的“吴侬软语”或是“乱弹秦腔”。电子技术的无所不在和无一不能让我们不得不开始追求另一种在场,而这种追求恰恰引申出对现代人听觉以及听觉文化的强调,除了要将听觉文化理解成为宏大的、可以从根本上让现代人改变自己与外部环境的感受思考方式之外,听觉文化同时还关乎现代社会听觉领域本身的培育以及调整。对电子媒介时代逐渐受到戕害的听觉环境进行改善,对不必要的噪音进行消除,对无法避免的声音用心设计使之独具特色,也应当成为克服“视觉霸权”之后重新诉诸听觉,“洗耳恭听”的应有之义。
B089
A
1000-7660(2017)06-0107-08
张 聪,河南镇平人,文学博士,(天津 300071)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第60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的听觉文化研究”(2016M600183)
(责任编辑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