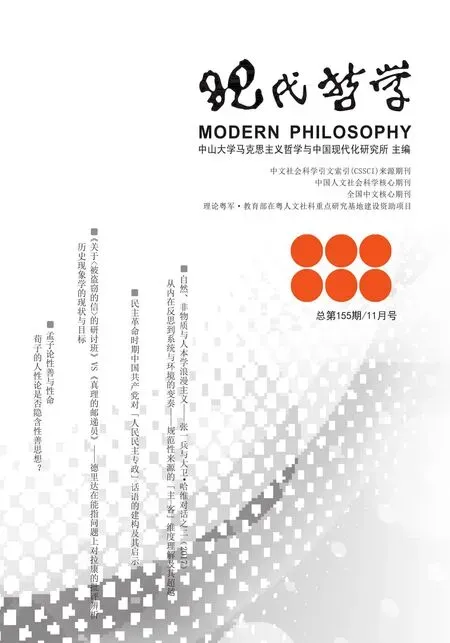“我”的双重“他者”
——《寻找丢失的时间》中意识结构的伦理价值
2017-01-27郭晓蕾
郭晓蕾
“我”的双重“他者”
——《寻找丢失的时间》中意识结构的伦理价值
郭晓蕾
《寻找丢失的时间》通过提出两个叙事主语,时间性的“我”和超时间性的“真我”,丰富了巴赫金关于“对话”与“复调”美学猜想。“我”的时间性形式必然引致的病理症候是虚构抽象的他者和具象的他人;而“真我”则描画着作为自我构成性前提的、超时间性他者存在的可能。双重他者勾勒出存在的复调形式,同时呈示出自我中可能潜在的对全权式伦理形式的抑制性基因。
普鲁斯特;他者;他人;对话;复调
一
《寻找丢失的时间》这部漫长的虚构叙事重复着现代小说叙事和哲学叙事共同的重要母题——“欲望”(le Désire)。《寻找》中的“欲望”,描述的不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与超越性存在的关联,而仅仅事关速朽的现象世界。*关于这部小说中欲望的发演机制、“真我”的意涵及其与“我”的关联等,笔者曾在另文中做过详细的讨论。本文意接续之前的讨论,就“我”与“真我”这组不同时间形式的主格形式可能具有的伦理意味展开探究。但为此,本文须在行文中扼要陈述之前讨论的若干结论。(参见拙文:《〈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第164—177页。)小说中,欲望的主语是时间性的主格形式,包括主人公、叙述者“我”(Je)和其他人物;欲望的代名词是“爱情”,而各种爱情均缘起于主体“感到”被客体排斥、压抑,“我”(其他人物亦一样)或是因为“被”某人疏远、轻慢、拒绝,或是因为被某人具有的显在的现实客观性(社会位阶、声誉、才华)震慑,从而爱上了对方;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诞生于客体,恰恰相反,叙事一再重复以下两个事实:焦虑(l’angoisse)先于爱情,而爱情先于客体。*焦虑是小说中所有欲望主体的基本心理状态,叙述者陈言:“他(斯万、小说中一位重要人物)一生中也曾饱受此般焦虑的折磨……这焦虑也许注定是爱情的专利……但它却也钻进了像我这样一个还没有经历爱情的人的心里,它漫无目的、四处游荡,并无一定的对象,只等着有一天为某种情感效劳,这情感也许是对父母的依恋,也许是对同伴的友谊。”叙述者更径直告白:“爱情早已存在,正四处游荡,它停在哪个女子身上,无非因为这个女子显得无法企及而已。”(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coll. “Quarto”,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Yves Tadié, Paris, Gallimard, 1999, pp.33-34、673. 译文由笔者译出。)
不仅如此,普鲁斯特对爱情显微镜式的透察更曝露出,欲望的真实宾语不是任何现实的客观性,而是某种被预设、“想象”(原文用词)出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抽象的客观性。现实客观性是此一客观性的具象形式,构成欲望的形式宾语;在与这些现实的、而根本是想象(虚构)出的客观性的关联中,在一种“被”——被阻碍、被排斥、被抗拒——的意向关联中,“宾格的我”得以显现。而这一显现令意向的展开方向发生转向,或者说,令占有意向得以发生——借由这一发生,“主格的我”得以生成和显现。也就是说,时间性存在达成自身主格形式显现的必由路径是宾格化、是“被”;所谓欲望,即是时间性存在为使自身主格形式得以显现而将自身宾格化的意向冲动。所以,作为一种主格意识的“自我”(le moi),并非是一个既成的、先验事实,而是在一种空间性关联中才形成的。
这一透视结果与巴赫金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建构的“对话性”(le dialogisme)美学理论的存在论暗语是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完全对话了的……离开自己和别人充满张力的交际,主人公就连在自己心目中也将不存在了……并且,对话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对话在这里不是动作的前奏,而就是动作本身。它不是揭示和表现似乎成为现成的性格的一种手段,不是的。在对话中,人不仅仅外在地显现自己,而且头一次逐渐形成为他现在的样子……这不仅对别人来说是如此,对自己本人来说也是如此。存在就意味着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就是一切终止之日。”*[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4—335页。笔者据法译本(M. Bakhtine, Esthétique et théorie du roman, Paris, Gallimard, 1978)对中译文做了些许调整。
在巴赫金看来,陀氏的虚构叙事一再重复的一个主题就是:没有“对话”(或“交际”,巴赫金常用的一个等价术语),就没有所谓的自我。如果说“对话”描述着时间性存在与世界空间性关联的展开,那么,作为空间性意向的“欲望”自然是一种“对话”。“在对话中,人才头一次逐渐形成为他现在的样子”,这意味着没有先于交际、对话的人物的本质,“我”的本质,人的本质。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描述的不是单纯的叙事方式、叙事形式,而根本是存在的形式。如果时间性存在的主格形式的显现是存在自身被感知——“在自己心目中存在”——的必由途径,那么,这一途径的展开方向就是存在将自身与世界之间预设性地、虚构性地建立一种“被”的意向关联。事实上,不仅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构叙事同样曝露出这一事实(碍于篇幅,不再详述)。
《寻找》中一再出现的主体因“感”被排拒而心生“爱情”的事实,无疑印证着黑格尔(“主奴关系”)、拉康(“镜像反应”)、甚至萨特(“锁孔理论”)视“他者”(l’autre)为自我意识生成的绝对必要条件的理解。而《寻找》对主体虚构欲望宾语、并深陷自身虚构的桎梏的再现,令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他者”这一命名能够涵涉的内里。
抽象的客观性必然具有一个属格,这个属格同样只能是抽象的;如果我们将这一抽象的属格命名为“他者”——“被”这一动作真实的施动者,宾格化这一动作的真实主语,那么,真实宾语的具象形式、现实客观性的属格,便是宾格化的真实主语的具象形式——我们或可将之称为“他人”(l’autrui)——也就是宾格化的形式主语。“我”和斯万面对不具有显在的现实优势的阿尔贝蒂娜和奥黛特时,无可抑制地展开对情敌的“想象”,因为想象,这两个原本在两位男主人公眼中平庸至极甚至一无是处的女子竟然显得“遥不可及”,于是,“我”和斯万那各自早已存在、正“四处游荡的”爱情再次得以落脚。《寻找》的叙事不断重复着这样的事实:如果宾格化的真实主语无法获得具象形式、宾格化的形式主语缺失,“爱情”就将无法展开,存在将自身宾格化的意向就无法显现出来。
但是,世界从未亦无法许诺给“我”一个现成的“他人”,正是“被”的形式主语非既成的事实引致《寻找》中的欲望主体们时刻无法摆脱的“焦虑”;当现实的客观性不是显然的,“他者”无法落实为“他人”时,焦虑便呈现为极端的心理躁动——仇恨——焦虑不过是仇恨的前奏或初发形式罢了。如果说“欲望”勾勒着“我”与世界的空间性关联,此一关联的根本内容、或说伦理形式就是“我”对世界的敌化想象——虚构“被”的形式主语,虚构世界的施虐形象(这同时意味着虚构“我”的被施虐形象),而这一想象同样必然地导向仇恨。所以,欲望这一意向关联根本的心理形式就是仇恨。仇恨必将引致“我”对“他人”展开施虐;“我”或斯万的所有爱情都是以仇恨和向爱侣施虐(程度不同而已)收场的;而小说中的一些同性恋者更将施虐与受虐的心理行为变造为物理性的肢体伤害。虚构中的人物在自身的受虐想象中展开对情人们的折磨,现实中的极端政治力量借由对自身受虐形象的疯狂塑造而展开对世界强烈的攻击——虚构与现实,没有本质区别。
欲望的真实宾语本身即是虚构的,于是,无论抽象的“他者”还是具象的“他人”,亦都只能是虚构的属格。萨特通过“锁孔反应”对时间性的“自为之在”(l’être-pour-soi)的生成过程进行描述,我们可以对这一过程做如下补充:预设性地虚构抽象的“他者”,是“自为之在”这一意向结构得以成形的关键逻辑步骤,而虚构具象的“他人”则使这一意向结构的维系成为可能。
“我”和斯万绞尽脑汁想象情敌的存在,就是在虚构阿尔贝蒂娜和奥黛特。虚构“他人”是现代叙事(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构叙事还是哲学叙事)一再向我们曝露出的存在性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描述着个体与世界空间性关联展开的具体内容,而且是人类政治关系展开的逻辑起点:将同类首先地预设为利益的争夺者、敌人,而非实现利益不可缺少的伙伴——这也是现代思想史叙事不断反思的问题。对“他者”的存在性依赖,对“他人”不可豁免的虚构,根植于自我的不完整性、非既成性。这样的存在事实令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是否能够完成康德留下的伟大的现代遗嘱——为自身立法?
当宾格化的形式主语是虚构的,经由此一主语显现出的“我”亦只能是一个虚构的主格形式。如果我们使用“异化”(l’Aliénation)这一命名,时间性的“我”不过是一种异化的主格形式,一种向着自身之外的主格展开运动的过程中显现出的虚构的主格。更麻烦的是,即如不同的“他人”是不同的主格形式,在与不同的“他人”的关联中显现出的“我”亦只能是彼此相异的。这一相异不仅会发生在同一历史坐标上,更会发生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之间——分裂是时间性存在不可豁免的存在形式。在柏拉图著名的“模仿论”中,艺术之所以不高贵,根由即在于其是对影、可感世界的模仿,而非对本质、抽象的理型世界、“真”的复现。非常有趣的是,《寻找》这部现代叙事意外地给我们提供一席关于“影”的现代证词。对“我”而言,不仅可感的具象世界是虚构性的,“我”也不过是一个虚构性的主格形式,就如在《寻找》中那样,“我”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二
不仅如此,《寻找》还通过对“记忆”(la mémoire)与“回忆”(le souvenir)这两种“我”对时间的基本再现方式的详细反思,曝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不仅必然地展开对世界的敌化虚构,“我”还必然地将时间虚构为空间——历史。前一刻的、过去时的“我”(j)根据将自身宾格化的意向冲动,“选择性地”(普鲁斯特用语)截取了那一刻的阿尔贝蒂娜(a)的某种“形象”(l’image),这一被选择出的形象便成为了j对a的“印象”(l’impression)。而这一刻、现在时的“我”(J)出于同样的意向冲动,“选择”将这一印象变为关于a的“记忆”,并“选择”根据这一记忆,准确地说,是“选择”根据对这一记忆的“回忆”,展开与现在时的她(A)的爱情。普鲁斯特一再申明如此的回忆是不可信的,因为它是选择性的、是“主动的”(volontaire)。“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经由j与a、j与J、J与A这三组功空间性意向关联依次展开,即构成着“我”的“历史”;通常的回忆就是将时间翻译为、虚构为三维空间。
但《寻找》同时提出另一种主格形式,“超时间性的”(extra-temporel)的“真我”(le vrai moi);“这个生命……只有置身于他唯一能够存活的那个界域时才会显现,这个界域,就是时间之外”*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coll. “Quarto”,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Yves Tadié, Paris, Gallimard, 1999, p.2266.。普鲁斯特此处所说的“时间”显然是指历史。小说开篇不久,叙述者讲到贡布雷的大教堂:“一座教堂,可说占据了一种四维空间——这第四维,就是时间(原文为大写)——一座教堂,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间伸展着它的殿堂,这殿堂,穿过一根廊柱与又一根廊柱间的距离,从一座圣龛到又一座圣龛,似乎不只是战胜、穿越了多少公尺,而是一个又一个时代,凯旋式地展现了出来。”*Ibid., p.57.当叙事接近尾声,教堂的隐喻变得更加清晰。J和j就如世纪、时代,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即如廊柱、圣龛是教堂的组成部分占据着一定的公尺、空间,J与j也只是空间性的存在;而殿堂象征着超越这些三维空间的另一种存在——第四维空间——这个殿堂就是“真我”。
历史中的“我”不断地从一个虚构的J变为一个虚构j,但横亘的“焦虑”却使“我”无法在感性上体认这些变化,恍若静止于历史之中。唯一有别于这些变化的变化,就是“我”对“真我”的发现,但这唯一的变化却迟至“我”暮年才发生。当这唯一的变化发生时,叙述者说,他回到了“时间(原文为大写)之中”*Ibid., p.2311.。“超越时间序列的一分钟”的“重现”,“是为了使我们感觉到这一分钟”*Ibid., p.2267.。“这一分钟”当然是“历史”中的一分钟。如果我们将两次“大写”并置观察,可以看到作者关于“时间”更加完整的理解。没有殿堂、“真我”,廊柱与圣龛只能是一根根石条和一个个石屋;而没有廊柱和圣龛以及间距、一个个三维空间、J和j,殿堂又从何谈起?廊柱、圣龛和殿堂共同构成了“教堂”;三维空间和第四维空间共同构成着四维空间:时间。*关于“历史”、一维时间的空间本质及其功利属性等,笔者在前注提及的论文进行过更加详细的讨论。
普鲁斯特一再强调,“真我”是完整的、“前后一致”的一种主格经验,叙述者曾在早年模糊地、体验到“真我”,只是当时他并不知其为何,而当他在暮年清晰地、体验到此一主格性存在时,他说“我在此刻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共同感受着它,以至我捉摸不定,不知道是身处过去,还是现在”*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coll. “Quarto”,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Yves Tadié, Paris, Gallimard, 1999, p.2266.。由于时间形式不同,“真我”无从与世界展开三维的空间性关联,故无从被异化,就只能“是我”(l’être-soi-même)。普鲁斯特提出的“真我”令人联想到萨特提出的“自在之在”(l’être-en-soi):超越时间性的、同一的、“是其所是”的存在形式;“自为之在”描述的则是“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存在形式。萨特希图借由前者来克服关于意识结构的“主-客”二元的理解模式,并为存在寻找同一性的本体论根据。在普鲁斯特的虚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同构的努力企图。
从“真我”、时间、历史,三者的关联与差异中,还可以看到现代世界对柏拉图的奇妙呼应。在柏拉图为可感世界提供的先验图示中,作为万物“元型”的“神”、永恒且完满的“造物者”首先创造了完满、唯一的、内涵最优秀的理智的“宇宙灵魂”这一生命体,再以其为“原型”创造出作为模本的、有形可感的宇宙;宇宙灵魂是造物者的造物,只能是“不朽的”(immortal),但相较于诸神更加趋近元型,所以柏拉图在论及这一灵魂时常直接用“永恒的”(eternal)。然而,造物者“要把这一本性(灵魂的永恒性)完全给予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造物者“决定设立永恒(eternity,原译为‘永恒者’)的动态形象,即设立有规则的天体运动”。这样一来,“永恒的形象就依据数字来运动”,“永恒的形象”便是“时间”(《蒂迈欧篇》*[古希腊]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柏拉图在此关于“永恒”和“时间”的思考直接接续着《巴门尼德篇》中关于二者的理解。巴门尼德斯认为“永恒者没有时间(此处同样是指历史)”。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将这一表述变为“永恒即现在是”时已然认识到时间语言在描述灵魂、这样一种历史时间之外的存在是无可避免的逻辑语病。后来,奥古斯丁在借用柏拉图的造物者与灵魂学说变造基督教神学叙事时,努力解决这一语病。直至阿奎那,具备完满理性的“现在是”最终被成功变造成了“上帝”。37D)。柏拉图赋予“时间”这一表述的意涵非常清晰:历史;历史并非本质性的存在,只是作为本质的“永恒”的“形象”。“天体存在之前,没有白天、晚上、年月等……它们都是时间的形式。作为时间形式的还有,过去是(was),将来是(will be),人们往往不加思考就把这些时间形式归为永恒,这是错误的。我们常说,过去是,现在是(is),将来是。(但)只有‘现在是’才准确描述了永恒,因而属于它。‘过去是’和‘将来是’是对生成物而言的。它们在时间中,是变化的。那不变的自我相同者(宇宙灵魂)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老或(变)年轻。它不会变,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蒂迈欧篇》37E-38A)
作为本质,永恒的宇宙灵魂是历史/时间能够成立的元因。“一般来说,那些在变化中的可感物体,其生成所依赖的条件都与那永恒无分。不过,作为时间形式,它们模仿永恒,并按数而运转……于是,时间和天体一同产生。一同产生便会一同消失,如果它们有一天会消失的话。时间是根据永恒本性造出来的,它尽可能与原本相像。原本是永恒的,而天体和时间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蒂迈欧篇》38B-38C)。柏拉图在此确表示,时间/历史的实质内容是空间——时间和天体一同产生、一同消失,天体和时间/历史都是有时态的。
柏拉图意义上的“时间”和“永恒的灵魂”,与普鲁斯特笔下的“历史”与超时间性的“真我”,两组指称几乎有着对位性的关联。无手无脚、不在历史空间内运动,是柏拉图对宇宙灵魂存在形式的基本描述(《蒂迈欧篇》33C-34A)。这样一种存在又完整地充胀于可感空间,成为后者运动的元动力(《蒂迈欧篇》34B-C),并且对时空“全感全知”(《蒂迈欧篇》37A-B)。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叙事借由柏拉图的灵魂学说进一步论证上帝无处不在这一“丰饶原则”。
在西方思维语境中,普鲁斯特提出的“真我”并不十分新鲜,它呼应着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最基本的假设:“永恒”本身渗漏进历史,是生成物的成立根基。没有“真我”、“殿堂”,廊柱和圣龛就只是一堆石块和物理空间。没有“真我”的显现,在意识空间内,历史本身将无法完整地显现出其时间性的形式,“超越时间序列的一分钟”的显现,“是为了使我们感觉到这一分钟”。但呼应并不意味着完整地重复。在柏拉图看来,灵魂是“身体的主人和统治者”(《蒂迈欧篇》34C),而“真我”是一种不具有任何主动性的存在形式,即便“真我”真的对“我”展开过主动性的引领。这一假设没有成为小说的叙事事实。
经过一生的苦难的欲望历险,当叙述者于暮年确定地体认到“真我”时,他明言找到了 “致福”(lafélicité),《寻找》终究成为一场“喜剧”;如果认为“真我”的显现是对“我”人生的救赎,得救的结局却与“我”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我”从未向着发现“真我”展开过任何筹划,在后者显现之前,“我”对其是无知的——叙事亦多次强调这一事实;相对于后来的理性主义的神学叙事,《寻找》更接近原初启示叙事的法理。*中世纪的神学叙事赋予古典世界的“喜剧”(comdìa)以新的意涵:从不幸开始,以幸福收场,人生、历史终将是一场喜剧。古典世界对历史时间展开形式的基本理解是循环:赫拉克利特提出“大年”这样一个循环周期;柏拉图虽未明言、却也表达出类似的猜想,并明言没有神的干预,历史注定是一个堕落的过程(《斐多》《理想国》《法律篇》等);亚里士多德虽相对乐观地认为历史是潜能一步步变为现实的、趋善的过程,但亦在《物理学》中明确说明可感世界终究是遵循着循环的尺度展开运动的。也就是说,即便个体、世界可以获得一时一世的进步,所有的进步最终将被取消。然而,当基督教于欧洲合法化之后,历史不再是循环的(上帝不会再次创世纪,耶稣亦不会再次受难),尤其不再是悲剧性的。在原初的启示叙事中,世界的得救本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因为我们无法获知、亦不应窥探上帝幕后的运筹——且仅仅事关上帝的恩行;但在“理性”合法地登入启示殿堂之后,从奥古斯丁至阿奎那,得救这一事件一步步被变造为一个与人自身的完善和进步密切牵缠的“递进的过程”。“进步的人生、历史”是对“喜剧”这一启示真理的世俗化、理性化变造,令原本不可见的、作为预言的“喜剧”获得了现在时的、具象形式。
无论“真我”是否可以被视为内化的、世俗化的上帝,这一上帝却不具有神性上帝必然具有的对受造世界的宣裁功能。在文本范围内,“真我”明确具有的伦理功能只有一个:宽恕——令“我”与世界、与历史和解。焦虑的痛苦,仇恨的折磨,只对“我”存在。因为与世界置身不同的时间、空间维度,对“真我”而言,世界无法成为任何一种形式的“他人”。在那些瞬间中重现的“每一分钟”、重现的“历史”,不是“我”在敌意中虚构出的关于世界的“印象”的再现,而是世界在“真我”眼中的“形象”的显现——这便是“丢失的时间”。只有“真我”才能“找回我们的记忆和智性永远无法找回的丢失的时间”*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coll. “Quarto”,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Yves Tadié, Paris, Gallimard, 1999, p.2269.。当“丢失的时间”显现时,叙述者感到这个曾被他深深厌弃、憎恶的世界竟然显出了美。如果说列维纳斯对“大写的”、“彻底的”他者的言说,意在展开对“爱”世界的可能性的论证,那么,《寻找》对“真我”的描摹也明确流露出同样的企图。因为无从与这个世界展开空间性关联,“真我”无从贱视、敌化这个世界;只有当敌意被真实地抑制,“爱”才会变为真实的可能。
三
至苏格拉底提出作为宇宙本元的永恒的“善”,形而上学的探索彻底将可感的历史世界的伦理形式的根茎,深深地植入在抽象的本质世界。本质、存在是一,现象、影、模本是多。根据既成的却又不可感而只能经由理性认知的“唯一的”本质,或说存在的法则,制定出、规划出的历史世界的伦理形式,在逻辑上必然地、只能是“一种”,而不能是“多种”。这一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伦理理想,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形式,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全权主义”或曰“极权主义”(the totalitarianism)的权利结构形式。
阿伦特特别强调,全权主义描述的是一种与我们惯常理解的统治通则——即必然由一个人或一群人来统治其他人——截然相悖的权利结构形式。所谓全权主义,并非单纯意指权利高度集中的政治形式,而是指在权利高度集中的同时、实体统治者缺席的政治形式。极权主义就是一种“无人统治”的政治形式(这里无须述及全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部《极权主义》;[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城、刘小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在这种政体中,真正的统治者不是任何具体的人员、组织、机构,而是某种“意识形态”(the ideology)。根据阿伦特的描述,在这样的政体中,“统治术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认为人可以被彻底调控,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某种更高的历史力量或自然力量所排定的功能角色”*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Harcourt, New York, 1994, p. 379.。于是,实体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仅仅是这一预言的践行者、执行者。事实上,如此的统治者在古典的虚构叙事中一点都不罕见。在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舞台上,人间的真实统治者从来都不是城邦的王,所有的人物都被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安排着,这个力量就是命运、“必然”(la nécessité /ανγκη)——对人世、历史展开过程的预先设定。所有的人物、事件在舞台上的合法性根基即在于他们、它们都是印证预言的部件。
全权主义首先是一种思维形式,并且如阿伦特所强调,作为政体形式的全权主义并非只出现于20世纪,它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不过在20世纪中呈现出几乎最极端的形态。全权主义的伦理构想在虚构叙事中的表现,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独语”(le monologue)。在创作论层面,任何叙事的元主语都是作者,在独语叙事中,作者行使其治权的根本形式,就是根据其自身对世界、时间的理解,根据自身认同、秉持的价值和意义认断,来编织、虚构人物、情节等等,于是,人物、世界都成为再现或说模仿这一既成认断的工具。
针对“独语”,巴赫金提出“复调”(la polyphonie)叙事的美学理想。理想型的复调对话叙事的实现,意味着作者声音的彻底消隐。而消隐的具体路径是,“作者描写所依据的思想原则”和“主人公的思想立场”二者相统一,“这种统一应表现为作者的描写同主人公的语言、感受具有共同的单向性”,也就是说,令人物的声音完全变为作者的。*[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106页。独语叙事中,作者与人物的声音同样具有“共同的单向性”,但此一单向性的操作路径不是令“人物的”变为“作者的”,而是正相反。显然,巴赫金对作者声音参与叙事的强烈排斥,是意在抑制作者对人物展开全权式的伦理宣裁。
全权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就20世纪极端的政治现实,还有赖于另一个重要的伦理维度的介入。自奥古斯丁至阿奎那,神学叙事在将“存在”置换为上帝的同时,忠诚地延续着古典形而上学的基本认定——可感世界的次生性,和伦理法则的制定原则——将历史的伦理形式的根茎奠基于历史之外。如果说正是基于对此一制定原则的不满,康德一代“开始”将“存在”剥离神性的界域,现代世俗形而上学“开始”形成,此一轮新形而上学却继承了启示叙事对历史的基本预言——历史终将是一场“喜剧”。这一预言经由黑格尔、并伴随生物进化论的延展,获得了“科学”的修辞,被成功地变造成事关“进步”的规律和法则。于是,理想的、合乎道德的人生,就“应该是”配合这一进步法则、主动促成进步预言实现的人生;正义的制度就“应该是”有益于这一法则或说预言展开、并践行这一预言性法则的制度。这亦即是20世纪全权主义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根本辩词。*根据由人自身发现、发明的法则指导人世,这样的伦理制定法理自近代以来成为了“公理性的”。而在巴赫金(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这是对唯一合法的全权主语、上帝的严重僭越。巴赫金对独语叙事的反驳,始终流露着其根底里的正教情怀。一个小说作者在其笔下根据自身的认断虚构人物、虚构世界,这一美学行为不是其他,正是对上帝创世的模仿——对上帝的僭越。复调对话理论不是单纯的美学理论,亦不是单纯的存在论,而是一种世俗化的神学叙事。
虽然自休谟起,从“是”(be)推演出“应该”(ought)这一伦理制定法理已然被一再质疑,但事实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更加有效的、足以取代这一法理的伦理制定通路。康德提出“人为自身立法”这一近代以来最大的人类理想,似乎开启了摆脱本质决定论的伦理世界的曙光,但其最终仍将“法”的根茎立植在历史之外,虽然关于“物自体”的理论假设的动机是为人的立法主体地位做出完整的合法性辩护。自康德以降,西方存在论叙事即开始致力于寻找形而上的、神性本质隐退后,伦理形式在历史世界中的根基。但从胡塞尔至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似乎一再回归历史之外,直至列维纳斯、亨利、马里翁等,当代现象学叙事甚至呈示出向神学的回转。
列维纳斯提出大写的“他者”,其理论指向十分明确:通过回归“非形而上学的”上帝,重塑历史的伦理根茎。现代存在论叙事呈示出的置放伦理起点的两难困境,不仅一再质疑着“人为自身立法”的合法性,还提醒我们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什么”一旦被悬置,历史将不可获得有效的伦理形式,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回归本体论的同时,有效地避免历史世界陷入全权的险境?
“复调对话”这一美学理想的伦理暗语是意将上帝的归还上帝;而于今,在一种世俗化的视界中,这样一种美学理想可以很轻易地被变造为对现实政治结构形式多元化展望的美学辩词。但是,就如“复调对话”一直以来更多地只是一种叙事理想,而非完整的叙事事实,多元化的政治结构亦从未在世俗世界中获得完整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多元与真理(唯一)之间的矛盾,直至今日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们目前能够做出的判断仅仅是:如果希图化解多元与真理的矛盾,返回本体论,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如果无法在本体论层面有效地解构真理的一元属性,多元的伦理构想永远只能沦于一种理论猜想。
而普鲁斯特的虚构叙事正是在本体论层面提供出某种可能的解构方案。如果令人物的声音完全变为作者的,是“复调”实现的唯一通途,那么“复调”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作者唯有陷入重度的分裂方可将自己的声音完全消匿。而《寻找》呈示出另一种复调叙事的可能性。
首先,“我”与“真我”是两种不同时间形式的主格;如果说“欲望”勾勒着存在的空间形式,或者说,存在的空间形式是“对话性的”,那么《寻找》对两种主格形式的描摹则呈示出存在的时间形式是“复调性的”。与惯常的关于自我多重性的认知不同,“我”与“真我”之间无法构成空间性关联。通常意义上的多重自我描述的,只是经由不同的“他人”显现出的不同的“我”的同时性的存在现象,即时间性存在的空间性分裂形式罢了(无论这一分裂是发生在同一历史坐标上,还是在不同历史坐标之间)。
同时,“我”与“真我”,这两个主格共同地出现在《寻找》中,是两个叙事主语。这部叙事是以“我”在半梦半醒间的呓语开篇的。作者在小说开篇即示意读者,这部小说不是“我”对时间“主动”的“回忆”,而是“记忆”在一种“非主动”(involontaire)状态中的自我显现。直至叙事尾声我们才明晓,“非主动记忆”的主语不是“我”,而是“真我”。这一主语不在历史之中,故而是无时态的,或者说,对“真我”而言,时间无法显现为由过去、现在、将来编织成的历史。《寻找》叙事整体上呈现出的历史秩序的模糊,正是“真我”对时间的记忆形式的美学再现。在由“我”引动的叙事中,“真我”隐匿,叙事成为“我”的独语;当“真我”显现,整部叙事又成为“真我”的独语。这后一种独语不仅呈示出“真我”对世界的印象,同时更完整地(至少在象征层面)呈示出“我”对世界的印象。《寻找》的元主语,即如所有叙事一样,是作者,但普鲁斯特却没有将自身置于分裂的深渊,而是通过将存在复调性的时间形式翻译为叙事形式,实现了叙事的复调性。
《寻找》的叙事实践不仅丰富着巴赫金关于复调叙事的设想,更关键的是,如果存在的时间形式不是“一”,而是复调性的,那么历史合法的伦理形式就有可能不是一种。《寻找丢失的时间》是一部虚构性的美学叙事,它不是一剂救世良方,更没有提供一幅救世蓝图,但它却在虚构的讲述中向我们散露出本质有可能并非是“一”的启示。
列维纳斯意图通过论证大写的“他者”是存在之绝对的构成性前提,来抑制时间性的主格形式对世界的同一化冲动,《寻找》提出的“真我”具有着与“大写的他者”同样的伦理价值。“真我”的显现不仅令“我”的时间性形式得以完整显现,关键是在“真我”的记忆里,“我”对世界的敌化印象并未被稀释、更未被美化,“真我”无从将“我”彻底同一,因为“真我”与“我”是不同时间形式的主格——“时间的重现”并未成为对历史的改写。对“真我”而言,“我”是彻底他性的,反之亦然。
B512.5
A
1000-7660(2017)06-0099-08
郭晓蕾,(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存在形式的嬗变与叙事形式的演替:围绕普鲁斯特展开的欧洲小说现象学研究”(14YJC752007)
(责任编辑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