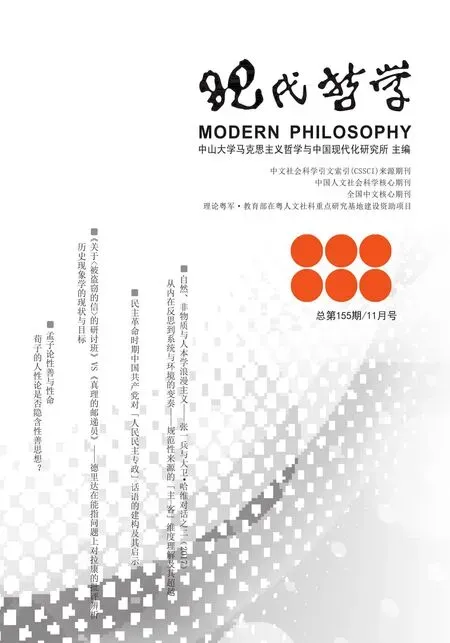历史现象学的现状与目标
2017-01-27卓立
卓 立
历史现象学的现状与目标
卓 立
历史现象学不应被理解为“现象学地看历史”,而应被理解为“历史地现象学地看”,这样才能建立对历史现象学诸含义的统一理解。历史性与现象学之间的本质关联在于,现象学本身就蕴涵着历史性。现象学不仅源于历史性问题,也强化了历史性,使近代意义的历史性发展成为绝对的历史性。这种绝对的历史性只有在后期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中才可能得到圆满的阐释,从而克服现代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相对主义问题。这意味着将近代理性主义“超越历史的理性”修正为一种“包容历史的理性”。因而,只有从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出发,才可能超越现代性前提,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对象领域重建理论研究的可能性。
历史现象学;历史性;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现实史
近年来,随着国内现象学研究的深入,“历史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Geschichte, phenomenology of history)这个术语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学界日益关注到现象学运动与历史问题之间广泛深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对具体领域的现象学研究,也日益彰显历史视角的重要性,相关的现象学思想日益显示出其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因此,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系统展开历史现象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至目前为止,我们对历史现象学的涵义、研究意义以及主要研究任务,都还欠缺足够整体的阐明。历史现象学作为一门完全意义上的学科不仅尚未形成,就连“针对现象学与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呈显出停滞不前的情况”*罗丽君:《历史现象学的基础研究——时间意识的原创建》研究成果报告(精简版) ,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2007年11月4日。。
一、“历史现象学”的涵义统一性问题
“历史现象学”一词,即使仅仅望文生义地理解,也包含了多种可能。在现象学成为显学的今天,它最可能被理解为指向历史领域的专门现象学,即“关于历史”的“现象学”;但对于不了解现象学的人,也可能被理解为“关于历史现象”的“学”。这种“句读”的不同根本上基于对“现象”的不同理解,即“现象学”之“现象”与通常所言“现象”不同。不仅是“现象”一词,对“现象学”和“历史”两词的不同理解,也会分化出不同的含义。对现象学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至狭者仅指胡塞尔的现象学,至广者则可能把诸如黑格尔、尼采、狄尔泰、萨特、德里达、雅斯贝斯等皆纳入。因而“历史现象学”可能既宽泛地指向广义现象学的范围,也可能仅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历史”一词,在目前多数语言中都既可以指历史本身,也可以指历史学*[法]雷蒙·阿隆:《论治史》,冯学俊、吴泓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95页。;前者与存在有关,后者则主要指向一种知识形式。因而,历史现象学既可指关于历史存在论的现象学反思,也可以指关于历史知识论的现象学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前者指向的不是通常的实在论视域下的存在论问题,而是现象学视域下的特有的存在论问题,它集中表现为“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historicity)问题。
就胡塞尔本人而言,即使是在其涉及历史现象学论述的晚期,他“本人似乎并未使用过历史现象学的概念,运用‘历史现象学’或‘现象学的历史学’概念较多的是德里达”*倪梁康:《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德里达对“历史现象学”一词的使用可见于《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法]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6页。而德里达几乎已经意味着现象学运动的尾声(仅就其经典著作而言),也就是说,在现象学运动几乎到达了末尾阶段,“历史现象学”一词才出现。然而德里达之后,“历史现象学”并未成为国际现象学界通行的固定术语,只是零星出现在论及诸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克莱茵(Jacob Klein)、萨特(Jean-Paul Sartre)等人的学术史研究中。但自2000年前后,“历史现象学”一词的出现频率逐渐增加。其中美国的大卫·卡尔(David Carr)摆脱了学术史用法,用“历史现象学”命名其从现象学出发研究历史知识理论的工作。在2006年出版的Analecta Husserliana第90卷,以“历史现象学”为标题的第一部分内容甚广,不仅包括学术史,而且涉及更宽广意义上的历史理论。*Tymieniecka, Logos of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Logos, Book Three, Volume 90 of the series Analecta Husserliana, Springer, 2006.这或许已经意味着“历史现象学”已经开始被理解为一种专门的研究方向。
国内学界方面,此词最早见于1996年雷戈的《历史现象学论纲》一文,指的是“关于历史现象”的“学”这最宽泛的含义*雷戈:《历史现象学论纲》,《学术界》1996年第2期。,这应该与彼时现象学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草创阶段有关。大致在2000年左右哲学界开始使用“历史现象学”一词,最初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张一兵及其《回到马克思》(1999)为代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丁耘在论文中对比胡塞尔与马克思时,将胡塞尔定位于“生活世界现象学”,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将世界“把握为历史现象”。*丁耘:《胡塞尔现象学的转型意义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联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3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就是说,此种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历史现象学”的用法,仍与“历史现象”有关,而不只是由于对“现象学”理解有异。此后,随着现象学思想的传播与研究的深入,“现象”的使用意义开始低于“现象学”,于是“历史现象学”一词的使用频率开始提高。并且,由于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梅洛-庞蒂等广义现象学家的思想都与历史问题紧密相关,在实质上推进了关于历史现象学的学术史研究。尤其是梅洛-庞蒂的“走红”是近年来“历史现象学”在国内外使用频率大增的重要动力,比如佘碧平《梅罗-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佘碧平:《梅洛-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7年)一书。但奇怪的是,直到2006年,“历史现象学”一词还与现象学的奠基者胡塞尔无关,因为此前胡塞尔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最不具有历史性”的哲学家*[法]保罗·利科:《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方向红译,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09页。。孔明安在2007年发表的《意义的历史及其回溯》中说:“如果说要把历史的哲学思考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联系起来, 则似乎就有点陌生和奇怪了。但细究起来, 我们则必须承认, 历史问题的确是胡塞尔晚年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它成为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并由此形成了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孔明安:《意义的历史及其回溯——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5期。同年,倪梁康在《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一文中也开始讨论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此文最初以《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为2007年“全国现代德国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后以《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发表于《哲学分析》2010年第2期。,此后他围绕这一问题方向发表一系列公开论文,甚至开始认为胡塞尔“就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倪梁康:《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 9期。至此,整个现象学运动都与历史现象学发生关联,使用“历史现象学”术语进行现象学研究开始通行起来。明确使用这一术语写作的国内学者此后还有杨大春、朱刚、方向红、李云飞、潘建屯、黄旺、任军、单斌、王庆丰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罗丽君早在2006年就开始以“历史现象学”为题开展胡塞尔研究*罗丽君:《历史现象学的基础研究——时间意识的原创建》,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2007年10月31日。,只是未发表出来。)
综上可见,“历史现象学”首先不适合称为一个原生的术语,即现象学哲学家原创自己思想时有意使用的术语,更适合理解为一个研究型术语;其次,当胡塞尔思想都被理解为与历史现象学具备重要关联,甚至胡塞尔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还早于海德格尔时,*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整个现象学运动(甚至连其外围)便都与“历史现象学”有关,那么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之间便不止是包含关系,而是具备更为深入的内在关联;再次,整个现象学都能与之发生紧密关联的历史现象学,或者说对现象学而言无法回避的历史维度,却是在反思自身和研究过程中才日益彰显出“历史”与“现象学”的内在关联性,甚至直到最后才回溯到胡塞尔现象学那里,其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反思。
目前为止,对历史现象学本身(尤其是其涵义)展开研究的,主要有倪梁康、孔明安、朱刚、颜岩、潘建屯、罗丽君等学者。颜岩通过区分古典现象学与现当代现象学,同时肯定了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至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及其变体”两种进路,也就相当于按“现象”的两种不同用法划分两种历史现象学,并认为两者之间是异质的。*颜岩:《现象学精神与“历史现象学”概念》,《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孔明安区分了广义的历史现象学与狭义的历史现象学,即胡塞尔后期的历史现象学与运用现象学方法探求“意义的历史性或历史的源初意义的特性”的广义现象学。*孔明安:《历史现象学与意义的建构——从〈几何学的起源〉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倪梁康主要是在孔明安说的狭义历史现象学的意义上使用“历史现象学”,即“将胡塞尔在‘起源’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所阐释的历史哲学思想称为‘历史现象学’”*倪梁康:《历史现象学与历史主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将历史现象学定位于对历史的内在本质或内历史的研究这一点,将历史现象学扩大为历史哲学的含义,从而把黑格尔甚至柯林伍德都包含了进来。罗丽君则认为“历史现象学”从字面意义看是指“一门从现象学中分支出来、具有完整独立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然而事实上“如此一门独立的科学至今仍未完成”,而主要集中于“针对人类存有之历史性问题进行现象学的反思”。*罗丽君:《历史现象学的基础研究──时间意识的原创建》,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2007年10月31日。也就是说,倪梁康与罗丽君实际上有将完全的历史现象学扩大至历史哲学的意图。潘建屯在《历史现象学内涵探析》一文继承了这个意图,在梳理“历史现象学”的概念及用法问题之余,认为历史现象学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应当同时考虑从历史哲学和现象学两种视角来界定历史现象学,但“想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一劳永逸的历史现象学概念是绝不可能的”。*潘建屯:《历史现象学内涵探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可见,目前关于历史现象学的理解和用法,基本上是分裂的。但是,我们可以仅仅因为当前历史现象学涵义的差异状态就认定它不可能获得本质上的统一吗?按照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本旨,对历史现象学涵义的把握或许不能是“一劳永逸”的,但却完全可以获得统一的本质把握。实际上,既然历史现象学是一个源于反思现象学运动的概念,那么它便更应当具备统一的内涵。米歇尔·亨利便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历史现象学”的,“把先前的那些现象学统称为历史的现象学或经典现象学。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胡塞尔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一是海德格尔及法国哲学所主张的存在现象学”。*杨大春:《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3页。大卫·卡尔则将历史现象学理解为一种“把历史视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来探究”的研究*David Carr, Experience and History: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并由此指向对历史经验的研究。在卡尔这里,“历史现象”与“现象学”被统一了,由此指向更宽广的研究视域。
这种统一性的根源在于“历史现象学”中的“历史”本身应被作为一种视角而非对象,“历史现象学”应当是“历史地现象学地看”,而非“现象学地看历史”。前者意味着“历史”与“现象学”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本质的观念关联,从这种本质关联出发,诸种现象学之间甚至也获得了一种统一性;后者则在作为对象的“历史”的差异性之中扼制了研究历史现象学的意义。
二、历史性与现象学的本质关联
把“历史现象学”的“历史”作为“视角”的关键在于,要把现象学所关注的“历史性”看成“视角”而非“对象”。或者说,正是由于“现象学的看”,才涌现了“历史性”问题,现象学造就了全新的历史性,现象学的“看”由此成为“历史性的看”,它指的不是那种演化地研究的历史方法,而是将历史性的生存或自我视为世界展开的根本,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之域由此重新构造起自身而成为“对象”。历史性与现象学之间是本质性的关联,现象学不是由于关注了历史问题才衍生出历史现象学,而是现象学本身即肇始于历史问题,进而发展了历史性,最终也是基于历史性来确立自身。关键在于正是现象学运动的出现才导致理性与历史的关系被改变,最终导致对理性主义与真理合法性的重新反思。
实际上,如果把现象学视为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所谓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本文大致在胡塞尔后期批判的伽利略主义意义上使用。这种理性主义构成西方近代整个现代性思想的中枢,它在古代西方哲学中是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与以赫拉克利特-克拉底鲁-智者-学园派为代表的怀疑论对立的,在近代的启蒙思想的意义上是与思想的蒙昧状态对立的,而在现代思想的意义上是与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对立的意义上成立的。的超越,那么它便是以消解理性与历史的冲突问题为中心,这正是“历史性”问题的意义所在。对于现象学而言,超越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意义便在于,近代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试图超越历史的理性主义,而恰恰是在近代理性主义中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反而导致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前提被消解。
近代理性主义试图超越的历史,必须在近代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念基础上理解。只是在近代,一个预先的自在的自然世界观念才被建立起来。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根本上是普遍数学的胜利,随着事物的属性和质料全面地被数学化,“质料”由此无穷地后退,最终成为神秘的自在之物。世界于是被整体地转换为一个被认识的形式的世界与一个永远不可抵达的自在之物的对置,世界在数学的无限的观念中成为一个永远预先在此的绝对容器。历史性问题从此便进入了哲学反思的中心区域。因为当哲学原本试图追寻的真理——那个“本质”成为无限远去的自在世界之后,它不仅不再是不变的,而且还成为“变”的源头,这就意味着真理试图超越的“变”从依附于“物”的“流变”,变成了依附于世界本身的本质之变。所谓历史性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本质,即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处于历史生成之中这种历史性,而它恰恰是基于自在世界这个近代理性主义的信念,对应于胡塞尔所批判的“事实的历史性”。绝对的历史生成意味着绝对的变化,因此历史性也就意味着对绝对的无穷而不可逆的变化的肯定。
这种肯定世界自身之绝对变化的历史性观念,引发了关于物的“生成”的观念。这意味着由于世界自身是绝对变化的,任何生于世界中的物也是绝对变化着的,从而都是有生有灭、有始有终的。历史实际上取代了“质”,成为多样性的源头,永恒的理性与瞬时的流变/感知的对立,转化为普遍的理性与多样的历史的对立,真理的最大目标从追寻永恒本质转变成超越历史。因此,哲学追问关注历史本身是近代的事情。传统哲学追问的是流变,这导致时间问题构成追问的内核,时间问题因而是哲学中的关键问题,而历史问题往往是在讨论时间时被笼统地包含在内。这也是在现象学中长久以来不直接提出“历史现象学”的一个原因。然而,仔细反思就会发现,自现象学诞生之后,历史一词显得越来越重要。实际上,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通篇谈的与其说是时间,毋宁说是历史。关键在于当我们把万物都视为是“生成的”,从而绝对地具备历史性之后,人本身连同人的理性也成为在世界中的历史性生成物,这意味着主客二元论(这一近代理性主义基本图式)的普遍主体这一极为之崩解了。于是导致一个近代理性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还有什么真理是超越于历史的?如果连数学真理都是生成的,那么近代理性主义自身岂不也成为相对于某一时代有效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
现象学正是诞生于这种试图超越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它“是由西方两千多年来的主流哲学中存在的内部困难和内部问题所引发的一场哲学运动”*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而历史现象学,从后期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海德格尔直到梅洛-庞蒂*佘碧平:《梅洛-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72页。,都是为了进一步超越近代理性主义。“我们应当把胡塞尔现象学理解为近代哲学的出路之一”*丁耘:《胡塞尔现象学的转型意义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联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3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所谓的“现象学还原”与“回到实事本身”都是为了抗拒“自在世界”这个导致理性主义自身悖谬的近代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期胡塞尔激烈地反对历史主义,至少是那种他视为自然主义变种的历史主义。
关键在于,当现象学把“万变之源”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的现象学,便开启了第二种历史性。在现象学的这种视野中,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被倒转了,人不仅不再是神的被造物,也不是被动生成于自在世界中的高级物种,而是一个自主的创造者,甚至世界也是因人而获得存在意义。生存着的人的历史性也就成为彻底的绝对者,以至理性再也无法凌驾它、超越它、拒斥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质直观最终催生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胡塞尔前期坚持的彻底的、纯粹的理性被绝对的历史性吞噬。
胡塞尔在后期已经注意到了新的历史性,这才引发了他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相关讨论可参见[德]兰德格雷贝:《舍勒和胡塞尔思想中的历史哲学维度》,《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扎哈维说:“胡塞尔现象学的彻底性恰恰就在于其一体化地思考历史性、世界分析与超越论哲学。”*D.Zahavi,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 Trans. E.A. Behnk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00.胡塞尔后期以《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为代表的历史现象学思想,不仅是基于存在论的历史性观念,而且仍然坚持先验(超越论)的原则,“先验自我在意识层的起源层面构造了社会历史世界”*J. Owensby, “Dilthey and Husserl on the Role of the Subject in History”, Philosophy Today 32.3 , 1988, p.222.,从而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历史性。“这种面对历史的理论态度被胡塞尔称为‘人之存有的第二历史性’”*罗丽君:《时间意识和历史性: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历史观点》,《台湾政治大学哲学学报》2011年第26期。,他将这种历史称为“内在历史”或“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历史。单斌认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性的根基在于人格自我的历史性,而纯粹自我则是非历史的。但是《观念Ⅱ》中胡塞尔在处理历史和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已经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回忆,对应于不同的历史性。尤其是对纯粹自我的习性之揭示,表露了纯粹自我作为习性的纯粹自我,已经是具有其‘个体化的历史’”*单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历史问题》,《学术界》2015年第8期。。这实际上意味着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是在坚持理性主义路线上对前期的推陈出新,“历史思考是胡塞尔破解其现象学困境的理论选择”*孔明安:《意义的历史及其回溯——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5期。,现象学因而“在研究的区域性限度内便发生了一次大胆的突破, 它越过这些限度走向了一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法]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第12页。。这种意义上的胡塞尔现象学不再是“超越历史”的理性主义,而是类似黑格尔的“包容历史”的理性主义,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理性主义才能真正是彻底的和严格的。从这样的新的理性主义出发,我们才可能走向社会历史存在领域的重新回归,重新奠定全部人类知识与人文社会历史理论的合法性。
三、历史现象学的任务
当前的历史现象学研究更多偏重广义现象学,较为忽视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即使是广义现象学家,也很少“有将上列哲学家们之历史观点进行统整论述的专著或论文”*罗丽君:《历史现象学的基础研究:建构的、存活的和叙事的时间性》,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2009年11月2日。。直到近年,随着胡塞尔后期文本研究的推进,胡塞尔后期的历史现象学思想越发引起学界瞩目,并主要针对历史性、发生问题、时间意识、习性自我、生活世界、几何学起源、交互主体性、被动综合构造等问题展开。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文本展开分析,具备较强学术史研究特征,但就历史现象学自身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
这首先体现在对历史视角和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学术意义认识不足。从历史现象学视角切入反思现象学运动,实际上要求基于后期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思想寻求对胡塞尔前期思想的修正。倪梁康认为,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开始,历史问题便开始逐渐逼迫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做出修正。*倪梁康:《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哲学分析》2010年第2期。大卫·卡尔也认为,发生现象学与交互主体性理论是两个贯穿胡塞尔思想的问题,最终引发了《危机》中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David Carr, Interpreting Husserl: Crit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Matinus Nijhoff Publisher, 1987, p.76.目前为止,学界对胡塞尔后期的历史现象学的评估,总地来说意见不一。有将胡塞尔的前后期主张视为并列和互补的,以倪梁康的“纵横意向性”学说为代表;有认为后期胡塞尔已经暗暗放弃了前期的本质哲学、背离了笛卡尔式道路的,以梅洛-庞蒂的观点为代表*[美]王浩:《哥德尔》,康宏逵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 277页。;有将胡塞尔历史现象学视为从近代理性主义通往海德格尔式后现代思想的“过渡性的人物”*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以上三种观点都没有把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置于现象学运动的最高地位。但近年已经开始出现有学者赞同兰德格雷贝“这一发展不应理解为他思想中的断裂,而应理解为他早期超越论哲学开端之结果”的立场,认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转向”“是其超越论现象学的必然结果,即对绝对事实与经验事实、超越论自我与经验自我关系的进一步厘清,是超越论现象学的彻底自身理解、自身思义”*单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历史问题》,《学术界》2015年第8期。。李云飞则从胡塞尔关于“活的当下”的思想出发,揭示出“历史性的本我”对胡塞尔思想转型的意义,甚至连同“意向性”这一中枢概念都随之进行了历史化的修正,使“原本在静态观念下作为一种‘前’与‘后’的空间性视域关系”也由此转变为“一种时间性的生成过程”,相当于用“纵”转换了“横”。*李云飞:《回到实事本身:发生性的起源与现象学的历史性向度》,《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这实际上意味着胡塞尔的后期历史现象学才是最终的超越论哲学方案,而他前期诸多论述的一再推迟面世,也与历史现象学问题对他前期思想构成的逻辑困难直接相关,比如时间问题研究和《观念Ⅱ》。另一方面,从历史现象学视角切入反思现象学运动,意味着有机会对现象学运动形成全局性的研究与统一理解。从现象学试图突破与历史相对立的近代理性,转变到包容历史的新理性主义这一点入手,不仅可以将黑格尔、尼采、狄尔泰这些以往被视为“前现象学”的哲学家纳入现象学传统中,而且可以重新建立黑格尔与胡塞尔之间被忽视甚至是被否定的本质关联,进而为存在之域以理性主义的方式重新回归奠定基础。
其次,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被忽视(包括被误读)是导致现代哲学至今弥漫着浓烈的相对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现象学运动推进了历史性的绝对化,才使历史相对主义成为瓦解现代性的思想内核,并进一步波及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然而也正是胡塞尔最为激烈地反对着历史相对主义,并且只有在胡塞尔这里才发展出了对历史相对主义思想根源最为深邃的反思。因而或许可以说,只有转向后期胡塞尔的先验(超越论)现象学才可能获得“克服‘历史相对主义’”的洞见*L. Landgrebe,“Life-World and the Historicity of Human Exist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 ed. B. Waldenfels, J. Broekman, and A. Pažanin, trans. J. Claude Evans,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engan Paul, 1984, p.189.。从后期胡塞尔的先验(超越论)自我的绝对历史性出发,不仅可以彻底摆脱历史相对主义,走向新的历史知识理论,而且可以将世界历史重新奠基于观念的历史之上,从而使“柏拉图以来对观念的理解”发生“根本的变革”,甚至前期“胡塞尔对作为超时间者、全时间者的观念的理解, 也会遭受被颠覆的命运”*倪梁康:《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进而通过修正后的本质直观方法重新建立历史理论的合法性。
其三,由于历史性对于历史现象学首先意味着“历史视角”而非对象,那么从历史视角出发,便可以重新对广阔的诸对象领域展开反思。胡塞尔以现象学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重新定义:“历史从一开始就无非只是原初意义构成和意义积淀之相互并存和相互包容的活的活动,不论什么东西根据经验作为历史事实被想起,或是由历史学家作为过去的事实而表明出来,它们必然具有自己内在的意义结构。”*[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49页。从历史现象学出发反思历史知识理论,将有可能引出全新的理论建构。大卫·卡尔已经率先进行了这种尝试,他试图以现象学式的经验概念为内核阐发一种与现行“形而上学”式或“知识论”式历史哲学都不同的现象学历史知识理论。但总地来说,有关历史学(无论是历史理论还是具体的历史学)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现象学至今在国内外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国内,对从历史现象学出发反思历史理论的合法性、历史研究方法、具体书写理论以及那些广阔的具体历史问题,都还欠缺足够深入的研究。这导致目前的历史知识理论(通常称为史学理论)研究尽管深受现象学(主要是广义现象学)影响,但却鲜闻现象学历史哲学之名。
最后,从历史现象学出发,我们将有可能展开一种彻底的观念史研究,以生活世界理论为核心,重新建立起对世界及其历史,以及诸种文化客体与意义对象的理解。将“历史视角”引入现象学研究必定意味着实际存在的出场,意味着现象学研究实践性的彰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存在的出场并非广义现象学存在论意义上的出场,也非德里达所说的“唯有存在论的发生才能创立现象学”*Jacques Derrida, The Problem of Genesis in Husserl’s philosophy, Trans. M. Hob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178.(否则存在之历史性必将消解理性),而只能是在观念论意义上出场。这便只能是以一种观念史的方式出场,也只能是以这种方式,历史理性才可能在突破现代性的前提下重新被建构起来。
就此而言,一种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内核的观念史的展开,不仅意味着历史理性的重新回归,而且意味着存在之域在先验(超越论)中的回归;不仅将使胡塞尔现象学有可能跨越两种“现象”概念的鸿沟与黑格尔对接,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理性层面,而且将可能重新建立对诸具体社会文化对象领域(比如伦理学、法律、艺术学等)的理论可能性的论证,包括基于超越论的生活世界理论,去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观念(尤其是儒学)及其观念发展历程。
总而言之,尽管胡塞尔本人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历史现象学,《危机》本身如兰德格雷贝所言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L. Landgrebe, “Life-World and the Historicity of Human Exist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 ed. B. Waldenfels, J. Broekman, and A. Pažanin, trans. J. Claude Evans,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engan Paul, 1984, p.178.,但历史现象学如能回归胡塞尔历史现象学这一现象学内核,并由此出发重新理解胡塞尔现象学及其现象学方法,便有可能真正消解理性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并由此出发建立一种新的理性主义和新的历史理性。只有基于这种新的历史理性,才可能真正突破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困境,使诸社会文化领域的理论重建在舍弃现代性的前提下成为可能。
B089
A
1000-7660(2017)06-0085-07
卓 立,福建霞浦人,(重庆 401120)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2014年度培育项目“中国现代实证史学知识论基础重建研究”(2014py31);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象学历史哲学知识理论研究”(16SKGH005)
(责任编辑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