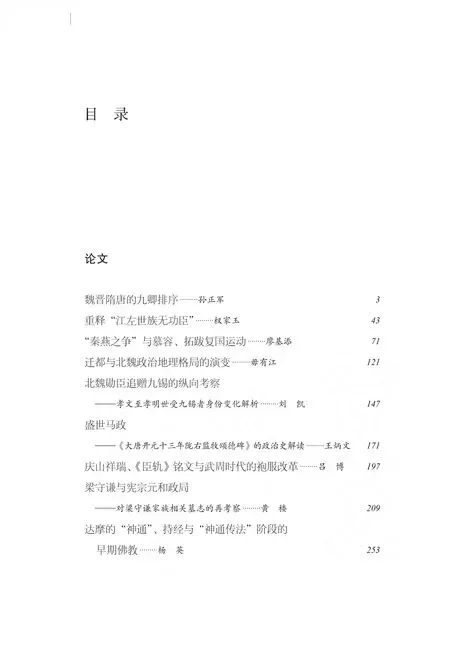《东晋贵族政治史论》
2017-01-27
一
李济沧著《东晋贵族政治史论》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作为《随园史学丛书》一种出版。据本书《代跋语:从龙谷到随园》,此书主体内容是作者1995年进入日本龙谷大学大学院东洋史专业跟随谷川道雄先生攻读硕士,后随都筑晶子先生攻读博士至2003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期间定型的。
全书分四部分,序论“贵族政治、皇帝权力与地方社会”、第一编“乡论、乡品与六朝贵族的本源”、第二编“东晋贵族政治的形成与皇帝权力”、第三编“东晋中后期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和附编。前三编下各置三章,每章实则皆可看作独立存在的论文。最后的附编两章介绍谷川道雄氏的学术路径与《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
在序论中作者回顾了东晋史研究中魏晋封建论、六朝贵族制论与皇权变态说等学说的学术理念与发展脉络,就六朝贵族自律性特点做了梳理,并总结了本书的框架与结论。笔者在此依靠作者的自我归纳,简述全书内容如下。
第一编围绕魏晋时期放达之风与九品官人法中乡品、官品的考辨展开,讨论门阀贵族阶层产生的本源与特色。作者认为元康名士的放达之风超越了个人、阶层与某些群体,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凭借社会上对放达的普遍认可,放达之士抵抗住了皇权的压迫进入官僚体制中。这显示了魏晋以来士人获官所需要的乡里舆论与王朝选官标准有差异。作者而后就学界对九品中正制提出的人品、资品与中正品概念做了辨析。作者认为这三个概念无法涵盖中正品第的内容与性质,并且是在否认乡里舆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乡品概念对地方社会的重视是与前三个重视王朝作用的概念根本分歧。东晋南朝乡里舆论依旧发挥着作用,故而乡品的存在阻碍了皇权的贯彻。这也说明门阀贵族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王朝之外的特点。第一编的最后,作者分析了乡品、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通过考辨维护了宫崎市定提出的乡品与起家官品大致相差四品的原则。并且提出在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实质与历史意义时,不仅需要讨论乡品、官品、官职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澄清乡品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第二编对具有自律性和社会性特征的门阀贵族流寓到江南后的情况做了分析,展现了以门阀贵族为中心的东晋政治特点与皇权动向。作者认为门阀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的权力与皇权在政治上的权威,一道构成了东晋的国家权力。同时这种权力结构立足于江南地方社会之上,只有获得了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皇室与门阀结合的政权才能稳定。在各自的利益需要下,东晋政治呈现出皇权、门阀贵族与江南地方社会的两层分权态势,形成了三方不能缺一的情形。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王导及其实施的“清静”政治,对东晋贵族政治的特征及其反映出来的贵族伦理精神做了分析。作者认为门阀贵族通过修习儒释道三家学问,磨炼自身的伦理精神,并将这一精神贯彻于个人生活及政治活动中,且作为家风世代传承。而这一贵族政治精神得到了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最后,作者以庾氏家族为个案,在传统外戚角度及田余庆先生家族权益维护论之外,通过对庾氏维护东晋皇权而对支撑国家的江南社会结构缺乏审慎考虑导致家族衰败的考察,进一步阐释了前面两部分所申发的东晋一朝皇权、门阀贵族与江南地方社会互相支撑的两层分权态势。
第三编从桓温、谢安之政及东晋地方政治的特点入手,探讨东晋中后期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从贵族政治的角度对东晋灭亡的原因做出分析,并阐释了刘宋对贵族制政治的继承。作者从桓温、谢安的“宽和”、“和靖”之政入手,分析东晋中期以来的政局变动、执政者政策与江南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正是桓、谢继承了王导的“清静”政策,尊重江南地方社会固有秩序,才使得东晋在中后期走向繁盛。接着作者结合史料中对东晋地方行政的几个评语,“清简”、“威惠”、“严猛”,具体分析了东晋不同时空的地方政治。作者认为东晋地方政治的主流是“清”这一贵族式理念支撑的“清静”政治。作者通过江南社会及民众的视角观察东晋贵族政治,认为门阀贵族虽然有着国家官僚的侧面,但并没有完全站在皇权立场上对民众进行彻底剥削,他们不以个人政绩为目的,而是极力维持地方安定,通过“清静”政策牵制了皇权对民众的直接统治。随后,作者考察东晋末刘宋初的政局,探索东晋灭亡的原因及展望刘宋建立的意义。作者认为东晋灭亡的原因在于王恭、桓玄等人不再坚持王导以来的重视江南社会的贵族政治传统,皇权方面则更为重视刑法,加强对江南豪族依附民的征发,导致了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社会不再支持东晋政权。而刘宋政权则有继承“清静”贵族政治的迹象。故而作者认为晋宋革命的意义需要从贵族政治、贵族精神的继承来加以阐释。
通观本书的理路与论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对京都学派中川胜、谷川史学的严格继承。在序论中作者明确提出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六朝贵族形成的渊源和贵族政治与东晋王朝兴衰之间的关联性(第29 页)。而他采取的视角则为谷川道雄所提倡的以基层社会为观察历史脉络的通路。在此基础上,全书着重分析了两个问题:(1)在脱离了华北乡里基础的情况下,作为伦理精神载体的门阀贵族如何继续在东晋国家与江南社会这一政治地域结构中与民众结合。(2)解释门阀贵族在失去了政治军事权力后何以依旧凭借门第获取高位并有着崇高的社会声誉。全书核心观点在笔者看来可以用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来概括,即“北来贵族群所领导的江南贵族制,是在极为先进的乡论主义意识形态与古代残余还继续存在的基层社会的过渡性结合上建立起来的”[1]〔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 页。。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本书以侨姓士族上层秉持清静思想者为门阀贵族,由此区别了南方土著士人(书中所言的江南豪族)与皇室(与门阀贵族有一定对立性的皇权代表)。同时,将颍川庾氏、太原王氏等高门士族在东晋的没落归因于丧失了清静之学。
本书在学术路径上是典型的川胜义雄、谷川道雄思想的延续,以谷川式精神联结的贵族共同体回应了川胜所提出的贵族高贵性的命题。主要讨论了贵族的“高贵性”在东晋朝局中的展现,并以“清静”这一气质为东晋门阀贵族掌控江南的根本原因。笔者于此结合川胜义雄的研究冒昧总结作者此书的四点基础认识:
1.清静可维持东晋国家与江南土著豪族的联系。
2.清是超越婚、宦的贵族高贵性所在。
3.静是东晋中央政治与地方行政的特征。
4.东晋末年南朝初期一系列回归皇权的举动都导致了南方的动荡。
二
六朝士族政治的研究,大体上有四种研究路径。其一曰婚宦门第,以杨筠如、王伊同为代表;其二为家族政争,以田余庆为典范;其三则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东亚传播有关联,特重人身依附关系及土地占有制度,1949年以后何兹全、唐长孺、王仲荦等著名史家对魏晋封建论的考察多带有这一特点;其四是日本自内藤湖南以来的文化史观,尤其是以川胜义雄为范式。这四种研究路径在研究实践中其实又是彼此交融的。其中婚宦门第的研究围绕士族本身进行讨论,然而这样的讨论有一个重大的缺失,即这类问题实则并不仅限于六朝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也不乏这类家族情况的出现。而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通过对几个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家族之间政争的研究,提出了“皇帝垂拱,门阀当政,流民出力”的东晋政治特点,是纯粹的政治史。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重视经济因素,从生产资料占有视角对六朝士族做的研究,于今看来有些过于教条。日本方面则是以历研派为代表的学者对人身支配做过很多研究,颇有涉及六朝的。而京都学派在这三种视角之外,特别重视六朝门阀的精神伦理特性,本书作者李济沧即继承了这种精神伦理考察的视角。
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为代表的战后一代京都学派提倡一种精神史观。对于这一史观,刘俊文曾做出简明扼要的归纳:“力图通过探讨六朝隋唐社会的支配者阶层——豪族名望家的文化教养和伦理道德,阐明六朝隋唐贵族制的社会基础,并进而说明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1]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7):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文史知识》1992年第8 期。关于川胜义雄及谷川道雄精神史观理论构建源流,应从宫崎市定对汉末至六朝时期农村世界形成的考察开始。[2]〔日〕宫崎市定:《中国にぉ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国崩坏の一面》,《东洋史研究》4,1960年;中译本《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载《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通过对都市国家解体的考察,宫崎市定认为地方社会成为了豪族控制下的世界,而这就是六朝贵族制社会的基础。在继承了宫崎学说的同时,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又延续宇都宫清吉关于六朝自律性时代格的判断[3]〔日〕宇都宫清吉:《東洋中世史の領域》,载氏著:《漢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弘文堂1955年版;中译本《东洋中世史的领域》,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 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并结合宫崎市定对九品官人法的研究[4]〔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最终确立起以乡论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在这一史观下,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分别从南北两方对六朝时期的社会构造做出了深刻的研究,代表成果即川胜义雄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与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在这两位看来,豪族通过道德的体现获得了乡里自耕农的认可,形成了在豪族指导下乡里信从的精神伦理联结体制,即豪族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所发出的声音,乡里舆论,即所谓之“乡品”。贵族就是凭借乡品清议而产生,从而对高高在上的皇权有独立性的一面。这些贵族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不脱共同体的本色,拥有川胜义雄所谓之高贵性。关于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两位的学术评介已经有侯旭东、徐冲的两篇极好的书评。[1]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介》,《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 期。
作者师从谷川道雄与都筑晶子两位学者,深受京都学派的影响,如前节所述,其书基本路径是以谷川道雄在华北地域得出的豪族共同体论,来进一步论证川胜义雄在江南所提出的贵族高贵性问题。故而,对于本书的评价,有必要涉及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两位的论断。尤其是川胜义雄对汉末以来共同体运动使豪族从武断乡里向义断乡里转变,从而将武力强宗的封建倾向改途走入贵族制社会的考察,成为了作者研究的前调。
作者这部《东晋贵族政治史论》正是沿着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的道路对东晋一朝的政治形态、地方社会与中央互动做出的具体性研究。如上所言,日本京都学派在谷川道雄一代已经在精神史观上形成了一套自洽圆融的理论体系,当这一理论体系落实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是否能一一符节合拍呢?是否能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中都得到合理施用呢?笔者以为一旦以理论先行作为研究的起点,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下面将结合作者的部分研究,对此稍加阐述。
乡论主义影子在作者的论著中经常徘徊。所谓乡论主义,川胜义雄说:“在乡论之地通过人物评价来构成政治社会等级秩序的思维方式。”[2]〔日〕川胜义雄:《从孙吴政权的崩溃到江南贵族制》,徐谷芃、李济沧译,载氏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149 页。在川胜义雄的认识中,失去了故土的南渡北方贵族通过先进的乡论主义成功地在江南建立了贵族制社会。作者显然接受了这一看法,在第二编“东晋贵族政治的形成与皇帝权力”第二章“东晋贵族政治的本质”中说维持“清”这一贵族精神的各要素中,来自地方社会的支持尤为重要(第153 页),从而进一步说东晋皇权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其政策理念不合“清”的贵族精神,故无法获得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第153 页)。但是,我们知道司马睿立国江东本身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的基础是薄弱的,刚到江南无兵无望,故东晋初期的皇权自出生起就是不振的,而门阀、江南豪族又并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皇权。那将不“清”作为皇权不振的原因,是不是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呢?这一逻辑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理论的过分依从,没有对当时政治环境做出符合历史情境的判断。
作者在第三编“东晋中后期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讨论了东晋门阀贵族体制与地方政治,认为东晋地方政治大体上属于清静政治,对地方的负担较小,就算有个例贪残地方,也有舆论的压迫存在。并比较了南朝皇权稍振、贵族制渐弱之时地方政治贪腐横行的情况,由此论证贵族制政治的存在制约了王朝对民众的彻底剥削。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在对贵族制有先行认识后对历史认识产生的偏差。
作者认为东晋的清静之政的模式为公私两面抑制私欲、不侵夺民众、不增民众负担、积极救济民众,而这与贵族高贵的精神伦理密不可分(第233 页)。然而,所谓清静之政的模式难道不能套合进任意时期良吏的作为吗?这真的是东晋贵族制社会的产物吗?笔者以为这里有一种观念先行而后寻找史料支持的痕迹。关于地方政治中的吏治,唐人在《晋书》卷90《良吏传》序中有一个概括:“莅职者为身择利,铨综者为人择官,下僚多英俊之才,势位必高门之胄,遂使良能之绩仅有存焉。”[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0《良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28 页。在良吏“仅有存焉”的情况下,东晋地方政治恐难言“清”。《良吏传·吴隐之传》中论及广州吏治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作者所列举的那些“清”的地方政治事例,能否解释“前后刺史皆多黩货”的情况呢?吴隐之这样的清静之官于此看来只是前后贪残官僚中间的特例吧。
对于东晋地方政治中贪残的一面,作者认为虽有贪残之政,但同时舆论对此有钳制之效(第224 页)。然而《晋书》中亦有反例存在。《晋书》卷78《孔愉传》中记载了孔愉和王导的一段对话:
(孔愉)表曰:“臣以朽暗,忝厕朝右,而以惰劣,无益毗佐。方今强寇未殄,疆场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臣等不能赞扬大化,纠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横受宠给,无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从之。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之乃止。[1]《晋书》卷78《孔愉传》,第2052—2053 页。
孔愉,会稽山阴人,孔氏自孙吴起即为江南大族,可以算是江南豪族的一员。孔愉指出当时“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王导则“非之”,并反问孔愉所指何人,引文字里行间颇能见王导对孔愉这些话的反感,更别谈接受批评了。如此,舆论有多大的作用呢?对东晋吏治腐败的谏言贯穿整个王朝历史,史书中颇有可见,如果舆论监督真有牵制贪残的效用,何至于累累谏言?
对于理论的过分依赖还体现在作者对东晋政治势力的二分法上。共同体及乡论体系构建中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乡里社会的存在。南渡的北方士族之所以称为侨民,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扎根的乡土社会。也就是说共同体的基础单元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运用乡论主义、共同体理论呢?作者是将整个南方视作一个大的乡里,将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中豪族与自耕农、部曲间的关系套用到侨姓贵族与江南豪族之中。若将国家层面的高门贵族列为A,豪族为B,乡党为C,谷川道雄是分析B—C 之间的关系,而作者则是分析A—B 之间关系。侯旭东在评论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时指出,在谷川道雄的研究中乡党是作为一个概括的概念,被支配的对象,没有自己的主动性。[1]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这一方面是谷川道雄在史料选择上忽略了地方文献(佛教造像、出土文书等),另一方面也是乡党这一群体在现存史料中本身的模糊性。如此,B—C 之间的讨论在先天层面上就容易导致一种自以为自下而上,实际仍然是以上观下的情况。作者的观察对象则为A—B 之间的关系。豪族作为历史上有政治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在史书中材料颇多,从这点上来说可以避免谷川道雄分析乡党时的模糊与笼统。但是在本书中,笔者发现江南豪族被作者视作一个整体观察,没有一个清晰具象的分析,与谷川道雄分析乡党时一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江南豪族是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呢?其实并非如此。贺循,会稽山阴人,其家在孙吴时期为将门,但本身家族传庆氏礼,在贺循一世就迅速摆脱了武力强宗的特征,在朝廷以礼称名。而武康沈氏的身份转换则要到刘宋时期。这种身份转换的时间差异,也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同一时段的政治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同样,一起被王敦所害的戴若思、周伯仁,一属南方豪族势力,一属侨姓士族,他们具体的差异性在哪?是否都能用江南豪族这一概念统一分析呢?笔者以为这需要更深一步的细化分析。江南地方社会上层人物、家族的史料丰富,笔者以为有很大空间能做出不同类型的区隔,如此能够更进一步研究侨姓贵族面对的不同江南势力所采用的不同措施。
笔者以上试举几例意图说明本书作者在依循京都学派谷川一系的理论上有着拘泥理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或许在这一系理论中并不成为问题。只是笔者作为旁观者,对于这些问题稍有不同认识,也请方家指教。
三
笔者在上节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批判,并不是要说明理论有问题,而是想指出现在中国学界关于士族或曰门阀贵族的研究中理论的一种迷失状况。日本学界在过往有着长期、激烈的中国历史分期辩论传统,从中产生了人身支配体系、豪族共同体、寄生官僚等学说。他们经过长久的理论洗礼,因而对六朝史为何关注士族研究有着鲜明的态度。反观中国学界,六朝士族研究虽然被认为是六朝史研究的重心,但为何是重心,笔者以为尚未进行合理必要的研讨。
本书就笔者浅陋所见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部依循谷川史学讨论中古士族政治的专著。其中得失自可评说,但理论意识鲜明是一大特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过往依循的理论路径不断遭到抛弃,如今的研究中往往另有一种理论饥渴的情况存在,对日本、欧美学界提出的种种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有着不加辨析而利用的现象。可以说,理论如何落实到历史语境中,或许是现今历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笔者看来,关键一点还是在于对史料的分析上。不应是从理论出发找相应的史料,而是以史料为基本点,寻找历史本身的逻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