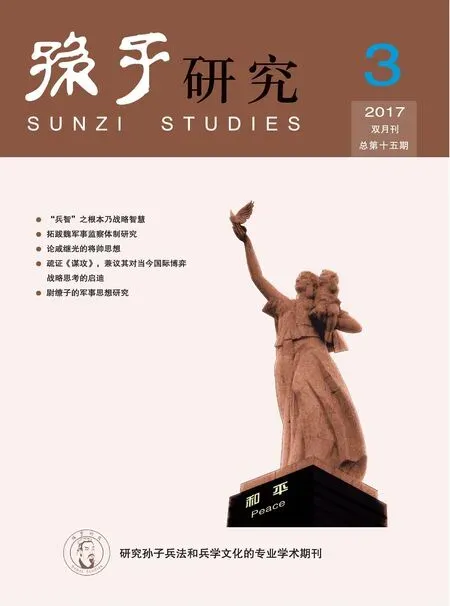尉缭子的军事思想研究
2017-01-27徐勇
徐 勇
尉缭子的军事思想研究
徐 勇
尉缭子大致生活在梁惠王至秦王政时代,他就是著名兵书《尉缭子》的述作者,其军事思想丰富多彩,极有特点。
尉缭子 战国军事家 军事思想
一、尉缭子的生卒年代
尉缭子是著名兵书《尉缭子》的述作者、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思想家。
关于尉缭子其人的原始记载,目前只能见到两条,一是在今本《尉缭子》首篇《天官第一》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的记载,二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这两条记载来考证尉缭子的生卒年代。
我们首先对梁惠王的有关史料进行考证和探究。梁惠王名罃,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年)即位,就是史书中所说的魏惠王,因其在位期间将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村)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被称为梁惠王。关于梁惠王的纪年及其在位时间,史料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司马迁《史记》本身的记述也大相径庭,现分别列举加以考辨。
《史记·魏世家》:“三十六年,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赵世家》《六国年表》的描述与《魏世家》相同,即认为魏惠王在位权仅三十六年,卒于公元前 333年。《史记·秦本纪》则记载:“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8年版。换算,秦武王元年为公元前310年。《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七年,与魏惠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孟尝君列传》也记有:“宣王七年,田婴使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候、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魏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换算,齐宣王八年为公元前311年。而齐国使用的历法为“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秦国使用的是“颛顼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所以实际上《秦本纪》的记载与《田敬仲完世家》《孟尝君列传》的记载并无歧异,即认为梁惠王在位五十九年,卒于公元前310年。
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史记·秦本纪》中梁惠王在位五十九年、卒于公元前310年的记载比较可信。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梁惠王在他晚年与年轻的尉缭子答对(正像今本《尉缭子》首篇中描述的那样),而在秦始皇十年,年老的尉缭子由大梁来到秦国,为秦统一全国献计(正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完全可能的。假设在大梁与梁惠王答对时尉缭子不满二十岁,那他在秦始皇十年入秦时大约有九十来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司马迁这段描述,事实甚详细,语气甚肯定,毫无含糊闪烁之词,当有所本。如无新的证据,不便轻易否定。
在秦国“大索,逐客”(《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一个刚入秦的魏国人,仅因献一条计策就被任命为“国尉”(张守节《史记正义》:“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这个秦国最高军事长官职务,地位竟然在先期入秦的蒙武、李斯等人之上。而且秦王政对原本是“布衣”的尉缭子极为谦卑尊敬,以至“衣服食饮与缭同”。即使在得知尉缭子指责他“少恩而虎狼心”后也不动怒,而是加以挽留,并派李斯等人负责具体执行尉缭子兼并诸侯的战略计划。尉缭子入秦后所受到的礼遇和重用,超过了商鞅、张仪、范雎等著名客卿,但却不见其立有军功的记载。按秦制“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所有这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尉缭子入秦时年事已高,仅出谋划策而不能亲自带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后关于尉缭子的事迹没有任何记载,估计他入秦后不久即死去),年轻的秦王政委尉缭子以高位,正是为了借重他的名望和学识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尉缭子名下仅注“六国时”三字,后来许多学者对此颇有微词,但我们从前面的考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注法是简明而正确的。
在谈到尉缭子的生平时,还有一个疑难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尉缭子的“尉”字是姓还是官名的问题。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时认为:“尉,姓,缭,名也。”而钱穆认为:“尉乃其官名……而逸其姓也。”(《先秦诸子系年·尉缭辨》)近人多采取后一种说法,而笔者认为还是颜师古的说法可靠一些。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先是说大梁人尉缭来,以后才说他被任命为国尉。如果“尉”是他的官名,难道他在魏国也当国尉吗?据载晋国确也有国尉官职,魏承袭晋并常自称晋,当亦有之。但尉缭子入秦后却称“我布衣”,证明他并没在魏国做官。我国先秦时以官名为姓者虽不乏其例,但更多见的是以地名为姓者,如商鞅原姓公孙,叫公孙鞅,因他是卫国人,所以也叫卫鞅,入秦后被封在商地,所以又叫商鞅。明人汪心所修纂的《尉氏县志》确认尉缭的原籍在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尉氏战国时属魏地,距大梁不远,尉氏人亦可称为大梁人,与史书记载是一致的。
二、“两个尉缭”等错误说法辩驳
也是因为两条原始史料的纪年问题,还有人猜测历史上曾有两个尉缭子,一个是“战国末期秦国大臣”①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断定”杂家尉缭,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缭”②马非百:《先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其实这种“两个尉缭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无法否定尉缭子是大梁人这一明确记载,两人同名在历史上虽不乏其例,但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出现两个同名都叫尉缭子的大梁学者,其著作内容又相近,这种戏剧性的过分巧合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由于持“梁惠王时人说”的学者和持“秦始皇时人说”的学者至今都不能说服对方,而他们各自所依据的那条唯一的原始材料,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又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引为直接旁证的记载。因此,他们为了鉴别《尉缭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都试图从该书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中去寻求内证。
“梁惠王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作者面对的国家,矛盾重重……民流地废,农战不修,‘人有饥色,马有瘠形’,民无定伍,军无定制,‘武士不选’,贤能不用。这样的国家,只可能是日趋衰落的梁,而不可能是生气勃勃的秦!”(二)“作者面对的国君,问题严重,他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倾向于‘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唯心谬论,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路线上,也不懂得任地、制民的富国强兵之道……这个人,只有可能是败国之君梁惠王,而不可能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三)“书中引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时间顺序上看,只引证到战国前期的吴起为止……从引证的历史事件看,唯独吴起以法治军、与士卒同甘苦而‘天下莫当’的事迹最多最详,其中特别是两次提到了‘吴起与秦战’这一富有历史特征的史实。”①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2期。(四)“尉缭在本书中,不断地对‘世将’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正确地反映士人向贵族争夺政权的战国早期时代背景。”②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1月版。
“秦始皇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战国时代战争投入的兵员和持续的时间,在早、中、晚期是有明显差别的,《尉缭子》反映了战国晚期的战争规模。”(二)“《尉缭子》体现了战国晚期独有的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三)“1974年发现的秦陵兵马俑阵,是战国晚期战场情况的写照,它的情况往往能与《尉缭子》所述互相吻合。”(四)“《尉缭子》……记有许多军制条令,往往能与《商君书》和云梦秦简的精神相呼应,证明其作者应与秦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当是秦始皇任为国尉的大梁人尉缭。”③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4期。
显然,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这些理由,除个别问题外,都是持之有故的。但是,他们对于对方提出的理由,却都不能给予全面而有足够说服力的反驳。这个矛盾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当我们遍集有关史料并经过反复分析后发现:如果把现有的各种历史记载联系起来考察,上述两种观点实际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子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时的尉缭子本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之前,对仅存的关于尉缭子事迹的两条原始记载,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执意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条!
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引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有人曾认为尉缭子的“许多重要议论与商鞅见解完全不同”④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还有人认为:“与其说尉缭‘为商君学’,不如说‘为荀子学’或曰‘为吕氏学’更合适一些。”⑤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4期。而我们将《尉缭子》与《商君书》及其他古籍中所记载的言论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观点接近、主张相同。至于存在某些分歧,其实那很自然,因为战国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即使是同一学派的人,其思想观点也未必完全一致。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嫡传弟子,他们与荀子的观点尚有分歧,何况尉缭子与商鞅的经历和所处时代都不相同。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时尉缭子也许还没有出生。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①商务印书馆1927年发行。中指出:“为商君学者,盖不必亲受业。”这是很有见地的。正因为尉缭子的主张对商鞅的刑名之学既有继承,又有变异,所以他的著作才被班固分别列在了“杂家”和“兵形势家”。总之,刘向说“缭为商君学”完全讲得通。而其他一些说法如尉缭子是“魏人鬼谷高弟”②《子书百家》本《尉缭子》序,湖北崇文书局开雕。“尉缭作为信陵君的门客”③《子书百家》本《尉缭子》序,湖北崇文书局开雕。以及前面谈到的说尉缭子“为荀子学”或曰“为吕氏学”等等,大都出于论者臆测,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可能性,但是只可存疑而没有任何史料作为确凿的依据。
三、尉缭子就是兵书《尉缭子》的述作者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杂家”类的《尉缭》有二十九篇,列在“兵形势家”类的《尉缭》有三十一篇。由于班固没有对两者之间关系给予说明,而流传至今的《尉缭子》仅有二十四篇,与上述两种《尉缭》的篇数均不相符,这就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银雀山竹简《尉缭子》出土之后,对其述作者问题的争论更加热烈、深入了,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概括起来讲,学术界曾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一)认为“实际上就只有一种《尉缭》”,“班固的《汉志》(实际上是刘歆的《七略》)把这部书既分在了杂家,又分在了兵形势家内,就因为他用的是互著法”④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2期。。(二)认为“杂家《尉缭》、兵家《尉缭》本是一部著作”,“却被《汉书》的作者班固分在‘杂家’与‘兵家’两大类中,当成了两部书,从而引起了误解,造成了混乱”,“今本《尉缭子》就是班固所说的《尉缭》”。⑤徐召勋:《互著与别载》,载《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三)认为“兵家和杂家《尉缭》显然是内容不同仅同书名的两本书”,“杂家书没有流传下来,今本是兵形势家《尉缭》”。⑥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文物》1978年5期。(四)认为“今本《尉缭子》当是原杂家书”,“兵家书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的正是隋唐时的杂家《尉缭子》”。⑦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
我们认为,以上四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其难以解释的矛盾,何法周的《<尉缭子>与互著法——三论<尉缭子>》⑧何法周:《<尉缭子>与互著法——三论<尉缭子>》,《史学月刊》1986年2期。一文和龚留柱的《<尉缭子>考辨》⑨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4期。分别对上述第一和第二、三、四种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驳难,可以参看。龚留柱的文章中,根据三方面的线索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认为今本《尉缭子》“应该是原杂家和兵家书的两个残本合编而成的一部古代兵书,前十二篇基本属于原杂家《尉缭》的内容,后十二篇应为原兵家《尉缭》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应作些补充和说明。
我们判断一部古书属于哪家学派的著作,仍应首先从分析其内容的思想倾向出发。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兵形势家”的概括是:“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他对“杂家”的概括是:“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从概念上看,杂家与兵形势家确有不同,但实际上《汉书·艺文志》对所谓“杂家”书和所谓“兵形势家”书进行的划分并不十分科学,明显带有班固或刘向父子、任宏等人主观的成分。如:在《汉书·艺文志》中,同是商鞅的著作,被分在“法家类”的有《商君》二十九篇,被分在“兵权谋家类”的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同是吴起的著作,被分在“杂家类”的有《吴子》一篇,被分在“兵权谋家类”的有《吴起》四十八篇;同是伍子胥的著作,被分在“杂家类”的有《伍子胥》八篇,被分在“兵技巧家类”的有《伍子胥》十篇。我们从杂家学派的代表作《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可以看出,所谓“杂家”其实就是杂取各家学派观点而成的。因此,兵形势家思想作为杂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未尝不可。另外,班固还在“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句下注有“入兵法”三个字。这些都说明“杂家《尉缭》”与“兵形势家《尉缭》”只有内容侧重上的某些不同,而不能断然地分为两部书。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尉缭子》同许多战国时代的作品一样,并非一部系统的专著,而是由尉缭子或其弟子根据他的言论在不同时期写成的几十篇作品的合编。最初大约共有六十篇,其中二十九篇的内容杂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具有杂家的色彩,于是到了汉代就被刘歆、班固等列在了“杂家类”,而另外三十一篇适应战国晚期形势、类似军令实录的作品,就被任宏、班固等列在了“兵形势家类”。东汉以后,逐渐佚失,到了宋代《武经七书》本《尉缭子》成书后,成为官方推广的读物,而古本《尉缭》(包括原杂家部分和原兵形势家部分)因不受重视而失传了。在宋代以前的书籍中,还能见到古本《尉缭》佚文的零星词句。唐代徐坚所著《初学记》卷二十四句“宅第八”引《尉缭子》曰:“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历代之宅。”李昉等编著的《太平御览》引《尉缭子》曰:“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缨。”这两段文字是今本《尉缭子》中没有的。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引尉缭子入秦后的两段议论,虽也不见于今本,但却与《兵教》篇的某些内容接近,可能也是源自《尉缭子》今已佚失的部分。另外,在银雀山出土的竹简中,除了六篇与今本《尉缭子》相同的内容外,还有一些载有《尉缭子》佚文的零散竹简,如:“小鱼鱼渊而禽其鱼,中鱼鱼国而禽其士大夫,大鱼鱼天下而禽其万国诸侯。”这段话就具有鲜明的思想和语言特点。我们应该把这些文字和出土竹简一起作为研究《尉缭子》的重要补充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先秦兵书《尉缭子》述作者就是尉缭子本人。
四、尉缭子军事思想评价
(一)进步的战争观
在《尉缭子》一书中,尉缭子吸取了兵家以及其他学派前辈的有关“义兵”和“以战去战”等思想,结合他自己对战争问题的深刻理解,构成了本书进步的战争观。尉缭子根据各种战争的不同特点,将它们明确地划分为“挟义而战”(《攻权》篇)和“争私结怨”(《攻权》篇)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大类。他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支持进行那种“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武议》篇)、“伐暴乱而定仁义”(《兵令下》篇)的战争,认为这有利于维护“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武议》篇)的社会安定局面;反对发动那种“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武议》篇)的战争,认为这样滥施武力,杀害无辜,是强盗的行径,会造成社会的极大动乱。尉缭子的这种说法同那些表面上鼓吹“去兵”、实际上却穷兵黩武的虚伪言行相比较,他的“义战”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重视战略决策的作用
所谓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策划和指导”①《辞海》战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尉缭子对于战略决策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在《尉缭子》一书中有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有“道胜”“威胜”和“力胜”三种途径②《战威》篇。,而最高明的是“道胜”,即靠谋略取得的胜利。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膑曾说过:“知道,胜。……不知道,不胜。”③《孙膑兵法·篡卒》。他所说的“道”就是尉缭子所说的“兵道”④《战权》篇。,包括天时、地利、人心、敌情以及作战方式等等,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因此,孙膑认为指挥作战必须“知道”,即认识战争的本质和掌握战争的规律。尉缭子也强调要“在乎道之所极”⑤《战权》篇。,坚持实事求是的作战方针,战前“高之以廊庙之论”⑥《战权》篇。,制订周密仔细的战争计划,“安其危,去其患,以智决之”⑦《战权》篇。,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造成一种压倒敌人的威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以“权”字为核心的用兵之道
“权”是先秦兵书中被常常用及的一个军事概念,《尉缭子》中对此也有较多的论述,这集中体现在三篇以“权”字命名的文章中。在《兵权》篇中,尉缭子着重谈到了集中优势兵力这一用兵原则,他指出:“兵以静固,以专胜。”认为部队必须兵力集中,“动静如身”,有很强的机动性和对敌进行突然打击的能力,才能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他还告诫说:“搕战无胜兵,佻战无全气。”反对打无计划、无准备的仗,提出要“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只有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作了对比研究之后,才有赢得战争胜利的把握。“是故兵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在《守权》篇中,尉缭子则具体论述了关于城市防守的战术问题,除了谈到守城的必要条件和城防布局等问题之外,他还重点论述了城内守军与城外援军如何相互配合,“中外相应”,巧妙地打击围城之敌,这是对守城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战权》篇中,尉缭子引用“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就是说谁能在战争中及时而正确地运用权谋,谁就能夺得战争的主动权。尉缭子认为,用兵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去迷惑敌人,使其摸不清我军的真实意图,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尉缭子还提出了“故兵贵先”的观点,主张在战争中要先机而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但他所说的“贵先”并不是一味地快速进攻,而是与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密切结合的。尉缭子特别反对那种没有多少胜利的把握就“轻进而求战”的做法,指出这样“必丧其权”。他认为:“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当进时要不失时机,先发制人,当止时切不可贪功冒进,招致失败。
(四)灵活多变的“奇正”战术
“正兵合战,出奇制胜”,是历代兵家指挥作战的一种常用方式,也是我国古典兵法中经常被论及的一个重要内容。春秋时代的兵家先驱孙武就曾提出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①《孙子兵法·势篇》。的观点,尉缭子则从战国时代所面临的新的战争特点出发,更加重视对“奇正多变”用兵韬略的研究,《尉缭子》即是一部较早系统地讲述“奇正”问题的军事专著。在本书中,作者根据兵形势家“轻疾制敌”、出奇制胜的作战原则,明确指出:“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②《兵令上》篇。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运用正兵、奇兵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法。尉缭子尤为注重在训练和实战中打破一成不变的战法,他讲究奇正配合,避实击虚,主张运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他所提倡组建的带有奇兵性质的兴军、踵军等部队,以及他提出使用这些奇兵的方式,都是兵家关于“奇正”军事理论的具体应用。《尉缭子》中说过:“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③《勒卒令》篇。这段精辟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其“奇正多变”作战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五)指出选拔将帅的重要作用
《尉缭子》一书中贯穿着比较进步的人才思想,尉缭子很重视为部队选拔得力的指挥者,在许多篇中都重点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将帅与广大士卒形象地比喻为“心”与“四肢关节”之间的关系,“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比背”④《攻权》篇。。他以吴起等人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事迹为榜样,主张:“勤劳之师,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盖,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险,将必下步。军井通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饥饱、劳逸、寒暑必身度之。”⑤《战威》篇。在谈论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时,尉缭子指出,他们身系国家安危,责任重大。不仅要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且要能够随机应变地指挥作战,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坚定的必胜信心。这样在“临难决战”时,就可以做到“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⑥《兵谈》篇。,“无主于后,无敌于前”⑦《武议》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尉缭子认为,作为一军的统帅,不仅需要具备很高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应该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他着重指出:“凡将,理官也。”⑧《将理》篇。就是说将帅既然担负着像法官一样的职责,掌握着生杀大权,就应“不私于一人”⑨《将理》篇。,公正地处置各种事情,以确保部队的团结。用兵打仗也一定要慎重,“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⑩《兵谈》篇。,千万不可意气用事,轻易发动战争。他认为,不轻易发怒,不贪图钱财,胸怀宽阔和清正廉洁是一名指挥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而“心狂”——狂妄自大、“耳聋”——信息不灵、“目盲”——眼光短浅,则是为将帅者的三大弊病,应坚决地加以避免。
(六)对部队训练和管理等问题的论述
尉缭子深知完善的管理和严格的训练对于部队加强战斗力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尉缭子》一书中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着墨较多。在《兵谈》篇中,他指出平时积极训练,治军有方,使部队纪律严明,常备不懈,一旦战争爆发,就能进退得宜,运用自如,“兵之所及”,无往不胜。尉缭子还强调,在战场上能够有高昂的士气,“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者胜成去”。在《勒卒令》篇中,他参照吴起治军的成功经验,着重叙述了金、鼓、铃、旗的指挥作用,以及使用这些信号指挥部队训练和作战的有关步骤、措施等。尉缭子不仅一一说明了“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的各种规定,而且强调了协同指挥、号令一致在训练和作战中的关键作用,他要求:“将、帅、伯,其心一也。”特别是他还效法吴起,采用了“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的先进训练方法。在《兵令上》篇中,他详细讲述了部队临敌布阵的方法:“兵之恒陈,有向敌者,有内向者,有立陈者,有坐陈者。向敌所以备外也,内向所以顾中也,立陈所以行也,坐陈所以止也。立、坐之陈,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坐之兵剑、斧,立之兵戟、弩,将亦居中。”尉缭子的这种阵法,具有很强的实战价值,考古工作者从陕西秦始皇陵前发掘的陶俑坑中所见到的,正是这种军阵形式。在《分塞令》篇中,他把阵法与宿营联系起来,要求按照“中军,左、右、前、后军”各支部队列阵时的“分地”来设立军营,据险而守。在各营区的周围“皆营其沟域”,“方之以行垣”,以防备敌军偷袭。他还建议在营区内实行严格的警戒制度和通行规定,以防范间谍混入。将、帅、伯各级军官在宿营时都要各就各位,不得有误。任何人在营区内不许随便走动,如有违犯就要受到惩罚。在《兵教上》篇中,他从研究将帅、士卒的心理出发,主张“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在部队中实施既严格又讲求方式方法的军事训练,希望以此提高士卒的训练情绪,保证部队的训练质量,“令守者必固,战者必斗”,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协调一致。
(七)提倡明赏正罚,以法治军
尉缭子同其他许多卓越的军事家一样,在其著作中自始至终大力提倡“明赏正罚”,以法治理军队。他首先强调了在军队中确立法制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凡诛者,所以明武也。”①《武议》篇。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②《重刑令》篇。,才能真正做到“赏如山,罚如豁”③《兵教下》篇。,“刑赏明省,畏诛重奸”④《原官》篇。。尉缭子严厉地批评了战场上由于将领的无能而产生的种种无制之兵的现象,一再要求:“凡兵,制必先定。”⑤《制谈》篇。指出:“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⑥《制谈》篇。这样部队才能统一号令,协力作战,“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⑦《制谈》篇。。
尉缭子虽然也赞成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武力来贯彻实施法令,但是他坚决反对滥施刑罚,残酷镇压,而是主张严明法制和道德教育并重,提出:“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⑧《战威》篇。“夫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攻权》)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尉缭子坚决主张执法要公正,“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兵令上》)。在治理军队时,必须打破等级的限制进行奖赏和惩罚。他说:“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武议》)认为只要敢于“刑上究,赏下流”,就能“诛一人无失刑”(《制谈》)、“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伍制令》),使大家心悦诚服,真正调动起将吏士卒们杀敌立功的积极性。
(八)从“杀”字看“兵贵精,不贵多”的裁军思想
“兵贵精,不贵多”的裁军思想是《尉缭子》全书中主要的闪光点之一。过去曾有不少人认为,《尉缭子》中有片面鼓吹严刑峻法的“思想糟粕”,其根据是,在《兵令下》篇中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一段话,过去论者凡言及此,大都将“杀”字释为诛杀、杀人,认为这是尉缭子在鼓吹大肆诛杀所属士卒,并且将这一点作为《尉缭子》全书中一个主要的“糟粕”而加以斥责。明代刘寅就将本篇中的“杀”字释为诛杀。①见清代朱墉辑著的《重刻武经七书汇解》。清人姚际恒在其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中认为:“(《尉缭子》)教人以杀,垂之于书,尤堪痛恨!必焚其书然后可也。”在华陆综的《尉缭子注释》②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台湾学者刘仲平的《尉缭子今注今释》③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发行。的译文中,都将本篇中出现的“杀”字解为“诛杀”“残杀”。刘路在《<尉缭子>及其思想初探》④刘路:《<尉缭子>及其思想初探》,《文史哲》1979年2期。一文中,指摘本篇的“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一段话是“阶级的局限性”“走向极端”。祝瑞开在《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⑤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也认为尉缭子的上述一段话,是“鼓动对‘不用命’的士卒进行血腥的残杀。这反映了封建主对待农奴的残酷本性,也是这时阶级矛盾激化在军事上的反映”。霍印章和张实群在他们各自的近作《孙膑兵法浅说》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和《<尉缭子>对军事心理的分析》⑦《国防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1期。中,甚至分别谴责本篇的内容“其思想是消极而反动的,根本不把士卒看作是人,主张将帅杀自己的士卒越多越好,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凶恶的本性,简直是一派荒谬绝伦的胡言”,“这是其剥削阶级奴役士兵的阶级本质的表现”。
我们认为,上述这些对“杀”字的译释和解读完全误解了尉缭子的本意。因此,对他的种种批评、责难也都是无的放矢、不能成立的。
“杀”字在我国先秦两汉时的文献中固然多用作“诛杀”“杀死”,但是在本篇中出现的六个“杀”字,作者都不是作为“诛杀”来讲的,而是作为“削减”“减省”来用的,亦可引申为“裁减”,我们试从四个方面为此说提供证据。
第一,《兵令下》篇的前一篇《兵令上》篇中,作者指出:“王者伐暴乱而定仁义也”,“兵以安静治,以暴疾乱”。这与所谓尉缭子主张无故屠杀士卒的说法无论如何也统一不起来。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孙膑兵法·杀士篇》释文①文物出版社1975年2月版。和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的《武经七书注译·尉缭子》②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也都发现并试图解释这个矛盾,他们将《兵令下》篇中的“杀”字释作“牺牲”,引申为使士卒甘愿去战死的意思。这虽然比直接译为“诛杀”婉转一些,但似乎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与本篇及前面各篇的思想体系仍然难以统一,其意未洽。蒋伯潜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矛盾,他所著的《诸子通考·诸子著述考》③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中有这样一番议论:“(《尉缭子》)其论兵也,尝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其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之所加也,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何其仁也!但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威加海内;能杀十三者,力加诸侯;能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又何其暴也?同出一书,何以自相矛盾如是?”虽然蒋先生由此得出《尉缭子》“疑系伪书,不足观也”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但他提出的质疑还是能给人以启迪。
尉缭子的确主张以法治军,他在本篇及其他篇中规定的一些刑令也确实非常严酷。但是,仔细阅读《兵令下》篇后可以看出,作者是主张有罪则严惩,无罪则不惩的,并且将“全明之赏”与“必死之刑”结合起来使用,以赏罚分明、恩威并重的方法来治军。他在本篇详尽地规定了何罪“尽斩之”“皆当斩”以及何种情况下“与同罪”“尽同罪”的同时,也阐述了在何种情况下“赏”;在何种情况下“赦之”“罪赦”。逻辑严谨,条理清楚,在某种意义上确乎如作者所自诩是“赏明如日月,信比四时”。这也与前面各篇中所一再主张的“明赏于前,决罚于后”④《制谈》篇。“审法制,明赏罚”⑤《战威》篇。的思想是相互联系、完全一致的。那么,此处尉缭子怎么会突然又提出,无缘无故地将自家军卒屠杀掉一半或十分之几,这岂不是自己破坏自己制定的军法吗?实在是于情不合,于理难通。况且怎样申明军纪,禁止士卒逃亡,本篇前文已有了惩治的具体办法和规定,在论述层次上也不需要再重复赘述,多费口舌。
第二,从《尉缭子》的全书内容来看,主张精兵慎战和鼓励爱卒,是作者军事思想精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尉缭子在各篇中多次明确阐述了要精减士卒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存有生力量的观点。在《兵谈》篇中,他告诫梁惠王:“兵起非可以忿也。”认为“车不发轫,甲不出囊,而威服天下”,才是治军者所追求的;在《制谈》篇中,他严厉谴责了“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这种“资敌而伤我甚焉,世将不能禁”的现象,反对无辜牺牲士卒的生命;在《战威》篇中,他强调对待士卒民众,要“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在《兵权》篇中,他谈到了使士卒悦服和畏威的辩证关系:“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在《十二陵》篇中,他提出:“孽在与杀戮。”并把它视为治国、治军时应避免的十二种错误做法之一;在《武议》篇中,他一开始即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在《将理》篇中,他主张执法要公正,反对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并警告梁惠王:“今申戍十万之众,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 ……在本篇中,他更是强调指出:“军之利害,在国之名实。名在军而实居于家,{军}不得其实,家不得其名。聚卒为军,有空名而无实……”士卒逃亡后,国民仍要负担他的费用,“是有一军之名,而有二实之出,国内空虚尽竭”,不可不虑。对此尉缭子郑重提出了效法前人裁减军队的办法,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之后,尉缭子又总结说:“百万之众而不战,不如万人之尸;万人而不死,不如百人之鬼。”全篇前后紧密相连,文辞一气呵成,顺理成章,又与其他各篇彼此呼应,思想一致。其意甚明,毋庸置疑。
第三,从“杀”字在古籍中的不同运用来看。它的含义同其发声相关,在《广韵》中“杀”字有两读,其声母相同而韵母不同,一为“所八切”的入声字,读shā(εατ),其义为“杀死”“诛杀”;一为“所拜切”的去声字,读shài(εαi),其意为“减少”“减省”。《尉缭子·兵令下》中出现的六个“杀”字都应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先秦两汉的古籍中,“杀”字的这种用法是很多见的,下面试举一些例子:
(一)《诗经·幽风·鸱鸮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①《毛传》谓:“谯谯,杀也。”
(二)《论语·乡党》:“非惟裳,必杀之。”
(三)《周礼·地官·廩人》:“诏王杀邦用。”
(四)《周礼·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由二聚万民……八曰杀哀。”
(五)《周礼·考工记·轮人》:“参分其幅之长,而杀其一。”
(六)《周礼·考工记·矢人》:“羽丰则迟,羽杀则趮。”
(七)《公羊传·僖公廿二年》:“春秋词繁而不杀者,正也。”
(八)《庄子·天运》:“尧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
(九)《荀子·正论》:“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
(十)《荀子·大略》:“仁之杀也。”
(十一)《荀子·大略》:“冰泮杀内。”
(十二)《荀子·礼论》:“缌小攻以为杀。”
(十三)《礼记·乐记》:“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唯以杀。”
(十四)《礼记·乐记》:“是故志微唯杀之声作,而民思忧。”
(十五)《礼记·文王世子》:“亲亲之杀也。”
(十六)《礼记·玉藻》:“其杀六分而去一。”
(十七)《史记·礼书》:“以隆杀为要。”
(十八)《汉书·韦元成传》:“亲疏之杀。”
(十九)《汉书·杜邺传》:“阴义杀也。”
据古今许多学者的训释以及我们对各句前后文辞义的考察,以上例句中的“杀”字,都可解作“减少”“减省”。这样的例句,还可以举出许多。
第四,从先秦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争霸激烈、战争残酷,动辄杀人成千上万,多者也有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但是,无论在尉缭子之前还是与他同时代的“善用兵者”,均未见有屠杀士卒一半或者十分之三、十分之一的历史记载。试想,如果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无故诛杀自家军队中这么多的有生力量(或者如《武经七书注释·尉缭子》所说使半数士卒甘愿战死),那么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的。这样的将帅又怎能称得上“善用兵者”呢?
尉缭子当时如果是有意渲染,故弄玄虚,而他的后学弟子们又将这番谬误如此明显的“名言”记录下来,使其广为流传,并且奉为治军经典,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只有将《尉缭子·兵令下》的思想内容,放在战国时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吴子·励士篇》记载,战国前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曾向魏武侯建议:“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有死事之家,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尉缭子对吴起非常钦佩,将其视为治军的楷模,对于吴起“励士爱卒”的做法,他一定会效法学习,而绝不会反其道而行之。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先秦时代的其他兵家著作中,也都有与《尉缭子》大同小异的“兵贵精,不贵多”的治军思想,而战国时期运用这种思想治理军队从而富国强兵的也不乏其列。这里应当指出,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论述。《孙膑兵法·杀士篇》中也有“……杀士则士……”一句。据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和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考证,前一句中的“杀”字为伤亡之意,我同意他们的这种说法。孙武的意思是,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而城还攻不下来,这是盲目攻城的灾害。虽然《孙子兵法》此处对“杀”字的用法与《尉缭子·兵令下》有所不同,但是在主张慎战、减少士卒伤亡的认识上却极为相似。而后一句中的“杀”字,论者曾有不同解释,因竹简前后文字严重残缺,目前还难以判定其确切含义,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从《杀士》篇其他残简中“必审而行之”的内容来看,讲的似乎也是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杀士则士……”一句中的“杀”字,似也应解为减省之意,与《尉缭子·兵令下》中“杀”字的用法是一样的。
对“杀”字的正确解读,使我们可以对《尉缭子》全书及尉缭子本人的“精兵”“爱卒”思想得出全面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价。尉缭子的这种治军思想固然是站在他本阶级的立场上,受着历史的局限,而且也是同严刑峻法互为补充、交替施行的,但这毕竟是先秦兵家思想中的精华,是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尉缭子的军事哲学思想
《尉缭子》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军事思想的提出,都是以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在本书中,作者能够自觉地、鲜明地将自己的军事理论建筑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坚持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去论述战争问题,因此在《尉缭子》全书中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进步认识论。
兵阴阳家所宣扬的“天官、时日、阴阳、向背”思想,在战国时代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尉缭子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继承了西周、春秋以来朴素唯物论者“天人相分”的进步观点,以很多实际战例为依据,指出决定胜负的因素根本不是什么“阴阳向背”那一套,而在于人的主观因素。尉缭子从理论上反对兵阴阳家的错误思想,也反对“时日”“卜巫”“祷祠”等迷信做法,主张要面对现实,根据客观情况因势利导,努力进取,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天官》篇中,他明确指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在《战威》篇中,他又进一步总结说:“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尉缭子非常厌恶和蔑视那种靠迷信鬼神来进行战争的做法,他说:“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凶吉,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武议》)《孙子兵法》“计篇”中尚存有“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的观点;《吴子》中论兵,也还不能完全摆脱神鬼的束缚,它认为:“是以有道之主……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后乃举。”(《图国》)比较起来,可以看出尉缭子的认识较之孙武、吴起的认识,已经有了意义重大的飞跃。尉缭子的哲学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进化论和无神论特色,承认宇宙的客观存在及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性,而且能够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针对当时人们的某些观念,尉缭子提出了:“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这段很有勇气的话。正因为他具备了这样坚实的哲学基础,才使得其作品能够在先秦的军事著作中独树一帜,特点鲜明。
“气”在先秦时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各家的经典著作中对此都有论及。兵家著作也不例外,《孙子兵法·军争篇》讲:“故三军可夺气。”《吴子·料敌篇》讲:“先夺其气。”《尉缭子》中也将“气”这一概念直接用于阐述军事问题,尉缭子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战威》)意思是说在实际战争中,影响胜负的除了物质力量因素外,还有精神力量的因素。“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即一支军队的士气高低、精神状态如何,直接关系着战争的结局。由此,他进一步要求军队的指挥者要想方设法使部队提高士气,同时要千方百计地使敌人士气低落。
从理论上探索战争的实质问题,进而揭示出战争发生的根源,是先秦军事家们所面临的一大课题。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还没有能把政治与军事紧密地联系起来论述;成书于战国前期、中期的《吴起兵法》和《孙膑兵法》,虽然阐明了军事同政治的互相关系,并且提出了对付各种类型战争的比较具体的方略,但是它们对于战争本质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于战争性质的划分仍然是比较粗浅的,而《尉缭子》对此则在理论阐释上有所突破。作者首先根据政治性质的不同,把战争分为“狭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直接指明了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产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对于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尉缭子从辩证的角度提出见解:“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植};以武为表,以文为里;以武为外,以文为内。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败矣。”(《兵令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治对于战争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战争也对政治有很大的反作用。他把军事与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栋”(房梁)和“植”(立柱)的关系,二者缺一,房子就会倒塌。正如作者所描述的:“兵之用文武也,如响之应声,如影之随身也。”(《兵令下》)尉缭子认为,要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首先要求当权者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故兵胜于朝廷,胜于丧纪,胜于土功,胜于市井”(《兵谈》)。他主张把治军与治国特别是国家的改革结合起来。只有不断进行政治改革,国家才能真正治理好,只有治理好了国家,军队才能强大起来,才能在对外作战中保持强大的态势,取得“车不发轫,甲不出囊,而威服天下”(《兵谈》)和“兵不血刃而天下亲”(《武议》)的战略效果。而军队强大了,在战场上打了胜仗,反过来又保卫和促进了内部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是“战胜于外,福生于内,胜福相应,犹合符节”(《兵谈》)的名句。尉缭子还从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出发,指出部队作战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后盾,他特别强调要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只有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才能保证本国的军需供给,而不至于出现“出不足战,入不足守”(《武议》)的现象。尉缭子认为只有广大民众生活得到改善,“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武议》),国家也“有储蓄”(《治本》),富国强兵才可能真正实现。尉缭子的哲学思想,较之成书约早二百年的《孙子兵法》,在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的某些论述,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六.尉缭子的历史地位
我们不想否认《孙子兵法》在军事理论上的种种建树和巨大贡献,但是应当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并不能代表我国先秦军事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城市作用的提高、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斗激烈程度的加剧、武器装备的更新、战略战术的变化以及哲学思想的飞跃发展等等,都是在《孙子兵法》成书以后出现而又对军事理论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我们不能苛求孙武在春秋后期就对几百年后战争情况的变化,做出完全正确的预言。似乎可以这样说,《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兵家专著,它代表了我国先秦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先秦军事思想同其他思想一样,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它绝不会停止不前。《吴起兵法》和《孙膑兵法》分别代表了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期兵家思想的发展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以被分别称为先秦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高峰”。而生活在战国中晚期的尉缭子,有条件认识和研究最新的战争形势。《尉缭子》中也总结和吸取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在新的理论高度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因此我们认为,同韩非是先秦法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一样,尉缭子是先秦兵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同《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一样,《尉缭子》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
(责任编辑:周淑萍)
Study of Wei Liaozi’s Military Thinking
Xu Yong
Wei Liaozi approximately live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Hui of Liang and King Zheng of Qin. He is the dictation author of the famous military work Wei Liaozi , which has rich and varied military thinking with its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B22
A
2095-9176(2017)03-0086-14
2017-04-24
;徐勇,天津兵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教授。
Kew Words:Wei Liaozi; Militaris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ilitary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