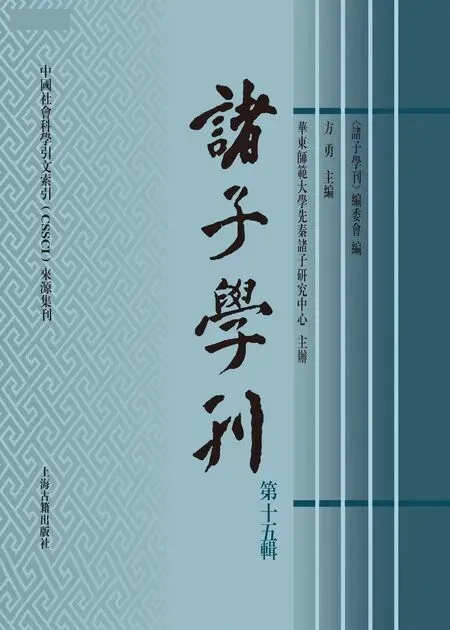白玉蟾《道德寶章》義理思想研究
2017-01-27臺灣林裕學
(臺灣) 林裕學
内容提要 白玉蟾爲宋代道教重要的代表人物,其内丹思想影響甚遠。其《道德寶章》亦爲南宋《老子》學之重要著作,歷來學者對此書探討多由以心合道、三教融合與内丹之學相應之觀點探討其内涵,對於此書之義理思想多概括在一個“心”底下,對於此書義理思想基礎甚少有系統地探討。在中國《老子》學發展過程中,自唐、宋以來多有注家以心性詮釋《老子》。至北宋末年,以心注解《老子》之詮釋進路已發展出初步理論架構。但今論《道德寶章》者多未將其義理思想置於《老子》學的詮釋進路發展脈絡中進行評價。故本文先論自唐代至北宋末年,以心性註解《老子》之詮釋進路,再析論《道德寶章》之義理思想,並將其置於唐宋以心注解《老子》之詮釋進路中探討其地位,希冀廓清白玉蟾《道德寶章》之義理思想面貌與在《老子》學史之地位。
關鍵詞 宋代老學 白玉蟾 《道德寶章》
前 言
白玉蟾爲宋代道教重要代表人物,論宋代道教不可略白玉蟾而言。其思想融合三教,丹道思想多有學者研究。其《道德寶章》爲注解《老子》之作,其内容亦爲南宋學者所重。但歷來研究白玉蟾者,多論其内丹心法,對於《道德寶章》思想内容則較少深入研究。目前對《道德寶章》有較完整研究者爲劉固盛《道教老學史》一書,其將白玉蟾置於重玄學之系統中,言白玉蟾論《老子》思想乃本於北宋張伯端,並言其以心解《老》乃爲其獨創[注]劉固盛言:“道教南宗向來有重視修心的傳統……受此影響,白玉蟾同樣是從本體與超越的高度把握心範疇的,這一思想也體現在對《老子》的詮釋上,在《道德寶章》中,白玉蟾不僅把心看作萬法現象後面的依據,而且把心釋爲修道得道的根基,並創造性地把心和老子之道溝通起來,從而體現出他詮釋《老子》的獨特風格。”(《道教老學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頁。)此以白玉蟾承張伯端道教思想,強調修心,其注《老子》亦強調心之意涵與作用,故以心解《老》爲《道德寶章》之重要特色,此説無誤。但劉固盛言白玉蟾創造性地將心與老子之道溝通起來,此説尚有可討論之處。北宋《老子》注家即有以心性詮釋《老子》者,如蘇轍、王雱即以心性詮釋《老子》之道。另外,與張伯端約同時的陳景元注《老》即有心性之説。故以心解《老》應非白玉蟾之創造性詮釋。,此説多爲學者所引。但究《老子》學之發展史,唐代成玄英《老子義疏》即有以心解《老》之詮釋進路,宋代注家如陳景元、蘇轍、王雱皆有以心解《老》之詮釋特色。這些注家,有文人,也有道士,其立場雖異,但其注《老子》時,皆以心性思想詮釋《老子》之思想。
因此,論《道德寶章》之思想,需先廓清宋代以來以心性解《老子》詮釋進路的發展,再以《道德寶章》爲主,析論白玉蟾透過詮釋《老子》所欲表現的思想内容[注]《老子》學研究離不開《老子》注本研究,由注本所呈現之義理脈絡,以明注家對《老子》義理之闡發,並建構其透過詮解《老子》所欲呈現之思想面貌。對於注本義理思想的研究,劉笑敢嘗言:“這是兩個方向的解讀: 一方面是面向歷史和古代文本的回溯的探尋,另一方面是向現實和未來而産生的感受和思考。從理論上,這兩種定向顯然是有矛盾和衝突的;但是從實際的詮釋過程來説,這兩種定向或過程是難以剥離的,也很少有詮釋者自覺地討論這兩種定向之間的關係問題。”(《老子古今》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頁。)詮釋古代經典方式有二,一是盡量接近文本原意,此爲“我注六經”之詮釋方向;一爲注家透過闡釋文本,發展自身之思想系統,此乃“六經注我”之詮釋方向。在理論上,回歸文本原意與面向現實和未來具有矛盾與衝突。但在實際詮釋過程中,以回歸文本原意爲詮釋方式者,無法完全背離主觀認知以建構原意,故完全回歸文本原意實不可得;而以面向現實和未來爲詮釋方式者,無法脱離文本而闡釋己意。因此,完全面向現實和未來亦不可得。所以回歸文本原意與面向現實和未來並存於實際詮釋過程中。,以明白玉蟾《道德寶章》在宋代以心性解《老子》詮釋進路之地位[注]《老子》學除了探討《老子》本義外,更包括各代注家與《老子》文本之視域融合,在注家思想與《老子》文本兩種不同視域下形成老子思想之新義,形成歷代老子學豐富多元之思想面貌。對於老子學之内涵,陳德和認爲:“唐先生之老子學完整地説固可包含着一部老學史,且它無疑就是一部老子道概念的詮釋史或老學的創造史,因爲他顯然同情地肯定歷代學者對老學探討結果的合適性,卻又不以何時何派的觀點足以朗現老學全部義藴並能够定於一尊而取代别家之詮釋者,這不啻承認詮釋者彼此間的各異其趣不外乎屬於‘詮釋的距離’,至於形成的原因則是由於彼此間都志在依附時代以發現或另開文本之意涵而非務必倒轉歷史去尋找文本締造時之原義的緣故,不過他們之所以可以被認爲是老子的追隨者,則是由於他們的詮釋結果都不背於老子智慧與本懷。”(《道家思想的哲學詮釋》,里仁書局2005年版,第52頁。)此論唐君毅之老子學涵括《老子》詮釋史與老子思想之創造史,歷代老子學皆以歷代《老子》注與相關討論文獻爲基礎,次第建立起理論規模,故中國老子學史即是歷代《老子》注之詮釋史。宋代《老子》學發展脈絡即繫於諸家注解《老子》之作。本文即透過析論白玉蟾詮釋《老子》之義理内涵,以明白玉蟾對《老子》本義之重建與創造之處,並據此衡確《道德寶章》於宋代以心性解《老子》詮釋進路之地位。。
一、 唐宋以心性解《老子》詮釋進路之發展
觀中國《老子》學發展,唐代以前注家多着重闡發形上道體與有、無之理。時至唐代,成玄英糅合佛教之説,發展重玄之理,並嘗以心注解《老子》。李榮發展成玄英之學,亦以心性注解《老子》。時至北宋,心性思想已成爲時代學風,陳景元、王安石、蘇轍與王雱皆有以心性思想詮説《老子》義理。以下分唐代與北宋探討白玉蟾之前以心性解《老子》之發展成果。内容分述如下:
(一) 唐代以心性解《老子》詮釋進路之發展
唐代以降,以心性思想詮釋《老子》漸爲《老子》學的重要發展方向。自成玄英、李榮注《老子》即言心性之理。成玄英《道德經義疏》對“正性”多所討論,其曰:“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注]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508頁。道本自然以化萬物,萬物稟正性而生成。又云:“道者,虚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注]同上書,第502頁。成玄英以道法自然,其體虚通,其化萬物則衆生皆有“自然正性”,故“虚通”與“正性”皆爲道也[注]劉固盛言:“何謂‘自然正性’呢?這是就人的本性來説的,人的本性自然純一,清浄澹泊,無欲無念,無爲無滯,此即自然正性。”(《道教老學史》,第122頁。)此以人初生之時,其性自然純一,無有欲念,亦無所滯也。。成玄英以“自然正性”言人稟道而生,皆具自然正性,建立以正性體道之心性理論。《道德經義疏》言:“道以虚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注]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第375頁。衆生正性與道體虚通皆爲一,則人可復其正性以觀道體虚通也。《道德經義疏》云:
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囂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不燭。……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違順兩空,故能容物也。[注]同上書,第408頁。
“真性”即“正性”也,“命者”則爲人之生存。人透過修養,心凝神寂以復真性。人歸於真性,則無所欲求,亦無滯於執。歸於自然正性,則能朗照萬物;順道而爲,則順生。成玄英以“真性惠命”言歸復正性,無所滯執,朗照萬物,以惠其命。並指出達致“真性惠命”之工夫在於“心神凝寂”,其曰:“欲得玄虚極妙之果者,須静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注]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第407頁。此言欲達虚通玄妙之境,須通過心之工夫。“静心”即“心神凝寂”也,心神凝寂以守一中之道,無滯於有、無,方可達致虚通玄妙之境。此即《道德經義疏》所言:“天道,自然之理也。隳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内朗,覩見自然之理。”[注]同上書,第471頁。坐忘静心,忘遺感官欲望,以心登入虚通之境,知道體生化之妙,以見自然之理也。對於心之修養工夫,《道德經義疏》又云:
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恆虚極,故言不亂也。……既外無可欲之境,内無可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幻,後又心虚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注]同上書,第382~383頁。
心神凝寂則不滯,不滯而知有形可欲者,皆爲道妙化生,其本於虚通,皆虚幻也。不滯之心知可欲有形皆虚幻,恣其耳目亦無所見也。故言外無可欲之境,内無能欲之心,不滯於有、無以至内外無欲,此爲一中之道,即爲“玄”也。再以不滯遣内外無欲,心境兩忘,即心無心以至虚通,此爲“重玄”也。心達虚通之境,明道體虚通而具化生之妙,故體妙一也。以心體道,則知物我皆道所化生,物我可等齊觀之,而無拘於形名之别。體道則無滯於有欲之境與無欲之心,境智兩忘以治天下,依自然之理而爲,則無不正之治也。透過重玄之理,成玄英建構“正性”與“虚通”一貫之理論。在此理論下,人可復歸正性以達虚通之境,其修養工夫繫於心之作用。
成玄英後,李榮以中道破兩邊之執,以達虚極之道境。對於體道工夫,其《道德經注》云:“唯道集虚,虚心懷道。道在物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注]同上書,第570頁。言以虚心以懷道,得以成仙。得道成仙之關鍵爲“心”,其就“心”以論體道之工夫。其《道德經注》曰:
日月迥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定,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本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時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泯是非以契道,遣情欲以凝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困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内,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注]同上書,第573頁。
以心合道則能明日月運行、陰陽更迭之理,法天地之道以至於無心,無心則無執於口目聲色之欲。心無執於欲,則能泯是非以守中,守中以歸於真道也。若執於感官欲望,則形逐欲於外,心因逐欲而倦疲,百年之身一如朝露,逝而無存。故心無欲體道,體道則知天地萬物死生更迭、生生不息之理。無心體道則無執於死生,此即“輕死”之義也。李榮言“心”,以虚心體道察萬物生生之理,其言體道皆不離“心”。《道德經注》云:
心迷得失,知近不知遠,情昏真僞,識淺不識深,但悦塵垢之小行,反笑清虚之大道。道深甚奥,上士之所難知,微妙玄通,下愚故非易識,今笑之不能令真使混濁,適足彰道之清遠也。物情不一,取捨異心,聖人設法,無教無不教,反情向背,有信有不信也。[注]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第619頁。
人心困於得失,其觀事物,只知近淺表象,未明深遠道體。故聞清虚之道而笑之。道體微妙玄通,故上士難知,下愚亦不識。世人聞道而笑,未濁真道,反彰其清虚深遠也。聖人知此,設法立教,以化世人。世人觀之,依心以取舍,上士之心近於道,能得聖人之法;下士昧於道,未識聖人之教也。上士與下愚之别,僅在其心。
李榮論修養工夫,盡爲心上之工夫。《道德經注》曰:
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虚極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内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染於聲色。内外清静,故曰明。物我皆通,故言智。[注]同上書,第607頁。
清重玄之路以達虚極之道境,達於道境以觀衆生,則知萬境皆空之理;臻於道境以觀自身,則知其身非有。知其身非有,則無逐於名利。知萬境皆空者,則不染於聲色。“萬境皆空”與“其身非有”皆爲内心之境界,要達致此境界,則須通過“心”之修養工夫。《道德經注》曰:“有道之人,遣情去欲,罪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善積成慶,幽顯咸享。惡積成殃,存亡俱累。”[注]同上書,第627頁。志於道者,遣去情欲而無存於心,則禍除矣。但無識於道者,放縱心性,馳於情欲,招致禍害。心無情欲以虚通,體道於内,行道於外,故曰“積善成慶,幽顯咸享”也。此以“遣情去欲”爲修養工夫,其以心存情欲則昧於道,當去情欲以體道。《道德經注》又云:“浴玄流以洗心,滌也。盪靈風以遣累,除也。内外圓静,同水鏡之清凝。表裏真明,絶珠玉之瑕纇也。”[注]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第576~577頁。此直言“洗心”爲修養工夫,心透過重玄之理,以玄遣有無之滯。有無之滯既遣,則心無情欲。再以玄遣玄,則心通於虚極之境。心達虚極,猶如水鏡清明,以映事物之本。心虚極以體道,體道以明本,心内身外皆圓静澄明。
(二) 北宋以心性解《老子》詮釋進路之發展
北宋學者爲復興儒學,吸收佛、道思想,援用佛、道思想以建構儒學之本體與心性理論,故富有形上思想特色之《老子》受宋代學者重視。且唐代成玄英、李榮以重玄解《老》,其論道體,亦言心性。而宋代承隋唐以重玄解《老》之義理發展,以心性詮釋《老子》之言,賦予《老子》心性思想之意義,此乃宋代《老子》注之突破。劉固盛言:“儒、道、釋三教在宋元老學中得到了統一,它們共同影響着老學的發展。從哲學層面講,宋代以後,心性論成爲儒、道、釋三教共同關注的時代課題,因此,這一時期的老學也受到了影響。對《老子》哲學思想的研究,其重心由宇宙本體論的闡釋轉移到對心性問題的探討,這是宋元老學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注]劉固盛《宋元老學研究》,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49頁。三教融合影響宋代學者以心性思想注解《老子》之言,將《老子》思想研究重心由魏晉隋唐以來宇宙本體之詮釋到轉移到心性思想之建構[注]對於宋代《老子》注研究重心之轉向,劉固盛繼云:“宋代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心性論成了儒、道、釋三教共同探討的時代課題,宋元老學既受到道教的輻射,又得以禪宗的影響,再加上儒學的刺激,其哲學重心發生了轉移,即以唐代老學中所出現有關心性理論,在宋元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熟。在此一時期的《老子》注中,既可見儒家的性命之學,又可見道教的内丹心性論,還有禪宗的明心見性。總之,在對《老子》哲學思想的闡發中,心性學取代了重玄本體論。”(《宋元老學研究》,第53頁。)宋代《老子》注家吸收三教思想,或以儒家性命之學論之,或以道教内丹之術言之,或引用禪宗明心見性詮之,皆以心性爲主體詮説《老子》之言,形成以心性解《老》之義理詮釋向度。除吸收三教之學以明《老子》心性思想外,北宋學者注疏經典,多本己意立説。駁前人傳注,考原典之非,爲宋代學術特徵之一。是故北宋《老子》注家不盡依前人之注,而以己意詮説《老子》之言。故北宋《老子》注家論《老子》之心性思想,多能别具新意,遂成北宋《老子》注義理發展重要特色之一。。
北宋《老子》注家如陳景元、王安石即論心性。陳景元由道論心性,認爲儒家道德屬非常道。《道德經藏室纂微篇》卷一云:“至于仁、義、禮、智、信,皆道之用,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自然。”[注]《正統道藏》第二十三册,新文豐1995年4月出版, 第6頁。此將儒家之仁、義、禮、智、信視爲道之用,可用者即可彰顯,可彰顯者即可察知,故道德心性屬道之用,爲非常道也。道德仁義既屬非常道,又非常道皆本於常道,故道德仁義應以道爲本。《道德經藏室纂微篇》卷五曰:“君子以無爲自然爲心,道德仁義爲用。”[注]同上書,第51頁。此乃明言君子應以道家自然無爲之道爲本,而儒家仁義道德爲用。
王安石注《老》論“有”、“無”不遷,或以“沖氣”釋道,由宇宙本體論道之化生外,亦與聖人合論。“聖人”一詞,已見於《老子》書中,王安石則對“聖人”之意加以闡釋,賦予“道體儒用”之内涵。其言“聖人”,先由其心論之,其注“不尚賢,使民不争”曰:“所謂不尚賢者,聖人之心未嘗欲以賢服天下;而所以服天下者,未嘗不以賢也。”[注]嚴靈峰《老子崇寧五注》,成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頁。此言聖人未有尚賢之心,而其所爲皆賢也。又言:
尚賢則争興,貨難得則民爲盜;此二者,皆起於心之所欲也。故聖人在上,使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此二者,則能使心不亂已矣。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惡之對也,有善則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注]同上書,第29頁。
言民有争盜之心,皆因治國者有尚賢貴貨之心。心尚賢,則分不肖也。人民因此争爲賢,争則亂也。故有尚賢之心者治國,不能安民心。聖人知此,故不尚賢、不貴貨,而使民心不亂也。並舉孟子可欲與不可欲之論,將尚賢貴貨歸於不可欲之欲,認爲人民競逐不可欲之欲者,國亂矣。聖人不以尚賢貴貨之心治國,即不好善也。不好善,則無分善惡,而能善惡俱忘也。王安石以“心”論聖人不尚賢貴貨,且論孟子可欲與不可欲之説,言孟子明善,故分欲有可欲與不可欲者。而老氏之説則無分善惡,即無分可欲與不可欲,乃言以心合道,超越可欲與不可欲之别。此説雖未盡符合孟子之意,但與孟子相同者,爲標立心性也。以心合道,此乃王安石注《老》之特色也。
王安石以心論《老子》治國用世,透過聖人之心,綰合道之體用,其所論之心乃屬形上者也。其曰:
此老子不該不徧,一曲之言也。蓋先王不尚賢,亦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亦非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亦非不見可欲。雖然,老子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賢,則不累於爲善;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累於爲利;惟其如此,故能不見可欲。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善積而充之至於神,及其至於神,則不見可欲矣。[注]同上書,第30頁。
其言《老子》雖言不尚賢、不貴貨,但亦非是要人盡廢賢或全舍難得之貨,言不尚賢貴貨,乃爲明一不該不徧之理也。故不尚賢貴貨,則不累於善、利。據其注文,其云“不累者”,當指“心”也,即不尚賢貴貨,則心不累於善、利也。又曰:“萬物莫不累我也,吾不與之累;故外之也。”[注]嚴靈峰《老子崇寧五注》,第37頁。言心不累於外物,方能合道。此所言外物者,除有形之萬有,亦包括善、利之欲。且指出《老子》不尚賢貴貨之説所論者乃一形上者,據王安石之言,此形上者爲“心”。故王安石注《老》乃以心合道,並將心歸於形而上者。再引孟子之説,闡述心善積而充之,能達於神。神者爲體道之境,臻此境者,心無有善惡之别,故無見可欲。其論聖人之心又云:
夫虚其心,所以明不尚賢;實其腹,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強其骨,所以明不見可欲。夫人之心,皆有賢與不肖之别,尚賢,不肖則有所争矣。故虚其心,則無賢不肖之辨,而所以不尚賢也。……惟其無求也,故不見可欲而有立矣;無所求而有所立,君子之所貴也。[注]同上書,第30~31頁。
此進一步闡言聖人虚其心,不以賢爲尚,無分賢與不肖而無求也。無求則民無所争,争不興,則民心不亂。聖人虚心無求而立教化於天下,不求賢而人民皆棄聲色之欲而趨善也。
此外,王安石注“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云:“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注]同上書,第41頁。言先滌除心中一切外在欲望,方能觀道之妙,而體道之有無化生。此“滌除”之意,指心而言。滌除,即虚其心也。聖人體虚其心,滌除欲望,觀道之妙,體道而不尚賢,以此心治國,民心不亂而皆趨於善,故天下治矣。
北宋中期理學勃興,以心性思想注解《老子》漸多,其中王雱與蘇轍爲北宋以心性注解《老子》之代表。蘇轍《老子解》中數見“心性”之語。蘇轍言“心”、“性”,雖皆言人之内在主體生命,但觀其天道心性一貫之理論架構上,“心”與“性”之意義尚有相異之處。欲明《老子解》之心性思想,當先詮定“心”、“性”之義。蘇轍言“心”,大抵意指人之内在主體,包含感官智識與本然之性。其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曰:
明白四達,心也。夫心一而已,又有知之主,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爲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有無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注]蘇轍《老子解》卷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 第8頁。
此言人能應物,全賴一心。心應於物,感官知覺受外物之牽引,欲望漸生,則心分爲二,一爲本然之心,一爲受物役使之心。爲物役使之心增長,遮蔽本然之心。人之迷妄,皆肇於此矣。爲除心之迷妄,蘇轍“以鏡喻心”,以鏡能照物無窮,乃不受物累,順隨物之變化而映之。此所言之“心”包含感官智識之心與本然之心[注]對於感官智識之心,蘇轍解“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之句言:“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老子解》卷三,第36頁。)言人以目視、耳聽、心思面對外物,且執於智識之追求,順其感官執念而爲,乃大愚。此言心思者,乃指智識之心,爲感官智識之屬。人以感官智識之心應於外物,易受其惑,迷妄漸增,則人將役於物而失其本然之性。除感官智識之心外,蘇轍言“心”又有另一義。其云:“其所以不攖於物者,惟心而已。”(《老子解》卷二,第19頁。)言聖人不因外物而迷妄,乃因其心不受其惑。又曰:“雖逝雖遠,然反求之一心,足矣。”(《老子解》卷二,第24頁。)此所言“一心”爲本然之心,返歸本然之心,則能體道。。
蘇轍以心爲内在主體之總稱,其範疇包含感官智識之心與本然之心。人以心應物,感官智識接於外物,漸生迷妄,故言心分爲二。若迷妄漸增,人心蔽矣。人心蔽於迷妄,則人應物待人,皆本感官智識而爲,盡失道德也。蘇轍以“心”詮釋人之内在主體,言感官之心與道德之心皆存於此主體之内,端看如何修養此心。其曰:“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注]《老子解》卷四,第58頁。此言聖凡之别,乃在於其心之異也。凡人縱心於感官者,累於外物,爲終日庸碌之凡人;修心歸道者,無累於物,則爲體道之聖人。蘇轍《老子解》言心,指出人有一内在主體,其以“心”名之。感官之迷妄生於此,體道之本性亦在此。一切修養,皆是心内之工夫。
王雱《老子注》則以盡性體道爲主體生命之實現,並言盡性體道者,道性合一而以無心應物,順物性而動。其曰:“豫者,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於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於務。’”[注]《老子崇寧五注》,第120頁。此言至人無心於物,應物不欲先動,先觀物性而後動,其行謹慎如冬履薄冰。又云:“至人沖虚,其行如水,無心於物,而順物之變,不與物迕,孰能傷之?故常全也。”[注]同上書,第139頁。至人無心應世,其行如水,因順物性而爲,無傷物我,無虧於道,故曰常全也。至人無心,無累於物,故能順物而爲。王雱嘗曰:
至人不見一物,善惡無所分,而不廢世人善惡諸法,但於其中灑然不累耳。自相去何苦。已上所以明心之無累,而無累者,本不自異於世。故種種分别,與民同之;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聖人絶累忘形,亦可患乎?而《易》有吉凶之象者,因民情而已。莊子曰:“不忽於人。”道既兼忘,宜若忽人事,而實無忽也。[注]同上書,第132頁。
此以至人之心無有執見,故不分善惡,不廢諸法,此乃因其心不累。無累於物,則無所分别,而能與民同吉凶,與世人無異也。至人體道兼忘天下,心無一物,察納萬物,以全人事。聖人不得已而立教化,雖有毁譽之分,但仍本無心以納天下。其言: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毁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怒之,乃不覺有異也。[注]《老子崇寧五注》,第193頁。
人因自私生妄見,而有善惡之别。但聖人以無心應物,其心無殊想,心無執妄。雖不得已立教化以化民,政行而分毁譽,但聖人無心,知善惡皆爲執妄,故無分善惡,皆以無心納之。又云:
聖人心合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爲也,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爲。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己樂能,爲之不已;故事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歔、吹、強、羸、載、隳之反復故爾。[注]同上書,第157頁。
無乃道也,聖人體道,故曰以心合無。心合於無,則爲無心。聖人無心以應世事萬變,其心如鏡以映萬物之性,故能順性而爲之,皆適可而止。並言世人有心,以妄見應物,樂於能爲,爲之不止而有過甚之失也。有心而有妄見,妄見蔽性則昧於道,而不知天下之理皆反復而行。故行事不宜太過,當爲之適可而止。此言體道無心以應世,察萬物之性,知反復之理,而應世不殆也。王雱欲明體道之用,故言無心以酬萬變,並以妄見蔽性、自昧於道以有心應物而有失也。對於有心之失,王雱又云:
有事則有心,有心則民亦有其心;雖欲取之,其去遠矣。原此篇,蓋無事者,道德之極致;爲天下者,事業之極致。學而日損,以至於無爲;故能與於此者。[注]同上書,第193頁。
以有心治世,風行草偃,世人亦有心,民皆有心則治無行,漸遠民心也。故老氏言道德之極致,乃以道德之極致言事業之極致也。又言老氏主張爲學日損,以至於無爲,雖是論體道之工夫,亦言治世之道也。據此言之脈絡,爲學所損者,爲去妄見以歸於本性,復性體道而能以心合無,無心應世以成聖人之治。王雱標舉“無心”以言聖人之治,透過“無心”與“有心”之相對,説明去除諸妄,方可從“有心”歸於“無心”。故“無心”與“有心”之别,在於主體是否可以去妄復性。
從成玄英、李榮、陳景元、王安石、蘇轍至王雱對《老子》思想的詮釋,可以瞭解以心性注解《老子》的詮釋進路逐漸明顯,注家義理架構也漸趨完整。從唐代至宋代,以心性注解《老子》已成中國《老子》學史之重要特色與發展方向。
二、 白玉蟾《道德寶章》之義理思想
南宋道教興盛,道士多有注解《老子》之作。其中白玉蟾爲道教南宗之代表人物,對道教發展影響頗深,其著作多受當時與後代學者重視。《道德寶章》爲白玉蟾注解《老子》之作,歷來論此書者,多言其三教融合思想與心性思想,但對其心性思想皆言其以心合道,對於體道工夫或其心性思想架構則罕言之。
今以前人研究爲基礎,進一步廓清《道德寶章》之思想内容,此將其分爲五部分進行論析,一爲《道德寶章》“即心是道”之義理思想;二爲《道德寶章》之思想架構;三爲《道德寶章》之工夫理論;四爲《道德寶章》之體道境界;五爲《道德寶章》之治世思想。依序析論如下:
(一) 即心是道,道即心也
白玉蟾注《老子》,承北宋老子注家以“心”解老之詮釋進路,直言“以心合道”(《道德寶章·辨德》),或言“心與道合”(《道德寶章·虚心》),將“心”與“道”直接連結,成爲“即心是道”(《道德寶章·象元》)的理論架構[注]“即心是道”一語,在《道德寶章》中出現多次。如“即心即道”(《道德寶章·虚心》)、“即道即心”(《道德寶章·虚心》)、“道即心也”(《道德寶章·守道》)與“即心是道,道即心也”(《道德寶章·謙德》)。這些注文字雖略有不同,但都爲“即心是道”的觀念。説明白玉蟾注解《老子》,“即心是道”爲重要思想。。
白玉蟾“心”與“道”合言,則此心是具有超越意義的,其曰:“身有生死,心無生死。”(《道德寶章·體道》)此言人有身與心,身爲形軀有生死之限制,而心爲超越性之存在,無局限於生死。又云:“此心本無生死。”(《道德寶章·成象》)同是強調心具有超越生死的性質。再者,白玉蟾言:“心無所始,亦無所終。”(《道德寶章·虚心》)説明心爲無始終,無受有限時間的影響,與道相同,皆是亙久長存者,故其曰:“此心長存。”(《道德寶章·韜光》)[注]此爲白玉蟾注《老子》七章:“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對“以其不自生”之句注曰:“此心長存。”對此章“故能長生”之句則注曰:“本無生滅。”若合二句注文,則爲“此心長存,本無生滅”,説明白玉蟾主張心無生死之超越性。以心能同道,且與道常存。白玉蟾以心無死生亦無始終,以心爲超越之存在。
對於道與心的關係,白玉蟾曰:“道者,心之體。心者,道之用。”(《道德寶章·玄德》)又言:“道爲一,心之體。”(《道德寶章·重德》)説明道、心互爲體用。其云:“道無窮,心無盡。”(《道德寶章·顯德》)以此説明道化萬物[注]對於道化成萬物,白玉蟾云:“此道常在,萬物之内。”(《道德寶章·任爲》)説明道化萬物且存於萬物之内,存於人者爲心。,存心於人,人可以心明道。其言:“心爲萬物之宗。”(《道德寶章·重德》)人以心體道,則能明道化萬物之理。又曰“一心所存,包含萬象”(《道德寶章·能爲》)、“心者,造化之源”(《道德寶章·爲道》)與“心爲萬法之王”(《道德寶章·後已》),皆言道爲萬化之本,而即心是道,則一切道理,此心可明。其言“一心自如萬物”(《道德寶章·異俗》)與“一理燭物,冰融月皎”(《道德寶章·能爲》),此“一心”爲體道之心,“一理”爲萬物造化之理。一心明一理,則天地造化、自然運行之理皆在心中。白玉蟾更以此心之外,一切虚妄。其曰:“於此心爲實,餘者即非真。”(《道德寶章·虚無》)説明心爲真如,乃萬物生外之本,以心觀物纔能不役於物,又云:“三界惟心,一切惟識。”(《道德寶章·知病》)此引佛家之説,強調心與道同爲一切萬物根本,提升心的地位,使其與道同觀。
白玉蟾言:“心同太虚。”(《道德寶章·能爲》)太虚即道,故心與道同爲無窮無盡的超越存在[注]與“心同太虚”相近的注文尚有“心包太虚”(《道德寶章·鑒遠》),皆言心與道同。。且此心乃人皆有之,故《道德寶章·淳風》曰:“此理素存,此心素有。”《道德寶章·爲道》又言:“口各有心,此心常存。”道化萬物,存心於人,故人皆有心,皆可以心致道。又以心爲道之用,且心爲人之首要。其云:“心君也。”(《道德寶章·象元》)強調心爲道之用,且爲人之主體,人一切思考活動皆由心而出,此乃殊於萬物之處。其曰:“萬物之中,惟道爲大;五行之中,爲人最靈。”(《道德寶章·虚心》)道化天地,萬物之中,人爲具有靈性者。所謂“靈性”即是指“心”而言,此乃人殊於萬物之處。人由此心,可以明道,且心爲人之主,故人存於天地之間,舉措行事當本於心,故言:“心不外物。”(《道德寶章·恩始》)即不需向外求道,修心即可達致“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道德寶章·韜光》)[注]此語爲白玉蟾解《老子》七章:“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其援用《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而言“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説明聖人以心體道,不分物、我,故治世無私。後解“故能成其私”,更直言“我即天地,天地即我”。説明聖人體道,明天地,知萬物,其心同萬物,故言天地即我。且《道德寶章》向内求心以致道的思想,也可視爲白玉蟾對張伯端内丹思想的闡發。《悟真》篇云:“要知金液還丹法,須向家園下種栽。不假吹嘘並著力,自然果熟脱真胎。”此言家園即内在主體,求道煉養須向内求,纔能獲得心性的超越與生命的提升。的理想境界。對此,劉固盛認爲:
白玉蟾將心概念與老子之道進行了轉换,認爲包含萬象的天地宇宙,都在心的活動之中,世界一切都是心的産物。這既是白玉蟾老學思想的旨趣所在,也是他對老子思想的一大發揮。[注]《道教老學史》,第190頁。
此言白玉蟾即心是道的義理思想,是將心等同於道,提升心之地位。但白玉蟾又云:“心同虚空,虚空非心。”(《道德寶章·反樸》)言心可以同道,但道非僅是心而已,道非是心。此指道的範疇而言,道化萬物,故道爲萬物,而萬物不可同於道。故在《道德寶章》中,即心是道,心可合道,但不可以心完全置换《老子》之“道”。在義理範疇上,道仍居最高層次與最廣範疇。
(二) 心中有性,性中有神
《道德寶章》強調“心”的地位與作用,其將人分爲身、心、性、神,身爲有形軀體與感官,心存於身中,其言:“身中之心。”(《道德寶章·贊玄》)同前所述,此心爲形上超越之心,包含性與神,其言:“心即性,性即神,神即道。”(《道德寶章·益謙》)此言心中有性,性中有神,神即道,則心亦即道[注]除此條注文之外,白玉蟾注《老子》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將“夷”注爲“身中之心”(《道德寶章·贊玄》);“希”注爲“心中之性”(《道德寶章·贊玄》);“微”注爲“性中之神”(《道德寶章·贊玄》)。説明心、性、神爲三層次,心爲外,性存心内,神又存性内,故心最外,性次之,神居最内。白玉蟾並將“此三者不可致詰”注爲:“不可以説説,惟當以會會。”(《道德寶章·贊玄》)“説説”爲以語言詮説,“會會”則是體會。合而觀之,白玉蟾以心、性、神爲不可詮説,只能體會。此乃與道相同也。又注《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與?”將“天之道”釋爲“心之性,性之神”(《道德寶章·天道》),此皆同心、性、神由外至内爲三層次觀念之理論架構。。白玉蟾以人包含形下可見之身與形上之心,而心具有心、性、神三個層次。其注《老子》三十九章:“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貴以賤爲本”注曰:“神者,性之基。”(《道德寶章·法本》)“高以下爲基”解云:“性者,心之本。”(《道德寶章·法本》)“侯王”一詞則注曰:“心也。”説明心、性、神三者皆同屬形上存在,尚有層次之分。白玉蟾認爲心由外至内可分爲心、性、神三個層次。心、性、神雖有層次上的分别,但白玉蟾多一體而論,其曰:“神無方,性無滅,道無盡,心無形。”(《道德寶章·愛己》)心、性、神與道相同,皆有無窮無盡、無生無死與無方無形之性質[注]白玉蟾注《老子》五十八章:“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將“深根固柢”解爲:“天崩地裂,此性不壞。”(《道德寶章·守道》)將“長生久視之道”注曰:“虚空小殞,此神不死。”(《道德寶章·守道》)此“天崩地裂”與“虚空小殞”皆言形下現實世界倘若崩壞,形上之心、性、神不會消滅,説明性與神不爲形下現實世界影響,皆爲形上超越之存在。其言:“性常存,神不亡。”(《道德寶章·辨德》)其意同此。對於心、性、神之性質,白玉蟾於《道德寶章·贊玄》與《道德寶章·同異》皆言:“神無方。”説明神爲無窮無盡者。又云:“性無體。”(《道德寶章·贊玄》)“性猶水也。”(《道德寶章·易性》)説明性無定形,與水相同,隨形而變。對於心,白玉蟾則言:“心無形相。”(《道德寶章·贊玄》)“心無方所。”(《道德寶章·任成》)説明心無定形。由上所述,可知白玉蟾皆以無形、無相、無方、無窮無盡論心、性、神,以説明心、性、神之超越性。因爲心、性、神具有超越性,故人可據此以體超越之道。。
對於心、性、神三者,白玉蟾言:“心者,大道之源。即心是道,神亦道,性亦道。”(《道德寶章·謙德》)此更明言心、性、神雖有層次之别,但皆屬道之範疇;心、性、神與道同爲形上超越之存在。又曰:“性不可窮,神不可測,心不可盡。”(《道德寶章·益謙》)此以心、性、神皆無窮無盡而不可測,説明此三者皆屬形上存在。白玉蟾言:“以心盡心,以性窮性,以神測神。”(《道德寶章·益謙》)能窮盡心、性、神者,唯有以形上之道。相對地,人亦能以此三者明形上之道。白玉蟾以心、性、神與道同爲形上存在皆不可測,故人可據此三者以體道,因此白玉蟾論修養工夫皆是對此三者而言。
白玉蟾將人之形上存在由外而内分爲心、性、神三層次,三者皆爲形上範疇,皆有超越性,故人可内求心以體道。其云:“以性全神,以心全性,以我全心,以無我爲全我。”(《道德寶章·去用》)此乃由内而外的體用架構叙述體道之理論架構。白玉蟾以“神與道存”(《道德寶章·守道》)説明道即神,神爲性之體,性爲神之用,故言“以性全神”,此乃“性與道合”(《道德寶章·守道》)之境界;性爲心之體,心爲性之用,故曰“以心全性”,此爲“以心合道”(《道德寶章·論德》)之境界;心、性、神皆全,人之内在主體以達體道之境界,此爲“無我”境界之實現,此爲人最理想境界之實現,故曰:“以無我爲全我。”[注]白玉蟾於《道德寶章》中,常以“我”指稱人之内在主體,其注《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對於“吾不知其名”解曰:“吾即我也。”(《道德寶章·象元》)此將《老子》文中之“吾”釋爲“我”,以人有内在主體可以求道,但不知該如何將所體之道加以明之,故暫以“道”名之。據白玉蟾所言人之内有心、性、神,故皆可體道,故“我”可以爲内在主體之指稱。《道德寶章·虚用》曰:“盡其在我。”此“我”即是指内在主體而言。
(三) 除垢止念,明心見性
白玉蟾提出心、性、神之形上心性理論架構後,便要對“人無法體道”提出解釋。對於人無法體道之關鍵在於“念”。其言:“此念不死,此道不全。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道德寶章·制惑》)其言“念”不消滅,則人終無法體道。又言:“念頭不已,心則越雜。誰使之念頭不已?誰使之心雜?”(《道德寶章·戒強》)念頭越生則心越雜。後二句設問,説明念頭生於心内,使人無法體道。念頭何處而來?白玉蟾言:“嗜欲殺身,情念不斷。”(《道德寶章·任契》)又云:“溺於情欲,必喪其本。”(《道德寶章·立戒》)此所謂“情念”或“情欲”者,皆爲人之欲念,欲念存於心,則人之心將失其本,身亦將不安。[注]白玉蟾言:“心之不寧,身之不安。”(《道德寶章·厭恥》)欲念入心,心逐耳目聲色,則無所安適。心無安,身亦不安也。又云:“用心不已,勞神不止。”(《道德寶章·異俗》)情念常存於心,則勞神不止,如何體道?故欲念入於心,於外使身不安,於内勞神不止。所以當以“除垢止念”(《道德寶章·謙德》)的功夫,去除欲念,使心虚無合道,方能超於萬物[注]白玉蟾言:“無所貪著,心超萬物。”(《道德寶章·重德》)貪即欲念。心無貪念則能超萬物,超於萬物則心不囿於物。《道德寶章·益謙》曰:“吋心不昧,終古長存。”同是説明心無昧於念,則能終古長存。此二注合觀,心無欲念,則能超於萬物且終古長存。説明心無欲,本然之心明,明心即合道,合道之心具有超越性,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
然則欲念自何而生?白玉蟾注《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將“令人耳聾”注曰:“貪外喪内。”(《道德寶章·檢欲》)説明欲念所生在於人之感官,其言:“耳隨聲走,眼被色瞞。”(《道德寶章·儉欲》)人有感官,接於外界聲色,因而欲念生[注]對於欲念,白玉蟾言:“凡有所相,皆是虚妄。”(《道德寶章·苦恩》)説明一切有形外物,皆爲虚妄,虚妄即爲欲念。又云:“人不能究心。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道德寶章·愛己》)人追求欲念而不在心上用工夫,則離道漸遠。心離道則昧於生死無常之理,身心皆困於生死之中。,欲念生則蔽於心。其言:“耳目所娱,真内已喪。”(《道德寶章·異俗》)“以物爲心,乃昧所見。”(《道德寶章·論德》)説明耳目等感官追求外在聲色之娱會蒙蔽心,使心失本然之真,心失真則離道遠矣。其注《老子》七十五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將“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解曰:“人之不知道,以其心之念不已,所以不知道。”(《道德寶章·貪損》)將“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解云:“人不得道,以其心之事不停,所以不得道。”(《道德寶章·貪損》)對“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釋曰:“人之不合道,以其心之情不盡,所以不合道。”(《道德寶章·貪損》)[注]《道德寶章·貪損》將欲念分别稱爲“念”、“事”、“情”,三者異名同實,皆爲心之累也。説明人所以無法體道,在於其心中欲念不斷産生,欲念愈生,離道愈遠[注]白玉蟾言:“累於貪故,必失其真。”(《道德寶章·立戒》)此近於《道德寶章·貪損》之説。欲念爲感官對於聲色外物之貪求,欲念多則蔽心,使心失本然之真。又云:“心念所形,起滅不停。”(《道德寶章·道化》)白玉蟾以爲欲念若存於心,則欲念將不斷生滅。《道德寶章·偃武》:“以心勝物,終莫能勝。”欲存於心,則人欲以心勝物。但一心何以勝萬物,故白玉蟾言欲存於心,則心爲欲所累。。
白玉蟾以欲念使人不知道,故消除欲念爲《道德寶章》之工夫,其注《老子》七十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解曰:“此念不死,此道不全。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道德寶章·制惑》)説明欲念爲體道之障礙,所以必須除去欲念,若欲念不絶,則人不知其心,況乎道也。又注《老子》七十四章:“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將“使民常畏死”注曰:“只知貪生,不知有死。”人追求感官欲念,則爲貪生之人。貪生之人追逐欲念,困於生死之間,終其一生不知有超越死生之道。白玉蟾對此言:“心無生死,情念死矣。心有力,則情念自消。”(《道德寶章·任信》)人之初心本無生死,但耳目接於物,情念入於心,心蔽於情念而昧於道,故情念使心死。又曰:“有力於剪除妄念也。”(《道德寶章·任爲》)剪除妄念爲心有力之表現[注]《老子》七十三章:“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白玉蟾注曰:“有力於剪除妄念,有力於守雌抱一也。”此以“勇”表示人之主體性,心能剪除妄念並持守虚無,此乃心有力之表現,心有力即爲勇。。因此,修養工夫在於心,心強而有力,情念不入而自消逝。
對於絶念,白玉蟾注《老子》七十四章:“常有司殺者殺。”發揮“殺”字之義,其論曰:“心爲司殺,能絶百念。”(《道德寶章·制惑》)心主“殺”以去念,以“殺”爲去絶欲念之修養工夫[注]在“司殺”之後,白玉蟾言:“我心與他心雖同,不可以我心代他心也。”(《道德寶章·制惑》)言你我之心雖同於道,但絶念工夫不可由他人代之,除念明心爲吾事,不可假於他人或外力。此乃強調主體之覺察,主體覺察即爲勇,勇則能絶殺欲念。。心能殺念,則“一念不生。”(《道德寶章·獨立》)[注]“一念不生”爲注《老子》八十章:“使民重死。”白玉蟾以人多重生輕死,重生則欲念生於心,欲念生則昧於心,故聖人治民,使民重死,心一念不生則能見道,心能見道則心不困於欲念。心有力而念不生,念不生才能達忘我得道之境[注]《道德寶章·貪損》曰:“勇於忘我,所以得道。”白玉蟾以“我”爲人之内在主體,“忘我”爲心無欲念,明心見道,不執於一我之得道境界。所以言“勇於忘我”乃言心上修養工夫,“勇”則説明能體道與否,在於其心是否願意向道,所以“體道”爲主動,而非被動。再者,白玉蟾以此“勇”字強調人之主體性,實爲此段注文最精妙之處。對於主體之心爲何能“勇”?白玉蟾在《老子》六十七章“慈故能勇”注曰:“其力大。”又“捨慈且勇”注曰:“逐物。”再者“慈以戰則勝”注曰:“身心不動。”白玉蟾以“慈”爲“勇”之本,又將“慈”注曰:“專炁致柔,能如嬰兒。”説明慈乃本然守柔之心,此心乃人生於世皆有之。人以此心方能除妄念並持守本然之心,此乃心有力之表現,故以“勇”言之。因此,白玉蟾以心之勇乃本於慈,慈即人本然所有,故人皆可剪除妄念以致道,此乃心之勇,亦爲心之慈。。白玉蟾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道德寶章·苦恩》)以心接於物,必有欲念生。欲念生而知除之,則能持守本然之心。又云:“自昧固有之心、本來之性。”(《道德寶章·俗薄》)若不知除欲,欲存於心,久之則蔽心性,使心性離道。
白玉蟾論“殺”與“儉”同,皆以爲心上修養工夫。其言:“儉視、儉聽、儉思、儉爲。”(《道德寶章·守道》)“儉”爲收斂,儉視、儉聽爲收斂耳目聲色之欲,收斂欲念則其思慮、行爲亦收斂,“儉”使心不蔽於欲念。白玉蟾又言:“儉視、儉聽,裕然有餘。”(《道德寶章·運夷》)説明收斂視聽之欲,使心裕然而遊刃有餘。白玉蟾言:“心無一塵,是謂之道。”(《道德寶章·歸玄》)心無欲念,如無一塵,心能持守無欲方可體道[注]白玉蟾除以“心無一塵”説明心無欲念,也言:“心如牆壁,乃可入道。”(《道德寶章·苦恩》)説明心無欲念爲體道之必要條件,還必須能持守“心無欲”之狀態,如牆壁一般,外欲不入,纔能以本然無欲之心體道。《道德寶章·淳德》:“抱虚守沖。”“虚”、“沖”皆道之性質,本然之心即爲道心,抱虚守沖即持守本然之道心。。對於欲念,白玉蟾又云:“剋人欲,求天理。”(《道德寶章·守道》)“以天理,勝人欲。”(《道德寶章·守道》)此援用宋代理學家天理人欲之説[注]此二條與“天理人欲”相關注文應本於《宋元學案·伊川學案》:“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即皆天理。”白玉蟾引用程頤之説,言“念”即“人欲”,“道”即“天理”。又注《老子》十五章:“猶兮若畏四鄰。”曰:“君子慎其獨。”(《道德寶章·顯德》)此援用《中庸》之言,言求道之事當謹慎而爲。由“天理人欲”與“慎獨”之説的引用,可見儒學與理學對白玉蟾注《老》思想之影響,也可見其融合三教詮説《老子》之詮釋傾向。,説明當去絶欲念,纔可致道。故言:“心無病而身自安,心無爲而神自化。”(《道德寶章·聖德》)心無欲念即心無病,無病心安而能歸無爲之心,無爲之心自可與道同化。説明修養工夫,以絶念爲先。
白玉蟾將《老子》之“殺”與“儉”詮釋成去除心中欲念的方法,透過殺、儉以達“明心見性”[注]對於心性修養工夫,白玉蟾言:“明心見性。”(《道德寶章·顯德》)説明去除欲念以明心,此心爲本然之心,以本然之心方可明本然之性。又云:“心開神悟。”(《道德寶章·顯德》)意同此理。《道德寶章·無用》曰:“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内無外。”據白玉蟾之言,心内爲性,性外爲心,去欲以存本然之心、本然之性,則内外皆合於道。因此,“無内無外”一語乃指心、性皆合於道。再者,對於體道《道德寶章·守微》曰:“道可恃,道可思,道可悟。”此段注文應解作“心可恃道”、“心可思道”、“心可悟道”,説明人明其本然之心方可悟道、恃道,本然之心爲無心,無心忘心方可思道之真。。其曰:“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道德寶章·玄德》)“閉目”爲去除欲念,閉目然後收心,纔可見本然之心。又云:“心性無染,體露真常。”(《道德寶章·苦恩》)此以“真常”意指本然之心,説明欲念不入於心,心性則無染。心性無染,纔能復歸本然之心,即所謂“任其天然,寂然無念”(《道德寶章·還淳》)的理想狀態[注]此可與“心兵不起,方寸太平”(《道德寶章·還淳》)合觀。 心無念則心兵不起,心自然太平,太平之心歸於寂然虚空,此爲本然之心。故念入於心,心動之如兵禍不止,心無太平,離道自遠。。心無念自安寧寂然,歸於天然,此乃本然之心。以本然之心見本然之性,即其所云:“盡其心者,知其性。”(《道德寶章·居位》)[注]此語乃出於《孟子·盡心章句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白玉蟾援用《孟子》之言説明心性修養工夫,可見其受宋代理學影響。立説以道家爲本,兼采儒家之言,此爲《道德寶章》之詮釋特色。本然之性以神與道冥合[注]白玉蟾曰:“心與道冥。”(《道德寶章·顯德》)此“心”乃真常心,即本然之心。白玉蟾論心、性、神之超越性,皆是在人可持守本然之心的前提下而論。。白玉蟾認爲“道不遠人,人遠乎道”(《道德寶章·異俗》),道本不離人,但人受欲念所蔽,離道漸遠。因此“明心見性”之修養工夫,昭示世人當去除欲念明其本然之心。白玉蟾以“人能虚心,道自歸之”(《道德寶章·任成》)與“道非欲虚,虚自歸之,人能虚心,道自歸之”(《道德寶章·體道》)説明心復歸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即虚無之道,故明心則見性,虚心則歸道也。所以白玉蟾言:“先忘其心。”(《道德寶章·後已》)説明體道之要在於明心見性,明心即虚心,虚心則無有欲念,無念則無我,無我之心即忘心[注]《道德寶章·能爲》:“無念無爲,無思無慮。”此“無念無爲”即心無念則歸於無爲之心,無爲之心則無有思慮,無有思慮方可忘心合道。。又曰:“不以我爲我,乃見心中心。”(《道德寶章·任德》)此“不以我爲我”與無念無我相同,“心中心”爲心中本有之道,故無念無我方能見心中之道心[注]白玉蟾言:“以心契心,以道合道。”(《道德寶章·歸玄》)“以心契心,以道覺道。”(《道德寶章·任契》)“知此心,即道心。”(《道德寶章·守微》)可知白玉蟾主張去除欲念以明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即道心。故言以心契心,以道合道,皆同以心合道。又云:“以心知心,以性覺性,以神合神,合神於無。”(《道德寶章·巧用》)此“知”、“覺”、“合”皆可解作“歸本體道”,“無”則解作“道”。此注文説明以心知心、以性覺性、以神合神,心、性、神皆歸於本然之心、性、神,則神自與道同。《道德寶章·還淳》曰:“忘形以養炁,忘炁以養神,忘神以養虚。”此注論述雖有不同,但都是由外而内言體道脈絡。其以形驅爲炁所化,故忘形而知形之本爲炁,忘炁則知炁之本爲神,虚即道也,故忘神可以知道。此注雖與前所言脈絡有所不同,但皆是由外而内,此雖言形、炁,皆是心上工夫。《道德寶章·虚無》曰:“了心而已。”修養工夫要旨爲心明道。《道德寶章·益謙》曰:“心上工夫,何分彼此?”乃言一切修養皆爲心上工夫,此心體道,故人我皆同,無分彼此。《道德寶章·後已》曰:“心所以能合道也。”説明體道要在心上下工夫,在於心本於道而存於人,故能合道。人可以心合道,故有心上工夫。。對於欲念之去除,白玉蟾認爲:“無念之念,亦復是念。一念不存,此心乃見。”(《道德寶章·知病》)將無念之念視爲一種欲念,會妨礙本然之心的呈現,故當去除,纔能見道。其言:“欲求合道,乃不合道。求欲凝神,神乃不凝。”(《道德寶章·偃武》)皆以欲求道者,則離道越遠,無以致道。
(四) 忘我忘世,遊心於物
白玉蟾言:“心不在物,無物無心。”(《道德寶章·忘知》)心不在物,則心無欲念,心無欲念即復歸本然之心,以本然之心體道,體道則無心,故此“無物無心”之語乃合心上修養工夫與體道境界而言。其注十六章將“至虚極”注爲“忘形”(《道德寶章·歸根》),將“守静篤”注爲“忘心”(《道德寶章·歸根》)。身即形,忘形即忘身,忘身忘心即身心俱忘之修養工夫,由此工夫以達“回光返照,見天地心”(《道德寶章·歸根》)。即身心俱忘以體道,體道觀物而能知萬物之理[注]《道德寶章·知病》云:“吾所謂知知與不知,不知之知乃是真知。”白玉蟾論修養工夫着重於“忘”與“無”,因此不可由智識以言道。要能“無心”、“忘心”、“忘形”纔可明道之真諦,此即“不知之知”也。其又言:“道無可學,心無可用。”(《道德寶章·巧用》)説明學爲智識之積累,智識不可體道,故道無可學。道心即無心、忘心,以用爲念無入於心,故心無可用。此二注同是論智識不可知道,忘心無心纔可知道。其言:“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道德寶章·虚心》)皆是以智識不可知道,以修心爲主方能合於道。。
白玉蟾以欲念爲人所以無法體道的原因,故以去絶欲念爲修養工夫。心能去念,則身心俱安。心復於本然之心,使心與道冥。人以體道之心復觀萬物,不爲物所困。其曰:“見色明心,聞聲悟道。”(《道德寶章·檢欲》)此似與絶念之説相違,但再觀“無事於心,無心於事”(《道德寶章·能爲》)[注]《道德寶章·論德》云:“無所事於心。”言以道心應物,行事無爲,亦無事可入於心。與“見物便見心,見心便見道”(《道德寶章·巧用》),心冥合於道,以無心應物,見色聞聲皆可明心悟道,所明之心爲虚心,以虚心納萬物;所悟之道爲萬物之道,悟道生化萬物之理而不執於物[注]《道德寶章·贊玄》曰:“見物便見心。”同於此理,無心合道以觀物,則萬物皆道。《道德寶章·顯德》又曰:“謂之道也,皆無心焉。”強調人能以心合道,其心必爲無心。無心忘我,方能身心俱忘,遊於萬物。。
對於體道之心,白玉蟾言:“心超物外而不外物。”(《道德寶章·巧用》)説明心與道合,超於物外,人以此心應事接物,故心不外物。又云:“不離生死,而離生死。”(《道德寶章·偃武》)體道之心雖離生死,但存於世,故不離生死。此與“不可以離生死而求心,不可脱心而離生死”(《道德寶章·巧用》)意皆同也。其借《莊子》之語而言:“遊心於物,而不爲物所囿。”(《道德寶章·微名》)體道之心不外於物,遊於物而不受物所困。又云:“用心一處,無事不辨。”(《道德寶章·偃武》)此“一處”爲“道”,用心於道則能察辨萬物而不困於其中。
白玉蟾以心體道,並非要人歸道離世,而是要人以體道之心待人接物。人之心體道,超於物外,故能放下身心[注]《老子》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白玉蟾注曰:“無欠無餘,放下身心。”道體虚無,體道之心則爲無心,無心則不執於身,故體道而無心無身,此乃“放下身心”之旨。其又曰:“有我則有身,無我則無身。”(《道德寶章·厭恥》)説明心有欲念,則屬有我,有我則不能忘身,身爲耳目聲色之欲,有我有身而着於外物。相對地,心無欲念,虚心體道,虚心則無我,無我則不執於身,不以身爲先,自然無困於外物。人以心體道在於得到内在主體的自由自適。《道德寶章》所言:“湛然一天,我亦非我。”也是説明天道湛然,存於内而使人忘我,故言“我亦非我”,此同“放下身心”與“無我無身”之説相類。,不執於感官欲念,如此方可“忘我忘世,天真自然”(《道德寶章·厭恥》)。人之心歸於天真自然,忘我而不執於物[注]白玉蟾言:“應無所著,動然無我。”(《道德寶章·還淳》)人之心體道而忘我,忘我則心無所執,故曰“無我”。虚心無我,故接物而能無所執著。,此乃無我之境界。白玉蟾又云:“心無爲,則天道乃見。”(《道德寶章·任信》)無我方能無爲,忘心無爲,方可見道。見道則明“生死自生死,此心自此心”(《道德寶章·巧用》)。此以“忘我”而知萬物生死皆本自於道,故曰:“生死自生死。”忘我自於忘心,忘心本於道而存乎心,故曰:“此心自此心。”白玉蟾言無心忘我説明人以心體道而歸於心,道本虚無,故體道之心亦虚無,虚無存於心,道存心則無心忘心,忘心而無所執。忘心然後忘身,身心俱忘而無所執,故能遊於物,而不着於物。
對於身心俱忘,白玉蟾以“身心一如”論之。其曰:“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道德寶章·反樸》)又云:“身心一如,大道得矣。”(《道德寶章·聖德》)[注]《道德寶章·爲政》也有“身心一如”之説。身心一如爲身心皆合於道,體道化生萬物之理,故能遊於物而不囿之,此爲體道境界。對於身心一如之描述,白玉蟾又言:“身如槁木,心若死灰。”(《道德寶章·異俗》)以“槁木死灰”説明身心不因欲念而動,此乃身心一如之境界[注]除槁木死灰之外,白玉蟾尚言:“寒灰枯木,死心忘形。”(《道德寶章·巧用》)説明心與道冥合,表現於外如寒灰枯木,此乃死心忘形之境界。此所言之“形”即“身”,故死心忘形即身心俱忘之境界。又言:“終日不違,如愚。”(《道德寶章·顯德》)形容身心俱忘者,終日行道,不好聲色,無求名利,形似愚昧,實則大智。。此外,其曰:“我無生死,我不能無生死。我能生死,我本無生死。”(《道德寶章·歸根》)説明以心合道,不可以離乎身。心合於道,則心能超越生死[注]白玉蟾言:“此心自若,本無生死。”(《道德寶章·貴生》)言心合於道則知本然之心本無生死。。心存於身,故心合道,身亦合道。身心合道則身心俱忘,以此身心應世則明生死之理,不困於生死[注]白玉蟾言:“心爲主,物爲客。”(《道德寶章·聖德》)説明人存於世,當以主體之心爲主,心能體道則萬物之理皆在心中;心不能體道,則心將困於外物。故言心爲主,而物爲客。此語言心合於道則超越生死,復觀萬物而知萬物生死皆本於道之説相同,同是以心爲主,心合於道則知萬物生死之理。如此則心無所囿,身心一如,遊於萬物。又云:“忘外而不忘其内也。”(《道德寶章·養生》)據白玉蟾之説,此所言“外”爲身與物,“内”則爲心也。説明人當以心爲主,因爲心能合道,心合於道則忘心,忘身與忘物。白玉蟾透過主與客、内與外説明心之重要性。。
(五) 以心治世,易知難行
除論修養工夫之外,白玉蟾在《道德寶章》中也論及治世之道。白玉蟾承《老子》之説,以聖人爲體道之人。對於聖人,白玉蟾言:“藏心於心而不見也,藏神於神而不露也。”(《道德寶章·任信》)[注]《道德寶章·無源》曰:“藏心於心而不見。”與《道德寶章·任信》之注相同,皆是言聖人體道於心,由外無可視見,故難以以道治民。説明聖人體道於内,由外無可知,故民難以學道。此外,白玉蟾還提出一個問題,其曰:“吾道易知而不易行,心易悟而不易於了。”(《道德寶章·任爲》)知道爲易,體道則難,故道不可以學而致知。
道既不可學,又易知難了,故聖人治世當以無爲之政。白玉蟾對《老子》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解曰:“心之所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道德寶章·無爲》)此言心存於人,故天下神器乃指人而言。不可爲則是無爲之意。依白玉蟾之言,人有心皆可合道,故治世當用無爲之政,方能使人民體會無爲之理,而可以心合道。又注《老子》八十章:“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解曰:“心心相照,照見五藴皆空。”(《道德寶章·獨立》)此言人心合於道,則以此道心照他人,人亦爲以心合道者。他人與我皆以道心應物處事,此爲“心心相照”[注]白玉蟾言:“心一而已,視人猶己。”(《道德寶章·巧用》)心一爲心同道,聖人以心合道,以此心視民,則民皆己。聖人視民猶己,方能行無爲之政,使民復自然,天下自歸道。。白玉蟾借佛語言“五藴皆空”言人、我相照,則明道體爲無也。
《老子》五十七章:“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白玉蟾注曰:“神之所化,性之所正,心之所富,我之所樸。”(《道德寶章·淳化》)説明聖人治世,以道心爲政,富人民之心,方可使天下歸於樸。《老子》五十八章:“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注曰:“簡從約,易從簡。先得此理,有所操存。”(《道德寶章·守道》)聖人體道治國,當以簡約之政行於天下,使民體會簡約之理並存於心。《老子》五十八章:“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解云:“剋人欲,求天理,克己復禮,道即心也。”(《道德寶章·守道》)此將聖人無爲之政解釋爲剋人欲、存天理之政,以此政行於天下,人民皆克己復禮,並進而以心合道。白玉蟾在此援用理學家天理人欲之説,説明聖人無爲之政將使人民存天理於心,天理存於心則見諸外即是克己復禮,人民克己復禮則天下無有争亂殺伐。
白玉蟾認爲,聖人與凡人皆有心,故無論聖凡皆能體道。其曰:“聖愚同性,忘内逐外。”(《道德寶章·無用》)聖人與凡人皆有本然之性,透過修養工夫,皆可以心合道。又云:“人心我心,同乎一性。”(《道德寶章·任德》)因爲人我同心,故聖人治世,行無爲之政,人民可以心契合其爲政之心。《道德寶章·異俗》曰:“一人之心有限,萬機之事無窮。”聖人體道,以道心雖一但可應萬機無窮之事。聖人以無我之心治世,納萬機無窮之事於心,故能使民契合其心,民皆無我無爲則天下歸道。白玉蟾言:“心無其心,是謂大同。”(《道德寶章·洪德》)聖人以無我之心治世,行無爲之政,使民歸道,此乃大同理想境界。
結 語
白玉蟾以“心”詮釋《老子》思想。其承唐、宋以來以心性注解《老子》詮釋進路,進一步言“即心是道”,直接連結“心”與“道”,確立心之超越性,故《道德寶章》全書皆以心爲主,論心性之理與修養工夫。對於心性之理,白玉蟾以心與道同,故爲超越存在,並以“心中有性,性中有神”將心由外而内分爲心、性、神三層次,但不可分而論之,《道德寶章》注文多將心、性、神皆視爲心也。
在修養工夫上,白玉蟾以心爲體道之要,故一切修養工夫,皆爲心上工夫,此與唐宋以來《老子》注家相同,如蘇軾、王雱言去妄復性之理,同是心上工夫。又其忘心、無心之説,與唐代重玄學與北宋注家相近,可見在白玉蟾注解《老子》,除承道教内丹學之外,也受到唐代重玄學與北宋《老子》注家之影響。白玉蟾進一步發展,主體以心合道,以身心皆忘爲體道境界,《道德寶章·厭恥》曰:“心猶君也,身猶天下。”此爲以心統身之義理架構,實與北宋注家如王安石所言“性情一也”或與理學家張載“心統性情”之説相近,皆以心性爲主體之超越主宰,通過内在修養工夫,無心以合道,則身心俱合道。又白玉蟾又言無心與忘心,在身心一如的義理架構下,心爲忘心,則身爲忘身,故身心一如爲身心俱忘,此與重玄學“雙遣雙忘”旨趣相近,強調以心體道,且不可執於心也。
此外,白玉蟾言體道工夫在於欲念之消除,消除心中欲念則人可歸於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即無心,無心以合道,故《道德寶章》去念、無心、合道皆爲一體之心上工夫。對此,白玉蟾特别指出無念之念亦爲欲念,故人欲無念以求合道,心即爲欲念所蔽,故將離道漸遠,此爲《道德寶章》論心性修養工夫之特色。觀《道德寶章》以心解《老》之詮釋進路與南宋理學家陸九淵發明本心之説頗有相近之處,白玉蟾與陸九淵皆言本心,以心本於道,爲人之大也,故立人當先立心,本心明方可應事接物,無受外物所蔽[注]陸九淵於《與趙監書》云:“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仁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頁。)此以道存於人則爲仁義,仁義即本心,故道即心也。再者,陸九淵言愚者蔽於物欲而失本心,賢者智者蔽於意見亦失本心,此説與《道德寶章》中“除垢止念,明心見性”之説相近。又陸九淵在《與邵叔誼書》言:“此天所以予我也,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陸九淵集》,第1頁。)“此者”即人之本心,陸九淵認爲本心爲道所予,一切修養工夫都是在心上工夫,與白玉蟾去心念之説頗相類。故言白玉蟾《道德寶章》以心解《老》之詮釋進路與陸九淵發明本心之義理結構甚有相近之處,此反映出南宋時期心學鼎盛,其影響所及不僅是儒學而已,道家道教也多受此時代學風影響。。
再觀《道德寶章》對聖人之闡述,白玉蟾與前代《老子》注家相同,以聖人爲體道之人。體道之人治世,當以無爲之心行無爲之政。並且提出道乃易知難行,聖人以無爲之心,行無爲之政以治世。既言無心、忘心方可合道,心與道合則無囿於治,無囿於治方能行無爲之政。行無爲之政,方能使民知道。白玉蟾認爲無論聖愚其心皆同,故聖人行無爲之政,民之心自能有所感而合於道,則天下大同。但如何使民心合道?即如何使民主動地去念無心以合於道?白玉蟾提出道易知難行之説,顯示出其已考慮到無爲之政可使民知道,但不一定能使民心合道,所以白玉蟾引用《論語》中“克己復禮”之説以詮釋聖人以道治世,説明聖人行道,民若僅知道而不行道,則至少使民歸於禮,爲聖人以道治世取得一折衷詮釋。
白玉蟾《道德寶章》之詮釋義理承前代《老子》注家之詮釋基礎與南宋心學之影響,進一步發展心性理論,建構出一套更加簡明的義理架構。並且對於心性思想有更進一步的思考,其言“無念之念”與“易知難行”皆是對《老子》義理詮釋之貢獻。故論《道德寶章》之義理思想,不可僅以一個心字概括,以心合道之義理架構也非是白玉蟾所獨創。在以心性注解《老子》之詮釋進路發展上,白玉蟾《道德寶章》確爲重要的繼承與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