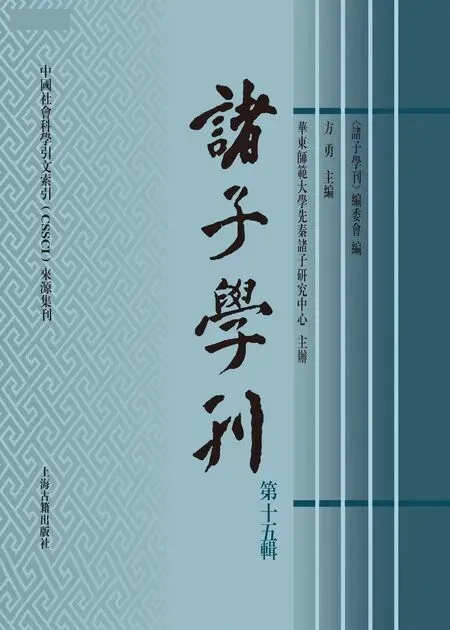論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現象*
2017-01-27侯文華
侯文華
内容提要 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現象,是指散文撰述者或者文中叙述議論的主體在闡發思想時對某些字詞或者概念作出的闡發注釋。這些訓釋性的文字出現在正文當中,與一般的非訓釋性文字融爲一體。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屬於早期的訓詁工作,是中國訓詁學的先聲,在訓詁學史上有篳路藍縷、導夫先路之功。“文中訓釋”現象之所以頻現於先秦諸子散文,與當時私學教育的興起、游説之風的盛行以及名辯思潮的湧動、文獻數量的驟增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
關鍵詞 先秦諸子散文 文中訓釋 訓詁材料 私學教育 游説之風 名辯思潮
一
先秦諸子散文中存在着一種較爲獨特的撰述現象,即在正文中常常會夾雜着一些具有闡釋功能的文字,或是對某些字詞做的訓詁,或是對某一概念做的注解。這些闡釋性的文字往往混雜在正文當中,與一般的非闡釋性文字融合在一起。這種語言現象,我們稱之爲“文中訓釋”。“文中訓釋”現象散見於先秦諸子文獻中,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或者出現在語録中,或者出現於人物之間的對話中,或者作爲論事説理的一部分而混融於長篇宏論當中。爲了更準確地説明本文的研究對象,兹舉例如下。例文中劃線部分即爲“文中訓釋”。
《論語·顔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莊子·讓王》:“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莊子·庚桑楚》:“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韓非子·五蠹》:“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
《管子·法法》:“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文中訓釋”現象在先秦諸子文獻《老子》《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管子》等中普遍存在,尤以戰國中期以後的文獻爲多。
從根本上講,先秦諸子散文的“文中訓釋”是一種闡釋現象,屬於闡釋學範疇。中國闡釋學在先秦發端,且在先秦時期已經形成多種闡釋類型,出現了多種類型的闡釋型文獻。先秦時期的這些闡釋型文獻,撮其大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在正文的叙述議論中夾雜一些闡釋材料,如本文所考察的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現象;二,同一部文獻的同一篇中,前經後解,即前一部分是經,後一部分是對經文逐句逐段的解説,如《管子·宙合》《心術上》以及《韓非子·儲説》等;三,同一部文獻中,其中某一篇或幾篇是對另一篇或幾篇的闡釋,如《墨辯》四篇中《經説上》《經説下》是對同書中《經上》《經下》的闡釋,再如《管子解》即《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四篇,分别是對同書中《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四篇的闡釋;四,兩部不同的文獻,其中一部中的某一篇或幾篇是對另一部文獻的闡釋,如《韓非子·解老》《喻老》是對《老子》一書思想内藴的闡釋;五,兩部不同的文獻,其中一部是對另外一部的詳細闡釋,如《左傳》之於《春秋》。
“文中訓釋”現象是先秦經典闡釋學的一種類型。與其他幾種闡釋類型相比,它的特點是服從於論事説理的需要,在需要作出解釋時就作出解釋,可謂逐便制宜,具有偶然性、隨意性。“文中訓釋”現象,並非僅僅是一個孤立的文獻現象,它與先秦時期的語言文化、教育制度、政治氣候、學術風潮密切相關,是我們瞭解先秦語言文化、教育制度、政治氣候和學術風潮的一個視窗。因此,我們必須將其放在先秦尤其是春秋戰國的時代大環境中纔能透徹地理解它所折射出來的文化意義。
二
基本上可以這麽説,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是以訓詁學中訓釋的形式呈現的。“用語言來表述詞義的工作,統稱訓釋。”[注]王寧《訓詁學原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頁。案: 本文對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所涉及的詞義訓釋體例的分類主要依據王寧教授《訓詁學原理》的理論體系。後世一些常見的訓釋形式在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中已初露端倪,這反映了訓詁學的早期形態。
根據訓釋目的的不同,訓詁學將訓釋分爲義訓和聲訓兩類。這兩類訓釋在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中多處可見。義訓的目的是對藴含在詞裏的客觀内容加以揭示。義訓以義項爲單位,每個義訓只能訓釋詞的一個義項。如: 《荀子·大略》:“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聘,問也。享,獻也。”《孟子·滕文公上》:“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莊子·庚桑楚》:“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知者,接也;知者,謨也。”這些都是典型的義訓。形訓是一種特殊的義訓,它通過追溯造字意圖來挖掘詞義。漢字是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因義構形、形義統一的特點,所以人們可以通過漢字的形體結構來推求所訓詞的詞義。《韓非子·五蠹》:“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其中,關於“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即屬於典型的形訓。“私”的本字爲“厶”,其古文字像自我環繞之形。“公”字從厶從八,八有分、背之意,因此“背私”會意爲“公”。聲訓的目的是通過揭示訓釋詞與被訓釋詞之間的同源關係,來説明詞義的來源並顯示詞義。同源詞在聲音上相近或相同,在語義上相通,即所謂的“音近義通”。《孟子·滕文公上》:“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荀子·君道》:“君者何也?曰: 能群也。”庠與養、校與教、君與群三組詞語之間明顯存在“音近義通”的關係,屬於典型的聲訓。《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玄注:“庠之言養也。”“庠”與“養”音近,即將養老人之地。《廣雅·釋詁四》:“校,教也。”“校”與“教”音近,即教育子弟之地。《群經平議·春秋左傳一》“群臣不協”,俞樾按:“君與群聲近義通。”所謂“君”,就是能統治衆人之人。
根據訓釋方式,訓釋可分直訓和義界兩大類。這兩類訓釋在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現象中也已經大量出現。直訓是以單詞訓釋單詞。上舉“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等都是典型的直訓。義界是用定義或描寫的方式來表述詞義的内容並展示詞義的特點,從而把詞與鄰近的詞或義項區别開來。義界是以句釋詞,典型的義界是定義式,其訓釋方式可歸納爲: 主訓詞+義值差。主訓詞一般取共時共域的同義詞和上位的類詞。義值差則是藴含於詞義中的反映事物形狀、位置、動態、形貌、用途等特點的經驗性内容。如《荀子·修身》:“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其中的“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即屬於典型的義界。聞、見均爲主訓詞,多、少皆爲義值差。
筆者認爲,先秦諸子散文的“文中訓釋”現象,是保存在典籍原文中的訓詁,是中國訓詁學的先聲,在訓詁學史上確有篳路藍縷、導夫先路之功。
“文中訓釋”所用的程式化訓釋用語如“……也”、“……者……也”、“曰”、“謂之”、“之謂”、“猶”等,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學術自覺,已爲後世的訓詁工作所普遍沿用。“文中訓釋”所做的義訓、聲訓、直訓、義界等訓詁工作,爲後世的訓詁學研究作了材料的積累和理論上的準備,這集中體現在隨文注釋、纂集專書等領域。
在漢代以後浩如煙海的訓詁材料中,很大一部分是隨文注釋,包括傳注類、章句類、義疏類、集解類、徵引類、音義類等。大量“隨文注釋”材料直接采用了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的成果。例如: 《左傳》隱公三年“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唐孔穎達疏引《老子》三十九章説“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詩經·邶風·北門》“終窶且貧”,孔穎達疏“無財謂之貧”,與《莊子·讓王》文詞全同。《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唐李周翰注引《老子》十四章説:“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也。”《孟子·告子下》“與讒諂面諛之人居”,清代焦循正義引《莊子·漁父》云“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知”訓“接”爲常訓,如《墨子·經上》“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知者,接也”,王引之《經義述聞·禮記中·物至知知》因此説:“古者謂相交接曰知,因而與人相交接亦謂之知。”
纂集專書是在隨文注釋的基礎上形成的,按一定原則編排起來的,有目的地類聚字、詞、義的訓詁材料。就纂集目的的自覺程度和對材料的整理程度來分,纂集專書分爲集合貯存型(如《爾雅》)、整理編選型(如《方言》)和理論證實型(如《説文解字》)。東漢許慎《説文解字》的訓釋一般都是形訓,其中對“公”與“厶”的訓釋直接吸收了《韓非子》的成果。《説文解字·厶部》釋“厶”:“奸邪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注]許慎《説文解字》,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89頁。《説文解字·八部》釋“公”:“平分也。從八,從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注]同上書,第28頁。《説文解字》訓“君”爲“尊也”,與《荀子·致仕》“君者,國之隆也”相合。《廣韻·文韻》對“君”的説解完全引用《荀子·君道》“君者,民之源也”。唐《慧琳音義》對“希夷”的説解,也完全引用了《老子》中關於“希”和“夷”的訓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文中訓釋”這一闡釋行爲並非出於語言研究的動機,其訓釋的目的在於爲叙事和説理張本。“文中訓釋”選擇的被訓釋詞大都是一些涉及哲理、道德、禮制、宗法等方面的名詞性詞語,且多抽象概念,罕見對動詞、形容詞或虚詞的訓釋。正如李宇明所指出的那樣,先秦諸子的時代,不可能把語言本身作爲研究的對象,也不大可能産生關於語言的專門理論。但是,語言屬於人類的重要行爲範疇,人們在觀察社會、談論人事時,必然會論及語言。先秦諸子的著作共同“構建了中國早期的語言學思想庫”[注]李宇明《〈論語〉之論語》,《語言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4期。。
先秦諸子散文的“文中訓釋”既有對單條詞語的獨立訓釋,又有對具有反義或近義關係的多條詞語的集中訓釋。上引《荀子·修身》中教與諂、順與諛、知與愚、博與淺、閑與陋、治與秏都是在内涵上截然相反的概念,荀子將它們集中在一起進行界定,做詞義對比,使各自的内涵一目了然。近義詞之間内涵往往存在交集,不容易區分。先秦諸子散文的“文中訓釋”也每每通過詞義對比的方式,使其内涵更加清晰。如《孟子·離婁上》:“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其中“自暴”和“自棄”是一對含義較爲接近的詞語。二者内涵中既有相同項,也有不同項。相同項是二者都有自我殘害的意思,不同之處在於“自暴”側重言語,言語冒犯禮義謂之“自暴”;“自棄”側重行爲,行事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再如,《孟子·梁惠王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其中“鰥”、“寡”、“獨”、“孤”是一組近義詞,都有“缺失”的詞義特點,但所“缺失”的對象各有不同,《孟子》在文中逐一進行注釋,各條詞義的特點得以彰顯。
“文中訓釋”中存在“同詞多訓”的情況,這顯示出諸子們具有了一定的語義闡釋意識。“同詞多訓”表現爲某“子”對同一詞語在不同篇目中做出不同的訓釋,以及多家對於同一詞語作出不同的訓釋。例如《荀子》在不同的篇目中都有對“君”、“賊”和“順”的訓釋:
《致仕》:“君者,國之隆也。”
《君道》:“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
《禮論》:“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
《王制》:“君者,善群也。”
《禮論》:“殺生而送死謂之賊。”
《修身》:“害良曰賊。”
《君道》:“從命而利君謂之順。”
《修身》:“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王制》:“能以事上謂之順。”
再看同一概念多家做出不同訓釋的例子:
《荀子·修身》:“傷良曰讒。”
《莊子·漁父》:“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莊子·讓王》:“無財謂之貧。”
《韓非子·難三》:“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
《論語·爲政》:“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荀子·臣道》:“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荀子·修身》:“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
《莊子·漁父》:“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韓非子·解老》:“郊者,言其近也。”
《荀子·禮論》:“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論語·堯曰》:“慢令致期謂之賊。”
《孟子·梁惠王下》:“賊仁者謂之賊。”
《荀子·修身》:“少見曰陋。”
《管子·侈靡》:“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
《韓非子·詭使》:“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
《論語·顔淵》:“克己復禮爲仁。”
《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孟子·盡心下》:“仁也者,人也。”
另外,先秦諸子散文的“文中訓釋”經常將相關概念類聚在一起,進行集中訓釋。如《莊子·漁父》:“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 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掛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其中,對相關概念“八疵”(摠、佞、諂、諛、讒、賊、慝、險)和“四患”(叨、貪、很、矜)分别加以類聚並進行訓釋。
先秦諸子散文的“文中訓釋”既有對單條詞語的詞義訓釋,又有對具有反義或近義關係的多條詞語的集中訓釋及辨析,還有“同詞多訓”以及相關概念集中訓釋等現象,這顯示出先哲們樸素的詞彙系統觀念和語義場意識。這種對意義和概念集中探討的風習,久而久之必然促使傳統語言學——小學從經學中獨立出來並自成體系。
綜上,“文中訓釋”反映了訓詁學的早期萌芽形態,爲後來專門的訓詁工作做了材料積累和理論儲備。“文中訓釋”所藴含的語言文字思想至今依然閃耀着智慧的光芒。
三
“文中訓釋”作爲闡釋性的文本不只出現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在同期的史傳散文等文獻中亦有不少用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莊王語曰“止戈爲武”等。相對而言,作爲一種語言文字現象,“文中訓釋”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出現尤多[注]此處需要説明的是,《左傳》是一部對《春秋》進行傳釋的文獻,屬於上文中所説的先秦闡釋體系中第五個類型,即一部書對另一部書的專門闡釋,與“文中訓釋”的訓釋目的和方法均不同,所以本文未曾將其作爲考察對象,而是將其作爲另外一種闡釋類型另文考察。。這與當時私學教育的興起、游説之風的盛行以及名辯思潮的風行、文獻的驟增有關。“文中訓釋”既是語言文字問題,也是政治風氣和教育問題,同時也是學術問題。
(一) 語言的古今流變使得諸子們在叙事説理時對某些内容作出一定的闡釋成爲一種必要。
時有古今,地有南北,語言文字在時間演變過程中會産生古今差異,由於地域的不同會産生方言差異。語言的古今流變和地域差異,都會給交流帶來障礙。清代陳澧《東塾讀書記》云:“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蓋時有古今,猶地之有東西南北,相隔則言語不同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别國如鄉鄰,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注]陳澧《東塾讀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頁。訓詁也就是“釋古今之異言”,翻譯也就是“通方俗之殊語”,都是爲了掃清思想交流方面的障礙。
方言是語言地域差異的突出表現。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音辭篇》:“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語言的地域差異給交流帶來障礙,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來了。《説苑·善説》記載春秋時期楚國鄂君子皙泛舟江中,聽越人擁楫而歌,聽不懂歌辭,於是召來兼通楚語、越語的譯官將歌辭翻譯爲楚語,即《越人歌》。孟子説許行是“南蠻鴂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許行是南楚蠻夷之人,説的話就像鴂鳥(伯勞鳥)一樣,北方人聽不懂且覺得不好聽。孟子與宋國大夫戴不勝討論怎樣纔能使宋王向善時,講述了楚國大夫欲讓其子學習齊國方言的故事。《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楚國與齊國言語不通,楚人要學習齊語,由楚人教導則不如齊人教導;由齊人教導,則不如乾脆到齊國生活。
雖然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林立,語言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多地方言並存,但是我們在閲讀先秦文獻時,幾乎不會因爲撰寫者的方言問題而産生閲讀障礙,而先秦諸子文獻中也幾乎看不到因爲方言不通而需要作出闡釋的記載。這是因爲,在春秋戰國時期,漢民族早就存在一種通用的共同語——雅言。雅言出現的時間雖然學界存在争議,出現於西周,還是更早的夏、商,現在還不能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共同語已經成爲社會各階層之間交際往來的通用語言了。晉公子重耳流亡異國,北方諸侯國的卿大夫到南方出使聘問,孔子周遊列國,孔子教授來自其他諸侯國的弟子等,都不存在語言不通的問題。究其原因,就是共同語在起作用。春秋末戰國時期的諸子們在著書立説、課徒授學時,用大家都能聽懂看懂的通用的共同語,所以,在諸子文獻中,也就不會出現“通方俗之殊語”的訓釋現象,不需要對方言進行闡釋。諸子們真正要做的,是“釋古今之異言”,即解釋語言文字因時間變遷而産生的意義模糊。
語言文字的古今演變給交流帶來障礙,先秦時代的文化階層就已經感受到了。古時一些婦孺共知的字詞,到了近世需要做出一定的注解纔能使人通曉。《孟子·離婁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遝遝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遝遝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遝遝,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詩經》時代人們所説的“泄泄”,到了孟子所生活的戰國時代已經不爲人所理解,所以孟子用戰國時代人們熟知的“遝遝”作出解釋,即“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這是典型的“釋古今之異言”的訓釋用例。
(二) 私學教育的興起、游説之風的盛行,也促使諸子們在課徒授學、與君主進行對話晤談時對於所述的某些内容作出一定的闡釋。
春秋末戰國時期,原來貴族子弟專享的王官之學被打破,私學教育興起。孔子之前,已有賢達之士開始創辦私學,招收門徒。《吕氏春秋·下賢》載:“子産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子産爲鄭國相時,跟隨壺丘子林學習,與其弟子同坐。座次的安排以年齡來定,而非權勢地位。與孔子同時的少正卯在魯國“聚徒成群”(《荀子·宥坐》),曾經致使孔門“三盈三虚”(《論衡·講瑞》)。可以推斷,少正卯應該是一位很善於講學、很有思想吸引力的師者,不然不至於屢屢將孔門弟子吸引過去。孔子無疑是春秋末期興辦私學最成功、教授弟子最廣泛的人物。他“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死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漢書·儒林傳》)。弟子們又各自招收門徒,將私學教育發揚光大。“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儒、墨並稱顯學。墨子自稱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墨子·公輸》)。墨子死後,墨離爲三,門徒弟子很多。
及至戰國,隨着社會對士人階層的需求增大,聚徒講學之風更盛。齊國稷下學宫是戰國諸子們聚居之地,它既是議政場所,同時也是諸子們進行學術交流、開展私學教育的場所。諸子們在學宫内享受優厚的物質待遇,招收門徒衆多。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駢在齊,“訾養千鐘,徒百人”(《戰國策·齊策》);至齊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已多達“數百千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戰國時代舉凡著名學者幾乎没有不是聚徒講學、不是“率其群徒,辯其談説”(《荀子·儒效》)的。像惠施這樣的辯者,外出時追隨他的門徒也常“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吕氏春秋·審應覽》)。即使許行這樣一個“爲神農之言者”,到小而落後的滕國,也有“徒數十人”跟隨(《孟子·滕文公上》)。
先秦時期的私學教育不僅學生數量龐大,且生源複雜。庶民子弟、商人、大盜、暴徒均可趨於私學就學。孔子“有教無類”,自云只要弟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荀子·法行》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是以雜也。’”《吕氏春秋·尊師》對於先秦私學教育生源複雜的情況有一段詳細的描述:
子張,魯之鄙家也;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虜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子張、顔涿聚、段干木、高何、縣子石、索虜參等六人的出身,或爲庶民,或爲商人,甚至是爲人所不齒的暴民和大盜,由於接受私學教育而成爲爲人所敬重的名士顯人。此六人體現出春秋晚期私學教育生源複雜的事實。由於生源複雜,學生品質參差不齊,因此很難保證所有學生都能成爲合乎理想的人才。子張等六人後來成爲名士顯人,跟個人天資和後天努力不無關係,他們只不過是衆多門徒中爲數較少的佼佼者。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也不過七十有二,餘者恐怕多是尋常之輩。
從事私學教育的諸子們對當時的學風也並不滿意。《論語·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論語·先進》: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魯哀公和季康子都曾經向孔子詢問過弟子們的學風問題。孔子對二人的回答幾乎是一樣的: 顔回好學,可惜短命而亡,其他弟子都不好學。在《雍也》中,孔子又説:“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顔回可以長時間地居仁由義,其他弟子只不過偶爾纔能做到罷了。《公冶長》記載宰予竟然“晝寢”,遭到孔子嚴厲批評:“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或許,正是基於學風的不够理想,孔子纔反復強調“好學”的重要性和“不好學”的危害: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治長》)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
由於學生數量龐大,生源又較爲複雜,且整體學風不够理想,作爲交流對象的師生之間文化層次差距較大。因此,老師在向廣大弟子(即使是好學的弟子)傳達思想、傳授知識時,就必然需要作出一定的解釋。這是諸子散文中含有闡釋型内容的重要原因。
春秋末戰國時期,在波譎雲詭、風雲變幻的時代環境下,各國諸侯常有存亡之虞。爲了將諸侯國存在下來甚或期冀争霸稱雄,他們必須向新興的知識階層——士——時時求教。因此,禮賢下士對各國諸侯王、卿大夫們來説,就不僅僅是一個姿態,更是一種必要。對於士人階層來説,游説諸侯是他們宣揚自家學説並將其付諸政治實踐的最好途徑,也是他們極其看重的功業行爲。然而,作爲一國之君的諸侯王或者位高權重的卿大夫們並不占有文獻優勢,他們的文化層次不及士人階層,對於歷史掌故、典章制度不够熟悉,對具體的治國方針政策綱領等也没有清晰的見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就記載了春秋晚期齊國大夫慶封來魯國聘問,因不懂《詩》而出醜的事: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降至戰國,諸侯王、卿大夫的文化層次甚或不及春秋時代的諸侯王、卿大夫。因此,士人階層在對他們進行游説時就不得不作出一定的闡釋解説。《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孟子向齊宣王游説,導之以“與民同樂”之理:“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他通過徵引《詩》來增強游説的可信度,又擔心齊宣王不懂《詩》中“畜君”的含義,於是就做了“畜君者,好君也”的注解。又,《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孟子)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孟子在回答齊宣王何爲“王政”的詢問時,徵引周文王執政時對“鰥”、“寡”、“孤”、“獨”四者的撫恤,並對四者的具體含義作出解釋,以此説明何爲“王政”。
(三) 名辯思潮興起,知識階層思維能力增強;同時,文獻驟增,知識階層有足够的文化儲備。此二者都爲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現象的出現提供了助力。
如果説先秦游説之風和私學教育的興起以及語言文字的古今流變使得知識階層在論事説理時作出一定的注解成爲一種必要的話,那麽,先秦邏輯學的發展則爲這些注解的産生提供了強大的思維能力的保證。
我國古無“邏輯”之名,只有“形名”或“辯”之稱。《莊子·天道》:“形名者,古人有之。”晉代魯勝《墨辯注序》:“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形名”、“辯”與西方所講的“邏輯”其實是一致的。那麽“形名家”(《戰國策·秦策》)、“辯者”(《莊子·天下》)大體可以説就是致力於邏輯研究的人。班固《漢書·藝文志》雖然將名家、辯者定性爲“苟鉤鈲析亂”之流,但是他們的言論中所藴含的邏輯學成就是無論如何不能抹煞的。撮其大要,先秦邏輯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先秦邏輯關於“名”的理論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揭示了“名”的本質:“名”是用來反映事物的(《墨子·小取》“以名舉實”),是對許多事物共同本質的反映(《荀子·正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提出了“正名”的思想: 名要有確定性(“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名實要相符(《墨子·經説上》“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對名作了相當科學的邏輯分類: 從外延分,《墨辯》將名分爲達、類、私三類,《正名》則把名分爲共名和别名;從内涵分,《墨辯》將名分爲形貌之名和非形貌之名,居運之名和數量之名,《正名》則將名分爲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從語言表現形式上,荀子分爲單名和兼名。公孫龍子和墨家還提出對事物進行分類的“偏有偏無有”原則,即必須以一方偏有、一方偏無有的屬性作爲事物分類的標準,並且偏有偏無有的屬性應該是事物的本質屬性。提出了名的約定俗成原則: 《墨辯》:“君、臣、萌(民),通約也。”《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第二,先秦邏輯在“辭”(即判斷)的理論上貢獻突出。揭示了辭的本質,即辭是連屬不同的名以明白表達一個思想的思維形式(《荀子·正名》“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的任務是抒意(《墨子·小取》“以辭抒意”);指出正確的思維要“當其辭”,即辭表達思想要準確明白;總結出“辭”的一些形式,如“盡,莫不然也”(即全稱判斷)、“或”(近似特稱判斷)、“必”(必然判斷)、“假”(假言判斷)等。
第三,先秦邏輯在“説”、“辯”(邏輯推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闡述了“説”、“辯”的本質: 從狹義上講,二者意義各有側重,“説,所以明也”(《墨子·經上》)、“以説出故”(《墨子·小取》),主要指推理;“辯,争彼也”(《墨子·經上》),指的是争論一對矛盾對立的雙方孰是孰非,即辯難。從廣義上講,二者同義,都是指推理、論辯。推理論辯必然有對有錯,有勝有負;提出許多具體的判斷推理形式,如假(假言判斷)、必(必然判斷)、盡(全稱判斷)、或(特稱判斷)、類(類比推理)、取(歸納推理)、予(演繹推理)等。
專事中國邏輯史的學者指出,“先秦邏輯史是中國邏輯史的開始階段。先秦邏輯和我國秦以後的邏輯比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先秦邏輯是中國古代邏輯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秦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百家争鳴没有了,中國古代邏輯也日趨衰微了。魏晉時期,名辯思潮復興,出現了像魯勝那樣有成績的邏輯家。但總的説來,卻没有達到《墨辯》的水準,更不用説超過先秦邏輯了。一直到清朝,考據之學興起,對諸子之學的評注之風日漸高漲,隨之帶來了中國古代邏輯的復興。這個時期不僅出現了對《墨子》《公孫龍子》《荀子》等書的許多注疏本,還出現了一些關於《墨辯》、惠施、公孫龍、荀子名辯思想的研究專著。但是這些工作,也旨在整理、注疏先秦名辯古籍,進而揭舉其中的名辯精華,還不見多少創新與發展。這個事實進一步説明先秦邏輯確實是中國古代邏輯史上的高峰。”[注]周雲之、劉培育《先秦邏輯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311頁。而先秦諸子散文中之所以出現“文中訓釋”現象,與當時知識階層思維能力的提高有着密切的關係。
一段完整的思維序列應該包括“名”、“辭”、“推”,即界定概念、作出判斷、進行推理三部分。先秦諸子散文“文中訓釋”現象主要是“定名”,即界定概念、解釋名詞内涵的部分,是思維序列中的一環,而且是首要的一環。只有將概念、名詞的内涵界定清楚,纔能進行判斷和推理。而在叙述、議論過程中有意識地進行“定名”,正是思維自覺的表現,也是知識階層思維能力提高的産物。
春秋戰國時期,文獻大量增加也爲散文中出現“文中訓釋”現象提供了強大的材料支援。據過常寶教授考證,先秦時期曾經出現過兩次文獻編纂的高潮: 一次是西周初期周公制禮作樂,神道設教,掀起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新運動。而在這次革新運動中,文獻編纂意識甚爲強烈,《詩》《書》《易》等文獻被編纂出來。另外一次就發生在春秋末戰國時期。“春秋晚期開始了中國古代第二個文獻編纂的高潮。這一文獻高潮的到來,有賴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禮崩樂壞的局面形成,致使神道設教漸漸失去效力,迫切需要新的經典,以推動社會意識形態的進一步革新;二,宗教意識的衰落,使得舊有文獻不再神秘,不但貴族君子可得而觀覽,一般士人也可通過種種渠道掌握禮儀和文獻;三,史官朝不保夕,其中一些人只能以文獻謀生,以順應士階層求學的需要,文獻可能成爲教學的材料。基於這三方面的原因,春秋末期的史官和士人開始對舊有文獻進行較大規模的編纂活動”[注]過常寶《先秦散文研究·緒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隨着文獻的大量增加,知識階層所能閲覽到的史料也就越多,對於古史、古代典章制度越來越熟悉,因而有能力在叙述、論説過程中對這些爲普通人所不熟悉的知識做出解釋。《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春秋時期晏子向齊桓公解釋古時的巡狩、述職制度:“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論語·季氏》載:“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這大概是孔子向弟子們講授古史時對古代諸侯王妻子各種稱呼的解釋。正是得益於文獻的驟增,知識階層在課徒授學或者游説諸侯、與君主議政時纔能够掌握足够的材料對古史、古老的典章制度作出解釋。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階層,一方面處於思考能力大爲提高的歷史時代(雅斯貝爾斯稱之爲“軸心時代”),另一方面又能够閲讀到足够多的歷史文獻。他們既有思考能力的保證,又有文獻資料(論據)的強大支持,因此,無論是叙述還是説理,都能得心應手應對自如。他們明確了自身作爲知識階層的身份體認,以傳播知識、創造思想作爲自己的職業責任。在傳播知識、創造新的思想主張的過程中,有時需要對某些内容作出解釋,他們也有強烈的闡釋欲望,又有足够的闡釋能力和論據支撑。這就促使先秦諸子散文中出現了大量的“文中訓釋”型材料。這是先秦諸子散文中“文中訓釋”現象出現的内在原因。
綜上可見,先秦諸子散文中出現“文中訓釋”現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