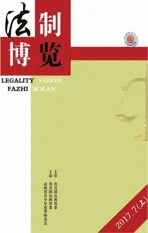国际法视阈下当前军控与裁军规范体系的局限性
2017-01-26丁铎钟卉
丁 铎 钟 卉
1.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1100;2.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1100
国际法视阈下当前军控与裁军规范体系的局限性
丁 铎1钟 卉2
1.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1100;2.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1100
军控与裁军条约、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条款、联大与安理会相关决议、防扩散机制下相关协定以及当事国单方面措施共同构成了国际法上军控与裁军的规范框架。这一规范体系在核武器削减与防扩散、禁止生化武器和常规军备控制方面存在着效果有限、进展缓慢、普遍性不足等局限,多边条约的实施受制于主要国家的掣肘。军控与裁军规范的拘束力依赖于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规范存在的认知,其效果取决于这些国际法规范如何被内化于国家行为之中。
国际法;军备控制;条约;拘束力
一、引言
裁军与军备控制有着漫长曲折的发展历史,早在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Israelite)与非利士人(Philistine)和平时期,双方曾达成一致,限制各自军队中铁制兵器的使用;公元前5世纪左右,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亦曾约定各自控制新建城郭的规模以维持彼此间均衡与和平;公元前201年,罗马与迦太基(Carthage)签订的扎马条约规定,迦太基只能保有10艘舰船并且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战象。从现代意义上来说,世界各国是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认识到军备控制是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当前,军备控制与裁军体系存在三个结构层级,即国际条约规范体系、国际组织以及国家自我管制。国际条约从国际法规范性层面,强调军控与裁军议题的基本原则与法律规范,国际组织代表着执行国际法规范的国际多边机制,国家管制则是以国内法体系补充并强化国际管制的不足,由这三项管制结构体系的严密程度可以了解国际社会对于军控与裁军议题的态度。
目前,在中文文献中就国际法上军控与裁军的规范体系及其局限性进行论述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关于军控与裁军国际规范的研究论文更多是侧重于对某一条约或机制的技术性剖析而欠缺国际法理论层面的思考。不可否认,军控与裁军议题涉及到军事科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多个领域,而国家对于这些规范与机制的认同与接受乃至在何种程度上其内化为国家政策的框架与规则,则是国际法学者的关心所在。基于此,笔者拟从军控与裁军的概念入手,在国际法层面对目前相关规范体系及其局限进行分析梳理,并就其拘束力与国家间的共同认知展开思考,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二、军备控制的国际法解析
(一)裁军与军备控制的概念
在不同时代,学者对裁军的概念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传统观点上来看,裁军是指能够反映国际政治实际状况的对军备规模的限制与缩减,也即从量的层面上来对其作出定义。[1]按此传统观点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在军备控制协商机制中所达成的诸多军备削减举措、限制措施、互信机制以及防扩散机制则不被包含于裁军的概念范围内。[2]与裁军的概念相比,军备控制的范围更加广泛,包含了军备有关的限制措施、冻结措施、监督核查措施、双边或多边信息机制、防扩散机制以及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依国际法所采取的特定军事举措、为避免双方误判而依国际协定建立起来的军事沟通机制,为防止偶发军事冲突的互信措施,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能被归为传统意义上的“裁军”范畴。
(二)国际法上的军控与裁军规范体系
一般而言,与武器系统相关的国际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战时特定武器系统如何运用的国际法规范,二是平时关于特定武器系统开发、制造、保存、转移、实验以及废弃等问题的国际法规范,军备控制规范体系属于后者。军控与裁军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尽可能减轻战争带来的危害,以此为目标,国际社会长久以来在军控与裁军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特别是1950年代提出通过“普遍的与全面的裁军”努力将各国军备限定在人类共存所必需的水准之上。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严峻的冷战形势使国际社会意识到普遍与全面裁军的重重困难进而转向部分裁军的军控机制,并将核裁军作为最优先和最紧迫的任务,各国之间亦进行了诸多双边与多边谈判,其最大成果便是先后缔结的诸多国际军控与裁军条约,这些条约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军控条款、联大与安理会相关决议、武器防扩散机制相关协定以及当事国单方面军控与裁军措施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法上军控与裁军的规范框架。
1.《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军控与裁军的条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在其规约第一条第二款和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中规定了与军备相关的一般性义务。与此不同,二战之后,联合国宪章中并未具体规定军控与裁军的具体责任,而是代之以会员国承担的对联合国总会及安全理事会的义务,换言之,宪章中未对会员国作关于军控与军备的具体义务规定。究其原因,一方面,宪章导入了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并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同意安全理事会在履行此项责任时,即代表各会员国;另一方面,历史上国际联盟规约虽规定了一般性裁军义务但始终未能得以全部实施,1932年至1934年间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亦未获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对联合国可以说是前车之鉴。
宪章中言及军控与裁军的条款有二,第11条第1款规定,联合国大会可以考虑裁军及军备控制等普通原则,并赋予了其就此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的权利;第47条规定,安理会设立军事参谋团,以便对于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及军备控制及裁军问题,向安理会贡献意见并予以协助。除此之外,宪章序言、第2条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33条至第38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宪章第七章部分条款(对于威胁、破坏和平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虽未直接涉及军控与裁军,但为其为军控与裁军提供了充分依据和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基础。
2.有关军备控制及裁军的国际条约
国际法学者穆勒曾经指出,军控协议的拘束力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缔约社群的凝聚力,二是领导者,三是大国之间的合作,除非达成这些条件,否则军备控制规范的拘束力议题将举步维艰。[3]首先,多边军备控制协议将创造出一个由条约当事国组成的社群,这些国家可能出于不同原因而加入统一条约,但其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普遍性核心性的共同目标,条约实际履行方式以及条约如何调整缔约国之间的关系是维系这一缔约社群的关键。其次,就遵守条约而言,领导者必需符合三个条件才能达到维系缔约社群凝聚力的目的,即透明度、义务履行与规则限制。第三,主要大国间对条约本身的共同意志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在遵守条约时表现出的承诺和支持以及持续通过多边机制强化军备控制的意愿,对于军控协议的拘束力有着直接影响。
一般来说,为实现军备控制与裁军,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是最为确实的一种途径,条约生效之后当事方此前对于缩减军备的各种承诺成为国际法上需要承担的具体义务,这对于缔约方而言也最具约束力。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对这些条约做赘述,仅将诸多条约依照不同的军控领域加以整理,以期通过更为直观简洁的方式反映出在削减核武器、核不扩散、限制生化武器及常规军控方面的基本规范性框架。目前各国缔结的军控条约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三个领域,一是核武器军备控制条约,体现在有核国家特别是核大国战略核武器削减、防止核武器扩散、全面禁止核试验等方面;二是生化武器军备控制条约,主要包括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关国际条约;三是常规武器领域的军备控制条约,主要包括对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使用限制,对人员杀伤地雷的限制,对集束弹药的限制以及常规武器贸易的相关协定。
3.与军控和裁军相关的联大决议与安理会决议
与军控和裁军相关的联大决议范围广泛,数量众多,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其反映了联合国大会对该问题的一般性建议,从促进国际法渐进发展的角度而言也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设立各种军控及裁军委员会的相关决议、推动促进会员国缔结各类军控条约的相关决议、防止核战争及不使用核武器等方面的相关决议。
相比于联大决议,安理会关于军控和裁军的决议更具强制性也更为具体化,主要集中于防扩散领域。例如,1995年安理会第984号决议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安全保证的合法利益,并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体缔约国都必须充分履行其所有义务;2004年4月2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540号决议,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材料和技术的国内管理和出口管制据此决议,安理会成立防扩散委员会(1540委员会),审议各国提交的报告,此后安又先后三次通过决议将1540委员会任期延至2021年;2009年安理会通过第1887号决议,重申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以促进国际稳定的方式,根据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寻求建立对所有国家都更安全的世界,并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创造条件。
4.相关武器及军事技术防扩散机制下非正式组织的相关准则
国际社会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防扩散体系。这一体系对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说是有效的。在核不扩散领域,这一体系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桑戈委员会和核供应国集团为组成部分。桑戈委员会的控制机制由A、B两个备忘录和一个附件组成,备忘录对原材料、设备或材料出口作了定义。该委员会的决议、备忘录对成员国没有法律拘束力,只对各国制订核出口政策起指导作用。在常规武器领域,美国主导建立了包括一份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和一份军品清单在内的瓦森纳安排机制,将其作为在自愿基础上的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以提高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转让的透明度。瓦森纳机制从其成员国组成和实际运行来说,瓦森纳机制具有明显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地缘政治考量。
三、国际法上军控与裁军规范体系的局限性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在二战后经过七十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以来的持续努力,形成了以普遍性多边条约为主要法律基础的军控和裁军规范框架,在诸多区域性多边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系列防扩散与核查机制,特别是2013年联合国大会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并陆续得到诸多国家的批准,这些成果无一不体现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然而就目前而言,其在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军控与裁军方面也存在诸多局限性。
(一)核武器军控规范的局限性
就实际削减核武器而言,首先,美俄间《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于2010年开始生效,即便条约规定至2018年两国大幅削减战略核武器数量,但届时双方仍可各自保留至少1550枚核弹头,从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来讲,这一数量级的核弹头保有量所能够带来的打击依旧是毁灭性的。其次,为履行该条约中规定削减销毁核武器之义务,所需费用开支数额巨大,这不可避免地成为条约顺利实施的实际障碍,就此而言,截至2020年条约效力终止时,美俄两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条约规定削减目标仍然是个未知数。第三,在美俄两国缔结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诸多双边条约中规定有核查机制,实地核查作为手段之一,其对象被限定在美俄双方事前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设施范围内,这对核查机制实际效果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最后,目前削减核武器的双边条约只局限于美俄两个核大国之间,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核武器拥有国中虽不乏有国家就核武器使用限制作出单方面声明,但并未以更具法律拘束力的形式参与实质性核武器削减。
就限制核试验而言,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虽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但目前仍未生效,究其原因,条约规定在其附件二中所列的44个有核能力国家全部交存批准书后第180天起生效,截至目前这44国中尚有美国、中国、埃及、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没有批准该条约,条约尚不符合生效条件。对此,国际法学界最为悲观的看法认为,44国中一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很可能始终不予批准该条约,进而使得该条约的生效要件永远不会达成。其次,《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未禁止在实验室内进行的核试验和计算机模拟核试验,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超级计算机的不断更新换代,通过模拟实验得出核试爆数据早已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条约尽管名义上为“全面禁止核试验”,但依然为核武器的继续改进与开发留有很大空间。
(二)生化武器军控规范的局限性
在禁止生物武器方面,首先,截至2015年共有171个国家成为《禁止生物武器条约》的当事国,这其中有13个国家对条约的部分条款提出了保留,虽然这有助于各国就加入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客观上也削弱了条约的普遍性。其次,为确保条约义务得以履行,条约第四条规定了当事国应当采取的国内措施;第六条仅规定缔约国如发现任何其他缔约国的行为违反公约义务时,可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各缔约国承诺在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而发起进行的任何调查中给予合作。除此之外条约在核查机制方面并未做更多详细规定,缺少包括实地检测在内的更为有效的核查措施。第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生命工学技术的发展,生物科技领域一些军民两用技术与装备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由此带来的生物武器扩散的风险日益加剧。尽管公约要求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剂、毒素及其武器,但始终无法消除生物武器扩散的潜在威胁。[4]
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宣称主要目的是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虽然其最后达成的协议有限,但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战争法规编纂方面签订了多项公约和宣言,其中“1899年海牙第二宣言”规定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又签订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但这些协议在之后历次世界大战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拘束作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目前共有190个当事国,但以色列、朝鲜、缅甸等化学武器拥有国依然没有加入该公约。就国内措施而言,公约第7条规定涉及各缔约国为确保公约的执行而必须采取的国内措施和国内立法,同时规定缔约国应设立或指定国家主管部门作为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进行联络的中心。
四、结语
国际法学者哈罗德教授曾指出,国际法规范为国家所接受,大概经过三个阶段:互动、解释与内化。[5]国家间以条约或习惯方式互动,形成国际法规则,而后经过国家实践与解释过程,逐渐形成一套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执行机制,最后国家普遍接受该规范与价值,并将其视为国家必须遵守的国际法规范并内化为国内政策与法律规范。国际军控与裁军规范包含着国家间相互交错的共同意志,国家对于诸多军控与裁军规范有着共同认知,尽管目前近乎全部的国际军控与裁军规范都是依条约建立起来,但国家对于这些规范的共同认知使这一规范体系的拘束力得以强化。另一方面,国际军控与裁军规范体系经过长期的发展与积累,在核武器削减与核试验限制、生化武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常规武器限制等方面各有成果,其作为目前国际安全议题层面的主要规范之一,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家利益的界定,时至今日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大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军备政策的影响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
在国际安全议题上,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建立起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军备控制与裁军等基本共识。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角度而言,目前国际体系并非单纯由国家权力关系构成,规范国家行为所建立的一系列法的规则也是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撑,[6]可以预见,在稳固的国际法环境下,军控与裁军规范的拘束力将会得到不断强化。若各个国家能将多边主义的国际法规范内在化,那么多边军控与裁军规范的拘束力将会获得最佳效果,甚至经过长期国际协商与实践而产生的军控规范体系,不仅可以提供国家的行为准则,也能构建以互惠和合理期待为基础的规范机制。
[1]Philip John Noel-Baker,Disarmament(London:The Hogarth Press,Reprint 1970,New York:Kennicat Press).
[2]H.Lauterpacht(ed.),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Vol.II(London,Green and Co Ltd.,1952).
[3]Harald Müller,“Compliance Politics:A Critical Analysis of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Treaty Enforcement,”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Summer 2000).
[4]Laurence Lustgarten,“The Arms Trade Treaty:Achievements,Failings,Future”,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ume 64,Issue 03,July 2015.
[5]Harold Hongju Koh,“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The Yale Law Journal,1997,Vol.106,No.8,Symposium:Group Conflict and the Constitution.
[6]Leslie G.Green,“Reviewed Work:Rules,Norms and Decisions: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by Friedrich V.Kratchowi”,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23,No.4(Dec.,1990).
The Limits and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Disarmament Law
International disarmament law is composed of the disarmament provisions of the UN Charter,the resolution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the guide lines of the multilateral weapon and technology expert control regime,including disarmament treaties.Since the disarmament issue is in relation with secure,strategic,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each country,the fulfilment of disarmament is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Multilateral treaties are managing only certain type of weapons.Disarmament treaty has a verification regime with shortage and limit.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disarmament law depends on the consensus over the legal regim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nd the effect relays on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legal norms.
International law;Disarmament;Treaty;Binding force
D
A
2095-4379-(2017)19-0006-04
丁铎(1986-),男,汉族,海南海口人,法学博士,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际法专业,研究方向:国际法与海洋法一般理论;钟卉(1987-),女,汉族,海南海口人,翻译学硕士,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合作与海洋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