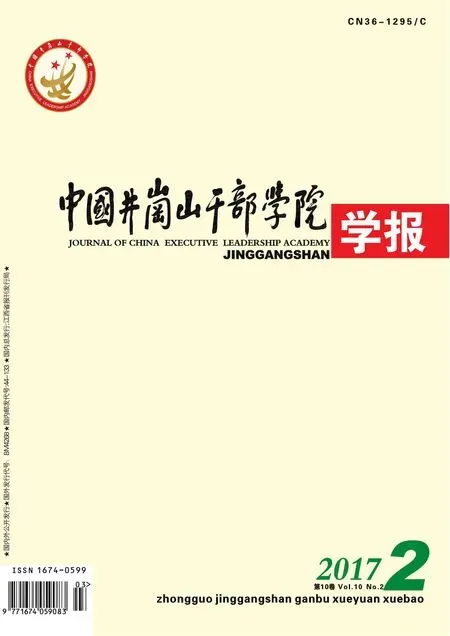论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生与演进
2017-01-25李红梅
□李红梅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思政部,广东 广州 510640)
论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生与演进
□李红梅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思政部,广东 广州 510640)
党的群众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与演进的过程,呈现出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态势。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党初步形成了群众观点和群众意识,提出了一些零碎而粗浅的工作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不仅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而且将其确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使群众路线发展为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群众路线作出了完整规范的表述,对群众观作出新的概括,提出了一系列贯彻群众路线的新方法,使群众路线上升到成熟而科学的理论形态。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根本工作路线;产生与演进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党的群众路线有一个产生与演进的过程。它产生于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不断丰富与完善。本文依据大量翔实的史料,回顾了党的群众路线产生和演进的历史,认为这是一个各个阶段相互联系而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要全面把握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有联系地把握各个阶段的内容,充分了解这一路线产生与演进的历史。
一、在大革命洪流中,党对群众路线的基本方面有了初步认识
党的群众路线发轫于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这主要是由党当时所面临的革命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党从创建时起,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党的一大明确规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P1然而,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封建势力。中国近代历次革命的失败,无一不向中国共产党人昭示: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仅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难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
正因为如此,群众意识和群众观念就成为党与生俱来的内在特性。党在创立之初,就围绕其任务、纲领,提出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一大党纲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P1;党的二大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P162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1]P162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运动揭开序幕,党立即把群众工作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认为工农联合是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的四大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参加非党组织的工会,在工会里“为各种具体的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以取得对我们的信仰”;“在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须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使群众作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2]P231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指出:“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党。”[2]P59五卅运动前夕,党在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中说:“有明确的政治观念,有集合的战斗力,在国民运动中能够加给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力量。”[2]P363五卅运动之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党又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2]P472正是由于有了基本的群众意识和群众观念,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书斋,深入工厂;离开城市,来到农村,卓有成效地动员人民群众,使大革命洪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华大地。
在这一时期,党初步认清了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工农联盟。从中共成立到五卅运动,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密切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壮大了党的阶级基础。五卅运动后,党总结革命斗争经验,认识到“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农民和工人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3]P106因此,党开始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发动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支援北伐战争。党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见解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该报告尖锐地驳斥了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高度评价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和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一旦中国农民发动起来后,“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4]P13,一切反动势力都“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4]P13。
这一时期,党提出了关于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一是要勇于承担领导责任,而不能犯落后于群众的右倾错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边指手画脚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二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必须立场坚定,划清同反革命和机会主义的界线,大力支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三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当然,由于理论水平的局限,加之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匮乏,党在这一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对上述观点和方法加以系统的分析,形成全面的认识。但是,上述认识毕竟已经涉及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点。
二、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群众路线实现了理论飞跃
从1927年7月到1949年10月,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党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与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经验和脱离群众的教训,从而正式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并且把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8年党的六大后,李立三在与浙江地区党的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争取群众路线”的提法,但他强调的重点是“争取群众”。1929年9月,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提出并两次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指示信》在论及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时提出,筹款工作“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5]P35;在论及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时,则强调“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5]P39。从此,“群众路线”开始不断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并与群众观点、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一起,得到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
第一,党更深刻地认识到做群众工作、争取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重要性,解决了“依靠谁”的问题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法宝,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不久,他就把做群众工作规定为红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之一。1928年8月,党的六大制定的十大纲领,则把做群众工作确定为党的“中心工作”和“总路线”,即党的中心工作为“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党的策略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而不是组织起义。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针对部分党员和干部不懂得依靠群众、单打独斗的不良倾向,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指出,肃反、筹款等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经费开支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要防止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等等。[5]P35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回答红军要不要做群众工作,以及群众工作在党和红军工作中的地位等问题时,也阐述了要争取群众的观点。毛泽东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4]P86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一与十之比。毛泽东认为,“政治的观点即群众观点”,“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4]P88
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之际,党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1930年3月,《中央给广东省委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一切工作应尽量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同时指出,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压境,中央革命根据地危机四伏,毛泽东始终坚信群众的伟大力量,科学地预见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4]P139抗战期间,党所面临的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党反复要求“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必须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6]P525-526抗战胜利前夕,党对建党以来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依靠谁”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七大党章指出:“每一个党员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7]P535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对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进行如此深刻的阐述。
第二,党逐步提出了群众路线核心观点,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答了“为了谁”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劳动人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心人民的生活,解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就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也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与拥护,引导人民群众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因此,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周恩来就提出,“应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用各种方法帮助群众组织起来。[5]P35毛泽东也强调,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就要关心群众生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人民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限光荣的旗帜”。[1]P138-139抗日战争时期,党一方面对土地革命时期取得的经验和形成的观点加以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及时地总结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新鲜经验,最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命题。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地梳理了党的群众观,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认为,“只有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8]P354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刘少奇的“群众观点”作了进一步升华,提出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9]P1094党的七大采纳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7]P535载入了党章总纲。自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党的宗旨。
第三,党正式提出了根本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解决了怎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要实现自己的正确领导,就必须掌握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内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的第一人。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党正确的策略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共产党员的正确的不可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面能够产生的,它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1]P115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提出,群众工作必须采取“群众化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1]P124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阐述了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力量,并且首次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认为这是与关心群众生活、动员和发动群众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因此“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4]P139,即要采取实际的具体的、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和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伴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党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认识日益成熟。1943年6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正式提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9]P900,党必须要广泛而深入地实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9]P902。毛泽东强调,这种工作方法是无限循环的。“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9]P899这是迄今为止党对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最为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正式形成的标志。
第四,党和毛泽东从搞好党的建设的目标出发,把群众路线确定为党的优良作风
党的建设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基于此,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并将其总结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中,思想建设是根本性的、首要的建设。只有通过思想建设,才能确保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组织建设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是全党步调一致,发挥无穷战斗力的保证;作风建设是关键。党的作风是党的世界观、性质和宗旨的外在表现,它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关系到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使得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并在七大对党的作风做出了概括。七大的政治报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9]P1093在党的三大作风中,密切联系群众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党的正确的理论和决策都只能来源于千百万从事着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党的自我批评和反省就更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毛泽东还强调,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9]P1094。从此,群众路线得到了全党广泛而普遍的理解和认可,并在各项工作中得到自觉地贯彻和执行。党和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总之,党的群众路线在这一阶段已经发展为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党不仅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而且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并把“密切联系群众”确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相对于前一阶段的群众路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取得这样的发展是由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一,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被迫由中心城市转移到偏僻落后的广大农村,一方面是自然条件恶劣、物资供给匮乏,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的封锁和“围剿”。在空前的生存危机面前,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依靠谁”的问题,即如何赢得最强有力的支持,以克敌制胜,度过难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党的依靠力量唯有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如果党能够和劳苦大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领导他们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领导他们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就能获取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物力。其二,党深刻地总结并吸取了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大革命高潮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革命形势之所以蓬勃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比较好地坚持了群众的观点,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而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反“围剿”的失利,则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密切相关。党正是通过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才逐步认识到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0]P299其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和红军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环境。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利用这一大好时机,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这就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理论前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在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路线日臻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群众路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实践方面来说,建国后,党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理论方面来看,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不断与时俱进,提出了许多符合时代要求的重要思想观点。在这一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显著特点是:其内容得到不断的充实和丰富,成为完整、成熟而科学的理论形态。
第一,形成了关于群众路线内涵的完整表述
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根据革命战争年代党关于群众路线论述和成功的实践,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等做了进一步阐释,并将其统一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来表达。邓小平指出,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群众的观点,即“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同甘苦的工作作风”;[11]P217另一方面,则是群众工作的方法,即“领导的工作方法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1]P217后来,邓小平又在《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文中对群众路线再次进行了解释:“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11]P287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就更加明确、更加完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得到了不断深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群众路线做出了简明而科学的界定,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P834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则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再次进行了完善,加上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至此,党就形成了关于的群众路线的准确、完整和规范的表述,这就是:“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13]P67这一经典表述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对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全国执政的地位使得一些党的组织和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的增加了”,因而“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1]P221党的八大告诫全党:“如果正确地执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11]P221不过此时党还没有指出与民主革命时期相比较,在执政条件下正确执行群众路线重要性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之初,党在总结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八大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群众路线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起,确定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认为它们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活动中”。[12]P832-833可以看出,党此时仅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而且把它放在实事求是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吸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对群众路线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具体体现在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决定》提出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新论断,明确指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4]P928所谓根本工作路线,即党的工作所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和达到预期目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必须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离开了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另一方面,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仅如此,《决定》还确定群众路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命线。《决定》强调:“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兴亡。”“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14]P928此后,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就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作了大量的论述。尤其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即重申“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15]P120。为了教育党的干部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认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为期一年左右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第三,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作了新的概括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面对新的党情、国情、世情,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对党的群众观进行了新的概括,作出了新的论述。一是把党的群众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要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懂得,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4]P937二是提出了“权力观”“责任观”和“党群观”等新观点。《决定》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的观点。这些重要观点,近几年来,有的被搞乱了,有的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淡漠了。”[14]P938进入新世纪,党的群众观又有了新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并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核心内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认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和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15]P11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要“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6]
第四,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积累了一系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工作方法,诸如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抓中心环节以及耐心的说服教育等等。这些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依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不断走向深入,党所面临的任务和形势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人民的团结。毛泽东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党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党的八大进一步提出:要系统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之善于开展典型调查;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下级可以自由地批评上级,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成为反映民意和批评争论的讲坛;从国家的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督工作;采取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些方法都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提出来的,旨在克服实际工作中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具有具体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党把新的技术和新的理论运用到领导工作中,从而推动着党的工作方法从制度化向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发展。具体说来,“民主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倾听不同意见,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法制化”就是重大决策“要经过人大和政府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科学化”就是一方面要“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比较、鉴别和论证,有的重大决策在实施之前还需要试点”;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强决策研究、决策咨询机构的工作,发挥它们的参谋作用”。[14]P340
群众路线之所以在建国后继续得到发展,并不断完善成为完整、成熟的而科学的理论形态,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与民主革命时期党主要从事军事斗争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艰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因而所取得的经验也更加丰富多彩。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创造了前提。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党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由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实地代表着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于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因而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与拥护,从而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胜利,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因此,党执政后更加重视群众路线,并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不断深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第三,党对自己违背群众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一度曾错误地把群众运动等同于群众路线,企图通过搞群众运动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结果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通过总结与反思,强调指出:“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12]P835第四,党吸取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出现这种历史悲剧,固然有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和演变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长期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最终丧失了执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邓小平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17]P372;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8]P2279;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5]P92的群众观;习近平则郑重地提出“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19]P156。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步伐而得到继承、丰富和发展。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6]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6-19.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读本[Z].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姚金果)
On the For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LI Hong-mei
(Depart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GuangdongPolytechnicofScienceand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510640,China)
The Party’s mass line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forming and evolution,presenting a trend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marching forward with the times.During the Party’s creation and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the Party primarily formed the mass view and the mass consciousness,and brought forward some fragmentary,primitive working methods.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the Party not only brough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ss line” and elaborated it comprehensively and profoundly,but also defined it as one of the three styles of the Party,endowing it with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etical form.After the new China was established,the Party worked out a complete,normative formulation of mass line and a new generalization of mass view,and brough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methods for carrying through the mass line,thus updating the mass line to a mature,scientific theory.
CPC;mass line;basic working line;forming and evolution
2016-12-16
李红梅(1972—),女,湖南怀化人,侗族,博士,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学科共建项目“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1921-1949年)”(项目编号:GD15XDS01)、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研究项目(德育专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6JKDY20)的阶段性成果。
D23
A
1674-0599(2017)02-00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