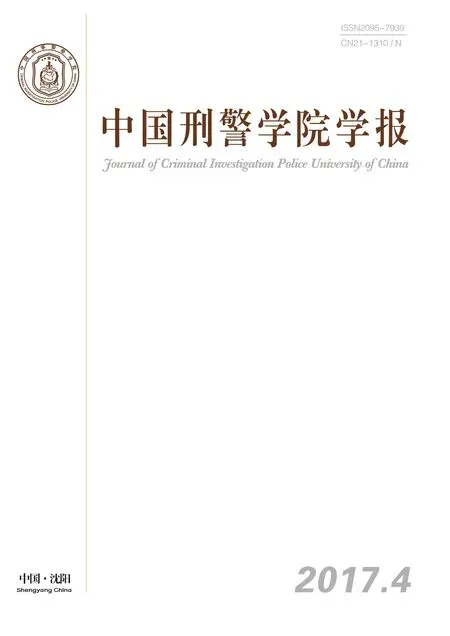论我国警察开枪面临的风险与应对策略
2017-01-24高长永
高长永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上海 200002)
论我国警察开枪面临的风险与应对策略
高长永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上海 200002)
我国警察开枪面临的有形风险与无形风险是现实存在的,这些风险是由法律规范不完善、缺乏科学有效的开枪后心理干预机制、开枪争议解决机制不健全等因素所引发的。应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改进制度缺陷,健全警察开枪后的心理干预机制,做好公共关系危机应对工作,有效应对警察开枪后面临的风险。
开枪风险 心理干预机制 开枪后调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9条规定了警察可以使用武器的15种紧急情况,《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第11条也规定人民警察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和危险程度,及时选择鸣枪警告、开枪射击等措施。但实践中,警察开枪时高度紧张,所处现场复杂、时机易逝,即使是训练极其有素的警察也不能保证开枪效果的绝对理想化。因此,笔者认为警察开枪所面临的风险是存在的,这种风险对警察心理、责任承担及警察权威,甚至是社会稳定、和谐都会造成影响。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警察开枪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系统研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1 基本概念辨析
实践中,警察开枪不仅会给警察自身带来风险,还会给相对人即犯罪嫌疑人、围观群众(主要是流弹误伤)等带来风险。
1.1 “风险”的含义演进与界定
风险在英语中的拼写是“risk”,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期的大航海时代,风险意味着海上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给探险家和商人带来的危险。传统社会或者说前现代化社会[1],风险主要来自洪水猛兽、风雨雷电等自然灾害。进入工业社会后,风险主要来源于当时的工业技术,其发生后果的可能性及损害程度在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2]。20世纪下半叶,“风险问题”逐渐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他们将现代意义上风险的发生作为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过程,把风险概念作为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演进的重要标志。“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发展的副作用。”[3]本文是在“风险社会”这一语境下对警察开枪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研究,明显区别于上述自然风险与工业社会技术限制所带来的风险,关注的是人的主体特征(即以警察为研究主体),侧重从制度化层面研究社会问题(即讨论现有法律规范、组织构架、体制机制等使警察开枪所面临的风险)。
1.2 “开枪”与“使用枪支”的区别
《规范》第3条第5款规定,“使用枪支”包括持枪戒备、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开枪射击4个阶段。“使用枪支”与“开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枪支”包括上述4种行为,而“开枪”主要是指鸣枪警告与开枪射击两种行为。是否扣动扳机、子弹是否击发是判断是否“开枪”的标志,持枪戒备、出枪警示只是在做形式上的威慑,不能认定为“开枪”。本文所讨论的警察开枪风险是指从鸣枪警告或开枪射击到整个事件平息这个阶段。
1.3 我国警察开枪面临风险的现实存在性
有些学者认为,警察只要按照规定程序开枪,就不会存在风险问题。笔者不同意此观点,原因有三:其一,警察平时佩带枪支,就承受着枪支丢失、被抢的心理压力。即使开枪射击符合法定情形,在面临犯罪嫌疑人被击伤或者击毙时,警察也会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出现心理障碍。其二,假设警察按照规定程序开枪,那么后果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同样也会存在风险控制问题。其三,实践中,警察依法开枪后,会遭到社会、媒体质疑,甚至会被“舆论绑架”。“就我们所经历的风险无处不在而言,我们只可能做出如下3种反应:否认、漠视和转型。”[4]警察开枪面临风险的现实存在性,需要公安机关正视这一问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应对策略。
2 我国警察开枪面临风险的识别
警务风险尚属新兴研究领域,借鉴相对成熟的风险理论,对我国警察开枪面临的风险进行科学分类,有助于准确及时地识别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许新源教授在《警务风险的概念、特征与结构》中将警务风险分为:“有形风险和无形风险,这主要是从风险损失的性质划分的。有形风险包括前面提到的财务风险、人身风险、资产风险等。警务中的无形风险主要有警察因工作失误、失职受到纪律处分,以及因警方的执法不力、腐败等对警察形象、警民关系、警察权威、社会公信力等产生的消极影响。”[5]本文将警察开枪面临的风险分为有形风险与无形风险进行研究。
2.1 有形风险
有形风险主要包括警察个体心理应激障碍、责任风险。个体心理应激障碍主要是指警察个体适应生存环境出现的身体反应;责任风险主要是指警察开枪后在人身自由及财产等方面面临的处罚风险。前者属于人身风险,后者属于人身与财产风险,两者皆为有形风险。其特点是作用于警察个体,易被识别。
2.1.1 警察个体心理应激障碍
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开创了现代应激研究。应激反应其实是一种生物普遍具有的适应生存的反应,适度的应激反应能激活和唤起身体机能,使机体处于合理的兴奋状态,以提高应对能力,更好地适应环境。但是,在遭受重大的刺激或者严重精神打击时,机体会呈现过度的焦虑、紧张,对信息的认知能力下降,应对力减弱,同时可能造成内分泌或免疫系统紊乱,抵御疾病能力下降,甚至可能导致各种心理疾病。这种有损身心的心理反应一般被称为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6]。警察开枪后的应激障碍主要表现为:侵入性症状——枪击事件反复地、侵入地、痛苦地进入回忆;回避性症状——尽量回避与开枪事件有关的所有线索;高警觉症状——过度警觉,容易被惊吓、激惹,睡眠障碍,以及不计后果的自我毁灭[7]。
2.1.2 不确定的责任风险
《条例》第9条规定了警察可以使用武器的14种法定情形,并在第15项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基本涵盖了《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第4条、《监狱法》第46条、《看守所条例》第18条等法定开枪情形。作为兜底条款;《条例》第10条规定了警察不得使用武器的两种情况;《规范》对警察枪支使用、调查处理等作出了规定。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为警察用枪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同时也设置了若干限制。但是,警察开枪所面临的现场情况复杂多变,法律规范很难将警察使用枪支的方方面面涵盖其中。虽然《规范》第11条为应对紧急、突发情况规定了警察“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和危险程度”选择适当的用枪措施,但并没有进一步出台更具操作性的解释和指导性用枪案例为警察开枪提供有效参考。法律规范的模糊性、滞后性无法为开枪警察提供合理的预期,使其可能承担不确定的责任后果。《条例》第14条规定了警察违法使用武器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其所属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条例》第15条规定了警察依法使用武器造成无辜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应承担的补偿责任。人民警察违法使用枪支可能触犯《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罪名;行政责任主要是指警察违法使用枪支,尚未构成犯罪,但应该接受的公安机关内部行政处分;《国家赔偿法》第16条①《国家赔偿法》第16条第1款:“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规定的追偿制度,使得经济赔偿的最终责任落到违法使用武器的民警身上。
2.2 无形风险
无形风险主要包括警察群体的消极心理和警察公共关系危机。警察群体的消极心理并不能对警察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实质损害,主要影响的是警察群体合法及时开枪的积极性。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后果则是导致警察权威的弱化。无形风险不像有形风险那样直接作用于警察个体,其大部分作用于整个警察群体,而且不易被发现。
2.2.1 警察群体的消极心理
群体心理就是“在某种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互影响或经常往来的社会心理共同体,它是由共同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是群体全体成员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性心理”[8]。警察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有着大致相同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追求,个体间会以内心的情感体验作为纽带,容易出现感同身受的心理共鸣,从而对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公安机关如果不能有效消除警察开枪后出现的应激障碍,不仅会影响警察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还有可能使消极心理在警察群体当中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公安队伍的战斗力。
2.2.2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主要是指除了自然灾害危机、社会宏观环境危机以外突然发生的,严重损害警察形象甚至造成相关人、事、财、物的重大损失,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受到公众的指责乃至敌视对抗行为的危机事件[9]。作为警察强制力最集中的体现,警察开枪事件常常成为社会舆论热点。群众关注的不仅仅是警察开枪事件本身,还关心公安机关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置态度与处置方式。在一些警察开枪事件中,官方公布的警察开枪行为合法的调查结果仍会受到舆论的非议,很大原因是公安机关未能做好后期信息公开及舆论引导工作②2012年9月21日,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一派出所副所长张研在处置一起因拆迁补偿引起的村民闹事时,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开枪,一村民当场死亡。事件发生后,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及盘锦市相关部联合成调查组,向社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开枪民警枪支使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是,针对此事件,各大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85%的网友对此表示愤怒,96%的网友认为警察开枪违法。。警察使用枪支不当、公安机关后期处置不及时、媒体报道失实等都可能引起警察公共关系危机。
警察开枪事件引发的警察公共关系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警察权威的弱化。某些被利益驱使的新闻媒体歪曲警察开枪事实,导致警民和谐关系遭到破坏,警察权威不断弱化。枪支配备本应成为警察执行公务时最有力的保障,但模糊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领导对枪支使用的谨慎态度及社会舆论压力,使开枪成为警察身上的一个负担③2014年昆明暴恐事件,面对歹徒持刀疯狂砍杀无辜旅客造成多人死伤的紧急情况下,特警队员还两度鸣枪示警,直到歹徒离其1米时才开枪射击,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心有余悸地担心自己开枪是否合法。。
3 我国警察开枪面临风险的成因分析
3.1 法律规范不完善
我国警察开枪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鸣枪警告、开枪标准及开枪结果控制3个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
3.1.1 鸣枪警告方式存在缺陷
《条例》第9条确定了警察开枪以事前警告为前提,以直接开枪为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18条、《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第6条也都规定除遇到特别紧迫的情况外,警察开枪都要先行警告。2015年公安部颁布的《规范》第11条、第15条、第16条突破性地对警察用枪流程做出了规定,即按照持枪戒备——出枪警示——口头警告——鸣枪警告——开枪射击顺序由轻到重使用,并确定若干例外④《规范》第14条规定:“来不及口头警告的,可以直接鸣枪警告。”《规范》第15条规定:“经口头警告或者鸣枪警告无效的,可以开枪射击。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开枪射击。”。但实践中,鸣枪警告方式存在的弊端正日益暴露。一是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无辜群众伤亡⑤2010年广西凤山县民警为控制酗酒滋事人员而向天鸣枪示警,意外致死一名在居民楼围观的男子;2015年佛山市禅城区警察为控制一起学生聚众斗殴案件鸣枪警告时,流弹致死一名学生。;二是使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对鸣枪警告和开枪射击犹豫不决,容易错失开枪的最佳时机,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脱;三是当只有开枪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两人在开枪现场的情况下,事后很难界定清楚鸣枪警告和开枪射击的先后顺序。
3.1.2 开枪标准的操作性有待加强
《条例》第9条列举了警察可以开枪的15种法定情形;《条例》第10条列举了警察不得使用武器的两种情形;《条例》第11条列举了警察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的两种情形。但这种列举式的立法形式并不能涵盖警察开枪现场出现的新情形。《条例》第9条使用“判明”、《规范》第11条使用“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和危险程度”等表述,虽然赋予警察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使用枪支的自主裁量权,但因缺少相关解释和指导性案例,致使不同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
3.1.3 最小损害原则的不合理使用
《条例》第4条规定警察使用枪支理应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包括犯罪嫌疑人)伤亡为原则,这体现了比例原则中的最小损害原则。但如果以这一原则对警察合法开枪行为造成的伤害程度吹毛求疵,不免有些矫枉过正。警察开枪时的情形多是紧急、复杂的,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警察去瞄准,即使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警察也无法做到“指哪打哪”。
3.2 缺乏科学有效的开枪后心理干预机制
警察个人心理调节能力因人而异,开枪后大多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如果缺乏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很有可能形成心理应激障碍。
3.2.1 警察开枪心理素质训练有待加强
现阶段,无论是公安院校对学员开设的射击课程,还是公安系统对在职民警的射击训练考核,普遍侧重于射击姿势、精准度等技术方面的训练,忽视对警察开枪心理素质的训练,比如情绪调节能力、心理应变能力等。警察开枪后,心理调节知识与技能的缺乏,使警察在开枪过程中出现的情绪反常、心理应激障碍无法及时有效调节。
3.2.2 心理干预工作“政工化”色彩浓厚
无论是在高强度的日常警务执法工作中,还是在开枪后,警察都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但公安系统内部尚未建立成熟的警察心理干预机构。目前,多是采用政工兼顾心理工作,大部分警察开枪后主要是接受领导、政工人员谈话(谈心)。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必须通过相应级别的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但政工人员中符合条件并能够独立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少之又少。同时,政工人员深受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影响,不自觉地会将其照搬到心理干预工作中,其弊端是可想而知的。
3.2.3 外聘专业心理工作者开展心理干预效果不佳
公安机关因其专业心理干预人员的缺乏,在个别影响较大的警察开枪事件中会从外界的研究机构、高校或者医院中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工作人员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目前,国内对警察心理问题尤其是警察开枪后心理干预开展的研究甚少。此外,警察开枪的技术性强,外聘专业人员缺乏对公安工作的切身体会,从而导致外聘专业人员开展心理干预很难被警察认同,其实际效果往往不佳。
3.3 开枪争议解决机制不健全
3.3.1 警察开枪后的调查制度有待完善
《条例》第12条、第13条,《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第9条、第24条基本明确了警察开枪后要及时报告,造成人员伤亡要通知检察院。2015年《规范》的出台对调查处理的报告程序(第18条)、处置程序(第20条)、调查报告(第22条)等进行了细化。但现行法律规范仍存在值得探讨之处:《规范》第19条明确由警务督察部门牵头,纪委监察、法制部门联合开展调查处理,也就是说警察开枪的调查处理程序基本是在公安机关内部独立完成的,只有在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才需要通知检察院。既是执法者,又充当“裁判者”,调查结果的可信度不免会受到质疑。《规范》第23条提到“检察院介入调查”,但哪些案件检察院可以介入及介入后的调查程序均未明确。调查程序各个步骤的时间节点,调查结论是否应当向公众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都属空白。《规范》第20条只规定警察不服调查结论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却未赋予相对方提出救济的权利。
3.3.2 以既成结果评价不确定的现场情况
现阶段存在的以既成结果评价警察开枪现场不确定状况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警察当时开枪符合法定条件,事后证明其当时开枪行为是必要的、适当的,那么开枪行为则会被接受。相反,如果警察当时开枪符合法定条件,事后证明其开枪行为并非必要,则开枪行为就会被否定。例如,犯罪嫌疑人持枪拘捕,警察向其开枪,事后查明犯罪嫌疑人持有的是仿真玩具枪,那么,警察开枪行为就会遭受非议。警察的职责要求其须根据现场紧急状况做出开枪决定,但是群众与媒体倾向于带着结果去看待警察开枪行为,而不能用“在当时的情境之中是合理的”标准去评价警察开枪行为,这就造成警察当时的开枪行为往往经不住事后的“倒推”。
3.3.3 公共关系危机应对机制不健全
目前,公安机关多是抽调专门力量、采取应急措施应对警察开枪所引发的公共关系危机。《规范》第20条提到,警察开枪造成人员伤亡的,事发地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做好舆情引导工作,但并未规定舆情引导的具体流程。由于缺少常态长效的工作机制,警察开枪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往往需要向上级请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应对策略,这就可能使公安机关错过公开事件信息的最佳时机;媒体则会发布其从各种非官方渠道获取的片面的、甚至是失实的事件信息,给群众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多是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通报情况信息,或单方面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上发布情况通报,这种简单的应对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根据著名的塔西陀效应,在警察公信力不断弱化、警察形象亟待重塑的今天,无论警察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说假话。
4 我国警察开枪风险应对策略
相较于危害、灾难等这类确定将会发生的不利后果,风险只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是否会出现不利后果、发生时间、危害程度等一系列因素都是不确定的。正是因为警察开枪面临风险存在不确定性,才为公安机关采取相应措施规避风险提供了机会。
4.1 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4.1.1 完善开枪标准
《条例》仅仅列举了15种警察可以开枪的情形,实践中警察需要判明存在上述情形后方能选择开枪。在紧急、复杂的犯罪现场,要求警察记住所有情形并做到一一对应存在一定难度。可以借鉴美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在列举若干种警察可以开枪的情形前,明确警察可以开枪的抽象标准(原则)。香港在其《警察通例》第29章第3条①警务人员可在下列情况下使用枪支:一是为了保护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以免生命受到危害或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二是有理由相信某人犯严重暴力罪行应当加以拘捕或犯严重暴力犯罪的疑犯企图拒捕;三是平息骚动或暴乱。但警务人员必须是不能以较温和的武力来达到目的时,才能在上述情况下使用枪支。确立警察可以开枪的抽象标准;美国警察在使用枪支时拥有较大的裁量权,但也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合理确信原则。美国多数州都在联邦法的指导下确立了这一原则,如新泽西州规定警察开枪是“一种客观估计,它是基于具有理性并经过相似训练后的警察,在同一情况下能够作出的一般反应”[10];二是生命安全原则。如美国司法部规定:执法人员只能使用所需要最低限度的力量,以降低事故危害、实施逮捕、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伤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明确我国警察开枪应遵循的3个原则:一是正在面临可能造成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死亡或者重伤的现实危险;二是除了开枪以外没有其他方法予以制止;三是警察有合理依据确信符合开枪标准。
4.1.2 对鸣枪警告方式作出改进
除特殊情况,我国警察开枪射击前都要履行鸣枪警告程序。鉴于鸣枪警告存在的弊端,建议借鉴德国经验对我国鸣枪警告作出改进。虽然德国警察开枪程序中也规定了鸣枪警告程序,但鸣枪警告并非开枪射击的前置程序②德国黑森州内政部所颁布的《〈黑森州公共安全与秩序法〉执行细则》明确规定:“只有在满足开枪射击条件时,才能鸣枪示警。”。只要满足开枪的条件,警察就可以鸣枪警告或者开枪射击;如果没有满足开枪条件,警察也不可以鸣枪警告。这样的改进既有利于减少误伤又便于开枪后开展调查;既有利于警察把握开枪最佳时机又可以有效震慑犯罪嫌疑人。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细化警察开枪前口头警告的流程和内容。口头警告要做到清晰、响亮,比如“警察!放下武器!不然开枪了!”,并辅以掏枪、举枪、瞄准等动作,以达到有效震慑作用。
4.1.3 合理规制警察开枪的自由裁量权。
《条例》第9条使用“判明”、《规范》第11条使用“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和危险程度”等表述,表明警察可以根据当时所处的环境裁量开枪。《条例》第10条规定了警察禁止开枪的两种情形,《规范》第16条在《条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警察禁止开枪的情形。根据现实情况,明确开枪原则、增加禁止开枪情形,可以有效压缩警察开枪的自由裁量空间。合理规制警察开枪的自由裁量权而非过分规制,实质上是对警察开枪自由裁量权的尊重,是为了让警察更好地行使这一权力。同时,建议学习最高检、最高法采用指导案例为检察官、法官办案提供参考的做法,编写警察开枪指导性案例,以弥补上述法律规范表述抽象难懂的缺点,为民警用枪提供直观形象的案例参考。同时,通过指导性案例的不断丰富,让警察清楚地知道在哪些复杂情况下可以开枪,在哪些情况下开枪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4.2 健全警察开枪后的心理干预机制
4.2.1 打造专业化心理干预队伍
警察心理干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能把心理干预工作等同于公安政治工作来做。建议公安机关通过引入心理学专家学者、招录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外聘心理学教授、返聘公安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成立专门的警察心理干预机构,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心理干预队伍。及时对开枪民警进行心理干预,跟踪开枪民警的心理压力舒缓状况,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将开枪对警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建议借鉴香港成功经验,广泛发展心理健康志愿者,通过聚会谈心、游玩等方式为民警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倾诉、沟通环境。开枪民警所在社区、家属所在单位应该定期上门慰问、安抚民警和家属情绪,关注民警及其家属的心理动态,防止河北肃宁特大枪击案①2015年6月8日,肃宁县发生特大枪击案,案件造成4死5伤,包括肃宁县公安局政委薛永清在内的两名干警牺牲。6月10日4时许,薛永清的妻子因过度悲痛从酒店跳楼身亡。的悲剧发生。
4.2.2 采用专业化的开枪后心理干预方法
建议采用“六步干预法”[11]在警察开枪后48小时之内对其进行强制心理干预:①确定心理风险。这个阶段主要以倾听为主,以保密性、信赖性、整体性、非指导性为原则,了解掌握民警在开枪后可能存在哪些心理风险;②保证干预对象安全。使被干预对象对自己和他人的生理、心理危险降到最低,排除自杀等倾向,营造令其安心的干预环境;③积极给与干预对象支持。强调与干预对象的交流沟通,尽可能以积极方式接纳民警,满足其暂时需求,让开枪民警相信组织以及心理工作人员;④提出应对方式。端正干预对象对自己开枪的看法,减轻应激和焦虑水平;⑤制定心理干预计划。对可能出现的长期心理应激障碍制定干预计划,有效改善警察的情绪失衡状态;⑥争取得到干预对象承诺。经过4~6周的干预期,民警的情绪症状一般会得以缓解,要得到其诚实直接的承诺,并及时中断心理干预,避免产生依赖性。
4.2.3 增加射击训练中心理素质的训练
在射击训练中增加心理素质训练内容,让学员学会应用心理学知识进行心理自控。通过心理素质训练,首先让受训警察明白开枪后出现的应激反应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正常反应,不要过于紧张、焦躁,只要接受合理的心理干预就能恢复正常。其次,让受训警察学会心理自控的技巧。比如,开枪时使用心理暗示方法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沉着冷静”、“我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歹徒,如果不及时开枪制止歹徒,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如果开枪后自己不能平静下来,要学会通过交流倾诉、做运动、听音乐等寻求心理干预的方式进行自我调适,缓解紧张情绪。
4.3 完善警察开枪后的调查程序
4.3.1 检察院全程参与调查
《看守所条例》第18条规定,开枪射击后,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主管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为了体现警察开枪调查程序的正当性,建议通过修改法律规范,将检察机关纳入调查主体,明确应由公安与检察机关组成包括枪弹、法律方面专业人员在内的联合调查组。警察开枪后应当第一时间向所属公安机关或者当地公安机关及同级检察院报告。联合调查组对警察开枪事件开展调查,认定事件性质,联合向开枪警察及其所属配枪部门,伤亡人员及其家属、所属单位宣布调查结论,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在调查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事件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听证程序展开辩论。如果不服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进行申诉。
4.3.2 设置科学的警察开枪评价标准
警察开枪现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事后结果评价警察开枪行为,不仅无法对警察开枪作出客观的评价,还不利于警察用枪法律规范的有效执行,不能引导警察合法、合理开枪。应该根据警察开枪当时的现场状况及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评价警察的开枪行为,不能以既成结果评价不确定的现场状况。只要事后查明警察是根据当时的现场状况及法律程序作出了理性的开枪决定,哪怕是出现了不可控的严重后果,也不能否定警察开枪的合法性。
4.3.3 明确具体调查项目
按照从案件发生到公布调查结果顺序,详细列举出需要调查的事项。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强制力报告表》[12],将调查事项规定为以下内容:①案件基本情况。包括案件发生的事件、地点、在场人员等;②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包括基本个人信息、涉嫌何种犯罪、是否持有武器以及受伤情况等;③开枪民警基本情况,包括基本信息、受伤情况等;④犯罪嫌疑人反抗程度。包括反抗警察的控制、用身体威胁或打击警察、使用钝器、刀具、车辆或枪支等危险程度不同的武器威胁或打击警察等;⑤警察枪支使用情况,包括使用枪支的类型、开枪程序及依据、造成人员伤亡情况等。
4.4 做好公共关系危机应对工作
一方面,成立警察公共关系应对机构。建议在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成立专门应对公共关系的机构如“警察公共关系科”或“新闻发言人”,统筹应对警察开枪等重大事件,统一口径对外公开事件信息。平时注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新兴媒体,定时发布包括警察用枪信息在内的实用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警务信息,让群众了解警察开枪的必要性及哪些情况下开枪是合法的,以便出现警察开枪事件时能争取到群众更多的支持与理解。另一方面,规范开枪后公共关系应对流程。公安机关应出台警察开枪事件的危机应对章程,建议分为4个阶段:①调查初期,成立公安内部调查组,及时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并根据当事民警心理干预情况掌握案件细节;②调查中期,公安机关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如实公布事件初步调查情况,并公布调查组成人员和时间节点;③公布调查结论期是公共关系危机应对的关键时期,要注意最大程度及时公布最新调查结果,并争取媒体和其他权威机构的支持,控制不利舆论;④事件结束后,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5 结论
我国警察开枪面临的个人与群体的心理风险、责任风险、公共关系危机是现实存在的,通过采取完善法律规范、健全心理干预机制、完善调查程序等措施,可以有效应对警察开枪所面临的风险。风险的有效应对不仅可以为警察的依法开枪行为提供保障,使其敢于及时开枪,并且还能合理规制警察开枪行为,有效提高警察开枪的合法、合规性。同时,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执法环境的变化性,要求公安机关只有做到与时俱进,及时识别警察开枪所面临新风险,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1]夏和国.吉格斯风险社会理论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4:47-50.
[2]Dirk Matten,The impact of the risk society thesis 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J].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004(4):380-383.
[3]贝克,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0-122.
[4]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05(5):208-246.
[5]许新源.警务风险的概念、特征与结构[J].公安学刊,2007(6):45-49.
[6]杨艳杰.危机事件心理干预策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47-51.
[7]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M].4th ed.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4:424-429.
[8]顾杰善.群体心理学导论—对群体心理现象的实证分析与理论探索[J].社会学研究,1992(3):29-34.
[9]陈娴.警察公共关系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24-126.
[10]Use of Force:Attorney General's Use of Force Policy [EB/ OL].(2010-09-10)[2017-05-24].http://www.state.nj.us/lps/ useofforce2001.
[11]皮华英.警察心理健康及其维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338-350.
[12]徐丹彤.美国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概要[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93-96.
(责任编辑:焦 娇)
D035.34
A
2095-7939(2017)04-0058-07
10.14060/j.issn.2095-7939.2017.04.010
2017-03-14
高长永(1988-),男,江苏邳州人,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指挥处民警,主要从事治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