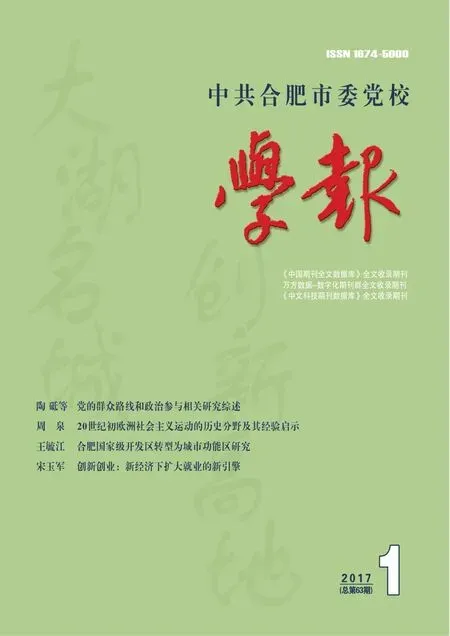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述评
2017-01-24王红辉
王红辉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述评
王红辉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逐渐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性战略布局,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围绕“四个全面”,学界从历史渊源、时代价值、内在逻辑关系、同其他重大命题的逻辑关系、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进程。但是,目前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视野仍需拓展,如实现路径研究比较薄弱等问题,亟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充实“四个全面”的理论内涵,助推“四个全面”的实现。
十八大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研究述评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提出了“四个全面”。次年2月,党中央将“四个全面”定位成战略布局,由此,“四个全面”便成为学术界的高频词汇和研究热点,出产了一大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经中国知网检索,以“四个全面”为关键词的期刊论文近四百篇,学术专著也公开出版十余本,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脉络、重大意义、内在逻辑关系、涉及的重大命题关系、多角度解读、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归纳、梳理和论述,旨在理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历史渊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脉络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脉络研究,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分析角度:一是整体分析,全面系统梳理“四个全面”的发展过程;二是具体分析,将“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分析和整理。学者们虽然分析角度不同,但基本达成共识,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历史中来,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一)整体分析:首次提出-理论成熟-实践指南
易善武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四个“全面”到“四个全面”阶段。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旗帜,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直到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四个全面”。二是“四个全面”的理论成熟阶段,提出之后,逐渐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布局。三是“四个全面”成为实践指南阶段,2015年全国“两会”围绕“四个全面”展开热烈讨论,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建言献策,推动其成为实践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吹响胜利号角[1]。
(二)具体分析:从四个“全面”到“四个全面”
秦宣、王钰鑫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2]。学者们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全面梳理“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的发展脉络,揭示其不是凭空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概括总结为“四个全面”,并将其上升到战略布局层面,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提出,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3]。
可见,学界仍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来探究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脉络,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前的中国革命史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历史素材。,因此,学界需要拓展理论视野,进行纵深研究,更全面系统地梳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脉络。
二、时代价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充分阐释和论证,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推动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程。
(一)理论意义:新飞跃、新认识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飞跃。王国敏、陈加飞从目标、动力、保障、主体等维度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揭示其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内在共通性,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束锦则从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地位着手,指出其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4]。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石云霞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的飞跃,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5]。徐艳玲、陈明琨则进一步强调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化认识与全新概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执政目标的新概括,全面深化改革是执政路径的新拓展,全面依法治国是执政方式的新改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提升执政能力的新要求[6]。
(二)实践意义:新境界、新方略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张乾元、李琨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看,指出“四个全面”深刻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总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布局,从社会合力、时代内涵、方法论特色三个方面开辟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7]。邸乘光等学者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角度切入,全面系统总结二者关系,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要求,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过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方略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护航。秦宣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重要抓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纲领和新方略[9]。张建则从实现民族复兴角度来看,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作用,从关键、动力、保障、核心深入阐释了“四个全面”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护航作用[10]。
(三)世界意义:新契机、新思路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提供新契机。陈金龙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道路的集中表达和理性升华,其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实施助力国家形象的建构,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提供新机遇[11]。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其他国家发展转型提供新思路。王仕国、杨海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但具有中国整体发展转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为和谐世界的建构提供了思维方法的启迪[12]。周明海等学者则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定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为其带有普遍性的价值,促进构建各国共赢格局,为其他国家的转型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借鉴[13]。
可见,学界全方位、多层次剖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学界应注意多增加学理分析来阐述其意义,运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结合当今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来展开逻辑论证,以增强其理论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内外剖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
学界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一方面纵向研究,整体解读和跨学科探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关系,另一方面横向研究,揭示“四个全面”同“三个自信”、“五位一体”等重大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纵向维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关系
1.整体解读“四个全面”。“发展目标·改革动力·法治保障·组织保证”四维度:井琪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重大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支撑,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组织保证,四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14]。
2.跨学科探析“四个全面”。其一,政治意蕴角度。陈朋亲等学者认为,政治理想层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勾画了实现中国梦的新蓝图;政治发展层面,全面深化改革助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政治价值层面,全面依法治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治生态层面,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良好的执政氛围和环境;国际政治层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15]。其二,哲学意蕴角度。刘文华等学者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联系观来看,“四个全面”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来看,“四个全面”是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看,“四个全面”将实践主体、客体和载体有机结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四个全面”作为社会意识,来自于中国当代的社会存在,又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16]。陈浩、鞠连和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凝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系统观、过程观;双传学、毛俊则从唯物史观角度,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历史决定论与选择论、群众史观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四大理论基石[17]。
(二)横向维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其他重大命题的逻辑关系
1.“四个全面”与“三个自信”。唐贵伍、肖宝佳认为,“四个全面”是“三个自信”的战略抓手和实践保障,“三个自信”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方向指引。伊文婷进一步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应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足够自信的基础上,同时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也是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过程[18]。
2.“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周明海、毕照卿等学者从二者共性着手,指出二者在产生背景、价值旨归、目标愿景、改革理性、思维方式、治国理政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涵义功能、生成路径、布局本身、现代化指向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区别[19]。
可见,学界从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探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应注重拓展研究视野,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探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具有较大的研究纵深空间。
四、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
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学界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分别展开论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遵循正确的实践原则,是实现“四个全面”的理论导向;全局定位党群良性互动的目标和“三改一拆”的区域性工作试点,是实现“四个全面”的实践保证,这些学术成果丰硕而厚重,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进程。
(一)理论层面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丛松日等学者指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处理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20]。
2.遵循正确实践原则。龚培河等学者认为,推进“四个全面”必须遵循五个实践原则:以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抓手原则;矛盾阻力·压力·动力转化原则;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原则;协调性与全面性辩证统一原则;党员身先示范原则,以此助力“四个全面”的实现[21]。
(二)实践层面
1.全局定位:党群良性互动。黎育生、汤志华认为,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继承群众史观,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凝聚人民群众的合力才能取得成功[22]。同时丛松日等学者也指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党在推进“四个全面”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力量良性互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23]。
2.区域策略:“三改一拆”。陈晓熊、王根土等学者在《关于浦江“四个全面”试点工作的几点建议》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四个全面”同浙江“三改一拆”工作的契合之处,并指出推进“四个全面”在浙江实践的路径建议,在推动浙江“三改一拆”工作的过程中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4]。
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问题的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探讨,相对缺乏应用性强的对策性研究,且仍停留在区域性对策探讨方面,从宏观的理论视野探究“四个全面”同区域性实践工作的关系具有较大的纵深研究空间。
五、学术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自2015年党中央将“四个全面”确立为战略布局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回顾、梳理和评价,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脉络、重大意义、逻辑关系、实现路径等方面,其研究视角多样,哲学、政治学、系统学等多角度展开研究。其研究领域广阔,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等多个领域。然而,目前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研究比较薄弱,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全国各个地方的实践效果,从宏观视野探究“四个全面”同区域性实践工作的关系等方面,亟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充实“四个全面”的理论内涵,助推“四个全面”的实现。
[1]易善武.“四个全面”的逻辑脉络与实践特性探析[J].学习论坛,2016(4).
[2][9]秦宣.“四个全面”:形成发展、科学内涵和战略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6).
[3]王钰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的历史脉络述论[J].理论导刊,2015(11).
[4]王国敏,陈加飞.“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J].理论学刊,2015(8).
[5]石云霞.论“四个全面”的重大理论贡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19).
[6]徐艳玲,陈明琨.“四个全面”开拓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新境界[J].理论探讨,2015(4).
[7]张乾元,李琨.“四个全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8]邸乘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指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J].湖南社会科学,2015(5).
[10]张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J].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2).
[11]陈金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解读[J].学术研究,2015(12).
[12]王仕国,杨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四个全面”[J].求实,2015(12).
[13]周明海.比较视野中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3).
[14]井琪.“四个全面”: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
[15]陈朋亲,杨天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政治意蕴[J].学术探索,2016(2).
[16]刘文华,范志轩,朱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17]陈浩,鞠连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意蕴[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12).
[18]唐贵伍,肖宝佳.“四个全面”与“三个自信”的内在关系研究[J].人民论坛,2015(35).
[19]周明海,毕照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关系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6(2).
[20][23]丛松日.“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学术论坛,2015(4).
[21]龚培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J].求实,2016(1).
[22]黎育生,汤志华.群众观视角下“四个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J].广西社会科学, 2015(10).
[24]陈晓熊,王根土.关于浦江“四个全面”试点工作的几点建议[J].党政视野,2015(8-9).
责任编辑:汪晓梦
2016年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高职分会科研课题(立项编号:YB201603)。
2016-12-26
王红辉,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社会科学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