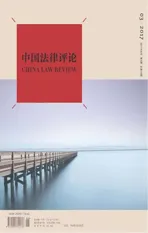循庸问恶:庸常规则、道德无涉与国际法*
2017-01-24刘洋
刘 洋
循庸问恶:庸常规则、道德无涉与国际法*
刘 洋**
我们在讨论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时会忽略一部分规则而集中于另一部分规则。我们会认为一部分法律规则与道德讨论没有关系,它们不能从道德上进行评价,因此是道德无涉的。本文以国际法为例,讨论了这种现象的缘起和影响。本文认为,法律规则的道德无涉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国际法学人团体在与大众的互动过程中通过知识手段将规则技术化,限制专业团体与大众的互动。建构的道德无涉遮蔽了相关规则的道德立场,影响了大众对法律规则的道德性乃至合法性的评价。
国际法 道德性 道德无涉 社会建构
目 次
一、庸常规则
二、道德无涉
三、社会建构
四、国际法
五、循庸问恶
一、庸常规则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在哈佛法学院1997年的霍姆斯讲座的主题是“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1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1, (1997-1998), p. 1637.这篇讲座的稿本经过扩充,后来成为专著出版。经过译介,在中文学界也广为人知。在这篇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波斯纳法官指出,虽然法律也对某些行为予以禁止或者惩罚,但这些行为是难以用道德评价来区分的(morally indifferent)。他举的例子包括(反垄断法中的)固定价格、(证券法中的)内幕交易、雇佣非法移民、开车不系安全带,等等。2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p. 1695.他认为,这些规定的背后可能有其原因,但这些原因和道德直觉或者道德理论没有多少关系。3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p. 1695.德沃金(Ronald M.Dworkin)在《论规则的模式》中有一个关于限速的交通规则的例子。4Ronald Dworkin, "The Model of Ru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35, (1967-1968), p. 25.哈特(H.L.A. Hart)也提到过车辆禁止进入公园的规则。5H.L.A.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71, (1958), p.607.不论在法律与道德的论题上持哪种立场,学者们似乎大都同意,在探讨法律与道德性问题时有些规则似乎没有多大评价的意义,与交通有关的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时,学者大多都把精力集中在与疑难案件有关的规则上。6例如 Ronald Dworkin, "Hard Case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88, No. 6 (1975), pp.1057-1109。比如德沃金提到的杀人继承案。7Riggs v. Palmer, 115 N.Y. 506, 22 N.E. 188 (1889). 相关讨论参见Ronald Dworkin, "The Model of Rules", p.23。毕竟霍姆斯(Oliver W. Holmes, Jr.)法官有言,“难案生恶法”(hard cases make bad law)。8原文为: “Great cases like hard cases make bad law. For great cases are called great, not by reason of their real importance in shaping the law of the future, but because of some accident of immediate overwhelming interest which appeals to the feelings and distorts the judgment. These immediate interests exercise a kind of hydraulic pressure which makes what previously was clear seem doubtful, and before which even well settled principles of law will bend”。Northern Securities Co. v. United States, 193 U.S. 197, 400-01 (1904)(Holmes, J., dissenting).在关于恶法的讨论中,如果实定法律规则与某些高级原则存在冲突,该法律规则就可能被视为恶法。9需要注意,由于不同法律体系的法律渊源存在区别,所以理论上恶法可能存在于各个渊源中。比如普通法系关于恶法的讨论很多是关于作为案例的具体个案的。另一个例子是宪法中的恶法。此外,广义来讲,虽然成文法国家的法律渊源不包括判例,但如果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违反了高级原则,这个案件一般也被视为恶法。本文的讨论主要指法律规则,在个别情况下也包括国际法中的判例。基于不同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高级原则是道德,也可以认为是其他原则,比如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或者是经济效用。10参见Frederick Schauer, "Do Cases Make Bad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73, (2006), p. 883。本文仅讨论其中的一种情况,即依据道德对法律规则进行评价的情形。如果规则不符合道德,就会被认为是恶法。不过,不是所有的规则都需要进行道德评价,就像波斯纳和德沃金举的例子一样,许多法律规则虽然规制着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重要。对这些被认为不涉及道德评价,或者在道德评价上没有意义的规则,笔者将其称为庸常规则。对于规则来说,被认为不涉及道德评价,或者在道德评价上没有意义的这种现象,称为道德无涉。11部分中文著作将这个概念表述为非道德性。参见李学尧: 《非道德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莫纪宏:《论人权的非道德性》,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但从字面意思来看,非道德性可能含有不道德,即道德否定评价的意思。道德无涉表达的是没有进行道德评价,不能进行道德评价的意思。它甚至和道德中立的状态也存在区别。道德中立是指经过道德评价之后,评价的结果是中立,而道德无涉是指没有进入道德评价。
庸常规则因为细琐所以显得无聊:在大砖头的法条汇编里面记满了高速公路限速是60英里/时还是70英里/时,每年的纳税申报是截至4月1日还是6月1日,等等。这些规则十分具体而技术化,一般观察者如果没有法律专业知识很难对它们的影响做出估计,也不知道怎么从道德上去评价这些规则。所以李普斯坦说道,不少名家认为道路交通规则涉及利益的衡量,而不涉及自由等根本问题。所以,政治哲学很少对交通规则这类东东进行严肃的讨论。12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33.但正如李普斯坦(Arthur Ripstein)指出,交通规则不仅并非与自由无关,而且恰恰是康德意义上自由的题中之义。13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p. 238.类似的,我们也不禁要问,庸常规则难道真的在道德讨论中不重要吗?我们依据什么标准来认定一个规则是道德无涉的?
本文的观点很简单:法律规则的道德无涉状态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在讨论恶法问题,讨论法律与道德之前,我们应该对前提性问题保持警醒:我们观察、讨论和研究的对象的边界是不是被局限了?如果这种边界和限制是人为的,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人为的边界是可以挑战的,那么挑战这一边界的意义是什么?文章的第二部分对本文讨论的对象——道德无涉进行了界定。第三部分简述了专业团体社会建构的原理。第四部分结合国际法的实例进一步讨论了法律规则道德无涉的状态以及成因。最后的结语部分简要讨论了庸常规则中可能的道德偏见,以及新兴学人应该如何面对庸常规则。
二、道德无涉
道德无涉是本文关注的现象。14现有的法学作品关注这个问题的较少。英文作品有 Beth Stephens, "The Amorality of Profi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2002), pp.45- 90。但是这个现象与若干概念存在纠缠。所以在展开讨论之前,有三个相关概念问题需要厘清。
其一,本文讨论的道德无涉是大众认知上的现象,不是哲学上的道德状态分类。在道德理论上,有人认为道德无涉是一个单独的道德状态,与道德、不道德、道德中立等状态是并列而独立的。某些事实是与道德评价不相关的,例如科学事实,这些事实在道德评价上没有意义。15Dale Dorsey, "Amorality",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2016, Volume 19, Issue 2, pp.329-342. 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任何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可以评价的。See Samuel Scheffler, Human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如果这一观点是成立的,那就意味着法律规则的道德状态是由其客观性质所决定的;某些规则与其他规则存在某些客观性质上的关键差别,所以这些规则是道德无涉的。不过,要搞清哲学上的道德无涉是否存在,可能需要一本《道德的概念》来讨论。16当然,德沃金在《刺猬正义》中认为法律是政治道德的一部分,就可能暗示着所有法律规则都有道德影响。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10. Waldron, Jeremy, Jurisprudence for Hedgehogs (July 5, 2013). NYU School of Law,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 13-4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290309, pp. 7-8; Mark Greenberg, "The Moral Impact Theory of Law", Yale Law Journal, Vol. 123, (2014), pp.1288-1342.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充满信心的结论。17Dale Dorsey, "Amorality", p.330.但本文这里讨论的不是哲学问题,是大家对规则能否被道德评价的认知状态:大家为什么会认为某些规则是道德无涉的,而不是大家的这种看法在哲学上有没有道理。可能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大家对法律规则在道德判断上的认知。可能有人经过哲学探究,坚信这些规则本质上就是道德无涉的;也可能是因为这些规则与自己熟悉的法律部门领域相去甚远,乍看之下大家没有弄清其中玄机;甚至可能是早饭没有吃好,或者是昨天没有洗澡。影响认知的因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哲学上的认识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因素。但即使是哲学上的判断,也可能会受到其他认知因素的影响。因此,哲学上的结论并不能代替这里对大众认知现象的探究。即使一位法哲学教授已经充分论证了道德无涉在哲学上是可能的,在他对面的一位路人对同样一条规则的判断结果却可能完全不同;或者结论相同,但理由却迥然相异。本体论上的未决并不妨碍我们追究为什么某些规则在认知上不被大众纳入道德评价的范围。
其二,道德无涉与法律的道德性讨论不同。道德无涉关注的是道德评价(是否可能);而法律的道德性是在道德评价的基础上关注合法性(legality)(是否受到道德评价的影响)。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律哲学的经典问题之一。哈特式的实证主义,德沃金的非实证主义,以及后来衍生出的包容性实证主义以及排他性实证主义,诸多学者在此问题上近年来进行了有趣的探讨。18包容性实证主义, 参见Jules Coleman, "Beyond the Separability Thesis: Moral Semantics and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7), pp. 581–608;排他性实证主义,参见Joseph Raz,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2nd ed., Clarendon Press, 1980; 非实证主义,除了德沃金以外,另外参见Greenberg, "The Moral Impact Theory of Law"。其中,实证主义主张法律与道德是分离的,道德不是法律的渊源之一。实证法学的立场乍看之下与道德无涉有些相似,都是讲法律与道德的无关,也确有作品把这种实证法学立场总结为“无涉道德”,19邹利琴:《无涉道德的宪法——重读戴西的宪法理论》,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笔者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实证法学立场与本文中的道德无涉有部分表面的相似性。这里不是要对“道德无涉”的中文用法进行权威判断,也没有指责该文误用概念的意思。相反,从正文来看该文作者用意是清晰的,是指宪法在合法性的问题上是无涉道德的,即道德不是宪法的一部分 。但其实两者相去甚远。不论是实证主义还是非实证主义法学,他们都默认某些法律规则有道德影响,可以被道德评价。他们的分歧在于这种道德评价对法律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实证主义认为,即使一项规则的道德评价与法律本身没有关系,即使一项法律被认为是恶法,这也不影响该规则的法律效力。虽然实证主义者认为道德与法律效力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公众的道德讨论。这里的规则不是不能被道德评价,恰恰相反,这里的规则都是可以被道德评价的。20非实证法学派也同意法律规则是可以被道德评价的,但他们认为道德评价的结果对法律本身有影响。因为道德是法律的一部分,如果一项规则被认为是恶的,那么这个道德判断则有可能影响规则的法律效力,有可能影响规则的合法性。因此,道德性争论关注的是可以被道德评价的规则。只不过,法学家们关于道德性的讨论只是集中于某一部分规则,而对庸常规则却显得缺乏热情和兴趣。21德沃金在他的遗作《国际法新哲学》一文中,回忆当年在牛津求学时,国际法课上讲授的海洋法相关内容“枯燥乏味”(tedious)。Ronald Dworkin, "A New Philosophy for International Law",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41, (2013) p.2.他们虽未明言,但这种处理和观察到的态度似乎暗示庸常规则与道德性讨论没有多大关系,某些规则可能是道德中立的,甚至是道德无涉的。22道德中立和道德无涉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道德中立是指在道德上既不被鼓励,也未被允许,但也不被禁止。道德无涉则指向某种超越这三种状态的情况,即某规则在道德上可能不能够被评价。此处感谢陈庆的评论。详见Dale Dorsey, “Amorality”, p.330。
而道德无涉的出发点与上述争论完全不同。道德无涉关注的是在道德评价上没有意义的规则。所以本文的道德无涉问题与关于道德性的经典争论问题关注的是不同规则。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对道德无涉的关注暗含了对道德性争论的外部反思:我们在讨论道德性、讨论恶法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部分规则上,而忽视了另外一些规则,这种区分是否合理,是否带有偏见。法律的道德性讨论是研究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法律的道德无涉关注的是为何将道德讨论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以及在这个区域的知识高墙外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其三,道德无涉与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为了利于讨论,我们可以暂时简单地把对规则的道德评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判断某个规则在道德评价上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可以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第二个阶段是确认可以进行道德评价之后,适用某些标准来进行判断。23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所进行的简单划分。实际上道德评价的过程可能只有一步。因为第二阶段的道德规范与道德理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第一步的判断。比如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火星人吃土星人。在一个以人类个体为中心的道德理论中,没有关于别的星球物种的行为或事实的规范。又假设类比在道德判断中不适用。那么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可能也会认为这个事实在道德判断上没有意义。这样,第二步中的道德理论和道德标准也会影响第一步中关于道德无涉的判断。如果对我们的道德理论进行发展,将外星人的行为纳入新的道德规范,那么火星人吃土星人的行为就不再是道德无涉的,而是在道德判断上有意义的。那么道德无涉与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对应的是不同的阶段。道德无涉的判断是第一个阶段,道德规范是第二个阶段中进行评价的标准。如果从认知上(而不是哲学上)来理解道德无涉的现象,那么道德无涉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引导人们关于对哪些规则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知识。如果将道德规则比喻成一本评价手册,道德评价的过程就是按照手册的内容对规则进行评估。而道德无涉和手册本身的内容关联不大, 讲的是使用手册评价规则之前的一步。它更像是关于在哪里适用手册的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本身并不对具体的法律规则进行道德评价。它只是在这幅图上标明,哪些规则可以依照手册来进行道德评价,而哪些法律规则被视为与手册不相关,不需要适用手册进行评价。依据地图的知识,如果规则被视为细碎繁琐、道德无涉,我们就不会对它们进行道德评价。循着第一步中的这幅地图,大众进而在第二步依照手册对法律规则进行道德评价的实践:哪些是恶法,哪些是善法,哪些是道德中立的法律。他们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意识不到,这幅地图上的某些区域被屏蔽了。虽然在那些区域里可能有法律规则,但是依照这幅地图的提示,他们不需要去进入屏蔽领域进行道德评价实践。本文认为这一幅地图是由社会建构的。现在看起来,人们不难接受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社会构建的。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社会共识,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建构出不同的道德规范。即使道德客观论者不认同这一点,也对这种说法不陌生。除了极少数的观点(如认为道德与法律皆出自神意),一般大众都承认道德的内容不是从自然世界中来的,而是在社会世界中由社会成员所建构的。24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6-47.但本文要讨论的不是道德规则的内容,而是我们对于法律规则是否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认知,是指引大众关于对哪些法律规则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如何被构建的?
对道德无涉问题的研究,与哲学研究不完全一致,与法律的道德性讨论的旨趣大相径庭,也更加不同于具体道德规范形成过程的探究。法律的道德无涉是一种大众的认知,这种群体的认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品,是在国际法专家、知识分子以及大众的互动中形成的。对此过程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际法中的道德话语背后所包含的偏见与变革机会。
三、社会建构25本部分是对社会建构理论的一个非常初步的概括。如果专业读者发现此处有什么创新,那很可能是因为笔者对文献的理解存在偏差,欢迎批评指正。
有学者认为,我们对某些事物进行习以为常的分类,然后在各自的分类中适用不同的知识和分析。比如,哪些问题属于国际法,哪些属于国内法;哪些属于经济问题,哪些属于法律问题,等等。这些区分是基于某种背景知识而形成的,而这种背景知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专家群体建构的。26David Kennedy, A World of Struggle: How Power, Law, and Expertise Shap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08-167.借用此种分析,我们也可以这么看待关于道德评价的知识。大众对法律规则进行道德评价,也会首先依据某种背景知识进行分类:这些是属于在道德评价上没有意义的,是道德无涉的;那些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那么,这种背景知识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27
社会建构理论的核心在于挑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区分。强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人们所认为的自然存在的现实并非当然如此。这些现实其实依赖于我们的社会性中的偶然性。最为典型的说法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去做,这些东西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以这种形式存在。28Paul A. Boghossian, "What is Social Constructi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February 2001., available at http:// philosophy.fas.nyu.edu/docs/IO/1153/socialconstruction.pdf.社会建构的矛头主要指向那些被认为是客观的现实,29Paul A. Boghossian, "What is Social Construction?".[英]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如科学事实。在国际政治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无政府的国际结构。30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建构主义学者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屈从于这些所谓客观事实的前提,而应该看到,通过我们的努力, 这些一般被认为是基本事实的存在其实本来可以呈现为另外一种样态。31Roberto Unger, False Necessity: Anti-Necessitarian Social Theory in the Service of Radical Democracy, Revised Edition, Verso, 2004, p.2.由此可见,这种建构论带有激进的色彩。被国际法学界和政治学界更为熟悉的是另一种更缓和的建构主义。这派学者认为社会建构的主要对象是依赖于人类主观能动的认知,比如利益。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可以被建构的。
27社会建构理论受到了一些质疑。比如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它的假设是难以被验证的,因为持论者几乎可以主张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中文的简要介绍可以参见张舜翔:《社会建构论之后:一个过量的方法论及其超越》, 载http://www. srcs.nctu.edu.tw/cssc/essays/18-2.pdf;英文作品如 Ian Hacking,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Susan Marks, "False contingency", Current Legal Problems, Vol. 62 (1), (2009), pp. 1-21; Samuel Moy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9, pp. 2164-2189, at 2172。国家在认识自己的利益时,有可能基于规范与身份来认识哪些属于国家利益,而并非完全出于理性计算。因此,理性行为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为什么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仍然作出这样的选择。32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p.xiv.以中国的军控为例,江忆恩认为,如果纯粹计算中国军事实力利益,中国决策者选择的军控政策对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不利的,他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国防以及外交政治精英被社会化,影响了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因而接受了新的规范和观念。用社会建构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另外参见 Ian Hurd, After Anarchy: Legitimac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6。有国际法学者主张,通过国际条约的制度设计来影响国家对利益的认识,比如在人权条约中规定加入条约的标准。这样,加入该条约就会成为高人权水准的一个标志,而尚未加入的国家就会被标记为低人权水平。这种国际社会声誉的压力会通过某些国内机制转化为政治成本,从而促使国家政权加入条约接受人权法规范。33Ryan Goodman & Derek Jinks, Socializing States: Promo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p.89-109.
社会建构理论将自己研究的目标设定在解释那些被认为是不证自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某些理论家将这种现实称为日常生活,但其实它不仅包括了闲暇的生活,也包括了职业生活中的部分,这个叫法的重点在于日常,即习以为常。34[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20页。它是以特定的个体,围绕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而展开的。因此,凯尔森和哈特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奥地利宪法法院时期的凯尔森和在伯克利执教期间的凯尔森的日常生活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但不论是在职业领域在是在闲暇生活中,日常的部分都是指特定个体认为理所当然(因而也很少会反思)的现实。对于国际法学人或者广义的国际法律执业者(包括法官、律师以及外交部的法律官员)而言,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与国际法相关的部分现实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之一。比如,他们几乎都同意《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记载的是各国普遍认同的国际法的渊源,而浩瀚宇宙中的神秘力量不是国际法的渊源。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日常生活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社会中个体要对这个现实进行诠释。35[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17—18页。所以,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而言,他不仅是将日常生活(包括职业生活)中的存在视为独立于存在他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存在与他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产生意义,需要这位国际法学人对这些存在进行诠释。例如,一个木质的,有一个宽大平面以及四只脚的物体是一个存在。但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意义,就需要他对这个木质物体进行诠释:这是一张书桌,所以我可以它来看书写字,进行研究。再如,国际法中的禁止使用武力规则,也需要诠释。同时,这位个体也会认识到他还会面临竞争,还可能会有其他国际法律师、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大众对这个规则进行诠释。
所以,根据社会建构理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是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个体与他人在持续不断地沟通,对同一个存在的诠释进行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之间的目标和认识会出现不同,进而出现冲突和争论。比如禁止使用武力规则的法律性质和影响,在国家间,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不过在这个层面上的争论不一定会摧毁日常生活的共同认识。因为每个个体都认识到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必须在冲突的同时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背景知识。36[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21页。比如在上述的例子中,禁止使用武力规则是不是具有绝对效力的国际强行法?尽管各方会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但他们也会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基本一致:使用武力规则的讨论出发点是国家,而不是其他形态的政治或社会组织,更不是个人。各方也基本会同意:在国际法中的确存在一类特殊的规则,这类规则被称为国际强行法。这类规则具有绝对效力,在其他国际法规则与这类规则发生冲突时,强行法总是优先适用。37Article 53, 65, United Nations,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3 May 1969,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155, p. 331.虽然曾经有法国等国家反对这个概念,但现在强行法规则的确已经被普遍认可为国际法中的一类单独规则。在上述互动讨论中,就形成了共同基础。背景在这里被看成常识性知识,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不会被争论的各方所注意。38对于第一代的惯习或者背景的创造者来说, 这个背景的缘起是清晰的,构建的过程来说对他们是透明的,并无神秘可言。但是对于第三方,或者下一代人来说,这个背景或者惯习对他们来说就是客观的存在。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会在新的层面上再次重复。因为参与者的增加,原有的惯习或者背景由于新的互动而演化得更加复杂。就新生成的这一部分而言,参与者们可能可以意识到这是他们构建的成果。但对于既有的背景来说,那些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存在。[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50—70页。同时,这个背景不是自然存在的,它来自于参与争论和沟通的人。39当然,背景不一定仅仅在争议中才能形成。如果参与讨论的各方能够达成一致,那么这种认识也可能成为背景。特别是经过时间和空间的传递,比如在下一代学者那里,或者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学术团体那里,这种一致就会被视为当然的存在。背景的形成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适用策略的后果。但总体来说,背景知识总是在互动中形成的。40David Kennedy, A World of Struggle, pp. 110-111.即使使用策略,单独的个体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策略的目标。如果争论发生变化,这个背景可能也会受到挑战,不再理所当然,从而进入新的争议。随之而来的,会有新的背景形成。比如,假设在上述关于禁止使用武力规则的讨论中,有新的声音加入进来。这一派观点认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中,最主要的威胁之一不是来自国家的武力,而是非国家团体,如恐怖组织的武装攻击。所以传统的禁止使用武力规则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思维已经逐渐落伍,不能回应世界安全的主要问题。因此,在讨论通过国际法规则禁止武力、维持和平这个问题时,真正有意义的讨论是如何在现有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框架下对非国家团体施加法律义务,并有意义地执行。如果既有的讨论参与者面对这种挑战,也开始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那么原有的背景知识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新的背景也就形成了。这个新的讨论各方都认同的背景是,大家普遍认为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需要在结构上对非国家团体进行直接规制。当然,不是所有的新声音都会得到回应。另一种可能是既有的背景仍然维持,团体中的多数对这个挑战视而不见,没有形成新的互动。41就目前已经发表的作品来看,很难说假设中的这一派观点得到了足够的回应。相关的讨论参见Nicholas Tsagourias,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Law, Routledge, 2011, pp.83-96。所以背景的常识性知识是在主体间(intersubjective)建构而成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被社会中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另一方面这个理所当然的现实也来自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42[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17—18页。
背景也是知识分化的基础。如果两个个体正在建构一个背景,它会为双方的互动提供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两个个体的单独行动也因此获得了稳定性。所以背景的构建反过来使得个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化成为可能。43[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49页。在知识分化之后,随着知识的分配,社会被区隔成若干个子领域,如经济、道德、法律、宗教等领域。各个子领域继续分化、复杂化,形成专业知识。例如,一般认为国际法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大致是在真蒂利和格劳秀斯的著作出版时期为标志而形成的。从此时开始,国际法学说积累和发展开始离开宗教,成为独立的知识。44Alberico Gentili, "De Jure Belli Commentationes Tres",trans,John Rolfe,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mal Law, No.16, Vol.2, Clarendon Press,1933; 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Law and Peace, trans,A.C.Campbell, Richard Tuck,ed., Liberty Fund,2005.这种特殊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专门知识就将特殊群体与大众区别开来。专业知识必然与社会的共同存储知识相对。社会的共同存储知识,比如近亲不能结婚,是需要大众广泛接受的。45[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71页。而专业知识则是只有内行这个特殊群体才懂,外行人很难理解甚至获得这些知识。46同上。同时,在专业的内部,比如国际法学界,专家47在本文中,在讨论到国际法专业时,采用了若干相近的表述指向同一个团体,如国际法学人、国际法律师、国际法专家、国际法专业团体等,虽然在文义上有细微差别,但此处指代的都是受过国际法专业训练,以国际法的研究、教学、法律服务或者外交中的法律顾问等为职业的学者、律师以及外交人员,从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分享国际法专业知识的学生。们共享着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作为背景,为专业共同体提供稳定性,为行内人的争论提供基础。因此,专业知识形成了对内和对外两个有力的边界:对外来说,它是一道壁垒,防止外行人进入子领域;对内而言,专业知识起着凝聚作用。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互动会产生职业的伦理,防止行内人放弃本专业向外逃逸。由此可见,对国际法执业者这个群体而言,一方面它们要进行专业化,即将政治学者、道德哲学家以及国内法学者等局外人排除在外,而且要将局内人控制在共同体之内,维持国际法学人群体的身份。实现这个双重任务的手段之一就是将专业知识展现出来,使局外人认知这种区别程序的正当性,通过各种操控技巧来将职业边界正当化。
子领域从社会分化之后, 特殊群体不仅凭借专业知识在子领域内对大众进行排斥,还与其他特殊群体存在竞争。因为分化之后,各个领域内的知识形成了封闭,整个社会还需要将子领域进行整合。整合各个子领域的就是社会的共同存储知识。48[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71页。比如,职业物理学家与职业法律人出现之后,作为一般大众很可能不具有任何专业物理或者法律知识,但他会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告诉他哪些问题可能是物理学问题,哪些问题是法律问题。即使他不能自己解答这个问题,基于社会共同存储知识,他也知道应该去求助于物理学家还是律师。这样一来,特殊群体要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就需要将专业话语转化为社会的共同储备知识,转化为一般意义,使得局外人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认知这个群体的意义。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意义共同体,“它会将社会包含在内,为个体零散的社会经验与知识提供一个客观意义的整个背景”。49[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70页。这一点不难理解。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大众而言,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就像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会表明这一块领域是法律,那一块领域是伦理。这种关于专业领域范围和分布的一般认知会将局外人指向某一个群体,以寻求专业的帮助。这一个过程,就是专业群体获得社会认可,在一般意义上被认知的过程,也是获得权力的过程。比如一个人发烧,他会明白他需要医学专业人员的帮助。一般意义上的认知会将他的问题与特定的专业联系起来 ——这是医学问题,他应该去看医生,而不是去求签消灾。此时这种区分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些时候区分就模糊一些:比如一个人发烧,他是去看西医还是中医?这个时候,社会的共同储备知识会导向他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仅仅关乎一个发烧的人怎么治疗,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在社会的一般层面上中医与发烧的关联是否会被强化。中医与治疗疾病越相关,中医群体在社会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就越大。社会共同储备的指向和分配知识对于专业群体来说,就是一种权力。所以专业共同体就会在这一问题上投入大量资本和精力。职是之故,专业群体除了将知识专门化,设置专业门槛之外,另一方面又要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建构社会共同储备知识,将一般意义与本专业连接起来。换句话说,要找到存在感。
对于国际法专家来说,展示规则的道德相关性就是建构社会共同储备知识的一部分,是要寻求存在感,是建立国际法与社会关注议题的关联,是对权力的追逐。如果国际法学人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展示出国际法与道德议题的相关性(无论大众是否认为道德规范是国际法规则的一个部分),大众在面对道德议题的时候,就会把这些问题与国际法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我很关心,我也能听得懂,但也是与国际法有关,所以我要去听听国际法律师怎么说。50对于为什么要对实在法规则展开道德讨论,或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展开理论讨论,有一个更直白的解释。那就是通过道德讨论反思规则,从而改变规则。把这个观点简化表述,就是对国际法规则开放道德讨论是为了否定这些规则,而不是处于追求、巩固国际法群体权力。参见Benedict Kingsbury, "Legal Positivism as Norm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lance of Power and Lassa Oppenheim's 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2), (2002), pp. 401-436。
这些关联有的很容易建立,有的则没有那么直观。比如战争的正义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可以是道德问题,同时,受过一般教育的非法律专业大众也会大致了解,国际法中有一些规则是与战争相关的(不论他们认为这些国际法规则有没有用,是不是“法”,他们至少了解某些国际法规则在表面看来讨论了战争问题)。51参见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Basic Books, 1977。国际法关于战争的论著数不胜数。这里仅举例国际法学者对Michael Walzer著作的研讨与回应,参见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1) (2013)的主题研讨论文。除了这种明显的联系之外,有的联系并不那么直接,比如贫困问题。虽然有人会认为贫困问题也有道德面向,但大家很难把国际法与某个国家的国内贫困联系起来。相反,可能更多的人认为国际法与贫困问题没啥关系。但如果经由一定的解说,把国际投资协议中关于耕地投资的规定联系起来,说明这些规则可能产生跨国公司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土地,使得农业人口失地致贫,那么公众在贫困问题上就可能与国际法专业团体产生互动,建立联系。52从国内法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居多,例如 Olivier de Schutter, "The Green Rush: The Global Race for Farmland and the Rights of Land Users", Harva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2, Number 2, (2011), pp. 504-559。在国际公法上的一个初步思路,参见Alexandre Faure,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ntroversies Over Land Acquisition and Land Grabbing: A Socio-Legal Perspective" (April 18, 201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596019。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来探讨贫困问题,参见Thomas Pogge,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producing Massive Poverty", in Samatha Bensson and John Tasioulas eds.,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17-436; Robert Howse and Ruti Teitel, "Global Justice, Pover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Samatha Bensson and John Tasioulas eds.,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37-449。所以,建立联系的手段是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专业知识的壁垒,或者通过主动介入,将专业术语转化成大众可以理解的内容,将国际法规则的后果和影响呈现出来,从而引导大众展开讨论和和互动。
展示与道德评价的关联仅仅是争夺权力的一个方面,这不是无限制的。另一方面,国际法专家也要对这种关联的范围进行选择和限制,决定在哪些问题上和公众进行互动,在哪些问题上阻止外行人说三道四。53本文关注的是为什么国际法专家要进行道德无涉的区分建构。至于他们如何进行选择,在哪些规则上开放,哪些规则上不开放道德讨论,以及如何解释这种选择,这可能是更有趣的问题,但需要以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为基础。这种策略的形成,除了上述知识——权力方面的原因,还可能是为了维护道德立场。54周林刚指出这种现象可能不是国际法专家的策略的结果,而是法理学者的偏好所致。但本文认为法理学者的偏好也有知识构成上的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正是要解释为什么法理学者有这种偏好。因为国际法专业内部已经就某些规则达成了背景性的共识。由于这个背景是在职业群体内部的讨论中形成的,所以它不一定是中立的,很可能含有道德立场的偏向。如果把这些规则向大众开放讨论,那么原有背景就可能由于新的讨论的出现而被而挑战。在原有背景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立场就可能会被拿出来重新检讨。新背景不再是专业内部讨论的产物,而是专业团体与大众互动而形成的知识基础。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国际法专业团体需要限制大众与专业团体的讨论议题,使得某些国际法规则的影响难以被评价,甚至难以被感知。
四、国际法
今天,很多学人已经在抱怨国际法规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虽然在某些议题上的主要规则还有待形成,但国际法在很多领域已经充斥着各种技术性规则。在以国际法为专长的律师、政府官员以及学者看来,哈特式的追问“国际法究竟是不是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有多少回答的必要。55Jeremy Waldron, "International Law: 'A Relatively Small and Unimportant' Part of Jurisprudence?", in Reading HLA Hart's 'The Concept of Law', eds., Luís Duarte d'Almeida & James Edwards, Hart Publishing, 2013, pp. 209-223; Daryl J. Levinson and Jack Goldsmith, "Law for States: International Law, Constitutional Law", "Public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2, (2009), pp. 1791-1868.
国际贸易法(以及国际投资法)已经不用多说,这个领域在知识上如此密集,除非专精此业,一般的国际法学人也很难进入讨论。在传统的国际公法的领域,要弄清芜杂的条约、飘忽的习惯法以及繁多的判例,也需要国际法专家的支持。许多条约的起草都是由行话术语所武装,如果不借助国际法学人的专业支持,我们很难对约文含义有准确的了解。在习惯法领域,相关的问题更加突出。56某些机构对习惯法的研究会受到司法共同体的广泛关注,有些研究甚至会被广泛认可。比如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条约法,国家责任的研究,秘书处位于比利时的国际法研究院对于国家继承的研究,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法协会对许多习惯法规则对编纂和评论。国际红十字会对习惯人道主义法的编撰。哈佛大学对武装冲突法以及国家责任法草案的编撰,等等。由于还没有权威机构对习惯法进行全面的编纂,所以是否存在一条相关的习惯法规则就处于待证明的状态。而国际法上的习惯法一般被认为是由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个要素构成的,所以要说清楚有没有某条习惯法规则,习惯法规则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就需要掌握国家实践的证据。57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Judgement,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Reports 1969, pp.3-56.但对一般公众来说,即使这些信息是开放的,要搜集获取这些知识也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除此之外,具体的判例形成了密集的知识。要对一个条款进行解释,已经不能仅仅只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中规定的解释方法作为抽象指南来进行自由发挥。58United Nations,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3 May 1969,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155, p. 331.几乎所有的主要概念都需要放回到一系列案例背景中去考虑。所以要搞清楚国际法的规则是什么,以及国际法有没有这种规则,都需要国际法专业的知识支持。
随着在部分领域国际事务法律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规则呈现出技术化的形态。如果沿用前面地图的比喻,乍一看来,很多规则都在地图的遮蔽区域里。比如产品的原产地如何界定?59United States-Rules of Origin for Textiles and Apparel Product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port of The Panel, WT/ DS243/R, 20 June 2003.潮汐线的划定是采用最高平面线还是平均平面线?60Clive Symmons, "When is an 'Island' Not an 'Island'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Riddle of Dinkum Sands in the Case of US v. Alaska", Maritime Briefing, Vol. 2 (6) (1999), at https://www.dur.ac.uk/ibru/publications/view/?id=237.领海基线有几种划法?61Clive Schofield, "Departures from the Coast: trend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rritorial sea baselines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27 (4) (2012), pp.723-732.如果让一般公众、知识分子,乃至非国际法专业的律师来对这些规则做阅读理解,产生的无聊感可能不异于看到孔乙己绘声绘色地念叨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疑惑这些知识与真实的道德生活究竟有多少关系。因此,这些规则看起来都是道德无涉的庸常规则;这些规则在地图上都是被遮蔽着,很少得到关注,即使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获得关注,在缺乏解说的情况下,也很难和道德评价拉上联系。
另一部分国际法规则的待遇显然不同。似乎这些规则具有明显的道德意味和道德影响,显然不是 “领海基线有几种划法”这种档次的细碎问题。不少名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国际法训练,也都敢于在这些问题上一试身手。比如美国在违反《日内瓦公约》和相关习惯法,在反恐战争期间对恐怖分子嫌犯使用酷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家沃德伦(Jereny Waldron)就写了一本书来讨论相关规则。62Jeremy Waldron, Torture, Terror, and Trade-Offs: Philosophy for the White Hou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美国超越《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引发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甚至于在十年后德沃金在其最后一篇论文中还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63Ronald Dworkin, "A New Philosophy for International Law".这些规则(以及相关行为)的后果十分明显,所以即使不用进入国际法律推理的语境,他们也能进行道德评价。64这不代表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就直截了当。事实上,国际人道法在此问题上有细致而技术化的规定,相关的法律争论还涉及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冲突适用的问题。此处的法律论辩的结构是高度复杂的,但作为外行人,他们不需要对所有细节都有所了解。哲学家只要能在必要的程度内对规则的后果有所了解,就可以展开道德讨论了。
这两种规则的区别在哪里?国际法专业共同体是通过什么具体的知识手段来对这些规则进行区别建构的呢?
从道德评价的方式来看,一般认为有两种路径。一种以规范为中心的道德评价,可以被概括地成为道德义务论(deontology),65参见Kant, Immanuel,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Mary Greg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0。即看法律规则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此外还有一类观点,认为道德评价要根据后果来进行(consequentialist)。66关于后果论的介绍,参见Walter Sinnott-Armstrong, "Consequential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5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此外,明确的规则可能会抑制道德讨论;而当某些规则使用了比较模糊的标准,这种内容的不确定性可能反而引导和鼓励道德讨论。69Seana Shiffrin, "Inducing Moral Deliberation: On the Occasional Virtues of Fog",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3, (2010), pp. 1214-1246.比如“公平” 标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在两国划定大陆架界限的时候,要根据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协议来进行,以达到公平的解决。然而,“公平”的含义是十分模糊的。不仅在抽象的层面上我们可能对“公平”标准进行多种阐发,即便是在具体的个案中,“公平”作为一个法律标准应该如何在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适用,也存在多种讨论。70“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States with opposite or adjacent coasts1.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States with opposite or adjacent coasts shall be effected byagreement on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8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n order to achieve an equitable solution.” Article 83,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oncluded Dec.10, 1982, Entry into Force, Nov. 16, 1994,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883, p.3.相反地,如果国际法规则本身看起来是明确具体,可以直接操作的,类似的道德讨论就会被抑制。71不过,关于模糊标准的讨论虽然会被抑制,但不一定会去除对于这条清晰规则的道德评价。比如针对海洋法规则中的中间线原则,大众可能会质疑选取中间线原则的道德基础:坚持这种绝对原则是不是公平,是不是符合主权的道德性,等等。仍然以《海洋法公约》为例, 在两国需要划定领海界限的时候,《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是具体而明确的中间线的划法,而不是“公平”这样模糊的标准。72“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ea between States with opposite or adjacent coastsWhere the coasts of two States are opposite or adjacent to each other, neither of the two States is entitled, failingagreement between them to the contrary, to extend its territorial sea beyond the median line every point of which isequidistant from the nearest points on the baselines from which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s of each of the twoStates is measured. The above provision does not apply, however, where it is necessary by reason of historic title or otherspecial circumstances to delimit the territorial seas of the two States in a way which is at variance therewith.” Article15,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oncluded Dec. 10, 1982, Entry into Force, Nov. 16, 1994, United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883, p.3.在这条规则下,关于领海划分方法是否公平的道德讨论就可能少很多。
另一类别的原因在于程序性规则后果的不明确性。比如国际法院认定其对格鲁吉亚诉俄罗斯违反《种族歧视公约》一案有没有管辖权。73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Georgia v. Russian Federati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Reports, 2011, pp.70-141.大众对案件后果的期待是法院依据法律决定谁对谁错,谁输谁赢。对于专业外的人来说,程序的后果本身的意义很难被了解,因而也很难被关注。所以大众对国际法上管辖权规则的道德评价也兴味寥寥。这些实体后果在程序性阶段是难以预计的,因为进一步的案件事实,以及其他与实体相关的规则都会发生影响。我们不习惯对中间性的程序结果进行道德评价,案件实体部分的结果又不能确定,所以这一类规则也被认为是道德无涉的。其他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制度。不论是规定国际条约在国内有直接效力,还是规定需要国内立法机关专门针对相关条约立法才能适用,在缺乏具体的条约背景,不清楚条约具体的规定之前,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这种规定对某个具体案件实体结果的影响,那么我们很难在这个阶段就判断采取哪一种制度更好。在这一类问题中,我们难以直接对后果进行直接评估,最多只能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所以这一类问题本身即使引起道德评价的兴趣,也难以处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也是来自于国际法院。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纠纷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它的管辖权严格基于国家同意原则。如果国家没有明确地表示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国际法院对案件就没有管辖权。甲国于1992年4月成立,并且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其中《公约》第9条规定,关于公约的解释,执行以及公约下的责任的相关争议,公约当事国可以提交至国际法院。74乙国将甲国诉至国际法院,要求甲国就1992年4月之前发生的事件承担违反《公约》的责任。但问题是,在1992年4月之前,甲国在国际法上根本还不存在。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如何裁断?法院的判决是,由于条约效力不溯及既往,甲国仅就加入《公约》之后承担公约下的义务。所以《公约》第9条并没有授权法院对1992年4月以前发生的行为进行管辖。但是由于《公约》第9条规定法院可以就公约下的责任纠纷进行管辖,即使这里的责任不是由该国的行为产生的,法院对此也有管辖权。由于甲国继承了1992年4月以前的国家责任,所以依据《公约》第9条下的国家授予的同意,法院对此争议可以管辖。对法院这种对管辖权规则超出常规的条约解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道德评价?这就是著名的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案件,是国际法院历史上审理时间最长的案件之一。75由于涉及的是罪中之罪的种族灭绝,这也是国际法院卷宗中大众关注度最高的案件之一。当2015年判决公布的时候,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学者关注的是法院最后是否把当时发生的强迫种族迁徙认定成《公约》下的种族灭绝行为。而对判决书的前90多页关于管辖权的部分普遍缺乏兴趣。这么看来,管辖权规则是庸常规则么?实际上,在法院内部,法官之间最激烈的争论不是在种族灭绝罪的认定,而恰恰是在管辖权的程序规则上。从法官发表的个别意见来看,法院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对立。一部分法官的立场是哪怕采取类似溯及既往的方法,也要让法院对1992年4月以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管辖;另外一部分法官认为,国家同意管辖是国际法院最基本的原则,是国际司法的基础。回溯性管辖违反了这一规则,具有严重的问题。但一般大众难以估计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这种做法的后果。因为法院的管辖权包括各种类型的国家间纠纷,包括人权、环境、边界、使用武力等议题。在这个案件中管辖权的扩张可以被视作保护人权,但在下个类型的案件中可能就会视为对主权的过度干预。所以难以一概而论管辖权扩张对实体问题影响的结果。所以对于这类规则,需要知识、经验甚至专业直觉,才能就它们的后果有一个估计,才能有道德评价的基础。
国际法规则的道德无涉正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社会建构与国际法规则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如技术化、繁琐化、 程序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对道德无涉的社会建构,并不是指国际法专业共同体建构了法律规则的内容,不是直接指他们去建构了技术化和程序化的法律规则。因为我们不能断定遮蔽大众道德讨论是他们的主要动机。而且事实上,这可能不是设计规则的主要动机。国际机制的设计考虑的主要是在协议达成后如何促进各方遵守条约,比如为了增加违约成本而提高规则的明确性。76另一个考虑是,即使专家团体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也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比如条约谈判,本质上是政治协商,所以条约的内容超出了国际法律师可以设计的范围,决定权也不在律师手中。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作为法律专家,在诸多形式问题上国际法律师的设计可能仍然至关重要。他可能处于法律理由,将条约条款设计得十分复杂,难以读懂;或者在程序性条款上设计得很烦琐,作为法律陷阱或者法律防御。这种设计可能会附带产生规则技术化的后果。国际法专家以规则的这种状态为基础,可以进一步进行社会建构。这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专业团体与大众的讨论与沟通,在于向公众开放道德讨论需要的法律专业知识,来对相应的规则进行解说,使大众获得必要的信息。并不是说技术性的国际法规则自然地就被认为是道德无涉的规则,而那些概括的规定自然地就会吸引大众的道德讨论。但是如果国际法专业团体不将技术性的国际法规则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的话语,不解释程序性规则在司法过程中的影响,那么既有的知识壁垒就会阻止大众就这些规则与国际法专家形成对话,大众也因此缺乏进行道德评价的知识基础;相反地,有时国际法专家可能会进行解释、概括,甚至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将某些规则与道德评价联系起来。77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在这个通过控制开放专业知识形成对话的过程中,国际法专家不能单方面起到决定的作用。这个建构过程还要受到其他因素制约。比如,即使通过专业知识的解说,某些规则的影响还是很难预测或者描述。
五、循庸问恶
国际法中庸常规则的区分造成了什么道德后果?国际法的庸常规则——那些看起来不需要从道德角度来评价的规则——转移了大众的注意力。通过人权法、跨国法等议题,国际法专家把公众的讨论热情引向了有限的议题,进而设置了道德讨论的议程。在与大众有限的互动中,让庸常规则的道德无涉看起来是那么自然,那么合理,以至于我们在讨论(道德性意义上的)恶法的时候不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换句话说,规则中的道德偏见因此被日常化了,它们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存在,不会被大众去关注或者讨论。当我们讨论低潮高地在国际法上是不是可以作为领土被国家取得的时候,觉得这里面没有多少道德问题;78Stefan Talmo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Observations on the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5 (2), (2016), pp. 340-344.当我们讨论WTO中条约解释规则的时候,也不觉得这里有多少道德问题;当我们讨论条约在中国是直接适用还是转化适用的时候,也很难说出这里有多少道德问题;只有当我们讨论种族灭绝罪的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国际法规则有道德面向。但问题是,这样的讨论是在别人建构的问题意识下进行的,我们可能看不到庸常规则里面的问题。
规则的道德无涉是被建构起来的,而这种道德无涉的必然性是虚假的。79Roberto Unger, False Necessity, p.xxx(i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Edition).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知识和权力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通过策略性地开放一部分道德评价,国际法专家实际上将更多规则从道德评价地图上遮蔽,让他们看起来成为庸常规则。从而依据法律知识的壁垒来巩固在这条边界内国际法专家共同体的权威和权力。所以在这些看起来特别技术化的规则上,大众会依赖于专家的法律知识和分析。另一方面,很多庸常规则起着结构性的作用,对实体的后果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不一定会直接决定实体的后果)。所以,“道德无涉”的规则可能实际上隐藏了某种道德立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际法院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大会先后向国际法院提起了咨询意见,都要求国际法院回答使用核武器是否符合国际法。80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med Conflict, Advisory Opinion,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 C. J. Reports 1996, pp. 66-85;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Reports 1996, pp.226-267.这个案件在实体上是一个典型的疑难案件,因为法院发现国际法中既没有没有明确的规则允许,也没有明确的规则禁止使用核武器,所以难以在此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确定的回答。81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p. 266.围绕适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公众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包括道德评价。但大家较少注意的是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的处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法院以联合国环保组织提起的咨询请求不在组织职能范围内为理由,判决法院没有管辖权,回避了对咨询问题的回答。82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med Conflict, 84.在联合国大会提起的咨询意见案中,法院则在实体问题上作出了回答。回过头来看,对于几乎一样的两个请求,法院在实体上的处理与在管辖权上的处理似乎反映了同样的立场——对于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个与国家安全和人权都具有生死攸关联系的问题,司法不适宜介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院在管辖权阶段依据的规则,进行的法律推理,以及作出的判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都可能含有某个道德立场。但这部分判决与相关规则在大众看来很可能是庸常规则。 因为大家关心的问题集中在于禁止使用核武器规则与核威慑安全理论之间的矛盾,以及允许使用核武器规则与人权法规范之间的冲突。
对庸常规则的思考不仅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的一项前提性工作,而且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我们目前的法哲学研究提供反思的机会。它的意义不在于终结讨论,而是铺设新的研究议程。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知识—权力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83关于在这个方面的范例以及两篇具有启发性的评论,参见David Kennedy, A World of Struggle; Ingo Venzke, "Cracking the Frame? On the Prospects of Change in a World of Struggle", Review of David Kennedy, "A World of Struggle: How Power, Law, and Expertise Shap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7 (3), (2016), pp.831-851; Samuel Moy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Law"。也可以站在建构的立场,重新落脚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思考如何在新道德话语的基础上展开新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律规则。因此,新兴世界的国际法学人面临双重任务:其一是在国际法专业内部确立地位,在专业知识上得到同行的认可,进而在共同体内部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将旧背景放到台前来质疑;同时要面向专业领域以外的大众(包括其他领域的专家,如哲学家),通过国际法专业知识对庸常规则进行去技术化的解说,恢复被遮蔽的道德争论,在这些规则上开放大众与国际法专业的互动。其二是要有法哲学的理论自觉,对国际法中已经设立的道德议题保持警醒,结合对政治现实的体察与对理想秩序的主体性想象,通过对理论的发展来祛除国际法中的偏见。84例如,如果我们大致同意目前国际法中的道德话语过于偏向个人为主体的人权法,那么针对庸常规则的可能就要求我们思考以国家为中心的道德理论。这并不代表对既有人权法制度以及道德基础的反动,而是要在庸常规则中开辟关于国家道德性的新讨论空间。相关的讨论可参见Bruce Williams, "State Mor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1 (Feb., 1923), pp. 17-33。此外可参见 Michael Walzer, "The Moral Standing of States: A Response to Four Critic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9, No. 3 (1980), pp. 209-229;Gerald Doppelt, "Walzer's Theory of Mor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8, No. 1. (1978), pp. 3-26。感谢许章润教授的启发性评论。
影 像
Image
*本文初稿曾在主题为“恶法”的历史法学年会(2016年秋)上宣读,其间受益于诸位参会学者的评论。其中,许章润教授与方朝晖教授就论文的旨向给予了启发;翟志勇博士指出了本文与恶法问题在理论上的关联;周林刚博士与屠凯博士对本文的概念与论证提出了细致而重要的批评,他们指出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关键问题,也迫使笔者修改了部分立场;陈庆博士提供了古典资源的参照。本文的部分研究系笔者在哈佛法学院全球法律与政策研究所进行访问期间完成,David Kennedy教授就本文核心观点进行了讨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的博士候选人Jonathan Gingerich在写作初期提供了阅读线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博士生马勤提供了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笔者在写作阶段能接触的中文译作资料有限,即使部分相关文献已有中文译本,笔者在写作中仍然参考的是英文版本。由此给读者来带的不便,特此致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博士候选人。
74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December 9, 1948,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78, p. 277.
75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roatia v. Serbia), Judgment,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ebruary 3,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