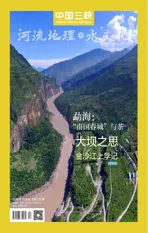康有为游荷兰
2017-01-19张林杰编辑任红
文 / 张林杰 编辑 / 任红
康有为游荷兰
文 / 张林杰 编辑 / 任红

荷兰阿姆斯特丹街景 绘图/李雨潇
光绪三十年二月,即公历1904年3月,康有为从香港再次去往欧洲。
此前不久,他离开养病的印度大吉岭,经南亚回香港探望母亲。他的身份虽还是个政治流亡者,但出亡之初那种奔命的紧张和组织保皇活动的热闹已经过去,他的政治生活随着革命浪潮高涨而愈来愈无足轻重,他也因此有了更多时间精力来投身个人兴趣。旅行看世界,就是他的兴趣之一。
一百多年前,交通条件比古代已大大改善,但从中国去往欧洲,仍然是相当漫长的旅程。康有为乘法国轮船离开香港,经越南、泰国到达马来亚的槟榔屿,然后换乘一艘英国轮船,经锡兰(今斯里兰卡)、从亚丁湾进入埃及,又沿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终于在意大利登岸,踏上了欧洲大陆。这次航程总共耗时差不多三个月。
自流亡以来,康有为去过了不少国家,在日本、北美及英国治下的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印度都有过生活经历。对他而言,海外不再是《镜花缘》中的秘境,欧洲也不再是《瀛环志略》中的陌生世界。因此,作为一个兴致勃勃的旅游者,尽管欧洲各国的政治、文化和建设成果依然让他称道不已,但欧洲列强在他的眼中,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光鲜亮丽了。他看到的伦敦与巴黎,繁盛宏伟却污秽不堪;德国井井有条,但警察治国,禁锢言论,缺乏自由;意大利并不比中国富庶,意人也“至贫多诈”,骗子、窃贼猖獗,缠住游客讨钱的乞儿一如印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如僻郡荒村一般,“道秽屋卑”,无可观揽。只有北欧小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是荷兰,更让他赞不绝口。
一百多年前的荷兰,如人们今天所见,已是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现代国家。在乘船去往北欧诸国的途中。经过荷兰海岸时,康有为见到的是“道路整洁,田畴平直,嘉树夹道,树影递天,牛羊被野,楼阁新靓”的景象,他兴奋得借诗遣兴,“叹荷之小而能治国也”。

①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 摄影/黄旭/ FOTOE ② 荷兰阿姆斯特丹街景 绘图/李雨潇
不过,他真正踏上荷兰土地,是在一个多月后。当他从布鲁塞尔乘五小时汽车抵达阿姆斯特丹时,已是晚上十点半。这座城市的夜景让他耳目一新:“海岛穿错,船火万亿,与楼台相映,境界甚新,行欧界以来所无也。”
康有为对荷兰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齐:“其屋极整齐,万家一律”,百姓的居住环境也相当整洁,“玻窗明艳,前临水木,极净美”。在阿姆斯特丹,不仅“道路广洁,百货骈辏,人民繁盛,楼宇峻整”,而且桥河纵横,“有桥三百余,岛九十余,花树菲菲繁盛,引溪开沟纵横千百,穿贯全市,而处处以桥通之”。大城市如此,乡村田畴也不遑多让,大块的田地,都呈长方形,田地四周河沟环绕,并用小桥连接起来,四通八达的水路,保证了灌溉,“故田野极绿,草树弥望”,到处植被丰盛,“其夹道必植树,树距丈许,树影相递,堤道极直,递百千里无际”。如此丰饶的田园景象,让康有为不禁想起了中国古代治水治田的圣人,他穿凿附会地称,大禹治理沟洫和孔子井田沟浍之法在荷兰得以“见实行之”。从荷兰人的治水治田,康有为也看到了一种理想的治国方式,他说荷兰人治国,就像有洁癖的人把自己的斋榻整理得精整无尘,像有花癖的盆景师将盆景收拾得纤悉不遗一般。这样的境界,“大地万国”中惟有荷兰做到了。他认为,这正是荷兰以蕞尔之邦成为强盛之国的原因。由此,他想起了自己所规划的大同世界:“他日大地大同,不能不取法荷夫!”

不过,康有为以大为美的趣味,也让他对荷兰的建筑略感遗憾,他认为,荷兰建筑多“甚卑小,不如英法德之宏大”。不久前,他才游览过的瑞士、比利时、挪威等国,建筑也同样显得卑小。他认为,这种小与国土有关:“凡国土之偏小者,其国之宫室器物必卑小偏狭。”五年前,在日本居留期间,他也曾注意到,日本“屋室、园地、杯盘、花木无不尚小者,人民亦气量偏狭”。用 “偏狭”“卑小”来形容小巧玲珑的事物,是因为重“大气”的康有为,把“小”视为一种气度缺陷。在他看来,大国均有一种伟大的气象,英、德、法、美等国皆如此,美国尤其如此,它“开阔豪爽,真有泱泱之大风”。这一发现,也让他对自己的国家颇为自豪:“吾国虽今守旧衰弱,而人士的广大豪爽,屋舍虽卑污,亦自轩昂广大,与日本迥殊。”他相信:“国土之感人甚深,囿人甚迫,而生其地者不能出其风土之外也。”这种对风土人情的解释,显然得自中国传统的“天人交感”理论,同时,这套理论也与当时欧洲盛行的从环境来解释民族精神的理论很相似。在史达尔夫人《论德意志》和丹纳的《艺术哲学》中,都有类似的阐释。
康有为游览欧洲,博物馆是必去的地方。博物馆不仅是他了解各国历史文化的窗口,更满足了他对艺术的独特兴趣。康有为自称“性癖书画”,早年曾收藏过不少国画、碑帖和古玩,流亡海外后,又四处搜罗了数百件中西绘画作品。在荷兰他也十分留意博物馆藏的绘画。荷兰绘画在欧洲颇有影响,不少绘画大师,如鲁本斯、维米尔、哈尔斯、伦勃朗等都是荷兰人。不过,康有为的绘画趣味太受宫廷画风影响,谈到国画时,他特别看重工致、讲法度、风格华丽细腻的“院体画”,而提到西画,他所喜欢的画家,更多是带着文艺复兴古典主义风格的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绘画更被他作为艺术的标杆。在这种趣味支配下,康有为对荷兰绘画显然缺乏领悟。他说荷兰绘画“以黝黑为体,于黝中着光色取神以为胜”,这一描述虽然抓住了荷兰绘画注重光影的特征,但他对这种特征却并无太大兴趣,断言荷兰画“黝然无味,神采去拉斐尔派远矣”。按照他的标准,欧洲绘画有三大派,西班牙派绘画最次,荷兰派绘画居中,而意大利派绘画最佳。这种充满成见的审美趣味,让康有为不仅对崇尚神似的中国文人画有所排斥,而且对写实绘画的欣赏也仅仅停留在甜腻、圆润、光洁的拉斐尔式风格中。
康有为的荷兰游记也时时流露出“帝王师”的心态。当年在上呈光绪的条陈和书稿中,他曾用俄国彼得大帝“微服作隶”,立志“变政”的故事来激励光绪变法,到荷兰后,他也不忘去彼得当年学习造船的“彼得学船之屋”参观。在阿姆斯特丹时,正好遇上荷兰女王巡视,接受群众的欢呼,这给康有为提供了一个直观西方君主与民众关系的窗口。他记述了女王出宫门时的仪式,并目睹了市民夹道欢呼及女王答礼的场景。他看到百姓不断向女王表达敬意,而女王也不断对百姓的欢呼回礼致意。认为这不只是礼尚往来,也是沟通君民之情的方式。由此,他想起中国古代礼制,都强调君臣之间的相互礼节。但元代之后,蒙古跪拜式军礼变成了国礼,跪礼成为习俗,并被明朝延续下来,结果君主对臣子越来越简慢,民众对“喝殿出门”的官家也很少致意。
康有为的政敌往往把他视为“妄人”,他既有士大夫的固执和道貌岸然,也有名士的狂妄和落拓不羁,他常常即兴发议论,不少议论在今天看来,都是缺乏“政治正确”,又颇为有趣的奇谈怪论。一天,在一个公园里,他偶遇一位和他同船来的荷兰女孩。这位丰满漂亮的女孩热情邀他去家中做客,把他引荐给家人,还用茶点招待他。康有为于是得出结论说,欧美女性都善交际,喜欢结交名流,“其好事、好名、好近贵介人,殆不可思议”。康有为也喜欢谈论女人。他听说荷兰女王以容貌秀丽而著称欧洲,但见到巡视的女王(康所见到应该是威廉明娜女王)后,他觉得不过是丰满端庄而已。不过,他认为欧洲出美女的国家,一是瑞典,一是荷兰。他用地理决定论去解释这个问题:说生长于湖海边的人都秀美,中国的杭州如此,欧洲的瑞典、荷兰亦然;生长于平原者则多丰满,如德国人;生长于山石之地的人多瘦癯,如广东山民。他将这种笼统的结论,上升到对种族的概括,说“英人多长,德人多肥,法、意人矮与中国同”,而“欧人之白,一因地度之高寒,二因波罗的海、地中海之水汽,非洲、印度人之黑,则日蒸使然”。甚至断言:“白人聪敏而黑人愚劣,则颜色与智慧竟相关,而颜色视所生之地。”这套地理决定种族的理论,也使康有为在白人面前有一种自卑感,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
康有为青年时代就喜欢旅行,这既让他能将书中知识“一一案之经历实验”,也为他提供了从人世纷扰解脱出来的途径。流亡海外后,他更是“三周大地,游遍四洲”,欧洲十一国之行,是他海外旅程的重要一章,而游荷兰,则是这一章中一段轻松的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