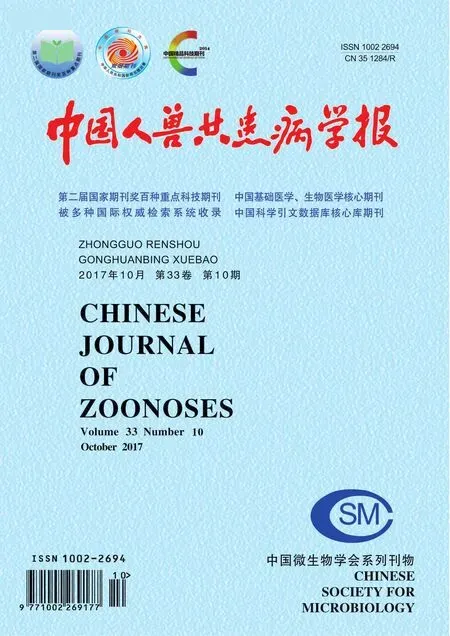黄热病的防控研究进展
2017-01-16杨秀惠严延生
杨秀惠,严延生
黄热病的防控研究进展
杨秀惠,严延生
黄热病是一种经蚊媒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在历史上曾引起欧洲港口城市及美洲一些地区疫情的暴发,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上世纪40年代,投入可终身免疫的17D系列疫苗对暴发地区的人群进行大面积接种以来,该病一度出现沉寂状态。但自上世纪90年代初,该病又陆续在非洲、南美热带地区和国家暴发流行,病死人数甚至超过2014年在西非3国暴发流行的埃博拉热;特别是2016-2017年在安哥拉、刚果和巴西流行以来,已经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此外,2016年我国从安哥拉输入了11例病例,这是有史以来亚洲首见疫情,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了2017-2026年消除黄热病流行的策略,其主要依据在于17D疫苗能够安全有效的控制本病的流行。蚊媒控制及疫苗预防接种,特别是对后者抱有很大期望,WHO的消除策略可能实现,但这需要有关国家强有力的执行保证,同时还需要各国共同遵守全球检疫条例的规定。为此,本文从历史及近期黄热病暴发流行的特点,结合预防接种简述了有关本病的的防控措施,期望WHO消除黄热病流行的策略能在2026年成功实现。
黄热病;自然疫源性疾病;17D疫苗;免疫保护
黄热病(Yellow fever, YF)是一种古老的蚊媒传染病,但2016-2017年以来,该病在安哥拉、刚果、乌冈达及南美的巴西等地再次暴发,特别是该病首次输入亚洲国家——中国[1-2],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似乎又成为一种新病,鉴于此我们需要对该病进行重新认识。
黄热病病毒是黄病毒科黄病毒属的代表种,经由伊蚊传播。其传播类型有3种:一是丛林型;二是丛林和城市交叉流行的中间型;三是人口众多的城市型。丛林型黄热病可经趋血蚊属,煞蚊属传播,以蚊—猴—蚊形成循环,疫情发生的周期性间隔3~7年不等,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循环传播,因此该病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丛林和城市交叉流行的中间型主要是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之间的交叉流行,其源头由丛林型引发,经过中间型人的感染,再传向人口众多的城市。在非洲、热带南美洲城市里传播本病的蚊子主要为埃及伊蚊,但它与同属的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和寨卡病等黄病毒一样也可经白蚊伊蚊传播。
黄热病病毒是直径为40~50 nm圆形有包膜RNA病毒,其遗传物质为单股正链,长约11 000个核苷酸的RNA,有1个单一的开放阅读框,编码一个多聚蛋白,可由宿主蛋白酶切割为3个结构蛋白(C、PrM、E)和7个非结构蛋白(NS1、NS2A、NS2B、NS3、NS4A,NS4B和NS5);其蛋白编码基因的排列与在基因组中排列一致。
蚊子叮咬人后潜伏期最短3 d后就可发病,主要症状为发烧、头痛和肌肉疼痛。大多数病人经历发热体征即可恢复,但一些病例可持续发展到毒性发作阶段,其肝、肾、心感染的地方并有黄疸出现,后者意味肝功严重受损[3]。如果这一阶段持续下去,其死亡率可高达50%,主要是由于肾功能衰竭,内出血与循环衰竭而死亡。对黄热病的治疗没有特异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只有支持疗法,所幸疫苗接种保护性很高,是预防的关键。
由于感染黄热病病毒后的高死亡率,因此其属于必须在BSL-4中操作的烈性病原体,该病也是国际卫生条例中规定的必须检疫的3种传染病之一[4]。
1 黄热病的疫情
1.1历史大流行简况 据Woodall JP and Yuill TM报道[5],历史上的黄热病最早记载的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由奴隶贸易引起,主要发生在欧美的港口地区。盛装饮用淡水的大木桶的帆船在欧美港口之间商贸游戈,舱底居住着用于买卖的奴隶,蚊子在盛装淡水的木桶中产卵,此后孵化出孓孓,黄热病在居住于舱底的奴隶中流行,孓孓成蚊后在染病的奴隶中叮咬获得感染性,因此一到港口后,随着人、蚊子下船引起黄热病在港口城市蔓延,致使浩劫发生。
在美洲,黄热病于1668年在纽约暴发,1691年在波士顿,1699年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在这些主要城市的流行夺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1776年美国建国后,18-19世纪期间,美国东部和南部有13个州卷入这个灾难。1793年发生在费城,死亡4 044人;1798年费城再次发生,死亡3 506人;1794年发生在巴尔的摩,360人死亡,1800年再次发生,造成1 197人死亡;1798年和1803年在纽约又分别再次暴发流行,1839年在加尔维斯敦(Galveston)流行,死亡人数约占当地人口的5%,1878-1879年在孟菲斯(Memphis)和新奥尔良流行,死亡人数达4 046人;在20世纪初的1905年,美国新奥尔良最后发生暴发流行,死亡人数达8 399人,这些暴发带来可怕的社会和经济破坏。
在欧洲,1897-1906年间,有4 000名欧洲移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因感染黄热病病毒死亡;1800年暴发发生在西班牙港口,60 000例黄热病死亡;1821年,巴塞罗那报告了黄热病死亡病例20 000例(约为当地人口的1 /6),1870年报告死亡病例的更多,疫情暴发是来自古巴船舶引发的。其他疫情发生在法国(1802-1861年),1804年意大利里窝那(Livorno),死亡人数 650例;1857年葡萄牙(Oporto和Lisbon),1852年和1865年英国(Swansea)均有疫情发生,1828年直布罗陀报告1 183例死亡病例。欧洲最后一次疫情大暴发是发生在1905年的直布罗陀。
在非洲,1986-1987年在尼日利亚一个城市暴发的黄热病造成约120 000病例发生,其中24 000例病例死亡,该死亡数多于最近在西非3个国家发生的埃博拉疫情死亡数。
1.2 2016年安哥拉和刚果的流行
1.2.1安哥拉疫情 2015年12月5日,安哥拉发生了首例黄热病病例。但2016年1月20日该疫情才在安哥拉媒体上曝光,两天后ProMED-mail通过互联网报告了此事,安哥拉政府于1月25日才向WHO报告,2月12日WHO在Disease Outbreak News 上公布了此信息。在这期间,疫情已扩散至首都卢旺达,5月18日后卢旺达才开展大规模的预防接种。目前推测疫情的传染源是从边远农村来的的矿工或农民引起的,卢旺达环境差,埃及伊蚊多,以致引起卢旺达黄热病暴发流行,疫情扩散至18个省,并跨境输入到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中央省。从2015年12月5日发现首例至2016年9月11日,累计发现4 100例疑似病例(其中首都卢旺达达2 072例),共采集到3 577份标本进行检测,实验室确证病例884例,确证病例高峰期从2月到4月,死亡373例,其中经实验室确证121例[6-7]。除DRC受其输入暴发疫情外,肯尼亚也报告从安哥拉输入2例,中国报告输入11例[6],5例福建,5例北京,1例上海,其中1例病死在北京[8]。
1.2.2DRC疫情[9]2016年4月23日,DRC卫生部宣布发生黄热病疫情。截至2016年5月24日,刚果中央省报告了459例(约90%)的疑似黄热病病例,死亡45例。该省与安哥拉接壤,上述2015年12月初就发现了首例黄热病病例。DRC卫生署吁请美国CDC帮助控制疫情,DRC中央省分别于2016年5月25-6月7日、8月17-28日进行了2次大规模黄热病疫苗接种,截至2016年8月18日,该省报道了410名疑似黄热病病例和42例死亡病例。从393份标本中实验室确认37例为黄热病病毒阳性病例。虽然没有很好的记载这次整个疫情发生的过程,但在这一地区其可疑病例还是很容易与疟疾、病毒性肝炎和伤寒区分开来的,其他可能的诊断还包括寨卡、西尼罗河或登革热病毒等,但实验室没有这些确认病例。37例确诊病例中有35例是从安哥拉输入的。三分之二的确诊病例是在刚果一侧的一个市场里发现的,在该市场每周有40 000多人跨境交易。因此疫情控制策略应放在改善协调卫生监督与边民跨境贸易活动以及加强实验室和病例监测上,此外还需相应加强对健康边民的筛查力度。
1.2.3巴西疫情[2]历史上巴西时有暴发黄热病疫情,但自1942以来,巴西就未报道过城市黄热病的流行。从2016年12月-2017年2月22日,巴西发生黄热病流行。在这场暴发疫情中,发现1 345例疑似病例,其中295例经实验室确认,215人死亡。在295例确诊病例中,男性占86%例,年龄从30~60岁。大多数病例生活在农村,从未接种过疫苗,鉴于他们工作的性质,暴露的风险也较大。大多数病例居住于Minas Gerais州,尽管该州已开展了接种疫苗,但未能全面复盖,致使病毒继续扩散。造成暴发黄热病疫情的原因尚不明了,但已发现80%~90%的褐吼猴已被感染,或部分已经死亡。推测黄热病病毒从感染的猴经蚊媒传至人,再在人类中暴发流行。
2 国际卫生条例
在黄热病疫区的免疫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要对那些前往和来自疫区的游客接种,避免感染者输入到新地区,由蚊媒叮咬感染者引起未经免疫人群新的YF疫情暴发流行。国际卫生条例[4]是约束有关国家(目前是196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措施,该条例是根据国际法,以防止疾病跨越国界传播,威胁人类社会。YF是个人跨国旅游需要传染病接种疫苗的病种,也包括从一个疫区到另一个国度(或地区)。应注意的是,并非一个国家全被视为疫区,这与地理有关,关注点主要应放在这个国家的疫区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各国都严格执行国际卫生条例中有关的YF的接种及其接种后的证明,其中包括未接种但伪造已接种的疫苗接种证[5],这很容易导致YF的疫情发生。
3 遏制黄热病的流行
遏制黄热病的流行主要采用两大措施:一是控蚊;二是接种疫苗。
3.1控蚊 蚊媒控制是控制蚊传疾病的关键所在,但难度很大。在蓄水池投放小鱼吃灭蚊子的孓孓来控制蚊子在蓄水池发育成蚊是控蚊的一个措施,但从蚊虫滋生角度来说,其作用实在有限。使用化学药剂喷洒灭蚊是一个应急的重要措施,但不能使用DDT类药物,其残留农药对环境及生物链破坏大,可用的是药效较为持久性的溴氰菊酯类药物。挂蚊帐可以防蚊子的叮咬,但这只能防止疟疾、乙脑等晚上叮咬传播的蚊子;而经蚊媒传播的黄病毒属病毒如黄热病、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Zika的蚊子均为白天咬人,它们所产的孓孓大多在在树洞、花盆,浇乘水容器、轮胎和野外搁置的废弃的瓶罐浅清水中,这就要依靠动员公众翻盆倒罐灭孓孓,尽最大力量降低蚊虫的布雷图指数,这措施对控蚊防病力度大。再一个将来可能可用的措施就是利用转基因蚊子如携带苏云金杆菌(Bacillusthuringensis)伴胞晶体基因和沃尔巴克(氏)体(wohlbachia),使次代蚊子不育,但这项技术进行控蚊的努力时间太长而不实用。
对城市型控蚊相对有以上可行的措施,而对丛林型和中间型疫区的控蚊是相当困难的。
3.2疫苗接种控制 由于17D疫苗在控制黄热病效果显著,因此WHO在制定全球2017-2026年消除黄热病流行的策略中,首提疫苗控制措施[10]。
3.2.117D疫苗发展史 1927年Stokes等从加纳一个轻症病例中分离出黄病毒Asibi株,并将Asibi株通过鸡胚减毒发展成17D疫苗。法国人则在塞内加尔从Francoise Mayali分离出黄病毒并在小鼠脑中传代减毒发展为嗜神经性疫苗株(FNV)。FNV在鼠脑中传260代后失去了亲内脏(肝脏感染)和感染蚊子的能力,FNV疫苗株主要用于非洲讲法语国家,使用后减少了大量的YF病例,但因为FNV疫苗株是通过鼠脑减毒,所以该疫苗株还保持着一定的嗜神经性,导致儿童接种疫苗后出现极少数病毒性脑炎,因此该疫苗被禁用于14岁以下的儿童。1980年随着17D疫苗成功应用, FNV疫苗即终止使用。尽管这样,FNV疫苗在1940年和上世纪1950年代在非洲控制黄热病中仍然功不可没[1]。
Asibi株首先在鼠胚胎中传18代后再在鸡胚中传58代,为了减少可能的副反应,接着再在除去脑和脊髓的鸡胚中传128代成为17D疫苗株,其在鸡胚中传176代后被鉴定为既减毒又具有高度免疫原性,相当理想的减毒活疫苗株。17D活疫苗株失去亲内脏、嗜神经性和感染蚊子的能力。疫苗病毒不到1 000个感染单位就可诱导产生具有高度免疫原性与保护性免疫的功能。1937年正式投入使用,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其研发者Max Theile为此获得诺贝尔奖。但研究表明该疫苗株在鸡胚中传400代后,由于过度传代反而使免疫原性降低,这就导致了在1945年建立 “种子源”批系统,用种子源病毒生产第二批种子病毒,继而用第二批种子病毒扩大生产制备疫苗[11]。这个种子批系统已经很好地运行了75年,生产出总数约为6亿5 000万剂疫苗。为了运输和使用的便利,该疫苗已制成冻干粉剂,通常每个剂量包含4 000到100万国际单位病毒,加无菌水重悬至0.5 mL,经皮下或肌肉注射。虽然研究表明99%成人接种30 d后可产生血清中和保护性抗体,但最近的证据表明,儿童接种后保护率不足 90%[12-13]。WHO认为该疫苗可终身免疫,不需增加接种次数。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遵循这一建议,如巴西仍要求每10年补种一次。
3.2.217D疫苗现状 自1940年以来直至目前疫苗在鸡胚中繁殖生产的技术变化不大,仍然使用种子批制。但疫苗病毒有3个亚株系。第一是17D-204株,Asibi株在鸡胚组织中传了204代,而疫苗株的生产和使用则介于234-238代; 第二是17DD株,该株在鸡胚组织中传了195代,另采用不同于17D-204株的其他传代方式再传,疫苗株的生产和使用则介于285-288代;第三是17D-213株,其系17D-204传至235代的后裔株,由德国Robert Koch研究所接手发展成疫苗,传代介于238-239。这三株基因组序列稍有不同[14-15],但并非认定为不同的基因型或表型,它们只是在包膜蛋白糖基化位点有一些变化[16],也没有证据表明疫苗的免疫原性有所降低[17-18]。这就奠定了疫苗使用的广泛基础。
目前有6家黄热病疫苗生产厂家。17D-204疫苗是在法国、塞内加尔、美国及中国(武汉所)生产;17DD疫苗是在巴西生产,17d-213疫苗是在俄罗斯生产。在这6家中,巴西、法国、俄罗斯和塞内加尔生产的疫苗经世界卫生组织审查鉴定,认定他们生产的疫苗符合使用标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定价购买后提供给有关国家使用。而中美两国生产的疫苗并未经WHO预审,生产的疫苗只在本国内使用。
3.2.3疫苗的供应和最低有效剂量 国际上6个疫苗生产厂家预测每年可以生产5 000-10 000万剂疫苗。由于疫苗生产仍然使用鸡胚,而鸡胚的供应并不恒定,且生产厂家间每年生产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疫苗的生产与需求仍存在很大问题。而目前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和南美洲热带地区有45个国家约10亿人口处于黄热病的威胁之中,每年平均估计有180 000病例发生,病死78 000例[19],因而每年建议的剂量数约336 200万,但这很难确认和实现。有暴发疫情的年份与无暴发疫情年份对疫苗的需求有很大差别,2016年安哥拉和DRC分别暴发了疫情,前者估计需要2 000万剂疫苗,而后者约需980万,还有一个与之不相关的暴发在乌干达,需要疫苗80万剂[20],而国际应急储备只有600万剂,这样大的差距是需要研究解决的。
幸运的是,Martins 和Campi-Azevedo两个团队分别与2013年2014年分别用志愿者研究了可诱导保护性免疫应答产生的17D疫苗的最少剂量[21-22]。涉及使用志愿者749名,均为成年男性,采用双盲、随机的方式进行疫苗免疫效果的临床试验。含27 476 IU病毒的正常剂量组疫苗病毒与5个组别(10 447、3 013、587、158和31 IU)低剂量组进行比较,结果未见严重不良反应事件。除158和31 IU组外,≥587 IU组均能诱导血清保护性中和抗体的产生,表明剂量为587 IU就有效;但与病毒血症相关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在不同的组别有差别,炎症趋化因子(TNF、IFNc, IL-2)、细胞因子(IL-5、IL-10)及病毒血症在3 013 IU以下组均低下,而≥3 013 IU剂量(即约1/9正常剂量)产生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效果与正常剂量组相当。鉴于该研究仅限于17DD疫苗,因此,世卫组织工作小组作出建议,允许巴西疫苗在应对疫苗供应不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最小接种剂量进行免疫。而其他两类疫苗和17DD一样均属于17D疫苗系列,其免疫效果没有差别,于是在2016年8-9月在安哥拉和刚果的大范围疫苗接种中使用了最小剂量接种,每一剂疫苗容积均为0.5 mL,用结核菌素注射器接种0.1 mL(已超过1 000 IU)进行预防接种,其接种人数可增5倍,其后200万份疫苗经该法可用于1 000万人的接种;而≤9个月以下组儿童则用正常剂量组接种,保证了疫苗不至于中断,大大缓解了疫苗不足问题。
4 展 望
黄热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要消灭自然疫源性疾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WHO制定全球2017-2026年消除黄热病流行的策略其依据在于17D疫苗安全有效,预防接种后可终身获得免疫,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一般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保护率能达到80%,这种传染病就难以传播起来,因此,WHO希望通过对存在疫情的非洲和南美洲热带地区的人群进行大面积免疫,另外要求各国政府严格遵守全球卫生检疫条例,就基本上能够达到消除该病的目的。这个策略是否能达到,关键要看各国政府的执行力。
关于疫苗的供需问题,确实难度不小,这里涉及到流行年和非流行年问题;其次在于流行地点与接种人群大小这一关键问题,估算大了,经济负担接踵而来;而估算小了,对于疫情控制就造成麻烦。因此测算疫苗的供求量,是保证该策略能够达到目的的关键因素。上述所言,≥587 IU组就能诱导血清保护性中和抗体的产生,而WHO制定的最小安全有效剂量是1 000 IU,≥3 013 IU组研究剂量是才能产生与病毒血症类同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这与产生保护性中和抗体是2个概念。所以在2016年的安哥拉及DRC的暴发流行中,WHO确定了1剂量用于5人份接种的策略,其每人接种量均已超过接种1 000 IU的所谓最低限,不论其是哪国生产的疫苗,因为它们都是17D的后裔株,并都严格遵循种子批生产原则,因此按照1 000 IU来进行应急接种,应该不会对“策略”产生大的影响。
目前该病在非洲和南美洲热带地区的流行仍未中断,至少说丛林型黄热病的流行肯定仍在进行着,那么它就有机会侵入人间。我国人口众多,有13亿之众,去年发生了11例输入性病例,这在亚洲国家间是第一次。随着现代交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我们所在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黄热病潜伏期病人无论是在非洲哪个国家,都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到达我国,另外从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福建某个村在安哥拉首都卢旺达就有2 000多人从事商贸活动,此外2016年福建从安哥拉输入的5例轻症病例中至少有2例从血液中不能检出病毒核酸的病例却在尿液中检出黄热病病毒核酸,不仅说明它们带毒时间长而且可能经性传播,更说明黄热病病毒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否一定要在深受白蚊伊蚊威胁的中国沿海几个省份进行大范围的黄热病疫苗接种,我们认为关键是要严格落实WHO的卫生检疫标准,严格对有影响地区的入境者进行免疫接种,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大范围的黄热病疫苗接种;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疫苗接种存在的副反应问题,相关的嗜神经和内脏疾病的发生率约为0.2/10万,因此除了沿海几个省份在6-11月份白蚊伊蚊大量繁殖的季节从疫情国输入大量的病例外,我们认为暂不考虑大范围接种这个疫苗的。除此以外,中国肯定欢迎和支持WHO在2026年消除黄热病流行的策略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1] Barrett ADT. Yellow fever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A very successful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but still we have problems controlling the disease[J]. Vaccine,2017,pii: S0264-410X(17)30338-30339. DOI: 10.1016/j.vaccine.2017.03.032
[2] Goldani LZ.Yellow fever outbreak in Brazil, 2017[J]. Braz J Infect Dis, 2017, 21 (2): 123-124.DOI:10.1016/j.bjid.2017.02.004
[3] Monath TP, Vasconcelos PF. Yellow fever[J]. J Clin Virol, 2015, 64:160-173. DOI:10.1016/j.jcv.2014.08.030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2005).Third edition [EB/OL].[2006-7-11]http://www.who.int/topics
[5] Woodall JP,Yuill TM. Why is the yellow fever outbreak in Angola a threat to the entire world[J]. Int J Infect Dis, 2016, 48: 96-97.DOI:10.1016/j.ijid.2016.05.001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Yellow fever outbreak weekly situation report w36,11 Sept 2016,incident management team-Angola[EB/OL].[2016-9-11] http://www.afro.who.int/pt/yellow-fever/sitreps
[7] Woodall JP. Another pandemic disaster looms: yellow fever spreading from Angola[J]. Pan Afr Med J, 2016, 24:107. DOI:10.11604/pamj.2016.24.107.9921
[8] Chen Z, Lin L, Lv Y, et al. A fatal yellow fever virus infection in China: description and lessons[J]. Emerg Microbes Infect, 2016,5(7):e69. DOI:10.1038/emi.2016.89
[9] Otshudiema JO, Ndakala NG,Mawanda EK, et al. Yellow fever outbreak-Kongo Central Provinc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ugust 2016[J].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2017,66(12):335-338.DOI: 10.15585/mmwr.mm6612a5
[10] WHO. Eliminate Yellow fever Epidemics (EYE): a global strategy, 2017-2026[J].Wkly Epidemiol Rec,2017,92(16):193-204.
[11] WHO. Standards for the manufacture and control of yellow fever vaccine[J]. World Health Organ Epidemiol Bull,1945, 1:365-370.
[12] Collaborative Group for Studies of Yellow Fever Vaccine.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clinical trial of two yellow fever vaccines prepared with substrains 17DD and 17D-213/77 in children nine-23 months old[J]. Mem Inst Oswaldo Cruz, 2015, 110(6):771-780. DOI:10.1590/0074-02760150176
[13] Belmusto-Worn VE, Sanchez JL, McCarthy K, et al.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hase III, pivotal field trial of the comparative immunogenicity,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of two yellow fever 17D vaccines (Arilvax and YF-VAX) in healthy infants and children in Peru[J]. Am J Trop Med Hyg, 2005,72:189-197.
[14] Hahn CS, Dalrymple JM, Strauss JH,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virulent Asib strain of yellow fever virus with the 17D vaccine strain derived from it[J]. Pro Natl Acad Sci U S A, 1987,84:2019-2023.
[15] dos Santos CN, Post PR, Carvalho R, et al.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yellow fever virus vaccine strains 17DD and 17D-213[J]. Virus Res, 1995,35:35-41.
[16] Beasley DW, Whiteman MC, Zhang S, et al. Envelope protein glycosylation status influences mouse neuroinvasion phenotype of genetic lineage 1 West Nile virus strains[J]. J Virol, 2005,79(13):8339-8347. DOI:10.1128/JVI.79.13.8339-8347.2005
[17] Pfister M, Kürsteiner O, Hilfiker H, et al.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BERNA-YF compared with two other 17D yellow fever vaccines in a phase 3 clinical trial[J]. Am J Trop Med Hyg, 2005,72:339-346.
[18] Chowdhury PR, Meier C, Laraway H, et al. Immunogenicity of yellow fever vaccine coadministered with menAfriVac in healthy infants in Ghana and Mali[J]. Clin Infect Dis, 2015,61(suppl_5):S586-593. DOI: 10.1093/cid/civ603
[19] Garske T, Van Kerkhove MD, Yactayo S, et al. Yellow fever in Africa: estimating the burden of disease and impact of mass vaccination from outbreak and serological data[J]. PLoS Med, 2014, 11(5): e1001638.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1638
[20] WHO World Yellow Fever Situation Report, 2016.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47198/1/yellowfeversitrep 5Aug2016-eng.pdf.[2016-08-05]
[21] Martin RM, Maia Mde L, Farias RH, et al. 17DD yellow fever vaccine: a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n a dose-response study[J]. Hum Vaccin Immunother, 2013,9(4):879-888.DOI: 10.4161/hv.2298
[22] Campi-Azevedo AC,de Almeida Estevam P,Coelho-Dos-Reis JG et al. Subdoses of 17DD yellow fever vaccine elicit equivalent virological/immunological kinetics timeline[J]. BMC Infect Dis, 2014,14:391. DOI: 10.1186/1471-2334-14-391
Advancesinpreventionandcontrolofyellowfever
YANG Xiu-hui, YAN Yan-sheng
(FujianProvincialCenterof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Fuzhou350001,China)
Yellow fever(YF) is a natural focal disease transmitted by infected mosquitoes, which had caused epidemic in some areas of Europe and America port city in the history, bringing great disaster to human society.Since 40s of last century, a series of derivative strain of 17D vaccines, providing lifelong protection, had been vaccinated a large population who are traveling to or living in areas at risk for YF, which avoid the outbreak of the disease, appearing quiet stat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1990s, the disease had outbreak successively in Africa, tropical American areas and its nations.The mortality was even more higher than Ebola happened in 3 countries in West Africa between 2014 and 2015. In 2016-2017the large outbreak in Angola, Congo and Brazil, has claimed thousands of lives.Yellow fever has never occurred in Asia until the introduction of 11 cases by jet travel from Angola to China,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Yellow fever elimination initiative strategic plan for 2017-2026 was launched by WHO,mainly based on that 17D vaccine whi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is disease. The measures of controlling mosquitoes and vaccination programs,in particular putting great expectations for the latter, are the main measures for prevention the disease and achievement the goal of WHO elimination strategic plan.But strong guarantees of related countries and abiding by the provisions of the global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re also importa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and the recent epidemic outbreaks of yellow fever, vaccination and other prevention measures, hoping that the WHO elimination of the yellow fever epidemic strategy will achieve successfully in 2026.
yellow fever; natural focus disease; 17D vaccine; immune protection
yysh@fjcdc.com.cn
10.3969/j.issn.1002-2694.2017.10.001
闽科计〔2016〕9号社会发展引导性(重点)项目资助(No.2017Y0011)
严延生,Email:yysh@fjcdc.com.cn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 350001
373
A
1002-2694(2017)10-0853-06
Supported by the Guiding Project for Fujian Social Development(No. 2017Y0011)
2016-06-16编辑梁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