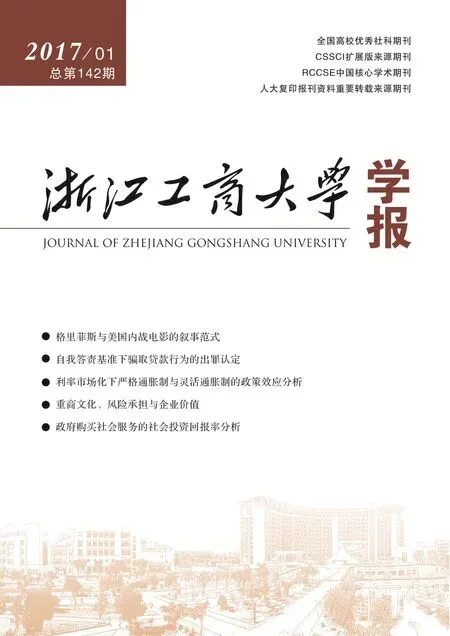格里菲斯与美国内战电影的叙事范式
2017-01-12李军
李 军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格里菲斯与美国内战电影的叙事范式
李 军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文章站在美国百年内战电影史的宏观视野,阐述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美国社会特别是南方社会对内战及战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和历史重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南方迷思”,重点分析这种历史迷思对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的直接影响,揭橥《诞生》创作主题的基本范式,以及对其后一个世纪内战电影的深远影响,从而为百年美国内战电影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化历史学的分析框架。
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内战电影;叙事范式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内战片在美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整个默片时代,大约拍摄了500多部内战电片[1]。有声电影兴起后,至今拍摄了200多部内战题材的长片。这样加起来,美国内战电影总数超过了700部。这还不包括数10部内战电视剧、内战纪录片,以及260多部反映内战老兵与内战纪念活动的新闻纪录片[2]。
本文站在美国百年内战电影史的宏观视野,阐述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美国社会特别是南方社会对内战及战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和历史重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南方迷思”,重点分析这种历史迷思对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以下简称《诞生》)的直接影响,揭橥《诞生》创作主题的基本范式,以及对其后一个世纪内战电影的深远影响,从而为百年美国内战电影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化历史学的分析框架。
一、 “失去的事业”:南方的内战集体记忆
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南方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树立起前邦联将士的塑像和纪念碑,仅弗吉尼亚州首府理士满的纪念碑街,相继耸立起罗伯特·李将军、斯图尔特将军、戴维斯总统、石墙杰克逊等一系列碑像。这种轰轰烈烈的“造像运动”是战后南方人重构内战历史记忆的重要努力之一。
在这场异常惨烈的战争中,南方人输掉了几乎一切,包括战前的庄园经济、悠久的奴隶制度、巨量的物质财富、高贵的自尊荣耀,还有28万死于战争的宝贵生命。战争结束后,对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南方精英们急于寻找一种对于这场战争的合理化诠释,为生活在战后废墟中的南方人提供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撑,同时也为争取北方民众对南方战后事业的认同与支持。
以罗伯特·李将军昔日部将加贝尔·欧利为代表的一大批邦联军队退役军人开始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文化精神层面的新的“南北战争”,他们通过出版战争回忆录、编辑报刊杂志、成立邦联退伍军人联盟等组织、修建纪念碑像、召开纪念大会、开展“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等方式,从南方人的视角重新书写内战历史,彰显南方在所谓的“正义之战”中的神圣事业与集体精神。与此同时,南方的政客、官员、商人也出于各自的目的,充分利用南方人的内战传奇作为政治资本。这两种力量声势浩大,相互激荡,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失去的事业”(the Lost Cause)的历史迷思。
从形式上看,“‘失去的事业’包括各种符号标识、神秘传说、典礼仪式、神学思想和各种组织活动,所有这些都为了满足战后南方人的重大关切”[3];从内容上看,所谓“失去的事业”历史迷思大致包括法理、社会、历史和精神四个方面。它将内战视为南方争取独立自由的正义事业,从而站稳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它以怀旧心理极力渲染战前南方社会的田园诗美景,美化奴隶制度下的南方生活,不断吟唱南方惨遭战争蹂躏的哀歌;它运用大量史实论证南方与北方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反差,强调南方人顽强作战、以弱胜强,终因势单力薄而不幸惜败;它突出南方人为保卫家园、捍卫理想而战的浩气长存,鼓舞战后南方人像前辈一样昂起高贵的头颅,重燃南方未来的希望。著名内战史学家格雷·葛尔格指出:
大多数直到战争后期仍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奴隶制共和国的前邦联分子,并不相信自己进行的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培植一种邦联集体记忆,将其战争的牺牲与失败涂上一层荣耀的光芒。这种内战诠释强调战前南方社会与奴隶制度的自然和谐,南方脱离的宪法基础,战争爆发的缘由,战时社会的特点,以及南方战败的原因。这种广泛流传的“失去的事业”邦联内战观念,直接产生于参战者的回忆录、退伍军人联盟的演讲、南方烈士墓的纪念活动,以及相关的内战文艺作品[4]。
在南方人声势浩大的政治活动与心理攻势下,越来越多的北方民众逐渐认同了南方兄弟的呼吁与诉求,不再用泾渭分明的是非态度看待这场已成往事的战争。尤其是经过1876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充满争议地登上总统大位,决定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战后重建的“结束”;对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战后重建的“失败”。此后,一股强劲的和解之风吹拂着美国南北大地。
在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所谓的“镀金时代”,出现了诸多政治腐败、道德滑坡等社会弊端,美国社会需要弘扬战争年代南北双方的正直、忠诚、爱国、献身精神,为民众提供正面教育的素材。因此,南北双方在内战历史认同上更趋一致。尤其是南方人,他们知道战败者的后代更需要了解先辈的光荣与梦想,更需要以“正能量”的历史教育激励人心。南方战后各种社会组织,如邦联退伍军人联盟、邦联之女联盟、邦联退伍军人之子等,纷纷自觉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使命。
19世纪80年代后期,南方兴起了一股内战儿童文学的热潮。在著名内战小说家奥普提克的作品中,“北军与南军战士为了各自的事业勇敢战斗,这种英雄主义精神远比双方的分歧更重要。一种新的美国国家意识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白人英雄主义基础之上”[5]。在注重“课外阅读”的同时,南方人没有忘记课堂教育的“主渠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精英们成立了“历史委员会”,对北方编印的内战历史教材予以谴责和抵制,同时加紧编写南方人自己的内战历史教科书。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南方人自己的“历史教育”在南方遍地开花,“失去的事业”迷思在邦联的旧土上深入人心。1875年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前邦联军队上校家庭的大卫·格里菲斯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并且对“失去的事业”迷思笃信无疑[6]。
于是,到了20世纪初,“南方人诠释的内战史”在南北大地上广为流布,并且成功地“感化”了北方同胞,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内战集体记忆”。而此时,电影艺术正好在美国兴起。
二、 内战默片:光电书写的历史
早期内战默片的片长大都为五到十分钟,最长不超过十五分钟。因此,当格里菲斯在1914年拍摄时长三个多小时的《诞生》时,许多人认为他在做一件近乎疯狂的事。
事实上,格里菲斯一点也不疯狂,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格里菲斯从小在壁炉旁聆听着父辈惊心动魄的内战故事,亲历了南方民众的“造像运动”,裹挟在纪念南方阵亡将士的巡街游行,感受着南北和解的脉脉温情,思索着“失去的事业”的深刻意义。可以说,战后南方内战文化的全面侵浸,造就了格里菲斯强烈的内战历史迷思。正如格雷·葛尔格在出版于2008年的《事业的胜利、失败与遗忘:好莱坞与大众艺术如何塑造我们对内战的印象》一书所说:
在战争、南北重新联合、南方重建的电影叙事中,格里菲斯(的电影)全方位地接受和反映了“失去的事业”历史迷思[7]17。
在《诞生》之前,格里菲斯已经拍摄了14部内战短片,包括《战斗》(The Battle)、《游击队》(The Guerrilla)、《造反有理》(The Fair Rebel)、《老肯塔基》(The Old Kentucky)、《关闭百叶窗的房子》(The House with Closed Shutters)等,借此寄托了自己的内战情愫。1911年,格里菲斯为比奥格拉夫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时长三十分钟的内战片《信任:一种内战传奇》(His Trust: A Civil War Saga),塑造了一个对奴隶主家庭无私照料的南方黑奴形象,极力展现南方黑奴与主人家庭之间牢不可破的忠诚关系。由于公司老板不看好“长片”,格里菲斯被要求把影片剪成两部时长各十五分钟的《信任》(The Trust)与《信任续集》(The Trust Fulfilled)。格里菲斯为此暗暗发誓,要独立自主地拍一部内战大片。当他读到托马斯·迪克森出版于1905年的畅销小说《同族:三K党的罗曼史》(The Clansman: An Historical Romance of the Ku Klux Klan),立刻被它深深吸引,决意将其改编成电影,并且声称“我仿佛已经看到了电影中三K党同族们白袍飘飘、策马疾驰的英姿”[8]98。经过加州南部历时一年的辛勤拍摄,在美国内战结束50周年之际,一部光电书写的内战迷思史诗片终于诞生了。
《诞生》是“一部因其臭名昭著而名垂青史的电影”[8]97。长期以来,格里菲斯为此饱受指责。其实,应该对这部电影中浓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负责的不仅是格里菲斯本人,更应该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美国内战迷思。正是在这种历史迷思的社会氛围下,才会有20世纪初托马斯·迪克森充满历史偏见的《内战三部曲》畅销小说,才会有百老汇红极一时的《同族》舞台剧,才会有格里菲斯不惜血本的《诞生》鸿篇巨制,才会有威尔逊总统观影之后“犹如一部光电书写的历史”的赞许。
当时美国观众对《诞生》的热烈追捧印证了这种内战迷思的强大影响力。该片以单场两美元的票价,一举创造了票房的奇迹。“影片在北方与西部大获其利,格里菲斯的拍摄技巧和出色导演令那里的观众口呆目瞪,影片中的种族主义倾向几乎不伤脾胃”[7]4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片在北方受到的欢迎程度超过了南方。直到1937年,《诞生》一直是美国票房最高的电影。“有人估计《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所产生的纯利润总共有2000万美元之多,这在电影方面是一个破天荒的纪录”[9]。由于长期受到“失去的事业”历史迷思的影响,格里菲斯以及当时大多数观众都确信,这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内战的史实。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强烈抗议这部“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电影时,格里菲斯言之凿凿地申辩说,他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这部电影严格遵循史实,许多场景甚至直接参照当年老照片进行布局,许多故事情节与父辈们当年亲口所述完全相符。事实上,格里菲斯知道大多数白人观众喜欢看什么,他努力迎合他们的口味,这就是他所谓的“真实”——只是观众的真实口味,而非历史的真实。
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社会现象,充分说明了内战迷思已经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对这场内战的集体意识形态。正如学者威廉·戴维斯所说:
迷思不是谎言,至少不是有意制造出来故意引人误解的谎言。迷思不是虚假。在几乎每个迷思的深层面上,都有些真理、事实,或自认为的事实。一些细微的基础事实被放大和夸大,以满足个人的、文化的、种族的、国家的需要与愿望,迷思就此产生[10]。
南方人民在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惜败”,为了获得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补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出种种战争迷思,最后形成了以“失去的事业”为核心的内战迷思。格里菲斯的《诞生》只不过是将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内战迷思成功地呈现在银幕上而已。
20世纪前二十年内战默片的“井喷”,正是美国内战迷思臻于完成并且广为流布之时,继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之后,电影成为美国民众表达内战情愫的最佳途径。刚刚崭露头角的美国电影人很快发现了这一现象,机敏地按照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内战集体记忆与情感倾向,连篇累牍地制作出一部又一部内战默片,“真实地”再现了昔日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极大满足了南北民众咀嚼这段历史的集体口味与审美心理,并且从中赚得盆满钵满。格里菲斯敏感地把握了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态度与评价,将几乎被普遍接受的内战迷思呈现在大众喜闻乐见的银幕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银幕上传播内战迷思的真正电影“导演”并不是大卫·格里菲斯或者托马斯·英斯这类内战默片先驱们,而是共同酿制内战历史迷思的美国民众,是他们决定了《诞生》等内战默片的历史基调和叙事定式。
三、 格里菲斯:一种内战电影范式的诞生
格里菲斯的《诞生》以电影艺术的形式,系统而形象地呈现了南方人内战迷思的基本要义。本文梳理了《诞生》十种叙事范式,来印证《诞生》主题思想与“失去的事业”历史迷思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是“老南方”范式。《诞生》竭力刻画一幅战前“老南方”的美好图景,以激起观众尤其是南方人对祖辈生活方式的怀旧情结。
影片一开始,格里菲斯就将镜头逐个推给卡梅隆一家的每个成员,男的神采奕奕,女的端庄美丽,老的安祥平静,小的活泼快乐,就连两只小狗也懒洋洋地躺在主人身边嬉戏,整个一幅“老南方”快乐大家庭的典型画面。“老南方”的快乐当然少不了黑人。在格里菲斯的镜头中,黑奴们劳作时埋头苦干,休息时载歌载舞,操持家务的黑奴们更是忠诚耿耿、尽心尽责。观众从黑奴的笑容中获得了明确的信息:黑奴很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不想有任何的改变,战争对“老南方”生活方式的破坏,就连黑奴都是一种损失。可以看出,格里菲斯以怀旧文学的方式,极力渲染“老南方”的温馨岁月,从而为南方人的殊死血战赋予一种正义价值与崇高意义。
第二是“无辜者”范式。《诞生》在叙述内战起因时采取了一种含糊其辞的方式,引导观众将内战发动者定位在北方人身上,把南方人描绘成内战的“无辜者”。
战争来临之际,银幕上出现了这样的字样:
风暴正在聚集。自1781年英军康沃利斯爵士向各殖民地投降以来所建立的各州主权,正受到新的国家政权的威胁。
场景很快切换到一个读报场面:卡梅隆和史东曼两家的年轻人一起围着老卡梅隆夫妇读报纸。报纸的标题是:
如果北方举行选举,南方就将脱离。
接着银幕文字又出现了:
林肯签署命令,首次招募75000名志愿军人。
镜头转到白宫总统办公室:林肯与一大帮议员、官员、阁僚在一起,亲手签下了募兵令。
银幕文字马上作了如下说明:
亚伯拉罕·林肯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总统办公室招募志愿兵,将国家权力强加于州权之上。
在格里菲斯的镜头里,没有萨姆特堡的炮声,没有奴隶制的罪恶,没有蓄奴州的脱离,只有联邦政府蛮横无理的征兵令。这一切都暗示,发起这场战争的责任在北方而非南方。
第三是“悲剧英雄”范式。在战争场面的刻画上,格里菲斯之所以要把小说《同族》中原本只有半页纸的彼得斯堡战役,渲染成一场足足十分钟的战争大戏,就是为了生动展示一幅南方将士骁勇善战却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倒下的悲剧英雄画卷,体现南方人在战争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精神。
影片浓彩重抹地描绘了“小上校”本率领残兵败将连续突破北军重兵把守的两道防线,继续奋勇突进,最后硬生生把邦联军旗插入第三道防线北军大炮炮口的场面。事实上,这个插旗的动作近乎荒唐,毫无军事意义,却表现了有心杀敌、回天无力的南方人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格里菲斯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在这场由北方人“挑起”的战争中,南方人义薄云天,虽败犹荣,而北方人则人多势众,胜之不武。
第四是“受害者”范式。《诞生》极力刻画战争以及战后重建对南方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不幸卷入战争的普通平民遭受的痛苦。
格里菲斯说过,他要用电影展示战争的残酷和可憎。如果说,格里菲斯让卡梅隆与史东曼两家的小儿子并排倒在血泊中,是要展示战争给南北民众带来的不幸;那么,当格里菲斯用被火光染红的夜空表现谢尔曼“向大海进军”时,他要极力渲染的是北方大军过境带来的巨大破坏。
在《诞生》第二部中,格里菲斯极力彰显的另一个主题是南方在战后重建中遭受的蹂躏和破坏,“破坏者”就是“翻身得解放”的黑人。格里菲斯运用各种史籍、传说,甚至杜撰子虚乌有的故事,来表现黑人政客与黑人士兵各种为非作歹的恶行,以及白人为此遭受的灾难和痛苦。至于格里菲斯将绝大多数黑人描写成凶巴巴、色迷迷,一副无知无畏、粗暴蛮横的嘴脸,更是肆意虚构。整部电影的种族主义色彩也主要体现于此。
第五是“南北家庭恩怨”范式。《诞生》将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冲突,微缩为一个南方家庭与一个北方家庭之间的恩恩怨怨。这种叙事结构单纯从艺术角度讲确实是十分取巧的,能够简单有效地通过两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来表现南北之间的恩怨情仇。然而,格里菲斯的用意不限于此,他的这种故事结构是要向广大观众传达“南北白人一家亲”的意蕴。
第六是“兄弟之战”范式。这种范式是“南北家庭恩怨”范式的进一步深化,就是在角色定位上将战场上相互厮杀的南北将士设计为亲如兄弟的密友。《诞生》特地安排了两个令人难忘的情节:在前线激烈的战斗中,查姆斯与小卡梅隆兵戎相见,最后倒在一起,命丧疆场;在彼得斯堡战场,菲利普将奄奄一息的本紧紧搂在怀里。这一生一死的生动画面,充分展示了南北军人之间兄弟般的生死感情,用感人至深的镜头语言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兄弟之战”。
第七是“南北之恋”范式。如果说“兄弟之战”彰显了南北敌对军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南北之恋”则表现了南北敌对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诞生》贯穿始终的男女情感故事是两个南北家庭儿女——本与爱茜、菲利普与玛格丽特——两对情侣之间可歌可泣、真挚动人的爱情,这种超越南北政治是非的伟大爱情既表现了白人“同族”同室操戈的悲剧,也说明南北之间应该化干戈为玉帛。
第八是“坏蛋”范式。无论是“南北之恋”还是“兄弟之战”,格里菲斯想要表达的是,内战是一场发生在“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战斗。当然,作为一部影片,按照叙事逻辑和戏剧冲突的要求,必须要有“坏人”,《诞生》设定的“坏人”或曰反面角色就是黑人士兵与混血黑人官员,其代表人物就是嘎斯和林奇。
最让白人头皮发麻的黑人邪恶莫过于“性”的问题。格里菲斯重点设计了嘎斯施暴芙萝拉和林奇觊觎爱茜两个情节,将丑化黑人形象推到了极致。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现代象征主义导演的先驱,格里菲斯电影中的许多人物、情节、道具都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黑人嘎斯施暴的意象内藏着一种隐喻:既象征着内战就是一场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强暴,也象征着战后重建中整个黑人种族对南方白人社会的强暴。
第九是“兄弟阋于墙”范式。《诞生》煞费苦心地刻画了南北白人联手打击“共同敌人”的情节,以“兄弟阋于墙”的方式表达了南北白人面对共同之敌,完全应该也能够摒弃前嫌、一致对外的主旨。
在影片最后那场小木屋战斗的桥段中,北军上尉菲利普、老卡梅隆等人拼死抵抗屋外黑人士兵的进攻。这时,银幕上打出一行字幕:
为了保卫雅利安人的天赋权利,曾经的南北敌人重新联合起来了。
紧接着就是本率领三K党徒“白袍飘飘”纵马驰救的场景,这便是电影界长期以来津津乐道的所谓“最后一分钟营救”,格里菲斯通过两个叙事空间平行动作的交叉剪辑,让观众在令人窒息的紧张悬念中,体验南北白人兄弟同仇敌忾,对黑人士兵大开杀戒的畅快淋漓。正如布鲁斯·查德威克所说:
最后,每一个人都与他人和平相处了,这就告诉观众,尽管经历了一场南北战争,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除了黑人之外[8]112。
第十是“宽宥者林肯”范式。《诞生》不遗余力塑造了林肯仁慈的“宽宥者”形象,格里菲斯借此暗示北方人民应该宽宥南方,鞭挞国会激进派在战后重建中对南方的无情欺压。
林肯宽宥士兵的故事,在早期默片中时有出现。在1908年的《蓝色与灰色》(The Blue and the Gray)、1913年的《战争的代价》(The Toll of War)、1914年的《睡着的哨兵》(The Sleeping Sentinel)等影片中,林肯分别宽宥了南军士兵或失职的北军士兵。《诞生》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突出了林肯宽宥将被处死的本这场戏,暗示这个国家应该像林肯一样,宽宥所有参与战争的南方叛逆者,将这场战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彻底了结。
在《诞生》中,格里菲斯花费很大笔墨,第一次将林肯遇刺的场面呈现在观众面前,他的用意并不是猎奇,而是要表现一个重要的主旨:作为一位伟大的“宽宥者”,林肯之死是南方的一场灾难,如果林肯继续主导战后重建,南方人绝不会落到如此悲惨境地。顺着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正因为林肯不幸去世,北方激进政客主导的南方重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南方人因此组织三K党奋起反击,也是迫不得已的。正如弗兰克·维塔所说,“如果林肯活着,他将致力于战后南方和解——这样一种林肯的仁慈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和历史叙事的主题,同时也是‘失去的事业’迷思的中心思想”[11]。
《诞生》以上十个方面的叙事范式,总体上构建了一种内战电影的格里菲斯模式:通过上述十种范式演绎内战及战后重建过程中南北双方的矛盾冲突,巧妙回避南方人当年分裂国家、挑起战争的历史责任,竭力彰显南方人追求自由、顽强奋斗的可贵精神,生动展示南北白人作为命运共同体捐弃前嫌、一致对敌的兄弟情谊,最终体现南北双方从冲突走向和解、共同创建一个白人至上的新生国家的完满结局。正如布利安·维尔斯所说:“邦联失去战争,但是通过格里菲斯的电影,战争中被击碎的南方正在赢得和平”[12]。
格里菲斯的内战电影模式反映了当时美国民众的心声。在内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许多美国民众希望南北之间“相逢一笑泯恩仇”,希望消除南方人多年以来内心深处的伤痛。“北方的出版商发现他们的读者渴望医治战争的心理创伤,渴望读到有关战前南方生活的书籍”[8]25。美国战后文学,包括诗歌、小说等,都倾向于散播这种历史迷思。格里菲斯运用电影“新媒体”为这样的社会心理找到了一种巧妙投射的载体,这是他敢于投入巨资拍摄这部时长三个多小时巨片的重要原因。
还应看到,在格里菲斯准备拍摄《诞生》之际,正值第一次大战前夕,美国正逐渐成为一个走向世界的强国,需要南北双方忘却过去恩怨、共同面向未来。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下,一部反映内战题材的鸿篇巨制将主题定位在“南北和解”的基调上,应属情理之中;而美国白人观众予以普遍的认同,也不在意料之外。
四、 格氏模式:历久弥新的影响力
格里菲斯的《诞生》根植于战后南方人内战迷思的沃土之中,反过来又以大众视觉媒体的传播方式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民众对于内战历史的认知,而且他所确立的十种叙事范式也深远地影响了后来好莱坞编导们的内战片创作模式。
拍摄于1939年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通过更加细腻精致的刻画,将格里菲斯镜头下的“老南方”怀旧情结模仿和放大到了极致。《乱世佳人》“美化了‘老南方’社会,并且深受‘失去的事业’迷思影响,极力表现了无辜的南方人残酷地遭受到占压倒优势的北方人攻击和蹂躏”[13]。
面对战争造成的一片废墟和荒芜,斯佳丽脑海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塔拉庄园。影片将塔拉庄园隐喻为南方人的故土,那是南方人的精神家园,就像斯佳丽父亲早先所说的,“土地是世界上唯一了不起的东西”,是“唯一值得为之工作、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东西”,也是南方人再次重新崛起的地方。后来在诸如电视连续剧《南北乱世情》(North and South)等不少影视剧名片中,这种熟悉的老南方怀旧画面不断重复出现。
《乱世佳人》借助彩色与有声两种当时尚属新颖的艺术手段,在表现战争与战后重建给南方人带来的痛苦方面可谓技高一筹。当葛底斯堡战役的消息传到亚特兰大,导演设计了大街上的一场众人争抢死亡名单的重头戏,此时军乐队奏响了《迪克西》音乐,为凄切的场景平添了一种悲壮。紧接着,影片通过斯佳丽与媚兰在临时充作医院的教堂里照顾伤兵的一个个惨不忍睹的镜头,把战争的残酷与无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最经典的一幕当属亚特兰大火车站遍地伤兵的场面:镜头随着斯佳丽的步履不断推移,场面越来越大,伤兵越来越多,最后定格在一面高高飘扬的邦联战旗上——象征着无数南方战士为邦联浴血奋战,最后倒在了邦联战旗之下,这是对“失去的事业”的生动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乱世佳人》也设计了一个北军士兵对斯佳丽谋图不轨的场景,被斯佳丽一枪毙命。后来的《冷山》(Cold Mountain)以及电视连续剧《南北军将士》(The Blue and the Gray)中也再次出现类似的镜头,不能说与格里菲斯的影响毫无关系。当然,后三部影视剧的北方“坏人”士兵都换成了白人。
在后来诸多内战电影中,渲染战争及战后重建对南方的破坏依然是不变的主题,而南方人战后反抗压迫的斗争则是好莱坞津津乐道的题材,从《乱世佳人》到《美国逃犯》(American Outlaws),可谓络绎不绝。当然,在战后重建中,黑人政客与黑人士兵不再是南方破坏者的主角,毕竟美国社会的种族平等意识在逐步提升。
“兄弟之战”范式可以说是后世内战电影屡试不爽的故事结构。当然,这里所谓的“兄弟”,不局限于血缘或亲属关系,当年西点军校的“同袍”也算亲如手足的“兄弟”。电影《圣非小路》(Santa Fe Trail)、《燃烧的土地》(Class of '61)和《南北乱世情》等都是典型之作。
“兄弟阋于墙”内战片可以说达到了层出不穷的地步,套路和情节当然也更趋复杂。当然,在不同的拍摄时代,这种“共同的敌人”是不尽相同的。在《八虎将》(Rocky Mountain)、《西部两面旗》(Two Flags West)、《亚利桑那伐木者》(Arizona Bushwhackers)、《血战勇士堡》(Escape from Fort Bravo)、《箭在弦上》(Finger on the Trigger)等影片中,南北双方共同对抗的敌人是印第安人;在《擒贼擒王》(Rio Lobo)、《龙城龙将》(Best of the Badmen)、《马革裹尸还》(They Died with Their Boots On)等影片中,南北双方联手清除的败类是白人坏蛋、奸商、政客;在《无懈可击》(The Undefeated)、《邓迪少校》(Major Dundee)等影片中,南北双方一致对付的是墨西哥人。随着民权运动的推进,黑人已经不在“坏人”之列了。
“南北之恋”一直是内战电影最重要的爱情叙事范式,如《魔鬼骑兵队》(The Horse Soldiers)、《重围浴血战》(Hangman’s Knot)、《牡丹花下》(The Beguiled)以及《血战勇士堡》等。当然,这些爱情故事复杂程度与感人指数远远高于格里菲斯当年的作品。
好莱坞电影对林肯情有独钟。据统计,林肯至少在150多部电影、50多部电视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中出镜,次数超过了任何一个美国人[8]153。格里菲斯将林肯称为“伟大的心灵”,在他拍摄于1930年的《林肯传》(Abraham Lincoln)中,再次出现了林肯宽宥北军士兵的桥段。受此影响,拍摄于1935年的《小上校》将林肯赦免南北军人的范式推向了高潮。其后的短片《林肯在白宫》(Lincoln in the White House)也表现了林肯宽宥站岗时入睡的威斯康星士兵。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跨越4月5日》(Across Five Aprils)还在使用这样的伎俩。
尽管美国内战电影在不同时期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但在这些印记的背后常常可以发现格里菲斯《诞生》叙事范式的影子。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对美国百年内战电影的文化分析是难以想象的。
[1]RUSSELL W B.Civil War Films For Teachers and Historians[M].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8:2.
[2]SPEHR P C.The Civil War in Motion Pictures: A Bibliography of Films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97[M].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61.
[3]WILSON C R.Baptized In Blood: The Religion of the Lost Cause, 1865—1920[M].Athen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11.
[4]GALLAGHER G W, NOLAN A T.The Myth of Lost Cause and Civil War History[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1.
[5]FAHS A, WAUGH J.The Memory of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Culture[M].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86.
[6]LEHR D.The Birth of A Nation: How a Legendary Filmmaker and a Crusading Editor Reignited America’s Civil War[M].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4:32-33.
[7]GALLAGHER G.Cause Won, Lost, Forgotten: How Hollywood and Popular Art Shape What We Know about the Civil War[M].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8]CHADWICK B.The Reel Civil War[M].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9]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M].徐昭,胡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135.
[10]DAVIS W C.The Cause Lost: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Confederacy[M].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175.
[11]WETTA F J, NOVELLI M A.The Long Reconstructio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in History, Film, and Memory[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32.
[12]WILLS B S.Gone With the Glory: The Civil War in Cinema[M].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13.
[13]SACHSMAN D B, RUSHING S K, MORRIS R.Memory and Myth: The Civil War in Fiction and Film from Uncle Tom’s Cabin to Cold Mountain[M].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7:241.
(责任编辑 杨文欢)
Griffith and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the American Civil-War Movies
LI Jun
(School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vie history of the centennial American Civil War,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vil War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nation, especially the southern states, where the “Southern Myth” was born. I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rect impact of this myth on Griffith’sTheBirthofaNation, exposes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 theme, and demonstrates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following Civil-War movies within the century; henceforth it provides a cultural histor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American centennial Civil-War movies.
Griffith;TheBirthofaNation; Civil-War movies; narrative pattern
2016-09-30
李军,男,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文化史研究。
I235
A
1009-1505(2017)01-0005-08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