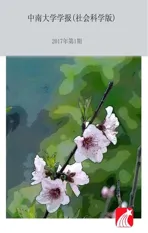主体建构的叙事时间化
——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
2017-01-12王正中
王正中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主体建构的叙事时间化
——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
王正中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人作为主体,是被建构出来的,而叙事时间化则是主体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叙事时间化的作用,弗洛伊德的本我才转化为现实中的自我;本我中起支配作用的快乐原则才转化为自我中现实原则支配下的快乐原则。而主体的叙事时间化则是通过叙事认同而获得的,换言之,正是在叙事认同的作用下这种叙事时间内化为主体的叙事身份。而叙事认同发生的动力则来自于叙事力,即叙事中所包含的主体需求。简言之,通过叙事力而发生叙事认同,通过叙事认同而获得叙事时间,通过叙事时间主体获得了现实形式。
主体建构;叙事时间;叙事认同;叙事力;弗洛伊德
一、叙事时间:自我的形成
主体生存于世,必然受时空的约束。而与空间相比,时间对于主体起着更为根本的规约作用,因为一切变化都是在时间中展开。因此,时间对于主体的塑形也就比空间更为深入。一般认为,时间分为两类: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1](239)保罗·利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其概括为:现象学时间和宇宙论时间,并认为“叙事时间像一座桥梁跨越在由于推理断裂而恒常开放的现象学时间和宇宙论时间的缺口之上”[2](244)。此外,利科还指出:“时间的实际重构通过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的相互交织而形成了人的时间。”[2](180)换言之,正是叙事时间将外在的物理时间与内在的意识时间、真实和想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安东尼·保罗·克比进一步认为,“生命内在地具有一种叙事结构,一个当我们想起我们的过去和我们可能的将来时我们所明白的结构。”[3](40)这即是说,主体内在地具有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正是叙事时间。戴维·卡尔则以胡塞尔“前摄−滞留(protention-retention)”的内时间意识理论为基石,认为现实之中内在地具有一种叙事形式,“叙事形式并不是一个包裹什么东西的服装,而是内在于人类经验和行为之中的结构。”[4](65)这种叙事形式主要指叙事的时间形式。而这种叙事时间与主体具有何种内在的关联,它的结构是什么,它对于主体而言又意味什么?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我们发现叙事时间正是自我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通过叙事时间将潜意识的本我转化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自我。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本我在潜意识中运行,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而无法进入现实;自我在现实中有意识地运行,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但自我是由本我转化而来,“自我就是本我的那一部分,即通过知觉—意识的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那一部分”[5](126)。并且由本我为自我提供动力,弗洛伊德常用骑手和马来类比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马提供运动能量,而骑手具有决定目标和引导这个强健动物的活动的特权。但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常出现不理想的情形:骑手被迫引导马在马自己想走的路上奔驰。”[6](48−49)即本我为自我提供动力,自我驾驭本我,但也常存在驾驭失控情况。这就是说,自我是由本我转化而来,并从本我那里获得动力。但由于自我受现实原则支配,而本我却受快乐原则的支配,所以,自我从本我那里获得动力,是以为本我提供快乐为前提的。换言之,自我需要在现实原则之下去满足本我的快乐。
在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主义论评》中,总结了潜意识的六个特征,即原始性、冲动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非道德性和非语言性。[7](136)这六个特征中涉及现实形式的有语言性、逻辑性和时间性。而在本我自我化过程中,与语言和逻辑相比,时间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正是时间组织了本我中占支配地位的快乐原则,而非语言或逻辑。但这种时间既不是纯粹客观的物理时间也并非完全主观的意识时间,而是如利科所言是“居中调节(Mediate)”的叙事时间。同时也只有在叙事时间中这些形式才可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进一步讲,正是叙事的时间结构将追求快乐的本我编织成现实中的自我。
弗洛伊德曾多次表示过潜意识是没有时间性的,只有意识系统才有时间性。“Ucs.系统的进程都无时间性,即它们不按时间顺序进行,也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与时间不发生任何关系。相反,在Cs.系统中的活动,与时间才建立起联系。”[8](361)在《超越快乐的原则》中,弗洛伊德更明确地指出,“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本身是无始无终的。这就意味着,首先,它们不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时间在它们身上不发生变化,时间的观念也不适用于它们。”[9](22)在后来的《精神分析新论》中,他进一步指出,“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时间的观念相对应,也没有时间推移的认识。”[6](46)换言之,本我是无时间性的,时间是自我的工作方式,“自我依靠它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5](148)因此,潜意识的本我转化为有意识的自我的关键,在于赋予本我以时间结构,从而使得本我处于现实意识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时间结构,如前文所述恰是叙事的时间结构。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完全服从于现实原则,而同样是在寻求快乐的满足,并且这种寻求往往并非是潜意识的。所以,本我与自我是一体的,自我是服从现实原则下的本我,是叙事时间化了的本我。
在分析作家与白日梦的关系时,弗洛伊德指出愿望的时间结构正是通过幻想而被串联起来:
一般来说,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幻想似乎徘徊在三种时间之间——我们的想象经历的三种时刻。心理活动与某些现时的印象相关联,与某些现时的诱发心理活动的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可以引起主体的一个重大愿望。心理活动由此而退回到对早年经历的记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在这个时期该重大愿望曾得到过满足,于是在幻想中便创造了一个与未来相联系的场景来表现愿望满足的情况。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叫做白日梦或者幻想,其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和某段经历的记忆。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串联在一起了,愿望这根轴线贯穿其中。[10](62)
换言之,梦是愿望的满足,而叙事作品则类似于作家的幻想或白日梦,它的动力同样也是“尚未满足的愿望”[10](61)。在《释梦》中,弗洛伊德提出梦的材料往往是由近期的清醒意识所构成,而梦的实际来源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幼儿期。与此类似,作家的创作也是由近期的事件所诱发,而其根源却深埋在“童年时代的经历”,是“童年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替代物”[10](64)。因此,作家的创作是将在现实中无法体验的童年游戏中的快乐编织进现在的叙事作品中,通过叙事作品构造的将来场景来满足过去的愿望。这就是说,过去的快乐被放入到现在的叙事幻想所描绘的将来场景中。可见,叙事通过真实与想象的融合,而将本我的快乐原则和自我的现实原则融入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结构之中,从而使得潜意识的本我转化为现实中的自我。
然而,这种叙事时间并不仅仅运行在叙事作品之中,它也同样组织着现实中的主体。易言之,现实中的主体同样通过叙事的时间结构,让本我时间化到现实中来——将本我组织进现实生活而成为自我。即叙事通过对本我愿望的时间化,使得本我具有了一种符合现实的时间结构,将本我的力比多及起支配作用的快乐原则组织进愿望的时间性结构中,从而使其符合现实原则。本我在这种叙事时间中,为自我提供了动力,它将原始的、冲动性的及非道德性的动力,导入线性的时间结构中,并将其组织进未来,将本我无方向的“爆动”转化为由未来定向的牵动。这种动力主要来自于快乐的体验,即把本我追求即时的快乐,放入到未来符合现实的情境中去,并由这种未来的快乐体验,牵引着自我,为其行为提供动力。从而尽可能地缩短这种时间距离,期待快乐的来临。在这个过程中,本我逐渐转化为自我:从原始、冲动、混乱的无时间性转变为有序的时间性,从非理性的情欲转变为合乎逻辑的理性。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便是这种生活叙事的典型,信徒在“此岸”的磨练是为将来进入“彼岸”的“极乐世界”所做的功课,甚至为了早日成功地进入“极乐世界”而实行苦修,将当下本我的快乐转移到未来之中。而这个“极乐世界”却只是想象中本我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世界、快乐世界。然而,现实生活中本我的时间化,实际却是来自于叙事中本我的时间化,而这种源流关系的关键则在于叙事认同。
二、叙事认同:时间的内化
叙事认同来自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弗洛伊德认为认同作用是“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结果,在某些方面,第一个自我像第二个自我那样行动,模仿后者,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后者吸收到自己之中”[6](40)。简言之,认同作用就是一个自我在某种动力或引力的促发下,使自身成为另一个自我的过程。而叙事认同则是叙事接受者为叙事中某一人物所吸引,使自身成为该人物的过程。然而,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fication)与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却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叙事身份是从叙事中所获得的那种在时间中一致性的身份,是某个“谁”;而叙事认同则强调的是叙事身份所获得的方式或过程。换言之,叙事认同形成叙事身份,叙事身份是叙事认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的认同作用主要分析的是超我的形成过程,而这只是叙事认同的一部分。换言之,叙事认同不仅建构了超我,它还建构了叙事身份。利科认为叙事身份是“凡人皆有的通过叙事的中介功能而获得的那种身份”[11](188),这种叙事的中介功能主要是指“情节的中介功能。这种中介功能意味着‘异质综合’的概念”[12](176)。即,叙事身份是通过情节编织的“异质综合”功能而形成的一种自我统一性。利科进一步认为这种叙事身份“并不局限于文本之内。作为一种动态身份,它出现在文本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交叉的地方”[12](183)。即是说,叙事身份不仅是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它还同样是现实中个体及群体的身份(Individual and Community)。而叙事认同则是沟通故事世界①与读者世界的主要方式,从而通过故事世界中的叙事身份建构起读者世界的叙事身份。
弗洛伊德的超我便归属于这种叙事身份,在叙事身份中就已经包含了超我的道德责任。弗洛伊德认为形成超我的认同作用主要包含三种内化,即:外部的压抑力量内化为内在的罪疚感;外部的“父亲”内化为自身成为“父亲”;外部的传统价值判断内化为自身的超我。而这三种认同实际上均是通过对叙事中人物的认同而形成的。也即是说,超我主要是通过叙事认同中的人物认同而形成的,而除人物认同之外,我们认为叙事认同还包括主题认同和情节认同。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三种叙事认同。
人物认同,是基于读者与故事人物共同需求而言的,同时,通过对人物思想行为的认同而期望获得和该人物同样的需求满足的快乐。叙事身份的形成,往往直接来自于对叙事作品中人物的认同。例如,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郭靖,虽然资质平庸、天性愚钝,却胜过了众多英俊潇洒、天资聪颖的人物,如杨康、欧阳克等,不但赢得了黄岛主的宝贝女儿黄蓉的垂青,还练成了绝顶武功,赢得世人的尊敬。而读者对他的认同,则一方面奠基于与人物一样都是资质平庸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则为其获得满足的快乐所吸引,不但赢得了大家闺秀,还赢得了个人的成功,这些都是需求满足的快乐。前者是认同的基础,后者则是认同和模仿的动力。在认同的过程中,读者通过认同郭靖的行为思想(勤奋、单纯、厚道、安分守己及保家卫国)进而希望成为甚至取代郭靖,获得和他同样的需求满足的快乐。而该人物的这些行为思想往往就内化为读者的超我,使得读者具有勤奋、单纯、厚道、安分守己及保家卫国等道德教化原则。
主题认同,即在叙事作品中总会表现出某种主题倾向,这种主题倾向由人物和情节共同推动。叙事,是对事件的叙述,而事件往往都围绕某些具体问题展开,通过在这些问题中人物的选择与判断导致事件的发展。这些问题往往就构成了叙事作品中的主题,如爱情、亲情、友情、道德、信仰、伦理和法制,等等。这些主题有些通过人物的立场和命运而直接解决了,例如近来众多的韩剧、肥皂剧展示了爱情与亲情、爱情与法制、爱情与利益等的冲突,其中绝大多数以主角对爱情的选择而阐明了故事的主题,让读者认同对爱情的追求。而另外一些故事却没有解决,仅仅通过人物而引起读者对问题的注意或以开放性结局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前一种主题认同往往与人物认同类似,直接有助于叙事身份的形成和强化;而后一种认同却是一种开放性认同,它并不直接形成或强化叙事身份,而是“引诱”叙事身份的自我塑形。如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13](286)。就悲剧《安提戈涅》而言,安提戈涅代表的亲情与克瑞翁代表的国法之间冲突的悲剧结局,并没有暗示任何一方的胜利,而只带来双方需求满足的破灭。因此,它并没有直接给读者对需求满足的认同,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进而获得需求的满足。因此,这类开放性认同,实际上是“引诱”读者自己去塑造叙事身份。
在人物和主题认同之外,还有种情节认同,也即对叙事时间结构的认同。实际上,在人物和主题认同中就已经含有情节认同的要素,因为它们自身就已经具有了一种时间结构在内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六个成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14](37)。情节实际上正是叙事中事件的组织方式,对情节的认同正是对事件发展方向的认同。海登·怀特依据诺斯普斯·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的线索,认为“至少存在四种情节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或许还有其他模式,如史诗”[15](13)。而这些情节本身就赋予故事以某种意义。当叙述者为所讲述的本事选择一个情节的时候,就已经赋予这个故事以意义。情节本身就向读者展示了这个故事是“史诗、浪漫剧、悲剧、喜剧或闹剧”的[16](61),这个情节类型自身就是读者从该叙事中所获得的意义。克比也认为,“通过叙事情节编织的各种形式,我们的生命……获得了意义。”[3](4)实际上,情节正是时间化愿望的组织方式,展示了愿望满足的结局。情节认同,就是对本我自我化中时间化方式的认同,通过情节的认同获得本我时间化的方式。例如,在喜剧及一些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中,会促使人盲目地对其情节进行认同,从而成为建构道德的有效手段。我国传统戏曲作品多是大团圆的结局,对这种情节的认同往往会形成一种盲目信仰的思想,从而顺从压抑本我的倾向,建构起高度强化的叙事身份或道德感。我国封建社会得以稳定的统治,离不开对这些喜剧作品的认同而形成的叙事身份或道德感。而在一般的悲剧作品中,本我时间化的方式并没有满足生本能,而是遭到死本能的压抑,从而读者的自我无法对其直接认同,这与开放性主题认同类似,往往会引起读者的注意而自己去探索满足需求的时间化方式。正如马大康教授在《文学时间研究》中所指出的,“悲剧时间也就成为最鲜明地展示着人的生命力和人性深度的时间,它为人的生命所储满,显现为真正的人的时间。”[17](98)可见,叙事情节是本我愿望时间化的事件组织,通过对情节的认同来获得本我快乐进入现实的时间方式,满足本我的欲望。喜剧往往直接引起读者认同,而悲剧认同则是引导读者自己形成本我时间化的方式。
三、叙事力:认同的根源
在这些叙事认同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叙事认同中总存在着一个牵引力。我们将这种叙事中存在的引起读者认同的动力称为叙事力。正是这种叙事力吸引着读者走向故事世界,并对其发生认同。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分析认同作用时指出:“一个人的自我在某一点上……感知到与另一个人的自我有意义的类似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认同作用。”[18](79)这里提出了认同作用发生的关键“有意义的类似性”。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发生认同是基于这二者之间的“类似性”,这是认同发生的基础;而“有意义”则是在“类似性”基础上认同发生的动力。就弗洛伊德而言,这种“有意义”主要是和本我的快乐原则相关,是生本能或死本能满足中的快乐。然而,在现代心理学看来,这种动力显然忽视了人类文明高级的精神动力作用,而仅仅将人还原为动物。因此,我们在此引入马斯洛纠正弗洛伊德而提出的“整体动力理论”[19](40),即五个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这种动力,同样适用于叙事认同。换言之,叙事认同的动力来自于叙事作品中人物获得满足的需求,它们共同构成了叙事力。具体而言,即现实中的自我受叙事作品中另一自我获得满足的需求的吸引,而对其认同试图获得和该自我一样的需求的满足。前文人物认同的分析中,读者对《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认同,就是在这种叙事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在此,我们不打算逐条分析马斯洛的五层需求在叙事中的表现,而仅以弗洛伊德的本能动力为代表,来分析叙事力在主体建构中的引力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人具有两种本能:生本能和死本能。生本能的“目的在于把里面分散着的生物物质微粒越来越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生命复杂化,同时它的目的当然就是保存生命”[5](137),它包括自我保存和爱欲两种本能。死本能即“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状态”[5](137),分为两种倾向,一是对外表现为攻击、破坏欲;一是对内表现为自残、自虐或自杀。然而,就现实中的自我而言,它的主要任务却是自我保存,也即生本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力不包括死本能,与生本能在自我中运行不同,死本能是在本我或超我的潜意识部分中对读者构成吸引的。
而叙事力在生本能的两个方面(爱欲和自我保存)与死本能的两个方面(向内和向外)相互作用下,依据生本能的两个方面是否获得满足,可分为三种情况:同时满足、满足其中之一和都不满足。同时满足主要表现为多数喜剧及大团圆结局的作品;满足其中之一,表现为事业与爱情之间的抉择,而由于爱欲更为根本,因此,尽管事业失败但赢得爱情却仍然是喜剧,而“赢得了天下输了她”则往往带有悲剧色彩;而两者都没有满足则主要是悲剧作品。在叙事认同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简略触及喜剧与悲剧的分析,下面结合叙事力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喜剧及一般大团圆结局作品中,这种叙事力或生本能的两个方面都得到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梦中都有个“我”存在,同样,“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读者兴趣的中心,作家试图用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法来使该主角赢得我们的同情。”[10](63)而这个主角往往是“刀枪不入、英雄不死”[10](63)的,这种特性正展示了主角自身的自我保存的强大,而读者通过对主角的认同,从而将主角的自我保存赋予到自己身上来,仿佛具有和主角一样的能力。这在我们观看一些喜剧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侦探类故事及大部分好莱坞电影中,往往伴随着一种有益于生本能的快感体验。
就悲剧作品而言,其中的叙事力或生本能往往为死本能所压抑或取代,因此,其叙事认同依据死本能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这里的死本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向外的和向内的。在一般的悲剧作品中,主角的生本能遭到自身之外(如来自其他人物的攻击、破坏,或来自传统价值对爱欲的压抑等)的死本能的压抑,这是向外的死本能;而在另外一些悲剧作品中,则是主角自身的死本能取代了自身的生本能,这是向内的死本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死本能则是来自于外在死本能对主角生本能的压抑。尽管哈姆雷特自身犹豫不决的性格增加了悲剧效果,然而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其叔父克劳狄斯的图谋不轨,是哈姆雷特之外的他人的死本能给他的生本能造成的威胁。而在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其死本能则来自于维特自身。维特因对已订婚绿蒂的爱恋,而无法将自身生本能转化进现实,进而诸事受挫,其自身的生本能无法转化进现实,只能为死本能所取代。而读者对这两种不同叙事力的认同也存在着区别。
前者由于是来自于外在的死本能,而读者认同的是主角自身的生本能,所以外在的死本能对主角生本能的压抑并没有让读者认同主角之外的死本能,而是认同如何让主角的生本能避免外界死本能的伤害。所以这种悲剧,读者同样是以生本能为动力,去认同如何让主角的生本能不被外在的死本能所压抑,从而使读者认同自己为主角建构的满足生本能的方式。这样形成的超我显然与喜剧中直接来自于作品的超我不同,因为喜剧及大团圆作品直接给了读者一个认同的对象和模式;而这种悲剧中的超我,虽然同样来自于叙事中的主角,但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达成生本能的对象,而需要读者为悲剧主角去建构一个。因此,这种悲剧认同形成的超我虽然基于同样的主角,但对其认同却更为多样化。
而后者,悲剧中的死本能是来自主角内在的死本能,是主角自身的生本能或者因为转化进现实发生障碍或者为了更大的自我保存功能,而为死本能所取代。因此,读者在相同情境中对其认同往往会认同其死本能取代生本能。《少年维特之烦恼》所引起的维特效应,正是在这种认同情况下发生的。读者模仿维特的自杀,来自于认同维特生本能转化为现实的障碍进而为自身的死本能所取代的过程。同样,在众多的舍生取义类的悲剧作品中,正是这种认同在起作用。实际上,这种认同类似于喜剧的认同,因为它直接给出了一种解决的方法,即,要么如维特一样生而无望,要么为了群体的生本能,让位于自身的死本能。
综合而言,叙事力是调控叙事认同及形成叙事身份的根本性因素。这种叙事力将叙事认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受叙事力的影响而认同叙事中的人物获得满足的需求;一类是在叙事力的影响下,自己为叙事人物建构一个满足需求的方式,而对其认同,即开放性叙事认同。直接的叙事认同往往具有单一性,是塑造统一超我及服务于权力政治的有效手段;而开放性叙事认同,则是在需求动力的基础上的自我建构,具有多样性,而被称为是“真正的人的时间”。
四、结语
自古希腊德尔裴神庙门楣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为苏格拉底引用以来,主体之谜就一直纠缠着人类。直到笛卡尔仍然认为主体之内存在着一个本质,存在着一个主宰自我的小我。而进入现代、后现代社会以来,随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进而在巴特、福柯等人的理论中,主体也跟着死了。主体之中不存在一个内核或本质,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我们认为叙事则是建构主体的主要方式之一,叙事时间化则是其主要方面。从叙事时间的角度看,“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为了将来的你,现在的你去认识过去的你”。其中的“你”随着时间而流动不居,但又具有一种时间的一致性。换言之,在这种叙事时间中,主体获得了一致性的身份,并在其中将本我的愿望组织进未来,而成为自我行动的动力。而这种时间化的方式,则来自于叙事认同。也即通过叙事认同主体被叙事时间化了,从而建构起自身的连续性——叙事身份。而叙事认同发生的动力则来自于叙事中的叙事力,即叙事中的主体需求的满足。质言之,正是叙事力促进了叙事认同,也正是叙事认同主体才得以叙事时间化,进而被建构起来。
注释:
① 我们这里用故事世界取代利科的文本世界,因为故事未必就一定是文本之中的故事,同样可以是口口相传的故事。
[1]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3. [M]. Trans. Katheleen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3] Anthony Paul Kerby. Narrative and the self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David Carr.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车文博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6]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新论[M]. 车文博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7]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论评[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8] 弗洛伊德. 论潜意识[M]. 车文博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9] 弗洛伊德. 超越快乐的原则[M]. 车文博主编. 弗洛伊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4.
[10] 弗洛伊德. 作家与白日梦[M]. 车文博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11] Paul Ricoeur. Narrative Identity [C]// Wood Davi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12] Paul Ricoeur. The Text as Dynamic Identity [C]// Mario J. Valdes and Owen Miller. Identity of the Literary Tex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13] 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册. [M]. 朱光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4] 亚里士多德. 诗学[C]// 罗念生译. 罗念生全集.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5] 海登·怀特. 元史学: 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 陈新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6] 海登·怀特. 形式的内容: 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 董立河译.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17] 马大康. 文学时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8] 弗洛伊德.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M]. 车文博主编.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4.
[19] A·H·马斯洛. 动机与需要[M]. 许金声, 瞿朝翔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The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WANG Zheng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One as a subject, is constructed, while the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is the main part of this process. Because of this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Freud’s Id is transformed into Ego in the reality and the dominant pleasure principle in Id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pleasure principle which is under the dominant reality principle in Ego. Furthermore, the narrative tempor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formed by the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which makes the narrative time internalize into the subject. But this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gets the energy from the narrative force, which are the needs of life in the story. In other words, the subject is constructed by narrative time, and the narrative time of subject is formed by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narrative force.
subject construction; narrative time;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narrative force; Freud
I0-02
A
1672-3104(2017)01−0148−06
[编辑: 胡兴华]
2016−05−03;
2016−10−11
王正中(1985−),男,安徽无为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叙事学,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