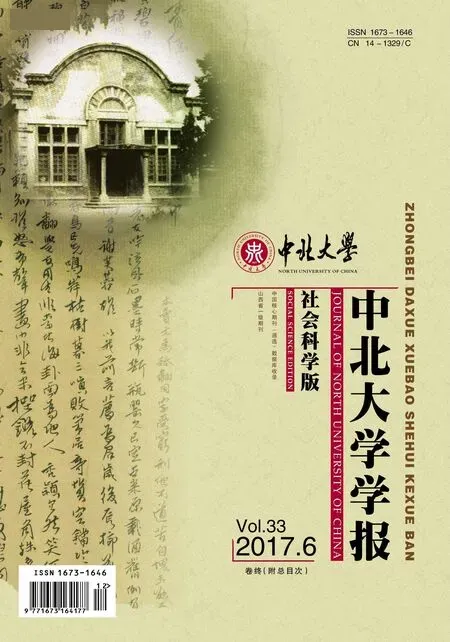从历史语境到经典诠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读*
2017-01-12龙昌黄
龙昌黄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从历史语境到经典诠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读*
龙昌黄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围绕“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来展开, 且这四个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 却某种程度上为有关论者所忽视。 围绕上述四个主要问题, 毛泽东揭陈了现有革命文艺实践的不良趋向, 更在对其纠偏和拨转的基础上, 规制了革命文艺运动继续推动和发展的前进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革命文艺; 毛泽东
0 引 言
自1942年5月发表以后的75年来,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需要指出的是,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发表的讲话, 其书面文本, 即《讲话》, 直至一年后才得以刊载和公开发表。 并且, 《讲话》从书面整理到最终正式“收入《毛选》时, 是作了一些修改”的。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8页; 刘增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版本考释》, 载《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本文所据为《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刊版本(第46~74页), 为行文方便, 以下其中所引不再作注。(以下简称《讲话》)对尔后中国文艺的发展,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迄今, 《讲话》仍是指导和规约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作为“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 “《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1]。 今天, 对于这部经典文献, 有关论述甚夥。 不过, 笔者发现, 相当一部分阐发多少有些游离于经典文献的本意, 使得原本为毛泽东本人所强调的问题, 未获得相应的重视。
但凡细读文本, 不难发现,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围绕四个主要问题, 即他本人所说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展开, 并且四者之间彼此紧密关联。 对此, 很大程度上, 有关论者多少有些忽视, 或者未及详论。 既然“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2]70, 那么, 也就更有必要重新回归文本, 在历史与文本的互释中重读这部经典文献, 并就此重审其内在逻辑和思想内涵。
1 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如所周知, 毛泽东首先作为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而走上历史舞台。 毫无疑问, 它构成了我们探究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讲话”的必然前提。
早在少年求学时代, 毛泽东就有了“造反意识”[3]97。 辛亥革命爆发后, 他参加了湖南的革命军。 不久, 因孙、 袁南北“统一”而退伍求学, 几经辗转, 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6年后前往北京, 在那儿结识了李大钊、 陈独秀。 一定意义上, 陈、 李二人可算是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和精神导师。*毛泽东曾回忆说那时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参见《红星照耀中国》,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115页); “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则“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参见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一)》,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 第45页)。早在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显示出他在开展农村工作方面的才华, 曾专门负责党内农民工作。 其间, 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1926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等, 开始对如何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进行探索。 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1927年秋, 毛泽东在湘赣边区发起了“秋收农民起义”, 组织农民革命暴动。 此后, 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中, 毛泽东逐渐成长为党内主要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一, 并最终在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最高领袖。
就现有历史文献材料来看, 尽管毛泽东年轻时就爱好文学, 并且他本人也是一位钟情于写作抒怀的旧体诗人, 却罕作有关文艺问题的评述。 他对革命政治的热情显然是第一位的。[3]90-140毛泽东有意关注文艺问题, 是在抵达延安之后。
1938年, 在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之后, 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如果说, 遵义会议从“军事路线和军事方向问题”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那么,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进一步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不过, 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 当时“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依旧存在一些分歧”, 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的“王明路线”依旧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 团结全党, 一场筹备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时, 发起于194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 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 并正式写入党章。 它宣告了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全面胜利, 最终从思想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 以之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因此正式建立和形成。[4]
2 毛泽东发表《讲话》的现实缘起
《讲话》的发表, 毋庸讳言, 是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一部分。 毛泽东对此毫不隐晦地指明要开展一场切实而严肃的整风运动, 以清除延安文艺界内部存在着的严重的“作风不正的东西”, 祛除一部分革命文艺工作者身上可能还存在的“唯心论、 教条主义、 空想、 空谈、 轻视实践、 脱离群众”等缺点, 从而使得这些“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的同志真正从思想上入党, 而不仅仅“在组织上入了党”。 也就是说, 作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欲解决的依然是党内的文艺思想路线问题。 胡乔木在一次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谈话中就说: “毛主席对文艺很关心……以后就是文艺界的思想状况, 确实有集中暴露的问题, 这样促成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他进而借一篇广播稿, 来揭示当时“延安文化人”所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
有人以为作家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 观点, 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 观点就会妨碍写作……
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 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 “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代表这些倾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 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 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 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 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 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 提高与普及问题, 都发生严重的争论; 作家内部的纠纷, 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5]53-63
广播稿所讲的这些“座谈会的背景”, 胡乔木认为是实际存在的。 还有, 毛泽东对此的了解, 不光来自于延安作家们已发表的作品, 也来自与一些作家(譬如萧军)的面谈。 而且当时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 也并非毛泽东一人对此有看法, 就连贺龙、 王震等军事将领, 也持相同或相似的态度。 贺、 王二人就曾当面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提出过批评。 身为毛泽东的时任秘书, 胡乔木不光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整风学习运动的过程, 还是《讲话》书面稿的主要整理者。 他在晚年时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相关背景的揭示, 应当是可信的。*20世纪90年代末, 邓力群在回忆延安整风的一篇文章中说: “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 现在要讲权威, 是胡乔木。 ”参见邓力群: 《代序——回忆延安整风》, 载《延安整风以后》,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年版。
这种文艺界整风的意图, 在《讲话》中也有所反映。 通过对“五四”以来中国革命史的梳理, 毛泽东指出, 此前的国共内战时期, 革命文艺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总的方向”上与一般革命工作也是一致的, 但由于当时特殊的革命形势, 文化斗争与政治军事斗争发生于不同的革命战场。 革命文艺工作者于抗战爆发后, 纷纷来到延安, 原本无法(因此也无须)顾及的文化战线(文艺工作)与军事战线(革命斗争)相结合的问题, 也因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到来而成了新形势下党在革命文艺思想战线上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所以, 在他看来, 这不只是纯粹的文艺问题, 而是关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武两条战线——“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如何统一、 协调起来, 从而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发挥其对内“赞扬”“教育”人民, 对外“打击”“消灭”敌人的笔杆子功能的问题。
也正基于这种政治和军事斗争现实需要的战略考虑, 《讲话》一开篇, 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指明了座谈会的目的: 同文艺工作者“交换意见, 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 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 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 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换言之, 毛泽东召开这次座谈会的主旨, 就是要同与会文艺工作者共同探讨革命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 使得前者更好地“协助”后者, 从而服务于“民族解放”这一现实的、 阶段性的革命目标。 在毛泽东看来, 革命文艺工作只是一般革命工作中特殊的一种而已。 革命文艺作为党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理应服务于党的革命政治需要这一大局。
当然, 《讲话》不能因此简单地被视为是对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当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应对。 从《讲话》所阐述的内容与《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揭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关系来看, 二者之间显然一脉相承。 所以, 《讲话》更应当被看作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等关于文化思想阐述的扩充和完善, 是对后者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丰富和细化。[6]文艺工作方面所存在的现实问题, 恰为此提供了阐述的契机。 也正由于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纲领之间的紧密联系, 《讲话》因此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文艺思想方面最重要的理论文献, 并事实上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
由上所述可以认定, 以《讲话》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从属于毛泽东的革命政治思想, 是后者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拓展和延伸。 虽然, 一个人对文艺的理解的确会受到其本人的文学鉴赏能力、 文学实践、 文化背景、 生活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是作为一位职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言, 毛泽东在思考文艺问题时, 明显带有革命政治的眼光。 也就是说, 现实革命政治的需要, 即是毛泽东发表《讲话》以阐述自己文艺思想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讲话》的发表, 所针对的主要不是文艺自身的问题, 而是掩藏在它背后的人(文艺工作者)的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 因此, 它所欲表达的, 与其说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诠释或解读, 不如说是他在革命政治的视野下, 对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军队”的规训(Discipline)和规制(Policing)。 这种鲜明的政治性, 因此也构成了毛泽东《讲话》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3 《讲话》的思想内涵与内在逻辑
正如文本自身所示, 整理之后的《讲话》因发表讲话日期的不同, 分为“引言”(1942年5月2日)和“结论”(1942年5月23日)两个部分。 “引言”中, 毛泽东开诚布公地指出, 鉴于现阶段民族解放这一革命目标的需要问题, 文章开头提及的四个问题务必要解决。 而在“结论”部分, 他指出, 座谈会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不难看出, “结论”中的中心问题关涉的, 其实就是他在“前言”中论及的“态度问题”和“工作对象问题”。
这四个文艺工作者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恰恰指向的是毛泽东对革命文艺的性质、 为谁创作、 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以及革命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学习与改造问题。
3.1 革命文艺的性质问题
很大程度上, 这一点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相关论述在文艺方面的具体阐发。 显而易见的是, 毛泽东并不避讳文艺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革命价值取向。 在他的眼里, 为求得民族和人民的解放, 革命队伍里不仅需要枪杆子(“拿枪的军队”), 还需要笔杆子(“文化的军队”); 不仅要从军事战线上打败敌人, 还需要从文化战线上打败敌人, 削弱并最终消灭“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 因此, 就有必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要做到这一点, 以实现现实政治的革命目标, 首先就需要文艺工作者解决自身的“立场问题, 态度问题, 工作对象问题, 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文中, “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实际上被简约为“学习问题”。。
所谓“立场问题”, 就是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政治和阶级立场, 要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边。 其依据, 即为毛泽东本人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判定。 也正基于这一判定以及这场革命的无产阶级属性, 得出工人、 农民阶级在其中应为革命主要阶级力量的认定。 《讲话》中, 毛泽东重申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有关表述: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并进而指出, 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 革命文艺“自然也是这样”。 于是, 革命文艺的阶级属性, 也就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无产阶级文艺。 虽然受苏俄革命的影响, 此前有关无产阶级文学和艺术的表述和阐述也数见不鲜, 并且已有像瞿秋白这样的革命家兼文艺理论家作出过诸如“每一个文学理论家其实都是政治家”[7]541这般的论述, 但像毛泽东这样放眼于革命政治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审查革命文艺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的, 还尚属首次。
3.2 革命文艺为谁创作的问题
依毛泽东所见,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 是在认同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属性的基础上, 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时应当替谁发声的问题, 也即毛泽东所说的“态度问题”。 它是“立场问题”的层递。 对此, 他说: “随着立场, 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 ”换言之, 文艺工作者有什么样的立场, 就有什么样的创作态度。 他进而指出, 创作时, 面对三种人, 文艺工作者要采取不同的态度:
对于敌人,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 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 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 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 坚决地打倒他们。 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 有批评, 有各种不同的联合, 有各种不同的批评。 ……至于对人民群众, 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 对人民的军队, 人民的政党, 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人民也有缺点的。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 应该是使他们团结, 使他们进步, 使他们同心同德, 向前奋斗, 去掉落后的东西, 发扬革命的东西, 而不是相反。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看待革命文艺工作所持有的态度, 也充分阐明了他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如何进行文艺创作的期待和大致的指导意见: 对敌人——“暴露”与“打倒”; 对盟友——“联合”与“批评”; 对人民——“赞扬”“教育”以求“团结”。 这三种不同创作态度的阐明, 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革命文艺写作方向的定调, 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指导革命文艺工作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之一, 事实上影响了此后三十余年中国大陆地区的主流文艺创作实践。
另一方面, 则是革命文艺作品的读者对象问题, 也即毛泽东所说的“工作对象问题”。 立场与态度明晰了, 革命文艺作品应当给谁看, 这一问题也就清楚了。 在毛泽东看来, 革命地区文艺作品的读者对象不同于国统区以及1937年之前的上海。 如果说后者的读者对象尚“是以一部分学生、 职员、 店员为主”, 那么“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 就应“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以及一部分将成为“未来的干部”的进步学生。 也就是说, 工农兵及党员干部构成了革命文艺作品的主要读者对象。 这种读者对象的差异之所以存在, 主要是因为: 无论是抗战前的上海, 还是这时的重庆(国统区), 革命文艺工作者“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 脱离群众的倾向”。 这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因, 那就是上述地区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 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相比之下, 革命地区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 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 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 因此, 此前限制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大众当中去及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的历史条件或障碍, 已经不复存在。 这样, 文艺工作者既然是为着革命的目标来的, 就应当“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为他们创作, 为他们服务。
3.3 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与改造问题
在明确革命文艺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利益, 且应为他们创作之后, 是否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就天然地具有直接为工农兵创作或服务的资格呢?毛泽东对此予以否定。 在他看来, 文艺工作者想要创作出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 使自己的创作实践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有其前提条件, 那就是: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 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 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 来一番改造。 没有这个变化, 没有这个改造, 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 都是格格不入的。 ”而这, 无疑是毛泽东针对不少“延安文化人”身上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发表《讲话》的题中之义。 因此, 革命文艺工作者完成自我的思想改造, 也就成了摆在眼前十分重要且十分紧迫的问题和难题。
至于改造的方式, 则是“学习”, 既要从理论的高度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又要在行动中放低姿态去“学习社会”。 前者是因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 尤其是党员作家, 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 就现实状况来看, 毛泽东认为, “现在有些同志, 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他们追求“超阶级的爱”, 追求抽象的“自由”“真理”“人性”等, “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因此, 应当彻底清除这种影响。 同时, 学习马列主义, 不是要教条式地学习, 只在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 要必须抛弃一切剥削阶级的立场(就革命文艺工作者而言, 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始终不渝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要自灵魂深处开始改造自己的思想, “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 要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
“学习社会”, 就是要在深入社会生活的实践当中, “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 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 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 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轻视工农兵、 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观念, 引导有着此类错误意识的知识分子“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 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 去表现工农兵群众, 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不能因为自己的出身, 光注意“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 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完成彻底的思想改造, 就必须痛下决心, 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深入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 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 简言之, 文艺工作者要想彻底地完成思想改造, 使其彻底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就必须将理论(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社会实践(深入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相结合, 从而在认识上、 行动上、 情感上彻底地改造自己。
3.4 革命文艺应当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 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了。 这一问题同样涉及两个方面: (一)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当为工农兵群众提供怎样的文艺作品(或可称作“写什么”); (二)革命文艺工作者怎样为工农兵群众提供这样的作品(或可称作“如何写”)。
关于“写什么”, 《讲话》中毛泽东没有正面提及, 却可以从以下论述中得以管窥:
革命的文艺, 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 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 受冻、 受压迫, 一方面是人剥削人, 人压迫人, 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 人们也看得很平淡; 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现象集中起来, 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 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 感奋起来,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 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 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
从中不难发现, 至少就历史现实来看, 毛泽东认为, 人民群众受奴役、 受压迫、 受剥削的苦难以及此间人民群众与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等, 这些“实际生活”的存在, 应当成为革命文艺的主要书写对象, 而这是由其背后的革命任务所决定的。 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也正因此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尽管毛泽东强调,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借鉴古今中外文艺遗产, 不过相比之下, 他更重视社会生活对革命文艺创作的影响, 认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在他看来,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因此, 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从中“观察、 体验、 研究、 分析一切人, 一切阶级, 一切群众, 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 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但与此同时, 毛泽东也指出, 革命文艺也不能因此而等同于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中“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也需要采挖和提炼, 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 乃是日常社会生活的集中和典型化, 因而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更强烈, 更有集中性, 更典型, 更理想”, 并更具“普遍性”。 这样一来, 既源于社会生活又高于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文艺作品, “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 感奋起来,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很显然, 毛泽东有关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并非简单的、 纯粹的文艺理论阐述, 而是嵌连在鲜明的革命政治当中的方针指引, 以利于“有力地迅速完成”现阶段的革命目标和任务。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之后, “如何写”的问题也就出来了。 《讲话》中, 毛泽东一再强调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 而不能拘泥于教条式的文学和艺术定义。 既然革命文艺的主要作用在于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 使之投身于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当中(“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 感奋起来,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那对于如何创作符合工农兵群众需要的文艺作品的问题, 就有必要从工农兵群众实际的文化水平、 文学素养的基本情况出发, 从促进革命事业“有力地迅速地完成”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出发。
这样, 就需要在文艺工作中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说: “普及的东西比较浅显, 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 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 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 并且往往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 ”而就目前来看, 不识字, 没文化, 是广大工农兵群众普遍存在的状况, 所以在现有的条件下, 首先需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提高”), 而是“雪中送炭”(“普及”); 换言之, “普及”远比“提高”重要和迫切。 因此, 他认为“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对“提高”的否定。 他说: “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 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 ”也就是说, 革命文艺的普及和提高, 是在具体的革命实践当中不断变化发展着的, 普及是为着提高的普及, 提高是基于普及的提高。 当然, 这是基于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 “普及是人民的普及, 提高是人民的提高”*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 常为众多研究者所刻意着墨的文艺与社会生活、 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 其实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一问题的从属性问题。 其之所以被过于凸出, 以笔者所见, 恐怕与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重要阐释者有关: 延安时期的周扬与“文革”后的胡乔木。 历史地看, 正是延安时期的周扬最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中, 完成了《讲话》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经典化建构, 并且首次将毛泽东《讲话》中所谈相关问题, 置换为大众化(其中即涉及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 以及“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问题。 周甚至直言, “这三个问题解决了, 就解决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 基本方针”(参见《周扬文集》第一卷, 第460页)。 胡乔木“文革”后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视为《讲话》的“两个基本点”, 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讲话》的精神”的“坚持”, 以及相当意义上因此提出的重新诠释(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58、 269页)。 相当程度上, 前者以《讲话》文艺问题化的形式, 加剧了革命文艺的政治化; 后者则在反思文艺过于政治化的后革命时代里, 再次审视《讲话》所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局限性, 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矫枉之后, 以文艺内部问题的面目重新经典化。。
综上可见, 在毛泽东那里, 上述问题是紧密关联的。 其中革命文艺的性质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则立场问题。 只有解决了立场问题, 自然也就决定了态度问题; 明确了态度问题, 也就知道自己应为什么人服务; 知道自己服务的读者对象, 也就须明晰自身是否具备并且如何具备相应的为之服务的前提条件, 或为之应做的改变; 革命文艺工作者唯有在完成了自身的学习和改造之后, 方才有资格去谈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 知道应该写什么和如何去写, 并因此明晰文艺与社会生活、 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 其中, 既鲜明地揭示出作为一位革命政治家关注文艺问题时独到而深刻的战略眼光, 同时又清晰地呈现了他作为一位“文章大家”[8]严密论证的内在逻辑。
在作完上述阐释之后, 毛泽东还从党内和党外两个方面, 论及文艺工作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 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斗争方法等问题。 毛泽东再次重申了“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是齿轮和螺丝钉”, 规定了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从属性质。 因此,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 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也就决定了现时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和斗争方法问题基本趋向。 在统战问题上, 在他看来, 首先要基于现实政治中“抗日”这一根本问题, 团结“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 其次, “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 再其次, 在“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团结起来”。 在斗争方法问题上, 要坚持“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与“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文艺批评的方针和策略, 在此基础上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由此, 更可确证, 革命的政治, 而非革命的文艺, 是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4 结 语
目前, 《讲话》依然是国家文艺生活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其理论意义, 正如有关研究所陈, 自其发表以降, “从专业的角度看, 并不是由于它在文艺理论上做出了空前绝后的贡献。 然而, 在某个方面, 就中国而言, 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文艺理论著作能与之相比, 因为它制订、 规定了未来数十年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的秩序、 标准和原则——这是它真正的权威性之所在”[9]24。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周扬认为, 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最正确、 最深刻、 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 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 并且把这个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10]460。 因此, 对于这部经典文献, 仍有必要予以重读。 “文本之外无余物”[11]158, 德里达此语或不无偏颇之处, 单就作为历史文本的经典文献而言, 却无疑是真理。 因为文本或语言本就是经典文献赖以存在的唯一方式。 对它的重读和诠释, 无疑都应建立在对其本义的深度理解基础之上。 所以, 回归文本自身, 在历史与文本的汇通中澄清经典文献的生成、 内在逻辑和思想内涵, 显然十分必要。 唯此, 方可辨明它在历史中的意义和影响, 并由此开展进一步的探究和诠释。 若如其然, 本文粗浅的尝试或不至于全无意义。
[1] 吴晶.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N]. 人民日报, 2012-05-24(01).
[2]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 王逢振, 陈永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 [美]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M]. 李方准, 梁民, 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4] 廖心文.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研究[J]. 党的文献, 2012(1): 43-51.
[5]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6] 李蓉.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2(7): 52-57.
[7] 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8] 梁衡. 文章大家毛泽东[N]. 人民日报, 2013-02-28(007).
[9] 李洁非, 杨劼. 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0] 周扬. 周扬文集(一)[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1]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FromHistoricalContexttoClassicalInterpretation——RereadingTalksattheYan’anForumonArtandLiterature
LONGChanghu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alksattheYan’anForumonArtandLiteraturemainly involves four interrelated questions: “stance” “attitude” “work object” and “learning”. This was more or less ignored by most scholars in this field. As for the above four questions, Mao Tse-Tung revealed some bad tendencies of the practices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djuste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TalksattheYan’anForumonArtand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MAO Zedong
1673-1646(2017)06-0031-07
2017-09-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文学艺术思想通史·现代卷(13JD750003)
龙昌黄(1978-), 男, 博士生, 从事专业: 中国现代文论、 中国现代汉诗批评。
A8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