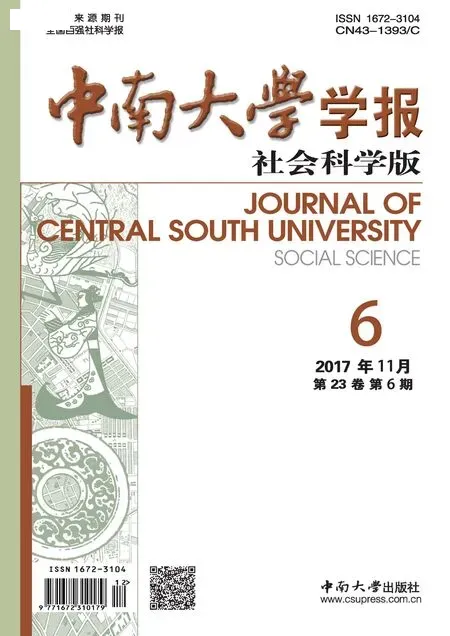六朝灵验类小说名义界定及其理论阐释
2017-01-11谷文彬
谷文彬
六朝灵验类小说名义界定及其理论阐释
谷文彬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灵验类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学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和界定。从小说类型学角度来看,灵验类小说的名义界定不仅要注重题材和内容,还要关注形式与内涵,并结合政治、思想和文化因素,对灵验类小说文化内涵作进一步的梳理:其创作主体是“为佛教文化所化之人”,对佛教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其叙事内容由形式和意识两个层面构成。要之,六朝灵验类小说侧重对观音灵验事迹的记录,是时代主题的反映,也是佛教文化传播进程的映射。
六朝;灵验类小说;称名;定义;理论阐释
六朝以来,佛教凭借自身相对完善的宗教组织和相对成熟的传教经验,其佛理、教义被越来越多的本土人士所接受,而佛教及其所承载的佛教文化亦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志怪小说对佛教的接受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志怪小说不仅在内容、技巧、立意、情节方面浸润颇深,而且还衍生出一种以“称道灵异”为主旨的新的类型小说——灵验类小说,如谢敷《光世音应验》、傅亮《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刘义庆《宣验记》、萧子良《宣明验》、王琰《冥祥记》等等,皆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灵验类小说虽在一些研究专著和论文中被提及,但在许多方面仍缺乏必要的、细致的探讨,比如对灵验类小说的称名、定义,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和具体细致的界定,对其文化内涵也缺少必要的梳理。这就会导致歧见迭出、概念模糊、边界失于宽泛。鉴于此,本文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文学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对灵验类小说的名义问题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以期深化对这类小说的认识。
一、当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几种称名及定义
就“灵验”一词而言,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灵”与“验”二字并未连用。“灵”,最初的意思是指巫师。如《说文·玉部》:“灵,巫也,以玉事神。”[1](19)《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王逸注:“灵,谓巫也。”[2](56)至于“验”,最初的本义是马的名字,如《说文解字》谓:“验,马名。从马佥声。”[1](464)后来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检查、验佐之意,如《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3](2236)《后汉书·张衡传》:“验之以事。”[4](1909)魏晋以后“灵验”一词连用,则有神奇效应之意。如晋孙绰《游天台山赋》:“睹灵验而遂阻,忽乎吾之将行。”[5](496)南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永祖既见灵验,益增至到。”[6](13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三:“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滩。瞿塘滩上有神庙尤至灵验。”[7](778)“灵验”被征引到佛教典籍中,则又被赋予宗教心理体验之意涵。如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世高传》:“此庙旧有灵验。”[8](509)《法苑珠林》卷六十:“夫咒是三世诸佛所说,若能至心受持,无不灵验。”[9](1774)由此可见,“灵验”指的是灵妙不可思议的效验,祈求诸佛、菩萨或持诵经典,而获得不可思议的验证。它与“感应”相似又有细微的差别。“灵验”强调的是人所闻见的灵妙应验效果,而“感应”则注重的是人神交会的经验过程。换言之,前者强调客观,后者偏重主观。
然而,在现代学术研究范式中,对于术语的运用并非以上论述的如此简单。它必须要有科学的界定。但是由于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结构等条件的限制,即便是面对同一事物,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也未臻一致。关于这类小说的称名和定义问题亦如此,学者们就这类小说的称名及定义所给出的答案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第一,以此类小说的社会功能为中心来称名和定义,我们可称之为功能性命名、定义。这种称名和定义以鲁迅为代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之《六朝鬼神志怪书(下)》中将其冠之为“释氏辅教之书”,云:
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视为小说。[10](32)
鲁迅论断虽简,但已触及到此类小说的题材、性质、功用、著录及文本存佚情况,大致勾勒出此类小说的轮廓及特征,极大地推进了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入,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可。如李剑国、王枝忠、侯忠义、张瑞芬、吴海勇、孙昌武等人均承袭了这一说法,或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或称之为“释氏辅教类小说”。客观而言,这种称名和定义看到了此类小说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产物,反过来又会对社会起促进作用。所以从小说功能而言,确实能点明此类小说的某些特征和属性。但如果仅从小说的社会功能角度来概括此类小说的本质,为其下定义,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称名和定义很明显忽略了此类作品的内在形式,甚至会存在把小说的社会功能无限夸大的倾向。
第二,以此类小说的信仰倾向为中心称名,即佛教小说,又称佛教志怪小说。称名虽略有差异,但考察其定义之内容并无多大区别,都是着眼于此类小说的信仰倾向性。其中以杜贵晨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汉魏晋南北朝佛教与小说》一文中指出:“入南北朝后,这类作品骤然增多,刘义庆《宣验记》以下,有傅亮《应验记》、张演《续观世音应验记》、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萧子良《冥验记》、王琰《冥祥记》、佚名《祥异记》等,都是专为弘扬佛法而作,在佛教为典籍,在文学则可视之为小说,似可称为佛教小说。这类小说在南北朝数量之大,一方面见出作者们为弘教而撰述的热情之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类小说对传布佛教的作用之大。”[11](75)又说:“这里所谓佛教小说非指一般佛教题材或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小说,也不是指汉译佛经中的文学故事,而是指古代中国人为佛教目的创作,旨在使读者发生并保持佛教感情和信仰的小说。这类作品在当时的作者和读者或以为是实事,而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则是志怪小说的一种。”[11](77)王昊则进一步分析佛教小说涵义云:“这些作品以‘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思想为基础,籍动人的神异故事来宣扬佛教的灵验,诱使人们遵循佛教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轨范,或以‘记’称,或以‘传’名,多采用了小说的表现手法,有具体的人物、完整的情节、虚幻的想象、传奇的色彩,以期通过生动、形象的故事,使一般庶众更易接受佛教教义。”[12](58)郑欣、刘惠卿、薛慧琪、李希运、张庆民等人,也在其相关论述中运用了这种或近似这种的称名和定义。然而这种命名和定义虽然看到了此类小说的信仰倾向性在编撰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等情况,并为我们研究此类小说的编撰目的提供了某种视角,但由此称名和定义此类小说在于信仰倾向的问题,是缺乏说服力的,它单纯地强调了信仰倾向而忽视其他要素,未免有狭隘之嫌。
第三,以信仰的对象为中心来称名、定义。即观音感应故事,又称观音灵应故事。我们称这种命名或定义为实质性命名、定义。因为这种称名和定义强调的是信奉者与信奉对象(比如观音)之间的感应。持这种说法的人有楼宇烈、王青、林淑媛、王建等人,他们认为此类小说主要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神力灵验的宣扬”[13],指出此类小说题材上的特点是观音灵验。应该说,较之“释氏佛教之书”“佛教志怪小说”而言,“观音感应故事”对作者题材及主题的界定更为清晰。然而,这种命名亦存在不少缺陷:首先,将此类具志怪特征的小说与宗教通俗宣传作品混为一谈,仅以“故事”概而言之,模糊了此类小说的性质。其次,以“观音灵验”来概括此类小说之题材也不准确。自六朝以后,佛风高涨,此类作品关于佛、菩萨的灵验现象,已不仅仅局限于《观世音经》和观世音,还包括《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等经书及相关菩萨。譬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阿弥陀经灵验记》等等,即是其例。若仅以“观音应验”总括此类小说题材特征,似乎亦失偏颇。
第四,以信仰者的情感体验为中心的称名、定义,即灵验类小说或应验类小说①。这部分学者应该是受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启发来阐述此类小说的本质属性,强调的是信徒的个人宗教情感体验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这类研究者的代表有王国良、郑阿财、夏广兴、黄东阳等人。郑阿财在其著述《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中,认为此类小说“是佛教信众的宗教见证,也是僧人的宗教宣传。因此,自来将之归属于佛教史传部。又因其传说性质,文士听闻之后辄加采录,而发为笔记小说,故有将之归属于子部小说类”,可见此类小说“具宗教与文学之双重特性”。此外,他还指出此类小说不受重视的原因,“但因非关教理,以致未受佛学研究者之重视;纵有小说志怪、灵异之姿,唯一般视为辅教之具,故于文学研究之中,也未能给予应有之关注”[14](3)。夏氏则进一步指出:“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强烈的宗教意识,是佛教中国化、通俗化历程的具体表现。”[15]郑、夏二人的称名及论述,看到了灵验类小说产生的心理要素,看到了个人情感体验在当时民众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又抓住了此类小说题材上的特点,突出了其文学价值。但如果深入探究,就可以发现,这种定义仅仅回答了灵验类小说是什么?但对其类型并未做出详细的说明,这一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
以上仅列举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称名和定义,其实还有其他学者对此类小说的称名和定义,如报应小说、报应故事、观音题材小说等。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类小说的称名和定义仍然歧见迭出。为何如此难于给此类小说命名和定义呢?原因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此类小说属性的复杂,即具宗教与文学的双重性质。这种特殊属性导致学者们在下定义的时候无法做到周全。二是学者们给灵验类小说命名和下定义时,往往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这就有可能有失公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此类小说研究还不够成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称名和定义问题含混不清。而含混的定义,会给我们实际的研究工作带来许多 不便。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准确地总结灵验类小说所具备的特征和内在本质,区分灵验类小说与非灵验类小说呢?我们不妨对灵验类小说的构成要素进行结构性分析以明确其定义。
二、灵验类小说的名义界定和理论阐释
到底应如何划分灵验类小说要素?我们不妨回到灵验类小说这一概念本身。我们在前面已说过灵验类小说是志怪小说的一个分支,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文学类型学的相关理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谓“类型是我们比较许多不同的个体、抓住在它们之间可以普遍发现的共同的根本形式,按照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各种特征把它们全部作为一个整体来概括”[16](80)。类型学即“是研究事物的共同性特征与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构成方式与变化过程的学问。作为类型学的一门分支,文学类型学是研究文学现象的共同性特征与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构成方式与变化过程的学问”[17](2)。灵验类小说,很显然是一种以题材、主题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类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区分文学类型呢?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的一段话或许会给我们不少的启发:“体裁形式本身不能构成类型,只有‘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的统一,某一独立的类型的个别‘尺度’唯一比例才能得以说明。而且,根据一种标准是无法把握这种‘内在形式’的。”[18](103−104)这意味着,对于文学类型,须从研究对象的多个方面来把握。基于此,姚斯又进一步说明用四种形式来描述不同的文学类型:“一作者与本文、二表现形式、三结构与意义、四接受方式与社会功能。”[18](105-110)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在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将其分为“内在形式(如态度、情调、目的以及较为粗糙的题材和读者观众范围等)”和“外在形式(如特殊的格律或结构等)”[19](274)。葛红兵则明确指出类型小说应具备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作品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一定的时间跨越度。……第二,具有较一致的态度、情调、目的,或具有连续的主题、题材。……第三,具有较为特定的审美风貌:特有的语符选择和编码方式。……第四,从读者的接受而言,能产生某种定型的心理反应和审美感受。”[20]
笔者借鉴和吸收上述诸家观点,认为灵验类小说要素的构成应符合如下几个原则:一是每一种要素都是这类小说必备的,不能有所遗漏;二是每一种要素都应有明确的划分,具备独特的内容及形式;三是不同要素之间有明确的结构关系,不能将不同级别的要素混为一谈。这三点与叶圣陶在《作文论》之《文体》篇曾提出的三项标准即包举、对等和正确是相一致的。
鉴于此,并结合前面已论述的相关定义的观点以及小说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其核心要素有:①题材特征上,宣扬观音等菩萨的法力是其恒定的主题,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延续性;②表现特征上,继承志怪小说的表现形式,篇幅短小、结构单一、布局紧凑、务求征实、结局圆满等特点,并由此形成较为稳定的叙事模式和叙事结构:“遭遇困厄→获致灵验→平安脱险”;③思想特征上,佛家的因果观和三世观是其主导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吸收了本土文化的“报应说”,从而形成因果报应思想,并藉此类小说为媒介,迅速在民众中流行开来;④功用特征上,劝善惩恶,宣扬佛教义理,吸收信徒,是其不变的意图,故此类小说社会功能较之其他功能更明显。对于完整的灵验类小说来说,以上这些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称为灵验类小说。
需要指出的是,灵验类小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必然会受当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对灵验类小说的定义界定还需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对此,张兴龙《“扬州小说”概念界定的理论阐释》一文,从创作主体、叙事内容和发展空间三个方面来界定其研究对象[21],给笔者不少的启示。笔者将借鉴其研究范式,从创作主体、叙事内容和佛教文化倾向性等方面来界定灵验类小说的范围。
首先,就创作主体而言,什么样的人讲述的灵验类故事,才是最具合法身份的灵验类小说作者,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关于灵验类小说的作者问题,大多含混其词,并未进行清晰的学理性界定。这就容易导致对灵验类小说的创作主体产生误解:一方面以为这类小说的创作者都是佛教徒,另一方面认为这类小说仅仅与小说的背景、题材和内容有关,而与创作主体的佛教素养关联不大,甚至无关。
那么究竟哪些人才是灵验类小说的最具合法身份的创作者呢?对此,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提出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22](6)的观点,或许可以给我们启发。凡是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的人,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可以将灵验类小说的创作者称之为“为佛教文化所化之人”。换言之,“为佛教文化所化之人”更多的是强调置身于当时佛教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佛教信仰有着长期的生活体验,对佛教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以佛教徒的心态、立场对佛教生活进行观照、反思的人。他们是当时佛教文化理念和精神的传承者。因此,“为佛教文化所化之人”就不仅仅局限于虔诚的佛教信徒,还包括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士人,他们亲身经历或者十分熟悉佛教生活,自觉地去传承佛教文化理念和精神。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为佛教文化所化之人”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两种情况的出现:一为“钦服灵异”之作,一为“慕其风旨”之作,即“虔诚”与“赏心”之别。这一点,在唐以后的灵验类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就叙事内容而言,什么样的灵验故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验小说呢?对此,笔者认为需要从两个层面加以观照。
一是形式层面,灵验类小说创作群体以佛教灵验事迹为主要描写内容,聚焦“灵验”的直观效果,并严格依循纪传体来撰述,交代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及出处,从而营造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上的空间,力求予人以真实。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张演《续观世音应验记》之“毛德祖”为例:
毛德祖始归江南,出关数里,虏便遣人骑追寻之。其携持家累十余口,闻追在近, 便伏道侧蓬莱之中,殆不自容。且徒骑相悬,分无脱理。唯阖门共归念光世音菩萨。有顷,天忽骤云,始如车盖,仍大骤雨。追者未及数长,遇雨不得进,便返。德祖遂合家免 出。[6](51−52)
小说叙述了毛德祖在归江南的路上,突遭困厄,进而呼唤观音名号来寻求观音的救助,最终脱离险境。在这个叙事环境里,主人公毛德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宋书》有其传记。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荒诞的灵验事迹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特殊的空间环境,在传递了一种真实感和现场感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特殊的佛教文化氛围。这样的例子在灵验类小说中比比皆是。这既可以看出创作主体听闻这类灵验传闻时是抱之以实录的态度记下的,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在宣扬佛学理念和遵循本土固有的史学创作传统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依靠灵验的传闻来想象观音的威神之力,另一方面又要不露痕迹地与本土史传写作传统相融合。这种努力无疑具有示范作用,此后同类小说均继承了这一体例。
二是意识层面,灵验类小说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叙述,来展示当时民众的社会心态和信仰心理、习俗,构建当时的社会空间,从而构成灵验类小说的深入形态。比如,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之“孙钦”条:
孙钦,建德郡人也,为黄龙国典炭吏。亦减耗应死。诵《观世音经》,得三百遍。觉身意自好,不复愁,锁械自宽,随意得脱。自知无他,所以不走。少时遇赦得散。钦性好猎鱼杀害,从此精进。[6](134)
孙钦本是失职,依照律法应当处死,但由于他诵《观世音经》,竟然得到观音救助,平安脱险。像这样的事例在灵验类小说中还有很多,如“高荀”“僧苞道人所见劫”“高度”“王谷”“唐永祖”等条。由此可以看出,为了获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和信奉,观音信仰不惜与传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背后是民众渴求神人救赎的心理,更是民众寻求一种不分阶级、善恶等条件的精神诉求。
最后,就佛教传播的倾向性而言,什么样的灵验传闻更容易受到创作主体的青睐?这也是我们需要明确的。六朝灵验类小说主要是围绕《法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以下简称《普门品》)展开,宣扬观音灵验事迹,这一点可以从三种《观世音应验记》看出。六朝以后,灵验类小说宣扬神迹的范围则不仅包括观音菩萨和《观世音经》,还包括弥勒佛、地藏菩萨和《金刚经》等。由此也可以窥见佛教在本土传播的过程。
三、六朝灵验类小说的文化内涵
阐明灵验类小说的称名、构成要素和边界之后,我们再来看六朝灵验类小说。纵观整个灵验类小说,六朝灵验类小说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六朝灵验类小说和六朝以降灵验类小说一样,都要具备一般灵验类小说的要素,体现灵验类小说的本质。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六朝灵验类小说是在六朝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必然会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六朝以降灵验类小说相比较,六朝灵验类小说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第一,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宗教情感更深厚,宗教色彩更浓厚。如上所述,灵验类小说的创作主体是“为佛教文化所化之人”。他们对佛教信仰有着长期的生活体验或者深切的体悟,对佛教文化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六朝时期的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即《光世音应验记》《续观世音应验记》《系观世音应验记》),是当时有名的灵验类小说,后世也将其视为灵验类小说的典范之作②。从这些灵验类小说对当时灵验事迹的记录情形来看,没有对佛教信仰尤其是观音信仰的亲身体验,没有对佛教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仅凭个人想象或者查阅相关典籍,是很难融入佛教文化尤其是观音信仰文化的,更不会如此深情地去创作灵验类小说。
第二,这一时期的信仰对象和信仰仪式单一。六朝灵验类小说主要是围绕《法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以下简称《普门品》)展开,宣扬观世音菩萨的灵验事迹。这一点可以从三种《观世音应验记》看出。当然,也有关于《首楞严经》的,如《冥祥记》中的“谢敷”条、“董吉”条。但那是属于个别现象,主要还是渲染观音法力无边。六朝后灵验类小说则不仅仅局限于观音菩萨和《观世音经》,还包括弥勒佛、地藏菩萨和《金刚经》等,如唐临的《冥报记》和郎余令的《续冥报记》就是很好的例子。段成式则在《酉阳杂俎续集》中单列一卷关于《金刚经》的灵验事迹[23](265)。这一方面反映了六朝时期《观世音经》和观世音信仰在民众间的盛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民众信仰较之六朝以后,呈现出单一化倾向。这一点与佛教在其本土传播的过程是相吻合的。
第三,六朝灵验类小说宣扬观音神力表现在“济七难”“满二求”上。其中“济七难”,是指《普门品》所宣扬的水、火、罗刹、刀杖、恶鬼、枷锁、怨贼;“满二求”则是指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考察这一时期的灵验类小说内容,“济七难”是最突出的,而这“七难”之中的刀杖和枷锁反复出现,展示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心理诉求,也为我们从佛教文化层面判断六朝灵验类小说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路径。
六朝以后的灵验类小说则不然,宣扬观音神力也有关于“济七难”方面的,但重点逐渐转移到了“满二求”上,这一点在明清时期的灵验类小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佛教世俗化密切相关。于是救难的观音转变为送子观音,而这些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因为“只有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式样,从那些不为人们所重视而又被人们反复实践着的日常生活中,从那些视而不见行而不觉的风俗习惯中,去发现那些隐蔽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动机,去探讨他们的真实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才是更科学更可靠的途径”[2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与“释氏辅教之书” “佛教小说”“观音应验故事”等称名相比较,灵验类小说之说更符合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借鉴了文学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并综合考量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定义如下:灵验类小说是指六朝以来小说创作主体是“为佛教文化所化之人”,对佛教信仰有着长期的生活体验或者深切的体悟,出于对佛教文化的认同,以宣扬佛法灵验为主要内容,以因果报应观为主导思想,旨在劝善惩恶、弘扬佛理、吸收信徒,风格意趣相近的志怪小说。灵验类小说的叙事内容由形式和意识两个层面构成,形式层面严格依循纪传体来撰述,交代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及出处,从而营造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上的空间,力求予人以真实感受;意识层面,灵验类小说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叙述,来展示当时民众的社会心态和信仰心理、习俗,构建当时的社会空间。要之,六朝灵验类小说侧重对观音灵验事迹的记录,是时代主题的反映,也是佛教文化传播进程的映射。
注释:
① 这里稍费笔墨,对“灵验”和“应验”的区别以及笔者为何要选择“灵验”一词进行一个简要说明。“灵验”和“应验”意思相近,但也存在细微的区别,“应验”一词的含义是指后来发生的事实与之前所预测的结果相符,而“灵验”除了有证实了之前的预测外,还强调了灵妙不可思议的效果,而联系六朝时期的这些小说来看,大都有称道灵异的意思在其中。鉴于此,笔者采用“灵验”一词来总括这类小说的特征。
② 比如,唐人唐临《冥报记》序云:“昔晋高士谢敷、宋尚书令傅亮、太子中书舍人张演、齐司徒事中郎陆杲,或一时令望,或当代名家,并录《观世音应验记》;及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宣验记》、王琰作《冥祥记》,皆所以征明善恶、劝惩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唐临.冥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2)。可以看出,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已被后人视为典范之作了。
[1] 许慎. 说文解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5] 萧统.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6] 董志翘.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7] 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8] 僧祐. 出三藏记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9] 周叔伽, 苏晋仁. 法苑珠林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0]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2.
[11] 杜贵晨. 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12] 王昊. 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58.
[13] 楼宇烈. 东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灵验故事杂谈[J]. 中原文物特刊, 1986: 45.
[14] 郑阿财. 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M].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2010.
[15] 夏广兴. 试论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 2004(3): 81−87.
[16] 竹内敏雄. 艺术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17] 徐龙飞. 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故事类型研究[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8] H.R姚斯, R.C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19]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20] 葛红兵, 肖青峰.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5): 67.
[21] 张兴龙. 扬州小说”概念界定的理论阐释[J]. 明清小说研究, 2016(3): 17−31.
[22] 陈寅恪. 寒柳堂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3] 段成式. 酉阳杂俎续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4] 王齐洲. 论文学与文化——兼析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文化分析的必要性[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 1997(6): 22−27.
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efficacious novel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GU Wenb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s to efficacious novels as a special type of fiction, there is no agreed appellation and defini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From the theory of novel typology, the name and definition of efficacious novels are not only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content, but also the form and connotation. By combining these with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present essay attempts to undertake further combing of efficacious novels, believing that the subjects of their creation are “those cultivated by Buddhist culture” who strongly share cultural identity with Buddhism, and that the content of narration consists of such two levels as form and consciousness. In a word, efficacious novel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lay emphasis on recording Kuanyin's efficacious deeds, which is the theme of that age, reflecting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Buddhist culture as well.
the Six Dynasties; efficacious novels; naming; definitio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编辑: 胡兴华]
2017−03−29;
2017−08−1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辩正”(15FZW057)
谷文彬(1987−),女,白族,湖南张家界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小说史及小说文献
I242.1
A
1672-3104(2017)06−01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