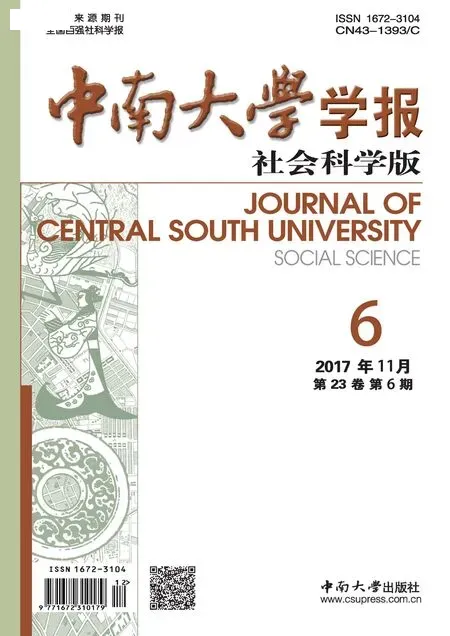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与“诗”学阐释的本质
——以“刺诗”“淫诗”之争为中心
2017-02-03石超
石超
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与“诗”学阐释的本质——以“刺诗”“淫诗”之争为中心
石超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从接收者“二次叙述化”的视角看,“刺诗”与“淫诗”的界定其实是不同时期的解释社群在面临《诗经》文本时,采取不同的“二次叙述化”方式导致的结果。“刺诗”与“淫诗”之争的本质也是不同时期的解释社群在接受《诗经》时的“二次叙述化”方式之争。解释社群不同,“二次叙述化”的方式就不同,对“诗”旨的阐释也就不同。
朱熹;接收者;二次叙述化;刺诗;淫诗
在《诗经》接受史上,“淫诗”与“刺诗”的界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某种程度上而言,孔子“不删郑卫”的做法就注定了后世的这一场“刺诗”与“淫诗”之争。汉儒以齐、鲁、韩、毛“四家诗”为代表,后来《毛诗》和郑“笺”被定于一尊,以“刺诗”为主导;从唐至五代,以孔颖达为代表,他们延续汉儒的看法,甚至将毛“传”和郑“笺”视为经文遵奉,以“美刺之说”解诗;宋儒以朱熹为代表,其《诗集传》背离“诗序”传统,认为国风中多有淫奔之辞,形成了与“刺诗”截然对立的“淫诗”之说;从元至清代,儒生则多复引“诗序”,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当下仍有不少学者研究“淫诗”与“刺诗”问题:如廖群先生从作者自言、代言视角切入,认为“诗序”以代言视之,是“刺诗”之作,《诗集传》以自言解之,为“淫诗”之作[1];莫砺锋先生则认为朱熹“淫诗说”的实质是正视人的情感,是从经学走向文学的转向[2]。除上述两位先生外,还有不少研究者涉足这一论题,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基本上都是立足于从《诗经》文本本身出发,为“刺诗”和“淫诗”的界定寻找立论依据。
从文本视角出发是解诗的传统路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淫诗”与“刺诗”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但从另一层面而言,这种解诗路径在确立“淫诗”与“刺诗”的标准时无法得到圆融的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完全从文本出发,并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面临一首叙事结构极其简单的诗歌文本时,“诗序”和朱熹的解释为何截然相反。而从接受的视角出发,可能更容易找到比较圆融的解释。因为每位读者在接收一个叙事文本时,其实都经历了接收者“二次叙述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意义的生成并不仅仅由文本构成,而是由文本的叙事框架和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共同 生成。
一、“刺诗”与“淫诗”之争的症结
朱熹和“诗序”关于“刺诗”“淫诗”的分歧主要在《国风》部分,且集中在《郑风》《卫风》和《陈风》中。《诗集传》言:“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恶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3]可知朱子并不认为郑、卫之诗皆为淫诗之作,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认为“卫人犹多刺讥惩恶之意”。也就是说,朱熹认可“诗序”所谓“刺诗”的解诗路径,但是认为其中有部分“淫诗”之作,即两者在解诗的路径上有其共通性,只是对少数诗作的认定存在差异。
关于朱子指认的“淫诗”篇目,后世学者多有争议,原因在于朱子的衡量标准并不明确。为廓清“诗序”和《诗集传》关于“刺诗”“淫诗”的认定标准,兹录表1进行比较:
朱熹从未正面阐述过究竟何为“淫诗”,但从朱子对诗篇的断语、与时人的问答以及后儒对“淫诗”说的辩解中,大抵可以推证出“淫诗”观念的核心要义。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根据《诗集传》所认定的“淫诗”篇目,提出淫诗即“指以为男女淫泆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4]。此概念中有两条标准,一是“男女淫泆奔诱”,意指诗歌所叙之内容;二是“自作诗以叙其事”,意指诗歌的叙事方式,需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是“淫诗”。通过细读表1朱子对于“淫诗”的判断后,我们发现,马端临所认定的两条“淫诗”标准,其实并不完全准确。

表1 《<毛诗序>与<诗集传>“淫诗”对照表》
就诗歌所叙之内容而言,“男女淫泆奔诱”并不是一条特别明晰的标准,原因在于其衡量标准是变动不居的。如《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陈风·月出》等诗作,《毛诗序》皆言“美刺”,而《诗集传》独标“淫奔”,今日看来,这些诗作亦不过是男女之间纯粹的感情之事,难说一定是“美刺”或“淫奔”。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诗作内容的界定是有偏差的,不可一概而论,朱熹量定的“男女淫泆奔诱”之辞,在别人看来未必尽然。就诗歌的叙事方式而言,虽有统一的标准,却无法丈量所有的诗作。如朱子认为《郑风·出其东门》即是“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可知非自作诗。在表1所胪列的“淫诗”中,朱子仅言《郑风·溱洧》乃“淫奔者自叙之词”,《郑风·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郑风·狡童》是“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除了这三首可视作是“男女淫泆奔诱而自作”外,其余“判词”的言说方式与《毛诗序》无异,无法直接判断是否为自作诗,从诗作内容层面亦难下定论。对于“非淫诗”的界定,朱熹也多用“自作”之语,如《周南·卷耳》,“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邶风·谷风》,“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卫风·伯兮》,“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这些诗均是自作诗,而朱熹却认为是“美诗”或“刺诗”。因此,用自叙诗这种叙事方式来界定“淫诗”亦不完全准确。联系上述两条标准来看,由于“男女淫泆奔诱”的标准不够明晰,所以很多诗歌即便满足了“自作诗以叙其事”的条件,亦不能形成统一的标准,认定其为 “淫诗”。
联系马端临总结的“淫诗”标准和朱熹对“淫诗”所下的判词,我们不难发现,《诗集传》与《毛诗序》阐释“诗”旨的言说方式并无二致,多是联系本事,直指诗作意旨。至于诗作本事何谓?则难有定论,“刺”“淫”之争自此而出。换言之,如果我们单从诗作文本出发,并不能总结出一条清晰明确的“淫诗”标准,既完全贴合朱子的判断,又能令儒生信服,那么,就只能从文本之外的因素寻求根源。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马端临才进一步阐明:“《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于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泆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5]也就是说,诗人的身份(“叙情闵劳者”“困役伤财者”“奔者”或“刺奔者”)以及诗篇所叙写之本事(“爱叔段”或“刺郑庄”)等“外部因素”成为判定诗歌性质的重要依据。不仅如此,此前的宋代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如黄曛在转述孔子与子夏关于“绘事后素”的问答后,盛赞子夏言《诗》的方式曰:“《诗》之为《诗》,岂可于言语文字间而有得哉?”[5]即要真正体悟《诗经》的旨趣,就必须超脱言语的桎梏。
综上可知,单从诗歌所叙之内容或本事并不足以厘清“刺诗”与“淫诗”之争的实质,还需要寻求文本之外的因素。
二、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与《诗经》的接受
通常认为,“叙述就是讲故事,给一系列事件以特殊的形式,从而产生相当于或大于各个部分之总和的意义”[6]。这里的叙述是指向叙述者的,即叙述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形式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组成一条有意义的符号链,呈现出开放性的结构以供读者接受。以《郑风·将仲子》为例,全诗以女主人公为叙述者,一边反复申述“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又一边自陈内心“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此诗既有当下时空的心理感受,即“仲可怀也”,又有对未来事件的预叙,即逾我里而折我树杞将导致父母之言,逾我墙而折我树桑将导致诸兄之言,逾我园而折我树檀将导致人之多言。此诗叙述者将当下与未来串联起来,事件与事件之间形成前后相连的情节结构,最终建构起一条有意义的符号链,顺利完成了叙述的任务。
如果说传统的叙述观念只涉及到叙述者这一个主体概念的话,那么现代叙述观念则关注到了两个主体,即除了叙述者这个主体之外,还有接收者这一主体的叙述问题。具体而言,“叙述包含两个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第一个叙述化,是把某种事件组合进一个文本;第二个叙述化,是在文本中读出一个卷入人物的情节,这两者都需要主体有意识的努力,两者经常不相应,但接收者解释出文本中的情节,是叙述体裁的文化程式的期盼。”[7]换言之,叙述者的叙述是“一次叙述化”,而接收者的叙述是“二次叙述化”。所谓“一次叙述化”,其实发生在文本构成过程中,即“在一个文本中加入叙述性,从而把一个符号文本变成叙述文本”[8](106),其过程就是符号的情节化加媒介化,如上文提及的《郑风·将仲子》文本。“二次叙述化,发生在文本接收过程中。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为叙述文本。这个过程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也并不只是回顾情节,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8](106)如《毛诗序》、郑玄、朱熹等人对于《郑风·将仲子》的理解,即是对文本完成“二次叙述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作为“一次叙述化”的文本而言,文本本身只是一条有意义的符号链,但无法直接昭示意义,它呈现的是一个开放性的情节结构,必须通过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才能最终实现其意义的传达。
“二次叙述化”不同于读者反应理论和接受美学,虽然后两者也认为文本意义的生成必须依靠接收者,但“二次叙述化”并未赋予读者更多的内涵和权力。在接收者“二次叙述化”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无标准的无限衍义,而是必须奉行一定的标准,即遵循“一个社会文化中的‘解释社群’在接受文本时大致遵从的规律”。简言之,就是把文本中的时间、人物、情景、变化等叙述因素加以“落实”,挖掘文本的意义[8](107),即“读者用一定的方式读出文本中的意义”。根据二次叙述要完成任务的复杂程度,赵毅衡先生将其分为四个等次:对应式二次叙述,见于“人文性”相当弱的叙述,如情报信息的传达;还原式二次叙述,见于情节比较混乱的文本,需要重建文本的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见于情节非常混乱的文本,需要再建文本的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见于情节自相矛盾到逻辑上不成立地步的文本,需要创建文本的叙述[8](107)。对于文学文本而言,简单的对应式二次叙述并不足以发掘出文本的深层含义,必然是还原式二次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甚至更多地需要创造式二次叙述。
除了必须遵循一定的方式外,“二次叙述化”的主体还必须是“拥有文化条件和认知能力的‘解释社群’”,因为“二次叙述能力并不是天然的,部分可能来自‘人性’(人类讲故事的能力),更大的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修养,此种能力,是某个文化中的人长期受熏陶的产物”[8](108)。换言之,并非任何一个接收者都能顺利完成“二次叙述化”的任务,它需要接收主体长期濡染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修养,拥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才能理解文本中的深层含义。正如一个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接收者,很难挖掘出《红楼梦》的深层含义。从《诗经》的历代接收主体来看,可以说他们都具有较高层次的社会文化修养,从小就饱读诗书,阅读理解能力自是不差。郑玄、朱熹等经学大师,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此可知,对《诗经》进行“二次叙述化”的接收主体都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之所以出现了“刺诗”与“淫诗”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原因在于“二次叙述化”的方式不同所致。
三、创造式“二次叙述化”与“刺诗”“淫诗”之争的实质
上文论及,“一次叙述化”文本无法直接昭示其意义,必须依靠接收者的“二度叙述化”才能最终生成其意义,且对“二度叙述化”的主体和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对于《诗经》而言,文本本身已经完成了“一次叙述化”,即文本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有意义的符号链,需要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来昭示其意义。作为《诗经》的历代接收者而言,也都是完全可以胜任“二次叙述化”任务的主体,即“解释社群”的行为个体。以《郑风·将仲子》为例,诗中的男女主人公、两者之间的故事以及故事发生的时间和情境都是相对明晰的,并未出现情节混乱或是逻辑不清的情况。全诗选取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呼号的“顷刻”,既可上溯到“顷刻前”——女主人公“仲可怀也”的心理,亦可推至“顷刻后”——折我树杞而致父母之言,整个故事简明直白,讲述的就是热恋中的少女对“仲子”的深情及矛盾心理。也就是说,“一次叙述化”所呈现出的叙述文本并不难理解,那么接收者在“二次叙述化”时无需大费周章即可“落实”文本的潜在意义,且意义的指向也应相对固定。
但从《郑风·将仲子》的实际接受情况来看,文本衍生出的意义并不是相对固定的,而是截然相反。《毛诗序》云:“《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郑玄笺云:“庄公之母,谓武姜。生庄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无礼。公不早为之所,而使骄慢。”朱熹则认为此诗为“淫奔者之辞”,即前两者认为是“刺诗”,而后者认为是“淫诗”。姚际恒和方玉润又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姚际恒认为:“女子为此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及人言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9]方玉润亦不认为是“淫诗”,“女子既有所畏而不从,则不得谓之为奔,亦不得谓之为淫。”[10]不难发现,后世接受者在面对《将仲子》这一叙事结构完备、情节逻辑清晰的文本时,本该指向相对固定的意义,却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综观《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陈风·月出》等《诗经》中的其他诗作,其结论亦是如此。也就是说,作为完全可以胜任“二次叙述化”任务的主体,在面对“一次叙述化”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文本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究其原因,只能是“二次叙述化”的方式不同所致。
对于叙事结构完备、情节逻辑清晰的叙述文本而言,只需对应式“二次叙述化”即可挖掘出其潜在意义。既然后世接受者对于《诗经》文本的解读不尽一致,则非对应式二次叙述、还原式二次叙述和妥协式二次叙述所能实现的,定是接受者在面对“在道义伦理上过于‘犯忌’的文本”时,进行了创造式“二次叙述化”,才衍生出不尽相同的解读结果。“某些叙述明显违反道德和文明准则,但是又不得不接受之,此时就必须找出文本的‘代偿价值’。任何叙述必须以道义立足,要想让犯忌的主题立足,就必须更新社会的道义准则,这在文学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8](113)如对于《红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一类的作品,既无法采取对应式或还原式二次叙述,又不能妥协,因此,“二次叙述就必须创造新的道德理由来接受 之”[8](113)。后世接受者对于《诗经》的解读即是如此,至于为何进行这种创造式“二次叙述化”,就得从《诗经》内容的编选中寻求答案。
一般认为,《诗经》乃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载:“‘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1]孔子返回鲁国的时间是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其编选《诗经》当在此之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记有吴国公子在鲁国观乐一事,其载:“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12]综合史料可知,早在孔子编选《诗经》之前,“郑音”的靡靡之态就已凸显。但这里的《诗经·郑风》与“郑音”是截然不同的,“郑风”反映的是当时正统的婚恋观念,是具有礼仪教化功能的,而“郑音”则是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所兴盛的通俗音乐。后世多混为一谈,所以诸多渲淫诲道之作才屡屡以孔子“不删郑卫”为借口,而宣扬其道统地位。如《青楼韵语》“弁言”即云:“如曰表章艳才、掇拾绮语,等于导欲宣淫,陷人于惑溺之蹊,则孔子大圣不删郑卫,渊明高士不讳闲情,亦得谓之导欲宣淫乎?玄度子云:‘此书从讲道学中得来。余亦以为此书非真道学者不能读’。”[13]
孔子编选《诗经》的宗旨在于教化民众,所选篇章的思想内容必然符合当时的礼制规范,正如其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足见所选诗歌的正统性和典范性。虽然《郑风》《卫风》多为爱情诗歌,但诗歌所反映的内容符合当时的礼仪。如《郑风·扬之水》表达了夫妻白头偕老的愿望,《郑风·出其东门》传达了男子对女子的忠贞之心,《郑风·萚兮》反映了上巳节男女相会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由此可见,诗中描写仲春之月的男女相会是符合周礼的,且是受到鼓励的。
《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不难发现,《毛诗序》对于“诗”旨的阐释与孔子编选《诗经》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即不仅要反映当时的婚恋习俗,还要隐喻一些政治事件,达到或“美”或“刺”的效果,以实现其教化意义。与后世相比,周代的婚恋观呈现出更大的自由度,但《毛诗序》和郑玄所处的时代毕竟已不同于周礼时期,原本符合周礼的爱情诗歌,此时恐怕难以被解释社群接受。因此,当《毛诗序》和郑玄迫于当时《解释社群》的压力时,并不能直陈其为“淫诗”,只能进行一番改造,进行创造式的“二次叙述”。即“当二次叙述者的忍耐力与道德能力推到极端,如果接收者,甚至整个解释社群承受不起,就会选择放弃,叙述交流就此中断。此时就必须假以时日,文化有可能让解释社群得到足够的‘教育培养’,改变接受态度”[8](113)。《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为了维护《诗经》的道统地位,也为了维护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面对道德上无法还原也无法妥协的“靡靡之音”时,《毛诗序》采取了创造新的道德理由的方式来诠释它,即将原本简单还原的二次叙述演变为创造性的二次叙述,以示刺示戒的方式迂回到道统上来,强化诗歌的教化作用。换言之,接受者必须将原本所谓的“诲淫诲盗”之诗强行纳入“经”书范畴中,符合其宣扬的“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才能维护其“经”书的地位。
我们发现,在汉儒阐释“诗”旨的过程中,除了力图维护诗教传统外,还因礼教观念的变化出现了对于爱情诗歌的不同理解。如经师们已用“淫风”(《郑风·溱洧》)、“淫佚”(《卫风·氓》)、“淫昏”(《陈风·东门之池》)、“淫乱”(《邶风·匏有苦叶》)、“淫奔”(《齐风·东方之日》)、“淫恣”(《桧风·隰有苌楚》)等词汇诠释诗旨,爬梳汉代“三家”《诗》之传说,亦是如此。清代王先谦认为“三家”诗对于《齐风·南山》《陈风·泽陂》等诗的诠释与“毛诗序”相似,均是讥刺君臣淫乱国中[14]。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汉儒对于《诗经》意旨的解读虽涉及到“淫”字词汇,但都创造性地回归到了“刺诗”道统上。这一点,清人也早已言明,“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15]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的“解释社群”得到了越来越多教育的培养,他们的接受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原本符合周礼的爱情诗歌此时再难让人信服,但囿于诗教传统的强大话语体系,只能遮蔽掉已现端倪的“淫诗”观念。
清代学者陈启源认为《诗经》中有“淫奔之辞”的观念应源于康成,其言:“郑以为女欲奔男之词,遂为朱《传》之滥觞也。”[16]可以说朱熹的“淫诗”说滥觞于汉代,他是将原先遮蔽的“淫诗”观念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直接呈现给了世人。因为对于《诗经》而言,宋儒是新的解释社群,汉儒那一套创造式“二次叙述化”得出的结果并不足以使他们信服,反而会显得欲盖弥彰。与汉儒不同的是,宋儒在论诗时,“诗”的创作主体及其叙写对象都变成了平民,不再是汉儒所认定的“庙堂”“公族”。如朱熹在认定“淫诗”时,常言某诗即是“男女淫奔”“男女相悦”之辞,而不是刺某公、某王、某公室。不仅如此,朱熹还在对《东方之日》序文的辩说中,直言《诗序》所谓“君臣失道”于诗义无征,荒谬无伦。不难发现,汉儒解诗的“美刺”框架逐渐被瓦解,诗旨不再指向上层的君主、公族,对其进行讽谏,而是转而成为吟咏普通男女情性的篇章。这种由上向下的转移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潜移默化中随着解释社群的变化而呈现出来的,这种变化趋势与文学叙述对象的下移也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宋儒们不再需要像汉儒那样为了维护经学道统之地位,重新创造新的价值观念,他们逐渐拆解了汉唐《诗经》学中的“美刺”阐释框架,显示出对诗歌真义的自觉反思,同时,也开启了对“思无邪”观念的重新解读。这种态度既源于宋代对汉唐学术的反思,也是宋人欲超越权威而必然采取的一种选择。
宋儒在正视“淫诗”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以心性解诗的路径。如姜夔认为:“《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17]而这也直接开启了清儒以心性观念消解朱熹“淫诗”之说的大门。由宋到清,《诗经》的解释社群又发生了变化,清儒们对《诗经》意旨的解读也随之而变,他们既不同意朱子的“淫诗”说,又无法回复到汉儒时代的“美刺”传统,因此,以应撝谦、毛奇龄为代表的清儒们从心性的视角对朱子的“淫诗”说进行了辩解。如毛奇龄对读《诗经》“思无邪”的观念给出了清晰的说明:
读《诗》无邪,读“淫诗”则必不能无邪。《桑中》、《鹑贲》皆刺淫诗。刺淫非淫,犹之刺暴非暴,刺乱非乱也,故可读。若朱子所改“淫诗”,皆君臣朋友,缠绵悱恻,刺心洞骨之语,一变作淫,则如嫪毐言淫事从胏肠道出,魂魄俱动,焉得无邪?故宋元中子(即黎立武)作《经论》谓:少读箕子《麦秀歌》惄焉流涕,稍长读《狡童》而淫心生焉,一若邻人之妇,皆目挑而心招者。既久读《小序》,然后知《狡童》刺忽,爽然自失。盖读《诗》之全系于说《诗》如此。今既已妄说,而又欲责读者以无邪,是置身娼室,亲闻咬声,而使之正心,其为大无理、大罪过莫甚于此。[18]
应撝谦亦云:“(淫诗)当时采之既不存其实,则读之亦不以其柄。或以意逆志、尚论其世;或赋诗断章、予取所求,今之毛、韩两家是也。皆善诵之微理也,读之不以其柄,则取之各以其意,不以淫诗解之,唯所欲言耳。”[19]不难发现,毛奇龄和应撝谦亟待消解掉朱子“淫辞”的概念,以重新建构起对“诗”旨的合理阐释。
综上所述,因为解释社群天然带有时代印记,所以不同时期的《诗经》接受群体,在阐释“诗”旨时会选择不同的“二次叙述化”方式,即便是都采用了创造式“二次叙述化”的方式,也会带有各自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因如此,各个时代的“诗”旨阐释才不尽相同。无论是汉儒的“美刺”传统,朱子的“淫诗”之说,还是清儒的以心性释“淫诗”,其实都不是面对《诗经》这一简单叙事文本进行的对应式“二次叙述化”,而是在各自解释社群的左右下所做出的一次较为合理的“二次叙述化”。因此,“刺诗”与“淫诗”之争,其实是不同时期的解释社群接受《诗经》时“二次叙述化”的方式之争,妥协接受《诗经》文本也罢,悬置文本、重新建构道德标准也罢,都是特定时期的解释社群选择“二次叙述化”的结果。
注释:
①马端临认为朱子所定“淫诗”有24篇([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第1540页);莫砺锋定为30篇(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檀作文定为28篇(檀作文著:《朱熹诗经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程元敏定为29篇(程元敏著:《王柏之生平与学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版,第863页);吴洋定“淫诗”25篇,“准淫诗”3篇(吴洋著:《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
[1] 廖群.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解释[J]. 文史哲, 1999(6): 57−63.
[2] 莫砺锋. 从经学走向文学: 朱熹“淫诗”说的实质[J]. 文学评论, 2001(2): 79−88.
[3] 朱熹.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72.
[4]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40.
[5] 于连·沃尔夫莱. 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13.
[6] 赵毅衡. 叙述者的广义形态: 框架——人格二象[J]. 文艺研究, 2012(5): 15−23.
[7]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8] 姚际恒. 诗经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01.
[9] 方玉润. 诗经原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936.
[11] 李梦生. 左传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866.
[12] 朱元亮, 张梦征. 青楼韵语[M]. 上海: 永印书局, 1914: 3−4.
[13]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83−384, 479.
[14] 程廷祚. 青溪文集[M]. 清代诗文集汇编(269),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4.
[15] 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C]//清经解(卷六四), 上海: 上海书店, 1988: 367.
[16] 姜夔. 白石道人诗说[C]//历代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81.
[17] 毛奇龄. 四书改错[C]//续修四库全书(165),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61.
[18] 应撝谦. 性理大中[C]//续修四库全书(950),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11.
The second narration and 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of: Taking argument of Ci and Yin as example
SHI C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In the view of’s accep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 (刺) and Yin (淫) is the difference of “second narration ” strategies adopted by different interpreting groups and the “second narration” is the nature of the argument of Ci and Yin. Different interpreting groups adopt different ways of “second narration” and therefore, the meaning of poetry is different.
ZHU Xi; accepters; second narration; Ci poetry; Yin poetry
[编辑: 胡兴华]
2017−03−18;
2017−07−2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152DB067)
石超(1984−),男,湖北钟祥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论
I207
A
1672-3104(2017)06−01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