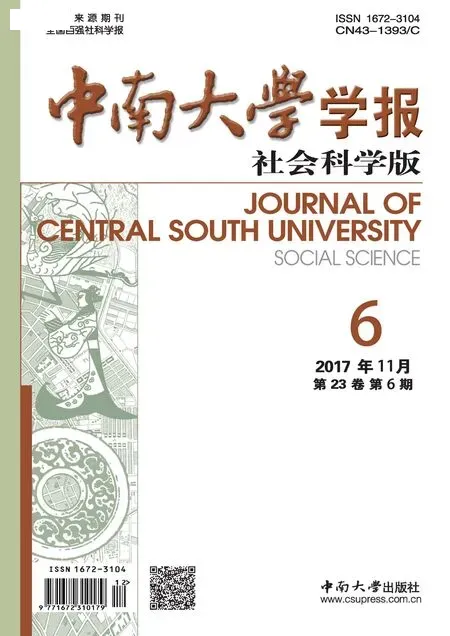从舍浊求净到浊净双遣
——论禅宗禅法思想之演进
2017-01-11汪韶军
汪韶军
从舍浊求净到浊净双遣——论禅宗禅法思想之演进
汪韶军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禅宗工夫论有一个从离妄归真,到即妄归真,再到无真可求、无妄可断的发展历程。早期禅宗与北宗主要破“浊边过患”,因而强调离妄归真,讲求拂的过程与定的工夫。而破除“浊边过患”不是南宗的特色所在,南宗主要讲“净边过患”,力破真妄之分及舍妄归真的修行方式。他们强化并贯彻般若空观,把一般禅僧所执着寻求的“净边物事”架空,防止对“净”的执着以及禅修实践上的沉空滞寂。南宗实则是把“浊边过患”与“净边过患”同时打掉,既不贪着于世间利益,也不执着于“净边物事”,从而达到彻底的不二中道、无分别、无取舍。
禅宗;般若空观;不二中道;“浊边过患”;“净边过患”
南宗禅沩仰宗祖师沩山灵祐(771—853)指出:“从上诸圣,只是说浊边过患。”[1](150)所谓“从上诸圣”,非从时间维度指称沩山之前的禅师,而是指早期禅宗(六祖慧能之前)、北宗及延续其禅法思想者。“边”为概念对子的其中一方;“只是说浊边过患”意为,早期禅宗、北宗这一法脉一味强调“浊”之患害并执着地舍“浊”求“净”,殊不知住于“净”亦同为患害。当然,后面一层意思沩山并未明确说出,且整个禅宗乃至佛教中都未出现“净边过患”一语。笔者现在基于六祖(638—713)及其弟子荷泽神会(684—758)批评“净妄”“细妄”的事实,拈出“净边过患”,这是切合南宗禅禅法思想的。
笔者在此尝试着由“浊边过患”与“净边过患”这对概念入手,探究禅宗禅法思想的演进过程,以及南宗禅心性论与工夫论的特色。我们将会发现,南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宗派,一般都把重点放在根除“浊边过患”之上,结果导致理论上未能融贯及修证工夫上的紧张;南宗禅则特别注意防止“净边过患”,他们消解了实体化的心,也有力地破除了真妄之分及舍妄归真的修行方式。通过这种研究还可发现,南宗禅一系列“革命性”的禅法思想,总根源在于他们将般若空观与中道思想贯彻到底,这是对佛教根本思想的深刻领悟。
一、早期禅宗与北宗禅法思想的重要源头
我们从对早期禅宗和北宗影响很大的几部经论开始说。《楞伽经》是印度后期大乘佛教思想的代表之作,其中的如来藏思想对早期禅宗佛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唐代以前,它有两种汉译本:436年刘宋求那跋陀罗的四卷本,以及513年北魏菩提流支的十卷本。两种译本相比,四卷本较为忠实,十卷本则添枝加叶太多,甚至偏离了本义。比如,四卷本将佛性与人心看成一事,十卷本则将两者截然二分,这是两种版本的最大分歧。
《大乘起信论》在十卷本《楞伽经》的基础上踵事增华①,其如来藏系统是一个典型的真心与客尘相对的系统。此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心开二门:“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2](16)二门的区分就基于真妄之分。《起信论》虽然强调生灭心与真如心非一非异,但说得更多的是两者的对立。论主认为,人由于无明而生妄念,妄念起则真心被遮蔽,故而从本觉的状态沉沦到不觉的状态中:“众生心者,犹如于镜。镜若有垢,色像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现故。”[2](156)但是,无明毕竟无根,真心终不泯灭。在缠之真心(即“妄心”“染心”)尽管是染污的,但由于其本性是清净的,所以保留了未来中还归清净的可能性。为此,众生应该以其真如去熏无明,达到觉了的境地,这是从不觉到始觉。就这样,依本觉有不觉,依不觉有始觉,这是一个偏离心源到回归心源的历程。众生本有光明觉体,但无明遮蔽了根本智,只有去迷妄、觉心源,方为究竟觉。可见,《起信论》中存在着真心与妄心的紧张对立,所以吕徵先生说:“《起信》所据的《楞伽》实际是十卷本而非四卷本。换句话说,《起信》完全用染净二心之说来组织其理论体系,根本上否定了一心说。其先慧可那样不避艰难坚持所信定要用四卷本《楞伽》来创宗立说,不意传到弘忍、神秀,口头虽说是慧可以来的一脉相承,而思想的实质,通过《起信》已经无形中与十卷本《楞伽》合流而面目全非了。”[3](309)
另一方面,《起信论》认为,真常心自体不空:“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2](22)这里是说,空是就妄心而言,并非说真心是空的。论主又认为,要去掉迷妄而达到还灭:“所言灭者,唯心相灭,非心体灭。……唯风灭故,动相随灭,非是水灭。无明亦尔,……唯痴灭故,心相随灭,非心智灭。”[2](71)因此从总体上看,《起信论》说的真心虽然是一个“虚样子”,但毕竟有“体”义在,这就与佛教缘起空观有所出入。应该说,《起信论》表现出来的空观是不彻底的。
以上十卷本《楞伽经》《起信论》的心性论可归结为:强调真妄之分,并认为真心不空。心性论是禅修实践论的基石;有什么样的心性论,就有什么样的禅修实践论。真心与妄心的对立,决定了这些经论在工夫论上的思路便是离妄归真。以《起信论》为例,论主强调无念、离念,而他说的念有正邪之分,要离弃的念是邪念,要依止的念是正念:“众生真如之法体性空净,而有无量烦恼染垢。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熏修,亦无得净”[2](137),“若出家者,为折伏烦恼故,亦应远离愦闹,常处寂静,修习少欲、知足、头陀等行”[2](161),“若修止者,住于静处,端坐正意。……心若驰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2](167)。论主还主张止观双修,而观有无常观、不净观、苦观等等。这些都造成修证工夫上的紧张及理论上的未能圆融。
二、早期禅宗与北宗对“浊边过患”的破除
在十卷本《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影响下,早期禅宗与北宗为了回归自性清净心,在禅修方式上也讲求拂的过程与定的工夫。据神秀再传弟子净觉《楞伽师资记》所载,禅宗初祖达摩(?—536)有《二入四行论》:“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教。”[4](156)同书载三祖僧粲(?—606)语:“猴着鏁而停躁,虵入筒而改曲。”[4](160)此喻来自《大智度论》卷二十三:“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为三摩提,秦言正心行处。是心从无始世界来常曲不端,得是正心行处,心则端直,譬如蛇行常曲,入竹筒中则直。”[5](234上)这类思想认定心“常曲不端”,所以在禅修实践上非常强调把持工夫,注重的是矫,而不是任。
四祖道信(580—651)的主张似乎有了很大变化。《楞伽师资记》载有他的答问:“问:临时作若为观行?信曰:直须任运”[4](163),“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念,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问:何者是禅师?信曰: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4](162)《五灯会元》卷二记载他对弟子牛头法融说:“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义,总在心源。……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6](60)
但是,道信虽然提倡“直须任运”,反对“沉没”,他的根本主张仍是调伏:“身中常空净,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4](165)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也谈无念,但他说的无念指排除妄念转而念佛:“《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 字。”[4](160−161)(标点经笔者重新点定)杜朏《传法宝记》亦载道信常劝门人“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 语”[7](178),又载五祖弘忍(599—672)“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7](179)。《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亦载弘忍“以坐禅为务”。
方立天先生总结说,道信与弘忍的东山法门,“一言以蔽之,就是静态渐修的坐禅、念佛和观心、守 心”[8](378)。其实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从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早期禅宗主要就是突出这一面。北宗的禅法思想更是如此。创始人神秀(606—706)得法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此偈可以说概括了早期禅宗与北宗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神秀的禅学思想至死未变,其“屈、曲、直”三字遗嘱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三、空观的全面贯彻与禅修实践的变革
如果说早期禅宗与北宗主要破“浊边过患”,那么,南宗则主要破“净边过患”,这是把般若空观运用到“净边物事”②上来的必然结果。
自佛教创立以来,空观便是佛教的一个根本观念。它是对万物性相的照察和判断,但最终是要落实到生活态度上来的,使不要执着世间利益的说教获得更大的说服力。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其般若思想中最重要的也是空观。我们知道,般若空观由“析空”“散空”“相空”进到了“当体空”,由果空进而认为因亦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般若空观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即认为有为法是空,佛法亦空。因为,既然佛教强调“一切法无我”,而这个全称判断也应涵盖佛法,不然就会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前部派佛教时期的说一切有部认为佛说的一切都是终极真理,大乘佛教则强调佛法也只是一种善巧方便。《金刚经》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佛说X,即非X,是名X。我们可以将相、世界、众生、庄严佛土、第一波罗蜜、心、微尘、福德等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代入X,比如:“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9](749中),“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9](751下)。这是极为彻底的空观。既然如此,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9](749下)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9](752中)。可见,此类说法的意图就是破执,从而对一切法(包括佛法等“净边物事”)有一个全新的 认识。
强调佛法的空性,必将引发禅修实践的变革。大乘初期,小品《宝积经》(即《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鲜的看法:“明与无明无二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10](633−634),“一切持戒成就禅定,终不能得坐于道场,成无上道”[10](634下)。那么,沙门应该如何修行呢?“于诸法无所断除,无所修行,不生生死,不着涅槃,知一切法本来寂灭,不见有缚,不求解脱,是名实行沙门。”[10](636中)这里据中道思想指出,住于“净”不能成无上道。诸法平等一相,皆虚诳如幻,所以分别取舍没有意义。舍浊求净(或者说离妄归真)也是分别取舍,而分别取舍是对空幻不实之法进行执着!
为了防止对“净边物事”的执着以及禅修实践上的沉空滞寂,后来的《维摩诘经》亦不惜强调同于烦恼入诸邪见,甚至谤佛毁法。此经《不思议品》说:“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法无戏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是则戏论,非求法也。……法各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非求法也。……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 求。”[11](610)苦集灭道是原始佛教提出的四谛(意为四大真理),佛、法、众就是佛法僧三宝,“于一切法应无所求”也否定了对三宝、四谛等的执着。《文殊师利问疾品》:“贪着禅味是菩萨缚。”[11](607)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攀缘佛道是贪着,出离三界是妄想;无三界可出,无涅槃可得。究其原因,这些都是分别见,违背不二法门,也违背了般若空观。《菩萨品》:“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三界是道场,无所趣故”[11](597−598),“断是菩提,舍诸见故。离是菩提,离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诸愿故。不入是菩提,无贪着故。……无乱是菩提,常自静故。善寂是菩提,性清净故。无取是菩提,离攀缘故。无异是菩提,诸法等故”[11](596−597)。
四、南宗禅对“净边过患”的大力破除
从早期禅宗与北宗,到南宗,都推崇一些经论④,但所推崇的经论有了很大变化:由推崇十卷本《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等,变为推崇《金刚经》和《维摩诘经》等。比如,《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便是慧能悟道的机缘,后来慧能无住为本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此。而其“出入即离两边”的主张,深契于《维摩诘经》的不二中道(此经在《坛经》中有时称《净名经》);慧能又依《维摩诘经》“直心是道场”对一行三昧做了重新诠释,这与四祖道信依《文殊说般若经》将其释为舍妄归真截然不同。
如前所述,北宗倾向于将真心实体化、对象化;南宗则将般若空观贯彻到底,从而消解了心的实体色彩。针对神秀得法偈,慧能也做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中,“佛性常清净”在后世被改成“本来无一物”。有关此偈的争论从未中断过。杨曾文先生认为两者没有本质区别。郭朋先生认为这是篡改者把般若思想的“性空”误解为“本无”,然后用它来否定妙有的佛性思想[12](17−18)。杜继文等人则认为表现了两种不同倾向的佛性学说,是“两个慧能的对立”[13](130−131)。笔者以为,真空是空,妙有还是空,郭氏之见证明他本人对“妙有”尚嫌执着。“佛性常清净”即使不被改为“本来无一物”,原偈的关键字就已经是“无”,即用般若空观来破除对象化的执实和把持,所以杨氏观点近乎事实。当然,改动之后更加凸显了对北宗看心看净的批评。这是将六祖所说的“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进一步展开,不能理解成“两个慧能的对立”。
北宗看心看净是用真心去对象化地拂拭、把持妄心,慧能则指出:“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14](123)这里明确说,执着于净,会生出“净妄”。南宗所说的本心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清净心。传统意义上的清净心(如北宗要“看”的心)被慧能斥为虚妄,因而,南宗说的本心是连“净妄”都已被破除的彻底清净之心。前面“佛性常清净”亦应如此理解。马祖弟子大珠慧海(生卒年代不详)说:“菩提无所念。无所念者,即一切处无心”[15](842下),“一切处无心是净。得净之时不得作净想,即名无净也”[15](843下)。“无净”实指不住净,传统的清净心也被无掉了,所以南宗虽然也讲心,但此心已是无心之心、任心之心。
南宗禅又从不二的角度力破真妄之分。据《坛经》记载,神秀弟子志诚转述北宗三学:“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14](151)可见,北宗时时不忘分别善恶,调伏妄心。慧能则针对性地说:“心地无非是自性戒,心地 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是自性慧”,“得吾自性,亦不立戒、定、慧”[14](151),“邪正悉不用,清净至无 余”[14](146)。这就是用般若空观把“浊边过患”与“净边过患”同时打掉,不思恶亦不思善(此处的善恶非就伦理道德而言,而是意指好坏、真妄、净浊),达到彻底的不二中道、无分别、无取舍。
慧能对北宗的批评点到即止,神会则加大了火力:“贪爱财色、男女等,及念园林、屋宅,此是粗妄,应无此心。为有细妄,仁者不知。何者是细妄?心闻说菩提,起心取菩提;闻说涅槃,起心取涅槃;闻说空,起心取空;闻说净,起心取净;闻说定,起心取定,此皆是妄心,亦是法缚,亦是法见。若作此用心,不得解脱,非本自寂净心。作住涅槃,被涅槃缚;住净,被净缚;住空,被空缚;住定,被定缚。作此用心,皆是障菩提道。”[16](8)神会指出的“粗妄”与“细妄”,大致对应于沩山指出的“浊边过患”与笔者拈出的“净边过患”。“粗妄”指对世间利益的执着,但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神会批评的重点显然不在“粗妄”,因为自佛教产生以来,便一直在批,其他宗派乃至一般思想界都不缺乏此类思想,所以神会只用一句话带过。神会的重点是批评“细妄”(即其师慧能指出的“净妄”),因为“为有细妄,仁者不知”,此正沩山所言:“从上诸圣,只是说浊边过患。”“细妄”意谓“净边物事”亦为虚妄,但舍妄归真者不明白这一点,所以需要强调着说,反复地说。神会明确指出:“净亦是相,是以不看”[16](122),“只如学道,拨妄取净,是垢净,非本自净”[16](13)。“垢净”指以净为净,这样的净如同金屑在眼,也会成病;而“本自净”则指不分浊与净,如此方能彻底清净。方立天先生比较过早期禅宗与南宗在心性论上的区别:“在准备期,禅师多偏于真心与妄心的对立,强调去妄求真,灭妄存真;而兴盛期的禅师则强调真心和妄心的统一,甚至不讲妄心,主张直指本心(真心),顿悟成佛。这是在慧能,尤其是在马祖道一、石头希迁以后,与慧能以前禅师的心性论乃至整个禅学教义的主要分歧所在。”[8](369)这一判断是比较准确的。
与心性论相应,禅宗工夫论也有一个从离妄归真,到即妄归真,再到何有妄真(无真可求,无妄可断)的发展历程。北宗强调拂的过程与定的工夫;南宗则以慧摄定,否定形式化的戒定及舍妄归真的修行方式,从而得到大解放,活泼自由,透脱自在。
慧能吸取《维摩经》的有关思想,对坐禅、禅定做了重新解释。《景德传灯录》载其语:“道由心悟,岂在坐也?”[1](81)“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1](85)慧能所说的坐禅不是静坐息虑,不动不起,而是“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内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14](124),做到“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 在”[14](122)。慧能指出,坐禅习定是障道因缘,作茧自缚,求法反为法拘。需要注意,“一切境界”“万境”“离相”等说法都是包括“净”在内的全称判断。
神会亦否定作意摄心:“去心既是病,摄来还是病,去来皆是病。……莫作意,即自性菩提”[16](13),“只如‘凝心入定’,堕无记空。……‘住心看净,起心 外照,摄心内证’,非解脱心,亦是法缚心,不中 用”[16](9−10),“法身体性不劳看。看则住心便作意,作意还同妄想团。放四体,莫攒玩,任本性,目公官。善恶不思即无念,无念无思是涅槃”[16](128),“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不看净,不观空,不住心,不澄心,不远看,不近看,无十方,不降伏,无怖畏,无分别,不沉空,不住寂,一切妄相不生,是大乘禅定”[16](122),“一切善恶,总莫思量,不得凝心住,亦不得将心直视心”[16](9)。应该说,神会对北宗看心看净的批评是非常深入的。
五、结论
早期禅宗与北宗在十卷本《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等经论的影响下,偏重妙有的佛性论,他们将真心实体化,并突出真妄之分,故在工夫论上重在破除“粗妄”“浊边过患”,其禅修实践于是表现为舍妄归真而住于“净”。
但是,执着于“浊”是执着,执着于“净”还是执着。执着的对象虽然不同,就其为执着而言,则没有什么不同。既然佛教的根本目的是破除各种执着以达到智慧解脱,则从逻辑上来说,就也要防止“净边过患”,而这一点几乎是南宗禅以外其他佛教宗派的理论盲点。看不到这一点,就容易在理论上有违空观与中道思想,禅修实践上则走向沉空滞寂。
南宗则从《金刚经》《维摩诘经》等经典中吸收了彻底的般若空观与中道思想,他们消解了心的实体色彩,并同时强调“净边过患”,这样就把一般禅僧执着寻求的“净边物事”也架空了。禅师们认为,光不透脱,只因目前有物。就禅宗内部而言,“物”主要指“净边物事”,因为一般禅僧都能破除对世间利益的执着,却被“净”一叶障目。石头希迁弟子大颠宝通(732—824)说:“但除却一切妄运想念见量,即汝真心。”[1](268)“妄运想念见量”更指住于“净”之念想,因为破除其它念想并非南宗的特色所在,其他宗派没有哪家不讲,而且做得更绝对。对世间利益的破除,在南宗思想中的重要性已是次而又次。我们来看百丈怀海(749—814)对“心解脱”“一切解脱”的阐述:
问:“如今受戒,身口清净,已具诸善,得解脱不?”师【怀海】答曰:“小分解脱,未得心解脱,未得一切解脱。”问:“如何是心解脱?”师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畏地狱缚,不爱天堂乐,一切法不拘,始名为解脱无碍。”[17](642)
南宗全面贯彻般若空观与中道思想,既不执着于世间利益,也不执着于“净边物事”,且主要是把后一方面加以放大。也就是说,他们在其他宗派的基础之上,重在破除“净妄”“细妄”“净边过患”,故能“浊”“净”皆不住。南宗实际上要来个彻底清净,一尘不染,寸丝不挂。“净边物事”这类金屑落在眼里,哪会有什么般若眼?由于这一转折,禅宗的本心开始通向当下念念不断的现实人心。与此相应,禅修实践的世俗化与生活化倾向愈来愈浓。禅宗成为“人文主义的宗教”(柳田圣山语),原因就在这里。
注释:
① 《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在古代已是一段公案,到了近现代,更成为佛学研究中的一个争议热点。中日学者都曾就此展开过持久而激烈的论战,出现了中土撰述说、印度撰述说、翻译撰述混合说等。大体说来,更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部伪论。不过,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大乘起信论》并非中土伪撰,而是真谛的编译,参见杨维中:《梁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目录学考察——〈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二》,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笔者也不认为它是中土伪撰,而是把它当印度大乘佛教论书看。
② 此为笔者自造语,用以指称一般禅僧执着追求的佛、法、道、心、菩提、涅槃、经论文字等。
③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圭峰宗密(780—841)《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卷上释曰:“若人分别佛土是有为形相而言我成就者,彼住于色等境中。为遮此故,故云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等也。而生其心者,则是正智。此是真心。若都无心,便同空见。”(《大正藏》第33册,第161页中)按,宗密理解的“真心”似乎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净心”,其特点是与六尘对立而住于“净”。这种“清净心”与经中所说的“无所住心”其实不是一回事,因为“无所住心”强调的是无住,不住于包括“净”在内的一切相。《金刚经》:“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大正藏》第8册,第750页)而宗密说的“清净心”虽不住于“浊”却住于“净”,尚有笔者所说的“净边过患”。
④ 人们常说禅宗不立文字,并把它理解为摒弃语言文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不立文字不是不用文字,而是不执文字,不把经论文字立为权威以束缚自己(转法华而不被法华转)。从僧传和灯录等材料可以看出,大多禅师其实都熟悉经论,他们或悟前颇阅经论,或悟后读经以教人。
[1] 道原. 景德传灯录[C]// 蓝吉富. 禅宗全书(第二册). 台北: 文殊出版社, 1988.
[2] 高振农. 大乘起信论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3] 吕徵.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 石峻, 楼宇烈, 方立天, 等.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 龙树. 大智度论[C]// 鸠摩罗什, 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6] 普济. 五灯会元(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7] 杨曾文. 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8] 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9]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C]// 鸠摩罗什, 译. 大正藏(第8册).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10] 普明菩萨会[C]// 失译. 大正藏(第11册).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11] 维摩诘所说经[C]// 欧阳竟无.藏要(五). 上海: 上海书店, 1991.
[12] 郭朋. 坛经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3] 杜继文, 魏道儒. 中国禅宗通史[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4] 周绍良. 敦煌写本《坛经》原本[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15] 大珠慧海. 顿悟入道要门论[C]// 卍续藏经(第110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
[16] 杨曾文. 神会和尚禅话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7] 静、筠二禅师. 祖堂集(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From abandoning Zhuo and pursuing Jing to dispelling both Zhuo and Jing: On the evolution of Zen Buddhist Thoughts
WANG Sha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 Communic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Zen Buddhism of cultivation has such a development course: Firstly, it insists on turning away from Wang (妄) back to Zhen (真); then, it holds returning to Zhen without abandoning Wang; and finally, it emphasizes that there is neither Zhen to pursue nor Wang to abandon. The early Zen Buddhism and the Northern Zen mainly break away from harmfulness of Zhuo (浊), hence stressing the process of dusting and the effort of dhyãna. However, banishing harmfulness of Zhuo is not what the Southern Zen focuses on. They mainly remind us of the harmfulness of Jing (净), so they are opposed to distinguishing Zhen from Wang, and endeavor to stop sekha from abandoning Wang to return to so-called Zhen. The Southern Zen reinforces prajnã, carries it through to the end, and consequently undermines the so-called Jing which sekha persistently seeks. By doing so, they prevent sekha from clinging onto the so-called Jing and being addicted to emptiness in meditation practice. Actually, the Southern Zen simultaneously banishes the harm of both Zhuo and Jing. They neither attach themselves to secular interests, nor do they pursue the so-called Jing. Therefore, they attain complete madhyamā-pratipad: no differentiating, no admiring or detesting.
Zen Buddhism; prajnã; madhyamā-pratipad; harmfulness of Zhuo; harmfulness of Jing
[编辑: 谭晓萍]
2017−05−21;
2017−09−18
教育部“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子项目“海南文化软实力科研创新团队”(01J1N10005003)
汪韶军(1973−),男,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大乘佛教与禅宗
B948
A
1672-3104(2017)06−0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