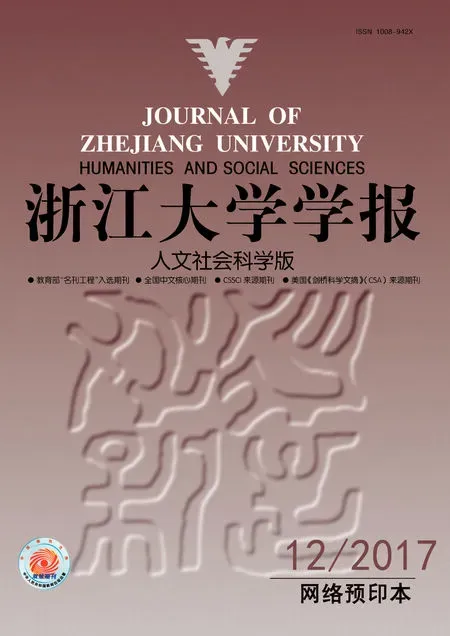论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责任适用
2017-01-11陈信勇叶增胜
陈信勇 叶增胜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说明义务是指一方当事人负有主动告知对方对其决定有重要影响之情事的义务[1]§241,Rn.110。说明义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广泛存在,并在民事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所承担的说明义务,也就是所谓的先合同说明义务。在现代社会,先合同说明义务对合同机制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如果信息上处于劣势的一方未能掌握必要的信息,那么其意思形成就会遇到障碍,其缔约决定也就无法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事实上,让信息上的优势方承担说明义务能够有效消弭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平衡,劣势方可由此获得自主决定的能力,在缔约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并对其缔约决定负责,使合同这一机制重新获得“担保正确结果”的功能[2]110。而对先合同说明义务来说,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违反后的责任承担,因此,如何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课以适当的法律责任,既可避免不同的责任制度在评价上发生矛盾以达成体系上的圆融,又能恰当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责任竞合及其适用困境
(一) 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
一般而言,合同责任以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在缔约前的准备商议阶段,一方当事人因他方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遭受侵害时,原则上仅能依侵权行为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但侵权行为的要件较为严格,不易具备,并且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磋商、谈判甚至订立合同时,彼此间的信赖随之俱增,权利义务关系乃有强化的必要,因而产生了介于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缔约上过失责任*先合同义务之违反由德国法学家耶林创设,在德文文献中通常表述为“culpa in contrahendo”,我国学者翻译为缔约上过失,其相应的责任为缔约上过失责任。就其内涵而言,缔约上过失责任中的“过失”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最为有力的证据就是缔约上过失在德文文献中又被称为“Verschulden bei Vertragsverhandlungen”,其中的“Verschulden”本身就是过错的意思,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其不仅包含过失,还包括故意的情形。因此,先合同义务违反之责任翻译成“缔约上过错责任”更为准确,更能全面体现对行为人主观要件上的要求。我国学界将其译成“缔约上过失责任”,可能是受我国台湾地区翻译的影响,因为有关缔约上过失责任的详细中文文献首先出现在我国台湾地区,典型的如王泽鉴《缔约上之过失》,载其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26页。此后,学界沿袭了该译名,详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24页。本文仍然采用“缔约上过失责任”的译法以符合我国学界的用语习惯,但需要明确的是,其中的“过失”应当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3]180。在我国,缔约上过失先是作为法学继受的产物被引进,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专门做出一般规定(第42条、第43条),至此,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为学说继受的成果正式被立法全面采用[4]124。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上,先合同义务的违反通常会涉及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2项明确要求当事人须就其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承担缔约上过失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加以规制,本身就属于缔约上过失责任主要的适用场合之一,缔约上过失责任也因此可以看作调整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行为的一般性规则。
(二) 恶意欺诈规则的适用
在合同订立前,如果一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而引起、加深或维持对方的错误观念,并使对方因此做出意思表示的,其行为就可能构成恶意欺诈*欺诈须基于故意,德国法上称之为恶意,因此故意欺诈与恶意欺诈只是用语不同,其内涵并无二致。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页。。恶意欺诈制度旨在保护意思决定的自由,并不涉及对财产的保护(如我国《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5]§123,Rn.20,因此不存在具体财产损害的情形同样可以适用。表意人在对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形下主张恶意欺诈的,可撤销其所订立的合同,且无须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6]。由此可见,主张恶意欺诈对表意人较为有利,但必须证明对方在主观上存在故意,因此在举证上难度较高。此外,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恶意欺诈情形的表意人须在发现欺诈的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该撤销权归于消灭,相较于缔约过失责任所适用的为期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依据新制定的《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从原来的两年变为三年。,该规定对表意人在权利行使的要求上更高。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民法上认为恶意欺诈的规定不能为其他规范所排除,否则就意味着对欺诈人的保护,实施了欺诈行为的人不具有受保护的理由[7]343。这一考量在中国法上同样适用。因此,尽管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可能会涉及缔约过失责任,但恶意欺诈并不会因此被排除,而是可以由当事人选择适用。
(三) 适用后果上的相似性
在恶意欺诈场合,表意人行使欺诈撤销权的,其所为的意思表示经撤销者,视为自始无效。因此,在一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并订立合同的情形,构成恶意欺诈的,对方须通过行使欺诈撤销权来使双方订立的合同归于无效。另一方面,主张缔约上过失责任的,依据我国《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一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缔约上过失所导致的损失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应当根据具体的情事加以确定。在一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形下,对方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通常表现为其因此订立了对自身不利的合同,而在正常情况下则根本不会订立或不会以这样的条件订立合同。此时,受误导的当事人将面临两难的困境:选择履行合同,将承受合同中的不利条件;选择不履行合同,则将因此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这一不利合同的订立本身就属于因过失违反说明义务的行为人给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失”,但要让相对人的利益状态恢复到不利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则需要让该不利合同的效力归于无效,使当事人从中解放出来并不再受该合同的拘束。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民法典》规定了统一的损害赔偿方法,并以恢复原状作为损害赔偿的原则,其第249条第1款规定,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恢复未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事时所应有的状态。一方因对方违反说明义务致使其订立对自己不利的合同,主张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德国民法典》第280条,241条第2款及第311条第2款),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要求对方恢复原状。在已订立不利合同的情形下,“恢复未发生致损情事时所应有的状态”的可行方式应当是废止该不利合同。因此,在缔约阶段,一方因对方违反说明义务致使其订立对自己不利的合同而主张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可以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的规定请求废止双方所订立的合同。
反观我国的现行法,新制定的《民法总则》第179条规定了11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分别是“(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其中的第五项“恢复原状”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其内涵不同于《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所规定的作为损害赔偿方法原则的“恢复原状”,通常仅指受到损害的财产(一般为有体物)通过修理等手段恢复损害前的状态[8];其余十项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从文义上看也并不可能包含“废止当事人所订立的、对其不利的合同”的情形。因此,在中国法上无法通过直接援引《民法总则》第179条所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来达到废止当事人所订立的、对其不利的合同的目的。而且我国《民法总则》第179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全文仅有法律后果,没有规定构成要件,其适用存在先天不足。另外,与德国法就损害赔偿的方法规定了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作为例外的立法模式不同,我国并未规定统一的损害赔偿方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的损害赔偿方法相较于德国法也更为多元,可以考虑通过对具体语境的解释来确定损害赔偿的方式。就当事人因对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而订立对其不利的合同的情形来说,主张废止其所订立的合同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在现行法上也已有部分专门性规范对此加以明确,如我国《保险法》第16条以及《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第53条对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导致相对人因此订立不利合同的,都允许相对人通过解除合同来使不利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
因此,在中国法上,无论是通过行使欺诈撤销权来撤销合同,还是通过主张缔约上过失责任来解除合同,两者都能够取消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并使双方的利益状态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在法律后果上趋向于一致。
(四) 过失情形的适用困境
恶意欺诈与缔约上过失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并不相同,其中最为显著的不同点在于,缔约上过失责任在主观要件上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但要构成恶意欺诈,则行为人的主观要件仅限于故意。因此,在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同时有缔约上过失责任以及恶意欺诈规则的适用,此时,当事人可以择一主张,两者在适用后果上的相似性并不会导致彼此的构成要件被规避。
但是,在对方仅具过失而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形下,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此情形,表意人由于主观要件上的限制无法通过主张恶意欺诈来撤销其所做的意思表示,却可以通过主张缔约上过失责任来解除合同,使自己从所订立的合同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与行使欺诈撤销权相似的法律效果。此时,恶意欺诈主观上的故意要件就因为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行为人仅具过失情形的适用而被规避,其最终也将导致合同法中的欺诈制度整体失去意义[9]。因此,在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需要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性做进一步的考察。
二、 理论上的解释可能及其局限
在理论层面,对于在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下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会造成恶意欺诈主观上的故意要件被规避的适用困境,我国学者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对恶意欺诈中的故意要件进行扩张解释,使其涵盖“过失欺诈”的情形,其理由在于故意还包括意图层面的要素,并且根据意图的强弱还可以继续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对意图强度的不同理解以及将不同强度的意图与认知要素相结合,完全可以将故意的意涵扩张至过失的领域[9]。但这样的解释已经明显超越了“故意”本身的文义,也不符合传统民法理论对恶意欺诈的主观要件的界定[10]281,因此无法解决恶意欺诈主观上的故意要件因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而被规避的难题。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德国法上对过失情形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性也有专门的讨论。有学者通过对相关条文的考察,认为《德国民法典》在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设置了故意责任[11]16,据此,行为人在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场合无须承担缔约上过失责任。还有学者提出,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须以存在具体的财产损害为要件,仅有不利合同的订立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当事人并不能通过主张缔约上过失责任来废止合同。具体来说,Lieb教授认为,在德国现行法中明确区分意思自由与损害,并分别为两者规定了不同的惩罚机制,对于这种现行法上的体系性区分,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越雷池半步,否则就相当于规定了一般性的反悔权,凭借这一反悔权,合同当事人能够在事后通过援引说明义务毫不费力地从已经显示出对自己不利征兆的合同中“金蝉脱壳”[12]。Stoll教授则更进一步认为,通过损害赔偿方法中的“恢复原状”(《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来达到废止合同的法律后果与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基础并不相符,其原因在于缔约上过失责任并不保护意思自由,仅仅是先合同义务的违反并不会导致债法上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发生[13]。联邦法院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但又稍有不同,认为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发生必须以存在财产损害为前提,仅仅只是合同的缔结并不会自动构成损害[14]。应该说,须存在具体的财产损害这一构成要件无疑提高了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门槛和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恶意欺诈与缔约上过失责任的竞合可能带来的冲突。也有学者肯定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性,认为应当承认一般性的基于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合同解除权[15]。即便是在新债法颁布之后,德国法上缔约上过失与欺诈的评价矛盾仍然存在,并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关于上述评价矛盾的争论还将长期存在[9]。
三、 现行法上的破局: 《合同法》第42条的解释适用
就立法层面来说,我国现行法似乎已经对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能否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给出了明确答案。学界通常认为我国《合同法》第42条及第43条已对缔约上过失责任做出了规定[4]136,其中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上述条文中与先合同说明义务直接相关的是第2项规定,从文义上看,该项规定要求在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况下,要构成缔约上过失责任,当事人主观上必须存在“故意”,但并不包括“过失”的情形。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进路。由于《合同法》第42条还在其第3项规定了兜底条款,这也就意味着除该条第1项及第2项所规定的情形外,“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能将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纳入该兜底条款的调整范围之内,则同样有可能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一般认为,先合同义务须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托,诚实信用原则又通过先合同义务及其他附随义务而具体化[4]136。具体到说明义务,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并不负有一般性的说明义务,尤其是交易双方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利益对立状态时,信息不对称反倒是达成交易的条件。一般来说,当事人何时负有说明义务,需要结合个案情形,依据诚实信用与交易观念而定[10]280。德国法院的判例对说明义务的发生提供了一套公式,即“在对方当事人依据诚信原则并顾及交易观念对于事实的说明有期待可能性的,并且该事实对于对方当事人的意思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则发生说明义务[1]§241,Rn.124。可以看出,说明义务通常都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发生的。在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说明义务已经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其特殊性在于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失而非故意。从《合同法》第42条的架构上看,其第1项所规定的“恶意磋商”及第2项所规定的“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同样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只是立法者鉴于其重要性而对其单独加以规定。从常理上说,因为《合同法》第42条第2项仅规定了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形,就认为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该条第3项所规定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是不合适的。过失相对于故意虽然在可非难性程度上有所降低,但仍然属于缔约上过失责任一般性的归责原则。因为通常对构成缔约上过失责任的主观要件的要求,过失即为已足,并不要求存在故意。从比较法上来说,德国民法对违反说明义务构成缔约上过失责任在主观要件方面也并未做出特别的规定,而是适用《德国民法典》第276条关于债务人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即存在故意或过失即可。据此,则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属于《合同法》第42条第3项所称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因此,从解释上来说,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同样也可以纳入《合同法》第42条第3项之中,从而同样可以构成缔约上过失责任[9]。
此时,似乎可以发现,由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进路,对我国现行法中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是否排除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依然没有定论。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合同法》第42条第2项是专门针对先合同说明义务进行规制的条款,立法者只肯定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做法可能蕴含着对该情形所涉利益的特殊考量,因此相对于该条第3项所规定的兜底条款,第2项的规定属于特殊规定。按照特殊规则优先于一般规则的基本原则,《合同法》第42条第3项不应适用于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形,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也就不能通过适用第3项的兜底性条款构成缔约上过失责任。可以作为对照的是《合同法》第42条第1项的规定,有学者认为依据该项中“恶意进行磋商”的文义,只包括恶意开始磋商和恶意继续磋商两类,无法涵盖恶意终止磋商之情形,因此,若要将中断磋商之行为纳入缔约上过失责任制度的框架,通常只能通过该法第42条第3项“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解释来确定[16]。从中可以看出,缔约上过失责任之所以能通过第42条第3项的兜底条款适用于中断磋商的情形,其原因在于中断磋商并不在该条第1项所规定的“恶意进行磋商”的文义射程范围内,但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本身就是该条第2项所规制的对象,不应适用该条第3项所规定的兜底性条款。
通过对《合同法》第42条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认为其第2项规定明确限定缔约上过失责任仅适用于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而排除了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行为人仅具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可能性。同时,考虑到缔约上过失责任适用于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所导致的恶意欺诈主观上的故意要件被规避的困境,应当说现行法上的这一安排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能够有效避免体系上扞格不入的困境。
四、 重大误解的功能性补位
(一) 过失责任的必要性证成
事实上,否定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并不表示行为人无须对其过失行为承担任何责任,此时尽管无法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也应当通过其他途径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其理由在于:
首先,虽然恶意欺诈制度仅就行为人的故意行为进行了规定,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法律无意非难其过失行为以及否定其所应承担的责任[14]。理由在于,在一方存在过失行为的情况下,另一方非因过失而为对方所误导,后者无疑更具保护的必要。对整个民法体系而言,对法律行为的决定自由的保护是维护私法秩序的核心任务,一旦行为人无须为其过失行为承担责任,则对法律行为的决定自由的保护就是不周延的,相对人将因此单独承担所有的风险[14]。此外,根据《民通意见》第68条的规定,在恶意欺诈情形,欺诈人之故意不仅包括实施欺诈行为之故意,而且包括令相对人因此陷入错误并基于错误做出意思表示之故意[10]281,由此可见,对故意要件的证明绝非易事。因此,对过失情形行为人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予以肯定还能产生有益的“副作用”,亦即弱化恶意欺诈中故意要件证明的严苛性,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
其次,肯定行为人须就其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行为承当相应的责任,能够有效提升从事法律行为的主体对法律秩序的整体信任度[14]。一旦行为人仅须就其故意行为承担责任,相对人将单独承担前者因过失未说明或未能正确说明的风险。因此,在合同磋商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行为人所做说明的信任,担心其因过失未说明或未能正确说明,相对人不敢轻易相信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在获取相关信息时需要更加谨慎,甚至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核实或进一步获取必要的信息。长此以往,对整个社会而言,其整体的交易成本将显著提高,先合同义务原本能够尽可能地确保交易往来的顺利进行、降低合同磋商的成本的功能也将因为当事人之间信任的缺失而大打折扣。
最后,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国法律基本上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过失责任予以肯定[14]。首先在大陆法方面,奥地利的《普通民法典》中并未规定缔约前的义务,但学说上肯定一般性的缔约上过失责任,特别是错误说明或违反义务应说明而未说明情形的责任。奥地利最高法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改变了从前否定因过失而误导的看法,转而肯定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赔偿责任。在瑞士法中,瑞士联邦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强调缔约上过失责任不以恶意行为为前提,而且在丰富的文献中也并未出现以《瑞士债法典》第28条第1款中对欺诈撤销情形要求主观上存在故意为由提出异议的情况。在法国法中,实务与学说基于《法国民法典》中第1382条的侵权条款肯定了过失违反说明义务的情形,并当然地与《法国民法典》第1116条所规定的恶意撤销并行不悖,其教义学上可能出现的对故意要件的规避在法国学界及其文献中很少提及,其原因可能是过失行为只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性质就可以予以认可。在意大利法中,可以从《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中推导出其肯定过失违反说明义务的情形,根据意大利学界的通说,负有说明义务的合同当事人不仅须就其已知的情事进行说明,而且对其应当知道的情事也负有说明义务[14]。在英美法方面,英国合同法则规定了错误说明责任,其功能相当于德国旧法中的第123条、第463条以及缔约上过失责任,与欧洲大陆的恶意撤销不同,其对主观要件进一步进行了区分:不仅包括故意和过失错误说明的情形,而且还包括非因过失错误说明的情形,因此,在因过失应说明而未说明的情形,义务人承担一般性的过失责任。美国合同法同样肯定因过失错误说明或者应说明而未说明的责任,在合同法领域,被误导的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在侵权法领域,被侵害人可以因此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14]。
(二) 重大误解的适用性探讨
1.适用的可能性探讨
对于重大误解的界定,《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以及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在合同情形,重大误解通常发生于合同订立的过程中。不仅如此,重大误解与合同的订立或合同条件存在因果关系更是其构成要件之一,具体来说,正是误解导致了合同的订立,如果没有这一误解,当事人将不会订立合同或者虽然订立合同但合同的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否则不构成重大误解[17]。在一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况下,对方可能会因为缺乏相应的信息而对与合同相关的情事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因此缔结与自身意思相悖的合同,此时就可能构成重大误解。而且,重大误解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一方在主观要件上并无要求,因此,在行为人仅具过失的情形也同样适用。可见,在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重大误解确实具备适用的可能性。
2.适用的合理性探讨:与恶意欺诈的竞合关系
在适用的可能性之外,尚需进一步探讨的就是在此情形适用重大误解是否合理,特别是其适用是否会与恶意欺诈发生矛盾或冲突。就该问题,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民法的通说认为恶意欺诈与意思表示错误可以自由竞合[7]343,其原因在于主张恶意欺诈撤销权并不发生信赖利益的赔偿,但主张意思表示错误却必须向相对人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因此,在恶意欺诈与意思表示错误自由竞合的情况下,就其实体效果来说,基于恶意欺诈的撤销权对撤销权人更为有利[10]283。表意人通常会选择主张恶意欺诈来撤销合同,以避免在主张意思表示错误时所面临的信赖利益赔偿问题。但在中国法上,两者是否可以自由竞合则存在疑问,其原因在于中国法上并未要求主张重大误解撤销权的表意人赔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18]。对于中国法上的这种做法,学界持批评意见者甚多[6,18-20],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法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选择了尊重表意人的自由却全然不顾相对人信赖保护的立法模式,该立法明显落后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当加以修正[6]。但即便是在新制定的《民法总则》中,也并未要求主张重大误解的表意人承担信赖利益的赔偿。因此,由于缺乏表意人赔偿信赖利益的规定,如果允许重大误解与恶意欺诈自由竞合,表意人选择行使恶意欺诈撤销权在实体效果上不会比行使重大误解撤销权更为有利,而且在程序上,主张恶意欺诈的举证责任更重:当撤销相对人表示异议时,受欺诈的撤销权人必须证明对方存在恶意欺诈行为[10]283。因此,在允许两者自由竞合的情况下,表意人将更倾向于选择主张重大误解撤销权,从而导致恶意欺诈的规定被规避。
但即便是在规定有信赖利益赔偿的德国民法中,其适用也存在例外的情形。德国民法于相对人引发错误的情形,排除信赖利益赔偿的适用,而适用与有过失的规定。其理由在于,信赖利益的赔偿实质上属于与有过失的特别规定,从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出发,应当适用信赖利益赔偿的规定;但在相对人引发错误的情形,错误的意思表示不再是表意人所独有的风险范畴,此时信赖利益赔偿的规定不再适用,而应当适用更具普遍性的与有过失规则[21]。事实上,德国民法要求主张意思表示错误的表意人向相对人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其理由在于意思表示的意义是可归责于表意人的,因此表意人必须对表示的意义承担责任;如果表意人表达有误,使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做出了不同于表意人所想表达的理解,那么表意人必须承认相对人实际所理解的意义是有效的[18-19]。这也就意味着,法律之所以要求表意人对相对人承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主要是着眼于通过保护相对人的信赖以尽量弥补撤销意思表示对交易安全所造成的不良影响[18]。有鉴于此,德国(《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第1款)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规定都要求表意人承担信赖利益的赔偿,其错误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表意人的意思自主、兼顾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及交易安全。但在缔约过程中一方违反说明义务使对方发生错误时,相对人的信赖不再具有保护的必要,表意人主张意思表示错误撤销权的则无须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这也就意味着在德国民法中,于相对人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表意人无须向对方承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这种利益衡量在中国法上也同样适用,因为信赖利益赔偿的根源在于错误的意思表示属于表意人自身的风险范畴,但在相对人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引发错误的情形,错误的意思表示的风险便不再由表意人自行承担,因此表意人也就无须向对方承担信赖利益的赔偿。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我国并未就重大误解撤销权规定信赖利益的赔偿,从而给重大误解与恶意欺诈能否自由竞合带来疑问,但由于在相对人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使对方发生错误的情形原本就应当排除信赖利益赔偿的适用,此时,中国法上未能在重大误解制度中规定信赖利益赔偿的规则安排不应当成为适用重大误解的障碍,而是应当允许当事人通过主张重大误解撤销权使自己从不利合同中解放出来而无须向对方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并适用与有过失的规则。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恶意欺诈撤销权为期一年的除斥期间,新制定的《民法总则》第152条将主张重大误解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从原来的一年缩短为三个月,这一变动要求表意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客观上也使重大误解撤销权与恶意欺诈撤销权在法律效果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区分。
五、 结论及展望
在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普遍存在的今天,先合同说明义务在确保合同机制有效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先合同说明义务之违反,有缔约上过失责任与恶意欺诈规则之适用。在一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并因此订立合同的情形,两者的适用都能够取消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使双方的利益状态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因此两者在适用的法律后果上具有相似性。但是,恶意欺诈与缔约上过失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并不相同,特别是缔约上过失责任在主观要件上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要构成恶意欺诈,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存在故意。因此,在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同时有缔约上过失责任和恶意欺诈规则的适用,当事人可以择一主张。在仅因过失而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情形,表意人由于主观要件上的限制无法通过主张恶意欺诈来撤销其所做的意思表示,却可以通过主张缔约上过失责任来解除合同,从而达到与行使欺诈撤销权相似的法律效果。此时,恶意欺诈主观上的故意要件就因为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而被规避,最终将导致合同法中的欺诈制度整体失去意义。
对于两者在过失情形的适用困境,有学者希望对恶意欺诈中的故意要件进行扩张解释,使其涵盖“过失欺诈”的情形,但这样的解释已经明显超越了“故意”本身的文义,同时也不符合传统民法理论对恶意欺诈的主观要件的界定。德国民法学者则试图以故意责任以及须存在具体的财产损害等来限制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的适用,但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在我国现行法上,通过对《合同法》第42条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认为其第2项的规定已明确限定缔约上过失责任仅适用于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而排除了在行为人仅具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可能性。同时,考虑到缔约上过失责任适用于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所导致的恶意欺诈主观上的故意要件被规避的困境,应当说现行法上的这一安排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能够有效避免体系上扞格不入的困境。
但否定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并不表示行为人无须对其过失行为承担任何责任,考虑到肯定过失责任在保护法律行为的决定自由、提高法律行为主体对法律秩序的整体信任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比较法上的大势所趋,应当通过其他途径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在缔约上过失责任之外,重大误解具备适用于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我国现行法不要求主张重大误解撤销权的表意人承担信赖利益赔偿责任的规则设置也并不影响重大误解规则在相对人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
从进一步研究的角度来看,对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责任竞合问题的研究能够在理论深度上触及恶意欺诈、缔约上过失责任以及重大误解这三大基本制度在整个民法体系上的定位问题,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进一步研究必须扎根于对上述三大基本制度的深刻理解之上。同时,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还能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厘清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缔约上过失责任、恶意欺诈以及重大误解之间的竞合关系,也就能够洞见三者在整个民法体系中作用和价值。
[1]Bachmann G.,MuenchenerKommentarzumBGBBand2:Schuldrecht-AllgemeinerTeil, 7.Auflage, Muenchen: C.H.Beck, 2016.[Bachmann G.,CommentaryofMunichtotheBGB,Vol.2:TheLawofObligations—GeneralPart(7thEdition), Munich: C.H.Beck, 2016.]
[2]Rehm G.,AufklaerungspflichtenimVertragsrecht, Muenchen: C.H.Beck, 2003.[Rehm.G,DutytoInforminContractLaw, Munich: C.H.Beck, 2003.]
[3]王泽鉴: 《债法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Wang Zejian,PrincipleofLawofOblig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4]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Han Shiyuan,TheLawofContract, Beijing: Law Press, 2011.]
[5]Hefermehl W.,SoergelKommentarBand2AllgemeinerTeil2.§§104-240BGB,13.Auflage, Stuttgart: Kohlhammer, 1999.[Hefermehl W.,CommentaryofSoergeltotheBGB,Vol.2,thegeneralpart2. §§104-240BGB(13thEdition), Stuttgart: Kohlhammer, 1999.]
[6]朱广新: 《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第114-120页。[Zhu Guangxin,″Cancellation of Declaration of Will Because of Mistake and Protecting Reliance of the Counterpart,″ScienceofLaw, No.4(2006), pp.114-120.]
[7]Bork R.,AllgemeinerTeildesBuergerlichenGesetzbuchs, 3.Auflage, Tuebingen: Mohr Siebeck, 2011.[Bork R.,TheGeneralTheoryofCivilLaw(3rdEdition), Tuebingen: Mohr Siebeck, 2011.]
[8]崔建远: 《关于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辨析》,《当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63-74页。[Cui Jianyuan,″A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is on Restitution and Restoration,″ContemporaryLawReview, No.1(2005), pp.63-74.]
[9]刘勇: 《缔约过失与欺诈的制度竞合——以欺诈的“故意”要件为中心》,《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55-70页。[Liu Yong,″On the Concurrence of Culpa in Contrahendo and Frand,″ChineseJournalofLaw, No.5(2015), pp.55-70.]
[10]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Zhu Qingyu,TheGeneralTheoryofCivilLaw,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Grigoleit H.C.,VorvertraglicheInformationshaftung, Muenchen: C.H.Beck, 1997.[Grigoleit H.C.,LiabilityofInformationinContractingPhase, Munich: C.H.Beck, 1997.]
[12]Lieb M.,″Vertragsaufhebung oder Geldersatz? Ueberlegung ueber die Rechtsfolgen von culpa in contrahendo,″ in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zu Koeln(Hrsg.),Festschrift600JahreUniversitaetKoeln, Koeln: Carl Haymanns, 1988, S.251-270.[Lieb M.,″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r Monetary Compensation,″ in Faculty of Law at University of Cologne(ed.),CommemorativeCollectionof600YearsoftheUniversityofCologne, Cologne: Carl Haymanns, 1988, pp.251-270.]
[13]Stoll H.,″Hafftungsfolgen fehlerhafter Erklaerungen beim Vertragsschluss,″ in Jayme E., Kegel G. & Lutter M.(Hrsg.),FestschriftRiesenfeld, Heidelberg: C.F.Mueller, 1983, S.275-300.[Stoll H.,″Liability Consequences of Erroneous Declarations in Contracting Phase,″ in Jayme E., Kegel G. & Lutter M.(eds.),CommemorativeCollectionforRiesenfeld, Heidelberg: C.F.Mueller, 1983, pp.275-300.]
[14]Fleischer H.,″Konkurrenzprobleme und die culpa in contrahendo: Fahrlaessige Irrefuehrung versus arglistige Taeuschung,″ArchivfuerdieCivilistischePraxis, No.200(2000), S.91-120.[Fleischer H.,″Competition Problems and Culpa in Contrahendo: Negligent Misdirection Versus Malicious Deception,″ArchiveoftheCivilLegalPractice, Vol.200, No.1(2000), pp.91-120.]
[15]Mertens B.,″Culpa in contrahendo beim zustande gekommenen Kaufvertrag nach der Schuldrechtsreform,″ArchivfuerdieCivilistischePraxis, No.203(2003), S.818-854.[Mertens B.,″Culpa in Contrahendo in Contract of Sale after the Reforms of Law of Obligatons,″ArchiveoftheCivilLegalPractice, Vol.203, No.6(2003), pp.818-854.]
[16]周江洪: 《缔约过程中的磋商义务及其责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7-15页。[Zhou Jianghong,″Duties and Obligations in Ccontract Negotiation,″JournalofShaoxing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6(2010), pp.7-15.]
[17]隋彭生: 《关于合同法中“重大误解”的探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第104-110页。[Sui Pengsheng,″An Exploration of the So-called ′Important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Contract Law,″ChinaLegalScience, No.3(1999), pp.104-110.]
[18]冉克平: 《民法典总则视野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构建》,《法学》2016年第2期,第114-128页。[Ran Keping,″Building the Mistake of Will Declaration System under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Code,″LegalScience, No.2(2006), pp.114-128.]
[19]梅伟: 《试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3期,第69-76页。[Mei Wei,″On the System of Untrue Declaration of Will,″GlobalLawReview, No.3(2008), pp.69-76.]
[20]张驰: 《论意思表示错误的认定及其效力》,《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3-19页。[Zhang Chi,″Identified and Effectiveness of Untrue of Declaration of Will,″JournalofShaoxing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2(2009), pp.13-19.]
[21]Singer R.,StaudingerKommentarzumBGB-Buch1: §§ 90-124; §§ 130-133(AllgemeinerTeil3), Berlin: de Gruyter, 2012.[Singer R.,CommentaryofStaudingertotheBGB-Book1: §§ 90-124; §§ 130-133(thegeneralpart3) , Berlin: de Gruyter,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