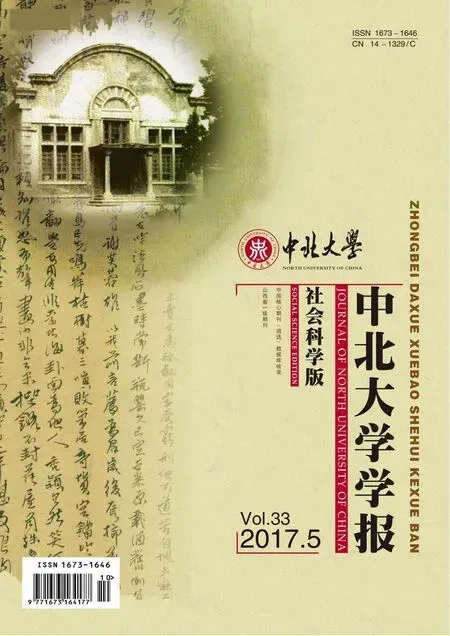经历·言说·回归
——托尼·莫里森《家》的战争创伤书写
2017-01-10詹作琼
詹作琼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经历·言说·回归
——托尼·莫里森《家》的战争创伤书写
詹作琼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家和创伤是莫里森小说的永恒主题。 在《家》中, 美国黑人从南方迁徙到北方工业城市, 在寻找身份建构过程中遭遇排斥、 隔离和创伤。 主人公弗兰克和妹妹茜的成长过程经历了罹患创伤、 言说创伤和回归正轨。 南方黑人社区为身处绝境的兄妹俩提供了庇护、 引导和治疗。 黑人社区力量在治愈黑人创伤、 保存民族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
《家》; 战争创伤; 黑人社区; 托尼·莫里森
0 引 言
2012年5月托尼·莫里森第十部小说《家》(Home)出版, 业界好评如潮, 该书虽然篇幅较短, 但是沿袭了莫氏一贯的优美文风、 诗意语言和极具悬念的叙述手法, 体现了浓浓的黑人民族的创伤。
创伤书写贯穿于托尼·莫里森四十余年创作生涯始终。 她在作品中反复再现了奴隶制、 白人种族主义、 父权制度对黑人和黑人女性造成的创伤。 从初出茅庐的作品《最蓝的眼睛》 (TheBluestEye), 到巅峰之作《宠儿》 (Beloved), 再到获得诺贝尔奖后首部作品《乐园》(Paradise)和2012年的《家》(Home), 每一部著作都充满了黑人民族浓浓创伤。
《家》围绕黑人士兵弗兰克的经历展开。 他和妹妹茜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洛特斯小镇度过了抑郁的童年, 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小镇生活, 他和儿时玩伴迈克尔和斯塔夫奔赴朝鲜战场, 然而残酷的战争夺去了好友生命。 战后, 弗兰克在北方芝加哥与黑人女工莉莉相爱, 但两人爱情最终由于物质主义和种族主义对黑人民族的内化而幻灭。 此时, 位于北方亚特兰大的茜蒙难, 弗兰克将她带回洛特斯, 并在社区黑人妇女的帮助下救活了茜, 完成了自己的创伤治疗过程。
在《家》中, 主人公弗兰克对朝鲜战场的回忆, 穿插着现实和梦境, 深刻地再现了战争创伤对黑人士兵的伤害。 仔细推敲, 莫里森在《家》中体现出有别于前九部作品的乐观精神, 并首次将战争创伤作为故事发展的主线。 国内外对《家》的研究热度和深度远不及莫里森的其他作品, 为了扩大《家》的批评视阙, 挖掘深层内涵, 本文尝试运用耶鲁创伤学派批评方法分析小说主人公弗兰克的战争创伤, 探讨莫里森小说在书写历史、 表征创伤、 探索黑人创伤治疗方面的现实意义。
1 朝鲜战场: 经历创伤
《家》中弥漫的创伤气息离不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 《家》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4年。 朝鲜战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死伤人数角度来看, 此场战争吞噬了约58 000名美国士兵的生命, 美军死亡人数远超后来的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人数的总和。 从战争舆论宣传角度来看, 美国政府号召士兵为真理和荣誉而战, 高举匡扶正义、 铲除邪恶的旗帜。 然而, 这场旷日持久、 伤亡惨重的战争结果却不尽人意, 而美国政府战后也未能兑现对少数裔军人的承诺, 民众开始怀疑战争的初衷。 战后经济开始复苏, 但是白人群体和有色人种经济差距继续扩大, 黑人在就业、 教育、 政治和薪酬方面备受歧视。 国际形势和国内种族问题导致民权运动开始萌芽, 黑人在反抗种族歧视过程中, 渴望寻找心灵的家园。 在《家》中, 莫里森再次赋予作品强烈的历史政治性。 她希望将美国各界的目光引向朝鲜战争对美国黑人民众所带来的伤害, 希望政府能认清20世纪50年代一片繁荣景象下尖锐的种族矛盾。
“创伤”(Trauma)本意是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 其当代核心内涵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 种族大屠杀、 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 毋庸置疑, 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创伤级别之高、 创伤后遗症都是最严重的。 耶鲁学派创伤研究的代表人物卡茹丝认为: “对于突如其来的、 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就是创伤, 而创伤引发无法控制的延后反应则通过幻觉或其他方式反复出现。”[1]96这是由于受创者无法理解突如其来的创伤, 导致创伤场景在“索引”的刺激下, 以“闪回”方式闯入受创者的生活, 这个过程是不可控制的、 无法预测的。[2]137
在朝鲜战场上, 弗兰克经历了三次让他心灵震撼的惨死情景: 被一枪轰飞了脑袋的朝鲜小女孩、 童年伙伴迈克和斯塔夫的相继殒命。 从战场归来, 弗兰克罹患了严重的“创伤后精神障碍”疾病。 回国后, 生活中任何与朝鲜战场相关的事物都会成为创伤记忆的导火索, 碎片化的创伤经历, 反复出现在弗兰克的意识中, 让他几乎崩溃。 “大海让他想起沉入水底的战士们冰冷尸体[3]6; 在列车上, 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正在把肠子塞回肚腹的男孩”[3]18; 在桥边看到的一个被救起的溺水小女孩, 弗兰克感到“悲伤像打桩机般击中了我(他)”[3]69; 在教堂, 一个小女孩的笑脸让他落荒而逃[3]77; 电影画面, 让他回想起, “在那片冬日风景的黑与白之间, 血的殷红成了主角”[3]18。 他经常“梦见狗或者鸟在吃他战友的遗体, 长着手指的脚, 或者是长着脚趾的手”[3]75。 除了“闪回”, 弗兰克还出现了生理和情绪问题, “一切色彩都消失了, 世界变成了一块黑白电影屏幕”[3]21。 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在夜里醒来, 攥着拳头, 一声不吭地坐在黑暗中”[3]78, 他“坐在沙发上直勾勾地盯着地板, 不管喊他名字或是靠近他的脸, 他都没有反应”[3]75。 战争的巨大创伤让弗兰克回国后在生理、 认知、 情绪和行为层面都出现异常。 短期色盲、 胃痛, 头晕、 幻觉、 闪回和噩梦不断困扰他; 情绪上, 他焦虑不安、 冷漠疏远、 容易愤怒。 战友的死让他深深自责, 只能靠终日酗酒麻醉自己。 通过对弗兰克罹患创伤后精神障碍的生动刻画, 莫里森揭露了战争对年轻人无可挽回的伤害, 也侧面表达了她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的反对。
2 洛特斯小镇: 言说创伤
“创伤治疗的重点是帮助受创者摆脱无法言语的恐惧, 完成创伤修复。”[4]23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安全感; 第二阶段追忆与哀悼; 第三阶段与他人建立联系, 回归正常生活。[5]56
从战场归来的弗兰克由于无法面对牺牲战友的家人和抑郁的小镇生活, 选择在北方芝加哥游荡, 但是北方却不是黑人的乐土, 在这里黑人被彻底边缘化。 这位在战场上从不退缩的英雄被警察抓进疯人院, 当他向梅纳德牧师求助时, 对方的目光充满鄙夷和敌意; 城市中的黑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 警察随时会对黑人进行搜身和管制, 并没收他们的财物; 有些白人警察视黑人性命为草芥, 即便黑人妇孺的安全也无从保障。 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不可使用公共厕所; 不得到白人的餐厅和商店购物, 黑人任何挑战或逾越黑白界限的行为都会招致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惩罚。 面对艰难的生活, 女友莉莉成了弗兰克的精神寄托。 莉莉是一名力争上游、 向往都市白人生活的黑人女性。 她梦想能够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 但是在攒够首付之后, 却被告知黑人没资格在该社区买房。 这对黑人恋人同样饱受种族主义歧视, 但内化了白人物质主义的莉莉与弗兰克对生活和前途有着不同看法。 莉莉将人生的成功等同于钱财的积累, 也逐渐对收入不稳定、 身无长物、 举止怪异的弗兰克心生厌恶。 北方工业城市剑拔弩张的社会关系、 艰难的经济状况将弗兰克彻底边缘化, 也直接导致他“创伤后精神障碍症”恶化。
喧嚣的北方都市并不是黑人的乐土, 而记忆中的南方故土又令弗兰克望而却步。 从小弗兰克和父母受到白人驱逐, 离开家园, 投奔在洛特斯的祖父。 到了洛特斯后继祖母丽诺尔尖酸刻薄、 父母忙于生计, 家庭未能给弗兰克和妹妹任何教育和爱护。 弗兰克和妹妹茜只能在社区四处游荡, 偶然目睹一群白人在马场草草掩埋了一具黑人的尸体。 亲眼目睹谋杀, 这种恐怖是年幼的孩童无法理解和克服的。 家人的刻薄和疏离也决定了无人为两个孩童进行心理疏导, 马场谋杀现场成了兄妹俩幼年的心理噩梦, 这也是弗兰克和茜不顾危险离开洛特斯的重要原因。 莫里森认为黑人女性担负着传承黑人文化的责任, 但是如果女性为白人种族主义或物质主义所侵蚀, 无视家庭责任, 那黑人家庭的福祉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将是镜花水月。[6]124《家》中的莉莉和弗兰克的继祖母丽诺尔都是属于内化了白人思想的黑人女性, 所以他们无法为爱人或亲人建立爱的家园。
然而妹妹茜病重, 在北方孤立无援的弗兰克无奈将妹妹带回南方故乡。 当弗兰克带着病重的茜回到南方洛特斯, 出乎他的意料, 黑人社区接纳了他们。 以埃塞尔小姐为首的黑人妇女们用传统的草药和天然疗法挽救了茜的生命; 同时引导茜坚强独立, 自信自强。 茜日渐恢复, 弗兰克也重新振作、 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摆脱酒精依赖的弗兰克开始重新审视洛特斯, 发现这里有着曾经被自己漠视的美丽。 “儿童的笑声、 妇女的歌声、 老人的班卓琴声不绝于耳, 毒辣的阳光下, 每家每户的菜园仍然郁郁葱葱, 五彩缤纷。 这种安全和亲切的感觉有些夸张, 但它的滋味却是真实的, 人们在这片自然条件恶劣的土地上, 还是顽强地生活。 他难以相信自己曾经那么痛恨这个地方……如今, 它看起来既清新又古老, 既能给人安全感, 又需要人劳心费力去对付。”[3]122洛特斯社区其实一直不乏大爱互助, 社区居民救助外乡黑人少年, 帮助他免遭白人毒手就是社区友爱互助的力证。 黑人社区的大人为了生活日夜操劳, 言语行为粗鲁, 对家中孩子疏于照顾和沟通, 而年幼的弗兰克也无法透过大人疲惫的身影去理解他们内心的热情和善意。 当“受创者处于安全环境中, 拥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和恰当的倾听者”[5]87时, 他才能开始重新审视创伤经历, 并迈出了重建正常生活秩序的第一步。 在南方, 友善的黑人社区、 美丽的家园、 茜的陪伴、 安稳的家, 弗兰克在洛特斯获得安全感, 逐渐走出心理阴霾, 关注内心蛰伏良久的述说冲动。
“每个幸存者的内心都有讲述故事、 理解创伤的欲望, 唯有理解埋藏在内心的真相, 幸存者才能获得新生。”[7]65人们遭遇创伤以后, 会在心理上产生很重的负担, 为了让别人能够理解这种创伤, 往往构建一种叙事, 即故事, 并把它讲述出来。[8]79弗兰克渴望诉说, 然而他的内心极度矛盾, 诉说真相的渴望, 难以启齿的羞耻感令他备受煎熬。 朝鲜战场成为弗兰克心中永远的痛, 不仅是因为儿时玩伴和战友的死亡, 更是由于在朝鲜他开枪打死了一个和茜年纪相仿的女孩。 弗兰克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肩负重任、 锄强扶弱、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可是面对这个与妹妹年纪相仿的小女孩, 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施暴者。 在暴力事件中, 并非受害者才会罹患创伤, 有时候施暴者也会备受煎熬。 作为施暴者的事实彻底颠覆了弗兰克的自我认同, 碾压了他的男子气概, 要克服罪恶感, 重新接纳自我, 并非易事。 莫里森运用多声部和叙述主体的交替, 巧妙展示弗兰克诉说施暴经历的心理抗争。 小说第一次枪杀朝鲜女孩, 是弗兰克作为叙述者描述了在战场目睹的暴行:“那个美国大兵一枪打爆了她的头。 我想他是感受到了诱惑, 那才是他正在想杀死的东西。”[3]96第二次由故事叙述者讲述:“在此之前, 他(弗兰克)曾目睹过一次惨死, ……那个孩子被大兵一枪轰飞了脑袋。”[3]100第三次则是由弗兰克以第一人称向叙述者诉说自己的罪行:“打爆朝鲜女孩脑袋的是我。”[3]139叙述人称的变化隐喻弗兰克对自己的接纳, 通过叙述, 承认施暴事实, 他接受了自己, 并开始与过去告别。
诉说创伤经历、 直面创伤真相是治疗的必由之路, 幸存者必须遵循由讲述、 理解、 恢复的治疗过程。 “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一个人治愈了创伤, 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 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 享有美好未来。[5]57弗兰克在诉说真相后, 走出了回忆创伤的阴影, 开始了新的人生。 言说创伤未必是要对着现实中的他人诉说才能够达到效果, 莫里森在过往的作品中通过多种方式让受创者言说、 发声。 例如《宠儿》中, 莫里森通过作者的口吻, 以冷静的语调描述了母亲塞丝杀婴的动机; 在《慈悲》中, 佛罗伦丝将心上人铁匠作为倾诉对象, 在鬼屋的墙壁上书写创伤。 无论是口头言说、 还是书面言说; 无论是对着真实对象还是假想对象, 言说都为受创者提供了倾诉的渠道, 让受创者回忆追思过去, 重新面向未来。
3 马场埋骨: 回归生活正轨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 3K党暴行肆虐美国南方, 许多黑人被驱逐出家园或虐杀。 幼年的茜和弗兰克曾经在洛特斯马场边目睹3K党徒掩埋一个被谋杀的外乡黑人, 这一幕成了他和茜的童年梦魇。 “看到那只粉红色脚底布满泥土的黑脚被他们敲进墓穴, 她(茜)整个人开始颤抖。 我(弗兰克)抱紧她的肩膀, 想把她的战栗吸进我自己的骨头。”[3]3回归故里后, 弗兰克依然牵挂当年这位外乡黑人的故事。 经多方打听, 弗兰克获悉: 这位黑人和儿子被3K党徒绑架到洛特斯, 并被迫参与“斗狗”活动。 父亲选择牺牲自己, 死在儿子刀下, 后者在洛特斯黑人社区居民帮助下, 逃出生天; 父亲则被草草掩埋在马场边。 此时距离美国废除奴隶制已有半个世纪, 但是黑人的人权依然没有保障, 3K党徒针对少数裔美国人, 尤其是黑人的暴行屡见不鲜。 美国黑人作为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仍然是镜花水月, 人们不禁要思考, 饱受民族创伤的黑人族裔如何面对过去, 走向未来?
在随后安葬黑人骸骨的场景中, 莫里森不惜笔墨, 运用大量与美国黑人历史和非洲文化息息相关的符号隐喻, 包括百纳被、 月桂树、 垂直墓冢、 河流和阻特装, 表明了黑人治愈创伤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黑人集体力量。 百纳被是由不同布匹边角料缝制而成、 图案精美的被子。 作为黑人妇女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手工艺品, 百纳被的制作过程通常是由家庭和社区中的黑人女性协作完成, 因此百纳被象征了黑人族裔的集体力量, 是公认的非洲黑人文化坐标。 在《家》中, 洛特斯社区黑人妇女在茜康复后向她传授了百纳被制作手艺; 而弗兰克则用茜缝制的第一条百纳被包裹被谋杀的黑人骸骨, 并在一棵被劈开呈V字型的月桂树下挖了一个垂直的墓冢, 将骸骨以站立的姿势埋葬。 月桂树在西方文化中具有胜利和荣誉的隐喻。 月桂树树干被劈开, 树冠也被削去, 但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象征黑人族裔面对迫害百折不挠的精神。 骸骨以站立的姿势入殓也表明黑人的不屈。 在结束安葬后, 茜恍惚间看到河边一位身着阻特装的矮个子黑人男子。 河流在美国黑人故乡西非具有重要的地位, 当地人认为神灵依河畔居住[8]45, 由此可知, 茜看到的黑人男子可能是被谋杀的黑人的灵魂, 他身着象征黑人反叛精神的阻特装, 表明了黑人族裔反抗种族迫害的决心。
埋葬骸骨场景对于弗兰克意义非凡, 即追忆过去, 了解缘由, 告别梦魇, 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见证创伤经历有助于创伤受害者获得自我感及世界观, 有助于他们融入群体, 并重新确立对自我极为重要的联系。”[3]72
4 结 语
莫里森曾在访谈录中曾说:“南方是什么, 黑人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即使现在也令人困惑, 作为作家, 我对此并非总是很清楚。”[9]171在《家》中, 弗兰克对南方的感情五味杂陈, 这个童年的地狱却在成年后成了他和妹妹的庇护天堂。 广大黑人成为种族主义受创者, 无论是受伤个体还是集体, 为了存活下来, 必须寻找治疗方法。 治疗过程对于亲身感受过创伤的人来说极具挑战性, 个人的力量极其微薄, 受创者需要在群体协助下, 才能治疗创伤。 黑人社区是广大黑人受创者建立安全感、 追忆过去、 言说创伤、 最终回归新生活的力量来源。
莫里森曾在2016年跟中国学者的访谈中, 就美国黑人的未来出路做出过总结。 她认为黑人唯有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 才能实现生存价值, 找回尊严和自我。[10]3而价值观包括黑人传统文化和黑人社区的集体主义精神。 莫里森认为黑人群体不应该远离南方, 盲目投入喧嚣的北方大都市, 否则会迷失自我。 洛特斯代表了黑人民族文化之根, 虽然这里并未给予弗兰克美好幸福的童年回忆, 但是在遭遇创伤后, 只有回归南方, 依靠黑人社区力量, 才能得到治愈。 黑人女性承担着种族文化传承重任, 应当抵制白人种族主义和物质主义侵蚀, 守护黑人家庭精神家园。 莫里森为弗兰克安排了一个完美结局, 表明了她对黑人社区的乐观。 同时, 莫里森也透过弗兰克在战争中作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承受的内疚和创伤, 表达了她的反战观点。
[1] 陶家俊. 耶鲁派大屠杀创伤研究论析[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4): 124-131.
[2] 李伟. 未治愈的创伤——解读《达洛卫夫人》中的创伤书写[J]. 外国文学, 2014(1): 134-139.
[3] [美]托尼·莫里森. 家[M]. 刘昱含,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
[4] Herman J. A Scholar’s Tales: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a Displaced Child of Europe[M]. New York: Fordham UP, 2007.
[5] Herman J.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6]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颜凡博. 从创伤理论角度解析《第五宰场》中的主人公形象塑造 [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0(1): 78-82.
[8] 曾梅. 俄亥俄河畔的非洲水神——非洲传统文化在小说《秀拉》中的反映. [J]. 山东外语教学, 1999(1): 42-46.
[9] 王玉括. 对非裔美国文学、 历史与文化的反思——评《莫里森访谈录》[J]. 外国文学研究, 2009(2): 169-172.
[10] 焦小婷. 文化的情调——托妮·莫里森访谈录 [J]. 外国语文, 2016(4): 1-4.
Experience,SpeechandReturn——TheTraumaWritinginToniMorrison’sHome
ZHANZuoqiong
(Dept. of Applied Language,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Home and trauma are two important themes of Toni Morrison’s novels. InHome, American Black people experience rejection, segregation and trauma while migrating from the South to the industrial cities in the North in search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protagonists Frank and Cee go through trauma, speaking about trauma and returning to normal life. Black community in the South of the United States saves the desperate brother and sister by providing shelter, treatment and guiding. Black community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healing black trauma and preserving black national culture.
Home; war trauma; black community; Toni Morrison
1673-1646(2017)05-0097-05
2017-03-26
詹作琼(1980-), 女, 副教授, 硕士, 从事专业: 英美文学。
I172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5.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