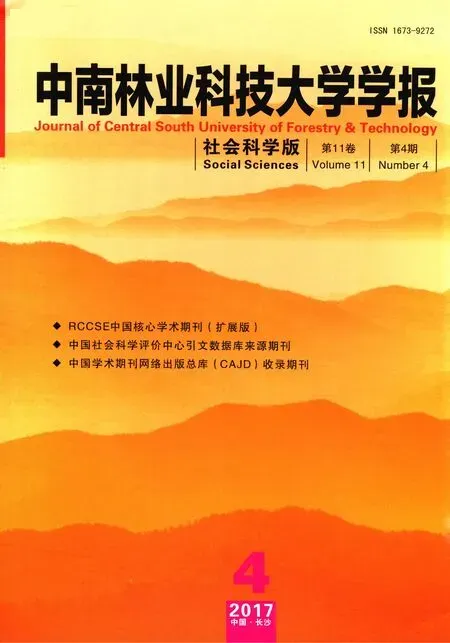“候鸟人”对长寿乡“迁徙”造成的生态伦理困境及对策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2017-01-10潘才宝
潘才宝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候鸟人”对长寿乡“迁徙”造成的生态伦理困境及对策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潘才宝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随着当代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的繁荣,人们对身心和谐的追求逐渐显著,欣赏自然,回归自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长寿乡作为延益生命奇迹的地方,吸引了大量“候鸟人”的迁徙,伴随着这种“迁徙”浪潮的不断高涨与当地居民的非理性的狂热,打破了当地原有的生态平衡。因此,从生态伦理学视阈下研究长寿乡居民长寿的秘诀以及“候鸟人”的“迁徙”造成当地的生态伦理的困境,并针对这一困境提出一些参考性对策。
“候鸟人”,长寿乡,生态伦理困境,对策
长寿乡因当地人的长寿人数多、寿星寿命长而扬名,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来这里度假、观光、养生。而这些游客就这么一个显目的集体即“候鸟人”群体。“所谓的‘候鸟人’就是为了谋取求生或居住的舒适性,效仿候鸟,进行季节性迁移的人群。”[1]他们会随着季节的推移而规律性迁徙到长寿乡来住上3个月到6个月。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下文简称巴马)列为世界第五大长寿之乡,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喀斯特地貌,夏无酷暑,冬无寒冷、降雨丰富。如此的地形气候造就了茂密的植被,空气中的小径粒负离子含量极高,因此形成了“天然的氧吧”。此外还具有古老神秘的长寿文化,古朴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巴马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与神秘的长寿文化吸引了大批来自国内外的“候鸟人”前来观光、养生、度假,这就无形中为当地面临着生态伦理困境埋下了伏笔。
一、生态和谐的内涵以及生态和谐对当地人的影响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类从上帝那里拿回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和本质力量,唯科技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了极点,一切有助于征服自然界行为都当做正义的,理所当然的。此时人类对自然界的进军正是“凯歌高奏,捷报频传”中,但却忽视了自然界会对人类进行报复。恩格斯曾经就警示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的胜利,期初确实都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和再往后就完全不同了……”[2]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就是在这种理性的狂妄下所产生的。在此背景下生态失衡就成为了人们尤为关注的焦点。生态和谐这一主题也就应运而兴,生态和谐广义上多个学科的母命题,它交叉生命科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心理学,生态美学,文化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内涵。但狭义上生态和谐主要是指生态伦理关系平衡即人与自然界的道德关系的平衡。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并不是仅仅意味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人——社会——自然的三维结构,换言之就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同人与自然三对矛盾错综运动的表达。人与社会的关系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折射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它们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在内容上渗透,在功能上互补。”[3]生态和谐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和谐。生态和谐的特征是“生态系统中的平衡与稳定、协调与统一、有机与有序、自由与自然。”[4]
只要从生态伦理学视角细心考察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个长寿乡之所以能延益人类的生命,秘诀在于他们一直遵循这生态和谐这一原则,保持天地人三材之间的平衡,而人类生命的长寿恰恰是对生态和谐的表征。接下来本文以巴马为例,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他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这三个维度分析,进一步揭示生态和谐对当地人的寿命影响。
(一)天人之和
这里的“天”属于一种狭义意义上的说法,特指自然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巴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温和的气候,丰富的降雨,适宜的阳光,神奇的土壤等条件造就了巴马产生“天然氧吧”的茂密植被,对人体有益矿物泉水,含量极高小径粒负氧离子的空气,对人体有利的磁场等。但这些都只是延益生命的“硬件”,如果当地人缺乏“天人之和”的共生和谐理念,这种延益人寿命的优良“硬件”就会被破坏掉。当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万物为一,是巴马人的生存原则。他们尊重自然的一草一树,试图“天人合一”,共生共存,倾听大自然的心跳,把大自然融入自己的生命里。巴马人民在长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劳作中就产生了这么一句谚语“人的生命来源于土,土生人,土养人。”他们感激上苍给予他们土地、山川,河流、植被等,所以对土地、一草一木都带有浓厚的爱护情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尊重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巴马人民的长寿正是表征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能延益人们的寿命。
(二)人际之和
人际关系的和睦也是巴马人民长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马克思在科学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社会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他们人群之间的感情离合。而巴马人生而淳朴好客,温和大方,在巴马聚居的有汉、壮、瑶等12个民族,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民族风情,不同的饮食习惯,但他们之间却能做到不同而和,共生相处。种族与种族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族内以及家庭之间都能以诚相待,极少出现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山歌在广西境内是极为普遍的艺术形式,在巴马也是极为受人们的欢迎,他们喜欢通过唱山歌来排解内心中的苦闷、焦躁,当然他们也经常用山歌来化解人际之间矛盾,一些年轻人还经常用山歌来表达对异性的爱慕之情。巴马人由于自身的生性温和而产生这种和睦的人际交往纽带,对巴马人长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三)身心兼修
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不仅仅只是自然性的存在,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巴马人的长寿现象除了自然性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条件之外,精神上的安宁(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也是巴马人长寿的一个重要条件。董仲舒对身心和谐能延长人的寿命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仁者之所以多寿,外无贪而内心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而养其身。”《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这样的论述在巴马人的生活中却是真实的存在。巴马地形地貌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由于地形地势的因素,大部分的族群居住之地都偏远隔绝的山区,主食主要以水稻、玉米为主食,以蔬菜和薯类为辅食,这种长期艰苦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的物欲追求,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形成了他们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洒脱性情。在巴马很多地区常说这样的一句谚语“命带八百,不求一千。”它要表达的正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样的一种豁达的知足常乐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巴马人消极出世,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相反,这恰恰是巴马百岁寿星洞察世间的人生哲学——在现实与理想中寻求的一种“中庸”平衡点,不做脱离实际的幻想,节制贪欲,坚守内心平和。除此之外,宗教的精神寄托对于巴马人来说也是心灵安放之处的一个重要场所。走访于巴马母亲河——盘阳河沿岸的村落就会发现,特别是壮族的村落,他们存在着对大榕树、“命河”、“长寿山”等景观的信仰,并认为自己生命是这些神灵与土地所赋予的,所以要对它们进行敬仰与爱护。这种朴素的宗教信仰不仅仅满足了他们内心的精神需求,同时也凸显了他们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伦理观。还有一些“补寿粮”“添寿棺”等习俗对巴马长寿星们也有一种心灵上的安抚作用,使他们保持心境平和。
二、“候鸟人”的“迁徙”而造成长寿乡的生态失衡
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各个元素平稳与有序性的统一,它们各部分、各元素之间的相依相生、相亲相和,走向共生的有机整体。但随着“候鸟人”“迁徙”到长寿乡,这种生态平衡关系逐渐被打破,它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失衡。这些“候鸟人”以中老年人为主,突出群体为养生者、癌症患者以及一些暂时来长寿乡居住的游客。“巴马的旅游起步于2006年,短短的十年间,旅游发展风生水起,游客人数从11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373万人次,入境人数3.4万人次,创造了广西旅游发展史上的‘巴马现象’。”[5]从来巴马十年来旅游的人次数据分析,由此可见由于数量庞大的“候鸟人”进入长寿乡,虽然催生当地经济一定程度上的繁荣,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众多人口的涌入无时不考量着当地的生态承载能力,随之而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破坏等问题,这种生态的失衡就变得异常的凸显。走进巴马便会发现劈山凿地、填沟造陆等景象随处可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长寿疗养院、度假山庄、养生馆、农家乐餐馆、休闲客栈的兴建,如同雨后的春笋从宁静的土地上破土而出,现代的钢筋水泥住房取代了往日的栏杆式木房。从近年来巴马环境质量分析,巴马的空气和盘阳河的水也开始变质,当地居民为了迎合“候鸟人”的市场需求,盘阳河岸很多村落开始兴建许多疗养院、休闲宾馆、酒店客栈等,村落的范围不断扩大、钢筋水泥建筑不断增多,加剧了生态链条“腐蚀”程度。在人口的不断膨胀与利益的驱使下,温室种植蔬菜与化肥、农药的使用也不断增多,随意向河流排放生活污水和乱丢垃圾也变得习以为常。巴马镇的“坡月村委书记黄大尚说:巴马‘候鸟人’大增之后,污水处理设施未配套一些污水直接排入河中,场面惊心触目,这两年的河水变得浑浊很多”[6],当地人原有那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逐渐弱化之后,使之空气质量与水源质量都大幅度降低了。长寿乡的当地人这种无节制的开发与扩张破坏了原本使人长寿的“硬件”,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割裂之后,那么“长寿乡”也就变成一个徒有其名的躯壳,延年益寿也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候鸟人”“迁徙”进当地不仅仅打破原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新一代长寿乡的年轻人,这让他们的人际关系与身心关系和他们老一辈相比,存在着极大的区别,金钱至上与消费主义被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信奉为“真理”。在当地各种休养场所、宾馆、酒楼兴建和“候鸟人”的涌入的背景下,打破了原来村落与村落、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那种淳朴的、和睦的人际交往,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竞争关系,有些地区、村落还出现了像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圈地运动”,为了争夺土地而在地区村落间发生矛盾变成常有的事情。同时,在互联网进入长寿乡的村落家庭,家庭与家庭,亲人与亲人之间的言语交流变成短信或微信上冰冷的文字交流,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生疏,那种淳朴人际交往被物与物的交往所掩盖,当所有含情脉脉的人际交往被抽象为冰冷的物物交换时,这种“物化”或者“异化”现象使现代长寿乡的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缺失,这种现象导致人们情感交流上的脱节,在此以往下去,长寿乡也会“折寿”。
心灵上的安宁也是长寿乡获得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心灵上的安宁表现在知足性情与朴素的宗教信仰上。巴马地区大部分的长寿星们都有朴素宗教信仰,他们崇敬土地与自然的山川河流,这种敬仰能使他们心神安宁。可在“现代社会,任何完全封闭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文化始终处于不断传播、交流、渗透的相互影响之中。”[7]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上看,“候鸟人”的“迁徙”所带进来的文化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带来冲击,打破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物质相对匮乏的长寿乡,很多当地人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他们开始去接受和迎合“候鸟人”所带来的文化,这样新旧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另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当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的越多,他们对原有的传统文化的宗教感情就越淡,无神论思想在他们的脑海中逐渐生根,传统宗教在心灵上的慰藉作用也逐渐淡化,导致那种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上所形成敬畏天地、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面临着消逝的困境,如此的困境不仅打破原有的身心安宁,还会产生向自然界无限索取的理性狂妄。
当长寿乡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之后,那么长寿乡的长寿现象也会随之消失。重建生态和谐就成了守护长寿乡长寿现象关键任务。
三、重建长寿乡生态和谐的对策
巴马作为长寿乡世界五大长寿乡之一,位广西的西北部,属于喀斯特地貌,在这种山多土少的地区,一旦脆弱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恢复的周期是极为漫长的,这些实际情况不得不使人们重新审视长寿乡所面临的生态伦理困境而寻求可持续的发展道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就明确强调“中国将遵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8]通过上文分析“候鸟人”的“迁徙”造成长寿乡生态伦理困境,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切入思考,对重建长寿乡的生态和谐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树立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培养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意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候鸟人”对生命延益的渴求日益强烈,这样的诉求使他们来到长寿乡现实自己的长寿梦本无可厚非,但绝不能以破坏当地生态平衡为代价。长寿乡当地人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转换那种向自然界无限索取的传统发展逻辑,遵循生态系统平衡规律,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突出生态、养生、休闲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寻求两者的“中庸之道”协同推进。同时,不管是“候鸟人”还是当地居民都要培养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意识,树立“巴马是我家,和谐靠大家”的家园情感。“有些追求养生、长寿的‘候鸟人’为了达到自我养生、治病的目的……充当起破坏着环境的角色,到盘阳河去泡澡、泡脚导致当地人不敢直接饮用而不得不另寻水源。”[9]长寿乡巴马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候鸟人”家园情感的缺失,而这种“家园情感”的主要体现为个体中“小我”与集体中“大我”之间关系中。所以树立“家园情感”的生态意识首先就必须先厘清“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生命个体的“小我”是集体“大我”具体展现,集体的“大我”则是寓于“小我”之中,这两者不是压抑或分离的关系,而是“小我”与“大我”在生生不息中融合与统一。只有这种融合才能使“候鸟人”由外出“家园”的感觉转变为“在家”的体验。从那种狭隘的眼界中解放出来,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长寿乡即是“候鸟人”的“家园”,如此他们便无法忍受“家园”的河流变得浑浊,无法忍受“家园”的天空变得灰暗,更无法忍受“家园”变成满目疮痍面貌。当地居民或者“候鸟人”只有这样广阔的视角和长远的眼光去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培养生态和谐意识,才能在长寿乡的生态平衡中实现自我养生、长寿的目的。
(二)发挥当地政府管理作用,强化对生态治理的宏观决策
政府的决策在生态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在做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时应以生态伦理准则和生态伦理规范为指导思想,把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候鸟人”“迁徙”到长寿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食品加工等商家的进入,政府部门在对企业进行审核批报时不能因为其刺激当地经济的繁荣而一路绿灯,要充分考虑企业的生态破坏程度当地环境生态承载能力,杜绝不合格商家对土地与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定期对相应商家进行检测,规范其运营方向,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原则上发展当地公共事业。“绿色发展方式需要借助制度载体才能方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10]所以政府相关部门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与地方法规,对每个村落的当地居民、“候鸟人”、酒店宾馆进行有序的管理和调配,并分析当地环境人口承载力,有必要时要采取相应措施,对“候鸟人”入境人次进行限制,把数量调控在当地村落生态承载的能力范围之内;对随意向河流排放生活污水和乱倒垃圾的也要进行相应的处罚,做到可测、可控、可调、可罚“四位一体”,使当地生态系统能在规章法规保护下平稳运转。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当地管理者还应积极发挥科技优势,不断优化生活生产的产业结构和模式,调整产业布局,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气废水以及白色垃圾的排放,把科技效益转变为环境效益,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系统等公共设施,加快公共服务的发展,推进人与自然之间协同发展。
(三)重构长寿乡传统的民族文化,由文化和谐走向生态和谐
长寿乡以人的长寿现象而扬名于世,而外来的“候鸟人”只是看到了长寿乡的“硬件”——水、空气、磁场、阳光等条件,却没有看到长寿乡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文化作用正是以人际关系与身心关系表现出来。当外来“候鸟人”带着现代的文化进入长寿乡,冲击了原有祥和、宁静的传统文化。“就连百岁寿星也开始做这样的选择——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宁可折寿几年甚至十几年也要出去旅游一次,也不愿意在这里多活几年。”[11]多数的“候鸟人”带着养生、休闲的目来到长寿乡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却没有领会当地居民长寿的另一个秘诀——生活的本质——人际关系的融洽与身心的平和。如果只是一味的享受自然的馈赠追求,必然会使由人与文化的分裂走向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在这种冲击下,重构天地人三材之间的平衡的传统文化成为了长寿乡由文化和谐走向生态和谐的必由之路,重构这种文化生态首先要做就是政府要为这些文化提供生存的空间与载体,出台一些地方法规去保护当地的民族风情(民族节日、民族服饰、民族习俗、民族传说以及民族宗教信仰等),并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加大力度去宣传当地的民族文化,增强当地人民对传统文化归属感和自信心,再者以食品、服饰、手工艺术品等载体把长寿乡传统特色文化元素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把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伦理观渗透到“候鸟人”的思想里。同时,“候鸟人”的“迁徙”也使长寿乡的建筑风格不断趋于现代化,加上“农村缺乏发展规划或者规划没有从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出发,传统建筑文化得不到保护和传承,样式单一雷同,地域特色正逐步消失。”[12]长寿乡的古建筑是在特定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反映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态建筑理念以及审美情趣。那么挖掘长寿乡的历史建筑遗迹,修复地域风格的建筑就成为了重建当地文化生态和谐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这个修复过程中要秉着“继承传统,生态创新”的原则,吸收当地建筑中优秀的文化元素,结合现代工艺与材料,把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文明元素、生态和谐理念有机结合于修复的建筑之上,这不仅仅有利于重构巴马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引导和协调着当地人与“候鸟人”文化冲突,由文化和谐走向生态和谐。思想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发心动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只有重建具有具有生态理念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态,才能有效的引导人们由文化和谐走向生态和谐。
[1]周 凯,等.候鸟人群体社会管理模式——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宜春学院学报,2012,35(11):49-5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3]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2.
[4]袁鼎生.生态和谐论[J]广西社会科学.2007(2):40-45.
[5]韦 婕.巴马瑶族自治县旅游概况[DBOL].http://news.hc wang.cn/news/20161116/news2373138876.html 2016-11-16.
[6]水蓝天.候鸟人与长寿乡[J].绿色中国,2013(19):48-50.
[7]王朝元,陈 静.全球语境下黑衣壮族群文化发展及其认同[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3(2):44-48.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211.
[9]范子军.巴马尴尬警示养生必须先养环境[N].中国绿色时报,2014-2-13(A03).
[10]宋 刚.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1):7-9
[11]兰世兵.巴马盘阳河及其沿岸村落生态和谐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5:34.
[12]何丽芳.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传统生态文化继承与发展[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4):11-14.
The “migration” of “Migratory people” to Longevity Township Caused Ecological Ethical Dilemma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Group in Bama Yao Autonomous County
PAN Caiba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conomy and material prosperity,the pursuit of the harmony of body and mind will be gradually remarkable.Appreciating the nature,returning to nature is more and more favorable for the people.Longevity township,as a place of extending the miracle of life,attracts a large number of “migratory people”migration,accompanied by the “migratory people” wave of rising with the irrational fanaticism of local residents,to break the local original ecological balance.Based on the case of China’s rural ecological longevity Bama,for exam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under the Bama and “migratory people” the secret of longevity “migration”caused the plight of the local ecological ethics,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referenc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dilemma.
“migratory people”; longevity-township; the local ecological ethics dilemma; countermeasures
F205
A
1673-9272(2017)04-0006-05
10.14067/j.cnki.1673-9272.2017.04.002 http://qks.csuft.edu.cn
2017-06-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教农业生态伦理思想研究”(16XZJ020)。
潘才宝,硕士研究生;E-mail:530525328@qq.com。
潘才宝.“候鸟人”对长寿乡“迁徙”造成的生态伦理困境及对策——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4):6-10.
[本文编校:罗 列]